趙燕菁:“土地財政”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基礎
【文/趙燕菁】
改革就是一系列選擇。但哪個選擇真正改變了歷史,當時並不一定清楚。“土地財政”就是如此。從誕生到形成,它並沒有一項完整的設計。甚至“土地財政”這一概念,也是後來才提出來的。但正是這個來路不清、沒人負責甚至沒有嚴格定義的“土地財政”,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中國城市的面貌,甚至成為全球經濟成功與問題的根源。
“土地財政”這個術語帶來了理解上的誤區。我們後面會講到兩階段增長模型,根據這一模型,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在第一階段本質上是“金融”,只有完成招商引資後獲得持續性税收才來到第二階段成為“財政”。
“土地財政”這一模式是否可持續?是改進,還是必須全盤放棄?此乃十分重大的抉擇。但由於“土地財政”被“房價”“腐敗”“泡沫”等敏感的社會話題所綁架,摒棄“土地財政”幾乎成為學術界和輿論界一邊倒的共識。本應客觀、專業的學術討論,演變成了指責“土地財政”的競賽。
好的“學術”,不在於告訴人們眾所周知的“常識”,而在於能解釋眾所不解的“反常”。“土地財政”之所以抗風而立、批而不倒,就在於有着不為學術界所知的內在邏輯。本章試圖以“信用”為主線,重新評價“土地財政”的功過,思考完全拋棄“土地財政”可能帶來的風險,探討改進“土地財政”的可行路徑。
“土地財政”之“功”
信用:城市化的催化劑
城市出現了幾千年,有興有衰,為何到了近代卻突然出現了不可逆轉的“城市化”?絕大多數研究都認為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結果。這一表面化的解釋妨礙了我們對城市化深層次原因的認識。
城市的特徵,就是能提供農村所沒有的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是城市土地價值的唯一來源。城市不動產的價值,説到底,就是其所處區位公共服務的投影。無論城牆還是道路,或是引水工程,公共服務都需要大規模的一次性投資(fixed cost)。在傳統經濟中,一次性投資的獲得主要是通過過去剩餘的積累。這就極大地限制了大型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基礎設施巨大的一次性投資,成為制約城市發展的主要障礙。
突破性的進步,來自近代信用體系的創新。通過信用制度,未來收益可以貼現到當前,使資本的形成方式得以擺脱對過去積累的依賴,轉向預期收益。信用制度為大規模、長週期的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可能。
現代理論傾向於用技術進步解釋經濟增長。事實上,研發活動伴隨人類歷史數千年,但只有在信用制度出現後才獨立出來,成為一種關鍵的因素,這説明沒有信用制度和原始資本,技術創新不過是一次又一次的曇花一現,研發更不可能成為一種獨立存在的生產方式。
其實,如果把基礎設施也視作一種產品,城市化本身就可以看作工業化的一部分——用工業的方法生產基礎設施。這也部分地回答了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什麼在公元前3世紀到15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把人類自然知識運用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為什麼現代科學……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發展起來,而不是在中國或亞洲其他任何地方得到發展?”
正是由於現代金融和技術創新同時為工業化與城市化提供了原始資本,兩者才得以相繼啓動。因此,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共生關係,而非因果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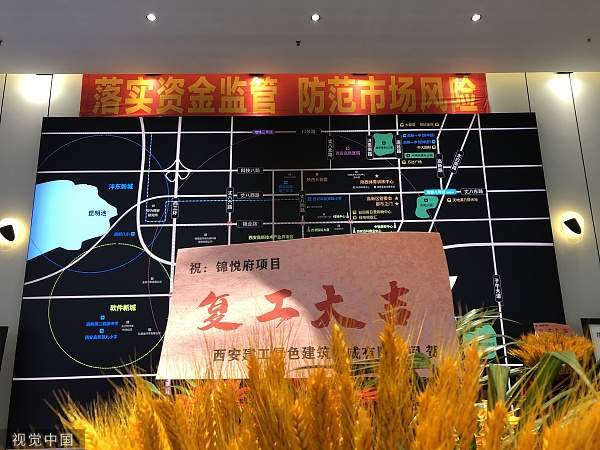
西安:樓盤爛尾九年 復工後開發商稱不能按照原價出售。圖源:視覺中國
只有資本才能為資本做抵押。
信用制度的關鍵是如何獲得“初始信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啓動,都必須跨越原始資本的臨界門檻。一旦原始資本(基礎設施)積累完成,就會帶來持續性税收。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資,自我循環,加速積累。
城市化模式的選擇,説到底就是資本積累模式的選擇。不同的原始資本積累模式,決定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歷史表明,完全靠內部積累很難跨越最低的原始資本門檻。強行積累,則可能引發大規模社會動亂。例如,秦朝投資長城、馳道、阿房宮,隋朝投資大運河、東都(洛陽),都觸發了全國性的動盪。
因此,早期資本主義的原始資本積累,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掠奪完成的。幾乎每個發達國家,都可以追溯其城市化早期階段的“原罪”。
傳統中國社會關係是典型的差序格局,民間信用在很大程度上侷限於熟人社會,因此只能是小規模和短週期的。“差序格局”一詞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費先生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格局,如同水面上泛開的漣漪一般,由自己延伸開去,信任程度逐層遞減。
近代中國的大門被打開後,中國不僅沒有完成自身的原始資本積累,反而成為列強積累原始資本的來源地。1949年後,中國重獲完整的税收主權,但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依靠掠奪實現原始資本積累的外部環境已不復存在。中國選擇了計劃經濟模式(趙燕菁,1999,2000)。
所謂“計劃經濟”,本質上是通過自我輸血,強行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的一種模式。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被分為農業和工業兩大類,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不斷將農業部門的積累轉移到工業部門。依靠這種辦法,中國建立起初步的工業基礎,卻再也沒有力量完成城市化的積累。超強的積累窒息了中國經濟,使生產和消費無法實現有效的循環。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在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二十幾之間。
從歷史上看,春秋末期中國的人口總數為3200萬人,城市人口為509萬人,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15.9%;北宋城市化率為20.1%,南宋城市化率為22.4%。梁庚堯估算,“南宋大部分城市人口比例可能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四之間”。吳松弟的估算數字為12%左右。而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僅為17.9%,基本處於同一數量級。
中國城市化的“最初的信用”
中國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始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當時,依靠農業部門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積累的模式已難以為繼。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仿效香港,嘗試通過出讓城市土地使用權,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
1986年,深圳改變了原有的無償劃撥模式,逐步形成了國有土地流轉市場。1987年12月1日,深圳首次公開拍賣了一個面積為8588m2的地塊,敲響了1949年以來國有土地拍賣的“第一槌”。第二年,憲法修正案在第10條中加入“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城市土地使用權的流轉獲得了憲法依據(張千帆,2012)。 從此,深圳開創了一條以土地為信用基礎,積累城市化原始資本的獨特道路。這就是後來廣受詬病的“土地財政”。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極大地壓縮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卻將當時規模還很小的土地收入劃給了地方政府,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財政”的制度基礎。
隨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城市股票上市”)和2003年土地招拍掛(即招標、拍賣、掛牌由賣方決定市場)等一系列制度創新,“土地財政”不斷完善。税收分成大減的地方政府不僅沒有衰落,反而迅速暴富。急劇膨脹的“土地財政”幫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原始資本。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逐步還清欠賬,甚至還有部分超前(高鐵、機場、行政中心)。
成百上千的城市,日新月異地崛起。無論是城市化速度還是城市化規模,都超過了改革之初最大膽的想象。從人類歷史的角度觀察,這樣的高速增長,只能用驚歎來描述。
的確,沒有“土地財政”,今天中國經濟的很多問題不會出現,但同樣,也不會有今天中國城市的高速發展。中國城市化偉大成就背後的重要原因,就是創造性地發展出一套將土地作為信用基礎的制度——“土地財政”。可以説,沒有這一偉大的制度創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句空話。
為何中國能走這條路?這是因為計劃經濟所建立的城市土地國有化和農村土地集體化為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創造了條件。1956年,三大改造運動開始,政府通過贖買收購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擁有的土地所有權,並通過人民公社化運動將農民個人土地轉變為集體土地。
這形成了國有為主、集體與私有土地並存的格局,城市超過90%的土地為國家所有。1975年憲法第5條正式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羣眾集體所有制。1982年憲法第10條重申: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
“土地財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場機制,將這筆隱匿的財富轉化為啓動中國城市化的巨大資本(朱雲漢,2012)。
改革開放前後的政策,看似相互對立,實則前後連貫。“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於2012年9月28日在題為《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的講座中指出:
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在這龐大的集體資產中,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30年快速發展的資本。其他很多國家沒有走這條歷史道路,就很難有這個歷史條件。這是前人留給後來政府的一筆鉅額財富。
美國的“土地財政”
“土地財政”並非中國專利。
從美國建國至1862年的近百年間,美國聯邦政府依靠的也是“土地財政”。同土地私有化的舊大陸不同,殖民者幾乎無償地從原住民手中奪得大片土地。當時,聯邦法律規定,創始13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州的境內土地,都由聯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配。公共土地收入和關税,構成了聯邦收入最主要的部分。土地出售收入佔聯邦政府收入的比重最高達到48%。
關於美國“土地財政”的規模,學界有不同的觀點。王克強、劉紅梅、張璇認為“早期美國的土地財政收入佔總財政收入的比重較高,達到了60%多,後來呈現緩慢下降的態勢。進入21世紀,美國的土地財政收入佔總財政收入的比重為30%不到,並且變化不大”,整理1820年7月至1842年9月聯邦政府土地拍賣收入情況後得出結論:政府總計收到95351萬美元,佔整個聯邦總收入的11%,其中1835年的土地拍賣收入超過當年關税收入。
對比中國“土地財政”,就可以想象當年美國的“土地財政”規模有多大:即使按10%計算,考慮到聯邦政府以贈予形式注入市場的土地,這也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比如,聯邦政府規定新州必須將其境內1/36的公共土地用於學校建設和其他小額贈予。對每個鎮的學校土地捐贈起初為81公頃,到1850年加利福尼亞州加入聯邦時擴展為162公頃。
聯邦政府還對各州建立州立大學和農業院校有專門的土地贈予規定。聯邦政府對道路、運河、鐵路,疏浚和提升航運水道,以及灌溉項目的贈予,是其土地捐贈中的最大支出項。通常,一條鐵路建設的全部原始成本可以通過銷售土地來彌補,有些鐵路通過銷售土地幾乎可收回其全部支出(駱祖春,趙奉軍,2012)。而中國的土地收入看似較高,但其中近40%是徵地拆遷的成本。
2012年,中國國税收入為11萬億元,48%就相當於5萬億元,而2012年“土地財政”收入實際不到27萬億元。中國的“土地財政”,即便從20世紀90年代初算起,也不過近30年。而美國從建國伊始,直到1862年《宅地法》(Home Stead Act)規定土地免費轉讓給新移民,前後持續近百年。1862年後,聯邦政府的“土地財政”才逐漸被地方政府的財產税所代替。
直到今天,聯邦政府仍是美國絕對的“頭號地主”。聯邦政府擁有的土地面積高達263億公頃,約佔全部國土面積的30%。聯邦政府擁有82%的內華達州、68%的阿拉斯加州、64%的猶他州、63%的愛達荷州、61%的加利福尼亞州以及將近一半的懷俄明州和俄勒岡州。這些聯邦土地不僅由聯邦政府全權管理,而且也因其聯邦所有權而享受徵税豁免權。
在國有土地方面能和美國一比的是加拿大。據統計,加拿大41%的土地為聯邦所有,48%為各省所有;兩者相加,高達89%的土地是屬於政府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僅剩下11%為私人所有。
有人或許認為中央政府的土地收益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不能混為一談。但在筆者看來,“土地財政”的本質,就是將土地收益用於公共服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差異,僅僅是提供的公共產品種類不同(比如前者可能是自來水,後者可能是國防)。除此之外,沒有本質差異。
“土地財政”的本質是融資而非收益
在土地私有的條件下,公共服務的任何改進,都要先以不動產升值的方式轉移給土地所有者。政府需要通過税收體系,才能將這些外溢的收益收回。税收財政的效率幾乎完全依賴於與納税人的博弈。制度損耗帶來的利益漏失極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條件下,公共服務的任何改進,都會外溢到國有土地上。政府無須經由曲折的税收,就可以直接從土地升值中收回公共服務帶來的好處。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聯邦政府的“土地財政”與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不完全相同。這還不僅是因為“初始地權”的獲得不同(美國靠的是對北美印第安人的屠殺和掠奪,中國則是通過計劃經濟的制度設計);還因為美國早期土地所有者是聯邦政府,所出售的土地並非附帶公共服務的城市土地,因而也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資本——直到1862年《宅地法》頒佈,土地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結合並帶來持續性税收,不動產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資本。
而在中國,土地一開始就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結合在一起,政府收入被用來改善公共服務。這使得土地不斷升值,併成為極佳的投資品。
相對於“徵税”的方式,通過“所出售土地的升值”來回收公共服務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於城市政府不僅可以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甚至還可以以補貼的方式為能夠帶來持續性税收的項目融資。
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這一獨特製度,使土地成為中國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斷增值的信用來源。不同於西方國家抵押税收發行市政債券的做法,中國土地收入的本質,就是通過出售土地未來的增值(70年),為城市公共服務的一次性投資融資。
中國城市政府出售土地的本質,就是直接銷售未來的公共服務。如果把城市政府視作一個企業,那麼西方國家城市是通過發行債券來融資,中國城市則是通過發行“城市股票”來融資。

房企融資迎來“第三支箭” 證監會調整優化5項措施。圖源:視覺中國
因此,在中國,居民購買城市的不動產,相當於購買城市的“股票”。這就是中國城市的積累效率遠高於土地私有化國家的重要原因。也正是依靠這一做法,中國得以一舉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兩個進程的原始資本積累。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住宅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為中國住宅的本質就是資本品,除了居住,還可以分紅——不僅可分享現在公共服務帶來的租值,還可以分享未來新增服務帶來的租值!當然,居住和分紅從流動性等金融性質方面來看並不完全相同,但就融資功能而言,本質是一樣的。
因此,中國的房價和外國的房價是很不同的兩個概念——前者本身就附帶公共服務,後者則需另外購買公共服務。
在這個意義上,“土地財政”這個概念存在根本性的誤導——土地收入是融資收入(股票),而不是財政收入(税收)。在城市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上,土地收益屬於“負債”,税收則屬於“收益”。“土地金融”或許是一個比“土地財政”更接近土地收益本質的描述。
對“土地財政”的認識,有助於解釋困惑經濟學家的一個“反常”——為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而股票市場卻長期低迷不振?如果你把不同城市的房價視作該“城市公司”的股價,你就會發現中國“城市公司”股票市場的增長速度和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十分一致,一點也不反常,並通過免交財產税的方式分紅。
由於土地市場的融資效率遠高於股票市場,因此,很多產業都會藉助地方政府招商,以類似搭售(tie-in sale)的方式變相通過土地市場融資。中國大量企業是在土地市場而不是在股票或債券市場完成融資的。例如,很多初始投資高、回報週期長的產業,往往要搭配一些“商業”或“住宅”作為平衡用地。更多的是政府拍賣項目周邊的土地,然後用獲得的收入對企業進行補貼。
“土地財政”相對税收財政的效率差異,雖然很難直接觀察,但我們仍然可以通過一些數據間接比較。
近年來,中國M2持續高速增長,但並未引發經濟學家所預期的超級通貨膨脹。通過抵押或直接出讓“平衡用地”,是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和招商引資的主要手段。這也間接反駁了那些認為“土地財政”抑制了實體經濟的指責。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M2的規模是有實際需求支撐的。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做法,就是拿M2和GDP做比較。2012年,M2餘額為9742萬億元,GDP約51萬億元,M2與GDP的比值達190%。有人認為,M2與GDP的比值逐年高企,説明資金效率和金融機構的效率較低。更有人擔心通貨膨脹迴歸和房價反彈。
但實踐表明,M2和GDP並不存在嚴格的對應關係。1996年是個分水嶺。從這一年開始,在中國M2超過了GDP,但此後卻長期保持低通貨膨脹,甚至局部時期還出現通貨緊縮。而改革開放後幾次大的通貨膨脹都出現在此之前。這是因為,合意的貨幣發行規模,取決於貨幣背後的信用而非GDP本身。如果説税收財政信用與GDP存在正相關關係,“土地財政”提供的信用與GDP的這種相關性就可能相較於同樣GDP的税收財政成倍放大。
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曾經以黃金為“錨”的世界大部分貨幣處於“漂流”狀態。美元通過與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掛鈎,重新找到了“錨”,使得美元可以通過大宗商品漲價,消化貨幣超髮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歐元試圖以碳交易為基準,為歐元找到“錨”,但迄今仍未成功。日元則基本上以美元為“錨”,它必須不斷大規模囤積美元,其貨幣超發,只能依靠美元升值消化。
而“土地財政”卻給了人民幣一個“錨”。土地成為貨幣基準,為中國的貨幣自主提供了基石。2013年,美聯儲宣佈要逐步退出“量化寬鬆”,新興市場國家立刻出現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匯率波動,而人民幣的匯率卻屹立不動。
這説明人民幣已脱離美元來定價,找到自己內生的“錨”。這個“錨”就是不動產:不動產升值,貨幣發行應隨之上升,否則就會出現通貨緊縮;貨幣增加,而不動產貶值,則必然出現通貨膨脹。也就是説,貨幣超發須藉由不動產升值來吸收,否則,過剩的流動性就會導致通貨膨脹。
日本面臨通貨緊縮時,安倍經濟學企圖通過日元貶值走出通縮,在筆者看來,這不過是日本貨幣戰爭的障眼法,其目的是用貨幣貶值對沖高負債率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一旦美國要求日元升值,超發的貨幣就會氾濫。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雖然沒有使GDP增加,卻使“城市股票”得以正式“上市流通”,全社會的信用需求急速擴大。同日本一樣,囤積的大量美元是人民幣信用的另一個來源。美元升值,人民幣就可以多發。如果人民幣貶值,不動產就必須升值,否則,就會導致通貨膨脹。
因此,在美元貶值的背景下,打壓房價,就是打壓人民幣。房價下跌,必定導致通貨膨脹,其後果可能遠比我們大多數人想象的巨大、複雜。之所以沒有發生通貨膨脹,乃是因為房價上升導致全社會信用規模膨脹的速度比貨幣更快。
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基礎
西方國家經濟崛起的歷史表明,效率較低的税收財政無法完全滿足城市化啓動階段對原始資本的需求。為避開國內政治壓力,外部殖民擴張、侵略便成為大多數發達國家快速完成資本積累的捷徑。貨幣作為一種“流量”,它對應的是整個經濟規模。GDP只是經濟規模的一個斷面,而沒有考慮不同發展“速度”通過信用制度貼現過來的“體積”差異。簡單地將GDP與貨幣掛鈎必然會出現極大的誤差。
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模式出現之前的西方模式必然帶來擴張和征服,新崛起的國家一定會和已經崛起的國家發生碰撞和衝突。如果不能從發展模式上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僅僅靠反覆聲稱和平願望,很難使其他國家相信中國的崛起會是一個例外。
有人認為,全球化時代的跨國貿易和投資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選擇非武力征服的外部積累模式。儘管這一理論來自西方國家,但它們自己並不真的相信這一點,否則就無法解釋它們為何仍然處心積慮地對中國的投資和貿易進行圍堵。的確,二戰後,一些孤立經濟體在特殊的政治條件下,依靠國際貿易和投資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也可以複製這樣的發展模式。
清末和民國時期的開放歷史表明,市場開放對交易雙方的好處並不像“比較優勢”理論認為的那樣是無條件的。國際投資和貿易既可幫助中國企業在全球“攻城略地”,也方便了國際資本的經濟殖民,利弊得失依賴雙方的資本實力——全球化只對競爭力較強的一方有利。
為何發達國家經濟長期作為更有競爭力的一方?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憑藉完善的“税收—金融”體制可以以很高的效率融資,從而獲得全球競爭優勢。因此,通常條件下,最賣力推動全球化的,往往也是資本最雄厚的國家。
但中國的“土地財政”打破了這一規則,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內,創造了一種比西方國家更有效率的融資模式。中國產品風靡全球,中國則出人意料地成為可與西方國家比肩的資本強國。
反傾銷歷來是發達國家對付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工具,現在卻被用來對付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以前從來都是城市化發展快的國家出現資本短缺,完成城市化的國家出現資本剩餘,現在卻反過來了,是中國向發達國家輸出資本。在這些“反經濟常識”的現象背後,實際上都有賴於“土地財政”融資模式的超高效率。
中國之所以能“和平崛起”,原因恰恰離不開“土地財政”這種融資模式,這使得中國不必藉由外部征服,就可以獲得原始資本積累所必需的“初始信用”。高效率的資本生成,緩解了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的信用飢渴,確保了中國經濟成為開放的和在全球化中獲利的一方。
因此,即使處於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化初始階段,中國也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希望維持現有國際經濟秩序,更有動力推動經濟全球化。“土地財政”的成功,確保了“和平崛起”成為中國模式的內置選項。
【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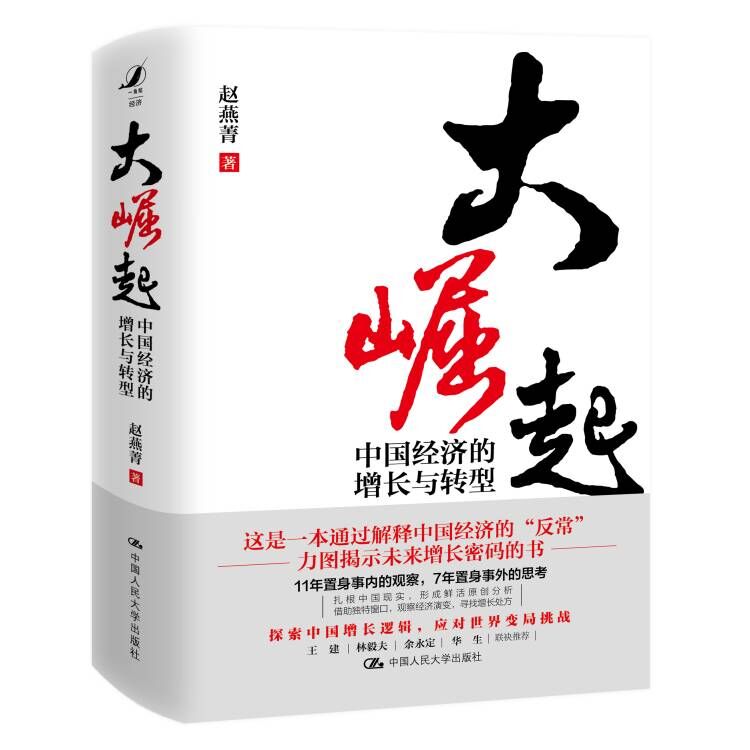
《大崛起:中國經濟的增長與轉型》。作者:趙燕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