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濤:強勢美元週期或接近尾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怎麼走?
(採訪/觀察者網 周遠方,整理/觀察者網實習生 孫甜甜、楊珈媛)
11月以來,美元指數明顯回落,Wind數據顯示,11月美元指數已從11月1日的111.56點跌至12月1日的104.7,11月美元指數累計跌幅超5%。近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公開講話中釋放美聯儲可能放緩加息步伐的信號。
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2022金融街論壇年會上指出,主要發達國家經濟衰退風險上升,通脹仍高於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將總體維持緊縮,美元短期仍可能高位震盪,市場機構預測美元升值動能減弱、強升值週期或已接近尾聲。
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隨之強勢反彈,12月2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數據顯示,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7.0542,較上一交易日上調683個基點,創2022年11月16日以來新高。當天,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開盤拉昇近250點,在岸、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均逼近7.0大關口。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在近日接受觀察者網等媒體採訪時認為,在本輪美元強勢中,中國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為我們保持匯率和經濟的相對穩定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2015年“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發生了一定變化,但這一進程總體上還在有序推進。從各方面指標來看,目前的美元在全球權重偏高,遠超過其在全球經濟、貿易中的份額,尤其是各國對於美元為中心的跨境結算依賴太大、美元濫用及美元的武器化正在影響各國安全,人民幣及其背後的支付清算系統也就是CIPS,能夠獨立於現在美國和SWIFT體系,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
管濤同時指出,對於中國來講比較現實的選擇是人民幣國際化儘可能地按照市場驅動、企業自主選擇的原則,相關部門不斷健全制度環境、基礎設施,為人民幣的跨境流通創造好的條件,使人民幣逐步從全球外圍貨幣爬升到次中心貨幣的地位。

2019年10月,易綱與鮑威爾在IMF和世界銀行財長和行長年會上合影
以下是採訪實錄:
觀察者網:人民幣本輪走弱伴隨美聯儲加息和美元走強,全球大多數貨幣是一起走弱的,但人民幣也表現出一定的特殊性,有一段時間是同美元一起走強的。美聯儲近期加息勢頭出現放緩,人民幣也出現兩次較大的反彈。
能否請您簡單描述一下美元、人民幣和其他一籃子貨幣之間的關係?客觀説,人民幣處於怎樣一個位置?
**管濤:**首先,中國的法定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8年最新修訂的《外匯管理條例》第五章第二十七條規定:“人民幣匯率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所謂“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是一種匯率政策,但不是對匯率制度的描述。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所以它既不是盯住某種單一貨幣(比如美元),也不是盯住一籃子貨幣,所以人民幣匯率本身既不存在跟着美元同漲同跌的必然性,也不存在美元強人民幣就弱的必然性。
其次,任何時候影響匯率漲跌的因素都很多,美元的強弱對人民幣匯率始終有一定的影響,只不過在某些階段可能影響大一點,某些階段可能影響沒那麼大。比如去年美元反彈了6.7%,美元對大部分非美貨幣都漲了,但是人民幣對美元仍然升值,出現這種現象,並不是説美元強對人民幣沒有影響,而是美元走強對人民幣的影響被其他因素抵消掉了。
去年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貿易順差很大,支持了人民幣的走強。中美利差去年收斂,今年倒掛,所以中美利差由正利差轉為負利差的因素,對人民幣的影響可能今年進一步顯現。今年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疫情的多點多次反覆散發,影響了中國經濟復甦,也影響了外貿前景。在這樣的綜合情況下,美元走勢只是影響人民幣匯率因素的一個方面,在不同的時候,它的影響力大小是不一樣的。
從制度上來講,人民幣匯率還是要更多由市場決定,根本上還是要看供求關係。
觀察者網:“貨幣錨”的問題一直被熱烈討論,如果追溯到人民幣前身“邊幣”時代和新中國前三十年,能否認為當時主要錨定的是實物生產生活資料、金銀、以及人民政府和軍隊的信用?改革開放以來,也有人認為人民幣錨定美元資產,而美元的“錨”也曾發生大變化。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您認為未來人民幣的“錨”應該落在哪個/哪些地方?
**管濤:**人民幣是一種信用貨幣,所以它不像過去商品本位的時代,要錨定哪個商品或者哪一組商品。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確立中央銀行法以後,明確了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所以要建立比較嚴格的貨幣紀律,包括禁止財政向央行透支等,這確實是維護幣值穩定的一個重要方面。
如果我們建立了比較嚴格的財政貨幣紀律,保持了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穩定,將有助於增強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這既能夠增強本國投資者對人民幣的信心,也能夠增強境外對人民幣的接受和認可,利好人民幣國際化。
過去確實有一段時間,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窄幅波動,保持基本穩定,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也主要是因為外匯佔款的波動引起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民幣一定程度上錨定了美元。
但是,在當時來講,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錨定美元,建立起了中國的貨幣紀律。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間,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通脹壓力比較大。而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反通脹後,經歷了比較長的物價穩定時期。所以我們通過錨定美元,也就是借用了美元的信用來降低通脹。
過去,我們是通過“央行再貸款”渠道來進行基礎貨幣投放,後來轉向通過外匯佔款渠道來吞吐基礎貨幣,不是説沒有問題。但是,在剛開始,我們用外匯儲備作為錨定的資產來吞吐基礎貨幣,這種方式相比完全的信用投放更容易建立起貨幣紀律。這在當時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未來人民幣肯定不會再次錨定某種實物資產,不論是某種商品還是一籃子商品。但是,建立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我們要儘可能長時間地保持貨幣政策處於正常狀態,就需要完善的貨幣調控機制和傳導機制,致力於保持物價穩定、金融穩定和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從根本上來講,這應該有助於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1994年後的一段時間,我們曾經藉助美元建立起自己的貨幣紀律,而美元的“錨”也曾發生大變化,美聯儲的政策好像執行的也不是很好,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您認為未來人民幣的“錨”應該落在哪個/哪些地方?
**管濤:**1992年南方談話以後,中國出現了經濟過熱的情況,當時的零售物價指數達到了20%,1994年匯率並軌初期,我們仍面臨高通脹的問題。之後三四年時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中趨升,就是借用了美元信用來建立我們的貨幣紀律,通過外匯佔款渠道來投放基礎貨幣,而不是通過“再貸款”的完全信用投放方式。這在當時來講,有一定積極的含義。
當然,在這方面我們既有經驗,也有教訓。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美聯儲採取了零利率+量化寬鬆的非常規貨幣政策。那段時間,人民幣匯率政策相對比較僵化,靈活性不夠,用增加外匯儲備的方式阻止人民幣匯率過快升值,導致了輸入型的流動性過剩。在2015年“811匯改”,特別是2019年8月份人民幣“破七”之後,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提高,靈活性增加,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為我們堅持“以我為主”的貨幣政策創造了條件。
特別明顯的是,在2020年這一波公共衞生危機的衝擊下,我國的貨幣政策不論是進還是退,都是“以我為主”,沒有跟着美聯儲的節奏走。到現在為止,我國的通脹雖然起來了一點點,但是屬於温和的通脹。目前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個別的經濟體,都出現了高通脹的迴歸,特別是美聯儲此次明顯錯判了通脹的形勢,這對美元的信用傷害比較大。反過來,也印證了我們堅持正常貨幣政策的正確性。正是因為匯率由市場決定,增加了匯率政策的靈活性,才使得我們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得到了制度保障。
觀察者網:對我們國家來説,當前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仍然存在,甚至比較嚴重,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管濤:**我們國家的通脹沒有那麼明顯。我國的PPI今年以來主要是整體單邊下行,到10月份已經轉成同比負增長了,CPI只有百分之二點幾,核心CPI一直在1%左右。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這也受惠於我們國家現在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我們採取了2009年到2013年的匯率政策,阻止匯率升值,增加外匯儲備,那麼我們國家前期也會導致輸入性的通脹和流動性過剩。恰恰是因為我們用匯率波動來應對市場變化,有效避免了外匯佔款的波動。從月度數據來看,現在外匯佔款的環比變化都很小,央行恪守匯率政策中性,基本退出了外匯市場常態的干預。
觀察者網:2015年“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出現了一定的放緩,如何客觀看待這樣的現象?
**管濤:**所謂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放緩”,可能是“8·11匯改”之後,一些政策的調整對離岸市場帶來了衝擊造成的。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人民幣存款一度從1萬億跌到了五六千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可以説人民幣國際化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
實際上,“8·11匯改”之後,人民幣國際化策略進行了調整,原來的策略是嚴格管制在岸市場,通過離岸市場來驅動人民幣的國際化;調整後,我們加快了境內股市、債市和匯市的開放,通過在岸市場驅動。因此,現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跟七年前相比,不降反升。
過去持有人民幣金融資產,只能到香港去做人民幣存款,在香港買人民幣點心債,而現在可以到在岸市場直接購買人民幣的股票和債券。根據人民銀行公佈的境外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的“四項合計”數據,最多的時候,境外持有的境內人民幣債券、股票、存款、貸款合計10萬多億,匯改之前只有三四萬億元人民幣。而且,內部結構發生了變化,過去存款和貸款佔據四分之三,現在七成以上是由股票和債券構成的。
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SDR的籃子貨幣權重進行了定值重估,把人民幣的權重提高了1.36個百分點,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出口市場份額上升,部分原因是境外持有的人民幣外匯儲備份額上升,還有全球人民幣外匯交易的份額上升。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策略發生了變化,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總體上還在有序推進。
觀察者網:我個人的理解是,現在人民幣股市或者其他資產的價格,相對全世界的水平仍處於窪地,因此它對於外資比較有吸引力。現在SDR的籃子里人民幣權重由10.92%上調至12.28%,將美元權重由41.73%上調至43.38%,同時將歐元、日元和英鎊權重分別由30.93%、8.33%和8.09%下調至29.31%、7.59%和7.44%,人民幣權重仍保持第三位。能否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力還是很大?
**管濤:**很多人拿SDR籃子貨幣的權重來衡量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力,我認為這是不對的。SDR裏有五個籃子貨幣,從全球外匯儲備的份額來看,只有美元的權重超過了它在SDR的權重,其他四種貨幣包括人民幣在內都沒有超過,所以不存在SDR佔10%以上,那麼全球持有的人民幣的外匯儲備增長均在10%以上的情況,實際數值無論低於或者高於這個數值都不奇怪。人民幣的股票債券納入全球指數後,一些被動型的基金是要跟蹤那個指數進行配置的,這跟SDR的情況是不同的。
剛才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人民幣有沒有配置價值?首先,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體,現在全球對於人民幣金融資產的配置是低配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境外持有人民幣的規模和份額上升應該有一定的空間。但是,同時也要認識到,不論是股票市場還是債券市場,我們國家跟國際上的成熟市場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至於你講到的投資價值,中國股市的市盈率跟自己比,目前處於低位,但是在國際市場上來看我們也不便宜,特別是我們金融市場的很多制度安排,跟國際市場不太一樣。所以,下一步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推動我們國家制度型對外開放,向國際的經貿規則接軌,特別是跟最高規則接軌,推動境內金融市場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觀察者網:您認為人民幣是否追求成為美元那樣的“中心貨幣”?我們追求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願景是怎樣的?
**管濤:**我覺得我們的國際貨幣改革的願景應該是多極化,要減輕對單一貨幣的過度依賴。現在的美元無論是從計價結算、價值儲藏,還是外匯交易等等各方面的指標來看,權重都是偏高的,遠超過了它在全球經濟、貿易中的份額。這樣來看,我們對單一貨幣的依賴是過重了。而且,我們現在明顯地看到,現行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着所謂的“特里芬難題”,即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難以同時兼顧對內對外均衡目標。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以國內的目標為優先,這其實沒有什麼值得質疑或譴責的。但是,我們很明顯地看到,無論是在國際計價結算還是投融資中,美元的佔比都很高,這導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不論是進還是退,它都有着強大的溢出影響,其他非美國家都深受其害。
不單是那些脆弱的新興市場受到了嚴重的衝擊,甚至一些發達經濟體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比方説歐央行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歐央行在今年年初的時候還表示,由於經濟復甦不充分,貨幣政策要持續寬鬆。但是迫於通脹的壓力,加上美元升值、歐元走弱的壓力,首次加息就是50個基點,一舉走出了實施八年之久的負利率時代。當時,在7月份議息會議之後,歐央行行長拉加德解釋首次就加息50個基點的原因時指出,歐元貶值疊加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加大了歐元區的輸入性通脹壓力是一個重要考慮。
所以,不單是新興市場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發達經濟體受害也不淺。不論匯率固定還是浮動,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均面臨貨幣政策難以完全獨立的“二元悖論”。所以,大家都想改變目前的狀況。
但是,國際貨幣體系確實存在所謂的網絡效應和路徑依賴。這就是一種寡頭壟斷。理論上,所有的貨幣都可以作為國際化貨幣。但是,如果所有的貨幣都是國際化貨幣,必然會大大增加跨境交易成本,那就沒有意義了。如果國際化貨幣最終歸為少數幾種貨幣,這些作為寡頭壟斷,大家集中使用,就會形成規模效應,然後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能某一種貨幣扮演中心貨幣的角色,發揮更主要的作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用得越多,流動性就越好,交易成本就越低。這對後起的國際化貨幣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且,美元成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貨幣,也不完全是因為其經濟實力,這是綜合國力等各方面因素影響的結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其他經濟體的綜合國力能夠達到美國那樣的程度。實際上,2015年人民幣首次加入SDR,當時10.92%的權重主要不是從美元來的,而是從歐元來的。這次重估,又是歐元損失了份額,同時不單是人民幣的權重提高了1.36個百分點,美元的權重也提高了1.65個百分點。可見,過去七年,美元的國際地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在上升。
這也沒什麼奇怪的,畢竟經濟強貨幣就強。美國在疫情之前是經歷了戰後最長的經濟景氣,而歐洲、日本是正在經歷長期經濟停滯。新冠疫情暴發之後,在全球經濟復甦過程中,是發達經濟體領先新興市場。而在發達經濟體內部,美國又是領先其他經濟體。所以,這也是沒有辦法的,經濟強貨幣就強。
觀察者網:您剛才談到多極化,然後一些貨幣組成寡頭貨幣,或者説是多極的貨幣集團,要實現去中心化,不存在一箇中心貨幣。這樣的願景是可行的嗎?是可能存在的嗎?
**管濤:**國際貨幣體系的多極化應該是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現實選擇。國際貨幣體系是分層次是,第一個層次是中心貨幣,目前只有美元;第二個層次是次中心貨幣,包括歐元、英鎊、日元、瑞郎等等;第三個層次是外圍貨幣,主要是一些不可兑換或者非國際化的貨幣。
目前,作為次中心貨幣發行體的歐洲和日本等都有自己的問題。比如,歐元區貨幣雖然統一了,但財政沒統一。如果這次稍有不慎的話,有可能歐債危機會捲土重來。屆時,歐元面臨的就不單單是漲跌的問題了,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最後有可能變成兩個歐元區。再如,英國脱歐對英鎊也帶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前一陣子英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互相矛盾就造成英鎊的崩盤。日本則是面臨長期經濟停滯。而其他的主要經濟體,不論是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還是瑞士,他們經濟體量太小了,扮演不了這個角色。
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人民幣在資本項下還沒有完全可兑換。流動性的話,除了本身金融市場要有一定深度和廣度外,還需要資本自由流動,做到資金進出自由。這方面,我們目前還沒有做出制度上的承諾。包括人民幣匯率,我們還是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儘管我們已經退出了常態干預,恪守匯率政策中性,但是我們還不敢在制度上做出自由浮動或者不干預是原則、干預是例外的承諾。所以對大家來講還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特別是我們現在的資本賬户開放,我們還是按照正面清單的方式,但實際上國際最高標準是負面清單,説明了什麼不能做,那剩下的都是可以做的。前些年易綱行長曾經説過,我們現在金融服務業開放已經是負面清單清零了,但是跟外資一瞭解,發現我們在實際操作中還是有很多行政許可,有很多障礙。
對於中國來講比較現實的選擇是人民幣國際化儘可能地按照市場驅動、企業自主選擇的原則,相關部門不斷健全制度環境、基礎設施,為人民幣的跨境流通創造好的條件。現在可行的目標是,我們要從外圍貨幣爬升到次中心貨幣。
觀察者網:您認為人民幣的數字貨幣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會發揮怎樣的作用?
**管濤:**我認為數字人民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補充,但不是替代。實際上數字貨幣原來並不是叫央行數字貨幣,不是現在説的這個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而是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我覺得關鍵在於跨境收付的支付清算系統是否能夠多元化。我們需要創造electronic payment(電子支付)的跨境,而不是digital currency(數字貨幣)的跨境。然後,央行的數字貨幣實際上是不能充分發揮貨幣的全部功能的,作為計價結算、價值尺度沒有問題,數字貨幣跟正常人民幣是等價的,央行數字貨幣的一塊錢跟銀行裏一塊錢是等值的,不會有根本的差別。
但是一旦要做到支付,還有投融資、價值儲藏,我覺得可能央行的數字貨幣在這方面的功能是有缺陷的,它是不能夠充分發揮這方面的功能的。比方説銀行做跨境業務有很重要的一個功能是KYC(KYC即“Know Your Customer”,意思是充分了解客户,對賬户持有人的強化審查,瞭解資金來源合法性)以及提供貿易融資,而中國央行的數字貨幣還做不到這些。
所以數字貨幣應該是補充而不是替代。我覺得更關鍵的是數字貨幣或許能夠提供跨境支付清算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因為現在大家對於美元為中心的跨境結算依賴太大、美元濫用及美元的武器化影響了大家的安全,這才是關鍵所在。實際上,數字貨幣背後的支付清算系統也就是CIPS,能夠獨立於現在美國和SWIFT體系,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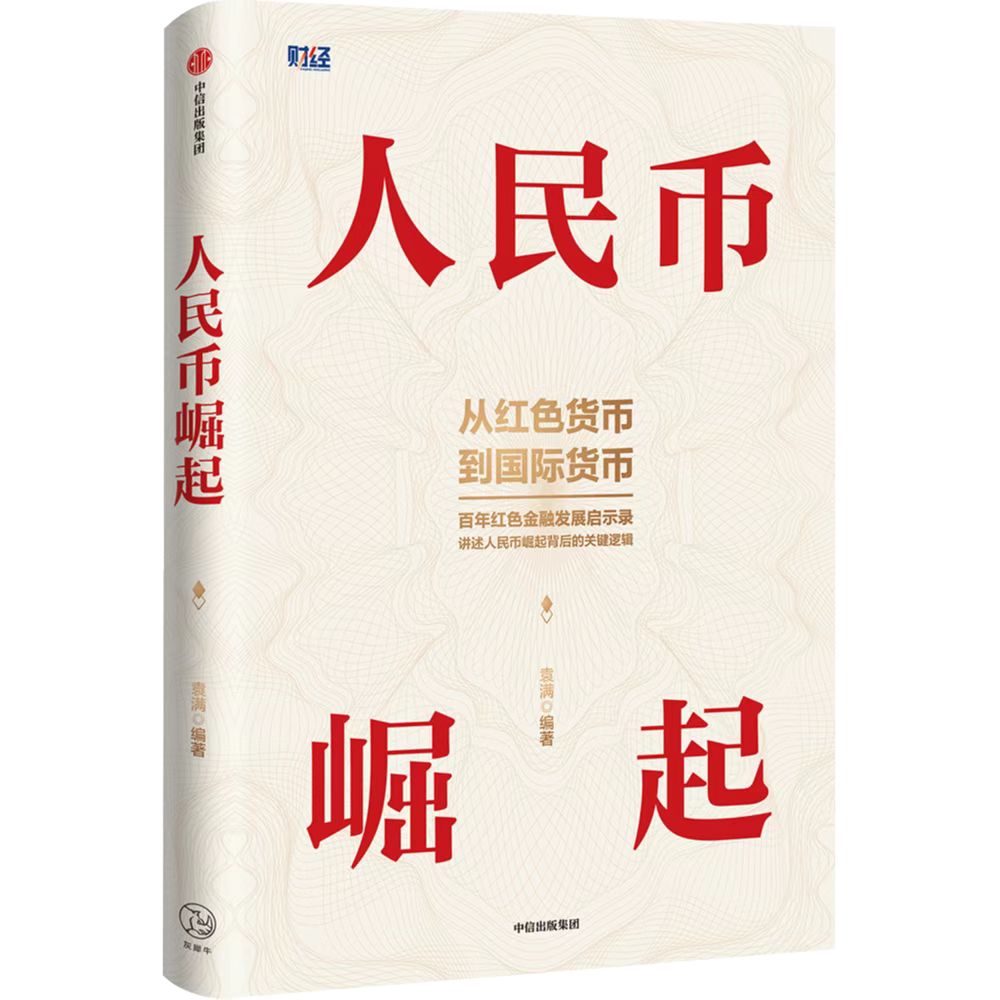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