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美國道德革命之辯
Barton Swaim
馬薩諸塞州薩默維爾市
審視21世紀美國公共生活時,很難不得出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我們正被一羣白痴領導。政治階層近來製造了一連串令人咋舌的敗績:阿富汗撤軍亂局、城市犯罪浪潮、早有預兆的通貨膨脹、南部邊境的失控、自釀的能源危機、收效甚微卻代價慘重的疫情應對。還有那些長期存在的國家恥辱:耗資驚人卻運轉失靈的福利體系、讓學生越學越笨的公立學校、培育破壞性怨憤與有害意識形態的大學、以及無人信任的新聞媒體。
讀者或許會對部分列舉提出異議,但很少有人能否認這種感受:這個國家的政府和主要機構正由一羣昏庸之輩掌管。七世紀前的歐洲也曾陷入類似困境——這是我從哈佛曆史學家詹姆斯·漢金斯2019年著作《美德政治:文藝復興意大利的靈魂塑造與治國之術》中瞭解到的。該書研究以彼特拉克(1304-1374)為首的意大利人文主義作家與政治家。漢金斯指出,14世紀人文主義的興起,源於人們對中世紀晚期意大利政教領袖腐敗無能的普遍厭惡。
人文主義者從根本上顛覆了希臘羅馬政治理論的核心命題:什麼是最佳政體?漢金斯寫道,對彼特拉克及其後繼者而言,“統治者的品德遠比憲法形式重要”。14世紀初,歐洲政治思想已退化為關於統治者合法性的狹隘法理爭辯。人文主義者認為這種爭論根本不值得嚴肅思考。他們的目標是"根除統治者靈魂中的暴政,無論統治者是一個人、少數人還是多數人"。
西方政治傳統最終將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走向以權利為基礎的憲政和法治。正如漢金斯先生所言,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發展的政治理想"美德政治"主要旨在讓善良且明智的統治者掌權;而憲政思想則主要旨在限制可能由惡劣和愚蠢的統治者造成的損害。“在這方面,人文主義者與另一位意大利文藝復興作家尼科洛·馬基雅維利(1469-1527年)截然不同。他建議採取一種不那麼有原則、更精於算計且殘酷現實的領導方式。漢金斯寫道,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喬萬尼·薄伽丘、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等人——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思考方式,相當於一種失傳的政治審慎傳統”。
我自己對古典自由主義的依戀使我對任何聲稱要賦予"善良"和"明智"的領導者權力而不首先關注其權力限制的哲學持懷疑態度。但我不得不承認:目前美國的憲政民主似乎並不太擅長限制惡劣和愚蠢的官員造成的損害。事實上,我們似乎被那些擁有馬基雅維利式狡詐但缺乏馬基雅維利式能力的統治者所淹沒。也許我們可以從美德政治中學到一些東西?
最近在拜訪漢金斯先生的家時,我詢問了美國人堅信改革社會的方式是改革法律和機構並創建新機構的信念。“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並不這麼認為,“他説。“部分原因與他們對天主教會的關係有關。“在古代晚期——大約五世紀——基督徒將文科重新設計為一套技能:語法、邏輯、修辭等。他們的想法是基督教將改變人心——教育不會做到這一點。相比之下,14世紀和15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作家與當時極其腐敗的天主教會的關係更為複雜。“你無法通過教會改革社會,“漢金斯先生解釋道。“你能做的是改善那些在城邦、王國和教會中擔任高級職位的人……你可以通過某種教育來實現這一點。這就是人文學科被髮明的原因。”
如今,“人文學科”一詞意味着從文學理論到文化研究等一系列軟性學科的混雜。對於最初的人文主義者來説,“它意味着你理解了人性向善、追求高貴——真正的高貴,而非世襲的高貴——的真正潛力。”他們希望精英學府的學生能沉浸於那些引導心靈追求高尚品格的著作中。“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充滿了高貴行為的典範,還有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他們希望男女——與(中世紀)經院哲學不同,人文主義同時面向男女——都能理解何為高貴……這些是人文學科的核心:語法、修辭、歷史、詩歌、道德哲學。為何要學歷史?因為歷史是審慎之師。”
漢金斯先生將人文主義者提出的理念稱為“政治賢能統治”。美國人通常用“賢能統治”(由英國作家邁克爾·揚在其1958年著作《賢能政治的崛起》中首創)指代由技術精湛的高成就者管理的社會。而人文主義者設想的是由最智慧、最具美德的人統治。
我們的統治階級當然自認為品德高尚。在前往漢金斯先生家的路上,我穿過薩默維爾和鄰近的劍橋,注意到許多庭院標牌用現代進步主義空洞的語言宣告着部落歸屬:“科學即真理”、“愛就是愛”、“黑人的命也是命”、“擁抱多樣性”、“賦權弱勢羣體”。漢金斯先生對鄰居們這些奇怪標語的解讀是:“他們在享受自我良心的認可,卻沒有通過道德努力以嚴肅方式訓練自己的思想。”
漢金斯先生指出,清晰而精確的語言恰恰是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綱領的核心。彼特拉克曾言,表達之明晰乃"智慧與知識的最高證明”。在人文主義者看來,賢明的統治者應當運用語言藝術説服民眾為公共利益行動。“人文主義者反對經院哲學那種通過辯論使人向善的觀點,“漢金斯表示,“他們認為需要觸動整個人——必須激發情感與慾望…以精準的語言和雄辯之才服務於崇高理想。”
若當代的彼特拉克評價美國精英會作何感想?“他們會嗤之以鼻,“漢金斯答道,“我列了份名單。每當華盛頓有人做出值得稱道之事,不為政治私利而為國家時,我就記下名字。“我早知結局如何,靜待他道出:“這份名單很短。”
部分問題在於漢金斯所稱的"科學主義”。何意?“即相信科學能解決所有問題,使人可以摒棄判斷力,拋棄希臘人稱為實踐智慧的素養——這種通過研習歷史、閲讀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等經典獲得的,關於做出明智決策的藝術。”
漢金斯認為,在防疫響應中最明顯體現了對實踐智慧的拋棄。“疫情中就明顯可見科學界對此眾説紛紜。對數據解讀存在各種分歧,但精英們卻決意屈從於那個科學。“他特別強調定冠詞,“當你説那個科學時,就暴露了問題。”
漢金斯先生的著作在美國新冠疫情暴發前一年出版,因此他雖提及但未着重探討彼特拉克在1347-49年黑死病疫情中的經歷。這位偉大的人文主義學者與幾乎所有幸存者一樣,在這場瘟疫中失去了摯友。他對意大利精英階層的消極看法是否源於此?“他傾向於將瘟疫視為上帝對時代腐敗的懲罰,但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彼特拉克對他所處時代的學問——無論是自然、法律還是醫學——都持嚴厲批判態度,認為它們傲慢、腐敗且唯利是圖。他尤其痛斥當時作為大學課程組成部分的占星術,認為其完全是場騙局。不知他對當今某些社會學科會作何評價。”
從某種角度看,正如漢金斯所闡釋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的論點既切中要害又無懈可擊。當幾乎所有人都在擔憂國會、司法部乃至總統職位等重要機構的公信力時,能聽到有人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機構正在喪失合法性,因為掌權者既無能又腐敗"確實令人耳目一新。但另一方面,顯而易見的反駁是:這種觀點對人類向善能力的認知過於天真。
漢金斯先生也承認,美國憲政秩序本質上承襲了奧古斯丁主義的世界觀——其制度設計基於對人性的悲觀認知。正如開國元勳們所設想的那樣,美國憲法默認惡劣統治者是政治生活的常態。對此,像我這樣的奧古斯丁主義者會説:解決之道應是對政治權力建立法律制衡,而非如彼特拉克等人文主義者所主張的培養更有德行的統治階級。
漢金斯先生自詡為古典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他並不認為英美憲政是政治思想的終極答案。“看看喬治·華盛頓接受的人文教育,“他説,“如果你瞭解華盛頓的成長經歷,就會發現那完全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模式——不僅要背誦道德格言,還要研讀普魯塔克著作、羅馬歷史以及那些對塑造行為規範至關重要的古典名劇。”
我試圖提出折中方案:我們當然不會迴歸以德治國的政治模式,但或許可以從人文主義傳統中汲取智慧?漢金斯先生否定了這個前提。“我不確定是否同意這個觀點。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一場道德革命,但在我看來,賢能政治是可以復興的。”
67歲的漢金斯在哈佛任教37年,談起學生時充滿感情。“年輕一代對老一輩感到厭惡,“他説,“媒體把所有注意力都給了’覺醒派’,但還有大批年輕人正期待着道德革命。”
這種思潮不僅存在於美國。他曾在中國講學交流,表示"這種變化也在中國悄然發生,正在積蓄力量。科學主義盛行。人們放棄道德判斷。我們的領導人只是遵循科學、算法和專家意見,甚至不願正視因經濟停擺而失業的人們?我們要讓祖父母在隔離中孤獨離世,只能通過iPhone與他們臨終告別?這簡直荒謬了。”
所有這些關於腐敗無能的領導人的討論讓我想起了漢金斯先生那份簡短的名單。上面都有誰?“我想到一些真正有成就的人,他們出於責任感為特朗普政府工作,明知會因此遭受磨難。比如詹姆斯·馬蒂斯、威廉·巴爾、馬克·埃斯珀、唐·麥加恩,還有其他一些人。”
關於唐納德·特朗普的話題,我們都對一些本應嚴肅的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無法用文明災難之外的語言談論這位第45任總統感到遺憾。為什麼寫了700頁關於美德政治領導力著作的漢金斯先生沒有被特朗普擊垮?因為他的職業讓他學會了從長遠的角度看問題。
“我是以歷史學家的角度思考的,”他説。“很多人沒有深入思考過生活在不同時代會是什麼樣子。他們沒有比較的意識。從歷史的長遠角度思考,你會對人類生活有更廣闊的視野。歷史是通往理智的道路。”
斯威姆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社論版撰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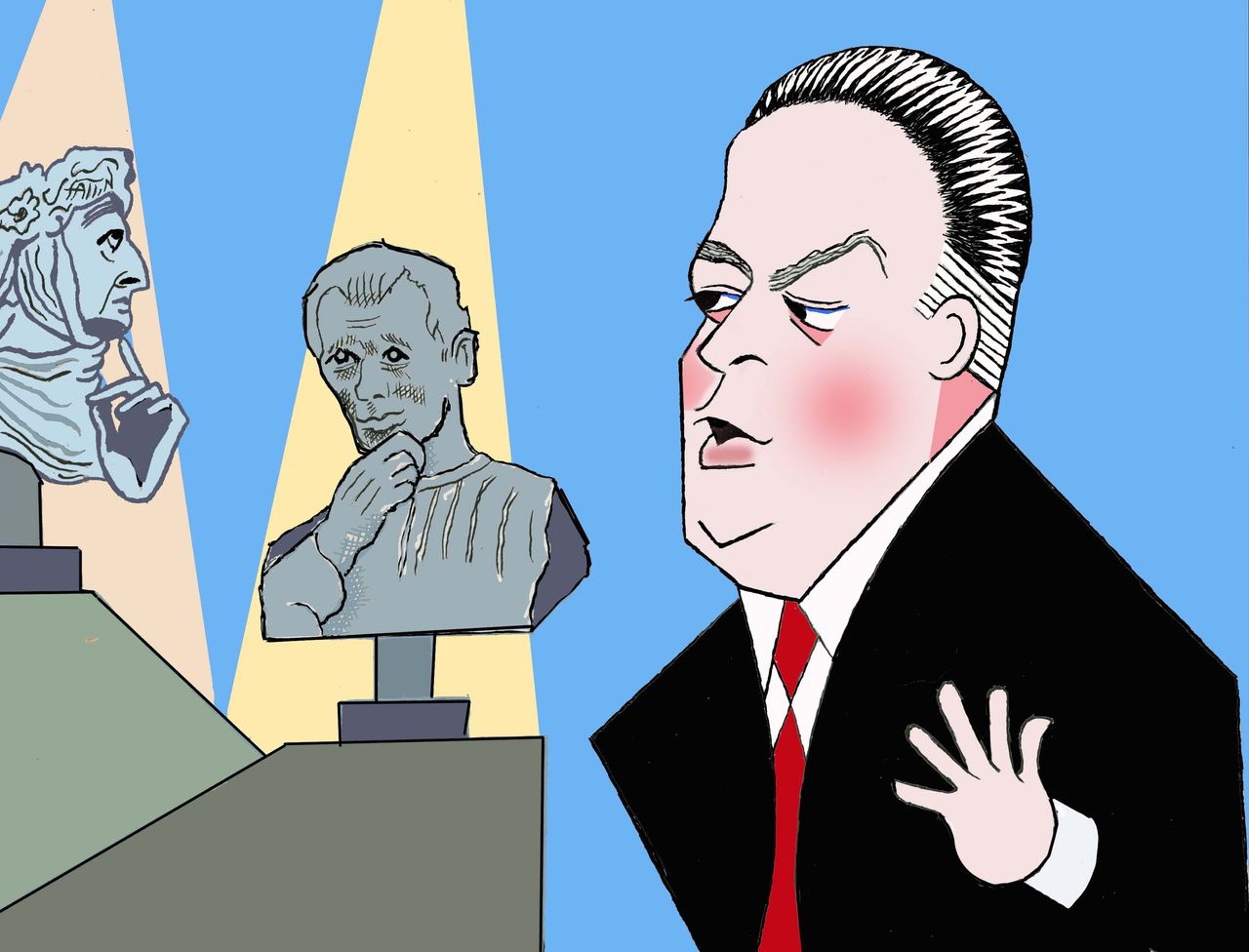 插圖:肯·法林本文發表於2022年8月20日的印刷版,標題為《美國道德革命的理由》。
插圖:肯·法林本文發表於2022年8月20日的印刷版,標題為《美國道德革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