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如何學會感恩已有之物,而非心懷愧疚
Francesca Fontana
 作者從祖母身上學到的重要一課:她的犧牲源於對家人的愛與期盼,這些付出從不計較回報或附加條件。插圖:艾比·洛辛我的祖母是個講故事的高手。經她講述,我們家族史就像電影般徐徐呈現。祖父母生於肯塔基州煤礦小鎮的貧寒之家,為謀生路遷往芝加哥這座大都市。兩人輪流倒班工作,一人白班一人夜班,在漫長工時中拉扯大兩個女兒。
作者從祖母身上學到的重要一課:她的犧牲源於對家人的愛與期盼,這些付出從不計較回報或附加條件。插圖:艾比·洛辛我的祖母是個講故事的高手。經她講述,我們家族史就像電影般徐徐呈現。祖父母生於肯塔基州煤礦小鎮的貧寒之家,為謀生路遷往芝加哥這座大都市。兩人輪流倒班工作,一人白班一人夜班,在漫長工時中拉扯大兩個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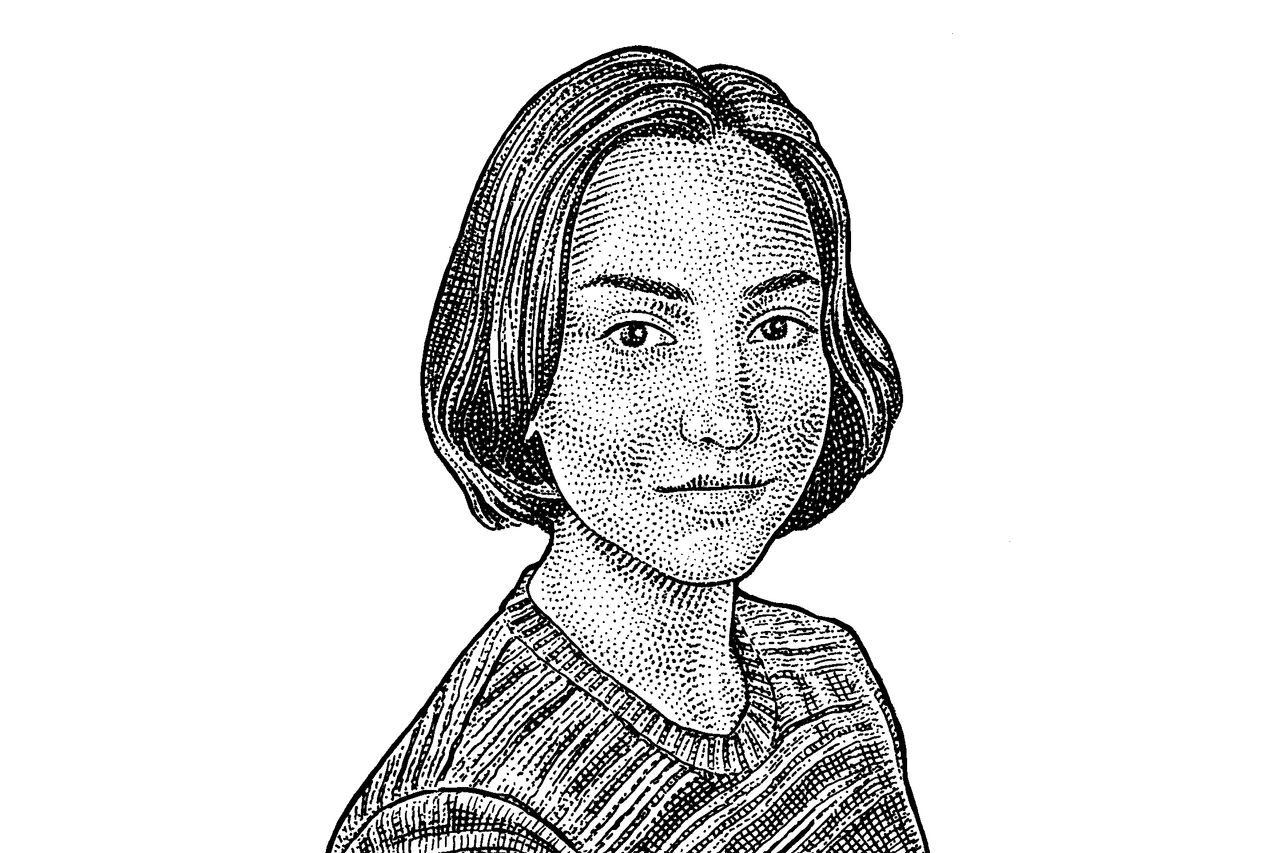 她的故事總以圓滿結局:他們突破出身桎梏,為子孫創造了更優渥的生活。我總愛聽她講述這段往事,珍視其中藴含的教誨。
她的故事總以圓滿結局:他們突破出身桎梏,為子孫創造了更優渥的生活。我總愛聽她講述這段往事,珍視其中藴含的教誨。
祖父母還傳授了其他人生課業:教我核對銀行賬單,為每個"A"成績發放零花錢(並鼓勵我儲蓄)。但我深知他們的奮鬥史尤為特別。這並非那種"上學要翻兩座山"的憶苦故事,不為強調艱辛或暗示我們這代人的安逸。我的祖母保利娜·“波莉”·赫夫曼·撒克希望我銘記家族根源,並相信這個世界充滿待我摘取的機遇。
今年初春,波莉因癌症離世。病情惡化迅猛,我趕回密歇根老家陪伴她度過最後時光。那個故事與教誨始終縈繞心頭。我始終覺得有責任回報家族——正是他們的辛勤勞作託舉了我的人生。作為家族首個大學生,我得以從事白領職業,獲得了更廣闊的財富前景。
自從畢業以來,我一直懷揣着一個近乎妄想的私人抱負,以及幾個近乎空想的目標:還清母親的房貸,或是資助弟弟完成本科學業。我想給家人一些實實在在的回報他們的付出;我想要照顧他們,讓他們分享曾給予我的一切。若做不到這些,對我而言就是失敗,既辜負了他們的犧牲,也浪費了自己的潛力。聽起來戲劇化嗎?或許吧。但這就是我真實的感受。
祖母的去世將這種愧疚感推向了極致。她即將離我們而去,而我始終無法擺脱一種感覺——我既不夠努力,積蓄也不夠多,所有想給她的回報都來得太遲。我失敗了。
非理性的愧疚
我知道這種愧疚毫無道理。悲痛與非理性總是如影隨形。
但這份愧疚也讓我頓悟:我從未意識到自己揹負着怎樣的重擔。回首往事,我發現它如何影響了我的財務生活和每個選擇。
我有一份全職帶薪工作,卻總覺得遠遠不夠。我把所有業餘時間都投入副業:轉賣衣物、出售藝術品,疫情期間還縫製口罩。我在收藏夾裏存滿零工招聘鏈接"以防萬一"。雖然個人財務還算穩定,但我總想要更多。
多年來我拒絕購買傢俱,寧願撿拾街邊的廢棄物品或在Craigslist上淘免費物件。我曾花數小時打包租車公司的貨車,把舊傢俱拖回家。直到遇見丈夫瑞恩,我才意識到這或許並非常態。他欣賞我的節儉,但鼓勵我給自己一些彈性空間。
去年,我和瑞安一起買了套公寓。但一種揮之不去的愧疚感沖淡了我的自豪與興奮。我們努力工作、抓住機遇,完成了曾認為不可能的事。可為何我仍感到不安?
「這是刻在骨子裏的」
金錢與愧疚總是如影隨形。
2021年一篇研究論文深入探討了這種現象。合著者邁克爾·奧唐納與埃倫·埃弗斯發現,消費行為受制於我們心中"錢該如何花"的信念。比如某人可能享受跨洲航班上的寬敞座位,但她認為不該為非必需品花錢——於是產生負罪感。這些自我設定的標準常與實際選擇衝突,違背時便會滋生愧疚。
我諮詢了一位靠食品券長大、後成為常春藤盟校律師的摯友。他的話令我難忘:他完全理解我的經濟負疚感。他放棄了嚮往的歷史研究生道路,選擇更賺錢的職業,只為資助兄弟姐妹上大學——這是他的責任。
“這種觀念根深蒂固,“他告訴我,“它關乎我的核心自我認知。“這也正是我的感受。
那麼,為何我會愧疚?
因為責任意識已成為我衡量所有消費的絕對標準。情感大腦的混亂神經不斷向我發出清晰信號:每筆自我消費——無論是冬衣、筆記本電腦還是公寓押金——都像在剝奪所愛之人的生存資源。可生活又迫使這些消費發生,於是我只能審判自己,任由愧疚啃噬心靈。
不理性?是的。誇張做作?或許吧。但我終於能理解了。
視角的饋贈
在波莉生命最後幾周的照料中,當我直面內心愧疚及其根源時,終於明白從來就不存在什麼虧欠。她的犧牲源於對家人的愛與期盼;這些付出並非交易,也不帶條件。我能在終點給予她的只是時間、關懷與慰藉。我珍視與她共度的那些日子。我得以與自己和解,釋懷那份債務。
我仍想在繼續財務生活時散播這份財富。為母親還清房貸的夢想不會輕易消逝。她不需要我的幫助;她經營着成功的事業。然而,我的責任感仍在。但現在,帶着視角的饋贈,我可以給自己喘息的空間。
我不再試圖讓所有空閒時間都產生收益,而是可以休息和照顧自己。我不再反覆糾結,而是能在家人來訪時享受與他們共享新家的時光。我不再翻遍克雷格列表和垃圾堆尋找免費書架,而是可以選擇一套我喜愛、負擔得起並能享受的。(我也確實這麼做了。)
當八月我們這個小家庭聚在一起安葬祖母時,我們帶走了失去帶來的尋常啓示:我們發誓要健康飲食、多打電話,更好地照顧自己和彼此。我也帶走了這一條。每當去看望她時,我都會感謝她:感謝她的愛、她的教誨和她的故事。
方塔納女士是《華爾街日報》駐紐約記者。聯繫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