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沙到烏克蘭,國際法真的重要嗎?- 彭博社
Andreas Kluth
 成比例嗎?
成比例嗎?
攝影師:Ahmad Hasaballah/Getty Images
各種派別的評論家們正在爭論如何解釋國際法。哈馬斯無疑以最嚴重的方式違反了國際法。但以色列也在這樣做嗎?這場政治性和法律性的爭議引發了一個更古老的問題:什麼是國際法,它是否真的存在?
毫無疑問,哈馬斯在10月7日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並殘忍地屠殺了大約1200人,其中大多數是平民,犯下了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行。當它劫持平民為人質時,它違反了國際法,當它開始將200萬加沙平民用作人質時,它又違反了國際法,這些行為在習慣國際法和條約國際法中都是非法的。
至於以色列,作為受害國,國際法明確賦予其自衞的“戰爭權”(jus ad bellum)。但它也規定了以色列在戰爭中必須如何作戰(jus in bello)。在這裏,法律的推理在理論上很清楚,但在實踐中卻很模糊。例如,以色列必須盡最大努力避免傷害平民,儘管合法的軍事目標可能會證明一些平民死亡是“成比例”的。加沙的死亡人數達到了11,000以上,這算是成比例嗎?
此外,國際法禁止集體懲罰。當以色列關閉整個加沙地帶的水、燃料和電力時,這是否是以色列實施的方式?以色列説不是。其他人説是,並指出以色列國防部長等人的評論,他在下令“完全封鎖加沙地帶”時,補充道“我們在與人類動物作鬥爭,我們也會相應地行動。”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曾引用申命記25:19,上帝在其中告訴以色列人“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除滅。”加沙人是今天的亞瑪力人嗎?
國際法的模稜兩可是一回事;對於誰會執行它,以及如何執行,存在的模稜兩可是另一回事。這在另一個背景下變得清晰,涉及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當他的部隊入侵主權國家烏克蘭時,他違反了國際法的基本規則。但聯合國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 因為俄羅斯在其安理會上擁有否決權。
普京的部隊隨後犯下了額外的暴行,從殘害、折磨、強姦和謀殺烏克蘭士兵和平民到綁架他們的孩子,這是種族滅絕的定義的一部分。對於後一種罪行,設在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 — 由1998年的羅馬條約建立,是國際法的一顆明珠 — 已對普京和另一位俄羅斯領導人發佈了逮捕令。
但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不是《羅馬規約》的締約方。(美國、中國或以色列也不是,儘管巴勒斯坦是。)只要普京不踏入其中任何一個123締約國,甚至在他這樣做時,他在任何合理的情況下都不會被逮捕。
像普京這樣的加害者顯然可以逍遙法外,這引發了懸掛在國際法上方的更大問題:它是否實際上是“法律”。從托馬斯·霍布斯到漢斯·莫根索,這些思想家規定,只有當法律可以被執行時,它才配得上這個標籤。而且,執法者需要像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説的合法暴力的壟斷。通常這意味着一個國家政府,可以合法地逮捕、監禁、徵用甚至殺人。
但世界上沒有相應的世界政府,因此也沒有一個擁有合法暴力壟斷的國際機構。因此,全球體系被稱為“無政府社會。”對於一些法律哲學家來説,國際法實際上不過是“積極道德”,一套容易被忽視和無法執行的規範和建議。
然而,歷代人中也有一些人認為這種分析中缺少了一些東西。在這一傳統中最偉大的思想家是雨果·格羅提烏斯,他是17世紀的荷蘭人文主義者和博學家,曾經通過躲藏在書櫃中將自己從監獄中走私出來,並倖存於一次海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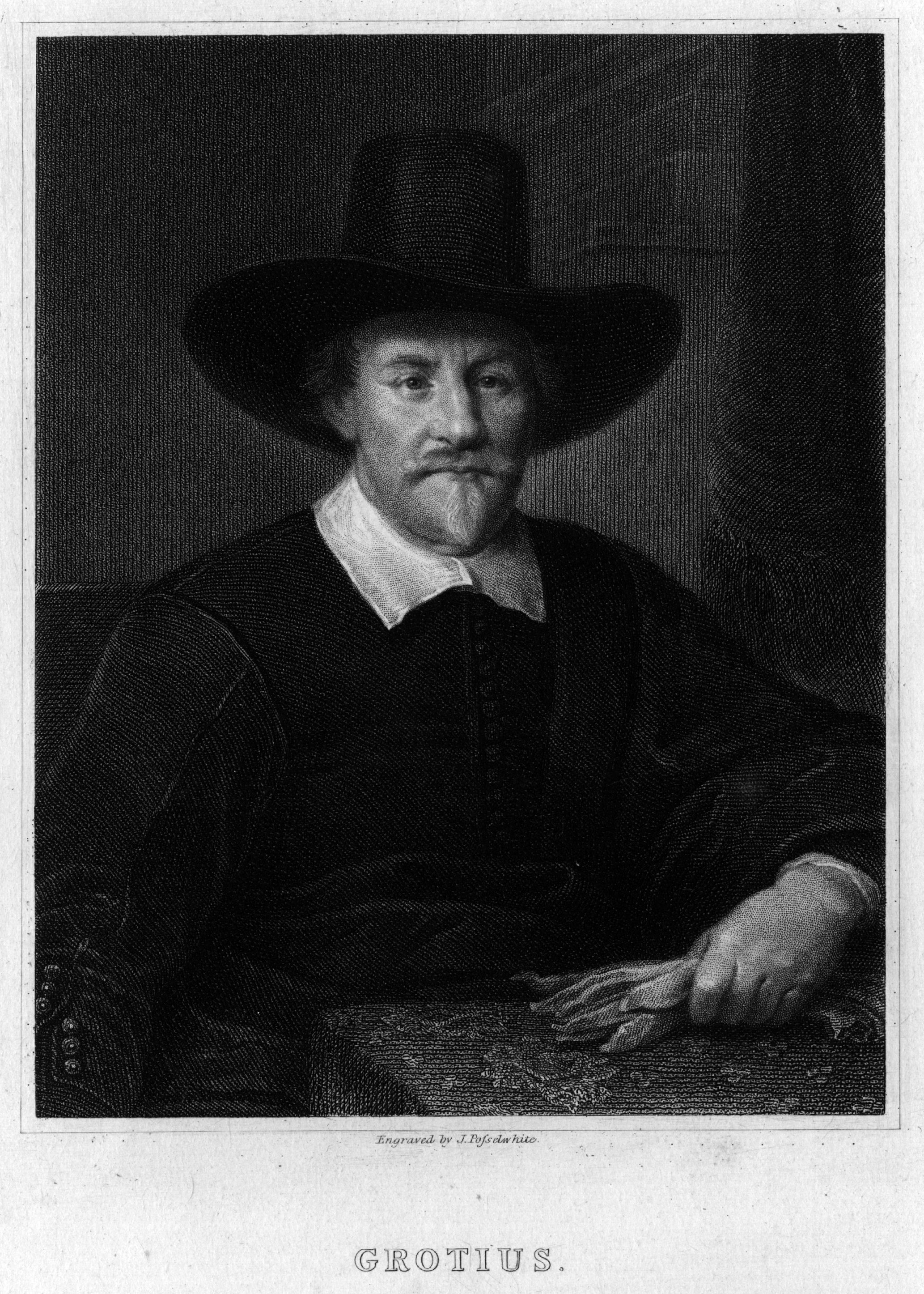 雨果·格羅提烏斯,“國際法之父。”來源:赫爾頓檔案館,由蓋蒂圖片社提供格羅提烏斯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期間,當時中歐某些地區超過60%的人口喪生。歐洲的大國以及私人軍隊進行了屠殺,沒有任何約束。作為一名知識分子 —— 後來作為瑞典駐法國大使 —— 格羅提烏斯幫助構想了現代國家體系,這一體系將從這場血腥事件中崛起。
雨果·格羅提烏斯,“國際法之父。”來源:赫爾頓檔案館,由蓋蒂圖片社提供格羅提烏斯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期間,當時中歐某些地區超過60%的人口喪生。歐洲的大國以及私人軍隊進行了屠殺,沒有任何約束。作為一名知識分子 —— 後來作為瑞典駐法國大使 —— 格羅提烏斯幫助構想了現代國家體系,這一體系將從這場血腥事件中崛起。
在此過程中,格羅提烏斯還制定了國際法的基礎文本,從規範海洋航行的規則(這些規則在聯合國《公海公約》中得以延續)到關於發動戰爭以及進行戰爭的規範 —— 也就是説,關於jus ad bellum和jus in bello。對於格羅提烏斯及其繼承者來説,國際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事物應該是這樣的。
幾個世紀以來,一套習慣國際法發展起來,基於先例,類似於普通法國家的案例法。在此基礎上,還有條約、公約和協議,相當於國家法中的法規。從19世紀開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國際紅十字會推動了特別是國際人道法(現代對jus in bello的同義詞)並幫助制定了《日內瓦公約》及其議定書。聯合國憲章以及有關貿易、勞工標準和太空探索等方面的公約完善了這一體系。
國際法無處不在,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在和平時期發揮最佳作用,當各國感到最受互惠約束時 — 只要你不在我的大陸架上鑽石油,我也不會在你的上鑽。但一旦國家或領導人感到重要利益受到威脅,尤其是一旦他們捲入戰爭,他們經常無視法律,就像普京一樣。(也就是説,他確實跳過了南非的一個峯會,而南非是《羅馬規約》的簽署國 — 也許他畢竟擔心被逮捕。)
然而,儘管不完美,國際法使許多人的生活比它本應該的更少惡劣、殘酷和短暫 — 比三十年戰爭時期 更少。它通過將戰爭的原因與方式分開來約束作戰方,正如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查理·卡彭特所説,通過區分“‘文明’暴力和徹頭徹尾的野蠻行為”。它為每個社會的温和派提供了一種語言,以便在槍聲平息後對付本國內部的嗜血者並在個人層面上追究他們的責任。它維護了人道主義的規範。
你可能傾向於霍布斯或格羅提,現實主義者或理想主義者。你可能懷疑國際法是否存在,也可能對它發誓。你可能認為它在加沙地帶失敗了,或者阻止了更嚴重的苦難。但讓我們感激國際法的存在,因為另一種選擇更糟。這已經足夠理由來捍衞它。
更多來自彭博觀點:
- 以色列-哈馬斯衝突將改變戰爭規則:蒂莫西·L·奧布萊恩
- 以色列加沙圍困面臨人民、隧道、政治:馬克·冠軍
- 以色列-哈馬斯戰爭考驗左派對“文化取消”:諾亞·費爾德曼
**想要更多彭博觀點嗎?**OPIN <GO> 。或訂閲我們的每日新聞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