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列車丨觸樂夜話_風聞
触乐-触乐官方账号-01-13 10:27
來源:觸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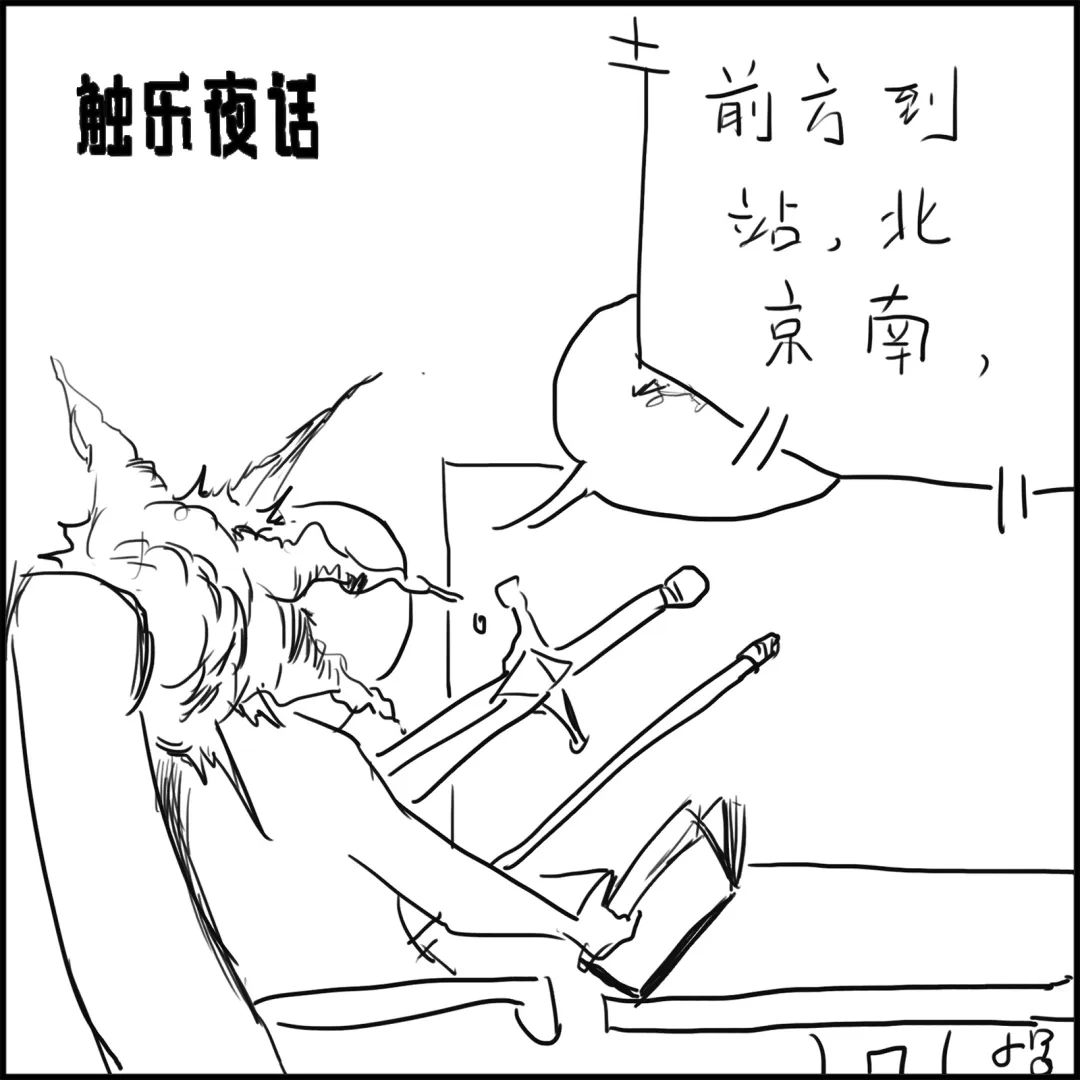
出發去下一站吧(圖/小羅)
觸樂夜話,每天胡侃和遊戲有關的屁事、鬼事、新鮮事。
因為準備到北邊過春節,週末坐動車去了一趟省會,收拾要帶走的衣服和書本。書很多——大部分是小説和筆記,在我回程的路上,那些小説就這麼堆在我面前,每本都被淚水和汗水弄得皺巴巴的,我伸出手拿過一本,隨意地翻頁。
我拿的小説叫《在切瑟爾海灘上》。這部小説以一次性事不遂為切入口,講了一對1961年剛剛完婚的夫妻無法用言語溝通,甚至不能説出最簡單的性慾,引發了許多誤解的故事。
這本小説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去年的5月份,我把它丟進書包,揹包去另外一個城市見喜歡的人,春天末尾的整整5天,我們都待在不見天日的海邊旅店中,房間小得只能放下一張牀,而昏暗不透光的窗簾下,在親吻中,我的血流在肌膚下微微跳動,上湧,像春花一樣綻放。在車上,我撫摸着書脊,人依然凝滯在那一刻,因為它甚於任何感覺,哪怕是耳後爆炸,長矛穿腹,或者靈魂折磨,儘管這些我一樣都沒感受過,那麼就甚於想到這些的時候的感受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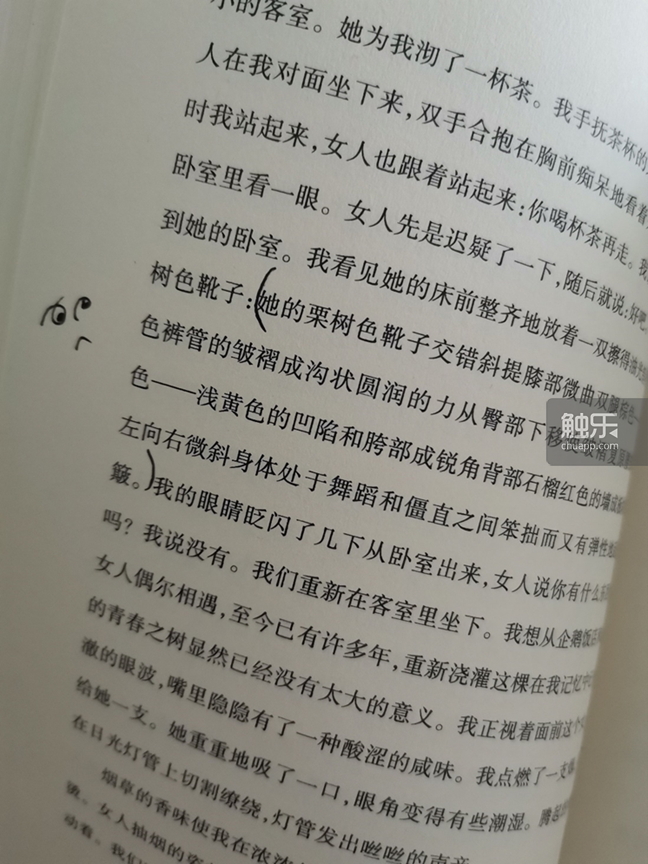
兩年前的塗鴉
一邊尋找着當時的感覺,我一邊把小説快速翻到了底頁,那兒有一道狹長的口子,口子周圍因為吸了水,變得很硬。春夏之交的那幾天,我一直在看這本小説,快到結尾的時候,我似乎和她爆發了一場爭吵。我睜開眼,她已經走了。夏天的滯重感在我周圍瀰漫,我由此悽悽慘慘,展開小説,想要看完,卻只能徒勞地任由目光滑過一行行字句,怎麼都看不下去,等我放棄的時候,手裏的那頁已經被我捏成了兩半。
在小説裏夾着的讀書筆記裏,曾經的我寫道:在親密關係中——如摯友、家人、愛人——我們心中的某一部分強烈抗拒用顯式語言表達這段關係應該説出的話語。當我們想要表達赤膽忠誠和心意相通時,我們更傾向於用行動來表達——我們一起吃飯、相互擁抱、如影隨形。
我盯着自己的字跡,任由思緒像幽靈一樣,遊蕩在過去的思考中。
如果把這些行動換成話語呢?“我承諾效忠於你”,這是表達你與部落或民族同心同德。“我對信條忠誠不移”,這是表達你對信仰的堅定。“我愛你”是想邀請另一方回覆“我愛你”。這不是在表達觀點,而是在完成儀規。
你不會説:“讓我們彼此相愛。你病痛時我照料你,我病痛時你扶持我。以後的家務我來承擔,錢我來賺,每週我們做很多次愛。”。似乎我們都認為,如此説話的人根本不懂得親密關係應該説出怎樣的話語,想必是因為顯性語言系統控制着談話,與大腦的理性、審慎、意識部分相關聯。
但如果你表達出這是由某些深層、原始的情感所控制,你就有理由讓對方相信這個承諾由心而發,相信你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轉眼就跑到門外。所以,要如何讓對方知道你的話是出於激情——而非理性的考量呢?
我合上小説,放回去。儘管過去了長達7個月的時間,我所面臨、思考的問題依舊沒有答案。隨着列車行駛時的微微顫動聲,我想要試着再找一次答案。
“我愛你。”想象中的我説。然後我又説了一遍,發出了一點呼氣和吸氣的聲音,然後又一遍,又一遍,直到我那殘留下來的最後一點自我意識,以及照這模式説話的愚蠢的感覺,也都消失殆盡,好像生活裏或者電影裏都從來沒有人這麼説過似的——我再一次張開嘴,終於聲音從胸腔中慢慢升騰而起,空氣在振動,我大聲説了一個詞,但是正好被列車到站的播報蓋過去了。
我輕輕嘆氣。目光掃過更多堆在上層的小説,我看見了《甜牙》。在《甜牙》的結尾,湯姆請求塞麗娜成為他小説的合夥人。
在我的筆記裏,合夥人這個詞被打上了橫槓。
“我要像湯姆一樣。”我規規矩矩地寫道。
“原諒我,我想要……不,我必須。”——這是小説的原文,我也一併照抄在了筆記裏。“嘗試你的孤獨,代入你的不安全感、對於爸媽和睦的渴望、家人的責任和義務之間的兼顧,代入你那不時流露的一點點探詢、一點點無知、一點點執著和一點點社會良知,代入你那些自哀自憐的時刻和遇事大多循規蹈矩的習慣。與此同時,沒有忽略你的聰明、美麗和温柔,沒有忽略你熱衷睡覺也喜歡玩樂,沒有忽略你的幽默和那種老是想保護別人的本能。”
這些字跡讓我覺得很陌生,怎麼也沒想到這是去年的自己。去年過去得如此之快,以至年終總結在這麼一個週末、在列車上悄然來臨。
被塞到《甜牙》下面的一本小説是《贖罪》,《贖罪》下面是一連串俄羅斯小説,那是年底在大學旁聽的時候,教授佈置的參考書目。以及,我沒有錯過那本佈滿灰塵,從垃圾桶底部打撈出來的張愛玲的小説集。裏面有一篇講霸王別姬故事的小説我還記得。
在那個故事裏,虞姬殺死自己前,給項羽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比較喜歡那樣的收梢。”
以這次夜話作為對過去一年的收梢,我覺得也還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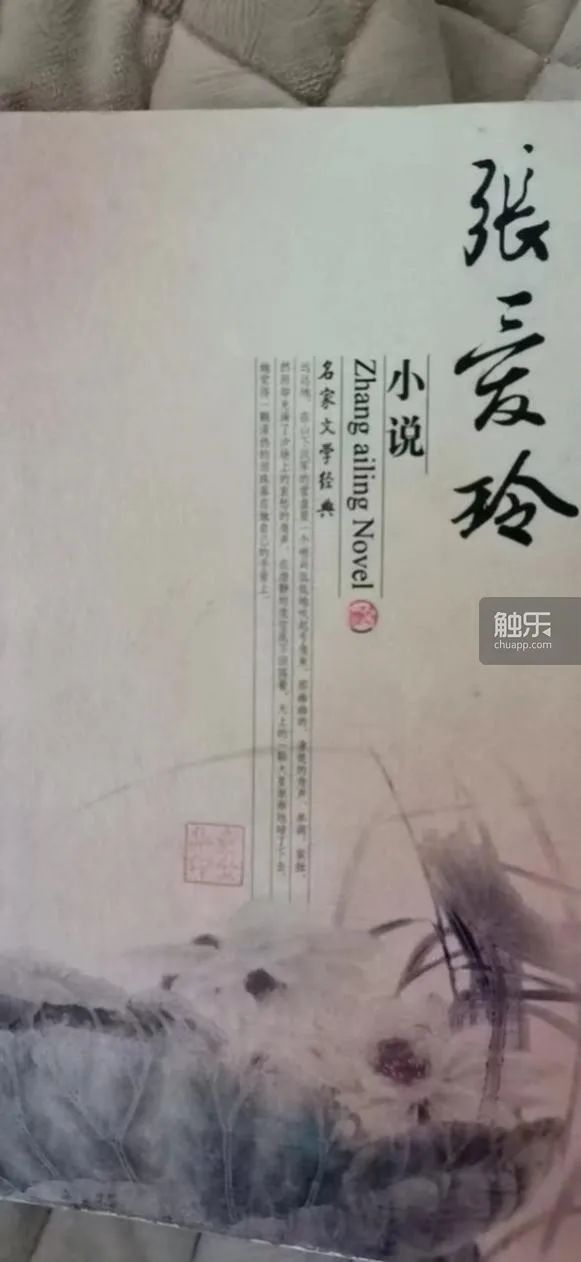
霸王別姬的故事就在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