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 | 明清之變何以改變中國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01-19 21:30
編者按
2023年1月12日,著名歷史學家、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馮天瑜因病辭世。馮先生長期深耕中國思想文化史領域,在建構中國文化史的認知框架、理解明清文化譜系與脈絡等方面多有創見。作為理解中國從中古形態向近代形態轉軌的關鍵歷史階段,明清時期是不能忽視的思想大時代,也是充滿爭議的一段特殊時期。在這篇2016年發表的文章中,馮先生指出,明清是古代中國社會的晚期,其時,延續幾千年的秦制弊端顯露,謀求變革的呼聲此起彼伏, 清初顧炎武稱自己所處時代“已居於不得不變之勢”。中國歷史上突破傳統格局、以工業文明—民主政治為目標的大變革,在清末民初得以展開,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恰是這一大轉折的前夜,這表現在:內部,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啓蒙文化出現;外部,西方近代文化東來。然後彼時“萌芽”幼弱、“啓蒙”聲希,明清文化主流仍延續秦漢以來的常態,而揚棄性的文化變革在潛滋暗長,所謂“常”中寓“變”、“變”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襲常與新變”來概括。這一論析,對於我們今天理解明清之變乃至現代中國的治理轉型,依然具有啓發意義。我們特重發此文,緬懷馮天瑜教授,亦供讀者參考。
襲常與新變的明清文化
馮天瑜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 》2016年第5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馮天瑜先生
**史學的功能,要者在展開歷史發展過程,明其變易,方能識破興廢成敗之底裏。**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觀史亦然,須從歷史流程(尤其是轉折處)着眼。討論明清文化,需要將其置於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波瀾壯闊的進程中加以考究。
一
明清是秦漢以下帝制系列的末端,但這個末端並非細枝微節,而是相當龐大繁複的,與帝制雄闊的開端——秦漢遙相照應。
周秦之際發生中國製度史上的一次大更革。秦代(前221~前206年)是宗法封建分權的“周制”向宗法君主集權的“秦制”變異的節點,這種由“多”而“一”的轉折,在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已然萌動,故王夫之《讀通鑑論》稱戰國為“古今一大變革之會”。經由這種變革,至“秦王掃六合”,一統天下,方正式確立“郡縣代封建”的君主集權政制,自此形成的定勢,籠罩中國史程達兩千年之久,人言:“歷代皆行秦政制”,即此之謂也。然而,這精要的概括只講出史蹟之半,秦以下兩千年並非單行“秦制”,或如某些昭示“仁政”的帝王及謀士宣稱的純以“周政”治天下。真實情形是:主法的“秦制”與儒家概括的“周制”互為表裏、相與交織,帝王無一不左手持儒家經典、右手揮法家利劍,漢宣帝講了實話:“漢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拙著《中國文化生成史》下冊第九章詳論於此,這裏不再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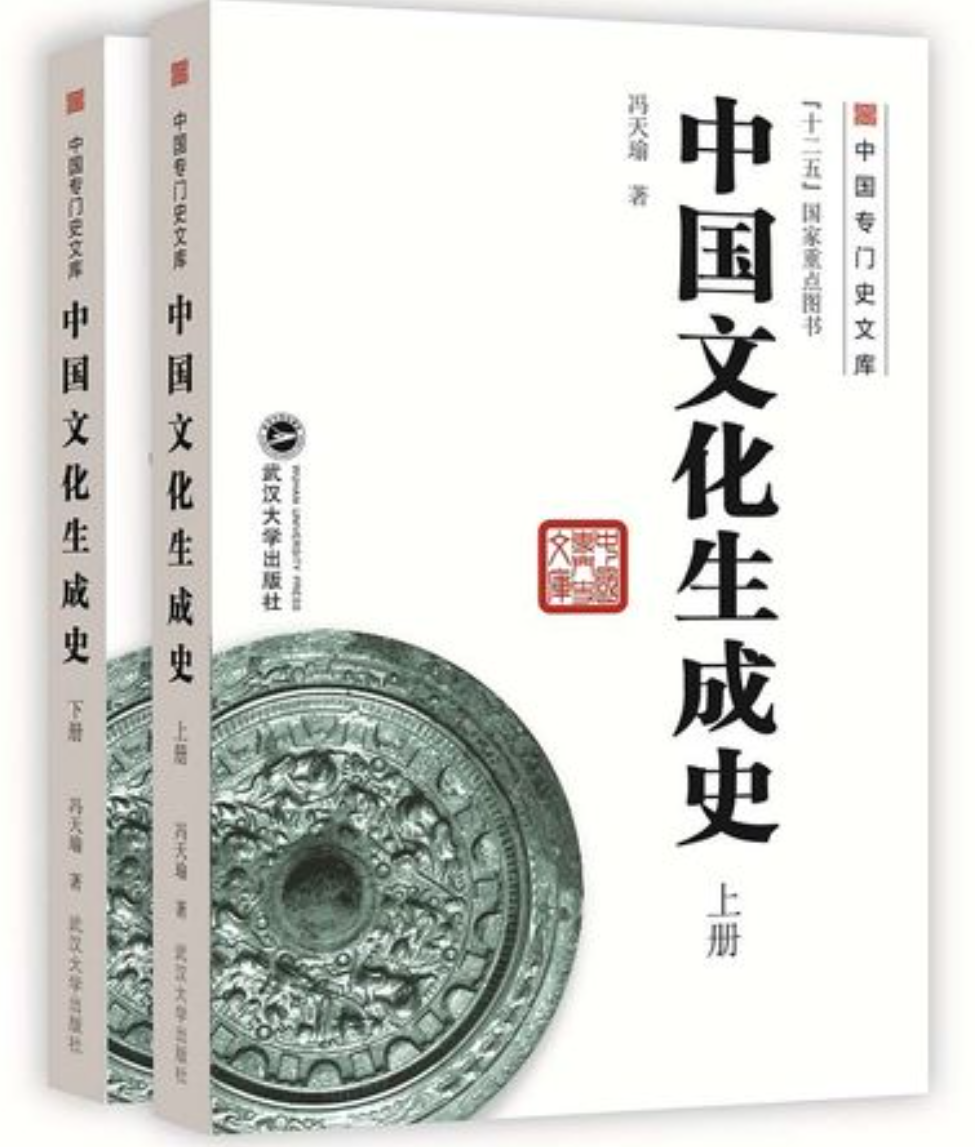
馮天瑜先生著作《中國文化生成史》
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是兩千年宗法君主集權社會的晚期,周秦兩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漢以來之慣常,不過秦制尤其眧彰,其弊端被時之有識者批評,謀求變革的呼聲此起彼伏,清初顧炎武稱自己所處時代“已居於不得不變之勢”。秦以下,有過漢晉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農耕文明—君主集權政治大格局內部的調整。中國歷史上突破上述格局、以工業文明—民主政治為目標的大更革,在清末民初方得以展開,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值這一大轉折的前夜,其國內表徵是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啓蒙文化出現,國際條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國。然“萌芽”幼弱、“啓蒙”聲希,明清文化主流延續着秦漢以降的常態,而揚棄性的文化變革在潛滋暗長,所謂“常”中寓“變”、“變”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襲常與新變”概括。
二
明清處於歷史發展的特別節點,略言之——
第一,自秦漢以降,歷經多個王朝興替(不算地方割據政權,列入正史的朝代有:秦、西漢、東漢、魏、西晉、東晉、宋、齊、梁、陳、東魏、西魏、北周、北齊、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北宋、南宋、西夏、遼、金、元、明、清),而明清是與當下最為切近的兩個王朝。此點似乎無須言説,卻因其為研討明清史不可輕忽的基點,故仍當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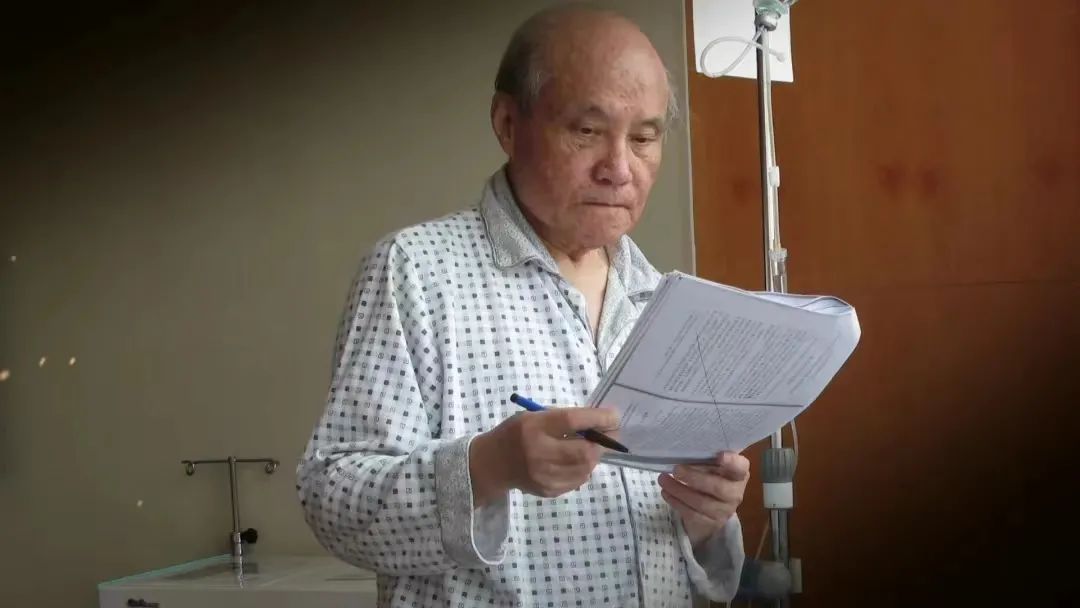
去古未遠的明清可稱之“近古”,其制度與文化,綜匯前代,無論從積極意義還是從消極意義言之,都為近現代中國提供了最直接的遺產。這裏且不議制度文化與形而上的觀念文化,即從可觸摸的形而下的器物文化論,唯明清保有較豐富的可供今人觀摩的實存體。以建築為例,中國曆朝宮殿無算,但秦之咸陽宮、阿房宮,漢之長樂宮、未央宮,唐之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宋之艮嶽,多毀於“改朝換代”的戰火,消弭於歷史塵埃,只可通過司馬相如《上林賦》、曹植《銅雀台賦》、杜牧《阿房宮賦》一類美文,遙想當年宮闕的壯麗,留下遠望憑弔的惆悵。今人能實在見到的完整皇殿,只有明清紫禁城,那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偉岸,彰顯帝制的威嚴;那藏品之淵富,昭示中華聲明文物的精深博大。先秦以下,京師、州縣城垣更難以數計,當下仍然屹立的南京城、西安城、荊州城、平遙城等碩果僅存者,皆明清所建。戰國以降,累代築長城數萬裏,而完整保存至今的磚築長牆只有明長城,吸引中外遊客的渤海邊山海關、金山長城、八達嶺長城、慕田峪長城、甘肅嘉裕關,在在如是。若以典籍為例,巨型類書《永樂大典》、最大辭書《康熙字典》、超級叢書《四庫全書》無不集成於明清。
在一定意義上,經由“近古”明清,方能辨識“中古”漢唐、“上古”先秦;透過“近古”明清,方能瞭然近現代的由來有自。
第二,兩朝五百餘年是中國史上連續統一時間較長的階段,只有兩漢集合的四百餘年統一時段略可與之比肩。
明代從政制、軍制、財制、文教制諸方面使掌控一統帝國的秦製得以強化,亦注意發揮周制的調適功能;清承明制,但張大了民族壓迫要素(清前期尤甚),又較充分地融匯周制與秦制,集皇權制度之大成。明清的重要歷史作用是,使秦漢以來一統國家的建構得以完備與強化,再無分權勢力尾大不掉。如果説,漢代封國、郡縣並列,唐代節度使掌握軍政,導致藩鎮割據,國家分裂不時發生(西漢吳楚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東晉後的五胡十六國、唐後的五代十國為劇演),而明清制度則杜絕分裂的可能,各種外力與內力皆不足以真正撼動統一大局。然而,明清使秦制極端化,專制羅網嚴密以至苛酷,障礙社會近代轉型,束縛人的自由發展。明清制度的雙重功能,為明清後時代提出維護“一統”與突破“專制”這頗相扞格的兩大使命,容易顧此失彼,中國近代化進程因以崎嶇錯綜。
第三,明朝是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清朝是繼元朝後第二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統王朝。
傳統中國有幾個重大分野,為士眾念念於茲,其中與“君子小人之辨”相提並論的,便是“華夏夷狄之辨”。明清易代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改朝換代,還有“華夷換位”含義,這是非同小可的一大變故,黃宗羲稱之“天崩地解”,王夫之稱作“地坼天乖”、“天崩地裂”,不僅震撼中國,在朝鮮、日本等漢字文化圈諸國也引起強烈反響。因此,清末的社會變革,不僅要實現時代性遞進(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皇權專制向憲政民主轉化),還要解決作為人口主體的漢族的民族性存續問題(太平天國與辛亥革命都曾以“反清復明”作號召,“排滿”具有最廣泛的民眾動員作用)。更重要的是,時至清中葉以降,國人在抗禦西力東侵之際達成中華民族共識,這是尤具深遠意義的新的民族主義命題。古老的“華夷之辨”又迭加近代民族理念的形成,構造了近古數百年,尤其是晚清數十年朝野競相求解的絕大題目,多少事變、多少人傑都圍繞此題運轉。這是明清史的複雜性超邁前朝的所在。

中國建立近代民族國家、形成文化認同,是在明清五百餘年的錯綜進程中得以實現的。一個眾族共生、多族互動的古老大國鑄造近代民族國家共同體,較之單一民族國家(如日本、德意志)的近代立國遠為困難。而明清兩代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值得詳辨的是,清朝既有民族壓迫深重的一面(以滿人入主中原初期為甚,清末推出滿洲親貴主導的“皇族內閣”為其迴光返照),又有滿漢成功交融的一面(漢人士子在清朝發揮重要作用,康雍乾諸帝對漢文化的精深修養為其表徵),還有實現諸民族親和的一面(朝廷特設承德避暑山莊接待北方及西北諸族首領,展示了謀求民族團結的智慧),識者當全面觀照,不可偏執一端。
第四,兩朝皇權制度完備,漢、唐、宋抑制皇權的要素(如貴族權、相權等)被大為裁抑,明清攀援至君主集權制的頂峯。
明代削奪封建貴族權力(永樂以後諸封王“授土而不臨民”,王侯未獲詔旨不得進京、不得相互聯絡,禁止干預地方政務),廢除秦漢以來沿襲千餘載的丞相制度,皇帝直轄六部和行省三司,內閣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秘書,還受司禮監製衡,又有廠衞嚴密監控,皇權幾近極至。清承明制,明代中央集權體制基本照單全收,但保留滿蒙貴族特權,又增設軍機處,皇帝在幾名近臣輔弼下獨攬朝政。明清的皇權政治多有“不衷古制”的弊政(如明代頻繁更迭以至殺戮首輔、廷杖處罰朝官,清代以文字獄恐嚇士人,令其就範文化專制),其流弊之一是敗壞官風、挫傷民氣。現代哲人反思的“官腐民懦”“精神勝利”“看客心理”等“國民劣根性”,其近源正在明清專制政治對官民的精神戕害。
明清皇權專制達於極端,而聲討皇權專制的思潮也潛滋暗長,但皇權制度根深蒂固、皇權思想影響力勁拔,久久控扼朝野,即使清末革命洪濤掀翻帝制,而民主政治仍遭遇難產,這與明清皇權專制的強勢遺傳頗有干係。
第五,進入地主—自耕農經濟成熟期,達到農業文明的最高水平。
明清的生產力規模,早期工業國尚不能望其項背。綜合各種統計,18世紀前後的中國GDP約佔全球二至三成,其經濟體量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強),並對早期工業國的產品有相當排拒力,而絲綢、瓷器、茶葉深受海外歡迎,因此外貿一直鉅額出超。史載:18世紀中葉,中國每年出口歐洲的生絲約1萬擔,價值約140萬兩白銀;英國人斯當東著《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記述:乾隆間,每年由外國商船運到歐洲的華茶約2000萬磅,價值近400萬兩白銀。當時正值西班牙等殖民主義國家在美洲墨西哥等地開採、冶煉白銀,西方以之換取中國產品。從明萬曆開始,西班牙銀元(時稱“本洋”)流入中國,清中葉達到高峯,中國成為白銀庫存量最多的國度,德國人貢德· 弗蘭克著《白銀資本》載:1545年到1800年,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6萬噸。1/3到1/2的美洲白銀,最終輸向中國,西方因以發生“銀荒”。直至19世紀初中期,“世界工廠”英國的商品也難以打入“農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中國市場,於是通過鴉片貿易使白銀從中國大量外流,又令中國人體質精神雙雙孱弱,成“東亞病夫”,以便驅使。此禍延綿百年。
明代中後期,既有資本(白銀),又有國際市場,長江三角洲、晉東南等地商品經濟繁榮,“機户出資,機工出力”的工場手工業發展,區域商品市場形成,晉商、徽商、浙商名滿天下,在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頗有建樹。然而,“農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生產方式對商品經濟的抑限,專制皇權(通過皇莊、皇店,礦監、税使)對民間工商業的超經濟剝奪,使資本主義萌芽如大石鎮壓下的植物,難以健康發展,一度享譽天下的工商品牌大多成“斷尾青蜓”(晉商、徽商乃至廣東十三行中的著名的商號皆未延傳下來),絕少日本的住友(1590年開端)、三井(1673年開端)、三菱(1870年開端)、安田(1863開端)那樣持續發展數百年的工商企業。此種情形延至當代,調查顯示,今之日本有150年以上歷史的企業高達21666家,而中國僅有“六必居”、“張小泉”剪刀、“陳李濟”、“同仁堂”等為數極少的“百年老字號”(多為餐飲業、中藥店及小手工業)。
明清鼎革之際大規模戰亂的摧折,使商品經濟遭受重挫(“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正發生在工商業經濟、市民文化最發達地區)。清初減免明代“三餉”、實行“攤丁入畝”,此皆善政,對復興農業經濟功不可沒,“康雍乾盛世”由此奠定物質基石,然這類“輕徭薄賦”舉措皆不逾古典範域,並無近代新機制可言,故清中“盛世”不過是舊道踱步。明史專家李詢説,明清“只有資本主義萌芽時期,而沒有資本主義確立時期”。誠哉斯言!
第六,國際環境異於往昔。
如果説漢、唐、宋面臨經濟落後、武功強勁的遊牧民族來襲,“御胡”是基本的國防任務,明代依然如此(抵禦北元和滿洲),然晚期又有攜西方早期近代文明的傳教士來訪,在中國文化池塘吹起漣漪。這是繼晉唐間南亞佛學入華之後,中國文化線與外來文化線的第二次交會。清中葉以降更有經濟先進、船堅炮利的西洋殖民者入侵,國防重心從西北“塞防”轉為東南“海防”,中國遭逢數千年未遇之強敵。晚清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無法沿固有軌跡運行,被動捲入世界近代化滾滾洪濤之中。
明初有鄭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的空前絕世壯舉(航海技術之高、船隊規模之大,均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西方諸次遠航之上),展示了高級農耕文明和一統帝國的富強和對外展拓能力。然而,此一遠航雖推進了商貿發展,然主旨並不在此,昭顯帝威才是宏願所在。乏於經濟收益及社會動力的政治性遠航被時人視為勞民傷財、無益有害的弊政,在發動者永樂帝、實行者三寶太監相繼辭世後,必然人亡政息,難以為繼,不僅自棄鉅艦,連遠航檔案都加以銷燬。誠如梁任公《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所謂:哥倫布、達· 迦馬後有無量數哥倫布、達· 迦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加之明清兩朝相繼厲禁民間海洋航運,中國自行退出15世紀末開端、一發不可收的世界大航海潮流(也就止步於近代工商業文明的門檻之外),中國在中世紀的“先進”地位就此打上句號,等待着四百年後西洋人以槍炮和工業品擊破閉鎖的國門。

自己終止“走出去”,必然被外人“打進來”,這是明清史昭示的教訓,也是從分散趨向整體的近代世界史作出的結論。
三
文化的某些成分(如風俗習慣、行為方式、藝術形式的若干斷面),不一定有先進落後之別,如中醫與西醫、筷子與刀叉、京劇與歌劇、水墨畫與油畫,各具特色、各有優長,不必作線性比較;而物質文化(以生產力水平為主要標誌),還有制度文化及觀念文化的某些部分,在歷史行程中後浪逐前浪,存在先進落後的線性序列。以後一側面而論,明清五百年,是中國在世界文化總進程中,從先進跌入後進的歷史轉折階段。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陳寅恪語),宋代生產力及科技、文化水平領先世界,明至清初大體與歐西持平,清中葉以降則落入“後進”行列。這並非是清代在衰退,而是因為自戀於“天朝上國”,固步徘徊,被國人十分陌生的工業化西洋及後起的東洋日本彎道超越(鴉片戰爭中國敗局已定之際,道光皇帝還不知對手英吉利是何方神聖,是否與大清接壤;中日甲午戰爭時,清方朝野對新興的日本茫然無知),陷入落後捱打困境。
近代以前,國人以“聲明文物之邦”傲視羣倫,很少作文明水平的國際比較,我們只得從外國人的評華言論中略見大貌——
元初入華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對大都、杭州充滿景仰,對“契丹”(實為中國)文明的先進性多有佳評;明末清初來華西人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白晉、張誠等留下多種對中國的觀察記錄,褒貶雜陳,卻未見從總體上指中國“落後”的言論。

18世紀的西歐,推崇中國文明(伏爾泰、魁奈等)、貶抑中國文明(亞當· 斯密、孟德斯鳩等)並存,然推崇佔主導。18世紀末葉以降,隨着英國工業革命的成效以加速度顯現,中西文明水平差距急劇拉大,發現中國落後的西人,由鳳毛麟角變得如過江之鯽。乾隆五十八年八月(1793年9月)為乾隆帝祝壽的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窺破貌似強大的“中華帝國”的虛弱本質,將清朝稱之“泥足巨人”。這是外人關於中國已入頹勢的較早評述。
19世紀入華西洋傳教士、商人、軍人、外交官、學者的中國見聞錄,更充滿指中國“落後”的記錄(林樂知、李提摩太、戈登、赫德等人的評華言論有許多尖鋭批評)。同為後進國的日本於江户幕府末期,在鎖國兩百年後,首次派官船“千歲丸”造訪中國上海,隨船日本武士原先多對文化母邦中國懷有敬畏,但他們目睹的清朝,一片破落景象,官腐民弱,日本武士的中國觀遂由崇仰轉為鄙夷,甚至萌生“率一萬騎,掃平中國”的狂念。須知,那時的日本尚處半殖民地弱勢狀態。
至於中國人,在門户開放後也開始注意中外比較,發現自身的落後,如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有六“不如夷”之論(“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船堅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而承認落後,正是奮起直追的開端,“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王韜更一反僅僅把西力東漸視作災禍的觀點,認為這同時也是中國進步的契機,他1864年所撰《代上蘇撫李宮保書》指出:“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所謂不世出之機也。”
自孫中山以來,覺醒、有擔當的中國人高喚“振興中華”,便是要抓住這“不世出之機”,從近二百年頹勢中超拔出來,追向世界文明的先進行列。
四
以上概述明清所處的歷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現“集古”—“萌新”的雙重屬性。
其一,明清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總彙期。
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規模展開,類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辭書《康熙字典》,叢書《四庫全書》均為中國乃至世界相關典籍之最。
訂正、考釋古典的考據學始於明中葉(楊慎等為代表),清中葉更為學術主流,代表學者有以惠棟為首的“吳派”(沈彤、江聲、餘蕭客、江藩、王鳴盛等);以戴震為首的“皖派”(段玉裁、程瑤田、金榜、孔廣森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阮元代表的“揚州學派”(任大椿、焦循、汪中等)。乾嘉考據學對古代典籍作系統整理、對傳統文化作全面總結,使得數千年來各個學科、各個領域的專門之學得到發掘、彰顯和條理化。其研究對象重在古籍、古史、古器物,治學態度如“老吏斷獄”,“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理性態度、實證方法,與近代科學並無二致,對中國乃至日本的近現代學術影響深巨。
明清集傳統科學技藝之大成,藥物學鉅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農學總成且汲納西學的徐光啓《農政全書》,手工業技藝百科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地學傑構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造園絕世經典計成的《園冶》,沿襲兩百餘年的雷氏建築術(僅國家圖書館就珍藏“樣式雷”兩萬多張建築圖樣),等等,均達到前工業時代的最高科技水平,即使今日觀之,也頗有發明、發現方面的啓示。
其二,程朱理學主導精神世界,繼之心學崛起,又復歸於程朱,構成明清形上學的圓圈,晚清新學勃興方突破此一圓圈。
自晉唐以降,佛教與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響力愈益增強,儒學退守,至宋明,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礎上,展開類似晚周孟子“闢楊墨”的“闢佛老”努力,一種思辨化的、以倫理為核心的新儒學——理學在宋代興起,提供克服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的精神武器。中經元代,至明清,朝廷推尊理學,將二程朱熹論證的“綱常”“天理”規定為倫理、政治指針,《四書》朱注成了科舉考試範本。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學,因為官方片面伸張、強力推行而趨於僵化,衍為一種御用的“制度化儒學”,禮教漸趨嚴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與亞里斯多德學説在歐洲中世紀教條化的情形頗相類似。而明中葉崛起的陽明心學,強調個體心性修為,倡導“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思想解放意藴在。由陽明學衍生的泰州學派反映市民階層突破禮教樊籠的訴求。

與心學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眼光投向社會實際的經世實學也有發展(自明末至清末多種“經世文編”的修纂顯示此學的昌盛),架設通向近代新學的橋樑。
極端的專制皇權激發明清之際“非君論”湧動,在市民文化及黨社文化中產生出繼承並超越先秦“民貴君輕”説的“新民本主義”,不僅譴責個別暴君、昏君,其批判鋒芒普遍地指向“今之君”,即秦漢以降皇權專制制度下的全體帝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唐甄《潛書》為代表作)。拙著《解構“專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有詳論,此不贅述。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代表的早期啓蒙思潮別開生面,但在皇權高壓下,此種思潮只能暗流潛行(“待訪錄”“潛書”兩書名傳神地表達了此種窘態),且在清中葉沉寂百餘年,嘉道間的龔自珍、魏源重振其説,成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導。而近代新學萌動之際,頗多對“晚明遺獻”的藉助,這正是一種“以復古求解放”的歷史辯證法之顯例。
其三,伴隨城市經濟發展,市民文學蓬勃興起。
俗謂:中古至近古文學主潮經歷了“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説”幾階段。小説確乎是近古最具特色的文學樣式。明清小説從“魏晉志怪志人—唐代傳奇—宋元話本”一路走來,漸成洋洋大觀。傳奇、話本都是短篇,明清短篇精進不已(明末“三言二拍”,清代《聊齋志異》皆短篇集合),更湧現長篇鉅製,講史小説《三國演義》,英雄小説《水滸傳》,神魔小説《西遊記》,世情小説《金瓶梅》、《紅樓夢》成為古典文學新的楷範。
明清出現將小説、戲曲提升到與詩文並列地位的議論,甚至認為其教化功能可與經書相比配。明人李贄稱《水滸傳》和《西廂記》“皆古今至文”,公安三袁服膺其説;清人金聖嘆稱:“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明清小説在思想及手法上一創全新格局的是《紅樓夢》。

小説、戲曲繁榮,文學走出象牙塔,活躍於市井勾欄,為雅士俗眾共賞。加上童蒙讀物流行,中國傳統文化的普及,以明清為最。
其四,“西學東漸”、“東學西漸”雙向互動。
明末清初,西歐耶穌會士東來,與徐光啓、李之藻、王徵等中國士人協同譯介西方文化成就(《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輿萬國全圖》、《遠西奇器圖説》等),清代順康兩朝,皇室愛好西學。與此同時,數以百計的來華耶穌會士又向西方譯介中國經典及社情,此為歐洲啓蒙運動的一種精神借鑑。西學東漸、中學西漸乃17、18世紀中西文化史上的盛事。由於清廷和羅馬教廷兩方面的原因,這種東西文化互動在清代雍正、乾隆前後中斷百餘年。清末以降,伴隨西力東侵,馬禮遜、丁韙良、傅蘭雅等歐美新教傳教士來華,在宗教殖民的同時傳播西方近代文化,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中國士人有輔譯之功。嚴復等啓蒙思想家躬親西學譯述,使“西學東漸”在更高層面和更廣範圍得以展開,進化論、民約論、民權論、自治論、民族國家論及科學技術傳入中國,激起波瀾,學堂、報紙、圖書館等近代文化設施雨後春筍般湧現,新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得以專科發展,知識分子取代士大夫成為文化人主體。王國維把“西洋之思想”比擬為“第二之佛教”,並預期對中國學術文化作出創造性貢獻的,必是中西之學的“會通”者、“化合”者。王國維斷言:“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梁啓超更寄望中西文化“結婚”,以產出健美的“寧馨兒”,以強吾宗。
新學取代舊學似成一不可逆轉之勢,然被統稱“舊學”的傳統文化自有其深巨潛力和廣遠影響力,在近現代文化進程中發揮無可替代的、或顯或隱的作用,故“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中西文化激盪(既相沖突又相融匯)構成清末民初的重要景觀,戊戌變法前後展開的中西古今的體用之辯,透露中西會通的廣度、深度及難度(此辯在學理層面、社會實踐層面一直延伸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