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為什麼人們不能夠離開此地”——伊斯坦布爾的地震恐懼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02-07 21:38
編者按
當地時間2月6日,土耳其東南部靠近敍利亞邊境地區在9小時連續發生兩次7.8級地震,引發全球關注。該場強震系過去一年全球最大地震,這場強震同時波及敍利亞、黎巴嫩、塞浦路斯、希臘、伊朗等國,其中敍利亞阿勒頗、拉塔基亞等多個省份遭受的影響尤為嚴重。目前,此次地震已導致該國超6200座建築倒塌,土耳其和敍利亞兩國在地震中遇難的人數已超5000,世衞組織估計,可能有2萬多人在這場地震中罹難。除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之外,令人惋惜的還有世界文化遺產加濟安泰普城堡被毀。土耳其作為橫跨歐亞大陸的國家,不僅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在地緣政治中也扮演着極其重要的特殊角色。從歷史長河中來看,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土耳其文明屢遭自然災害和大國博弈的創傷,文明常處於“失落之中”。本公眾號選取了土耳其著名小説家帕慕克的散文《伊斯坦布爾的地震恐懼》,描述了其在曾經伊斯坦布爾地震期間的親身經歷與感受;另一篇則從文明傳承的角度,回顧了從奧斯曼到土耳其帝國的發展史,以及在此期間土耳其政治和外交方略的演變。本公眾號特推出本組文章,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伊斯坦布爾的地震恐懼
奧爾罕·帕慕克
本文節選自奧爾罕·帕慕克:《別樣的色彩》,宗笑飛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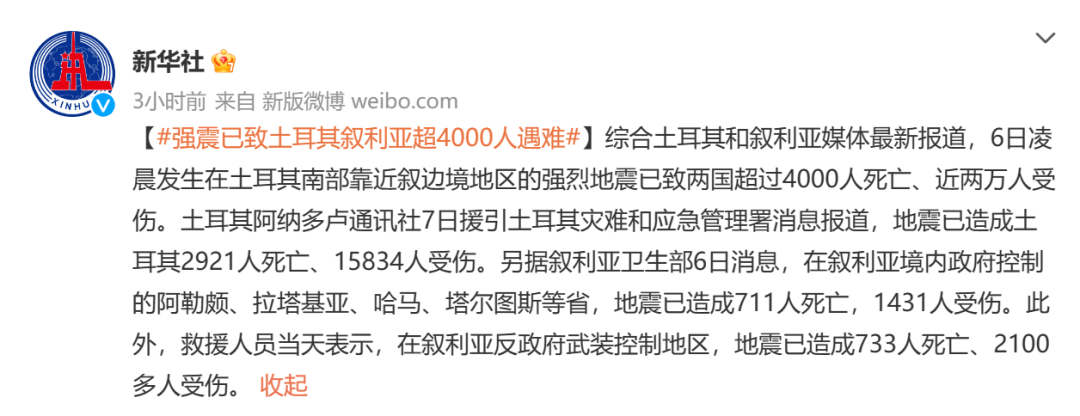
△ 土耳其卡赫拉曼馬拉什省當地時間6日凌晨4時17分發生7.7級地震,隨後附近地區又發生多次餘震,強震已致土耳其敍利亞超4000人遇難。
過去的日子裏,我總是好奇地在想,從我書桌這裏可以望見的那座清真寺宣禮塔,是否有一天會倒下來砸到我?那座清真寺是為了紀念卓絕的統治者蘇萊曼的兒子,年幼夭折的奇罕吉爾(Cihangir)王子而建的。從1559年開始,它就佇立在那裏,以它裏面兩座高聳、略有傾斜的宣禮塔俯瞰着博斯普魯斯,已成了存在永恆的明證。
第一次問到了我這個問題的,是樓上的鄰居,那時他來找我,和我聊起他對地震的焦慮不安。半驚恐半開玩笑的,我們走上陽台測算距離。**在四個月的時間裏,伊斯坦布爾就曾發生過兩次地震和難以計數的餘震,這些以及3萬人的死亡數據仍然清晰的印在我們腦海中。**更有甚者(這點能從我這個工程師鄰居的眼中讀到),我們都深信科學家們告訴我們的:在不久的將來,馬爾馬拉海某處距離伊斯坦布爾非常近的地方,一次大地震會瞬間奪去十萬人的生命。我們對宣禮塔進行了粗略目測,情況並不使人樂觀。在仔細研讀了一些著作和百科全書後,我們知道,在過去的450年裏,奇罕吉爾清真寺(那個“存在永恆的象徵”)曾有兩次被地震和火災摧毀,如今位於我們對面的穹頂和宣禮塔已經找不到清真寺最初的痕跡了。進一步研究後,我們發現,大多數伊斯坦布爾的古清真寺和古蹟至少都有一次曾被地震毀壞過(包括聖索菲亞大教堂[Hagia Sophia],它的穹頂曾於建成20年後,在一次席捲了城市的地震中坍塌。)另外還有少量清真寺不止一次被摧毀,隨後被修建,為了“抵抗更大壓力。”

△ 圖源網絡 | 2023年當地時間2月6日,土耳其馬拉蒂亞,地震後部分受損的清真寺。
而宣禮塔,遭遇更為慘烈。在過去500年間曾經席捲城市的最嚴重的地震中——包括1509年爆發的被稱為“審判小日”的地震,以及1776年和1894年地震——倒塌的宣禮塔要遠遠多於坍塌的穹頂。最近兩次地震後,我和朋友就曾在電視、報紙上,甚至在對地震區的訪問中,看到過無以計數的宣禮塔橫倒在地。多數情況下,它們都是砸在臨近建築物上:睏倦的守門人在深夜玩雙陸棋的學生宿舍樓;母親起牀餵哺嬰兒的居民屋;或是(在第二次玻魯[Bolu]大地震裏)一家人正圍着電視,看討論另一次地震的晚間新聞,而一座宣禮塔就轟然而倒,像切蛋糕的刀子一樣將房屋劈成兩半。**那些沒有倒塌的宣禮塔,也幾乎都遭到了損壞。**無法修葺的就用鐵鏈和起重機吊起,然後摧毀。在電視上,我們看過太多的宣禮塔緩緩倒塌,因此我和鄰居對它的倒塌方式非常瞭解。就像之前説的,下一次地震將來自博斯普魯斯和馬爾馬拉海,所以,鄰居和我開始通過對過去地震災害的分析,來計算這座宣禮塔會朝哪個方向倒下來:正衝着陽台上方的那部份,已經在八月地震中變得傾斜彎曲了;更早時候,曾有一次閃電恰巧擊中了宣禮塔頂部的新月和星體造型下的石塊,使它掉落在了清真寺廣場上。
考慮到所有因素之後,現在我們確信,假使宣禮塔真的能夠在預料之中,從我們用手和繩子丈量比劃的方向倒下來的話,那它就不會砸到我們:我們這棟可以眺望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樓,離宣禮塔還真很遠,遠在它的高度之外。“所以,宣禮塔是不會砸到我們的。”鄰居起身告別時説。“事實上,距離是那麼遠,倒像是我們這棟樓會砸到宣禮塔。”接下來的日子裏,我仍繼續着我的研究,想弄清楚,究竟我在此工作的這棟樓是否真會在坍塌時砸到那座宣禮塔,我和家人居住的那棟樓,情形是否也會和工作地類似。我已無法顧及鄰居。這倒不是因為他像很多我熟悉的人那樣,能用黑色幽默來調節自己對地震的恐懼。而是因為,他像另外一些人那樣,正用自己的方法全神貫注的應對死亡恐懼。他已經從我們這棟六層建築中取下了一塊腳料,寄給了伊斯坦布爾工程大學,讓他們測試一下混凝土密度。現在他正像成千上萬做了同樣事情的人那樣,在等待結果。竭盡一切努力之後,他發現等待是如此平靜。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對我來説,我深信,只有獲取更多的知識,才會帶來內心的平靜。**過去訪問震區的經驗告訴我,建築物坍塌一般主要有兩個原因:結構差,土質松。**因此,像有些人那樣,我開始研究我的居室和辦公室所在樓房的土質,它們的結實程度。我諮詢結構建築師,查找工程圖紙,和許多人交流意見。這些人像我一樣,倍受焦慮和恐懼的煎熬。

△ 震後嚴重坍塌的建築物
儘管最近兩次地震的震中都位於城市以外90英里的地方,但它們還是震醒了所有熟睡的伊斯坦布爾居民。3萬人的死亡數據揭露了建築部門在疏鬆土質上建造樓房的拙劣行徑,這使它們在地震面前毫無招架之力。居住在城市周圍的兩千萬居民,處在根深蒂固的恐懼帶來的夢魘之中,他們擔心自己的房子無力抵抗科學家們目前預測到的那次強烈地震。即使住宅樓和公寓是依照高的不可能的建築指數而建造的,但一想到那些數據要應對的,是強度遠小於此次將要來臨的地震,我們還是高興不起來。特別是,這些房屋住着的不是那些馬虎、卑劣、總是偷工減料的開發商,而是自己的父親、祖父,人們就很難期待它會安全堅固。同樣,許多公寓樓裏,由於賄賂了城建委員會,樓體通常會加建幾層,公寓面積和牆體也常被隨意縮小、減少,以增加一些商業空間,這使原本就脆弱的建築越發脆弱。更有甚者,即使你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你所居住的建築物沒有預期的抵抗能力,甚至你下定決心承擔相當於公寓價值1/3的翻修費用,你還不得不説服你的其他那些另有想法、牢騷滿腹、淡然冷漠、愁苦沮喪、無知愚昧、心懷僥倖以及一文不名的鄰居們也都這麼做。因此,儘管潛在的危險很大,我還是沒看到有哪個伊斯坦布爾居民肯面對現實,着手維修自己的房屋。而且我還確實知道,有相當一部分對地震感到焦慮的人,不僅沒能説服自己的鄰居,就連妻子、丈夫、孩子也不支持他們。還有些人,無力負擔整修房屋的費用,只好聽天由命,但仍然難以擺脱恐懼,於是就用玩世不恭的態度來逃避,説,“好吧,即便我傾盡囊中所有來修葺房屋,可是萬一街對面的那棟樓倒下來,砸到了我呢?”正是由於這種無助、無望的感覺,數百萬伊斯坦布爾人都沉浸在地震的噩夢中。

©nytimes
我的夢境和很多人向我描述的非常類似。在夢裏,你看着自己的牀,躺上去的一瞬間,忽然產生了對地震的恐懼。就恰在此時,地震瞬間而至,強烈無比。你看到牀前後搖動。隨着震動,你的小卧室、整個房屋、牀、周圍所有的一切都離開了原地,在晃動中扭曲變形。慢慢的,你的目光移至屋外,所見景象一如電視中直升飛機俯拍被夷為平地的城市廢墟,觸目皆是;此時,你意識到了災難的巨大。但儘管相信末日審判,你——彷彿夢裏不知身是客——暗自竊喜,因為能看到地震,就證明你還活着。同樣,還有責怪你考慮不周的父母、配偶:他們責怪你,但他們還活着。做這些夢,一部分原因是出於恐懼和戰勝它的願望,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都回憶説,儘管感到恐怖,他們還是覺得自己罪孽已除,就像做完宗教儀式之後感覺的那樣。很多因恐懼而顫抖的人,在半夢半醒的黑暗之間漂浮,總是覺得似乎在他們睡覺之時,真的會有一場地震來臨,正是這種真實的恐懼引發了這樣的夢境。如果身邊沒有可以叫醒並和他商量的人,如果無法確定那究竟是夢還是真實,他們就會在第二天清晨去讀那些有關餘震的最新報道。
由於深信不能保障自己房屋的安全性,因此我們相信,只有一條途徑可以讓我們擺脱那種所有地震生還者對災難即將來臨的痛苦感:回去求助那些曾警告我們伊斯坦布爾將會有一次強烈地震的科學家和教授們,讓他們再重新考慮考慮。
**土耳其惟一的一家天文台台長伊斯卡拉(Işıkara)教授最先指出,我們所處的地震帶從土耳其北部延伸至另一端,與加利福尼亞州的極其類似。**如果對最近幾次的大地震做一個製圖分析,你就會發現它們最初是從東部開始,一次一次接近伊斯坦布爾的。在1999年8月那次強烈地震後,所有的新聞媒體都來纏住伊斯卡拉教授,使他每晚穿梭於不同電台之間,重複許多年來都被人們忽視了的現象,那時所有現場觀眾都會問他同樣問題:“那麼先生,請告訴我們,今晚會有另一次地震嗎?”在早期的節目中他的回答總是,“地震會隨時到來。”後來,他發現上百萬人被嚇得失去了理智,更有上百人在極小的地震來臨時就從窗口跳了出去,並且聽到政府內部對絕望引起混亂的抱怨,於是他謹慎了一些,把回答改成,“現在還很難説下次地震會什麼時候到來。”雖然如此,在一次奪取3萬人生命的大地震兩天,餘震漸漸強烈起來之後,整個國家的人都在電視機前看着他的時候,我們還是認為他暗示了我們,那晚有另一場地震。因此我們都從家中出來,睡在公園裏、花園中、街道上。這位有趣的教授,有着像愛因斯坦一樣的外貌,不修邊幅,心神恍惚(儘管沒有他那麼天才),漸漸深為伊斯坦布爾人所愛戴。因為在那些最沒有希望的日子裏,人們對地震強度充滿了恐懼,是他滿足了那些徹夜不眠的人們的願望,給我們增添了一點明亮的,即便是不那麼可信的畫面(例如,暗示地震帶或許離伊斯坦布爾很遠,並不像之前預料的那樣)。而在宣佈壞消息的時候,他也總是面帶微笑,用最柔和的聲音對我們講話。
當然還有一些教授堅持自己的預見,拒絕以好話安慰民眾,辛戈爾(Şengör)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那像冷淡無情的醫生一樣的舉止激怒了每個人。他用“美麗”一詞來描述那奪取三萬人生命的第一場地震。但人們憎恨這些不肯柔和説出自己預見的科學家們,其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對即將到來的劇烈地震有着無可反駁的證據,以及他們近乎無理的斥責態度。在這類惡魔教授的憤怒背後,不僅隱藏着這樣一個事實:**上千萬人居住於此的危險建築將會在地震中毀於一旦,而卻無人對科學預警給予任何關注;還表明了,沒有人去認真聆聽對他重複了1300多次的國際新聞報道。**這就是為什麼他的表現像個憤怒的阿訇那樣,預言無神論者的懲罰將會很快到來。這些教授大多在娛樂節目中座談,嘉賓通常是選美小姐或是健美冠軍,主持人經常會打斷科學家們的詳盡分析,問,“先生,請問最近會有地震發生嗎?會有多強烈?”在11月14日一次最重要的新聞節目中,馬爾馬拉海地裂帶的最新數據引起了激烈爭論,以至於當天新聞在進行到第四十五分鐘時才對比爾•克林頓訪問土耳其給予了簡短報道。與其它節目類似,它直至結束也沒能對主持人執著提問了多次的問題給予明確答案。恰恰如此,這反倒使我們明白,我們能期待的只是更多沒有定論的討論、諮詢以及公開告示。科學家們從不願意説地震也許永遠不會來臨,以給予公眾希望,除非是極少數不令人信服的科學家。**因此,上百萬居住在建於危險土地上的危險建築物中的伊斯坦布爾人終於慢慢明白,他們必須依靠自己來擺脱恐懼。**於是有人將問題交付給安拉,或隨着時間的流逝乾脆簡單忘掉它。而另一些人,在上次地震後採取了一些防範措施後,現在沉浸在虛幻的安適之中。
許多人在牀邊放着大的塑料外殼手電筒,這樣在地震斷電時,他們可以在大火吞噬自己之前尋找生路。手電筒旁還放着哨笛、手機,以便屆時引導救援隊在廢墟中找到他們,有些人把哨笛掛在脖子上(有一次地震,居然有人在脖子上掛着口琴)。另有一些人,隨身帶着房間鑰匙,這樣地震來臨的時候就不用浪費時間找它們。有些人夜不閉户,以便可以毫無阻礙的從自己兩或三層的公寓中逃出。甚至還有人在窗户上繫條長長的繩子,這樣,在地震時分,他們可以直接滑到自己的花園中。在頭幾個月裏,有人被持續不斷的餘震折磨的心力交瘁,以至於在屋內也隨時帶着安全帽。由於第一次大地震是夜裏突來的,因此人們更加渴望做好一切準備——甚至是那些住在公寓高層,不管用多快速度也幾乎不可能順着樓梯逃生的人——他們睡覺的時候也是全副穿戴。我甚至還聽説有人極度擔心自己體力不支,氣喘吁吁,以至於他們上廁所或是洗澡時都匆忙不堪。有些被類似焦慮困擾的夫妻,連親熱的興趣也逐漸喪失。還有不少人建造了些避難蓬,儲存食物、飲料、鐵錘、照明設備等一切可以逃離城市火海的用品,幫助他們在沒有電力供應,道路、橋樑坍塌的情況下生存。上次地震後,還有人開始儲備大量現金。許多家庭認為角落是不安全的,於是牀被放置在遠離牆體、架子和衣櫃的地方。避難蓬搭在一些必須用具,像冰箱、烤箱旁,這樣,理論上,人們就可以在天花板塌陷之時保護自身,這就是一些報紙上的指導信息所稱的構建“救生三角”。

△2月6日,人們在土耳其馬拉蒂亞一處倒塌的建築上搜救。©新華社發(穆斯塔法·卡亞攝)
在那張我伏案寫作了二十五年的長書桌一頭,我也做了大量類似的工作。在放滿大部頭書籍的藏書室內——其中有四十年前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比它更早一些的《伊斯蘭百科全書》和使我瞭解過去地震的《伊斯坦布爾百科全書》——我在書桌下搭了一個避難蓬。為了確信它足夠結實,可以承受砸下來的混凝土磚石,我在幾次地震演習中,都按照指示像胎兒在母體內一樣躺在那裏,以保護我的腎臟。地震小提示同樣告訴我,要在安全角落儲藏一些餅乾、瓶裝水、哨子以及鐵錘,但這些我都沒做。我每天的生活充斥着這些警告已經足夠了,告訴我們裝這個,裝那個。我不願把它們搬到書桌這兒來,會不會是因為我隱約感到,那樣做會讓我的勇氣喪失得更快?不,還有更深層和更隱秘的原因。雖然人們很少説起,但它有時能從很多人眼中看出。我把它稱作是一種羞恥感,一種夾雜着些許內疚與自責的羞恥感。它有點類似於如果你有一個酗酒罪犯的親戚,或是你遭受了意外的經濟破產——你自我保護的願望就如同你想在其他人面前藏起必需品一樣強烈。當第一次地震之後,我國外的朋友或是出版商寫信詢問我的狀況時,我總是羞於回答。我斷絕了與一切人的來往,就像一個剛被診斷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讓任何人知道。在早些日子裏,如果想討論這個話題,我只會和與我處境類似,能夠分享我對下次大地震的焦慮,與我有着相同觀點的人説。儘管這些聊天更多時候更像是自説自話,但隨着我們生氣或激動地喋喋不休,那些樂觀也好,悲觀也好的專家觀點還是很快就被大家所熟知。**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注意觀察我的居所和辦公室的周圍地帶,試圖確定它們腳下的那片土地過去對地震的承受強度。**令我安心的是,我發現在1894年那場地震中,這地方只有少數幾棟建築坍塌。但是當我研究了所有倒塌房屋的記錄,讀到那些被倒塌屋頂砸死的那些人的名字——有希臘屠夫、送奶工人、兵營中的奧斯曼士兵——當我知道,那些我在很多地方曾見到過的古市場、歷史建築物都是毀壞後重修的,我就戰勝了生命短暫、人與宣禮塔是如此脆弱的哀傷。有一本雜誌刊登了一幅小地圖,預測了即將到來的地震走勢,它讓我憤怒不已。它把我周圍這片地帶用黑色陰影圈出,視其為有可能遭受地震毀壞最強烈的地區之一。或者,這僅僅是我這麼認為?僅憑一張如此之小,如此之粗劣的地圖就可以下此結論嗎?藉助放大鏡,我在這張沒有任何註釋的地圖的死亡帶上仔細檢查,甚至找我所居住的街道和房屋,並和其它一些更詳盡的地圖進行對比。我發現除它之外,再沒有報紙或是媒體上的地圖表明,我居住的周邊地區是特別危險的區域。我相信那張地圖一定是錯的,並決定忘掉它。而要想輕易做到這一點,我最好是不要對任何人提起它。可幾天後,我發現自己又在午夜時分研究這張地圖了,透過放大鏡仔細審視那片陰影區域。房東看出我有些擔憂這棟樓的地基質量,他拿出一張四十年前,工人們蓋樓時他自豪地與他們拍的照片。我在這片地區生活了四十多年,照片又喚起了我舊時的回憶。**但我拿起放大鏡,卻只是為了研究這片地區的土質。**科學家們彼此矛盾的觀點,就像媒體不負責任的口水戰一樣,使伊斯坦布爾居民處在焦慮的絕望和令人興奮的安慰之矛盾中。他們可能頭天晚上因為一則壞消息而難以入睡,第二天晚上又會因為一個情況也許並不那麼嚴重的暗示(根據最新的衞星圖片,地震也許只有里氏5級!)而同樣徹夜不眠,就像我前前後後地研究地圖上陰影地帶的土質。儘管我也相信那個雜誌編輯所説的,不要過於重視他們這張簡略的地圖,但我還是很久都在費力思索,為什麼那片陰影地帶會覆蓋在我的房子和我的生活上。整整這段時間,我還一直伸着耳朵留心傾聽外面的可疑聲音和各類傳聞,像城市裏野狗的狂吠。我聽説,如果地震後的日子裏海水變暖,那就預示着下次地震迫在眉睫。當聽説幾周前的日食和地震有着某種奇怪關係時,我一笑置之。“別笑得那麼大聲,”一個憤怒的年輕女孩子這麼斥責我,“如果有地震,我們就聽不到了。”還有人説,地震是因為美國人要來援助我們一艘軍事醫療船隻(“對他們這麼快把它帶到這來,你怎麼看?”陰謀理論如是説)。更離譜的是,據説那艘傳聞中船隻的指揮官,還在甲板上內疚地看着這一切嘆息道,“看看我們都做了什麼!”後來,更有一些偏執妄想開始轉向國內:每天早上敲你門鈴,給你送來牛奶和報紙的看門人,會用與警告你一小時後將停水的相同語氣説,預計一場大地震會在晚上七點十分來臨,將會摧毀整個城市。或者是,某個對即將到來的地震毫無自己觀點的可惡科學家已經逃往歐洲了。又或是,據説政府對即將發生什麼十分清楚,已經秘密進口了上百萬的遺體袋。你還會聽説,軍方已經出動大量挖土機,在城市外的空曠地帶挖了數個墓坑。一個對自己房屋構造質疑的朋友——當然還包括地基——搬到了同條街道的另一棟樓內,僅僅是想看看他的新公寓是否更安全一些。在耶斯尤特(Yeşilyurt)這個建造在伊斯坦布爾劣質土質上的富人社區之一,參加一次有關地震研討會的土地所有者們分成了兩個敵對陣營:**一部分人希望討論如何保護他們自身的安全,而另一些人卻認為這樣的討論會導致地產下跌。**大約就在同一時期,我的一個記者朋友告訴我,他們無法給我提供我想研究的地圖,來調查那張小地圖上的陰影地帶,擔心那樣會引起地產危機,激怒土地所有者。

△ 地震后土耳其金融市場動盪 ©新浪財經
兩個月後,樓上的鄰居在家中告訴我,他寄研究樣品的那所大學已經給他發回了檢測報告。結論——調查的是我辦公室所在的那棟樓——既不令人完全失望,也不那麼令人有信心,這取決於我們每個人怎麼看待它,就像那天我們在判斷宣禮塔是否會砸在我們身上時,所得出的主觀結論一樣。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我聽説一個音樂行業的老朋友,在路過一個被八月份地震嚴重損壞的城鎮格爾居克(Gölçük)之後,決定再也不回位於伊斯坦布爾的家了。他住到了自己認為建築建構更穩固的希爾頓酒店中。直到後來,他發現它也不夠安全,於是又開始在外面打發日子,通過手機處理所有事務,在街上跑來跑去,好像他忙得不可開交。聽説他這樣匆忙地,馬不停蹄地跑來跑去的時候,嘴裏還總是喃喃自語,“為什麼我們不離開這座城市?為什麼我們不離開?”這種感覺壓在我們所有人心頭,儘管第一次地震震中位於距離城市62英里的地方,還是有成千上萬的伊斯坦布爾人喪生於此,這使大量住在危險地區的人開始逃亡,導致房租下跌。但是,還有很多伊斯坦布爾人仍在它危險的建築中生存,毫不採取防範措施。在這點上,所有一切——科學家們的再三要求,比較可信的傳聞,遺忘的行為,千禧慶典的推遲,戀人的擁抱,大量的人辭職——都使人們開始接受,地震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有助於我們“與之共存”,就像人們今天説的那樣。某天,一位年輕的、剛剛結婚的、非常樂觀的女士來到我辦公室討論一本書的封面設計,她非常自信地和我談及自己應對地震的辦法。**“你知道,地震是不可預料的,是這個讓你感到恐懼。”**她説着,揚起眉毛,“可同時,你必須每時每刻都得像覺得此刻不會有地震發生似的活着,否則,你就什麼也做不了。這兩種矛盾的想法總在鬥爭,比方説,現在我們都知道,地震後站在陽台上是很危險的。可即便如此,我現在還是要站在陽台上。”她用一種老師的口吻説,然後,小心地、慢慢地打開門,走到了陽台上。我站在原地,她站在那裏,看着街對面的清真寺和後面博斯普魯斯的景緻。“站在這裏,”幾秒鐘後,隔着打開的門,她更加滔滔不絕地説,“我絕對不會相信,地震會恰巧就在這一刻來臨。因為如果這麼認為,我就會怕得絕不敢站在這裏。”又過了一會兒,她從陽台走回來,關上身後的門。“看,那就是我做的,”她説,帶着微弱的笑意,“走上陽台,身在彼處的時候,我就在心裏取得了戰勝地震的小小勝利。就是這些小小的勝利,使我們會戰勝即將到來的大地震。”她走之後,我來到陽台,欣賞着宣禮塔、伊斯坦布爾以及在晨曦中浮現出的博斯普魯斯美景。我的整個一生都在此度過。看到那個在街頭隅隅而行的人,我不禁問自己同樣的問題:為什麼人們不能夠離開此地。那是因為,我無法想像,不生活在伊斯坦布爾,會是什麼模樣。

△圖源網絡 | 加拉太塔,登上塔頂,可以遠眺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金角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