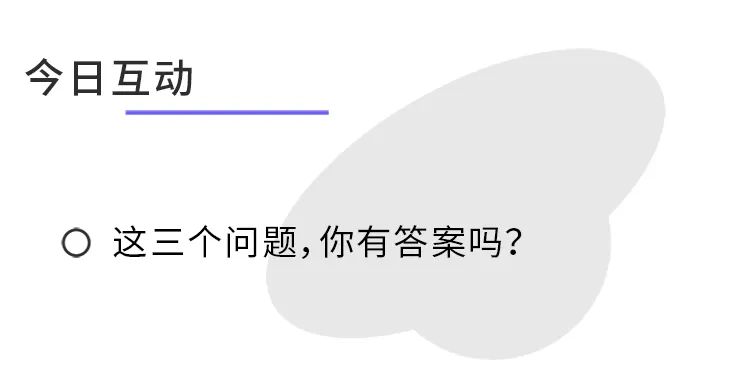《狂飆》收官,我們有三個問題想問安欣,也想問問大家——_風聞
KnowYourself-KnowYourself官方账号-泛心理科普与服务,美好生活从了解自我开始。02-08 10:06
撰文 / 盧舫
專業支持 / A.R.小點點
編輯 / KY主創們
《狂飆》播完好幾天了,人們從不同角度切入,解讀反派主角高啓強。卻似乎少有人書寫另一個主角,安欣。
大家説劇本對安欣的塑造太片面了,在道德上毫無瑕疵,永遠秉持絕對的正義。但為了堅持這絕對的正義,安欣付出了近乎悲情的代價 ——
放棄愛人、終身未婚,從被表彰的刑警變成邊緣的宣傳科科長,才40來歲,就滿頭華髮。
何至於此?值得嗎?人們不禁想問。付出了這麼多,甚至都沒有誰要寫你(不是)。
和看高啓強時總想要分析他不同,看安欣時,我們更多的是有問題想問他,其實這些問題,也是想問我們自己。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些平常沒有什麼機會問出口、也很難找到答案的問題。
「特級劇透預警」
第一問:正義是不是意味着,
永遠做正確的事情?
年輕的安欣,會認同這個説法。他幾乎沒有做過錯事。
不能對罪惡忍氣吞聲,他就當着所有人的面正面剛大Boss趙立冬;不能對疑點視而不見,即使是和自己感情頗深的師傅死了,他第一反應,也是對師傅的身份徹查到底。
甚至只是小小的一件事情,比如在送心儀對象去機場的過程中違反交通規則時,即使交警給他破例放行了,他也堅持要按照規定,把車留下,讓心儀對象上了別人的車去機場。

安欣堅持做正確的事,但每件事好像都不往他想要的方向發展。先是師傅離世、自己曾保護過的高啓強走上歪路,然後自己出生入死的好搭檔悲壯犧牲,自己的愛人也另嫁他人。
他本人呢?手臂受重傷,抓搶都抓不穩;被調到交警隊,再被調往公安局的宣傳科,無法再為自己心中的正義繼續奮鬥;到了四十多歲,孑然一身,無親無故,只有滿頭白髮。
付出瞭如此多代價,壞人卻始終未能繩之以法。
要知道安欣其實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有一個養父安長林,和一個親如養父的孟德海叔叔,全都身居高位。
劇中有一個真正的普通人,叫做譚思言,他是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公務員,秉持着安欣式的絕對正義,用收集材料、實名寫舉報信的途徑,想對抗黑勢力。他的結局是,出場了兩集後,屍體就和高速公路的混凝土融在一起。
似乎要實現百分百的正義,需要很大的資本和運氣。譚思言沒有,於是他結局悲慘;安欣有,但還是屢撞南牆。
意識到這一點,可能是安欣後來選擇忍氣吞聲、蟄伏十數年的原因。十數年裏,高啓強、趙立冬依然在為非作歹,但安欣卻默不作聲,兩耳不聞。顯然,這段日子並不輕鬆。安欣從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警官,變成一個暮氣沉沉的白髮中年。
我們很難想象他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多少糾結、灰心、以及自我説服,導演沒有過多展現安欣備受煎熬的過程,卻讓他那一頭白髮無聲透露。
無論如何,和年輕時不一樣,安欣沒那麼執着於“正確”了。這一次對“正確”的拋棄,卻讓自己在15年後等到了懲治罪惡的最佳時機——指導組的強勢參與。也許,實現正義,不需要一直正確。
第二問:
救壞人和追求正義衝突嗎?
很多人看完《狂飆》後,反而希望反派高啓強能夠做大做強。人們對反派的喜愛,也引來一些“三觀不正”的指責。
喜歡和同情壞人,和追求正義有衝突嗎?這個問題,安欣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這位正義使者,屢次對壞人流露出同情,甚至不惜拯救他們。
先是險些斷送了自己的手臂,救了十秒鐘之前還想置自己於死地的黑社會小頭目瘋驢子 ——

然後又在同僚想要羞辱高啓強時,幫高啓強解圍 ——

後來還給高啓強的兒子輸血 ——

高啓強最終落網後,安欣來探望這個自己對付了二十年的死敵,帶來了一份餃子,與高啓強相視落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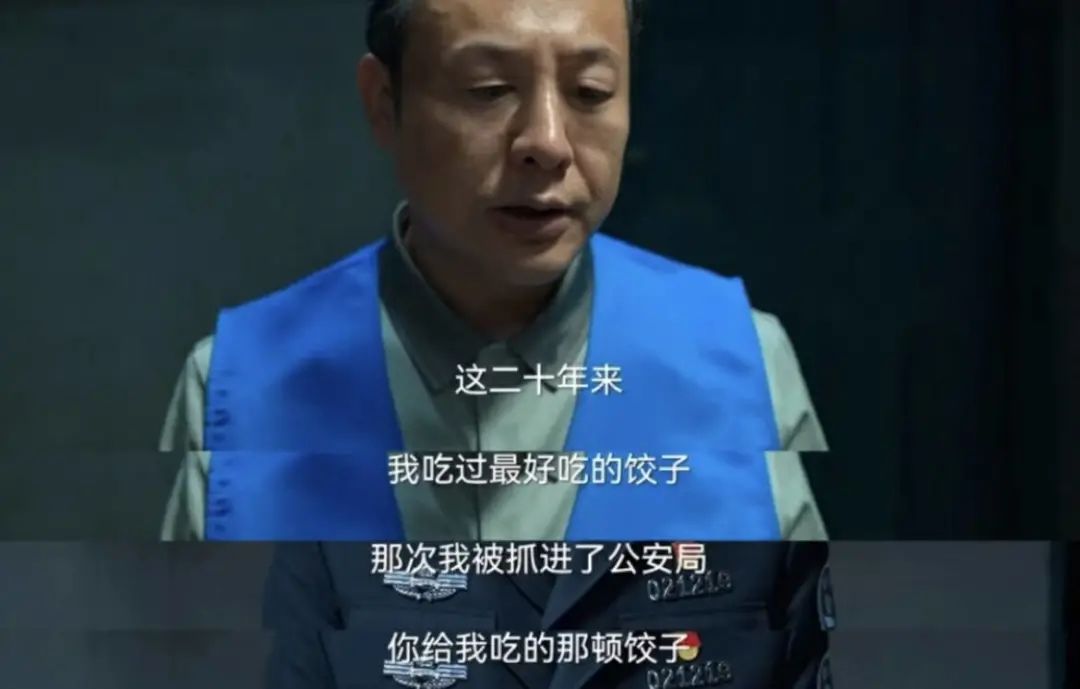

高啓強曾説安欣太善良,對付不了壞人。其實在安欣眼裏,也許沒有所謂“壞人”,只有“有罪的人”。
心理學上,有一個詞語,叫做“人格面具”。人們以一種“回應外部世界”的方式來活着,帶上“人格面具”,表演出不同的樣子,來追求他人尊重。
高啓強、瘋驢子等人,都是出身卑微的人,暴力與罪惡,讓他們獲得未曾有過的尊重和地位。而在罪惡的面具下面,安欣可以看見一個自卑、渴望生存、甚至對身邊人有着愛和關懷的普通人。
當他們陷入極端的困境時,罪惡的面具落下,露出脆弱而平凡的靈魂,那是安欣真正要拯救的東西。
大家對《狂飆》的誇獎,所謂把人物拍得立體,其實説的,也正是不僅描繪了反派臉上的罪惡面具,而且還刻畫了面具底下,反派們更真實的、更隱秘的面孔。
所以,同情和拯救一個脆弱的普通人,又有什麼錯呢?而讓安欣這樣一個正義的符號,擁有同情“壞人”的情結,可能這也是導演向觀眾的一次發問 ——
“正義的對立面是壞人嗎?還是讓人看起來像壞人的罪惡,以及讓人不得不與罪惡捆綁的環境?”
第三問:
完全犧牲個人的幸福
**來堅持正義,**值得嗎?
不知道是不是導演有意為之,劇中多數主要角色都有在家中的畫面,唯獨安欣沒有。
這彷彿是安欣人生的一個隱喻:一無所有,只求正義。他為了不讓壞人抓住自己的任何軟肋,拒絕了自己喜歡多年的青梅竹馬,一生未婚。
在《狂飆》的大結局裏,安欣心中的正義算是實現了,高啓強、趙立冬悉數落網,反派們一個都沒跑掉。
但是,看似大團圓結局的背後,有一些對話,卻值得玩味。
在趙立冬被抓之前,他和多年來同流合污的助手王秘書有這樣一段對話 ——

趙立冬口中,京海發展迅速的20年,正是他和高啓強等人官商勾結、無法無天的二十年。
安欣堅守着“讓京海變好”的願望,苦行僧一般地堅持二十年,終於得償所願,回頭看卻發現,敵人尚在的二十年,京海的經濟也得到了發展。
趙立冬可能是在為自己申訴的一句話,卻無意中讓安欣的苦苦堅持看起來平添了一分“徒勞”的陰影。
而讓人更覺安欣徒勞的,是最後,安欣與指導組組長在烈士墓前的對話 ——


當自己為一樁罪案拼搏二十年,一頭黑髮都變白後,想獲得一個自己消滅了罪惡的認可,卻被告知沒有罪惡的社會只存在理想中,這盆冷水有多冷,只有安欣自己知道。
罪惡倒下,會有新的罪惡崛起。用一生實現的正義夢想,在歷史的長河中看,可能只是徒勞的浪花,但自己卻為此付出了一生。
所以,到底值得嗎?
我猜安欣還是會回答“值得”。
趙立冬口中的“發展”,事實上只是純粹的高樓林立、經濟前進,但法治與道德上的破壞,是璀璨的霓虹燈所無法裝點的。那是唯利是圖者的“變好”,不是理想主義者的“變好”。
孤立地看,一個人維護正義的努力可能是徒勞,而把這份努力放入社會環境裏,正義才更有意義。社會心理學家認為,當自己對一件事需要採取什麼行動感到迷茫時,人們會傾向於參考他人的行為,這個過程叫做對情景的社會性定義(Kane, 2018)。
有趣的是,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本來有助人、利他的願望,但由於旁觀者在場、或者旁人沒有這麼做,ta們可能會變得羞於做好事。
因此,安欣的行為裏有比打擊罪惡更大的意義:不斷地讓更多人願意用更光明、更正向的方式,讓社會變得更公平公正。
罪惡是被推上山後會不斷再落下來的石頭,安欣的堅持,會喚來更多西西弗斯。
或許大多數人都不會真的想成為安欣,但還有那一小部分選擇這麼做的人,不該被定義為“軸”和“笨”。

KY作者説:
我們終其一生,可能都不會像安欣那樣面對如此極端的罪惡。
但這部劇依然讓我產生了對現實的思考:像安欣一樣擁有正義感的普通人,如何才能更“聰明”地維護內心的價值觀呢?
即使我們無需面對大是大非,但生活中依然時時會有衝擊價值觀的時刻。
生活裏的這些瑣碎的小是小非,其實不見得比劇中的故事簡單,許多時候,我們可能也要被迫面對自己無法改變眼前的現實,甚至需要忍氣吞聲、隨波逐流。這意味着我們背叛了自己的價值觀嗎?
我想起心理學上有個説法,叫做“人格靈活性”。它可以理解為一種當我們面對外界環境刺激時保持自我意識(sense of self)、整合自我的能力。無論在什麼處境中,當我們具有更高的人格靈活性,我們就能夠恰當地應對和處理這些外界刺激。
(公眾號主頁回覆關鍵詞“靈活”,看看人格靈活性到底是什麼意思。)
即使有時候無法對抗外界,也能讓心中的價值觀不至於被摧毀。
現實是複雜的,擁有更靈活、複雜的內心,是與現實斡旋的更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