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該脱掉她的絲綢手套_風聞
伍麦叶的熏笼精-作家,文化学者-02-16 19:47
(接上節)
第一章第二節
中國應該脱掉她的絲綢手套
中東精英對中國的奇異觀點引着我開始盡力搜尋更多的媒體,注意各家媒體的看法。
我找到了阿聯酋、沙特、黎巴嫩、巴林、科威特的幾家報紙與網絡媒體,以及埃及的《金字塔報》,還有伊朗的阿語媒體。儘管我找到的媒體集中在海灣國家,但這些媒體的作者來自阿拉伯各國,如埃及、摩洛哥、毛里求斯的學者作家都會出現,另外,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精英也像自家人一樣,經常發聲,尤其以土耳其官員和學者最是常客,半島等媒體都有開專欄的土耳其常駐作者。不僅如此,由於信仰的聯接,還有來自東南亞、中亞的聲音。
在這樣的景觀下,可以説,到二〇二〇年夏季,至少在中東媒體上,認為“中國必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導者”的一派大獲全勝,從那個季節一直到我開始寫本書,中東媒體的基調是這樣的:
“中國必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王者” ——實際上這是我們這裏能夠接受的表述,中東媒體上並不是這樣的説法,而是遠為激烈——已然成了前提,所有的作者都在這一前提之下展開討論。並不是説所有人都對中國持肯定觀點。很多作者依然堅信美國及其象徵的價值體系,可謂“親美派”;一些人對中國極其惡毒,是明確的“反華派”;更多的人是在把美國及其象徵的價值體系當做信仰的情況下,心情矛盾,觀點混亂。但是,即使親美派與反華派,也是在“中國如果不是一定也是多半會成為新的世界女主”[i]的前提下發表觀點。
也有一些學者,堅信美國統治的國際秩序不會動搖、中國不會取代美國。中東媒體為了表示貫徹言論自由、支持觀點多元,也會讓這些觀點得到表達,但是,明顯能感覺到,這類觀點,無論是媒體人員,還是讀者和觀眾,都不喜歡。
很有代表性的是半島電視台阿語頻道的主持人們,尤以《針鋒相對》黃金主持人為典型,為了達成“理中客”,他們一定會邀請持正反兩方觀點的嘉賓參與爭論,但是,節目中,主持人往往明確流露出看好中國的立場,把話題向這個方向引導。

《針鋒相對》金牌主持人法西勒·卡西姆
需明白的是,這種觀點,不能完全算是中東世界的原創。
那裏的媒體遭當代西方右派的意見徹底籠罩,掌握了媒體的中東精英在説法上與歐美右派精英同步,或者説亦步亦趨。西方右派大小權威們的文章,《外交事務》、《政策》、《世界報》等發表的長文,凡是關於中國而中東媒體認為重要的,都會盡快引進,而且,從本地作者們的反應來看,他們從來不會懷疑那些西方舶來的觀點。
但,中東媒體及其作者們並不是機械地照搬,而是會按照他們設定的中東人的利益,對那些西方來的觀點加以改造,或者説,加以利用。
中東精英羣體不僅是採信了“中國威脅論”,而且簡直是歡迎這種觀念。西方各路高人但凡圍繞該觀念發厥詞,他們都特別有興趣。不過,他們自有關注點:
那會對中東有怎樣的影響?
即使最堅定的親美派,也不得不承認,美國在中東搞得一塌糊塗。於是,整個中東天天聽着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暗自琢磨:如果美國真的被一個新的“大國”搞掉,如果真有一個新的大國領導世界,中東也並不會更糟。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後,讓陷在泥沼中的中東忽然看到了巨大的希望,於是,渴望中國取代美國,就成了壓倒性的意見。不僅親美派,就是反華派,也無法放棄現代化發展的機遇,於是他們的言説便十分混亂。
問題在於,中東的學者、作家,除了極少數左派,全部用徹底的帝國主義思維看待這一形勢。他們的思維,與西方右派的帝國主義思維完全一致,這也讓我驚訝地感覺到,在當代西方文明中,帝國主義思維,或説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不僅僅是西方思想的主流,而且很可能就是西方文明的意識形態自身。
帝國主義思維在西方人的意識中如此樹大根深,也是促使我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實際上,我認為,控制着西方人意識的,並不是理性的、由利益驅動的帝國主義思維,而是盲目的、信仰性的“帝國神教”和“帝國神話”,以一個超驗的、形而上學式的“帝國”概念為神。
中東精英與西方右派、中間派精英一道,在帝國主義思維裏來回轉圈兒,運行得十分圓滿,簡直可説是天衣無縫。
這也讓我逐漸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傳統,中國革命建立的一整套意識形態,連同中國傳統文明的思想體系,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個特例。
表現之一就是,中東精英(只有極少數左派除外。下文不再特意聲明)既然重視中國,便也試圖直接閲讀中國方面的主張。但是,就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那樣清楚簡單的綱領,他們都理解不能。一切中國方面發佈的文件,他們是每個字兒都認識,但是連到一起就是讀不懂。於是,他們的文章總是,先介紹一段中國的主張,包括引述部分原文,然後,就直接回到帝國主義思維中,展開的討論與前面引述的主張毫無關係。
在帝國主義思維控制下,中東人便十分相信“修昔底德陷阱”,幾年來,那裏的媒體上持續着無獎競猜活動,帶着種看大戲的興奮:中美是必有一戰嗎?哪一方主動開火?在哪裏開打?會是什麼形式?結局如何?——不過一位朋友繼在朋友們討論時指出,那並不是無獎競猜,猜對了還是猜錯了,可能關乎到中東人一家一國的命運。
中東精英就像西方精英一樣,意識不到:一家強權一定要做霸主,並且一定要靠戰爭成為霸主,一定要打垮另一家強權,所以強權之間一定會發生戰爭,這一套假設,並不是人類歷史的唯一法則,而只是帝國主義思維產生的幻覺,是帝國神教的簡陋教義。——且不爭論大國強權的定義,在強行假設對立的兩方當中,只要一方意志堅決、策略巧妙,仗就打不起來;至少,不是好萊塢電影式的簡單粗暴的雙方直接對轟。
換言之,歐洲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不是人類法則的結果,而是帝國主義的結果,並且也是帝國神教狂熱的結果。
由於中國人完全不懂那一套帝國神教的教義,所以,凡是聽我説起中東人坐等中美開戰,朋友們都浮起茫然的表情,有種“人在家中坐,鍋從天上來”的冤枉感。
最觸目驚心的,是那些狂熱看好中國的中東精英,姑且稱之為“擁華派”。他們中有些人對美國極度不滿,讓人誤以為他們是左派,但是,他們卻是用帝國主義思維去理解、解釋中國的崛起,而且非常亢奮。常駐中國的巴勒斯坦記者阿里·阿布·馬裏黑爾巧妙利用阿拉伯語構詞法,把taseinunan——“被中國化”一詞加了個前綴mu,構造了一個新名詞mutseinunan——“被中國化的人們”,用於諷刺那一派人士,意譯大致可翻成“精神中國人”。
這一派人士最鮮明地證明了帝國主義思維的完整與自足,那套思維像是包在一套硬殼兒裏,絲毫不給其他思路滲透的可能性。
近年,黎巴嫩陷入了致命危機,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沙特背景的英語大報《阿拉伯新聞報》發表了一篇報道《輪到中國影響黎巴嫩了嗎?》,九月九日,半島阿語官網上了一篇長文分析《中國在黎巴嫩——擁有貝魯特的解決方案嗎?》,竟不約而同暗示,中國會強勢接管黎巴嫩,而那也是黎巴嫩唯一的生路,能讓黎巴嫩轉危為安,享受到現代化建設的紅利。文中不僅用了帝國主義邏輯,還採用一種霸道的、決絕的語調——帝國主義者的語調。半島那篇有道是:
“總而言之,北京認識到了形勢變化是何等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地平線發生了修正,足以讓黎巴嫩成為中國的投資項目。”
該文出於一位巴勒斯坦記者的手筆,也是讓人嘆息。
出於好奇,我藉助互聯網的便利,開始搜索中東媒體以往的報道,結果發現,早在若干年前,中東就把中國當做一個強國,期待它對世界發揮一個強國“應該”發揮的作用。
阿聯酋的阿語報紙《海灣報》官網上,有二〇一〇年十月的一篇文章《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嗎?》**,**作者阿布杜哈辛·沙阿班是伊拉克學者、思想家和作家,當時為設在貝魯特的非暴力與人權大學的副校長,關注的領域包括現代化、啓蒙、文化批判、公民社會等。該文是向阿拉伯讀者介紹那一年在北京舉辦的一次中阿論壇,沙阿班瞭解中國的真實情況,文章一上來就説:
“首先,我們應該瞭解,在中國,一九四九年,偉大領袖毛澤東(原文如此)的革命取得勝利,只是千里路程的第一步。”
然而文中稍後竟出現了這樣一個比喻:“(中國應該)放棄她一直試圖憑之而表現的絲綢手套。”而且同一比喻用了兩次:
“前海灣合作委員會主席特派大使、也是這次會議的組織者之一阿卜杜拉則指出,中國通過確定其在國際層面的角色,參與制定合適的決策機制,而主動承擔起責任,具有必要性;應該採用脱掉絲綢手套的行動型外交,與之同步的,是為維護經濟利益而發掘其軍事力量。”
我被那個比喻裏藴含的暴力寓意震驚了,眼前馬上浮起一位制服光鮮筆挺、傲慢冷漠的白人軍官脱掉雪白手套打人的形象——一位英國紳士毆打一位中國苦力,或者一位德國軍官毆打一位波蘭勞工。
作為從小接受“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如何受西方帝國主義侮辱欺壓”教育的我,完全不能接受這個比喻。
可是該文不僅認為那是個恰當的比喻,反而提出了中東精英的集體疑問:
“作為大使的優素福·阿爾哈桑博士恰恰向與會者提出了一個前提性的問題,他説:也許,首先必須知道中國是否有興趣在世界上扮演類似的領導者角色?”
這篇報道讓人驀地回憶起,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互聯網興起之前,科威特就對中國發出過類似的聲音,那時是通過《參考消息》看到,因為顯得太過突兀和新鮮,所以始終記憶猶新。
而到了二〇二〇年,在中東,這樣一種觀點已經相當普及了:
中國出於自身利益必須“介入”、“干預”中東,它也有責任那樣做。而介入,還不僅限於出兵敍利亞解決一時的“叛亂”,而是包括派軍隊到中東駐軍。
聽我轉述這種觀點,朋友們又是一律驚異到有半分鐘表情空白。
很顯然,如此的動作根本不在中國考慮之內,於是,中東輿論場上竟是一片不滿,以及道德譴責:
她不願意,她沒有那個慾望,她對世界缺乏責任感,她只關心從中東獲取利益,而樂得讓美國用軍事力量去維護中東秩序。
早在二〇一〇年的《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嗎?》中,甚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科威特媒體上,類似的表達其實已經出現,只不過更為温和,只是責備和提示:
“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也不能放棄其角色,因為它在經濟和財富上的力量賦予其絕非小可的制衡能力,應該開始保護市場和穩定,保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裁軍和消除霸權主義,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而這一切會達成一個目標,那就是讓出口技術和進口石油的平台得以擴容,尤其是在中東,從而達成在穩定的條件下(從阿拉伯和伊朗)將近七〇%的進口,以及民族、人民和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和友好關係。
這就是中國在目前情況下,作為一個先進的發展中國家,以其具體情況、特殊性、以及在國際和人道主義方面的關係,可以所成之是。”
這段論述可以説代表了很多貌似左派的中東知識分子、一部分中間派甚至右派中東知識分子的奇怪態度:一方面,他們擁有那些進步觀念,和平,消除霸權主義(裏面隱含着對美國和西方霸權的反感),國家間平等,等等,另一方面,卻認定帝國主義方式可以達到目的,而且也只有帝國主義方式能夠達到目的。
本來,我以為,中東媒體上此般思潮的原因很簡單:蘇東解體後,再經過九一一事件,西方右翼反動思想瘋狂回潮,帶着新的內容,新的慾望,以及新發明的理論,向全世界氾濫。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半島一檔質量極高的欄目《電影紀事》上了一期節目:《沙漠、女人與血——好萊塢如何在電影中表現阿拉伯》。視頻分析性地展示,好萊塢電影中,阿拉伯是如何的刻板化、如何的負面。不過,其中有個片段特意談到,從阿拉伯世界走出了一位明星,奧馬爾·沙里夫,在好萊塢和歐洲都獲得了極大成功。過程中,我覺得聽到旁白介紹,這位明星出演過關於成吉思汗的一部電影。可是,看對應的畫面,他置身其中的那部電影,從服裝到環境,和成吉思汗實在是沒有一點兒關係,倒像是一部沒有左輪槍的西部片。我聽力又不行,反覆聽,就是覺得聽到了“成吉思汗”一詞,但是無奈聽不懂更多,看着畫面又狐疑,只得作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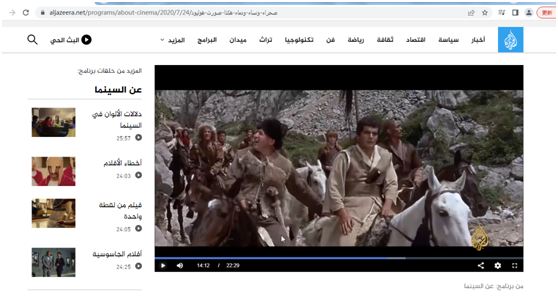
這畫面怎麼能讓我相信聽懂了裏面説的是奧馬爾沙里夫拍了部關於成吉思汗的電影呢?此刻的劇情是:青年酋長鐵木真遵循“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的精神,率年輕部落剛要走出瓦罕走廊,忽然看到前面的中國三人使團,驚呆了。右一的青年即為男主角鐵木真,未來的成吉思汗。
不過,重新看到童年時通過《梅耶林》初識的昔日明星,再加上新培養起的對阿拉伯世界的興趣,便觸起閒情柔如草了。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很幸運地,撞見電影博主“不良多瓦”在微博上介紹一部一九六五年的彩色大片《成吉思汗,征服者王子》。無法形容第一眼看到影片截圖時的感覺,下面的眾多留言表達了中國人一致的反應,基本是反感,討厭,怒斥西方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也有嘲笑。

不良多瓦推送給微博羣眾的電影截圖,別提多辣眼睛——對咱中國人來説。
不過,是奧馬爾·沙里夫扮演主角成吉思汗!
那時,我實際上已經忘記了《電影紀事》中的那個片段。只是出於某種敏感,我想:
既然是從阿拉伯世界走出的大明星,《電影紀事》的節目裏對他評價又那麼高,那麼,可能中東世界一直有人出於對他的興趣,而看那部老電影——就像中國永遠有觀眾,而且是一批又一批的年輕觀眾,會看尊龍主演的《末代皇帝》一樣。
於是我決定下載影片看一看。
頭一遍看,非常驚訝,又覺得好笑,又覺得荒唐,又被其中的很多精緻細節打動。
説起來你可能不信,這部影片和我的趣味是一致的,都是醉心清朝工藝美術那種紋樣繁瑣堆砌、顏色華麗又細碎的風格。
不過,重要的是,這部電影中宣傳的很多觀點,與我在中東媒體上撞見的各種嚴肅的政論,有微妙的一致;當今中東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呈現,與半個世紀之前這部好萊塢“歷史大片”裏對“中華帝國”的呈現,更是驚人地完全吻合。
為什麼近六十年前的一部西方商業娛樂電影,與經歷了那麼多動盪之後的中東媒體,在觀念上,有那麼多的一致?為什麼都展現了同樣的“中國”?
於是我決定分析這部電影,分析——電影裏的觀念,與中東媒體上的觀念,二者之間的關係。
本以為寫兩三篇文章就結束,沒想到開始了一項越伸展越長的工程。
電影裏宣傳的觀念,中東媒體上的觀念,西方知識界的觀念,三者互相映照,讓我不斷髮現更多的、以前從來沒有想到的思想現象,乃至精神現象。
這部電影的內容提供了一個限定的論述對象,讓我們可以把對中東媒體與西方知識界的觀察都限定在一個主題上——
那二者,以及電影本身,如何言説中國,展示中國。
也就是説,電影裏,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此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集中分析西方與中東如何理解“中國”,以及,可能有哪些因素決定了西方與中東製造它們的那一“理解”。
在這一番分析中,中國只是被西方與中東想象、被定義、被言説的“物”,是被動的“它者”,真實的中國恰恰缺席,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恰恰遭噤聲。至於原因,書中會試圖給一些解釋。
不過,由於中國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我們中國獨樹一幟的歷史經驗與思想傳統,同西方與中東的思路形成強烈對照,我也會適當引入我們中國人的觀點,以照清形勢。
最初,我只是覺得那一“跨文化”的現象很新鮮,因為恰恰是我們中國人完全沒有意識到,在世界上,流行的是怎樣的“中國史觀”。沒想到,在公號上嘻嘻哈哈當講笑話一樣寫了幾篇分析之後,好友植女建議,我應該寫成一本書。幾乎同時,繼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並且此後一再鼓勵我;櫻也每當我打退堂鼓的時候,就給我打氣,告訴我,展開研究是有意義的。
對如此嚴肅的課題,我是沒有理論準備的,也沒精力為這個話題再大量去讀理論書以提高能力。我只能在現有的水平上,把我觀察到的加以描述,再盡我能做些分析。
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我就覺得自己及格了:
使朋友們認識到,西方打造並引導全世界人民信受奉行的一套通俗“中國史觀”,與真實的中國歷史毫無關係,與我們中國自先秦以來的歷史敍事,也毫無關係。
而西方推銷中國史觀的目的之一也在於,將真實的中國歷史,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中國歷史,無論是古代史還是近代革命史,儘量封堵在國境之內,企圖使中國的聲音出不了國門。
[i]阿拉伯語裏,只有伊拉克等五個阿拉伯國家屬於陽性,其他國家包括俄美法英德全部為陰性,一旦稱某國為世界之主,便是賽義達特——女主人,行文中也一律用第三人稱陰性單數,她。所以,在阿語裏,世界王座之爭是一羣大女主打羣架互毆的羣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