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版“李子柒”:走紅10年,房子沒了_風聞
最人物-最人物官方账号-记录最真实的人物,品味最温暖的人间03-14 13:30
作者 | 三伏
來源 | 最人物

阡陌交錯,雞犬相聞;春花秋月,芳草萋萋;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
在媒體的渲染下,類似“李子柒式”的田園隱居生活勾動着在鋼鐵森林中那些不安的心,流於表面的美好也引起了陣陣迴音。
種地開荒,建造實驗。蚊蟲叮咬,蟑螂相伴。
這是唐冠華的“隱居”——早在還沒有互聯網喧囂浪潮的2010年,唐冠華就帶着他的睡袋躲進了位於青島的嶗山。
2014年前後,他被媒體吹捧為“隱居打造桃花源的先鋒戰士”,登上了電視台,連國外媒體都為他做過採訪。
但相比於“隱居”這一詞的寬泛含義,唐冠華更願意將自己山裏的生活描述成一場“生存實驗”。
他給這裏取名為“自給自足實驗室”:蓋房子、種菜、挑水、做實驗,他甚至還造了一個自行車發電機。
他告訴筆者,這是“家園計劃”的第一步。
在他的描述中,“家園計劃”像一個理想國。這將是與城市完全並行的、健康交流的另一片土地,有完善的醫療、教育和生產規劃。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聚在這裏,互相扶持,相伴終生。
而現實殘酷,在第15個年頭,“家園計劃“無家可歸。
唐冠華向筆者講述這些時,2023年的春天已經悄然而至,百花開始綻放,曾經的“家園”卻一度荒蕪。
一批又一批人夢碎于田園淨土,而逃離大城市的人依然不絕如縷。
田園將蕪,胡不歸?
只是,在這樣一個商品社會、物質時代,吾誰與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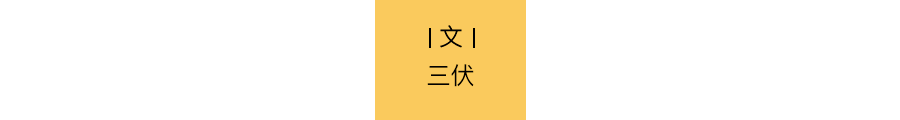

2010年,山東青島,嶗山的清涼澗來了個“奇怪”的年輕人。
他帶着一隻睡袋,鑽進了一個破房子,一住就是幾個月,還準備在旁邊的地上再蓋個房——只是他看上去就不是專業人士,敲敲打打了好些天,房子的雛形也沒見着。
來往的村民們好奇,問他來這做什麼,怎麼不僱個人來幹這些活。
年輕人笑了笑,開口是親切的青島話:“沒事,我邊學邊幹。”
村民們又納悶了,該不會是有錢人來體驗生活吧,遂旁敲側擊,還有人摸進去,把這座破房子看了一圈。
最後得出結論:乾乾淨淨,窮鬼一個。

彼時唐冠華租住的房子
山中村民淳樸,憐惜之心頓起,看年輕人過得拮据,偶然來送點菜,問他有沒有收入來源。
年輕人又笑了笑:“我花得少,吃得也少。”
村民們抬眼一看,這年輕人整天窩在破房子裏敲敲打打,要不就到處撿些“破爛”,衣服也沒見換幾身,確實也沒見花錢的地方。
看得多了,也就熟視無睹了。
幾個月之後,陸陸續續有人上山一起蓋房。兩年半過去了,一座由輕鋼、木頭、竹子、布匹,以及足足1.5萬個飲料瓶組成的房子,竟然真的蓋成了。
與此同時,山上也出現了媒體的長槍短炮,突然間,這小屋談笑有鴻儒,往來也有白丁了。
等到報紙賣到了村裏,村民們才知道,這年輕人一聲不響,成了名人——
所以這唐冠華,到底何許人也。

唐冠華在嶗山修建的房子
被媒體關注,唐冠華似乎早有準備。
他在一篇文章裏寫道:“我來到世間,就是要獲得影響力,要有名,要引發社會的爭議。
“有影響力、有名氣,我的作為才能被世人知曉,得到更多的支持,以為社會做出更多貢獻。社會在不斷爭議、不停反思中,才有進步的可能。
“雖然這將面臨繁重的工作,但只有這樣,犧牲才有價值,才可以為後代留下堅實的前車之鑑。”
他將這次在山上的生活定義為一場實驗,還給住所起了個名字:“自給自足實驗室”。
顧名思義,他的目的就是:探索人類能否擺脱金錢的束縛的可能性,實現自給自足。
在他原本的計劃裏,一切都要從零開始。
只是,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自給自足實驗室”
剛上山的那幾天,因為沒有鍋,地裏種的菜也趕不上收成,他吃的是生食,“看有什麼生的東西可以吃,其實非常多,水果都可以生吃,蔬菜裏黃瓜、生菜甚至白菜都可以直接生吃,就靠吃這些東西來過渡”。
那菜是如何得來的呢?唐冠華的回答是村民送的。
隨後,唐冠華的“自給自足實驗”漸入正軌,卻也意外頻發。
首先是技術上的難題。
唐冠華並不是通俗意義上的工科男,在那個流媒體視頻還未得到普及的年代,他想要製作一些生活工具,主要途徑只能來源於“搜索”。
“就是在網上查資料,會得到好多答案,我需要重新做好幾遍才能找到一個正確的。”
他因此受過傷,失敗的次數也要遠遠高於成功的瞬間。
比如焊接金屬時,為了能更清楚地觀看熔點細節,在沒有預算購置優質防護面罩的情況下,他只能用眼睛直視火光,最後弄得眼睛通紅,流眼淚流了一個多周。
他形容自己:既是“小白鼠”,又是“實驗員”。
再比如,他急需做一口鍋,滿足自己吃熟食的需要,但鍋怎麼也做不好,他只好從外面找來一口別人不用的舊鍋,“至少能夠有一個温飽的狀態,再去做一個個的研究,研究出來這個鍋之後再替代上”。

唐冠華設計製作的自行車發電機
其次是人員的配備,他意識到,一個人是遠遠不夠的。
獨自上山兩個月之後,唐冠華在網上發佈了“招募令”,尋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來做這項實驗,效果顯著。
先後有2000多名志願者來到這裏,其中也包括唐冠華的妻子邢振。
唐冠華與邢振在幾年前相識,彼時邢振的父親是位藝術家,與唐冠華更早結識,隨後兩個年輕人締結緣分。
在唐冠華上山之後的那段時間,邢振時不時會來探訪他的實驗進程,也是確認丈夫對這件事的態度是否認真——2011年,在唐冠華獨自上山一年之後,邢振決定放棄自己在城市的工作,追隨他一起踏進了這場實驗。
在一篇夫妻共同接受的訪談中,邢振提到過自己父母對她這個選擇的支持:“媽媽在我辭職的時候,説了一句讓我印象很深的話,‘太好了!我的女兒可以去過她想要的生活了,這也是我年輕時想過而沒敢做的。’”

志願者們在“自給自足實驗室”
家人的支持讓唐冠華再無後顧之憂,他對筆者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連續提到了一個詞語:“急切”。
“我需要證明這件事能行,因為我在網上查資料,沒發現有人做成這些事兒,只有一些國外電影(展示過),國內要不就是在終南山隱居,苦哈哈的,實現不了一個比較舒適又能自給自足的生活,所以我就想,如果我能實現一個樣本,大家就能夠從過去的下沉生活中走出來。”
他還告訴筆者,這只是“家園計劃”的第一步。

唐冠華在嶗山

“家園計劃”出現在唐冠華的腦海中,是在2008年。
彼時他只有19歲,已經工作多年。
在唐冠華的敍述中,他與所謂的主流觀念始終有些水土不服,當筆者問他是否與他遊離的童年有關時,他沒有否認。

唐冠華
1989年,他出生在山東青島。
他講到自己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沒有再寫過作業——學校里老師不管他,父母離異之後,也有些顧不上他。
唐冠華是跟着祖輩長大的,在爺爺奶奶家住一年,再去姥爺姥姥家住一年。
雙方老人截然不同的生活觀念,無形中引導了他第一次有關“共識”的思考,他説:“就比方説我奶奶家這邊是一個月才洗一次澡,但我姥姥那邊一天要洗兩次澡,他們就説對方是錯的。到底哪邊是正確的,在當時還困擾了我一段時間。”
後來他想,或許本就沒有對與錯吧,“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他們是有一種共識的,對於他們來説,共識能夠讓他們生活下去,組成一個自己的家庭或者社區,這就是一個共識社區,他們就可以可持續的運行——當然基礎是你不能去影響和傷害其他人”。
上了初中之後,唐冠華被陰差陽錯地划進了青島市最好的中學,升學率穩居前列,素質教育也熱火朝天。學校裏應聲開辦了有關機器人編程的興趣小組,唐冠華眼前一亮。
有人告訴他,這個興趣玩好了,要是能獲獎,可以保送高中。
他一聽,乾脆課也不上了,整天泡在興趣小組裏,於是,當保送的訊息變成烏龍,結果就顯而易見。
他落榜了。
沒考上高中,父親告訴唐冠華,要不然你想辦法創業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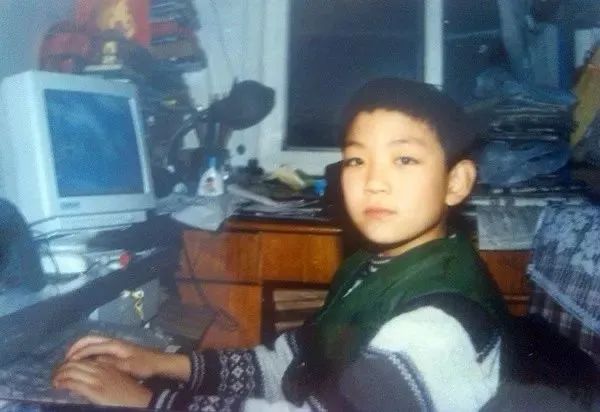
兒時唐冠華
根據唐冠華描述,他的父親曾是個詩人,後來下海經商,彼時在給企業做管理顧問。
他給唐冠華買來一些書籍,唐冠華至今對書名還有印象:“什麼17歲,什麼百萬富翁,什麼總裁,就説你看這個,這也是條路。”
似乎一切都有跡可循,唐冠華走上了創業的路,那一年,他只有16歲。
他開了一家小型的廣告設計工作室,卑躬屈膝的“乙方”做久了,內心想要表達的慾望也就越燃越烈。
偶然間,他接觸到了一種名為“觀念攝影”的藝術形式,“就是通過計算機做一些後期的特效處理,把想象中的畫面塑造出來。”唐冠華解釋道。
又能表達自己的觀念,還能通過後期的收藏等活動產生一定的收入,唐冠華因此入了行。也因為“觀念攝影”,他結識了一圈玩藝術的朋友。
2008年,19歲的唐冠華在青島美術館對面租下了一間房子,開了一個名為“館子”的藝術空間。
“只要想在青島做一些創作,我就接待他們,提供住宿,還有一些吃的東西。”
天南海北的創作者匯聚到這裏,各顯神通:有的創作文字,有的從事畫畫,有的人想要拍攝一個電影……但無一例外,都沒有錢——連住賓館的錢都沒有。

唐冠華於青島創辦的“館子”藝術空間
窮困潦倒的他們在“館子”的院子裏開辦了一場場小型演出,燃燒着一份份懷才不遇的夢想。
唐冠華看着他們,越來越感受到當下社會的荒謬與割裂,有些心事,就在這間小小的院子裏醖釀。
他想到了之前去過的澳門賭城,只要有錢,就可以“購買其他人的尊嚴”,“把錢變成一個無所不能的東西,大家為了獲得它,趨之若鶩”。
他開始越發清晰地感覺到:一些事情,不太對。

也是在2008年,因為一次探親的機會,19歲的唐冠華去到了日本。
日本的城市化與人羣的麻木性讓他難以忍受。
他走在街上,看到每個人都長着一張相似的臉,“這裏的人們隨時有可能爆笑,隨時有可能肅穆起來,有的人臉上時常呈現一種火山爆發前任何方式無法驚擾到的寧靜安詳,似乎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們有房子、有花園,但沒有個人時間,花園幾乎荒廢。他們有工作、講禮貌,但更像是浮於表面,競爭的暗流在私下裏湧動。

唐冠華在日本期間
在日本期間,唐冠華寫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用了很大篇幅敍述“電流與燈泡”、“貨幣與交換”、“道家”、“粒子”等等複雜高深的名詞,最後得出結論:生態是平衡的,資源是有限的,人類社會需要改變。
他洋洋灑灑寫下了自己的計劃,展開了對未來的種種想象,並闡明瞭自己的目標——
既然金錢支配着城市裏人類的生活,他就要以自我為試驗對象,“自主開始對私人生存能源的實踐和計劃,重點根據衣食住行四個方面提出並且加以驗證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簡單來説,就是他想要驗證,金錢不是生活的必需條件。
他給這篇文章起名《家園》,在文章的最後,他寫:“家園終將還給所有本該屬於人的權利和良知”。
回國之後,他開始踐行這個計劃,後來,他將腦海裏的規劃加以完善,命名為“家園計劃”,共分為三步:
第一步,用5年時間,實現自給自足的生活。
第二步,用 20年時間,吸引一定數量的人在一起生活,分擔生活中的必要工作,形成社區。
第三步,讓家園與城市形成良性的、健康的交流對話,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唐冠華
至於為什麼第一步計劃只有5年?因為嶗山的房子唐冠華只租了5年。
在這五年裏,他收留接待的流浪者、揹包客數以百計,來往的媒體更是數不勝數,作為主人公參與拍攝的海內外紀錄片十餘部,還受到了國際影展的提名。
他在採訪裏表示,自己已經完成了生活上70%的自給自足,是時候進入到下一階段了。
於是,他有意識地向前來採訪的媒體透露,2015年之後要找一塊更大的地,讓更多的人一起生活。
在媒體的密切關注下,這個願望很快得到實現。

“自給自足實驗室”中手工製作的生活用品
2015年10月,在一家基金會的幫助下,他們一行人來到了福州市閩侯縣關中村,基金會授權唐冠華可以以“實驗”的名義使用一塊位於村裏的,面積約500畝的土地。
唐冠華與同行者就這片土地未來的發展展開了討論與規劃,在這個階段,他們有意識地放棄了“自給自足”生活理念的必需性,更想要達成所有社區居民的“共識”。
三個月後,其中七、八個人決定留下來,共同建設社區,他們給這個社區概念起名為“共識社區”——一羣有共識的人共同組建的反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正式的稱呼是“南部生活共識社區試驗”(以下簡稱南部社區)。
這一年,唐冠華僅僅26歲。

2015年,共識社區的部分成員合影
最前方為唐冠華

試驗的開始,聽上去比較順利。
2016年,在社區正式建立的第一個年頭,唐冠華累計接待了上百位慕名而來的訪客,儘管最後能長期留下來的人屈指可數。
離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多是因為“失望”。
唐冠華告訴筆者,他們在傳播時會特意提到這裏並不是“世外桃源”,這裏就是“建築工地”,但還是擋不住有些人就是抱着逃離城市的避難態度,迎面撞上這裏的毒蟲與荒涼。
“落差感是必然的。”唐冠華説:“因為這個地方我們在建設,到處都是廢墟一樣的地方。我們甚至吃飯都沒個正八經的地方,每個人都很忙碌,誰也顧不上,所以説這根本就不是想象的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安居樂業需要你創造,可能十年以後才行。”

南部社區的活動現場
此外,要想變成南部社區的“居民”,也需要一定的門檻。
社區的創始人唐冠華對訪客沒有身份與年齡上的限制,但要想變成所謂的“居民”,則需要該人在社區裏累計生活超過一年,才有資格提出社區居民身份申請。成為“居民”就有了對社區建設的責任與義務:“要參與表決,參與決策,投入一些公共資金……”
所以,儘管這裏人來人往,生活在此的長期居民最多也不超過十人。
2018年是唐冠華口中南部社區的“高光時刻”,“達到了最融洽的社區氛圍,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社區價值”。
所有人各司其職,不再需要溝通分配工作:有人負責蓋房,有人喜歡種地,有人在搞教育活動,地裏有成熟的、可供食用的莊稼,山上有搭建完成的、充滿藝術感的穹頂房屋。
居民們彼此瞭解與愛護,有許多對戀人在南部社區定情——甚至在去年,還有孩子在這裏降世。唐冠華形容彼此是“沒有血緣的家人”。

唐冠華等人在南部社區建造的穹頂屋
有網友在網絡上分享去到社區生活的感受:“這裏確實沒有任何人來充當指揮者的角色。我需要依據自己的興趣去安排每一天。當然也可以選擇去協助其他夥伴,參與他們的勞動,但更多的情況下,還是需要我自己來發揮創造力。”
當然,沒有創造力似乎也沒有關係。
比如在這位網友到達社區的下午,就有居民説要在公共空間——當地廢棄的半成品房屋——的五樓做一個天台酒吧。
幾根粗糙的破木條隨性地架在一起,就是窗户;麻布胡亂地掛在牆上,就是壁紙;原來髒到海綿都漏出來的破沙發被套上布套,就是酒吧裏最温暖的座位。
看上去,城市的內卷、競爭、攀比等負面情緒在這裏得到了消解,但矛盾依舊肉眼可見。

唐冠華(右一)與社區居民在酒吧
因為素質教育的特殊意義,社區裏的孩子一般要去村裏的小學上學,儘管社區裏開辦了織布課、音樂課等多種特色課程,但這些課程更像是主流觀念裏的課外拓展——事實上,確實會有附近學校組織學生來此學習體驗,社區內也經常會組織給村子裏的留守兒童上課。
“那如何解決生病就醫問題呢?”筆者問。
“社區內就醫還做不到,但我們離醫院很近,我們也有了解針灸和中草藥知識的人,一般的情況下,我們自己會用一些中醫的方式——大家也都比較尊重這種中醫的方式,但是如果骨折了,或者是負傷了,我們也還是會去旁邊醫院搞一下。”唐冠華碎碎念着,隨即又補充道:“我當然希望教育、醫療、養老全在社區內解決,我很期待有這樣的社區,我想創造,因為我沒找到……”
只是,意外遠比創造更早到來。

社區內的暑期課堂
2018年,他們突然被告知南部社區所使用的土地屬於一類耕地,上面的所有建築在法律意義上不被允許,他們被迫停止修建。
那天之後,他們被迫撤到村中,租住在村民的房子裏,思考接下來的前路。
2022年,資助他們的基金會資金短缺,土地被村委會收回,土地上的建築被拆除。
許多常住居民因此離開,其中包括唐冠華本人。
“家園計劃”至此,無家可歸。
從2008年唐冠華執筆那篇《家園》開始,這個著名的計劃走到了第15年,倒在了寒冬中。
理想、家園、家人、感情,很多東西他依舊在苦苦尋覓,但有些東西,他也確實無能為力了。

唐冠華親手拆除建築

2023年3月,輾轉多地之後,唐冠華來到了雲南昆明的大墨雨村。
這是一個有些特殊的村子。
大墨雨村本是昆明西山區的一個傳統彝族村落,據資料顯示,隨着城市化的進程,約有70%的本地村民外遷,這裏一度成為“空心村”。
近些年來,有許多新村民來到此處,對當地民居進行改建,據唐冠華介紹,目前該村子裏,將近有一、二百人都是遷居於此的新村民。
新居民中有建築師、藝術家、軟件工程師等等,大多在這裏實踐着“半農半X”的生活理念——一邊進行簡單的農業種植,一邊根據各自特長開展着手工工坊、民宿餐廳、自然教育等各種活動。
這裏是理想的過渡地。這也是唐冠華選擇來到這裏的原因。
“我的考慮就是得找一個可能在發展中的社區,它有一定的潛力。如果讓我重新創造一個社區也可以,就是挺難找到一個合適穩定的土地,在國內,我覺得幾乎是非常難了。”而如今的大墨雨村人才濟濟,唐冠華企圖在這裏找到志同道合的好友,繼續他的“家園計劃”。

唐冠華
但與以往相比,他的“家園計劃”似乎又有了些變化——他將自己的計劃重心轉移到了為“少數人羣”發聲的領域,在他看來,這也是“家園計劃”的理念之一,殊途同歸。
“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從小就不同的,他們是獨立的,有獨立思想的,一出生就決定的,城市不培養這樣的人,城市淹沒這樣的人。”他在一部紀錄片裏説到。

“家園計劃”曾幫助跨性別者“大喜哥”出版書籍
上圖為“大喜哥”參加“家園計劃”活動
十五年前,唐冠華給“家園計劃”起了一個英文名字:anotherland,中文直譯是“另一片土地”。
他告訴筆者,對應着目前已有的這片土地,“家園計劃”要做的事情就要一直去開拓在已有的空間之外的,其他的生活選擇。
“它是一個持續的工作,沒有止境。”
他如此告訴筆者,又似乎在告訴自己。
此外,如今34歲的他,也坦率地説道:“我現在怕是買不起一張車票……”
他最想要的,或許還是那張通往夢想的車票。




圖一、二:唐冠華在青島“自給自足實驗室”
圖三、四:唐冠華在福州“南部社區”
唐冠華向筆者講述這些時,2023年的春天已經悄然而至,百花開始綻放,曾經的“家園”卻一度荒蕪。
一批又一批人夢碎于田園淨土,而逃離大城市的人依然不絕如縷。
田園將蕪,胡不歸?
只是,吾誰與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