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家暴的女人,逃不出這個小鎮_風聞
最人物-最人物官方账号-记录最真实的人物,品味最温暖的人间03-20 08:09
作者 | 阿爾莎
來源 | 最人物

同一片土地,相隔十幾公里,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一個是易小荷熟悉的現代化世界。這裏有追求經濟和精神獨立的女性朋友,有圖書館、便利店等現代城市基礎設施。在她的故鄉四川省自貢市區,夫妻吵架時,絕不動手打女人。
一個是依照古老法則運行的“彼世界”仙市鎮。這裏多數人沒聽説過女性主義,部分人近幾年才知道什麼是家暴。書店、影院、網約車,小鎮統統沒有。不少我們以為的普世規則,在此也不通行。
兩年前,易小荷有“預謀”地闖入了第二個世界,試圖打撈被遺落在小鎮的女人。
從17歲的少女到90歲的老嫗,每段經歷都稱得上驚心。她們勤勞、善良、能幹,同時忍受着伴侶的出軌、暴力或遊手好閒。可幾乎沒有人離婚,也沒人離開小鎮。
小鎮之外,還有許多的她們。
她們也是我們。


2021年夏天,四川省自貢市仙市鎮的麻將館裏,人們紛紛猜測着新搬來的異鄉女人的身份。
這個面積僅有55平方公里的小鎮,住了4萬多人。在這裏,短居一兩天的遊客常見,長租的外來人幾乎沒有。按當地人的説法,“劃一根火柴的功夫就能在鎮上轉一圈”。

仙市鎮
空降的異鄉人易小荷,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她和小鎮的所有女人都不同,獨自前來,沒帶孩子、丈夫,看起來不用工作、勞動,不燒火做飯,時常下館子。這裏唯一的娛樂——打麻將,她也不會。
細碎的流言最終拼出一個有錢有閒的女人:在這裏有三四套房子,是某高官的夫人。
易小荷啼笑皆非。不久前,她創業失敗,決定回老家,找一個沒人認識自己的小鎮,休息一段時間。沒人認識她,以上流言和打聽都無需理會。
她目的明確,想寫一本書,主人公是家鄉里不被關注的小鎮基層女性。
因此,鎮裏的人好奇打量她的同時,她也驚訝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抵達鎮子的第一天,易小荷發現,仙鎮的男性像消失了一樣。男人要工作,女人也要工作。可工作之外,洗衣做飯、照顧孩子老人,甚至重物搬運,所有家務天然屬於女人。

女人的揹簍裏,裝滿重物
打着茶館幌子的麻將館,是男人們最常聚集的地方,女人則總在忙。每個飯館、超市、美甲店裏,不管有沒有客人,易小荷總能找到看店營業的老闆娘。每天去不同餐館吃飯,就能從不同女人那兒收集到小鎮不同的八卦。
比起寫書,挑戰多來自生活本身。沒有外來人的小鎮,她托熟人找住宿的房子用了一兩週。隨後是作息,婆婆們早上6點多就開始説話。川蜀一帶,山多路遠,人們嗓門都大,小鎮房子又不隔音,易小荷也只能跟着起牀。
起牀後,首要問題是吃飯。快節奏的城市生活裏,她需要咖啡提神。而這裏的早上,永遠是冒着紅油的抄手。
書店,圖書館,健身房,咖啡館,電影院,跑腿、網約車,這裏都沒有。
“鎮上除了鎮政府,小學,中學和幾家幼兒園,擁有兩個大超市和4~5家便利店似的小超市,一家賣牀單被套的店。一家無名化妝品店。一家喪葬用品店,一個美甲店,若干家飯店,若干家茶館麻將館,幾個快遞點還有三家理髮店,一個從名字到菜單都很像A貨肯德基的漢堡店,三家説是糖水飲料也可以的奶茶店。一個小麻雀似的診所。還有一個大的衞生院。”易小荷寫道。

沒有圖書館和書店的小鎮,唯一可見的是小人書和實用書。
像JK·羅琳一樣坐在咖啡館邊聊天邊寫作的想法,宣告破產。
易小荷租下的二層臨河小樓,據説是鎮上最好的房子。可入住第一週的半夜,她就聽見屋頂上萬馬奔騰的聲音,可能是老鼠或者別的什麼。
她學會了和拳頭大的八腳蜘蛛在同一個屋檐下和平共處,習慣了逢三六九趕集背上竹簍。
適應這一切,對於易小荷來説不算什麼。早在20歲出頭,她就單槍匹馬去美國採訪,吃不到中餐,沒有駕照和電話,照樣生活。“不會有比那更難熬的日子,何況這裏是家鄉。”
適應之後,小鎮生活成了易小荷最輕鬆的一段時間。早上六點多起牀,上午去陳婆婆那坐坐,跟王大孃聊聊天。飯後去朋友那串門或一起散步。晚上六點多,太陽落山,小鎮就空了。回屋看會書,早早入睡,等第二天一大早被女人們響亮的交談聲吵醒。
每天下午是女人們固定的麻將時間,沒人願意聊天,她實在學不會,索性換上瑜伽服,在家裏做幾組帕梅拉。
下雨了,就去河邊看看漲潮的河水是什麼樣子。傍晚散步,去寺廟聽聽晚鐘。每天溜溜達達地過着,假日悠長。

易小荷在鹽鎮
易小荷問過鎮上許多人同一個問題,尤其是年過50的,他們都確認日子越過越好了。書店、咖啡館或小酒館或健身房,對他們來説不是生活所需,沒人覺得吃飽喝足之後,還應該有點兒別的什麼需求。因此,那些東西在此地也完全沒有市場。
他們打發時間的方式,還是那簡單幾樣。年輕男人在茶館打牌,年長者和女性坐在鎮口的黃葛樹下,看雲、看河、聽風、聽知了叫,都是一天。
空蕩的小鎮,陽光發白,時間凝滯一般,緩慢流淌,人人表情閒散,似乎並無他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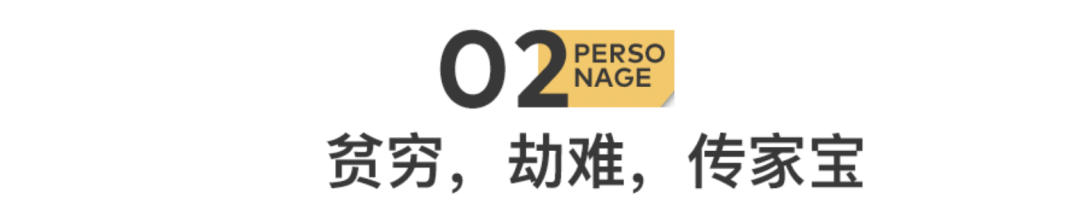
在這裏,苦難最尋常,且往復輪迴。
王大孃36歲時,結婚14年,仍不知道捱打這種行為叫家庭暴力,是違法的。
如今年過六旬,王大孃還會因為幾斤羊肉的誤會,被丈夫孫彈匠滿鎮子追着打。她記不清捱過多少次打,“隨便亂説的,五百多次肯定有了……”
鎮上的老鄰居,幾乎都見過落在王大孃身上的拳頭和耳光。青紫常見,有時,手也被打斷。打得最狠的一次,王大孃吐出口血,一口氣跑到觀音閣,求菩薩庇佑。可晚上八點後,她又摸黑回家,繼續洗之前沒洗完的衣服。
過往幾十年總是如此,被打後,她一邊哭,一邊繼續幹活。
她曾試圖求救,鄰居、婦聯主任推説這是家庭糾紛。她想過輕生,婆婆勸她,把兩個娃盤好才對。
易小荷發現,王大孃不是個例,幾乎每三户人家就有兩户存在家暴,這裏的男人沒有傳説中的粑耳朵(怕老婆),都是家暴的參與者或旁觀者。
可王大孃在鎮上還有另一重身份,最受歡迎的媒婆。夫妻吵架,她勸女人不要離婚:“一定要找個家。”
這片土地的規則是,男人家暴、賭博、遊手好閒……都可以容忍,可以被原諒,但離婚會被千夫所指。

仙市鎮上,男人與女人
鍾傳英年輕時,因前夫不思進取,主動選擇離婚。分開後,她回孃家被父親打,在古鎮被差點被女人們的唾沫星子淹死。年齡大的女人當面指着她的鼻子罵她。
她曾經不在乎那些指指點點。
二婚後,有人告訴她現任丈夫和誰誰在一起,她回:“很正常,殺豬匠都有(別的女人)。”她不再輕言離婚二字,怕被指着脊樑議論。
婚姻之外,貧窮和次生劫難如影隨形。
50元的書本費,生病的母親,都會導致一個成績優異的女孩徹底告別學校。梁曉清小學讀了一學期後,父親要她休學,理由是看過風水,家裏出不了讀書人。
90歲獨居的陳婆婆有6個子女,攢了四套房子,但她依舊一人住在小店裏,偶爾要隔壁餐館客人的剩飯,撿別人放太久而扔掉的豬兒粑小吃。夜裏,她睡在幾張椅子搭就的鋪上,始終沒有一張屬於自己的牀。
89歲時,陳婆婆生病住院,第一次躺着不用幹活,吃得還比原來好一點。她覺得這就已經算活夠本了。

陳婆婆説話時,一隻眼睛會流下渾濁的眼淚。
錯失的人生機遇,無休止的家暴,從肚子裏扯出的胎兒……回憶往事時,小鎮的女人們往往面色如常,她們眼神平靜地坐在那,張嘴講出一部驚心動魄的血淚史,卻又隨時準備着起身照顧孩子、招呼客人或忙別的家務。
有時,易小荷會看到女人長久地坐在木板凳上,一動不動盯着手機。女人的身邊,是舉着單反,拍台階、曇花、貓狗的年輕遊客。
後來她寫道:“貧窮和劫難,是家家户户的傳家寶”。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馬克思的這句話,印在高一的政治課本里,如果讀過高中,一定能熟練背誦。後來,它轉化為那句沒讀過高中也能聽懂的:“經濟獨立是人格獨立的前提。”
可在小鎮裏,這似乎是句空話。經濟獨立,只是經濟獨立。
陳婆婆是仙市鎮許多人心中公認的女強人,她做過各種小生意,樂於投入。白手起家,為三個兒子攢下了四套房子。
如今,她仍一人獨居在店鋪裏。店裏沒有廁所,最親近的兒子,每天去幫她倒一次尿桶。沒人給她做飯,老人都是隨便吃點。另一個兒子每天騎車經過,從不停下打個招呼。
別人送她的米麪、牛奶,她全部賣了換錢。只有屋子裏那桶充滿油漬的硬幣,她找不到孩子幫她擦。最後,易小荷陪她做完了清洗的工作。
王大孃配合老公彈棉花之餘,經營着茶水鋪,賣過菜,還成了遠近聞名的媒婆,有償撮合。可在家裏,丈夫不允許她穿短過膝蓋以上的裙子。她和朋友跨出仙市鎮一步,都需要丈夫同意。

仙市鎮,揹着揹簍的女人隨處可見
獸醫店、服裝店、理髮店、麻將館以及鎮上唯一一家美甲店,許多是這些被家暴、被壓迫女性們的生意。其中,唯一且熱鬧的美甲店,是梁曉清開的。
一年級被迫休學起,她一直在自救。
小時候,她捧着新華字典和故事書自學識字。十歲左右,她跟着朋友去三年級教室玩,面對老師的考題,自學的她,答得比其他同學都快。
梁曉清報班學習畫眉、做眉技術時,都是一次成功。當年去北京參加美妝會,老師主動邀請她留下。她心動不已,卻又一次回到了小鎮。
這些年,她不止一次拒絕了離開的機會。梁曉清的第一份工作可以申請一家人住的宿舍,她興奮回家,讓母親收拾東西,一起離開。母親卻哭着留下。
繼續在一起,爸媽的爭吵和打架也必然繼續下去,可梁曉清的母親自認為承受不起離婚後要面對的流言蜚語。“到那時候女的背的罪更多。”
如果她離仙市鎮太遠,母親一個人在家,可能又會受委屈,被父親打。梁曉清就再不願離開家,她要留下來,守護她的母親。

留在仙市鎮的梁曉清
許多女性因類似的原因留在仙市。
決心離開要考慮父母的贍養、孩子的轉學和學費問題,跨城搬家的費用,照顧孩子的時間。小鎮女性生活的本位是家庭,是孩子,離開是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複雜抉擇。
於是,在上海做到火鍋店店長的女孩回到仙市生孩子,本該留在北京的美甲師回小鎮開店。從早到夜不停轉的女人,忙着生意、孩子、家務,以及替無所事事的丈夫收拾一個又一個爛攤子。
留下的梁曉清,有時也會疑惑。她們村裏有個年輕女人,每年農忙時,總獨自一人下田做所有苦力活,丈夫從未出現過。農忙後,她又出去打工,賺錢回家,買車,開店。她的男人什麼也不幹,靠女人的錢活着,在深夜喊着有錢真好,但還打女人。而村裏的人,反而在背後叫女人坐枱女,極盡嘲諷。
梁曉清想:為什麼?憑什麼?
她還想不通,媽媽為什麼不離開家裏那個人?
她不知道,仙市鎮之外的地方,有許多人有着和她類似的疑惑:梁曉清為什麼不離開這裏?她會離開嗎?為什麼她還要這樣活着?

來仙市鎮之前,易小荷在上海,在北京,在紐約,她發現城市之間有一點已經很共通,女性的聲音越來越大,她們追求自由,而不僅僅是經濟獨立。。
那些年間,她的朋友多是精英、白領、律所負責人或某某大中華地區總裁,她們聊女性觀念,時事熱點,社會現象,互相推薦某本書裏的某個觀點。煩惱多是如何在行業裏更領先一步。
對那時的易小荷而言,她面臨的女性困境,是在職業上受到的性別歧視。哪怕已經是行業最好的記者,別人介紹時,永遠要加一個美女或者性別的標籤。
第一次見面的知識分子,開口問她:以前採訪過那麼多牛人,喬丹之類的,是不是要跟那些 NBA 球星睡覺?
朋友聚餐,不認識的男人,喝了點酒,居然拍着大腿,讓她坐上去。而周圍的熟人,總自覺形成男性同盟勸解:他跟你開玩笑的。
2017年,易小荷發了篇文章,自述被性騷擾的經歷。朋友圈裏,近一半的女性發來私信,説出曾遭遇的職場性騷擾。
可在仙市鎮,女性主義、中年危機,都是陌生的詞組。她們面前是更具體的困境,不被丈夫打,孩子有錢上學,有份穩定的工作。這份穩定,只是説她吃得起飯。

鎮上女人,不管做不做生意,都一定要會洗衣、做飯、做家務、照顧孩子。
在小鎮待久了,易小荷理解她們的同時,開始向她們靠攏,好好吃飯,好好寫書,重新理解生活的意義,“我覺得我的心態都變得很謙卑了”。
她意識到,她曾經在某種程度上和鎮上的女人是相通的。自卑,怯懦,沒那麼獨立,自由,以婚姻家庭為唯一目的。
大學剛畢業時,她不管不顧地去到男朋友所在的城市,常以淚洗面,仍一心想要結婚。
後來,她和她們走上了不同的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讀書,父親一直告訴成績不算好的她,要讀書,要考大學,一定要出去,走得很遠。
那份大學學歷讓她在當時找到了離開男朋友的工作,那些讀過的書,讓她有機會從自貢走到北京、上海,美國紐約。如今,她能去到世界上她想去的任何別的城市。
小鎮的女人們本來也有這樣的機會。
陳秀娥高中時,是學校裏公認的好學生,常有滿分作文,還曾投稿《少年文藝》,拿過幾十元的稿費。如今,她的生活以孩子為中心。客廳書架上的《餘秋雨散文》沾滿灰塵。
梁曉清十四五歲時,發現了一個好去處。跳上為郊區開闢的公交,就能去往自貢圖書館,裏面有《十萬個為什麼》《99個生活小竅門》,也有人生道理。
她泡在圖書館裏讀過不少書。有一個故事,她至今能複述出來:家境很差的孩子,靠自己的努力和節儉,讀完高中、大學,還賺了筆錢。
她告訴易小荷,當時沒太看懂那個故事,但一直念念不忘。
如今,當地圖書館的大門都已經常年緊閉,但館裏那個故事的名字她至今記得清楚。《沒有傘的孩子,必須努力奔跑》。

女人背重物的背影

在仙市鎮時,易小荷收到過一張鎮上女性朋友發來的照片。照片裏,月光慘淡,陳家祠發出點點陰冷的光,再遠處就是她居住的房子。

小鎮朋友分享給易小荷的照片
女人平時很少拍什麼,看易小荷平時四處拍,這才有了拍照興致。
照片拍得美極了。下一刻,易小荷忽然意識到:除了我,這種照片她還能發給誰?
無人可發。 這裏的每個人都雙肩沉重,少有交流。
陳婆婆和兒子女兒極少交流,哪怕是一家人團聚的端午,她也一言不發地吃完飯,放下碗就立刻回她的小攤。這裏許許多多女性都覺得,在這鎮上生活並不需要什麼朋友,因為根本不會有人真心誠意幫助你。
在仙市鎮,在鄉村,女人們很難找到能理解她們的朋友的人,也沒人理解她們的痛苦。
反而是易小荷,成為她們共同的聆聽者。之前,從沒有人,聽過她們説這麼多話。聽她們的一生,聽那些苦難、掙扎和困惑。
或許,易小荷也是唯一一個人,聽完會問她們,為什麼不離婚,為什麼不離開。如果是親朋街坊,大概率只會敷衍兩句,算了算了,這麼多年了,不能離啊。
在小鎮生活一年後,易小荷動筆打撈仙市鎮上的女性倖存者,如實寫下她們被忽視、被捶打的一生。她將她們的故事,取名“鹽鎮”。

《鹽鎮》
古時的四川產天下之鹽,仙市也因鹽設鎮。如今的鹽鎮,鹽味也是那些日日勞作的女人眼淚和汗水的滋味。她們的命運就此被“放鹹”。
從17歲的女孩到90歲的老嫗,她們所處時代不同,境遇不同,可同樣經受歧視、暴力,在這鎮上日復一日,無法出逃,又不斷與命運搏鬥。
易小荷將小鎮上的生活又比作一道道裂口:女人們常常在拼命止血,而男人們則在撒鹽。
《鹽鎮》出版後,易小荷通知了書裏的每個人。大家都沒什麼反應。一如當年她想寫她們的故事,女人們就説,你寫吧,從不好奇為什麼,也不覺得自己的生活有任何特別。
她們快速跳過書的話題,又聊回當下:學校的孩子、父母的生活、門店的生意。
每次聊完,易小荷總覺得,他們還是過着原來的生活,看起來沒什麼變化,不是為自己而活,而是在飯館、美甲店從早忙到晚,操心孩子的一切。

鹽鎮老人
但種子或許已經種下。
黃茜40出頭,沒有車,沒有房,沒有存款,卻堅持送孩子去重慶讀一萬六一學期的初中,而不是留在仙市鎮。
梁曉清告訴女兒,以後要像易阿姨這樣,不要那麼早結婚,要懂得自己真正要什麼。她希望孩子是自由的,不會像她一樣,被綁在這裏。
易小荷還在鹽鎮時,曾有小鎮的朋友勸她結婚找個歸宿。
易小荷問:“你覺得你的生活更好,我的生活更好?“
“確實你還挺好的。”
話題輕輕帶過。她再也沒被催過婚。
*圖片均由受訪者和出版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