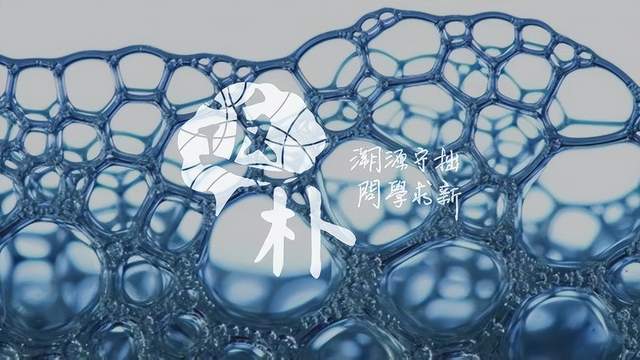抉擇:美國亞裔科學家與玻璃天花板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03-25 09:59
去與留,都有遺憾。遺憾之中,是期待。
撰文 | 洪緯
在華人生物界,幾乎人人皆知吳瑞。他生於北京,21歲時隨父母移民美國,在美國完成了大學和研究生教育,一生在美從事教學和科研。2008年,吳瑞去世時,《科學》雜誌(Science)以 “橋” 為題刊登了訃告,介紹了他於中美之間的橋樑作用。在20世紀80年代,很多生物學專業大學生渴望走出國門,繼續攻讀學位,但是大部人不清楚如何才能獲得入學資格。為此,吳瑞領銜成立了CUSBEA項目 (China-United States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s and Applications) ,在1982到1989年期間,為400多名中國大學生鋪砌了一條留美之路,造就了許多知名科學家。
《橋》也提及了吳瑞於1970年創造引物延伸法用於DNA測序。英國科學家弗雷德裏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正是在此基礎上改進技術,最終獲得了1980年諾貝爾化學獎。作為一位普通讀者,難免心生疑問:吳瑞是不是也應該獲得諾貝爾獎?他是否能夠獲獎,我想大多數人都沒有資格評論,況且,每年諾獎揭曉之後,總歸有許多知名科學家悶悶不樂。但是,憑藉他的貢獻,在一位普通讀者眼裏,我相信很多人——至少華人學者——希望在搜索DNA測序技術發展史的時候或者在生物學相關教科書裏能看見“吳瑞”。然而,罕見!
《科學》2007年刊登了一張關於DNA測序技術演變的巨幅海報,其中也沒有提到吳瑞。79歲高齡的吳瑞就此向《科學》編輯表達了不滿,要求他們將自己的貢獻補充進去。遺憾的是,事未遂人願,沒多久,吳瑞在80週歲之前因病離世。
吳瑞的遭遇不得不讓人聯想到“玻璃天花板”,也就是不公正待遇,説法再極端點就是歧視。
01
玻璃天花板的由來
1882年,美國總統簽署了《排華法案》,併成為《美國法典》的一部分。這項法案將所有華人勞工拒於美國之外長達十年。
現實遠遠比這殘忍。1883年紐約布魯克林大橋開通時,流亡美國的古巴詩人何塞∙馬蒂(José Martí)描繪了前來頂禮膜拜的簇擁人羣。他們來自不同種族和國家,希伯來人輪廓鮮明、目光敏鋭,蘇格蘭人臉色紅潤、身材魁梧,俄羅斯人眼神灼灼。
讀到他形容亞洲人時,我感覺非常不適。同為黃皮膚黑頭髮的亞洲人,緣何日本人優雅,中國人瘦弱而冷漠?他繼續解釋道,中國人是古代世界的不幸之子,是專制社會下的產物,他們的生活不是薰香的香爐,而是令人噁心的鴉片煙。我的憤怒瞬間轉化成悲憫。馬蒂的母國當時正處於為實現共和國進行抗爭的階段,他不過是指桑罵槐,批判專制主義。
在美國的各種政治宣傳海報中,來自清王朝的民眾形象也被徹底妖魔化,表情扭曲、怪異而且陰險。當我將一些19世紀的中國卡通人物展現給一位7歲的亞裔孩子時,在美國出生和成長的她發出了尖叫和反抗的聲音:“他們在侮辱我們!侮辱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牙齒、指甲、長相不是那樣的!”在一些作品中,中國男人還被描繪為具有同性戀傾向,因為相對一些人種,他們汗毛不夠濃密,身形不夠魁梧,看上去手無縛雞之力。
1881年刊於《舊金山黃蜂》上的政治漫畫:《即將到來的人》
儘管我們的先輩們遭受了奇恥大辱,但是“玻璃天花板”一詞並不是亞裔創造的,也不是其它少數族裔創造的。在美國的白人世界裏,女性的社會地位遠遠不如男性。女性到1920年才獲得選舉權,耶魯大學本科學院到1969年才開始招收女生。獲得耶魯大學終身教職的首要兩位女性之一,瑪麗‧博洛夫(Marie Borroff)在1956年博士畢業時持有的工作接受函均來自女子大學。顯然,當時少有男性認可女性有資格站在講台上教育男學生。或許,當他們產生這個想法的時候,他們完全將自己的母親拋之腦後了。
據一位20世紀60年代就讀耶魯大學英語系的女研究生回憶,人類學和英語這兩個領域在當時已經有相當一部分的女性進入研究生院繼續深造。她的同學在芝加哥大學讀人類學,男女生比例均衡,但是沒有女教授。她在耶魯大學英語系,只有博洛夫一位女教授。她的導師直白地問道:“你為什麼要讀這個研究生?” 接着又説,“或許,這對你來説是一個好主意。我們的確需要一個聰明並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當夫人。”
這就是女性當時所處的社會地位。1978年,管理諮詢師瑪麗蓮∙洛登(Marilyn Loden)首次創造了 “玻璃天花板” 一詞。身為女性,她對女性羣體的有限上升空間深有體會。阻礙如同透明玻璃,難以識別,卻又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政府宣佈官員的名單時,只要是女性都會加個 “女” 字,為何?女性太少!每當某位女性成功當選國家重要領導人,全世界都會進行報道,為何?她只是萬綠叢中的那一朵紅!這是數據的神奇魔力,它在昭告天下玻璃天花板的存在。
02
生活在玻璃天花板下的亞裔科學家
到1991年,玻璃天花板的説法被進一步應用到少數族裔,引起了政治上的重視。同年,美國國會頒佈了《玻璃天花板法案》( Glass Ceiling Act of 1991),成立了玻璃天花板委員會。法案旨在消除“提高婦女和少數民族人羣地位”的人為障礙,以及增加“婦女和少數民族人羣晉升到企業的管理和決策職位”的人數。
作為少數族裔,也許深受亞洲傳統文化的影響,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亞裔一般埋頭苦幹,謙虛謹慎。亞裔科學家也往往隱藏起自己得不到重視的境遇,即便公開談論,也常常將歧視歸因於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首位擔任美國大學校長的中國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也曾經表示過,亞裔美國人通常比較謙虛,不會爭辯,甚至在科學問題上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在美國工作和生活,除了掌握豐富的詞彙,還需要擁有一些社交技巧,比如自信和較強的表達能力。那麼,掌握了這些技能是否就暢通無阻了呢?諾貝爾獎獲得者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的太太黃詩厚(Alice Huang)十歲時隨父母舉家移民美國。生性聰穎,熱愛科學的她成為了一位知名微生物學家。1988年,她成為首位擔任紐約大學科學學院院長的亞裔美國人。1989年,她又成為首位擔任美國微生物學家協會主席的亞裔美國人,也是首批領導任何一個美國科學協會的亞裔美國人之一。
在常人眼裏,黃詩厚擁有了一個相當成功的人生。可是,她多次公開表示自己親歷過 “玻璃天花板” ,認為 “精英機構是最糟糕的” 。有一年,她成為了一所大學的三名校長候選人之一。招聘委員會問她將來是否有可能放棄這份職位。她直接回應説他們可能不會給她這個機會,因為她是亞裔。注意,不是因為她是女性!令人詫異的是,委員會成員當中竟然有人點頭默認。
不像非裔美國人,亞裔未曾被要求過坐在公交車後排,但是他們通常感到自己是被邊緣化、被異化或者被壓迫的人羣。我認識一位已故老太太,她曾經常常講述買房時銀行不放貸款,最後是猶太人幫忙的經歷。由於在美國遭遇的種種不快,她對大多數白人缺乏好感。當我與一位接受過良好教育並在美國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亞裔朋友談論此事時,她認為對於老一輩人,語言交流不暢和受教育程度較低是在他們在美國生活的攔路虎。
1992年,記者蘇珊∙米勒(Susan Miller)曾經就 “亞裔科學家的玻璃天花板” 問題採訪了黃詩厚,也採訪了其他華裔。部分亞裔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製造玻璃天花板的人不是別人,而是華人自己,因為文化不同,語言能力和社交技巧低人一等。他們期待生長於美國的下一代亞裔做出突破,而且部分亞裔二代也承認上升阻礙在減少。
03
他們選擇抗爭
亞裔們充滿期待,期待新生力量可以改變世界!意想不到的是,進入世紀之交時,一個事件震撼了亞裔科學家羣體。1999年,來自台灣並已經加入美國籍的李文和,被指控為中國大陸的間諜,竊取了美國核武器的機密,涉及罪名總計59項,被單獨監禁了9個月。
得到這個消息時,許多人驚慌失措。接受調查前,李文和曾經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the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他為提高美國核武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創造了核爆炸的模擬實驗。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從事核武器研究工作的亞裔人數曾經逐步攀升。
經過調查,很顯然,李文和被污衊了。2000年,李文和與美國聯邦政府達成了訴訟協議並被釋放,他承認了一項罪名,其它58項均被撤回。部分亞裔羣體迅速轉變了觀念:李文和事件告訴他們,在美國社會,作為亞裔,僅僅努力工作或者為人低調並不是闖天下的通行證。
來自台灣的Alexander Chao退休前曾在SLAC國家加速器實驗室(原為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工作。李文和事件發生時,他已經步入五十知天命的年紀。他曾經竭力避免政治,避免與當局產生衝突。即使在申請一個完全能勝任的職位卻因華人身份而遭遇失敗時,他都毫無怨言。但是,李文和事件徹底喚醒了他,他為李文和辯護募捐,協同組織舊金山同盟,宣稱李文和及亞裔科學家們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他在一點點地努力,為亞裔們還一個清白之身,不想讓所有的華裔被誤以為是潛在的間諜。
李文和事件也導致申請武器實驗室的亞裔人數減少了將近一半。他們擔驚受怕,疑慮重重。另一方面,李文和事件也將玻璃天花板和薪資不平等等長期存在的事實暴露於公眾面前。《科學》對亞裔人羣做過調查,生物學家饒毅在美國西北大學任職時也做過統計,英年早逝的病毒學家蔣觀德(Kuan-Teh Jeang)在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以下簡稱為NIH)任職時也做過調查。調查對象不同,但是結論皆指向:亞裔在科學界的底層數量龐大,能夠成為領導人物的少之又少。比如,2000年,《科學》對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亞裔人羣做過統計,專業人員(professional staff)中的亞裔佔10%,而在管理層(manager或者supervisor)中,亞裔比例只佔據4%。
當數據呈現給公眾時,每個人的反應不一樣。NIH的邁克爾∙戈特斯曼(Michael Gottesman)開始與蔣觀德和其他三位亞裔科學家討論NIH該如何做得更好。然而,有些人對這類數據卻持有不同的看法。饒毅2005年分別致信ASBMB(美國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和SfN(神經科學學會,Society for Neuroscience)理事會,指出了同一個問題:“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歧視。華裔傾向於保持沉默,部分原因是無人傾聽他們的申訴。但是,這是否就意味着亞裔必須永遠順從呢?”
《科學》記者傑弗裏∙梅維斯(Jeffrey Mervis)就此問題採訪了幾位亞裔研究人員,也採訪了相關組織的資深研究人員。其中,ASBMB理事會成員琳達∙派克(Linda Pike)反應較為激烈,她認為饒毅侮辱了他們,數字不能説明一切。她發出一連串炮轟:“多少人有領導能力?多少人回到他們的祖國?他們有多少人認認真真地考慮留在美國?”她和大部分人一樣也指出了一個共性問題:語言能力不足!這可能直接導致華裔申請基金時失敗,從而在晉級競爭中處於劣勢。華裔內部也存在意見分歧,有人甚至直接指出饒毅等人的觀點有些極端。
儘管公眾看法有分歧,但亞裔科學家的反抗激情一直在燃燒。2007年,温文儒雅的吳瑞在年邁之時也拿起了筆與《科學》爭辯。他的語調温和但堅定,提醒他們將自己的成果放進時間軸上。他承認桑格的突破增加了DNA測序速度,然而關鍵點是,桑格的方法是基於他的工作之上發展起來的。他告訴《科學》:“如果你們同意將我的貢獻加入測序技術演變圖中,你們應該在1970年時加入 ‘吳首次應用引物延伸法進行DNA測序’。” 吳瑞繼續建議,如此一來,介紹1977年,也就是桑格測序法公佈於眾時,就要註明是“發展出DNA快速測序法的時代。”
2014年,亞裔科技史學者麗莎∙翁長( Lisa A. Onaga)還原了吳瑞質疑《科學》雜誌的過程,並詳細展示了吳瑞的工作對於桑格發展出DNA快速測序法的重要性。譬如,吳瑞的博士生將吳瑞測序的關鍵技術教授給桑格,以及吳瑞在1970年到桑格實驗室訪學並與他經常討論DNA相關的研究工作。但是,桑格在1976年以後再也沒有引用吳瑞的文章,即使在1996年的文章裏承認了吳是DNA測序第一人,也指出吳的方法乏味和不具備普適性的缺點。
顯而易見,吳瑞確實在DNA測序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在桑格兩獲諾獎的巨大光環之下,吳瑞的早期研究成果逐漸被世人淡忘了。令人欣慰的是,被譽為實驗室“藍寶書”、由約瑟夫·薩姆布魯克(Joseph Sambrook)和大衞∙羅素(David Russell)主編的《分子克隆實驗指南》(Molecular Cloning: A Laboratory Manual)實驗教材裏提到桑格技術的想法源自於吳瑞。
04
他們選擇離開
進入世紀之交,亞洲經濟飛速發展,高等學府裏的科研條件和環境日趨完善,高新技術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高科技人員的工資待遇不斷提升,許多亞裔留學人員選擇迴歸本土。這種變化在中國尤其明顯。1999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政府實施了各種策略吸引海外人才迴歸。
印裔學者瑪麗∙保羅(Anju Mary Paul)在2022年出版了一本新書,主要研究在海外留學的亞裔科學家的流動問題。由於書寫和出版需要一定的時間,她的研究時段截止在2010年代中期。在她採訪的119名對象中,有52位回到祖國,34位回到亞洲其它國家,33位選擇不再回到亞洲。也就是説,只有三分之一人員繼續留在歐美。
有些人回到出生地,幾乎不需要過渡期。也有人承認,迴歸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適應。還有人甚至感覺沮喪。吳瑞曾經在2004年給《自然》撰文倡議:“中國科研要發展,就必須做出改變”。他提到許多留學生都想回國,但是國內科研環境讓人望而卻步。他還提到中國科研界曾經的流行語:“小資助,大審查;中等資助,小審查;大資助,不審查。”這透露出當時科研審批流程的弊病,也折射出大量科研基金幾乎被“大頭”瓜分、青椒們希望渺茫的現實狀況。
一位台灣學者回到台灣後,對瑪麗講述道:
當你迴歸時,必須容忍,並試着忘記曾經的美好、好的同事,以及美國同事做科學的激情和他們在科學上的奉獻精神。你必須要忘記這些。否則,你的滿意度會下降。你會沮喪。因為你知道還有很多更好的方式去做好事情。但是在這,你不可能那樣做,因為你資格不夠。
美國科學家的激情也讓我一度改變固有的“導師即老闆”的商業式管理的看法。我在美國工作的地方有老中青三代科學家,他們常常和學生一塊做實驗、修理儀器和佈置實驗室。為了避免歸國人員產生類似上述台灣學者的負面情緒,印度和中國正在積極創辦新型研究機構。在這些新興機構裏,研究人員可以營造新的文化研究氛圍,創建新的研究系統互相支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見到成效需要時間,也許十年、二十年,或許更久。
見效需要的時間太長,是一些在美生活已久的亞裔不肯回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他們也不願意再花費大量時間去適應另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已經有家庭的年輕亞裔科學家,大抵是為了孩子而選擇不再回歸。通常,孩子一旦超過十歲,適應一種新的語言、文化和教育體系,就變得相對困難了。從女性發展的角度來看,相對於一些等級制度森嚴的亞洲國家,美國的環境已經相當寬容。瑪麗採訪的一位日本女科學家在本國曾經被導師認為毫無發展前途,卻在美國獲得了重生。她獲得了自信,獲得了認可,最終在美國一所大學獲得了終生教職,實現了夢想。
有時候,美國的玻璃天花板也被帶進了亞洲。新加坡的官方語言是英語,這在吸引國際人才方面相當具有優勢。但是,在對待西方人和亞洲人時,新加坡卻給出了不平等條件,西方人的薪資和福利往往更高。有些進入新加坡的中國人對此相當不滿,最終選擇回到中國大陸。
事實上,職業上升受阻和享有不公正的工資福利待遇只是“玻璃天花板”的一個方面。曾經有學者在2000年嘗試通過“薪資”數據來研究“亞裔教授羣體是否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問題,結論卻模稜兩可。比如説,白人比亞裔擁有更多的途徑漲工資,這可以證明天花板的存在性。但是,如果亞裔參與一些類似委員會的服務性活動,他們的薪水漲幅又比白人高,這似乎又推翻了天花板的存在性。由此可見,數據雖有魔力,卻不能説明一切。亞裔科學家還深受複雜國際關係的干擾,近幾年來,類似李文和事件的鬧劇一直在美國上演,而且越演越烈。
通常人們在回憶歷史時,會有一切都變得越來越好的感覺。可是,回顧“玻璃天花板”的這一長串歷史時,痛苦、憐憫和希望時刻將我團團包圍。我想起了一位研究非裔美國人的知名歷史學者的一句話:“歷史並不總是朝着人人將變得更好的方向發展。”(History is not just about everybody always getting better!)
致謝:何塞∙馬蒂的《布魯克林大橋》原文為西班牙語,感謝翁妙瑋博士的講解。
註釋:文中提到的亞裔,通常指生活在海外並具有亞洲血統的人,而不論國籍,只有 “亞裔美國人”特指具有美國國籍的亞裔。
主要參考文獻
1、T.C.,Why are some scientists unhappy with the Nobel prizes? ,Oct 10th 2013.https://www.economist.com/the-economist-explains/2013/10/10/why-are-some-scientists-unhappy-with-the-nobel-prizes
2、José Martí, El puente de Brooklyn,La América. Nueva York, junio de 1883.https://www.cervantesvirtual.com/obra-visor/en-los-estados-unidos-escenas-norteamericanas--0/html/fef234ce-82b1-11df-acc7-002185ce6064_36.htm。
3、“THE COMING MAN” 1881,https://thomasnastcartoons.com/2014/04/03/the-coming-man-20-may-1881/
4、100 Women: ‘Why I invented the glass ceiling phrase’,https://www.bbc.com/news/world-42026266
5、Johns ML. 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structural, cultural, and organizational barriers preventing women from achieving senior and executive positions. Perspect Health Inf Manag. 2013;10(Winter):1e. Epub 2013 Jan 1. PMID: 23346029; PMCID: PMC3544145.
6、Miller, Susan Katz. “Asian-Americans Bump Against Glass Ceilings.” Science 258, no. 5085 (1992): 1224–28.
7、ANDREW LAWLER,Silent No Longer: ‘Model Minority’ Mobilizes, SCIENCE,10 Nov 2000,Vol 290, Issue 5494,pp. 1072-1077.
8、Onaga, Lisa (2014). “Ray Wu as Fifth Business: De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History of DNA Sequencing.”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C,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46: 1–14.
9、 Anju Mary Paul, Asian Scientists on the Move: Changing Science in a Changing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10、洪緯:綠衣女騎士——記首位耶魯大學最高級別女教授,澎湃私家歷史,2020年9月1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078129
11、Sanger, F. The early days of DNA sequences. Nat Med 7, 267–268 (2001).https://doi.org/10.1038/85389
12、Glass Ceiling Act of 1991,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2nd-congress/house-bill/3353/actions?s=1&r=51
13、Wu R. Making an impact. Nature. 2004 Mar 11;428(6979):206-7. doi: 10.1038/428206a.
本文受科普中國·星空計劃項目扶持
出品:中國科協科普部
監製: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