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我離開央視後的這八年_風聞
熊猫儿-03-26 20:30
採訪、撰文 | 燈燈
站在50歲的當口回頭望,李小萌覺得,她的人生上半場大致可以劃為兩個階段。
2015年以前,她是家喻户曉的央視記者、主持人,報道汶川大地震時掩面而泣的背影,打動了數億觀眾,成為國人對那場災難最柔軟的記憶之一;
2015年年末,她離開央視,在一個新聞節目主持人的黃金年齡,辭職回家帶孩子,由此引發的議論、揣測和好奇,到今天仍在持續。
三八婦女節之後,我在北京東二環的一座寫字樓見到了李小萌。相比過往在新聞節目中呈現的知性、端莊形象,如今的李小萌多了一份明快的生動。她一身運動服,化了淡妝,笑起來會露出可愛的小虎牙,為幹練的氣質添了幾分柔和。我帶給她一束鬱金香作為節日禮物,她喜出望外,“很久沒有收到女生送的鮮花了。”
距離從央視辭職已經過去了八年,李小萌早已有了新身份。她創業做自媒體,有一個20人的小團隊,演講、拍短視頻、直播、寫書都在她的工作範疇內,用她的話來説,“李小萌是一個IP,我就是這個IP的生化載體。”

工作中的李小萌 | 圖源李小萌微博
離開大機構出來單幹,她每天忙得“腳後跟打後腦勺”,聲帶因為用嗓過度長了小息肉,從前乾淨的嗓音變成了有些渾濁的“直播嗓”,但她不想自憐,“都是自己的選擇,這點嗓音的損失算什麼呢?”
前些日子,她出版了新書《你好,我們》。書中,她寫自己從央視離職的來龍去脈,寫44歲重新求職的艱難和殘酷,過往人生中那些羞怯、笨拙和難堪的時刻,被她毫無保留地攤開在讀者面前——如此程度的自我袒露,對於一個公眾人物來説,是罕見的。連她的朋友,都反對她如此向外界自我剖析。
李小萌説,敢於向別人袒露自己,對她來講是一個特別大的成長的標誌。身邊的人也見證了她這些年的變化。合夥人盧俊是李小萌的多年好友,他覺得李小萌如今的生命狀態都不一樣了,“鬆弛了、舒展了、自如了,從一個自我封閉的小萌,變成了一個更開放、不設限的小萌。”
我和李小萌聊了聊她的這八年。在兩個多小時的對話中,我愈發感受到,這不單單是一個全職媽媽如何重返職場的故事,更是一個女性經歷了漫長的束縛、掙扎和自我懷疑後,在50歲的年紀,重塑自我、自由綻放的歷程。
以下根據李小萌的講述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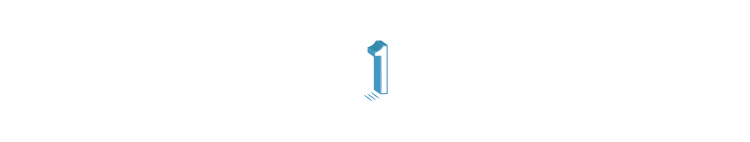
從央視主播到全職媽媽
2015年年底,我從央視辭職後,幾乎所有人都在猜測我為什麼辭職。這個問題直到去年都有人在問,在好奇,甚至在編造謠言。
其實原因很簡單,我找不到適合自己的節目形態了。
以前,我做的大多是訪談節目和現場報道,雖然壓力大,過程中充滿不確定性,但那種身為記者、身處現場、跟人面對面交流給予我的正向反饋,讓我始終有身為新聞工作者的榮耀感。


2008年李小萌深入北川災區報道,路遇善良的災民朱大爺,留下令人動容的一幕 | 圖源網絡
後來,新聞頻道改版,我做的訪談節目《新聞會客廳》關了,《東方時空》也從一個專題類節目變成了整點新聞播報,於是我陷入了一種機械化的工作節奏中——每天穿過長安街,走進辦公室,簡單化個妝,然後熟悉一下稿子。稿子的內容大部分是定好的,而且不許脱稿,必須念提詞器,這讓我感到以己之短搏人之長。
那兩年有一大批新聞人辭職。如今來看,似乎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我的同事張泉靈、趙普、郎永淳也和我在同一年離開了央視,不過他們接下來都有明確的事業方向,我完全沒有,是唯一一個回家當全職媽媽的。
“裸辭”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我小孩的爸爸跟我説,你就踏踏實實回家吧,我不會讓你因為我而後悔的。還有一個原因是,那時,我認為自己是沒有一技之長的人,沒什麼其他的選擇。
有些人會錯把平台當成自己的能力,而我是另一個極端,把自己的能力全部看成是平台的資源。我總覺得,如果沒有電視台和這些新聞事件做支撐,我是沒辦法做成什麼事的。

李小萌主持《新聞1+1》| 圖源網絡
回家後,一開始我給自己安排得特別滿,除了弄孩子,還給自己報了一堆烘焙課、英語課和油畫課,整天拼命健身,拼命節食。結果三個月後,身體吃不消了。有天在家吃飯,吃着吃着,我突然失去意識,身子往一邊歪過去。
我去醫院檢查,報告單顯示,總蛋白低,血壓低,各種指標都低。家裏人問大夫,她這是什麼病啊?大夫説,通俗一點來講,就是營養不良。大家都笑了,説21世紀的中產家庭居然會營養不良,你這是幹嘛呢?
後來我才知道,這其實類似“退休綜合徵”,是一種心理問題。具體表現為辭職、賦閒或者退休後,因為沒辦法自洽,又害怕自己停下來,只能把自己搞得特別忙活。
辭職前,我以為自己的心態會很穩,畢竟路是自己選的,況且我又不是以一事無成的狀態迴歸家庭的,我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主持人這一行最高的獎項我也拿遍了。
但是漸漸地,我能感覺到家裏的氛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以前當主持人的時候,一回家,家人都説,哎喲,寶貝女兒回家了。現在回家了,誰還管你,回來就回來了唄(笑),我好像沒那麼重要了。
還有一部分壓力是我自己給自己的。我不是那種全職以後依舊該花錢就花錢,該臭美就臭美的人。我覺得,既然我不掙錢了,那我就應該少花錢。其實這個想法非常糟糕,因為婚姻意味着收益和義務共擔,夫妻雙方如果有一方在家全職了,另一方的收入也不是個人收入,而是家庭的共同收入。但我“温良恭儉讓”慣了,我會不自覺地約束自己,總有一種不配得感。
有一天,我去幼兒園接女兒,在教室門口無所事事地等孩子下課。正東張西望呢,突然看到一個媽媽,穿着職業裝,風風火火地趕來,到了教室門口,找把椅子一坐,掏出電腦就開始投入地工作。
那個畫面在我腦海中停留了很久很久,久到讓我意識到,我是想念工作的。
女性並不是只有工作才有價值,只是對於我這樣一個身處職場多年、有工作慣性的人來説,迴歸家庭後,照看孩子只佔用了我小一半的精力,我還有一多半的精力無處安放。我迫切地想回到那種有事可做,被團隊和客户需要,能為社會創造價值的狀態裏去。

重返職場,擁抱真實世界
重返職場的路,比我想象中艱難。
從小到大,我一直過得順風順水。小學六年三好學生,保送初中,初中三年三好學生,保送高中,高考以北京地區文化課、專業課雙第一的成績考上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畢業後又直接進入中央電視台工作,一干就是20年。
這種順風順水也意味着,我的人生是相對被動的。大部分時候,我都在被環境和周圍的人推着走,而且結果還不錯。聽從安排、相信權威、努力打工、少操閒心,是我過去的生存哲學。

李小萌主持《新聞會客廳》| 圖源網絡
三年全職媽媽的生活結束,一切都變了。我不再是央視著名主持人,而是一個44歲的、離開職場3年的大齡女性求職者。失去了龐大系統的幫助和庇護,我只能像小馬過河一樣,一點點蹚着水往前走。
如今想來,我特別慶幸的一點是,在家的那段時間,我沒有斷掉和外界的聯繫。既沒有消失在朋友圈,也沒有停止學習。這可能是我們始終要做的人生日課吧。當時的身材和樣子,雖然沒有現在精神,但也不至於走形得太厲害。所以當我想要動身做一些事情的時候,還有朋友願意伸出橄欖枝。
一開始,我做獨立製片人,和東南衞視合作訪談節目《你好,爸爸》。做製片人和做主持人太不一樣了,我不僅要做好採訪和內容,還要負責背後一系列的統籌、商務工作。
起初真的什麼都不懂。東南衞視把合同發過來,我“啪”地在最後一頁把章一蓋,立馬寄了回去。對方打電話來問,小萌,騎縫章呢?我説,什麼騎縫章?對方沉默了。這件事被我的朋友們笑了好久,大家都説,小萌哪像在社會上闖蕩了20多年的人啊,完全是個生意上的小白,連最基本的商業規則都不懂。
邀請嘉賓對我來説也是一個巨大的障礙。以前在電視台做主持人,我只需要把內容準備好,聯絡、邀請嘉賓的工作基本都由編導和策劃完成。那時的我,就是一個老老實實上班的乖孩子,不懂得積累人脈,也不懂得規劃事業。
每次做完採訪,我從不主動和嘉賓合影,也不主動交換聯絡方式。看似清高,實際上就是不自信,總覺得工作都做完了,也沒有必要再聯繫了吧?又擔心萬一被拒絕了怎麼辦?總之就是張不開嘴。
和攝製團隊的磨合更令我頭疼。《你好,爸爸》籌備時,團隊上上下下,除了我,全都是男性。去機房審片,半地下室的房子,站了一屋子名字都叫不全的男人,空氣裏混合着煙味和體味。導演對我態度很好,可不管是拍攝計劃、場地、光線、機位,任何問題只要我有疑問,永遠得不到進一步討論,只有一句“您放心”,説白了就是“你別管”。

李小萌擔任獨立製片人的節目《你好,爸爸》| 圖源網絡
這些困難都是我之前沒有預料到的。但事已至此,我只能硬着頭皮上。
邀請嘉賓,對方拒絕了,那就一次次地磨,飛去他參加節目的現場,當面發出邀請;攝製團隊的佈景有問題,就算還有半小時就要錄製了,也要讓他們拆掉重來;片子質量不過關,即使項目不做了,錢退回給電視台,也不能就這麼糊弄過去。
從慣性地打一份工,到別無選擇開始創業,我的人生也從被動的狀態,轉向了被迫主動。盧俊説,他覺得我之前在央視的生活是高度濾鏡化的,從始至終都被服務、承接、保護得很好,而創業是一個強迫我進入真實世界,並擁抱真實世界的過程。重返職場後,我的第二次生命才真正覺醒。

乖女孩的中年覺醒
創業這幾年,帶給我的改變特別大。
我原先是個特別温順的乖女孩。一部分是天性使然,我媽説,她當年生完我,把我從醫院接回家,別人都不知道家裏來了個嬰兒,因為我根本不哭。
我生長在北京的一個小康之家。我爸是個老電視人,我媽是工廠醫務室的醫生。我爸對我很嚴厲,從來不會當着別人的面誇我,情緒來了還會打我,會發大脾氣。我媽屬於傳統的母親,雖然她跟我很親近,但她不可能幫我對抗我爸。
小時候經常出現的場景是,我爸把我打一頓,然後躺在牀上,假裝氣得吃不下飯。我甭管多委屈,就算哭得話都説不出來了,都得站在我爸牀前,極其恥辱地説,爸爸,我錯了,你別生氣。
現在想想,可能是我爸自己內心比較自卑,所以他對於和他有密切關聯的人也沒那麼滿意。我到30多歲了,我爸才對我説過一句“寶貝女兒回來了”,因為那時候我在事業上做出點成績了。

李小萌舊照 | 圖源網絡
從小到大,我從來不提過分的要求,給吃什麼吃什麼,給穿什麼穿什麼。這種習慣延續到了工作後。在央視,我的口頭禪是“隨便,都行”,被評為“最好伺候的主持人”。那時的我,既覺察不到自己的慾望,也不會提要求,更不曾為自己爭取過什麼。
在同事們看來,我乖得堪稱奇葩。在央視工作20年,我沒有當過一天正式事業編制職工,直到2015年離開,還是企聘合同工。唯一一次跟領導提要求,是在2011年懷孕後,我問領導,能不能給我辦個電視台的車輛出入證,不然走路進來很吃力。領導都懵了,説,你進台裏十幾年了,連個車證都沒有?
那些年,我在央視做了很多節目,拿了很多榮譽,但都是領導指派的。我只是做到了機會到手,就一定拼盡全力做到最好,因為我特別害怕讓別人失望。

李小萌獲得金話筒獎,並將獎盃送給朱大爺 | 圖源網絡
創業相當於強行改變了我的狀態。沒有人再替我安排,沒有一個大機構再給我庇佑和掩護,我想工作就要自己去跟電視台提案,當一屋子的人都在説這兒不好,那兒不好的時候,怎麼答辯,怎麼爭取,都要自己想。
我以前特別怕麻煩別人,主要是怕被拒絕。但自己創業以後,我喚醒了沉睡的朋友圈,發現求人居然是建立關係的非常有效的方法,甚至比被人求還有用。只要不怕被拒絕,願意伸出援手的朋友很多。
前兩年,我們開始做抖音。我老説,能把抖音做起來的人,都是別無選擇的人。熱點來了,就算是晚上十一二點,我已經躺下了,蓬頭垢面的,也要迅速起來收拾收拾錄視頻。去年年底,我們整個團隊都陽了,等到燒一退,説話還喘呢,又開始直播上鍊接了。做自媒體就像農民伯伯種糧食,下一天的地,就有一天的收成,不下地就荒了。
摸爬滾打了兩年,我漸漸意識到,在內容傳播這件事上,我是有熱情的,也有天賦。所有正向反饋都會慢慢沉澱為我的勇氣,一開始是壯着膽子做,後來變成“我可以這麼做”,再後來,我能判斷出接下來的走向和結果,對自己的篤定就又多一分。

50歲的重塑與綻放
今年,我就要滿50歲了。
我現在非常願意講我的年齡,因為它對我來説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心理支柱。二十幾歲的時候我反倒不願意講,那時候年輕,不自信,容易自我攻擊,總是怯生生的。
現在我一想到,我都50歲了,團隊裏的小孩們才二三十歲,我吃過的鹽比他們吃過的飯都要多,做決策時我就多了很多信心。白巖松很多年前和我説過,他渴望變老。那時我還不理解,現在明白了,歲月會帶給我們智慧和力量感。

李小萌和同事們在一起 | 圖源李小萌微博
我女兒今年11歲,她們班的同學有時候也會討論彼此的爸爸媽媽。有一天,她回家告訴我,她的同學們説,本本,你媽媽都50歲了嗎?太不像了,她像我們所有媽媽中最年輕的那個。你知道,因為我生孩子晚,我女兒同學的爸爸媽媽都是80後或者85後,她有個同學的姥姥只比我大10歲。
但我覺得小孩子們看大人,看的應該不是一個人臉上的色斑和皺紋,而是一個人的狀態。我女兒過生日,請了十七八個小朋友來家裏,我會和孩子們聊天,尤其是那些落單的。孩子們參加活動,大人一般都是服務者或者秩序維護者,但我更喜歡作為參與者,和他們混在一起玩。我跟我女兒説,你開生日party,媽媽就負責撿起那些沒有被你們注意到的小朋友。
養育孩子對我來説是一個很治癒的過程。我常説,只有當了媽媽,我才體會到愛別人有多幸福。目睹她一天天長大,也給了我重新審視自己生命的機會。

李小萌和女兒本本 | 圖源李小萌微博
我女兒的性格和我反差可大了。她從兩歲就學會了説“不要”,幹嘛都是“不要”,我那天還在跟她説,你這一天裏説的“不不不”,比你媽十年説的都多(笑)。
我以前特別害怕衝突,偶爾的情緒失控都會讓我內疚幾天。但作為媽媽,有時候我需要表達憤怒,讓我女兒知道我在支持她,保護她,為了她我敢於向外界展現攻勢。
慢慢地,這種習慣也會平移到我自己的工作、生活和社交中。我玩微博好多年了,最開始從來不管理負評。我想説,我尊重所有的評論。但這兩年我開始刻意訓練自己回覆負評,因為我發現,如果你自己都不敢站出來為自己説話,別人憑什麼支持你呢?

李小萌在演講現場 | 圖源李小萌微博
女性很多時候習慣於展現温和的那面,但我覺得,應該讓別人識別出你不好惹的那一面。如果你從來沒有炸出過你的逆鱗,別人就會不斷地越界,越到你的底線之下。
我有個微信羣,平常都好好的,有天,一個人突然發了一個針對女性的非常過分的黃段子。要是過去,我肯定划過去當沒看見。但那天,我第一時間説,這個段子對女性很不友好,希望你能撤回。那個人馬上回復,抱歉抱歉,手抖發錯了,我發個紅包,下回注意。之後羣裏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信息。
我是個很晚熟的人。敢於袒露自己的真實情緒,對我來講是一個特別大的成長的標誌,是我建立起了足夠多的安全感的表現。我以前是正相反的,把自己包裹得特別緊,永遠禮貌有餘而率真不足,總是做該做的事,做該做的反應。我希望別人給我的評價都是好的,比如她特別謙虛,特別低調,特別不張揚,沒有攻擊性。都是這種很窄的評價。
但是現在,我願意向這個世界敞開。我不想再陷入無止境的自我批判中,也不會讓自己躲在根本不存在的保護傘之下。當我把真實的自己袒露出來,經歷着日常的風晴雨露,我發現,我就是自己的保護傘和承重牆。這是即將知天命的我才完成的成人禮,雖然遲到多年,但我甘之如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