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獨大”未必是壞事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04-04 08:35

· 這是第5125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 土哥涅夫 | 文·
日前,“蕪湖發佈”刊發了一篇題為《“一城獨大”不是春》的文章,指出經濟強省其發展不完全依賴省會城市的“一城獨大”,而是得益於“雙城驅動”,甚至“多城驅動”。
而就在幾天前,安徽印發《關於支持蕪湖市加快建設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見》,明確支持蕪湖成為安徽經濟增長第二極和省域副中心城市。
無獨有偶,湖北近日也相繼發佈《襄陽都市圈發展規劃》和《宜荊荊都市圈發展規劃》。據媒體報道,2022年湖北共籌資2588億元(含地方債券資金1799億元),支持武漢、襄陽、宜荊荊三大都市圈建設。
事實上,早在2020年,《求是》雜誌就曾發文提醒,要避免“一市獨大”的弊端。去年發佈的《2022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也專門提到,嚴控省會城市規模擴張。
為此,近年來很多中西部省份紛紛開始加大扶持省域副中心的力度,打造第二增長極。名單包括:
四川:綿陽、宜賓、南充等;
山西:長治、臨汾、大同;
湖北:襄陽、宜昌;
湖南:岳陽、衡陽;
河南:洛陽、南陽;
廣西:柳州、桂林;
陝西:榆林;
江西:贛州;
安徽:蕪湖;
雲南:曲靖;
貴州:遵義;
甘肅:天水;
……
但,“一城獨大”真的有百害而無一利嗎?既然如此,這種局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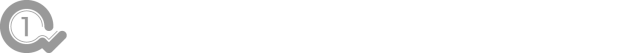
正如“蕪湖發佈”的文章裏所提到的,在中國,沿海省份往往擁有兩個甚至多箇中心城市,而內陸省份則基本都是省會獨大格局。而這也常常被一些網友拿來吐槽中西部地區實行的“強省會戰略”。
但,省會“一城獨大”的局面,真的是“強省會戰略”人為造成的嗎?
回顧中外歷史,城市類型大抵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獨立於王國統治之外的自治城邦,一種是中央權力傳導到地方的節點。前者主要出現在神聖羅馬帝國、統一前的意大利等四分五裂的地區,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後者則普遍存在於古今大多數國家。
這種形態下的城市,規模大小跟其距離權力中樞的遠近往往呈現正相關聯。比如倫敦之於英國、巴黎之於法國、東京之於日本,都是一城獨大的存在。即便是聯邦制的國家,比如常常被作為“小而美”城市典型的華盛頓,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也早已膨脹為僅次於紐約、洛杉磯、芝加哥、休斯頓的全美第五大都會區。反倒是像德國這樣以中小城市為主的國家,才是特例。
這其實也符合經濟學上的“馬太效應”。畢竟,大城市裏機會多,對人的吸引力也大,而隨着四方人羣的匯聚,各種消費、住房、娛樂、交通的需求日漸增長,相對應的,也創造出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城市吸引力進一步放大,從而形成了一個正循環。
相反,小城市裏機會少,辦什麼事都要靠關係,除非是“江西周公子”那樣的關係户,一般人很難憑本事出頭,只能選擇逃離。人走了,城市活力也跟着衰減,自然就更留不住人了。
久而久之,大城市變得越來越大,而小城市則日漸萎縮,最終形成一城獨大的情況。
一些人抨擊省會獨大現象,理由就是:這樣下去將影響到區域均衡發展,有違共同富裕的理想。問題是,共同富裕的着力點究竟應該放在哪裏?
談及共同富裕,我們常常會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種是以人為本的思路,即人們在哪裏更有利於脱貧致富,就鼓勵那裏的發展;另一種則是整體主義的思路,一味追求區域間的均衡發展。
但,怎樣才算“均衡發展”呢?如果我們追求的均衡發展,是人均意義上的,而非總量層面的,那麼其實完全可以換種思路。
大家看美國,多年來當地人口一直在往東西兩岸流動,所以就GDP總量而言,中部內陸的那些農業州遠低於沿海諸州,似乎出現了嚴重的中部塌陷。但另一方面,隨着人口減少,中部諸州的人均GDP其實並不比沿海的發達州少多少。相反,由於地廣人稀,出現了一批大型農場,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農場主的收入也不輸“紐洛芝”的白領。
既然州與州、省與省之間可以如此“動態平衡”,一省內部各城市之間,為啥非要追求總量意義上的“均衡發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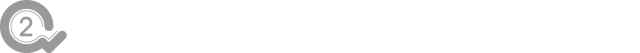
扯遠了,迴歸正題。
眾所周知,中國的省域疆界劃定於明朝,從那時起到現在,只有四個省搬過省會,自北往南分別是:河北省會從保定搬到石家莊,河南省會從開封搬到鄭州,安徽省會從安慶搬到合肥,以及廣西省會從桂林搬到南寧。
其中,石家莊、鄭州都是鐵路拉來的城市,屬於交通改變省內區位格局的幸運兒。
南寧取代桂林,雖有軍閥陸榮廷生於南寧的因素,但根本上還是隨着中原王朝對於西南邊地控制的深入,統治中心從桂北漢地“前進”至桂中南少數民族聚居區。
至於合肥,處在安徽地理中心,確實是最適合作為省會的城市。而反觀它的那些競爭者——安慶偏南、蚌埠居北、蕪湖太東,都難以輻射全省。事實上,上世紀50年代就有人提議將省會遷出合肥,而如今的“第二城”蕪湖也曾爭取過,但被毛澤東一句**“合肥不錯,為皖之中”**徹底斷了念想。
除了上述幾個,其他省份的省會始終沒動過,為啥呢?因為這些城市要麼地處全省中央,便於溝通各地;要麼臨近大江大河,水源充足,利於人口大量積聚。總之一句話,它們都是各自省內區位條件和自然稟賦最佳的城市。
比如武漢,位於長江與漢水的交匯處,地處江漢平原、魚米之鄉,又是九省通衢、華中咽喉。試問:湖北有哪個城市的區位比武漢還好的?同樣,西安所在的八百里秦川,乃整個西北難得的一塊膏腴之地。別説是一省首府,即便作為京師統攝全國,也未嘗不可。
由此可見,中西部“省會獨大”乃自古以來、自然形成的產物。所謂“強省會戰略”只是加強了這個趨勢,但作用不是根本性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市場這根指揮棒的作用下,人流物流資金流自然傾向於流入省城。只要我們還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就應該承認並接受“省會獨大”的現狀。動不動希望通過行政力量,來扶持所謂“副中心”,其結果很可能重蹈當年三線建設投入大量資源,最後多被廢棄的覆轍。
更何況,即便是在指令性計劃經濟時代,在最喜歡到山溝溝小地方佈局產業的三線建設高潮時期,絕大多數中西部省份也是“一城獨大”的。唯一的特例是四川,曾擁有成都、重慶兩座副省級城市。但隨着1997年重慶直轄,四川也泯然眾省矣。
至於“省會吸血全省”的觀點,同樣沒搞清問題的本質。對於廣大中西部地區來説,只有省會壯大了,才有資格參與全國城市競爭,才能把人才和項目留在本省。試想:一個沒有了成都的四川或沒有了武漢的湖北,當地人難道就會老老實實地呆在老家種地吃土?不,他們依然會走,只是去的是南方的廣東,或者東部的長三角。
事實上,改革開放頭30年,中西部各省基本就是這麼一副景象。但隨着這些年“強省會戰略”的實施,以成都、武漢、西安為代表的一批內陸省會的強勢崛起,大批外出勞工開始迴流。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跨省流動人口大約為總流動人口的1/3,剩下均為省內流動人口。這也反映出,除了一線城市外,省內大城市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在增長。
所以我經常説,對於廣大中西部三四線城市,“被吸血”是命,得認。關鍵在於,是被省會吸血,還是被外省吸血?因為兩者還是有差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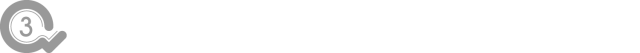
對此,可能有人要不服了,憑啥東部各省可以有“雙子星”,中西部地區就必須接受一城獨大,論人口、論GDP,像河南、四川、湖北等省份並不輸給東部的福建、遼寧甚至浙江啊?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得搞清楚,沿海省份的多中心格局是怎麼形成的。
省會自不必多説,無論沿海還是內陸,都是設在全省區位稟賦最好的城市。而且由於行省制度確定於農耕時代,所以大家仔細看,沿海省份的省會幾乎沒有真正沿海的。但它又需要對外做貿易,於是寧波、泉州等一批港口城市就興起了。
到了近代,隨着外國殖民勢力的到來,逐漸在沿海割據並建立起了諸如大連、青島、香港等一批真正意義上的濱海城市……三重因素疊加,這才造就瞭如今沿海各省“雙子星”甚至“三國殺”的局面。
儘管如此,在經過改革開放初期的野蠻生長之後,最近這些年,沿海省份的資源也逐漸在向頭部城市集中。過去的“三國殺”格局開始收縮為“雙城記”,很多省份曾經的第三極紛紛掉隊,比如山東的煙台、江蘇的無錫、浙江的温州,都退出了第一陣營的爭奪。
説了這麼多,我只是想替“一城獨大”正下名,但並不意味着,中西部省份不可以搞副中心、孵化第二增長極。畢竟像河南、湖北、四川等人口大省,不可能所有人都擠到省城。因為按照目前的技術條件,2000萬應該是城市有效管理人口的上限。考慮到中國相對落後的城市管理水平,以及地方自治能力的匱乏,實際數字還得往下減,否則就可能出現類似過去幾年那樣的失序混亂場面。
不過,中西部省份規劃副中心城市,也得滿足幾項先決條件:
首先,所在省份人口總量至少得在5000萬以上。像貴州、甘肅這樣人口低於4000萬,與重慶市同一規模的小省,更適合採取“一城獨大”的模式,以便集聚本就不多的人口和資源,避免肥水外流。
其次,省會得足夠強,這樣才有餘力培育“第二城”。畢竟國家發改委等部門發文要求的是,“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體,嚴控省會城市規模無需擴張”,而像江西、山西這樣省會都沒有發展好,都還只是個Ⅰ型大城市,就過早地培育副中心,到頭來很可能一個都發展不好。
事實上,江西這些年之所以被安徽拉開那麼大差距,跟安徽專心壯大合肥,以點帶面、輻射全省,而江西過早謀劃“昌九工業走廊”,拖累全省經濟20年有很大關係。
再次,副中心城市在地理上需與省會保持一定距離,這樣才有可能發展成為其所在次區域的中心城市。像蕪湖這樣處在南京、合肥兩大都市圈輻射範圍內的城市,GDP保持安徽第二或許不難,但要想發揮省域副中心的作用卻殊為不易。
**因為它本質上只能算寧合城市帶上的一個節點。**這跟滬寧城市帶上的蘇錫常,GDP甚至超過省會南京,但江蘇的省域副中心卻最終花落徐州是一個道理。
當然,即便符合上面所有要求,省域副中心的建設也還得遵循市場規律,順應人口流動趨勢。考慮到從七普數據來看,上面所列很多副中心城市的人口都在持續減少,不得不説,未來中西部有望崛起的省域副中心城市,還真沒幾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