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遊牧民世界的起源_風聞
吴金光-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理事-04-11 12:26
作者|杉山正明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

何謂遊牧民
若就歷史上實際發展的意義來説,或許可説農耕與遊牧是兩個體系對等並立。關於這點,對於人類及中央歐亞大陸來説,狩獵雖不可忽視,但若與農耕及遊牧相比,仍相對遜色。
“遊牧”是漢文名詞,在中國,大約是於明代開始出現。英文的“Nomadism”也經常翻譯為“遊牧”,但嚴格來説並不正確。所謂“Nomadism”,原本指反覆地變換居住場所的人,並非專指畜牧的遊牧,例如因採集狩獵或較少見的農耕遷徙(雖然就字面意義看來有些矛盾,但在歷史上確曾有幾個例子存在,如古代的日耳曼等)等都可以使用。相對地,英文的“Pastoral Nomads”是指“帶着牲口放牧移動的羣眾”,與“遊牧民”的意義及語感幾乎相同,就用語而言,或許後者較為正確。
遊牧,僅是畜牧生活的一種形態,其中“遷徙”是此種畜牧生活的重點,特別是指隨着牲口追逐水草生長的足跡而將整個家搬來搬去的形態。關於遊牧的起源,沒有固定明確的説法,有由農耕分離而成、人類主動靠近有蹄動物羣居等説法,但不論哪一種皆是推測。
或許這樣的生活形態很多地方都有,但“在中央歐亞某處曾經出現過”的觀點,是無庸置疑的。至於何時開始,大約在距今4000年到10000年前左右,目前還沒辦法追溯更久遠,不能確知具體細節。

遊牧生活的形態,可根據乾燥度不同或地勢高低等條件,有各種不同的變化。簡略地説,就是一邊管理飼育羊、山羊、牛、馬及駱駝等家畜,一邊視草糧被動物吃得差不多時另覓草地、水源的居無定所生活,但並非毫無目的到處流浪,是確實地配合季節移動。
在夏天,家族羣體依賴散佈在寬闊山麓或平原的草地生活;到了冬天,為了躲避嚴寒或積雪,就會羣體舉家搬遷到山麓南面或山谷之間。在此提到的“羣體”,指遊牧民社會的基本單位——相當於過去曾經被使用的“氏族”(這也是概念用語,類似英文“Clan”,但若光靠對於詞語的想象來思考現實,可能會有偏差)。
夏駐紮地與冬駐紮地間的移動路線幾乎是固定的,交通要衝設有井,牧草地則散落其間。遊牧的生活相當有系統,在遷徙和紮營間持續重複,以規律的原則管理家畜,尤其是羊羣,春季出生、夏日茁壯、秋冬宰殺(以小公羊為例)和配種培育等,在廣大無邊的大地無盡地循環。

相對於四季的自然規律,遊牧生活極端不穩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之類,草地瞬間荒蕪;情況最糟時若遇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襲,險境環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導致整個羣體滅絕。從日常生活用品到農業生產工具及各式戰鬥工具,亦常無法完全自給自足,綜觀以上,遊牧實在不是容易生存的經濟活動。
由於都市和聚落是經濟活動必要的聯繫,遊牧必須與綠洲共存共榮,在大草原逐水草為生的遊牧民族,需要帶着收成定期朝“點”狀的綠洲城市聚集。城市,既是人與物的交會處,也是集合生產、交易、移動、信息及文化的重要匯集點。從歐亞中間地帶人與物的流動來看,可見城市發揮了該具備的機能,更何況,人與人之間本能地相互需要,對住在人煙稀少之地的遊牧者來説,城市的意義實在重大。

若將遊牧當作生活的必然結果來看,遊牧及遊牧社會造就了幾個明顯的性格:機動遷徙、羣居,還善於射御之術。生活和環境的訓練讓遊牧者的危機應對極為優異,還能靈活自信統御團隊。且不論騎馬射箭是門高段的技術,馬匹也很重要,不論古代或現代,尤其在歐亞,戰鬥用的大型馬是相當貴重的財產,但對遊牧民來説,善騎的人與良駒都很普遍。
在近代槍火彈藥等武器從根本改變戰爭類型以前,遊牧民一向是世界上最優良、強悍的機動部隊,他們在世界史中的影響,多數都歸因於優越的軍事。
一般認為遊牧騎兵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約西周宣王時期)出現,直到17、18世紀中期左右為止,遊牧軍團的時代約長達2500年。他們以軍力所獲的區域納入版圖,其實不論綠洲大小,在版圖內的區域都該定義為“國家”,須特別留意的是,這些國家都不是由單一遊牧民形成,是跨越“民族”侷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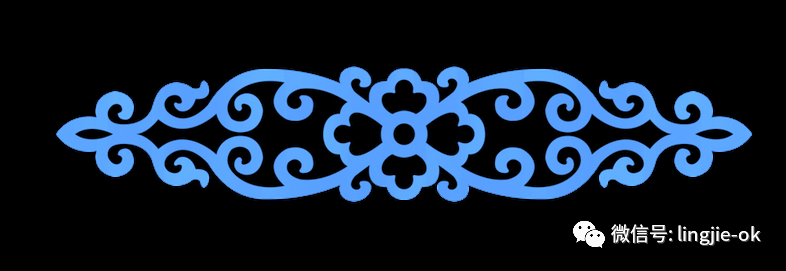
“什麼”超越“民族”?
一般使用“遊牧民族”或是“遊牧騎兵民族”來定義遊牧族羣,有時稱“遊牧民族國家”或“遊牧騎兵民族國家”,這是耳熟能詳的普遍用語。
但真的是那樣嗎?若説“遊牧民”尚可理解,但説“遊牧民族”或“遊牧騎兵民族”時所使用的“(單一)民族”,真的存在嗎?真有“民族”這個羣體嗎?或“遊牧民族國家”“遊牧騎兵民族國家”中定義的“民族國家”真有這回事?後者或許不是將它當作“(單一)民族國家”的意思,而是單純地指“遊牧種族”或“遊牧騎兵羣眾”所建立的國家,但即便如此,由“民族”及“國家”兩個詞彙聯結所產生的誤解,是不可否認的。
現在日本大眾所使用的“民族”“國家”的概念,具有強烈刻板的語意印象,那是以距今200年前的法國大革命為契機,根基於近代西歐所創的架構及價值觀中的。
所謂“Nation”這個人羣的“實體”,是被視作超越地位或身份、財富或階級而存在的,而國家則是被定義為以之為基礎的人工產物。這其實是某種“神話”。如果不這麼做,就算有波旁王朝,“法蘭西”也不曾存在。這種論述獲得普遍認同,德國及意大利的統一,都是利用此種趨勢應運而生。
19世紀是西歐最輝煌的年代,世界在其手中分割、支配。它的價值觀、國家觀及文明觀更是至高無上的標準,今日學問、學術上的“知識框架”,幾乎都與之同時形成。
以“Nation”為基礎的“State”,像是“Nation State”,更被視為歷史的當然產物。在許多地方,人們為了追求那個“理想”而努力,流血流汗。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稱為“Nation State”的國家接連建立,其中相當多數在實際上成為“區域國家”,而以特定族羣為政治核心的“Nation State”,其“國內”的對立,則是從一開始就結構性地存在。不過就一般而言,最大沖擊的還是在蘇聯解體前後開始的一連串轉變。
最初東歐有民主運動,也有許多人提倡西歐式民主的勝利,然而那都是短暫的黃花,“民族自立”“民族紛爭”及“民族純化”幾乎同時在各地頻繁發生、激變,多數人感到困惑,甚至彷徨不安。在“民族”“國家”“國界”及“社會”等既成概念傳遍各地前,近代西歐式的文明與思考模式便急速地褪色。
更直接地説,這也是必然的結果吧!只能説這種想法是一直以來都太不瞭解,或太不關注歐亞內陸的現實,或是歐亞世界史的實際狀態了。真是有點過於輕率的想法。
“回顧人類歷史諸多事象,西歐型‘民族’‘國家’的概念,雖然很完備,但充其量也不過是模式的一種爾爾。若能不要只將西歐文明作絕對、神聖觀,能夠更平易地重新檢視人類一路走來的步伐,就一定能夠意識到這點。”
對於那些將“Nation State”視作前提的美好故事,若是冷靜地觀察或可發現,大多數的事例都是先有“State”後才出現“Nation”。先有“國家建設”,才有“國民建設”,西歐的例子即是如此。(略)
在明治時期,日本人與中國人曾就“國家論”相互爭辯,但不管怎麼討論就是無法取得共識。後來仔細考慮,才知道是彼此對“國家”這個詞彙的認知不同,據説中國人的認知是“朝廷、王朝”,就是當時的統治王朝。
“國民”這個詞彙,是從“民族”及“國家”各取一字而來。第一個字是“國”,可推測是先有“國家”才有“國民”,若真是如此,就不是“Nation State”這個理念,反而是這裏所説的“國民”較切實際。
務必牢牢記住:絕不可輕忽文字和詞彙、翻譯用語產生的誤判。“Nation”及“State”這兩個詞彙,在日本翻譯成“民族”“國民”“國家”這類漢字,不管怎麼説,日本人在思考時,腦中總是會浮現與該漢字相關的印象。
話説回來,以“遊牧民族”或“遊牧民族國家”這樣的詞彙形容,可能有點言不及義。作者觀察世界史過程發現,數個創建堪稱“遊牧民國家”的案例幾乎沒有純粹僅由遊牧民建立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混合狀態,屬於多民族國家(Multi-ethnic State)。
作為國家核心的遊牧民集團,原本即是以集聚了各個團體、種族及勢力混合而成的“政治集團”或“政治聯盟”為一般形態。當它發展成類似“帝國”(在此只是為了敍述方便而用此慣用語)的統御廣闊疆域政治權力時,已可説是由多元種族或文化、社會並存一同混合而成的複合體。
不只在歐亞中間地帶,甚至以較寬鬆標準來看,這些曾於整體歐亞大陸的歷史中興起滅亡、生存毀滅的政治集團、王朝或國家權力,若以近代西歐型的國家觀為基準來看,都具有曖昧鬆散,輪廓與內容都不甚鮮明清晰的特質。不過,即便如此,那也是國家,也是政權。那是在悠長曆史中大致上的現實樣態。
若以近代西歐式的價值觀判斷裁定“這不是國家”,最後到底會剩下多少“國家”呢?反而可見近代西歐文明所描繪的國家樣貌,並不符合人類歷史的普遍性且嫌偏頗。觀察近代許多造成影響的“民族紛爭”可發現,西歐的“Nation State”觀念助長了“民族問題”,甚至讓問題更加顯著。(有一陣子,此用語被轉換為“地域”紛爭,應該是對“民族”這個詞彙語意困惑的緣故。)
因此,除了應該將歷史與現實確實釐清,更要避免被特定的價值觀侷限,換句話説,不是以身體去將就衣服,而是讓衣服合於身體。
歐亞歷史之於世界歷史,等於是構成了這個“身體”的大部分。尤其是聯結歐亞東西,成為歷史大幅開展中之主角的歐亞中間地帶遊牧民及其政治集團,正超越了“民族”的觀念。不論褒貶,他們都充分展現人類世界中“國家”的角色,至於這個超越“民族”的東西究竟為何,就是本書接下來要探討的。


可見於史料或隻字未提的文明
然而,所謂的歷史,實際上是有侷限的,在已知的史料當中,其實不太見得到遊牧民的姿態。一直以來,歷史之所以以西歐為首的文明圈為主體,也有其莫可奈何之處。
就如先前敍述的,遊牧民及其社會、與以其為核心建構的國家在歷史中的影響,都沒有以他們為敍述主體的敍述評價,不僅如此,反而常被片段歸類於負面形象,受到“野蠻”“破壞者”及“不文明”等貶詞稱呼,若論對錯,常歸咎於遊牧民。
其中的原因是至今留下以遊牧民為主體作史的記錄極少。即使有,也多是由居住在農耕或城市之民載記而成,因此總有些許漏失,且記錄的書寫方式也因立場不同而多有誤解或扭曲;即使確知來龍去脈,有時會以對記錄者有利的角度撰寫,甚至有時會顛倒是非。
雖然記錄者將自己當作“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應該不會侷限於特定的狹隘價值觀之內,但很可惜並非如此。不論古今,確實有時很難將自認是“文明人”的人與“偏見”“自傲”“自戀”等劃清界線。
遭受遊牧民攻擊、支配時所留下的文史,很容易受到被害者主觀意識左右;而在承平時期或自己發動攻擊時期的史料,又會透露過度的優越感或輕視。總之,從歷史記載可以發現,混合了驕傲、批判、抗拒或蓄意漠視等預設情緒以致下筆偏頗。
也許記錄或報道原本就難以做到中立,這一點從古至今都未曾改變。
書寫是可虛構的,或許也不該盡信書。因此,調查或研究歷史,會受限於既有的文獻,甚至更糟地刻意略過某些事件而不記錄,以其主觀武斷評論或自我膨脹。
留下記錄的史料與真實存在的史實之間,兩者的距離相當大,書寫者才是贏家。能留在史冊的是幸運,沒留下的便很容易就被後世妄下不合理的論斷。然而,是否要留下記錄事實上是根植於其生活中的某種價值觀。
那是隻要生存就會有的“形態”,也可説是“文明”的“形態”。至於留或不留下記錄,這件事本身就不是決定個人或人類集團之優劣的因素。
由於研究遊牧民有以上困境,在探討它所建構的歐亞史時,需要確實交叉比對原典及史籍之後還原史實,要達到此標準即具相當難度,因此必須從各類範疇和既存的眾多語言文獻中挖掘,遺蹟、古文物這類線索也不可放過。
這樣的研究不論在日本國內外,都刻不容緩地持續進行,只是距離目標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慶幸的是,原本進入蘇聯境內研究會遭遇的困難隨着蘇聯解體而相繼消失,中央歐亞的歷史研究,或許正迎向嶄新的光明遠景。
至少,遺蹟、文物或碑刻、出土文獻等的“原物”史料,讓研究視野有翻轉的機會,既有的史料在政治枷鎖解除後,或許可重新檢閲根源、平反及更新定義。歷史研究與政治並非毫無瓜葛,反而有根基的關聯或影響,一個自由的歷史研究,能否有自由的發想或空間?即是取決於這個國家或社會是否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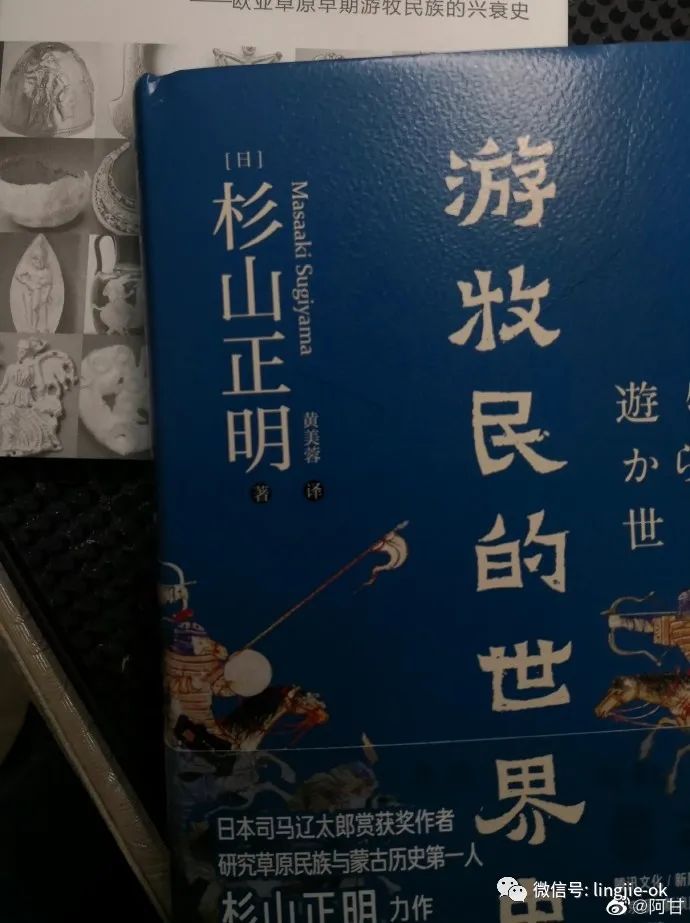
本書所要做的是,立足於以主要文獻為中心的知見,處理這段雖然或多或少有些新發現,但在根本上可能無法改變什麼的中央歐亞的歷史洪流。若要談到這對世界史有什麼重要性,我想關鍵就在它本身與其他“文明圈”歷史,在層次上有所不同。
這個世界,至今100年到150年間,都在奉近代西歐型文明為至上的價值觀中發展過來。然西歐文明僅是一種“文明形態”,觀察人類漫長的歷史可以發現,有各式各樣“文明形態”存在,價值體系也同樣有多樣性。
現在,以近代西歐型文明為極致而形成的“神話”,於現實上已面臨崩解的狀態,我們正站在文明史的轉換點,支撐近代西歐文明架構的“民族”“民族國家”及“國民國家”的思想,及其關連密切的“國界”概念,也該從基礎層重新檢視。
在這樣的架構下,本書以從古早之前就已存在的遊牧民及以其為核心的國家為中心,試着概括地討論其興衰及轉變。究竟是什麼超越了“民族”與“國界”的牢固框架?是什麼串聯起人類及地域而構成了“世界史”?本書希望可以從過去的歷史中發掘,冀求可以補充些許被遺漏的歷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