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代不需要「我們」了_風聞
芙宁娜-04-13 15:08
來源:公眾號“像一道光”
一.
成立「我們視頻」那天,大家想着給它起名,六樓的辦公室裏坐了一圈人。
每個人都可以提一個名字,領導拿着黑筆,在白板上挨個寫詞。白板上寫得密密麻麻,叫什麼的都有。
「看看人家澎湃名字起的多好,又是澎湃如昨,又是Paper諧音梗。」珠玉在前,大家爭執不下,腦洞開始不夠用了。
想來想去,最後是總編輯王躍春拍板,一錘定音。「就叫我們吧,我們視頻。」
名字一出,四下譁然,大家愣了,「到時候別人問我在哪裏工作,我説在我們視頻,人家會不會聽不懂?」
是吧,多難聽一名字,叫了6年,發現大家也越叫越順口了。
二.
開始做視頻的時候只有7個人。7個從社會新聞部轉進深度調查部,再轉出來的文字記者。
當年安心給報紙寫稿,可以一寫寫一輩子。大家都是學新聞出身,不少人連視頻格式都説不清楚。
但這並不妨礙小剛坐在空曠的辦公室裏面,給我們做鼓舞人心的動員會。
他清了清嗓子説,「我們要搞一件大事!」
「搞」這個字眼,他壓了重音。
他特別喜歡用「搞」「靠」這種帶着奇怪意味的詞彙,並且喊出自己獨特的氣勢。
其他的內容我完全記不清了,言而簡之,大致意思是,新聞資訊視頻的時代開啓了,我們就是短視頻新聞時代的奠基人,到時候,新聞史上一定有我們這羣人濃墨重彩的一筆。
那年確實新聞短視頻還方興未艾,小屏直播更少。新聞市場上的供給整體還是以大屏主導,打開屏幕就是漫長的口播,説着不少人都聽不下去的台詞。
那天我坐在底下,暗搓搓地想,就報社這羣人,懂個屁的視頻。
三.
確實,「我們」一開始就沒打算好好做視頻。
人家視頻要的是聲畫和諧,是構圖標準,是鏡頭穩定,而「我們」要的是核心現場、核心畫面、核心採訪。
那年還是「我們視頻」拍客的張建斌,拿着手機,在太原內澇的現場逮住了耿彥波。
耿彥波面對鏡頭,五分鐘里正面回答了他數個問題。當聽説奧體中心有不少居民被困,耿甚至直接叫來了交管部門,詢問事發現場的情況。
這件事讓大家大為震撼。活了大半輩子,做了這麼多年新聞,「原來新聞還可以這樣做啊。」
再後來,張建波來到「我們視頻」,成為一名記者。

再再後來,在河北保定男童墜井的救援現場,他和程彥斌、寇家祥、程媛媛、唐瑤,在天寒地凍裏面,為了直播,守了一天一夜。
他的人生軌跡,在30歲時拐了個大彎。
四、
被「我們」騙來的,還有朱必勝、馬駿、俞金旻、黃啓鵬等一干人。
沒有「我們視頻」,朱必勝可能還在四川某個地市台裏做編導,前兩天就不會撥通張繼科的電話,發出了全網獨家的那條消息;沒有「我們視頻」,馬駿可能還在蘭州待着,不會去土耳其現場,去體會大地震後的滿目瘡痍;沒有「我們視頻」,俞胖子不會因為自己超重的噸位,在颱風天的外灘上「一站成名」;沒有「我們視頻」,黃啓鵬也不用火急火燎從一個攝影記者轉型,一點點開始學怎麼寫文稿怎麼拍攝,不用在去泉州塌樓現場的路上,一邊在高速上駕車狂飆,一邊玩命回覆後方消息。

想想用騙這個動詞,真挑不出什麼問題。這都是玩命的活啊,給再多錢,是不是也要掂量掂量值不值得幹。
你説,人到中年,不想着安身立命,不想着老婆孩子熱炕頭,不想着趁還有心力去做個掮客,盤活手頭的那點資源,每天撲的不是爆炸就是水災,要不然就是塌方,得罪了一屁股人,難道圖的是一稿成名天下知嗎?
五、
就是因為工作太危險,導致「我們視頻」地方新聞部的團隊裏全是男丁。
招人的時候,郵箱裏面不是沒有收到過女記者的簡歷,於是我興匆匆發給小剛。
小剛抬頭就給我潑了一盆冷水。他問,女記者你招來以後,放在地方,然後讓她們去突發現場,安全性真的沒問題嗎?
我想想,就這工作強度,就這工作變數,萬一出點啥事,確實十個我都擔不起。
團隊裏面不是沒有女漢子。唯一個女漢子身高超過一米七,大腿比我兩隻胳膊還粗。
懷孕的時候,杭州桐廬廊橋垮塌,我猶豫了好久,要不要讓她去現場。而她連夜就從杭州趕到,不僅完成了現場搜救直播,並且還在醫院採訪到了傷者家屬。
現在回頭想想,發不發這條新聞,除了感動自己,又有個屁用?
六、
可當時的我們不是這麼想的。
我們鑽進了牛角尖裏,總覺得自己不做點什麼,就對不起年輕時候的自己,對不起自己帶着榮光的職業責任。
小剛説,做新聞不等天亮。於是大家也是這麼做的,手機都不敢靜音。
幾年前的一天晚上,半夜2點,吉林松原發生5.7級地震,當地震感強烈。
手機地震警報App突然響了,我從牀上一躍而起,開始挨個給睡着的記者和編輯打電話。
成片是半夜3點出來的。
早晨8點,騰訊新聞給微信推送的第一條新聞消息,就是松原夜裏發生的這起地震。
想都不用想,全網只有我們一家有現場視頻。
七、
「我們視頻」最牛逼的時候是2019年——一共接近150號人,日均產量穩定100條,開了包括《緊急呼叫》《回到現場》《我們直播》《局面》《世面》《有料》等接近10個欄目。
那三年,「我們」最長的一次直播開了106小時,記錄了廊坊墜井男童救援全程;泰國普吉島沉船持續跟進報道超過一年,回訪時在打撈出來的鳳凰號殘骸上,甚至發現了中國倖存女生的身份證;在四川涼山撲火犧牲烈士悼念儀式現場,「我們」在採訪中拍下了消防員獨自抱膝痛哭的感人瞬間;在江西張玉環的家中,宋小女對「我們」説,「他還欠我一個擁抱,這個抱,我想了好多好多年,我非要讓他抱着我轉」;在埃航墜機現場,「我們」還原了航班的墜機過程,在廢墟中找到了被燒壞的電腦、手機……

2019年上半年,六個月裏面,我們視頻主持的微博話題超過1萬個,119個微博話題閲讀量過億,日均閲讀5000萬+,月均自主熱搜話題上百個,單日最高微博閲讀量1.6億,秒拍單日播放量超3億,微博閲讀和互動量常年穩居機構視頻榜頭部。
八.
這種東西,回過頭再拿這麼多字去説,類似「爺當年也輝煌過」,聽起來似乎有點可笑。
可那時候,我們經常覺得,這是一支鐵打的團隊。放眼整個中國,「我們視頻」也是最牛逼的採編團隊之一。
想想「我們視頻」真是個世外桃源啊。
沒什麼派系,沒什麼勾心鬥角,同事都是朋友,爭執的無非是幾個選題到底應該給誰做,可以大大方方把後背交給對方。
就是太美好,離開以後,我經常想回去看看。但更多時候,是愧於踏進那個院子——畢竟自己已經做了逃兵。
想想那些在雨夜裏面繼續行走的同事們,想起齎志以歿的那些同行們,總覺得真心無顏再見江東父老。
九.
那時候的日子真是短,每天眼睛一閉一睜,天亮時往工位上一屁股坐下去,抬頭天就黑了。
從幸福大街6樓到2樓,從7個人到150個人,這裏的人來了又走,走了又來。
最好的那年剛好是2019年,報社在過16歲生日,推出了「石榴計劃」。
院子裏栽下的石榴樹發芽結果,掛在枝頭,噴上農藥然後腐敗,最後在冬天死掉。
第二年春天來了,前台大哥説,「這些石榴樹都沒活過來。」
十.
我在那家報社工作了7年,在「我們視頻」工作了5年。中間被紀委例行談話過,坦坦然然進去,坦坦然然出來。
離職時候,算了一下,7年裏面,一共有3000元推不掉的車馬費,我一分都沒敢裝進自己口袋。除了交公的,剩下直接捐給了慈善機構。
同事們大抵也很乾淨,這我是願意去相信的:收到封口的禮金,還會自己貼錢,打回到對方的户頭裏去。
十一.
前兩天,他們在告別合影,我沒能回去。
歲月沒有放過他們,照片裏面,他們也開始老了。
青春裏面,他們每個人都有很棒的故事,還有很多忘不掉的人生交集。合訂起來,就是一本厚厚的移動資訊視頻發展史。
我真的很想認真多寫一些他們的故事,記錄下每個人的名字。
我也真的想多用一些動情的句子,來表達我心底裏的熱愛和遺憾。
但想來想去,我只能落下這些平淡的句子。
十二.
這個時代裏面,耿彥波是少數,某些被新聞熱血點燃的時代也是個少數,世外桃源的同事情誼也是少數。
在少數的瞬間裏面,我們都覺得能為時代做點什麼,然後改變點什麼。
在少數的瞬間裏面,大家都一時忘記了,原來外面的世界每天都在槍林彈雨,依舊血腥殘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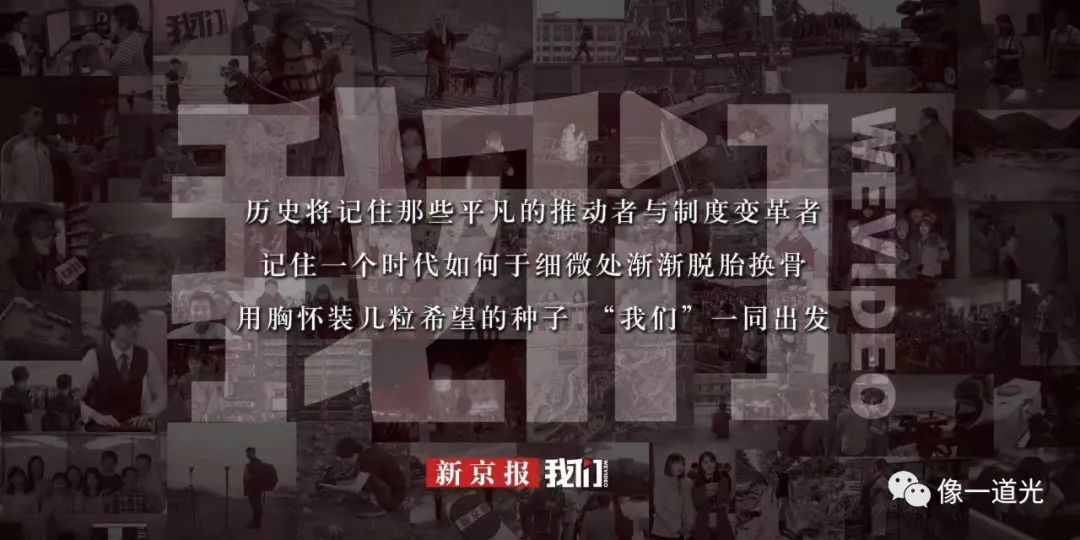
從2016年9月11日出發的「我們視頻」,還沒等來自己的7歲生日。
它會有新的活法,也可能會有新的身份,但是未必還有那批舊人。
這次,不是我們放棄了在時代裏面的掙扎和努力。
而是時代不需要「我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