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聊聊:好遊戲一定要好玩嗎?_風聞
毒眸-毒眸官方账号-文娱产业媒体,看透真相,死磕娱乐。04-13 14:12
“這遊戲哪都好,就是不好玩。”每名有點“遊戲閲歷”的玩家,都不會對這句評價感到陌生。
時間較近的案例,有俄羅斯開發商Mundfish的處女作《原子之心》。它靠一台滿嘴性感騷話的智能冰箱和一對身姿曼妙的機器人姐妹花在國內撩撥起了預想之外的熱度,而當人們真正進入遊戲世界,又會驚歎於它在背景構架和場景美術層面獨樹一幟的“原子朋克”美學體驗。

但或許是開發經驗有限,《原子之心》的戰鬥細節、技能體系、關卡流程等直接遊玩部分,都存在着被詬病的缺憾,就成了又一部“好看不好玩”的代表。
時間更遠的典型,莫過於業界翹楚Rockstar Games“開發8年、耗資8億美元”的心血《荒野大鏢客:救贖2》。喜愛者在那片栩栩如生的西部袤土上不捨晝夜,為亞瑟·摩根的故事潸然淚下;討厭者卻被遊戲過於“栩栩如生”的設計弄得煩不勝煩,擬真、繁瑣的操作和緩慢的節奏,讓他們在同一片土地上幾乎寸步難行,無奈地四處刷起那句“什麼都好,但不好玩”。

如果“遊戲最重要的是遊戲性”,那麼乍聽起來,“好遊戲必須好玩”似乎也沒什麼問題。但為什麼類似《荒野大鏢客:救贖2》這樣被各大獎項提名的“好遊戲”,會給很多玩家帶來不好的遊玩感受呢?
答案其實顯而易見,“好玩”不僅是種非常主觀的感受,很多語境下甚至意味着爽快、刺激等直觀的情緒宣泄。而類比“音樂性”、“文學性”之類需要靜下心來感受和思考、還通常要求具備一定鑑賞能力才能獲得的審美體驗,“遊戲性”也該是個更深層的概念,它不能和“好玩”劃等號。
用更通俗的例證便是,《百年孤獨》《追憶逝水年華》這樣的鴻篇都很難讀、不“好看”,這不妨礙它們是文學經典。其他藝術領域內,也不乏“難聽的音樂”、“看不懂的畫”或者“故事晦澀的電影”,卻被同時代的權威或被歷史本身認定成了該領域內的傑出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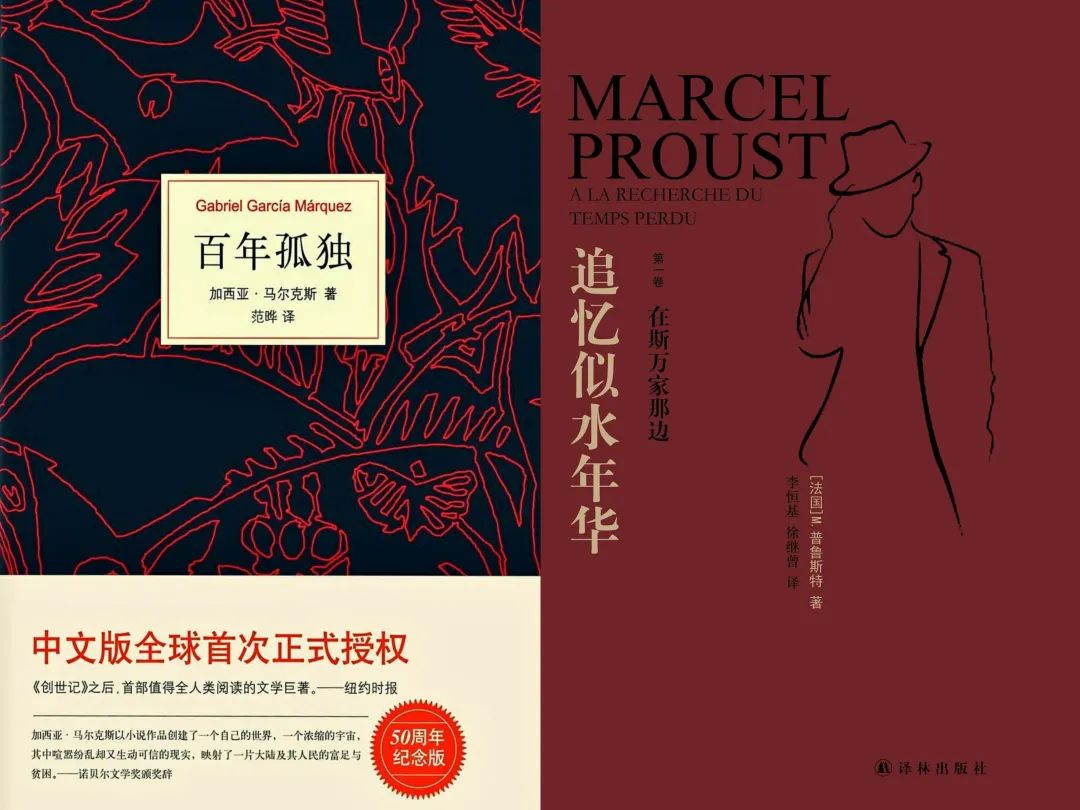
同理——好遊戲也不一定要好玩。既然“好書首先得好看”、“好畫首先要漂亮”是反直覺的,那也不該理直氣壯地聲稱“遊戲首先得好玩”。這話題到此結束?
不,我們還可以再繼續延伸談談。
首先得解釋下某項已經默認的前提條件——電子遊戲是與詩歌(文學)、建築、雕塑、繪畫、音樂、舞蹈、戲劇、電影並列的“第九藝術”。上述邏輯在該前提下才能成立。
雖然嚴格意義上,“八大藝術”並不是什麼嚴謹的定義,它源自電影業先驅喬託·卡努杜在1911年發表的文章《第六藝術的誕生》,該文目的是給電影正名。後來他又把歷史更悠久的舞蹈列入,電影就被擠到了第七位,時至今日電影也還有“第七藝術”的説法。
電子遊戲在很多涉及“共同認知”的層面都在走電影曾走過的路,“納入藝術”也是如此。有考證指出,“第九藝術”這個説法最早出自1997年6月《新潮電子》刊發的文章,作者只是一名大二學生,隨後它才廣泛流傳於中文互聯網。
但不論源頭如何、排第九是否準確,現在“電子遊戲是一門藝術”應該已經成為了一種“共同認知”,這不僅是遊戲業的自我標榜或來自玩家的呼聲,學界也有不少文獻對此進行理論驗證。海外一些國家甚至有過官方界定,如美國聯邦政府直屬組織美國藝術基金會(NEA)就在2011年發文宣佈將電子遊戲納入藝術範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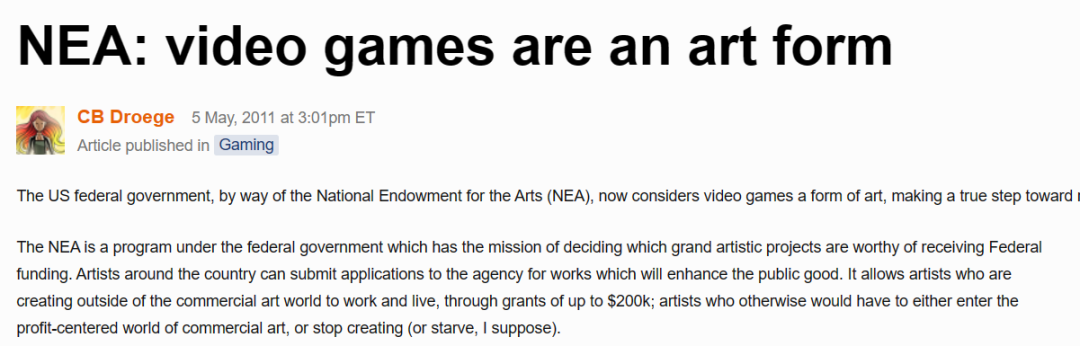
另外,遊戲有很多分類方式,按平台、按類型、按商業模式等等,不同類別差異太大就無法將“遊戲”視為整體分析了。北師大學者、國內首個“遊戲檔案館”的建立者劉夢霏在許多訪談中提過一種按遊戲生產循環邏輯的分類方式:作品型遊戲、消費型遊戲和賭博型遊戲。
作品型遊戲必有藝術表達,買的玩家多“作者”就可以不斷表達;消費型遊戲大多免費遊玩,目的是服務玩家,玩家在一套體系裏不斷消費才能回收成本並盈利;賭博型遊戲的核心是抽卡,或者叫“花錢買概率”、“玩概率”,玩家如何努力都不會改變遊戲世界。暫且將本文討論範圍框定為“作品型遊戲”,畢竟去賭博遊戲裏找“藝術價值”就屬於自討沒趣了。
明確這些後,我們將面臨一個新的問題:那些會被稱為“藝術品”的遊戲,怎麼反而總是些“遊戲性”好像不那麼強的遊戲?
《風之旅人》《去月球》《勇敢的心:世界大戰》《伊迪·芬奇的記憶》《最後的守護者》《死亡擱淺》《極樂迪斯科》……這可以是一份很長的名單,有獨立遊戲也有商業大作,它們飽受讚譽的同時,也總會有玩家認為“不好玩”。

電子遊戲這種年輕的藝術形式發展至今,內部確實有這樣一組矛盾。筆者認為這是由遊戲的構成屬性導致的,“成為藝術”其實有兩條路徑,其一是具有能融合其他藝術門類特徵的“綜合性”,正如能在戲劇裏看到文學、舞蹈、音樂等其他藝術的特徵,戲劇就可以算一門“綜合性藝術”,電影獎也會常設表演、劇本、配樂、特效等獨立的子獎項。而在電子遊戲裏,幾乎可以展示其他全部“八大藝術”,所以遊戲當然也是一門藝術。
其二則是有區分於其他藝術門類的“獨特性”,有自己獨特的藝術表達方式。在判定時,“綜合性”和“獨特性”滿足一條就行了,不過有“獨特性”可能會讓這種藝術形式的地位更高,如“表演”和“台詞”曾經是戲劇的專屬特徵,“鏡頭語言”曾經是電影的專屬特徵,它們作為藝術的地位就廣為人知且很難撼動。
對電子遊戲而言,“綜合性”很容易被感知到。《原子之心》就在美術、建築、雕塑等很多方面做到了極致,基於冷戰背景、原子能技術發展、蘇聯未來主義的設定,遊戲搭建了一套高度統一的視覺美學體系,並在遊戲開場就觀光式地呈現給了玩家,而這樣從社會風貌到物件細節都有濃厚“蘇聯味”的作品放在整個遊戲史上都罕見,已經可以算種“藝術創新”。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刺客信條》系列對古建築的還原、《新戰神》對遊戲鏡頭的探索、《極樂迪斯科》複雜的文字敍事、《寂靜嶺》留下的經典配樂……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看似和“玩”無關的構成要素,都服務於“作品”的“表達”,在“作品與受眾”的關係中,不能排除有玩家就是被這些要素所吸引,換言之,想“玩”的就是這些。
《如龍》系列也是個比較合適的例子,該遊戲的主線流程主要由日劇般的長段播片填充,在自由探索部分又填充了海量小遊戲,以至於在動作玩法之外,出現了“《如龍》就是看劇情”和“系列精髓是小遊戲”兩種截然割裂的玩家反饋,前者不能“玩”,後者是純粹的“玩”,但這兩種需求卻是同時存在的。
眾所周知,遊戲還有個代稱叫“交互藝術”,“交互性”就是電子遊戲作為藝術門類的“獨特性”。類似“文學性”的一種定義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獨特性質”,如果這麼理解,那“交互性”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等同於“遊戲性”。
略顯尷尬的是,絕大部分玩家不知道“交互”該從何欣賞起,所以在誇讚某某遊戲“像藝術”時,就只能側重“綜合性”那部分,也就是其他發展更久的藝術門類的特徵了。
這當然不是玩家們的責任。如果遊戲作品與玩家,也符合其他藝術與受眾間的關係,那鑑賞一種藝術毫無門檻反而是件奇怪的事。其他種類起碼在孩提時代,會由學校、家長提供“書單”、“影單”,上些美術、音樂課瞭解經典作品,對“什麼是好的”建立粗泛的基礎認知。不算“高等教育”,電子遊戲都不經歷這種基礎教育階段,也就只能憑感性認知了。
在某些國家地區已有改變,比如去年波蘭遊戲《這是我的戰爭》被波蘭教育局列入了“中學課外補充讀物”。不過鑑於電子遊戲本身短暫的歷史,大部分國家離“遊戲藝術”的理想接受狀態還比較遙遠。

靠感性認知“鑑賞遊戲”,有時就會得出一些不完全靠譜的結論。如《荒野大鏢客2》中無處不在的繁瑣交互——騎馬會被摔下、做食物要先搭營、和陌生人有幾種互動方式總按錯等等,它們實際上都是塑造遊戲沉浸感的手法,有了這些設計才會讓玩家感到彷彿“活”在那個世界,從而更好地代入角色的人生。能服務於作品表達的交互設計,理應屬於亮點而非缺陷。
順帶一提,大部分遊戲會簡化交互來方便玩家操作,有的只是純粹的依循慣例不構成藝術表達,有的也有服務作品表達的目的卻弄巧成拙,只能具體遊戲具體分析。
那除了“擬真”、“簡潔”這種區分,真有作品通過遊戲的“獨特性”來給予受眾獨特審美體驗嗎?
當然有,且不少。《伊迪·芬奇的記憶》中有一段流程,是讓玩家一邊以罐頭廠工人的身份不斷機械重複“切掉魚頭-扔進傳送帶”的動作,一邊控制“腦中小人”在幻想國度裏冒險,需要進行的操作就只是最基礎的按鍵和移動,卻又讓玩家能切身體驗到角色分裂的精神狀態。這份體驗的傳達就是通過精妙的交互設計來實現的,還達到了其他藝術形式都無法賦予的獨特震撼效果。

《死亡擱淺》被調侃成“送快遞模擬器”,但遊戲改變了“趕路-遊玩”的通用流程,把遊玩內容直接放到了“路”上,並以此為基礎設計了大量新穎的交互方式,比如通過扳機鍵來實現“抓緊揹包、站穩”等等,路途的疲憊、接近終點的舒暢通過遊戲媒介傳遞給了現實裏沒挪半寸的受眾。
《風之旅人》的全部流程可以理解為一場被符號化、虛擬化的“朝聖之旅”,遊戲世界裏的一切交互都服務於這個表達核心,而玩家是旅程的親歷者,沒看到任何現實風景卻收穫了和現實“朝聖”近似的心境……

上述這些還屬於碎片式的審美感知,關於“如何欣賞交互”,也確實有一些學者和遊戲從業者嘗試過建立起完整評價體系。2004年GDC(遊戲開發者大會)上,Robin Hunicke、Marc LeBlanc、Robert Zubek提出了MDA框架,這是一套能通過機制(Mechanics)、動態(Dynamics)、美感(Aesthetics)來分析所有電子遊戲交互性的普適體系,機制指提供給玩家的行為規則,動態指遊戲裏的變量,美感指通過機制和動態產生的體驗。
在《最後的守護者》裏,主人公與生物“大鷲”在冒險途中產生的羈絆是遊戲的表達重點,拿MDA框架分析就會發現,製作人將其構築在了“機制”層面上:給大鷲編寫獨立AI,它原本懼怕一種彩色玻璃,前期需要玩家打碎玻璃才能前進,建立長久感情後面對持有彩色玻璃的敵人大鷲也會飛來拯救玩家,利用玩家與AI的交互提升了藝術表達。

“變量”的一種代表性體現就是陳星漢引入遊戲設計的“心流”理論,指通過目標和反饋、挑戰和能力的動態平衡來讓玩家進入“心流”狀態,高度集中和高度沉浸感最終導向了其遊戲的“禪意”追求。
不過客觀上,電子遊戲在交互技術上的革命性進步並不算多,這也註定了它很難建立起完善的學科體系。
有學者就以1994年PlayStation遊戲機掀起3D化浪潮,和2006年由Wii遊戲機開啓的體感、VR、AR等新技術浪潮作為2個節點,一共劃分出3個階段。在1994年以前,遊戲的交互方式還比較簡單,藝術表現力遠不如同時代其他媒體,而種種所謂“新技術”,直到現在也沒得到足夠的作品支撐。
從第2階段到現在,技術提升所帶來的,其實更有利於遊戲在“綜合性”層面的擴展。
於是人們看到了“遊戲電影化浪潮”,早年的《使命召喚》系列、近年還有影劇改編問世的《神秘海域》《最後生還者》等都是“遊戲電影化”產物,已成一種固定類型的“互動式電影”則是該趨勢發展到極端的表現。

和其他門類的融合也一樣。相比上世紀90年代前,視覺升級讓如今的遊戲能展現更精細的建築、更多元的美術風格;體量擴大則能容納更龐大複雜的故事,同時也有更多空間探索諸如場景敍事、碎片敍事等新形式……
這種融合與此消彼長,也是導致遊戲的“遊戲性”和“藝術性”在玩家反饋中經常不統一的原因,但這種現象得分兩個方面看待。
一方面,“綜合性”擴展也不算就走入歧途了,它同樣是遊戲成為藝術的重要構成屬性,同樣見證和代表着電子遊戲的發展。
舉個極端的例子,“雲玩家”羣體在某些討論語境中幾乎帶有“原罪”,對遊戲遊玩部分的發言權也確實值得商榷,但某些類型的某些“綜合性”部分,雲玩家的確也能獲得審美感受,同樣是“藝術作品-欣賞受眾”鏈條的參與者。與其説雲玩家破壞遊戲環境,倒不如説這是遊戲藝術屬性的旁證。
另一方面,還是“獨特性”決定了遊戲作為藝術門類的上限。北歐是全球最早進行遊戲研究的地區,創刊於2001年、集中刊登相關文章的期刊《遊戲研究》已經連續發行20多年,早在其初創期,就經歷過“遊戲與敍事之辯”,即如果用敍事學理論研究遊戲,只是讓遊戲成為了其他學科的附庸,並沒有形成學科自覺。
而到近幾年,在《遊戲研究》刊發的相關文章中情況有明顯改善,會更側重突出遊戲自己獨一無二的敍事方式,如《生化奇兵》等遊戲中的“副文本”、《死亡循環》等遊戲中通過“時間”來顛覆傳統敍事等。但傳統的跨學科思路也一並存在,遊戲中的哲學、心理學,或者遊戲對社會、對兒童的影響這些角度,在全部研究中的佔比依然不低。

國內也經歷過類似的過程、正面臨類似的局面。目前有聲音認為“藝術學”是“遊戲學”最合適的學科依託,可喜的變化是2019年首部“遊戲學研究專著”《遊戲學》已經面世,但也只是處在從無到有的第一步。

《長江文藝評論》一篇文章指出,建構“遊戲學”的重要環節是推動遊戲的“作品化”和“美學化”,因為作品是藝術研究最基本的單元,離開作品一切無從談起。如果僅僅將遊戲定性為“產品”,那前面加個“文化”的帽子也於事無補。在產品邏輯裏,經濟利益就是其價值實現的最高甚至唯一目標。
可能有玩家乃至從業者會好奇,國內遊戲產業市場規模全球領先,作為文化產品挺成功的,為什麼非要費勁地建構什麼虛無縹緲的“遊戲學”?“玩個遊戲而已”,還要往藝術、審美上靠?
答案是:這能從根源上改變電子遊戲的社會認知。繼而引發的正向連鎖反應不可估量。如果一邊抱怨國內遊戲氪金嚴重、平均水準不高,或者是時常苦於版號政策和防沉迷政策,一邊又只滿足於提供/享受遊戲的娛樂價值,本就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樂觀期待的話,既然一些冰山腳下的微小變化正在發生,那就遲早會輻射到水面之上。當每代人話語權轉變,電子遊戲概念更新,也許有一天,它也能在國內擁有“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