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成 | 作為方法的“歷史-人心”——重構當代中國文化批評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04-17 21:33
羅成|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2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羅成
“文化批評的中國化”,是當代中國文化批評亟待自覺的重要問題。歷史地看,“文化批評”最早通過1980年代的“理論旅行”進入中國學界,標誌性事件是1985年美國學者詹姆遜(F. Jameson)受邀訪問並講學於北京大學。他的演講內容主要是當代西方文化理論,隨後翻譯出版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不僅奠定了人文學術新領域“文化批評”的學理性基石,並且揭開了“文化批評在中國”的歷史性帷幕。
1992年以降,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化,“文化批評”也由“文學批評”的最初附庸而逐漸獨立發展,直至今日蔚為大觀。一方面,當代文化風雲變幻,經歷了1990年代社會主義經濟市場化的劇烈轉變,“美學熱”迅速退潮,主流文學日益邊緣化,文化產業蓬勃興起,媒介文化日新月異,電視、電影、網遊、微博、微信、短視頻“你方唱罷我登場”。另一方面,文化批評與時俱進,漸次發展出人文主義、審美主義、歷史主義三種路徑。人文主義批評,遠承“文學是人學”的歷史召喚,從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到21世紀“文化詩學”,彰顯出文學研究對文化批評的包容性接納。審美主義批評,接受西方體驗美學的生命啓蒙,浸染着中國儒道文化的“感興”“虛靜”,吸收心理論、語言論、生活論等方法,構建了“日常生活審美化”“興辭論批評”等當代文化批評話語。歷史主義批評,始於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的知識移譯尤其是文化現代性問題域的開啓,通過重點借鑑文化社會學、知識譜系學、批判理論,將文化批評推進為場域化、譜系化、機制化的歷史展開。
進言之,**“文化批評在中國”固然呈現為人文主義、審美主義、歷史主義的多元圖景,背後實則隱現着互補性的學理指向:對於“現代性”的追求及其不滿。**易言之,當代中國文化批評在走向世界性、普遍性進步敍事的同時,重新發現了地方性、特殊性的歷史面容。啓蒙與反啓蒙這一組異邦新聲的變奏召喚,令當代中國文化批評面臨着一種二元困境:似乎只能二者選其一,或者居中調和。然而,要害在於,這對矛盾根本上是西方現代性的內部產物。作為後發現代性的當代中國文化,應在鏡鑑他者的同時重新認識自我,以避免日本學者竹內好所言的“轉向”心態:“當觀念與現實不調和時,便捨棄從前的原理去尋找別的原理以做調整。觀念被放置,原理遭到拋棄。文學家將捨棄現有的語言去尋找別的語言。他們越忠實於所謂學問所謂文學,便越熱中於舍舊求新。”當代中國文化批評的當務之急,並非限於追逐更新的潮流,更應夯實腳下的基石,找準自己的道路,從“文化批評在中國”走向“文化批評的中國化”。
本文嘗試提出“歷史-人心”這一命題,並將它作為“文化批評的中國化”的認識論裝置。“心”與“史”的關係,既是探究中華文明傳統的原理性問題,又是貫穿人文性、審美性、歷史性等當代文化批評的方法論問題。本文將立足中西文明互鑑,融合相關思想資源,從主體性根基、認識論邏輯、人文學旨趣三個維度追問“人心與歷史的綜合如何可能”的初步原理,在結構化、脈絡化、事件化的歷史視域中,探詢把握歷史主體精神能動性的有效方法,以期為當代中國文化批評的方法論自覺提供一種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可能路徑。
人間感:“歷史-人心”的主體性根基
在著名攝影批評《關於他人的痛苦》的開篇,美國文化批評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講了個故事:1938年6月,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出版了《三幾尼》(Three Guineas),對人類戰爭的根源做了勇敢的但不受歡迎的反思。書中面對律師所問:“你對我們如何防止戰爭有什麼看法?”儘管伍爾夫在回答中表達了對戰爭的反感,還援引並細讀了西班牙政府傳佈的戰爭照片,但在桑塔格看來,伍爾夫的理由卻絲毫未能擺脱陳詞濫調。桑塔格認為:“像伍爾夫那樣只在照片中閲讀一般厭戰觀點所證實的事情,等於是在迴避與西班牙這樣一個有歷史的國家的接觸。這等於摒棄政治。在伍爾夫眼中,就像在很多反戰辯論家眼中,戰爭是通稱,而她所描述的影像,則是無名的、通稱的受害者。”桑塔格對伍爾夫的批評狠狠打擊了唱着“人性”老調子兜售脱離歷史、脱離現實的廉價同情心的作家們。戰爭當然是殘酷的、慘烈的,但是真實的戰爭中必定有正義與不義,必定有紮根於民眾精神及其所處社會結構、歷史脈絡的大是與大非,濫情的人性感傷很容易淪為觀看他人痛苦時藉以宣佈自我清白的安慰劑。對此,桑塔格強調:“如果不對影像進行思考,那麼距離再近,也仍然只是觀看。”
實際上,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哪怕自己身臨其境,如果不對此境況、事件、人物、情感進行“思考”,同樣,那麼距離再近,也仍然只是“觀看”。早在古希臘時期,致力於認識自我的蘇格拉底就區分過三種類型的“看”:**打量(theaomai)、觀察(skeptomai)以及瞧(horaō)。**其中,“打量”強調心智的參與,“理論”(theory)一詞便源於這種類型的觀看;“觀察”則更重視感官和經驗的作用。同樣,亞里斯多德也強調過“看”的多重意義:“我們看見那些圖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為我們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斷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比方説,‘這就是那個事物’。”看,並非僅僅是直觀感受,同時也是理性求知,關於對象形成充分的理解。據此,桑塔格的文化批評強調富於認知思考的“打量”,而非純粹感官經驗的“觀看”。

蘇珊·桑塔格
作為方法的“看”連接着當代文化批評及其古典文明起源,體現出認識論、倫理學、形而上學的多重意義。始終凝視着同時代鮮活面容的文化批評,**不僅是一種感受性、經驗性的觀看,而且是一種歷史性、結構性的認知,更能成為一種理智性、真理性的洞徹。**在闡釋歌德的《親合力》時,被譽為“德國文學唯一真正的批評家”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特別強調“批評”與“評論”的差異:“批評所探尋的是藝術作品的真理內涵,而評論所探尋的是其實在內涵……一部作品的真理內涵越是意義深遠,就越與其實在內涵緊緊地連在一起而不易被察覺。”本雅明揭示了藝術作品具有真理性與實在性的雙重內涵,並指出批評和評論所承擔的任務有所不同。本雅明打了個有意思的比方:“如果把年歲遞增的作品看作熊熊燃燒的柴火堆,那麼站在火堆前的評論家就如同化學家,批評者則如同煉丹士。化學家的分析僅以柴和灰為對象;而對煉丹士來説,只有火焰本身是待解的謎:生命力之謎。與此相似,批評者追問的是真理,真理那充滿活力的火焰在那曾經存在事物的沉重柴火上和那曾經經歷了一切後輕飄飄的灰燼上繼續燃燒。”由此可知,**評論處理的是肉眼可見的語言、圖像及其作為實在軀體的意義,批評則是透過心靈之眼去攫取可見之中不可見、有形背後無形的精神對象及諸般奧秘。**無獨有偶,《莊子》亦有言:“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注云:“形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薪有窮,火無盡。”薪盡火傳的意象喻指中華文明傳統的“養生”“不朽”之道:立德、立功、立言。“火”所藴含的無形之神,亦即德行、功業、精神的創造力,遠遠勝過有限人生的有形之薪。以此觀之,真正的批評之道需要透過易逝之形去把握無盡之神,莊子的“常存之神”亦即本雅明的“生命力之謎”,皆指源於物質生命而又超越物質生命的精神創造力。
回到桑塔格與伍爾夫之爭,真正的批評不應只是抽象的反戰、濫情的傷感,而應透過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影像看到歷史真實的人心向背。相較歐美國家官方所謂“不干涉”的中立政策,來自全世界53個國家的4萬多名志願者,包括進步青年、工人、醫生、作家和知識分子,湧入西班牙支持共和國政府對抗佛朗哥政變及其背後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海明威(E. M. Hemingway)、奧威爾(George Orwell)、卡帕(Robert Capa)、奧登(W. H. Auden)、伊文思(Joris Ivens)、白求恩(H. N. Bethune)都在其中。這一國際反法西斯陣營中更有諸多中國人的身影,這場戰爭被譽為“震撼世界良心的內戰”。歷史的風雲並非僅有戰爭的傷痕顯影,更留下了那些毅然直面殘酷現實的抵抗行動及其國際主義情懷,他們視死如歸,雖敗猶榮。較之觀看影像的評論,思考人心的批評,也許更能切合掩映於歷史滄桑之中的人間正道。
思考人心的批評,亦即富於人間感的批評,而非直觀人性的評論。兩者的關鍵區別在於,**是否建立了一種既內在於批評者、也內在於歷史的“人間感”。**這種“人間感”既不同於伍爾夫那樣的“人性感”——意在通過旁觀他者的痛苦而誘發中產階級羣體那幾滴“人性”或“愛”的淚水,也區別於鮑曼(Zygmunt Bauman)那樣的“人口感”——帶着文化悲觀主義而將他者完全視為多餘的、過剩的“廢棄的人口”。“人間感”打量、思考的他者並非只具有作為對象而被觀看、被感受的客體性意義,因為他者同樣是一個主體,哪怕在邊緣化生活、嚴酷性歷史處境中同樣擁有自身的友情、善意、愛等豐富人性亦即人心。“人間感”籲求發掘對象自身的主體性及其能動性,突破西方近代以來的主客二元思維及工具理性,以敞開他者本真性的方式凸顯他者同樣擁有的主體性尊嚴。進一步,“人間感”將具有能動性而非自慰性的“人心”放置到“歷史”中加以結構化、脈絡化的把握,發掘“歷史-人心”作為事件的價值與意義。“人間感”不僅是主體性的,也是歷史化的,更是交往式的。見證個體苦難,不是為表達居高臨下的精英式同情,而是要突破“啓蒙”與“反啓蒙”的傳統知識幻象,記錄苦難個體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呈現基於真實歷史關係而非想象同情關係的“人世間”。“人間感”,就是要對人心與歷史的雙重變奏保持總體性的目擊道存。
一種“歷史-人心”的文化批評亟待開啓。從“人間感”出發的文化批評,需要將“人心”透過“歷史”來鑑別,將“歷史”置於“人心”而掂量。“歷史-人心”作為文化批評的認識論裝置,立足於“人間感”的涵育,提供分析、判斷、穿透社會結構和歷史脈絡的總體性闡釋效應,從而超越直觀式、個體性、浪漫化的“人性論”。“人間”如果僅僅只是早期現代啓蒙式“人學”詠歎調,那就太容易為當代資本操縱的大眾媒介所收編利用,流衍為小清新、小確幸等拉康式“想象界”的自戀文化或雞湯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抽象個性浪漫的單向度“人學”,和這個商品時代高度同質化而又加速流動的“交換價值”,構成了某種隱秘共謀:前者以重視“人”的名義而對具體的人、歷史的人進行了釜底抽薪式的簡化,後者則用“價值”的招牌遮蔽了使用價值、社會價值。借用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説法:“古典美學和商品拜物教都努力清除事物的具體性,把事物的感性內容從純粹的理想化形式中剝離出來。”作為方法的“歷史-人心”,既反思了康德主義的形式主義、非功利主義,又繼承了康德對“主體性”“自然向人生成”“文化—道德的人”的一貫關切,並將“人心”置於一個活生生的、流動的、物質的視野中重新考量。因此,“歷史-人心”的文化批評,本質上也是一種當代中國歷史唯物主義新形態的人文批評。
“人間感”是“歷史-人心”文化批評的主體性根基,它彰顯了主體性,也包含了主體間性,更承載着物質性、歷史性的認知潛能。在歷史遠未終結的當代,“人間感”彷若一個歸去來兮的幽靈,它以刺目的方式告誡着世人:“人間”的整全意義是“人-間”,亦即“人人之間”,這是一個有着鮮活物質痕跡與具體歷史温度的主體性際遇空間,而絕非那種後現代懷舊風景中顧影自憐式輕飄飄的“人性”和“愛”的造物。這麼説並不是要徹底否定“人性”與“愛”之於“人間”的意義,而是要強調只有物質性、歷史性及其造成的豐富性、能動性才能注入“人性”與“愛”以真正的“人間感”。魯迅曾説“人必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又説“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愛情若此,人性亦若此。“人間感”首先是生活於真實社會結構與歷史脈絡中的主體身心狀態,只有這一主體身心狀態與社會、歷史之間的連帶關係被自覺意識,才能產生附麗於真實人間而具豐富意藴、切人切己的“人性”與“愛”。並且,這種唯物的、歷史的連帶關係未必總能想當然地開展為順承、和諧、相安的“好狀態”,它往往飽含着主體身心與社會結構、歷史脈絡之間的牴牾、磨礪乃至超克。“人心”只有在“歷史”中不斷自我成長、自我革命、自我超越,才能真正具有完整生命力與充盈現實感,也才能實現“人性”與“愛”的“更新,生長,創造”。一言以蔽之,“歷史-人心”的文化批評,作為“人心的歷史”具有述願的意義,而作為“歷史的人心”更有述行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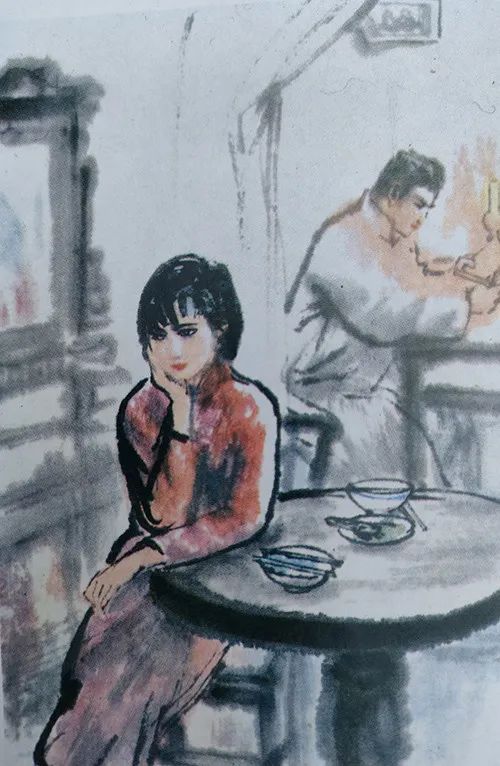
《傷逝》插圖
事件性:“歷史-人心”的認識論邏輯
隨着“歷史的終結”“藝術的終結”“哲學的終結”“意識形態的終結”等逐漸退潮,人類社會未曾終結的現實將歷史邏輯的再認知作為重大課題擺在了後黑格爾時代的延長線上。面對經驗與理論的挑戰,當代中國文化批評迫切需要重構恰切的歷史認知方法,亟待擺脱簡單陳舊的“還原論”和刻板固化的“目的論”,既要遠離不思進取的庸俗社會學與教條歷史主義,也要避免淪為戴着各種面具的虛無主義,自覺將文學研究、文化批評、文明闡釋放到一種更多元、更能動的認知框架中予以把握,保持對多元決定因素的經驗省察,不放棄對偶然性潛能的理論賦形。這種歷史認知方法,包含着歷史意識、社會意識、主體意識三者的內在榫卯,旨在更流動、更豐富、更具生成性地把握中國文化經驗與中華文明傳統。
作為方法的“歷史-人心”,具有內在連帶邏輯:“人間感”奠定了文化批評的主體性根基,以“人人之間”的尊嚴政治為倫理旨趣;“事件性”則凸顯着文化批評的認識論邏輯,以“偶然事件”的能動哲學為歷史要義。關於“事件性”的理解,我們可以借鑑歷史社會學的闡釋。美國學者休厄爾(William H. Sewell Jr.)針對20世紀以來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融合趨勢,強調歷史社會學向主流學界提出的挑戰,關鍵之處就在於用特殊的時間性概念挑戰了主流觀念。在歷史社會學中,有兩種主流的時間性概念:“目的論”和“實驗性”。“目的論”往往認為“是方向持續前進的永恆法則塑造了歷史”,據此判斷歷史的意義是“不為人知的長期因果力量的結果”,如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及其年鑑學派,其問題是忽視了歷史表層大量偶然事件。“實驗性”援引科學方法論,對數量有限的代表性歷史對象展開比較分析,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對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比較研究,以類似“自然實驗”的邏輯提煉“社會實驗”的結論,其問題是用非歷史性的比較方法造成了歷史的“肢解”與“凍結”。**休厄爾則提出第三種時間性概念即“事件性”(eventful)。他認為,雖然歷史中多數事情不斷重複地再生產出社會和文化的結構,“事件”卻是“能夠顯著改變結構的罕有一類”。一方面,“實驗性”時間性注重因果法則在社會生活中的一致性,“事件性”則認為社會關係中的因果性反而受制於文化範疇的內涵及相互關係,從後者來看,社會關係並非一成不變;另一方面,“目的論”強調普遍時間的同質性與一貫性,“事件性”則認為時間充滿了異質性,進而主張偶然事件關乎歷史整體,甚至有能力改變社會關係的深層與核心,**從後者來看,社會關係並非一以貫之。休厄爾提出側重偶然、意外、不可預測的“事件性”,意在關切歷史變化的潛在可能:“歷史有着頑固的持續性,也有驟然的改變”,“有關整體的偶然性的假設,不是説所有事物都在持續變化,而是説社會生活中沒有什麼是不可改變的”。

小威廉·H·休厄爾
“事件性”撬動的是因果一致、普遍同質的社會生活時間觀,通過發掘更為內隱的文化範疇,它重新關注那些表面雜多且具偶然性的平凡事情的不凡之處,並將這些事情予以概念化而形成“事件”。如果將休厄爾的“文化範疇”置換成“人心”,那麼,現代歷史社會學的理論反思,或許同時也呼應了中華文明傳統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經典命題。“事件性”跳脱了主流時間概念的目的論與實驗性,在近代歷史科學的必然性與決定性之外,在歷史認知意義上發掘了更顯主體性價值的偶然性與能動性。
對於當代中國文化批評而言,真正的“事件性”分析絕非僅僅描述事件、展示事件、重構事件,僅此實在無法與傳統實證研究形成區別。在常規的人文研究與文化批評中,無論重構歷史事件抑或還原文化語境,多少仍留有“還原論”色彩與“目的論”痕跡。返回歷史語境現場在逐漸成為重要文化批評方法的同時,也隱蔽地強化了以“視覺性”為認識論裝置的近代科學方法論。真正值得反思的反而應是那句廣為流行的網絡文化口頭禪——“有圖有真相”。“圖”等於“真相”嗎?“眼見”一定“為實”嗎?這般追問,並非意在附和時下所謂“後真相”的流行論調,而是意在深入思考一個更具人文意義的問題:如何在豐富的人心的歷史當中捕捉、把握、分析、賦形那些可見歷史事物背後不可見之人心,比如時卷時舒又瞬息萬變的情感褶皺、隨勢擺盪而起伏難料的意志微瀾等。“返回事情本身”或“回到歷史現場”並不代表理解了“事件性”,敍述、描寫也並不簡單等於思考、打量。“事件性”雖然關注偶然、意外與不確定的雜多事情,但絕不同於“故事”與“八卦”。“事件性”的敍事視野是開放的,具有生產性,它指向非感覺、非經驗、非表象的可能世界。“故事性”的視野則是閉合的,具有回溯性,它指向作為感覺、經驗、表象的現實世界。“事件性”不僅影響着我們的昨天,更以其生生不息的歷史潛能塑造着我們的今天和未來。“事件性”既具有“述願的”歷史效果,更暗含“述行的”歷史動能。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下、把握未來,這構成了“事件性”方法論的第一層要義。進一步,“事件性”又以飽滿的“人間感”為契機與旨歸,並非為成見或教條的簡單論證或直觀批判服務。“事件性”是浸透了“人間感”的歷史認知。**“事件性”方法論的第二層要義在於,“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如若缺失了糾纏於歷史與精神之間的主體身心狀態,它所能達致的效果恐怕很難擺脱傳統意義上的史觀批評或實證批評,同時突破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二元對立思維窠臼正是其題中之旨。
據此,當代中國文化批評應借鑑一種歷史反思的雙重視野。英國學者卡爾(E. H. Carr)辯證地指出,一方面,歷史並不能簡單等於“事實”:“對於歷史學家而言,事實與檔案是本質的東西。但是不能盲目崇拜事實與檔案。就其實質來説,事實與檔案並不構建歷史。”因為使“事實”成為“歷史”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學家以自己的思考重新構建過去的過程”。另一方面,歷史也不能被簡單當作“是歷史學家製造的”,因為這將“從根本上排除歷史的客觀性”。卡爾提供了一種關於“什麼是歷史”的重審契機:歷史既不是無所不包越多越好的“事實”堆積,也不是自由任性隨意編纂的“主觀”製造。“事件性”可視為在主觀與客觀、實證與解釋、過去與現在之間纏繞展開的某種獨特講述技藝。它既要避免直觀地指認“事實”為“歷史”的實證史學,又要避免非反思性地賦予“現實”以“意義”的史觀史學,因為這兩者皆可能陷入教條主義或虛無主義的思想泥淖。卡爾特別提示人們,“如果歷史學家不能以適當的方式接近其正在研究的人物的內心世界,也就不能撰寫出適當的歷史”,他將這種“適當的方式”命名為“富於想象的理解力”(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但是,卡爾如此接近被研究者的“內心世界”且“富於想象”的“適當的方式”仍有未曾思及之處:歷史對象的“內心世界”是純然自明的嗎?如果不是,那麼以怎樣的“想象的理解力”才能觸碰到歷史對象那豐富而微妙的“內心世界”?
“歷史-人心”要藉助“想象的理解力”來接近,其邏輯究竟是什麼呢?王汎森區分過“事件的發展邏輯”與“史家的邏輯”。在他看來,兩者的差別在於有無“後見之明”。**“史家的邏輯”是偏向於以結果推斷過程。“事件的發展邏輯”則要人看到,“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同時存在的是許許多多互相競逐的因子,只有其中的少數因子與後來事件發生歷史意義上的關聯,而其他的因子的歧出性與複雜性,就常常被忽略以至似乎完全不曾存在過了”。**因此,“事件”的意義就在於“如何將它們各種互相競逐的論述之間的競爭性及複雜性發掘出來,解放出來”。這一區分可以解決卡爾留下的疑問:歷史對象的“內心世界”並非純然自明,對“內心世界”的把握要自覺立足於對“事件的邏輯”或“史家的邏輯”的判別。而要避免僅僅在“後見之明”中把握“內心世界”,就應納入“事件性”的複雜性、豐富性及其內在張力。就“內心世界”本身而言,與其將它理解為“思想觀念”,毋寧理解為“精神事件”。“思想觀念”立足於“觀看”,“精神事件”則籲求着“思考”,這就是“歷史-人心”作為文化批評方法的認識論邏輯。
精神史:“歷史-人心”的人文學旨趣
通過“事件性”對“目的論”“實驗性”“故事”“檔案”“後見之明”的認識論突圍,“歷史-人心”這一認識論裝置逐漸呈現出一幅鮮明的卯榫圖景:文化個體的身心狀態深植於歷史感與現實感的纏繞境況之中。“歷史-人心”作為文化批評方法需要內在地把握歷史與人心、可見與不可見、感官經驗與非感官經驗的辯證法則,有效展開對“精神事件”的賦形與深描。
**“精神事件”的發現,還需要一種獨特的人文“好奇心”,亦即“以不奇為奇”的領悟力。**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發問:“什麼是作為事件來論述呢?”在溝口看來,“事件”即指“對那件事的出現以驚奇的目光進行關注”。他打了個有趣的比方,“事件”就像在沙漠上某個時間突然出現了一頂帳篷。對“事件”的驚異,應該是目擊“帳篷的出現”而生髮,而非“在帳篷中眺望帳篷”。溝口強調,要避免“為論述帳篷而論述帳篷”,亦即“為了材料的材料論”“為了結構的結構論”,則要關注真問題,亦即“帳篷的存在自身”就是一個“事件”。無獨有偶,歷史學家劉志偉也特別強調,“歷史學者的理性”並非在於將事實真相變為宗教,而是那種把握歷史變化的思辨能力。他稱之為“結構化和再結構化的能力”,並異曲同工地打了個比方:“我所謂的再結構化不是要把一座房子一再地拆了再重建,而是把這個房子本身的建造和改造的過程作為研究的主題”。無論“帳篷”還是“房子”,均指向避免用某種理所當然的自明性態度去對待歷史與人心的基本立場。
由此,“精神事件”的考察應秉持一種“非自明性”“去熟悉化”的態度,具體方法上,可列舉三個概念性路標。其一,“脱直觀理解”,不為傳統研究中二元對立的精英或大眾、主流或邊緣等立場性敍事所統攝,跳脱於直接對反的直觀籠統邏輯,以切問近思的方式扎進歷史深層的混雜、曖昧、糾結當中,把脈直觀理解有意逃避或無力迴避的歷史-人心難題。其二,“脱後見之明”,跳脱規範性、目的論的慣習敍事思維,特別是掙脱回溯性建構敍事的“後見之明”,不再將任何文化語境、歷史現場僅僅作為朝向某種未來必然方向的準備過渡階段,避免以“目的論”遮蔽“生成性”,深入展開人心與歷史之中的那些豐富、參差、錯雜、翻覆的經驗褶皺或精神剖面。其三,“脱認同敍述”,避免簡單以對象的認同為鵠的。傳統人文研究的還原或複述的方法很容易使研究者產生一種對象式認同,從而使文化批評簡化為有關對象的合法性論證。“同情的理解”並不等於“認同的理解”,“同情”應該是對批評對象持有一種“入乎其內而又出乎其外”的態度,既非簡單推崇或辯護,也非刻意批判或否定,而是實事求是地評價對象的歷史成就、歷史侷限,在緊貼對象的同時保持相對化距離,真正理性地打量與思考對象,肯定其所是,反思其所非。
立足於上述三種方法,“歷史-人心”就呈現為處於完整、動態、糾纏的世界結構中的一種歷史主體性的豐富展開。作為方法的“歷史-人心”,本質上是一種關注“精神史”的人文學闡釋,既不同於傳統的“思想史”“學術史”,也不同於近年興起的“觀念史”“概念史”,它涉及的是一種對人、事、物之間的流動狀態及卯榫結構的歷史性把握,包含着重新理解自我、詮釋歷史、改造世界的能動性契機。
如何避免表面的文人情緒又不失本色的人文情懷,迄今仍是當代中國文化批評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現代性工程中一個未完成的計劃。桑塔格“關於他人痛苦”這一文化批評的典範性啓示就是待人如己、隨物賦形,在一種現實主義的思考與打量中,仍不脱理想主義的初心與旨趣。這種理想主義不是悲苦、傷感、哀情於滿足對普通民眾的施捨、憐憫、慈善,而是積極發掘“人人之間”的內在主體性,從而區別於精英化的民粹主義與文人化的人道主義,區別於對“人”的孤立把握與客體對待。這種理想主義不是空泛、輕浮於“人性感”的抒發、喟嘆,而是要將生命之根扎進更為柔軟、細膩、養分充足的社會歷史土壤之中。“歷史-人心”的人文學旨趣可稱為“精神史”,即通過一種切於己身的連帶方式重新打開並進入人與社會、歷史糾纏的那個鮮活過程,去把握“人”之若此、“歷史”之若此的深層肌理。這一包括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辯證批評機制,我們不妨稱之為“人文的歷史化”。

“人文的歷史化”是“精神史”的核心要義,也是“人間感”與“事件性”結合而生的批評路徑。其啓示在於:文化批評應以“人間感”為基礎,它既可以呈現為主觀努力的主體精神,但又要與純粹主觀、不加反思的利己主義相區分。這一努力也可能遭遇現實文化的危機,因而更要避免掉入由懷疑主義誘發的虛無主義。鑑此,堅持理想主義就必須重構理想主義,重構的契機就在於以現實主義的方法紮根於自身的社會結構和歷史脈絡之中,以歷史、社會為媒介,捕捉“事件性”,重建“人間感”。傳統的人文主義批評,或由歷史理解的不足,常流於文人化的情感修辭;傳統的歷史主義批評,或由人文理解的匱乏,常流於學者化的知識話語。兩者的實質在於,為情緒而情緒,為知識而知識,以致失落了真問題,使人心與歷史相斷裂,造成了對“人間感”的嚴重隔膜。“人文的歷史化”打開了“人文”走向“歷史”的坦途,同時昭示了“歷史”迴歸“人文”的新境,故亦可稱之為“歷史的人文化”。對於現代西方學術方法,林毓生有過反思,“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因受到基本假定的限制,對人間事物的瞭解實在是有限的”,他特別提醒,“在攻讀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之時,我們要特別注意不要被其術語所眩惑,同時我們要探討它的基本假定與表面上看去頗具系統的理論之間的關係”。林毓生對“人間事物”的關切,並非意在否定社會科學,而是反思如何將人、事、物的研究置入更現實的“人間關係”而非“理論關係”,此即“歷史的人文化”。
在“人文的歷史化”與“歷史的人文化”這一辯證構造中,“歷史-人心”更鮮明呈現為“人文”與“歷史”的互相進入,既不是任隨跨學科的風尚使然,也不是發端傳統文人化的詠史喟嘆,而是出於“精神史”的內在理解。用老百姓的話來説,“歷史人心”就是“世道人心”。“世道人心”以主體內在的身心狀態、精神感覺(人心)為媒介,勾連世界外在的社會結構、歷史脈絡(世道)。“世道人心”在進行細膩、體貼的歷史分析的基礎上,呈現出一個個遠比直觀籠統印象更為複雜的主體身心狀態與精神感覺,然後將此種主體身心狀態與精神感覺再回置到一個屈折、糾纏、層累的社會結構及歷史脈絡中去審問、慎思、明辨,並經由“主體內在連帶”獲得真正的“精神史”理解。
所謂“主體內在連帶”,可作三層意義的理解。首先,它是指每一主體自身的連帶性,它並不將“人”的感性、知性和德性分成幾截,而是注重將“人”作為情感之我、認識之我、道德之我的完整結構來把握,由此才能抓住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超出固化身份認同標誌之外的鬱結、焦灼、憂慮、不安。其次,它是指每一主體與社會結構、歷史脈絡之間的連帶性,即這一完整主體並非靜態自足的,而是需要進一步放到流動變化的社會歷史境況中加以把握,才能真正破解他們如此鬱結、焦灼、憂慮、不安的深層結構性、歷史性因緣。**最後,它是指批評對象與批評者在“精神史”上的連帶性。**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第十八條中指出:“歷史主義心滿意足地在歷史的不同階級之間確立因果聯繫。但沒有一樁事實因其自身而具備歷史性。它只在事後的數千年中通過一系列與其毫不相干的事件而獲得歷史性。以此為出發點的歷史學家該不會像提到一串念珠似的談什麼一系列事件了。他會轉而把握一個歷史的星座。這個星座是他自己的時代與一個確定的過去時代一道形成的。”本雅明區分了兩種歷史認知方法,一種是“歷史主義”,它將歷史視為因果聯繫的一串念珠,看似前因後果緊密聯繫,實則抹殺了每個歷史事件的自身質地及特殊價值;另一種則是“歷史星座”,每一歷史事件自有其閃光之處,事件之間的關係不是由目的論或因果性的時間性決定,而是由哪怕時隔千萬光年的間距卻同樣自身閃光的特殊品質而遙相致意。“歷史星座”跳脱了“歷史主義”,在幽微星光中看到了另外一顆顆“歷史人心”的亙古共鳴。
“主體內在連帶”敞開了有關“歷史-人心”的諸問題,批評者藉此通向“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從而獲得“都和我有關”的“精神史”體驗。**在三重連帶性中,核心工作在於對“主體”賦以歷史性“去蔽”(Aletheia),並以此為契機,不僅突破近代西方形而上學的確定性真理觀及其主客二元對立的表象思維慣習,更要努力在歷史與社會的複雜規定性中重構自我。**那些不曾基於自我困惑、自我尋覓、自我反思的文化批評,實質上都是欠缺“人間感”的抽象之理、概念之理、形上之理。作為當代中國文化批評方法的“歷史-人心”,籲求“人文”與“歷史”、“人心”與“世道”等種種糾纏、屈折與褶皺在主體感覺、主體認知、主體意志上的不斷展開。

餘論
從“文化批評在中國”走向“文化批評的中國化”,是當代中國文化批評直面的時代性課題。“歷史-人心”作為一種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理論命題,其學理邏輯實則依託一條極為重要卻尤待澄明的方法論原則,即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一貫強調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科學方法。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歸納“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時,以“人”為例展開方法論闡釋。馬克思指出,古典經濟學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研究,看似正確,實則錯誤,因為拋開了階級、僱傭勞動、資本、交換、分工、價格等要素,“人口就是一個抽象”。馬克思主張,必須從“關於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深入到“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中去。在他看來,**“具體之所以是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燭照下,我們不難發現,一方面,當代中國文化批評從人文主義、審美主義走向歷史主義,不斷展開的正是有關人、文化、社會、歷史等認識對象的具體化、豐富化。與此同時,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學理意義上,另一個“具體的”方法論問題日顯重要:文化批評究竟如何實現中國化?正如對馬克思主義原理不能照抄照搬一樣,我們也不能將源自現代西學的文化批評範式簡單直觀地用於闡釋中國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
當代中國文化批評需要避免陷入對各種西方文化理論隨波逐流式的路徑依賴。借鏡西方固是學理通途,避免“反認他鄉作故鄉”亦須時刻留意,文化批評的最終目的還是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撥開各種“主義”之迷霧,西方文化批評的真正精髓在於通過自我反思達到自我更新。一旦跳出通常以德國批判理論、法國結構主義、英國伯明翰學派等為中心的學科化思路,直面當代中國文化批評的邏輯起點及學理意義,我們真正面對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在當代中國的歷史社會中理解當代中國人?
再次回到當代中國文化批評的歷史原點,重審詹姆遜那場頗具“事件性”色彩的講演,他從一開始就重點詮釋了“文化”(culture)的三重含義:**精神性的、社會性的、裝飾性的。在其中,個性的形成與人格的培養恰恰構成了“文化”的第一要義。三十多年來的當代中國文化批評走過了一段從“抽象的人文”到“具體的歷史”的進程,在日益深入展開批判性社會反思的同時,還應重視返回人心培育這一“文化的”(cultural)歷史初心。時至今日,馬克思的説法仍深刻提示着我們,文化批評最終要回到“人”,不是作為“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個在諸多規定和關係之中的“豐富的人”。孟子亦言:“仁,人心也。”人心的本質,不是抽象個體的自然人性,而是歷史共同體的“社會—道德”人性。走向“歷史-人心”的真批評,如採用一個更富於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的提法,那就是要達到“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見人還是人”的境界。“文化批評”的根本意義就在於經由反思性、批判性途徑而達致自我認識、自我培育、自我更新。**致力於分析、理解、闡釋“歷史-人心”,當代中國文化批評才可能提煉出那歷史灰燼或現實景觀中的生命力及人文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