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季節」掉分了,因為爹味?_風聞
Sir电影-Sir电影官方账号-05-09 12:41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
35萬人打出9.4。
沒有意外,《漫長的季節》口碑坐穩了五年內國劇頭把交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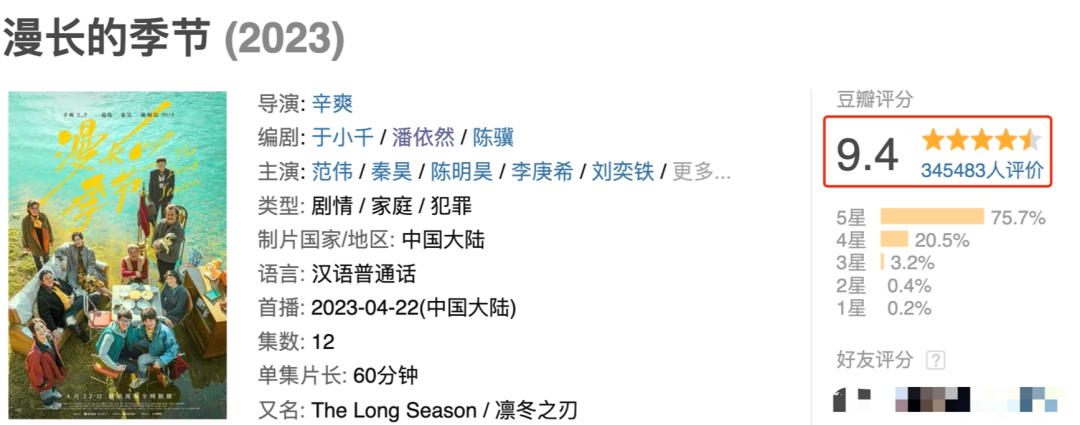
劇紅是非多。
大結局後,對《漫長的季節》火力最集中的差評是——
“爹味”。
理由:創作者是男的,主角也都是男的,男人****戲太多,女觀眾無法共情。
-男的能不能不要再當主角了
-非常非常陳舊的男性羣像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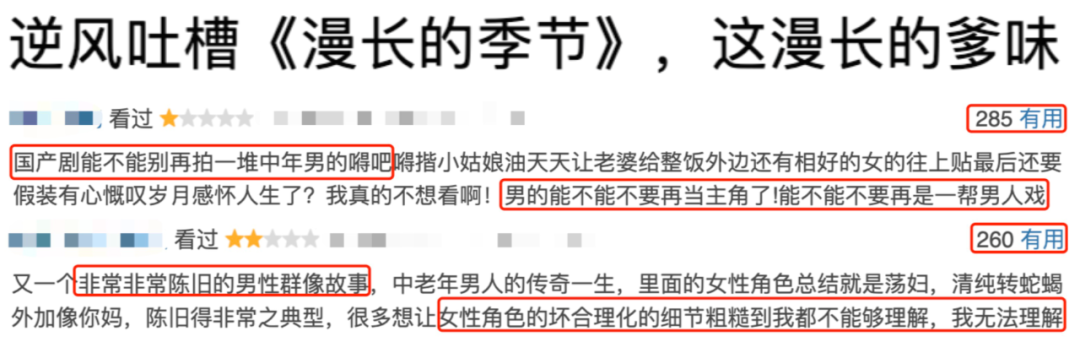
Sir屬實有些沒想到。
任何人都有因為無法代入、棄劇、差評、打一星的權利……

但是。
比起純粹感性的“不愛看”。
對一部作品提出**“男性視角”**的批評,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將作品讓位於更醒目的旗幟——追求平等、表達多元、解放人性……
這是我們現實中迫切的訴求。
如果將它們視為影視作品的責任,以及評價標尺,Sir會本能地打個問號。
或者再把問題拓寬——
當我們越來越在意、想要區分一部作品是“男性視角”還是“女性視角”。
我們會失去什麼?
01
男性視角是原罪?
首先釐清一個概念。
什麼是“男性視角”?
男性視角,與女性視角,都是一種敍事傾向,兩者平等。
影視批評中的確有一種與男性有關的概念,並非“男性視角”。
而是“男性凝視”。
但它的重點不在“男性”,而是**“凝視”**。
概念出自一位美國電影學者,她認為好萊塢的主流電影中,女性過多地作為男性慾望的客體出現,往往扁平、單一、刻板,對故事沒有太多的作用,僅僅作為花瓶和工具,來滿足男性觀眾的奇觀心理。


△ 經典電影《後窗》《迷魂記》都收到了“男性凝視”的評價
那麼,《漫長的季節》“凝視”了女性嗎?女性角色,只是男性的佈景板嗎?
從重要性上。
女性角色沈墨,當之無愧第一女主。
兩個懸案的核心,對劇情有關鍵作用。她被傷害,被控制,被保護,被追捕,承擔着複雜的戲劇性,也呼應了《漫長》要表達的主題——無常的命運,無力的時代,無解的悲劇。


其次,羅美素。
有人指責,不就是中國式傳統媽媽?國產劇老多了,已經不想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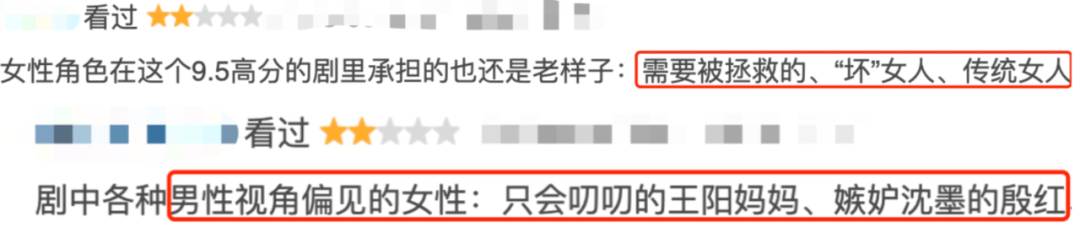
Sir覺得很可惜,因為導演明明塑造了一個非常鮮活的媽媽。
羅美素是全職主婦,但這不是選擇,而是受了工傷,被迫下崗。
為了不給家裏添負擔,她一直想討回醫藥費,爭取公道。
丈夫和兒子關係惡劣,她卻能讓兒子敞開心扉。
羅美素,其實比這個家的主導者王響,活得更明白——只有她看見了自己這代人的侷限,去理解和感受兒子的叛逆:
我們這身上是有個圈的
就在那兒按部就班地在圈裏那麼走着
也沒人問為啥 也沒人到圈外溜達過
就連踩了個線都害怕

或許羅美素的戲份不如王響。
但你能説,這不是一個鮮活的角色嗎?
在Sir看,這部劇的女性角色不僅不是男人和時代的佈景板,反而,她們的生命力越強,越是能折射出絕望、悄然的時代悲劇。
這也引出劇集另一個被詬病的“缺點”——
美化男性,醜化女性。
三個中老年已經一敗塗地,但不管怎樣都還有友誼。

但女性呢,就只會互相嫉妒、傷害。
羅美素説黃麗茹“浪”、大娘幫大爺控制沈墨、殷紅背叛同為淪落人的沈墨……
且不説這部劇的男主,各有各的大缺點,下場也各有各的慘,Sir實在看不出來又能比女人幸福多少。

至於把女性角色的互動,都定義成嫉妒互害,則是脱離人物背景的粗暴判斷。
殷紅和沈墨。
兩個都是活在地獄裏的人。
但對殷紅,最大的惡不是性與暴力,而是窮。

因此劇中借殷紅之口説過,她只是想不斷地抓住“機會”。
而這種機會是中性的。
利益衝突時,她抓住了沈默這個“機會”,就會顯得惡。

利益不衝突時,她挺身而出哄好別的老闆,替李巧雲頂酒,又顯得girls help girls,身有俠氣。
這是“傷天害理撈女”能概括的嗎?
歸根結底。
男性視角,不過是一種敍事策略而已。
姜文説——
我就是個爺們。
我當然只能拍爺們眼中的女人,你讓我拍女人眼中的男人,女人眼中的女人,我都拍不好,也不可能拍好。
《使女的故事》原著女作家也説——
我儘量避免使用“男性視角”這個説法。
**有些想法和態度,男人不可能有,而另外一些,女人又不可能有。**當我使用一個男性角色時,那是因為故事中的某個東西或某個人必須如此傳達出來,或者通過女性角色來傳達的話會改變我的本意。
只存在一種性別視角的作品,當然是我們現階段的遺憾。
但更大的遺憾或許是。
將一切不合理、看不爽的劇情都歸結於——
你是男的,你幫着男的。
好像一部劇出現了男女比例失衡,就要扣上爹味、厭女的名號。
這並非保護弱者。
而是加快讓強者戴上弱者的面具。
02
為何無法共情?
今天要接受男性視角指控的,不僅限《漫長的季節》。
《宇宙探索編輯部》。
男人負責公路旅行、探索宇宙,女人只有旁邊乾着急的份。
厭女。


《不止不休》。
女票苗苗戲份少工具化,又是厭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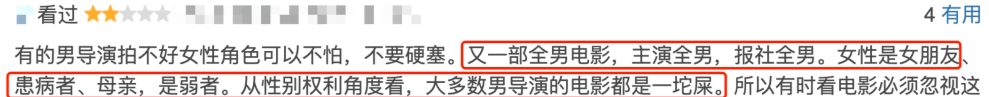

《滿江紅》。
電影裏東窗事發,偽裝成妓女的刺客瑤琴被帶走。
沈騰對士兵高喊了一句——
“殺可以,別糟蹋她”。
很多人揪着這句台詞:大男人、物化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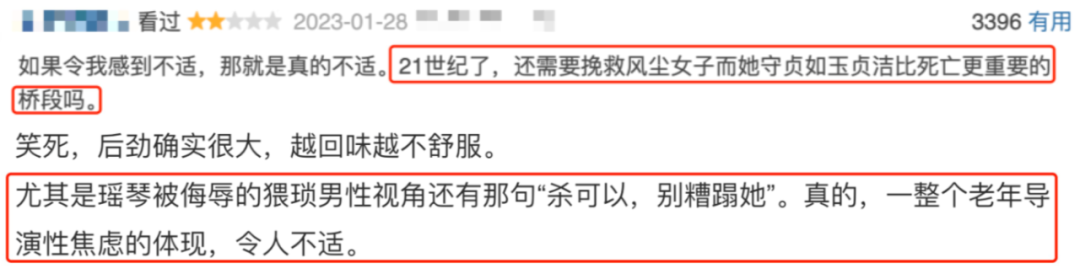
只看性別和台詞,好像是那麼回事。
問題是。
妓女,只是瑤琴“裝”的職業,她更重要的真實身份,是刺殺秦檜的間諜。

回到正常的人性邏輯。
間諜被發現,最可能的心願是什麼?
參照《風聲》被酷刑折磨到僅剩半條命的顧曉夢。
她最大的心願,就是立刻被殺,既是結束痛苦,也是斷絕更多泄密的可能。


於是。
顧曉夢看準機會,刻意咬軍官的耳朵,讓軍官大喊,讓外面的人誤會。
於是。
當別人掏出槍的時候,軍官才那麼生氣,因為審慣間諜的他,早就看穿了顧曉夢的心思。

看完這一段再來琢磨《滿江紅》沈騰的台詞。
你還會覺得,那是一個男人在“道德綁架”一個女人?還是同為間諜的他們,為了刺殺而棄車保帥?
Sir覺得,不是創作者用了男性/女性視角,導致女性/男性觀眾難以代入。
恰恰相反。
當你過分關注所謂性別視角,去評判它是否足夠平衡和公允時,才導致了更徹底的無法共情與代入。
簡單化、二元論的思維固然是“爽”的,但也就隔絕了你與故事中的那些複雜的人物,幽微的人性產生真正的溝通與神交。
回到《漫長的季節》裏舉例。
2016年的沈墨,重回樺林報仇。
有人説,怎麼大爺被殺的細節一點沒拍?反而罪狀更輕的大娘,卻被沈墨惡狠狠地剪指甲、列舉罪狀?

哦,又是搞性別歧視那一套?
男的做了壞事,可以輕描淡寫;女的只是幫兇,就要公開處刑。
進而又得出——
沈墨這個人,只是導演傳達爹味和厭女的“工具人”。
這種潛在邏輯可能比審查更恐怖。
這是在要求一個不全能的角色,一個有創傷的受害者,為了給觀眾一個絕對正義的爽劇結局,就要完美、公平地對分配恨意與懲罰。
細想。
沈墨為什麼恨大娘,她恨的只是大娘,還是大娘背後的廣泛沉默?
大娘是不想幫,還是不能幫?
不能,僅僅是為了維繫婚姻、被大爺精神控制?
想到這一層,Sir也困惑了。
於是又找了一些大爺的細節——
傅衞軍給沈墨寫的信,大爺為什麼能看見?
傅衞軍出獄前死在監獄,怎麼也沒人去查,骨灰直接就到大爺手裏?
再結合大爺對馬德勝説“我認識你領導”,對夜總會老闆説“會帶局長來”,對沈墨暗示:你早晚死我手裏。

大爺施暴的土壤,顯然不是隻有父權。
就像《朗讀者》説的——
文學的核心在於保密的觀念**,**人物性格整個建立在人們之間未能公開的某些信息上,其原因可能是多樣的,或卑鄙,或高尚,以致人們決心守口如瓶。
看一部作品,不要只看它拍了什麼,還要看它沒拍什麼。
有些畫蛇添足,是尺度的必需;
有些欲説還休,是導演給觀眾留的暗號。
Sir就點到這了。

03
人性的視角
Sir當然不認為自己的解讀有多高明。
但當一部劇中不起眼的閒筆,不起眼的人物,都能引起觀眾的注意、困惑和反覆琢磨。
這已經説明它是一部經得起考驗的好劇。
Sir今天説這麼多,就是擔心——
當驚鴻一瞥的《漫長的季節》讓我們看見了國產劇久違的,對觀眾和手藝的尊重,並贏得了所有人的駐足。
卻又迅速被推上越發激進的風口浪尖。
好內容還能留下多少呢?
如果説,以往把人區分成“好”和“渣”,是一種無視人性複雜的粗暴。
那麼今天,對創作者自身根本無法選擇的性別施以極端指控,則是一種直接刪除了“人”的霸道。
這樣下去作品會變成怎麼樣?
正常邏輯,要改變現狀應該去支持女性作者、女性向的作品,甚至致力於一個更包容的市場與大眾審美。
可我們卻屢次發現。
那些真正關注女性的作品,如《媽媽!》《臍帶》《愛很美味》大多票房慘淡。

火起來的卻是另一種“流量公式”。
——全程爽劇,全員惡人,以及批量生產的男/女復仇。
就像有些觀點認為,《漫長》的沈墨是一個工具人:“不就是九十年代東北版《白夜行》嗎?還以為會黑化,要麼像雪穗,要麼文東恩那樣狠毒,結果居然是個跳河的戀愛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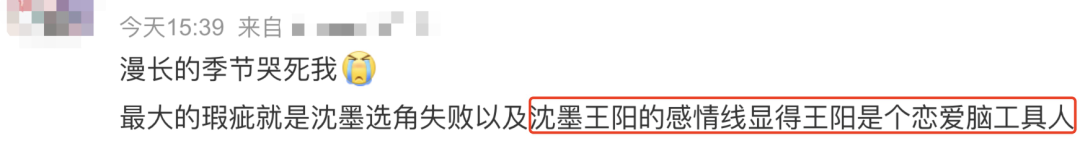
看看這些形容詞:
戀愛腦、黑化、白夜行……
任何一個描述本質都是固化和刻板的標籤,背後是粗暴的短視頻式審美。
當你這樣去看待沈墨,當然也就提取不出——
跟沈墨更貼合的人,不是《白夜行》或《黑暗榮耀》女主,而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四。
沈墨對港商、殷紅、大爺大娘的復仇,本質就像小四一樣,用兩敗俱傷的方式,來表達她對世故、無情、虛偽的成年世界的最後一擊。


王陽是什麼?
不僅是沈墨愛的人,更是她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念想,唯一的美好。

最後王陽決定犧牲自己,來保全沈墨。但他無法跟沈墨逃跑,絕非出於自私或世故。
那麼,沈墨又有什麼理由,要親手毀掉這份超乎她想象的美好?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對於文藝作品的期待只剩下了“爽”。
爽是為了解氣。
爽,也是因為安全。
它有仇必報,有怨必申,以酣暢淋漓的情緒繞開那些真正橫亙在現實中的結構性不平等,隱秘性暴力。
辛爽確實是叛逆的。
他明明可以再拍一次《隱秘的角落》,滿足大家對重口罪案的飢渴,對迷霧劇場的意難平,那一定比現在更出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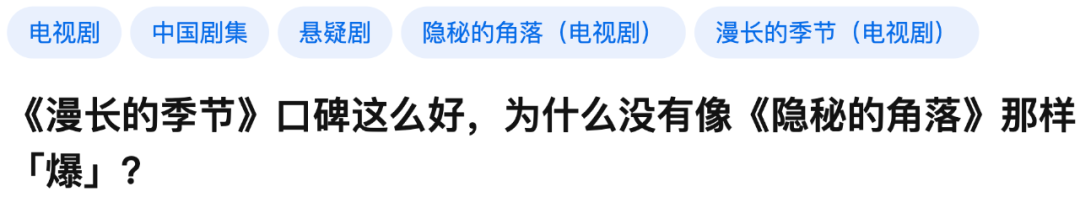
但他沒有。
《漫長的季節》色調很明亮,底色卻是悲涼。
它沒有在批判什麼,也沒有在歌頌什麼,僅僅完成了一首普通人在時代的泥石流中,掙扎生存的輓歌。
它告訴我們,曾經有一個時代,人的命運無比侷促。
但只有要有一絲向上生長的可能,所有人都會迫切地從縫隙鑽出來,想活明白一點,看看更大的世界。


是的,Sir提到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一部華語影史的經典作。
也是一種正在消逝,不斷消解的電影審美。
放在今天看,故事簡直“辱女”——
一個女生背叛了男生,男生反殺。
但這種短視頻都不想講的劇情,楊德昌會拍成四小時的電影來表達嗎?
當拘泥於性別視角。
是不是就想不起女生説過的話——
“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
其實,不是一個暴戾的少年,把背叛自己的少女殺了。
**而是一個年輕純真,對世界充滿希冀的靈魂,**選擇與這個不允許他活出自我的時代和世界,玉石俱焚。

那麼,回望我們自己呢?
楊德昌在《一一》的經典台詞,曾讓我們無比興奮,反覆背誦。
“電影發明以後,人類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長了三倍!”

如今。
當《漫長的季節》和更多的作品,就像《一一》喜歡拍後腦勺的小男孩,總是在用不完美的方式,想讓同樣不完美的我們,看見世界的背面,人性的背面。
而我們,在追求平等和正確的浪潮中,困於自己建造的價值繭房,反倒成了一個讓小男孩聽話的無聊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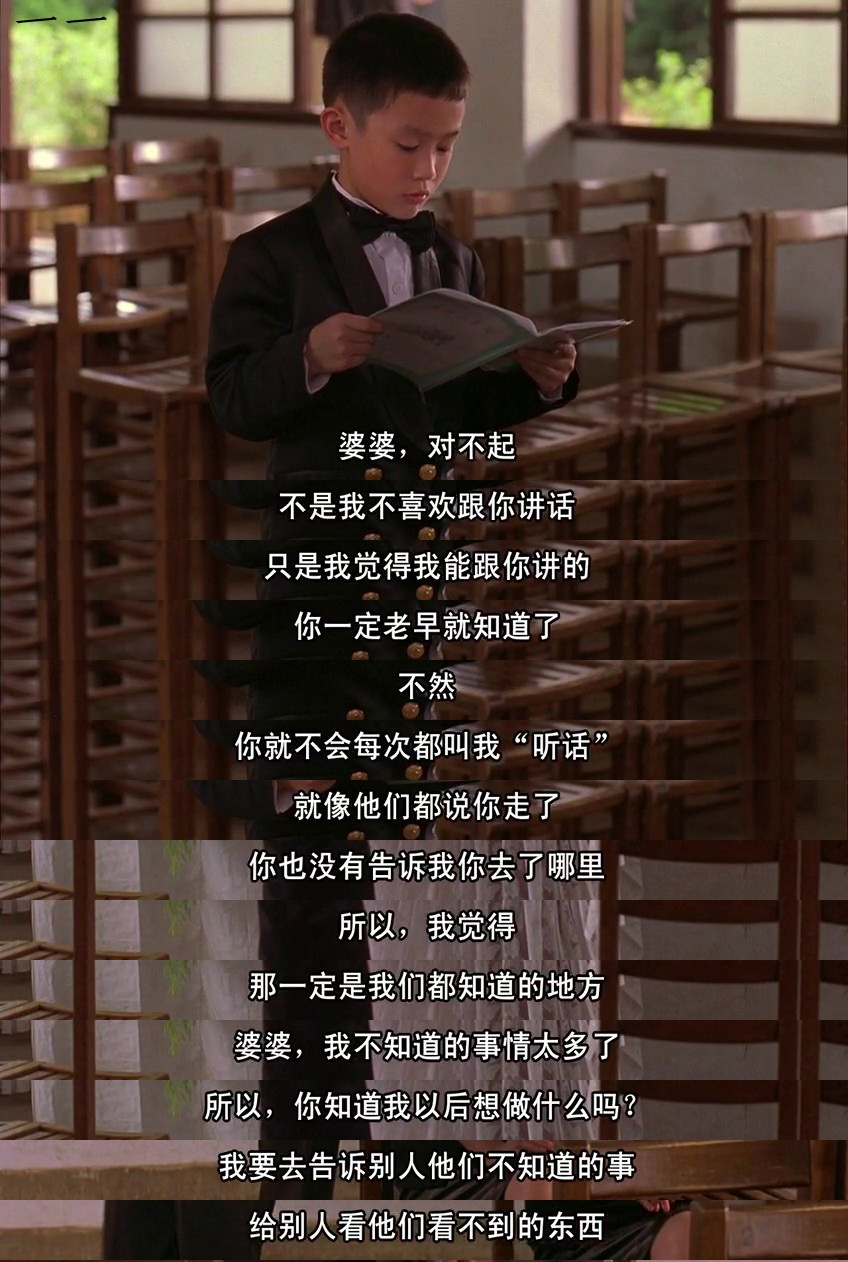
但Sir還是會選擇相信。
那一聲讓我們學會欣賞曖昧與複雜,從正確和刻板中抽離出來,能給人精神共鳴的響指。
才是留在時間裏的永恆。
也才是排除了男性/女性視角的。
人類視角里的終極救贖。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點擊閲讀往期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