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季節》,中國改開歷程中的一頁痛史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05-10 08:21

· 這是第5183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3k+ ·
· 土哥涅夫 | 文·
五一檔的影視劇市場,最火的莫過於由辛爽執導,範偉、秦昊、陳明昊領銜主演的《漫長的季節》。自4月22日甫一上線,就在豆瓣得到9.0的高分,隨着劇情推進,分數越來越高,5月1日大結局之後,更是衝上不可思議的9.4分,遠超春節檔的熱播電視劇《狂飆》。

如果説《狂飆》講述的是一部黑社會的長成史,那麼《漫長的季節》聚焦的則是改革開放歷程中工人羣體的一頁痛史。
關於改革開放的歷程,向來有兩副面孔:
一副是以安徽小崗村(農村改革)、深珠汕廈四大特區(城市改革)為發端,由點及面、不斷深入,積極向上、喜笑顏開的面孔。以往的主旋律文藝敍事多聚焦這一面,比如早年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到近幾年熱播的《大江大河》《人世間》等。
另一副則是由改革代價的承擔者,包括失地的農民、下崗的工人等弱勢羣體的淚水匯成的哭臉。只是因為這些羣體缺乏話語權,這一面以往很少被人關注。而《漫長的季節》以一起18年前的碎屍懸案為引線,追憶並呈現了改革不為人所關注的另一面,引發大量親歷者的共鳴,進而收穫到超出預期的口碑效應。
那麼,這頁痛史究竟有多痛?後來又是怎麼翻片的?為什麼不該被人們,尤其是年輕人遺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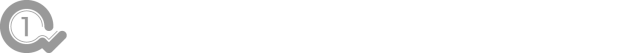
1949年以後大規模的就業難情況,大概發生過三次。**第一次是在1960年代中後期,此後全國便掀起了針對“老三屆”“新三屆”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該運動雖然裹挾着意識形態的因素,但很多學者都認為,它和50年代末以來一連串經濟政策失誤造成的城市就業壓力有密切關係。只不過在當時,由於普遍的貧窮、嚴格的管制以及革命話語的鼓動,經濟層面的因素並沒有對社會產生太大的衝擊。
**真正的衝擊發生在十年以後。**隨着知青的陸續返城,而國營單位又沒有那麼多崗位可以安置他們,導致城鎮待業人口激增。一些人因為無事可幹,整日遊手好閒甚至聚眾鬥毆,成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中國第一代的黑惡勢力,就是在這個時期冒出來的。
多年以後,作家孔二狗將這段經歷寫成了小説《東北黑道風雲往事》,一時爆紅網絡。當然,小説家筆下的故事都是經過美化的,而現實比這要殘酷得多。據公安部統計,進入1980年代後,各地惡性治安案件頻發。1980年,全國立案超過75萬起,其中大案5萬多起;1981年,立案89萬起,其中大案6.7萬起;1982年,立案74萬起,其中大案6.4萬起……這直接促成了1983年的嚴打。
今天的人談起那次嚴打,聚焦點多放在諸如唐山菜刀隊等黑惡團伙,或者朱國華、“二熊”等被正法的權勢子弟身上,而對於其背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遲緩、就業供給側不足等深層次問題,卻很少留意。
相較於廣大農村,中國的城市過去在“二元體制”下享有諸多特權,用農民的話講,城市職工是“吃商品糧”的。當時像鞍鋼這樣的國營大廠,職工穿着廠服走在大街上各個都是昂首挺胸,滿滿的自豪感和優越感。
但這也帶來了兩個問題:
一方面,人人擠破頭都想進國營大廠,而瞧不起剛剛萌芽的民營經濟。比如《漫長的季節》中,工人勞模王響念茲在茲的就是將兒子王陽送進樺鋼,哪怕彼時的樺鋼已瀕臨倒閉,也不願意他去夜總會掙每個月300塊+小費的“高薪”。
但另一方面,由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晚於農村,當農村的鄉鎮企業已經辦得熱火朝天,城裏卻還是各種國有或集體單位一統天下的局面。儘管它們通過開設分廠、職工子女頂崗等方式,吸納了一部分待業青年,但要想靠這些存量企業解決所有的就業問題,顯然不可能。
記得90年代初有一部熱播電視劇《孽債》,從孩子的眼光,講述插隊西雙版納的上海知青離婚返城後,子女從雲南到上海尋找父母過程中品嚐到的艱辛冷暖。但如果我們把視角切換到他們的父母,則又是另一番悲情敍事。不同於留在城裏的兄弟姊妹,這些人在邊疆、在農村吃了多年的苦,但回來後要工作沒工作,要住房沒住房。
好在嚴打的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拉開。很多人靠着擺地攤、跑運輸甚至各種“投機倒把”行為,攢下了第一桶金。反倒是像王響這樣曾經手捧鐵飯碗、受人尊敬、令人羨慕的國企職工,在幾年後淪為了另一場失業潮的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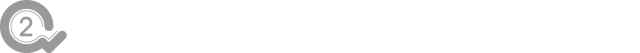
關於上世紀末國企改制的利弊得失,從學界到民間,至今仍存在不少爭論。
一方面,隨着市場化改革的深入,面對外企、民企的激烈競爭,國企體制僵化、效率低下、人浮於事等問題越來越暴露出來。到1997年底,全國16784家大中型國有企業中,虧損的有6599家,虧損總額達到666億元。光靠擴大企業自主經營權或推廣承包責任制,已無濟於事,必須進行產權改革。
但另一方面,產權改革必然涉及員工的分流下崗,而大範圍下崗潮所帶來的改革陣痛,落到每個家庭頭上,都是難以承受之重。數據顯示,單是1995年到2002年,國有和集體企業就精簡了6000多萬名職工。套用北野武的話説,悲劇並不是下崗了6000多萬人這一件事,而是下崗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6000多萬次。

南方還算好,由於民營經濟發達、外資企業眾多,下崗人員的出路還算廣,國企的接盤俠也多。
比如我媽她們家兩代五口人工作的造紙廠,先是將我舅所在的車間連機器帶員工賣給了一家德資企業,這部分人轉制後收入不僅沒降反而還漲了。而剩下的總廠部分,由於負擔相對較輕,又有政府的背書,所以對富餘職工採取“內退制”——通常比正常退休年齡提前五到十年,內退後每個月能從企業拿到幾百塊錢的“退休費”,而政府也針對這部分4050人員提供一些技能培訓,幫助其再就業。
比較慘的是東北,一來這裏國企工人數量多,二來民企、外企又少。一些年紀較輕或有一技之長的,下崗後紛紛選擇南下,形成了第一波東北人南遷潮——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90年代東北人口淨流出40.4萬人。
但更多的家庭,因為上有老下有小,即使是像王響那樣的熟練技工,也不得不留在原地。這部分人的境遇就相對悲慘許多。當時,諸如下崗工人冬天了沒錢交取暖費在家挨凍,生病了沒錢看在家等死,甚至丈夫騎着單車送妻子去KTV上班的報道比比皆是。
《漫長的季節》呈現的正是這部分人的心酸苦楚。據説劇中原有劉全力帶着兒子接在維多利亞做陪酒女的李巧雲下班一幕,記得那些年,每次跟大人去卡拉OK廳,他們唱得最多的一首便是劉歡的《從頭再來》,曲調是高亢的,但歌聲卻很淒涼。一曲唱罷,總會伴隨着一串對於社會、對於廠長的“祖安輸出”。以至於後來黃宏因為在春晚小品裏説了一句“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被全國的下崗工人足足罵了好幾年。
寫到這裏,突然想起被很多國人所批判的蘇東國家劇變後採取的“休克療法”,認為該法搞亂了這些國家的經濟,讓人民陷入貧窮。但某種意義上,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中國國企轉制改革,也不啻為一場休克療法。
但正如我們在東歐看到的,除了俄羅斯等少數幾個國家,大部分國家採取“休克療法”後的陣痛期只有短短几年,此後經濟便開始復甦反彈。而中國的運氣似乎比東歐還好,“國企三年脱困行動(1998-2000年)”結束後的2001年,中國便正式加入世貿組織,經濟從此步入快車道,失業率也隨之下降。
所以追劇時看到有評論説,龔彪如果不是因為黃麗茹而胖揍廠長宋玉坤,能熬過那幾年不下崗,像他這樣90年代的大學生,進入21世紀後一定能大展拳腳,前程似錦。這也是許多觀眾最同情龔彪,而不是死了妻兒的王響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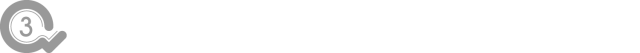
今天很多缺乏歷史知識的年輕人喜歡罵資本家,覺得天底下所有的壞事都是資本家乾的,不理解70、80後的人為啥會崇拜互聯網最初的那批創業家。但經歷過計劃經濟時代,品嚐過國企改革陣痛的人,想必都對那個年代的廠長有深刻印象。
名義上,廠長只是工廠的管理者,他們中也誕生過像張瑞敏、步鑫生等改革先鋒,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更多時候,廠長握有比今天很多民營企業主更大的權力,卻承擔着更小的責任——
這兩年由於經濟不景氣,很多民營企業主都吐槽“自己是在給員工打工”,而想當年,哪怕國企效益再差,廠長也只是打報告向政府求援,而在工人面前,依舊趾高氣昂、説一不二。工人受了委屈,還無處去説理,不像現在,可以勞動仲裁,也可走司法程序。
這種權責不對等帶來的腐敗空間,在國企改制過程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那時候誰留下,誰下崗,往往就是廠長、工會主席等幾個人説了算。甚至像《漫長的季節》中,龔彪因為黃麗茹的事打了廠長宋玉坤,後者便臨時將他的名字加到下崗裁員名單中的情況,也不是沒有。
更為惡劣的是,一些廠領導勾結外商、偷賣物資、中飽私囊、化公為私的情況屢屢發生,而像宋玉坤那樣被法辦的卻寥寥無幾。這些都在工人中間激起了廣泛的憤慨,直到零幾年的時候,還曾發生過吉林通鋼集團工人抗議重組打死新任老總的重大事件。
正因為有過這些經歷,很多人才會對21世紀以來市場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物資生活的大幅改善充滿感激,對白手起家、不依靠權力獲得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心生敬佩。《漫長的季節》結尾,年老的王響對年輕時的自己説的那句:“往前看,別回頭”,很能代表那代人的人生觀。
但是,這種進步主義的樂觀情緒並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像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這樣一路單邊向上高速發展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屬於非常態。
當非常態迴歸到新常態,青年人失業率持續走高,我們有必要回頭看,從歷史中去尋找經驗教訓和解決方案。這也是《漫長的季節》收穫比《大江大河》《人世間》等改革正劇更高評分的原因。
就像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所言:“充分地理解過去,我們可以弄清楚現狀;深刻認識過去的意義,我們可以揭示未來的意義;向後看,就是向前進。”

作者:長三角區域城市觀察家、允九智庫研究員、公眾號“三土城市筆記”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