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食時代的焦慮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05-17 10:21

· 這是第5196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3k+ ·
· 臧否 | 文·
特稿寫作中的一次機緣巧合,看到了一檔訪談類節目的粗剪,其中一期因故未能排播,嘉賓是著名的文化人梁文道。
近日得空回看了這期內容,發現其中觀念不僅並未過時,而且結合當下的紛雜,堪稱“空谷足音”。
這期訪談首先吸引我的,是梁先生對“讀書人”形象另一面的自我揭示,年少從中國台灣到香港求學,受青春期的自我膨脹作祟,到處跟人打架,因此被老師批評“沒希望”。
當然,他同時又酷愛閲讀,這樣的人格反差,恰似楊德昌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裏的Honey,穿着一款海軍服、慢條斯理、眼神澄澈,那份理想主義的神采,與頑主絕不相稱。
讀同學讀不懂的書,在當時是為了證明自己,在後來,則是“要讓你換一個腦子來看這個世界”。
它和上學從來是兩件事,和考試更是兩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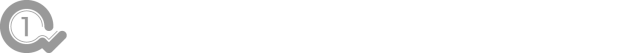
我在回看這期節目的同時,還抽空看了一期最新季的《十三邀》,發現同過往幾季相比,節目風格有些變化。具體來説,談話中思想的密度在下降,而編排的精巧、節奏的緊湊在提升。
朋友認為這樣的文化濃度剛剛好,我卻稍微覺得有些不過癮。
當然説一千道一萬,自《鏘鏘三人行》停擺後,在中文媒介裏,優質的文化類欄目總體上是供不應求的,算上《圓桌派》《十三邀》《見字如面》以及命途多舛的《和陌生人説話》,無論它往何處變,觀眾幾乎沒有更多的選擇。
眾多年輕人熟悉梁文道、前呼後擁地稱他“道長”,恐怕並不是通過他的文字,正是經由鳳凰衞視那些異彩紛呈的電視節目。也因為這一“電視知識分子”的身份標識,他也經常需要澄清一個有趣的誤會。
“國內特別濫用學者這個詞……我每次出場做一些活動,人家説著名文化學者,通常是這樣的,一種人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學者,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學者,又想叫他學者的時候,這種我們就叫他文化學者。”
梁先生經常需要解釋,自己是媒體人,不是學者,兩者職責很不一樣。自己曾經想過做學者,但後來發現由於好奇心太重,喜歡觸類旁通地考慮問題,沒辦法服從於學術工作的紀律。
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每當梁向人解釋這一點,對方都會認為他在自謙,“彷彿媒體人是低了”,這令他不得不對自己的解釋再作解釋——“他不理解就是,我多麼認為媒體人是個神聖的事”,這關乎一份深刻的責任。
或許也因為這份責任,他會告訴主持人,如今的媒體從業者多多少少都會有一種恥感。
《論語·泰伯》有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在百廢待興的時代,一個人卻碌碌無為,這是可恥的;如果情形恰恰相反,一個人卻獲得了世俗成就,這同樣可恥。
其實對於任何一個媒體人來説,平日裏也都會有自己的圈子,就像電影《神探亨特張》開場所表現的類似飯局。圈子就像球隊,欄目只是比賽,只要隊友還在,賽場就依然會有,只是它變小了,不再向公眾開放。
如同《鏘鏘三人行》到《圓桌派》所體現的尺度落差的背後,真正受損失的,從來不是嘉賓們,而是原本可以聽到更多思考角度的公眾。
佛法裏所謂“末法時代”,就是有識之士因故緘口不言的時代。與此同時,那些仍在默默耕耘、持續守望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則尤為顯得可貴而有必要。
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加賽特講過:
“今天,亟需提倡一種具有誇張意義的責任感,以激發那些能感覺到它的人。強調當今時代之危險徵兆已是迫在眉睫。毫無疑問,如果讓我們對當代公共生活中的諸多因素做一番權衡與考量,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其中不利的因素遠遠超過有利的因素,尤其是當我們從它們對未來的預示與徵兆來考慮,而不是從它們目前的狀況來考慮的話,情況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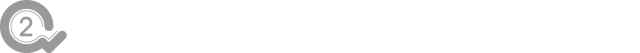
這期節目中另一個吸引我的地方,是人物同流行符號所保持的間距。
例如在某一年的寶珀文學獎的頒獎禮上,梁先生這樣講道:
“我們如果活在這個時代裏面,我們跟這個時代高度重合,這個時代所講的一切,我都相信;這個時代所鼓吹的一切,我都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個世界在我眼前展開的所有的物事,我都當做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來接受的時候,其實我就不是這個時代的人。”
就像魚和水的關係,魚在水中感受不到自己的遊動,只有當它離開水的時候,它才能意識到水的存在。
不與時代保持距離的庸眾,自以為與環境水乳交融,其實不過是被大環境裹挾和吞噬。真正在一個時代“活過”的人,都是那些懂得與時代拉開距離,用不合時宜的態度去尋找觀察切口的人。
這讓我想起與馬克·吐温同時代的諷刺作家安布羅斯·比爾斯在《魔鬼詞典》裏對“玩世不恭”的解釋:“他們總是能一眼就洞悉時代的本質,而不是它看上去的樣子。”
當然,保持距離需要付出代價。以梁先生為例,每天只在固定的時間回覆信息;手機聲音能關就關;甚至極少叫外賣。在生活之外,他要跟北京時間保持4個小時的時差。
作為一個媒體人,僅從職業角度看,是需要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交網絡與新聞事件及時進行觀察的,但有趣的是,在對訊息的跟進上,不蹭熱點的梁先生卻並未因這份主動“降速”而引發焦躁。
梁文道認為,在生活中慢下來絕不是壞事,尤其是當我們已經過快的時候。他隨即舉了一個1930年代文人筆仗的例子:魯迅和梁實秋、林語堂們罵來罵去,為什麼事後看上去並不那麼激烈?因為他們吵架的載體是報紙,一登二印之間,最激烈的情緒早就消散,剩下的都是智識和涵養層面的較量。
“那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由於社交媒體它(的)速度、節奏太快,那就很簡單粗暴,那被罵的人也就只能很簡單粗暴地馬上回應,你(在)中間沒有任何時間能夠停下來去沉澱這個情緒,去過濾對方所講的話裏面到底他的真正的那個內容,那個精髓在哪裏。”
而在今天,時代中央的情緒,除了憤怒,還有焦慮。今天的人很喜歡被“帶節奏”,動不動就狂喜或是淚目,大家需要經歷強烈的刺激,才會覺得一天沒有被浪費。
過去有不少人都指責過咪蒙式的寫作,但很少有人考慮的是:一個內容想獲取流量,就得對大眾情緒點進行猛攻,可如果人們真的排斥挑撥,它就應該沒有傳播市場,而非恰恰相反。
社會追熱點的弊端,就是把每個參與者都變成了“巴普洛夫的狗”,所有的價值都被稀釋和擱置了。而我們唯一的機會,或許是等所有人都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厭倦,並認識到生活的焦慮、壓抑與抑鬱,正與信息的獲取方式和獲取內容密切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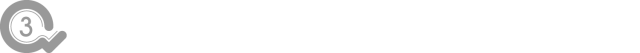
在如今這個流量時代,很多人説“文化節目在當下很難”,梁文道卻表示,以前電視台放《開卷八分鐘》,其實安排的都是垃圾時段,但在互聯網時代,推書進入了點播模式,貨可以自動匹配人,人也方便自動搜尋貨。你看,答案並沒有那麼糟!
主流觀點以為,現在的人注意力分散了,沒有耐心看長的內容,所以短視頻、口水文大行其道。但這幾年在微信裏流量很高的爆款文章,卻都是深度長文——因為大家在看慣了那些碎片化的垃圾內容後,還是願意去獲取一些思考和共鳴。
如果這一天遲早都會來,那你為什麼不是最先去那麼做的人?中國有14億人,如此大的一個市場,並且逐步走向細分,怎麼能用一種極端趨同的理念去搞策劃呢?
所以梁先生認為,是我們的視野決定了我們的廣度和高度。
用梁先生的話説,他這些年就像一個管道,不斷分享所見所感,讓別人看到那些更有價值的觀念、作品、現象與事物——“我不是一個對象,不是一個終點,你只是通過我去到某些地方,有一天你可能會比我去到更遠的地方,看到比我更高的山峯,那這樣子我會很高興的”。
這個過程肯定是孤獨的,但在儒學名家牟宗三的例子中,你卻能感到一絲寬慰。牟師當年在香港教學,周遭熙熙攘攘皆為利來利往,他清湯寡水的學術並不受到重視,只是保有一寸講台。
牟宗三卻説,知識分子是有道統的,從孔聖人到古仁人,“前面有很多,後面也有很多”,怎麼會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