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天賺幾元錢,到一幅作品賣300萬,這個小眾行業急缺人手_風聞
卖家-05-18 1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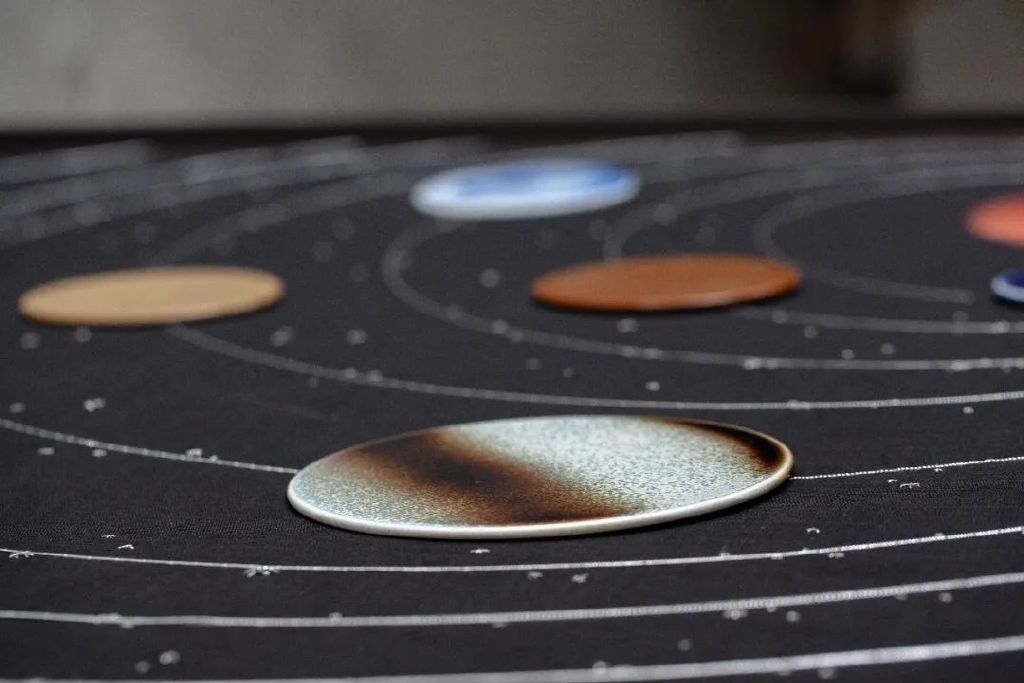
從牡丹到星辰。
文/吳鶴鳴
編輯/鄭亞文
很難想象,張雪家的倉庫裏大多是他和母親薛金娣的蘇繡作品,價值不菲,如果論作品和技法,薛金娣可以説是當代蘇繡的代表人物。
張雪家做的是蘇繡和蘇繡衍生文創產品,價格從幾百元到幾百萬元不等,展廳裏放着的一幅薛金娣繡的《千里江山圖》,有人出價100萬元,他們也沒有答應出售。

張雪
張雪上學時是“學霸”,大學專業是國際貿易。畢業後他放棄知名企業的工作機會,和國外名校的獎學金,開始跟母親學習蘇繡,至今已經12年。
他本有機會走另一條完全不一樣的路。張雪的作品選擇的題材和傳統蘇繡上注重花鳥和山水不同,他常常會用更具年輕審美設計感的畫面打動客户。
這些年張雪陸續走上《國家寶藏》《中國詩詞大會》《百家講壇》等電視欄目,多幅作品被單霽翔、郎平、李前寬、張國立等名人收藏,與網易、騰訊、阿里巴巴、別克、耐克等知名公司和品牌開展跨界合作。
他想拓寬蘇繡的消費羣體,將市場做大,也能激勵更多人從事蘇繡工作,解決今後可能無人可用的問題。
是藝術,也是生活
薛金娣的藝術館在蘇州繡品街主街的一個拐角處,周圍一圈都是高檔繡品館。展館平時不接待散客,只有老客帶新客,來了一般都會成交。少則上千元,動輒上萬元。有些預定的繡品可能要等上幾個月,複雜的作品要等一年。
蘇繡中一根頭髮絲粗細的繡線甚至還能再分出256份來,已經細到幾乎風一吹就斷的程度,有時候因為一根線的變化,就會導致作品失敗。這極其考驗手藝人的技法和眼力,所以連續刺繡的時間久了,很容易患眼疾。
街頭店鋪臨近太湖大道,早年太湖大道還沒修成時,大家要繞一圈才能出鎮湖。老店鋪的位置其實是當時的街尾,是最差的地理位置。太湖大道修成之後,這裏卻成了主街的入口。

張雪刺繡作品
繡品街上賣的都是蘇繡,或是和蘇繡相關的產品,零星開着幾家緙絲店鋪和裱框店鋪。2000年政府開始裝修繡品街,這些年隨着生意漸好,主街兩側延伸出兩三條小街道。街上的店鋪租雖然不便宜,但也是一店難求,這裏的年產值已經超過10億元,吸引着外來的人到鎮湖做刺繡生意。
早年鎮湖有“八千繡娘”,如今從事刺繡工作的人逐漸減少,手上有活的繡娘們年紀都不小,想要規模生產的條件越來越苛刻,所以會有個別商家拿外地的繡品在這裏售賣。
那時候鎮湖幾乎所有會刺繡的繡娘,都會早起來到鎮上的發放站門口排隊。清晨五六點時,刺繡廠會派發刺繡訂單,“有繡貓的,有繡牡丹的”,各種題材都有。
當時年僅十二三歲的薛金娣,已經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繡娘,“繡得好,速度快”。派活時,工廠總會把最難繡的給薛金娣,那時周圍的繡娘幾乎都大她一輪。為了繡好一隻“貓”,年少的薛金娣會盯着真實的貓一直觀察,看它們的姿態和神韻。這是薛金娣的習慣,是為了讓繡品更傳神。

張雪刺繡作品《楓橋夜泊》

張雪刺繡作品《二十四節氣之大暑》
1982年,16歲的薛金娣考進刺繡廠,是廠裏年紀最小的繡娘。已經名聲在外的薛金娣,跟着廠裏的師父們繼續學習,等再出廠時,薛金娣已經遠近聞名。
在張雪的家人看來,這是個辛苦的工作。因為活少人多,繡娘們需要在凌晨三四點就起牀。領了活之後各自回家工作,一直要工作到夜裏12點,完成繡品之後再交給工廠。這些繡品被賣到全世界,繡娘則按件領取佣金,一天只能掙幾元錢,為了掙到這些錢,他們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這也是張雪家裏人一開始並不支持他從事刺繡工作的原因,“很累,掙的很少”。
傳女不傳男
張雪家的展館分兩層,一樓擺的大多是張雪的蘇繡文創產品,有圍巾、包和耳機等等,有公司想要訂製時,可以挑選現成的產品。角落擺着兩張繡繃,會有繡娘在繡繃前工作。
二樓則是展覽間,陳列的大部分作品都出自薛金娣之手,也有少部分張雪的作品。上樓就能看到《簪花仕女圖》,曾經有人出價百萬想要收購,她也沒有出售。休息室旁掛的是重彩的《千里江山圖》,裏間最惹人眼球的是耗時多年才完成的《月曼清遊圖》,曾經有人出價單幅百萬元,全套上千萬元的價格,但這套作品花了太多心思和時間,薛金娣沒捨得賣。
展間裏薛金娣的作品多以古畫為題材,花鳥嬰戲,雅然成趣。連其中的國畫皴法、題跋的文字筆意、印章斑駁都一一還原,行走其間。繡品上絲線反射的光,會隨着腳步變幻,生出“2.5D”的立體效果。看蘇繡時,先遠看整體的效果,再左右看它的光影,細看細節處的針法,最後再一次看它的整體,才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

張雪
張雪的員工順順把薛金娣比作“掃地僧”,張雪則覺得母親更像藤原拓海,“她會一直不停給自己加難度,限定刺繡的時間”,薛金娣上下翻飛的手,有時候能看到重影。
在鎮湖,刺繡是一門傳女不傳男的手藝,薛金娣在懷孕時就想生個女兒,把手藝傳給她。即便生下張雪之後,心裏想的也是以後教張雪的妻子,從沒想過教張雪刺繡。
在從前,刺繡只是“工”,繡娘們以此為生,就像木匠做傢俱一樣。鎮湖的女子以刺繡為生,男子則有兩門手藝,一樣是種田,另一樣則是木工或是瓦工等等其他工種,繡得再好,也只是熟練度的差別,“大環境對刺繡手藝並不寬容,如果誰對外説自己是做刺繡的,和一般的紡織廠工人並沒有差別”。
生下張雪之後,薛金娣一家一直苦心經營,所以張雪從小家裏就不寬裕。
上大學選專業時,張雪選擇了國際貿易,他學習刻苦,每年都拿一等獎學金。真正讓張雪入刺繡行做了繡郎的,還是臨畢業前的一件事。
怎麼讓年輕人喜歡
張雪念大三那年,家裏接到一個訂單,要定製一扇刺繡屏風。對方專門請了第三方設計師把關設計,“其實做這行的很少有商家為客户做原創設計”,這次的圖案設計稿卻遲遲沒有通過。
此時正在放暑假的張雪想幫母親試試,他交了二三十稿,都沒有通過,只能摒棄傳統紅木雕刻的思路,到網上找其他靈感。最終,他將青銅器上的鳳鳥紋做變形處理,用在屏風上。傳統雕花紋飾、技法繁複,張雪用了變形後的飛鳥紋,畫面簡潔乾淨,對方看到設計稿後立刻就通過了。
這是讓張雪想要從事蘇繡的原因。很多人採訪張雪時,都想得到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但張雪説,做選擇的時候是整個從業最掙扎的時候。“因為你知道,選擇一條路時,就意味着要放棄另一條路上的東西”。


他選擇蘇繡,放棄的是國外名校的學習機會,放棄名企高薪的金融崗位。而他要面對的是當時並不友好的環境,是大家根深蒂固的觀念——男生為什麼要拿起針做刺繡?
最早的幾年,薛金娣在接受採訪時,都會不大好意思,説自己的兒子在跟着自己學刺繡。這麼多年,母子二人一直默默承受這樣的眼光,母親瞭解兒子的心性。
興許是有天賦,也是張雪肯努力鑽研。學藝期間,他每天早晨7點起牀,一直到凌晨2點睡覺,幾乎將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刺繡上。一片平繡的葉子繡到第5片,母親説:“繡得很好。”能得到薛金娣的誇讚並不容易,尤其是作為她的兒子,繡娘們聚集來看,都不相信這片葉子出自張雪的手。
“這個講究心手合一”,很多事就是一個頓悟的過程。平繡練習熟練了,再上手其他的針法就相對簡單,張雪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他總結出一整套蘇繡的針法——在從前幾乎沒人做這個事,多是口口相傳,他的作品《星空》裏,運用了蘇繡的20多種針法,堪稱蘇繡的教科書——要知道,現在大部分蘇繡作品中用到的針法,往往都不超過五種。
張雪不想再用傳統的畫面製作蘇繡,滿滿當當的畫面可能已經不再適合現在年輕人的審美。他開始用一種從沒人做過的風格闖進大眾的視野,畫面中大量的留白顯得更為樸素清雅,主視覺簡潔又極富視覺衝擊力。
他有一幅獲得金獎的作品《佛》,畫面中只是一張明式几案,一尊香爐,一炷線香,一縷香煙嫋嫋而起,繞出一個書法字體的“佛”字,雅緻寫意。一位新加坡的女生看到這幅作品,當下就想跟張雪到蘇州學習刺繡。
這樣“雪式風格”的極簡蘇繡一開始並不被“傳統派”看好,張雪只能下班之後偷偷和合夥人在火車站的麥當勞一起討論設計稿。
張雪的作品一經推出就受到年輕人和市場追捧,傳統蘇繡造價高昂、耗時漫長,難免曲高和寡,讓人望而卻步。張雪想用一種更年輕的方式讓蘇繡有更多的市場——只有受眾更廣,才能讓更多人下場,將市場進一步做大,更有利於傳統手藝的可持續性發展。


刺繡衍生品
這些年,張雪努力將蘇繡和各個領域融合,玩起跨界。網易遊戲中的道具、龍魂人形社的娃衣、寶可夢中的皮卡丘……年輕人喜愛的很多IP周邊產品,都能用蘇繡重現,年輕人更願意為自己認可的“價值”買單。
張雪還與高新區文旅局合作首批鎮湖蘇繡數字藏品,上線幾分鐘就被搶購售罄;會動的蘇繡拍出了16萬元的高價……傳統與現代並非二元對立,這中間的辯證已經在歷史長河中討論過無數次,也經代代流傳延續至今,靠的是一代代的工匠和藝術家的突破和巧思,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
張雪在努力把自己手裏的“牌”打好,很多時候他不像一個大師的孩子,反而會因為這層身份承受更多的壓力和責任,就像一幅《星空》,他的員工笑説,他是想把蘇繡帶向前人未曾去過的“星辰大海”。
受訪店鋪:彌惟刺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