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樁震驚世界的龐氏騙局!最大的瓜來了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05-24 23:19
Hi藝術2023年05月24日 17:35:010人蔘與0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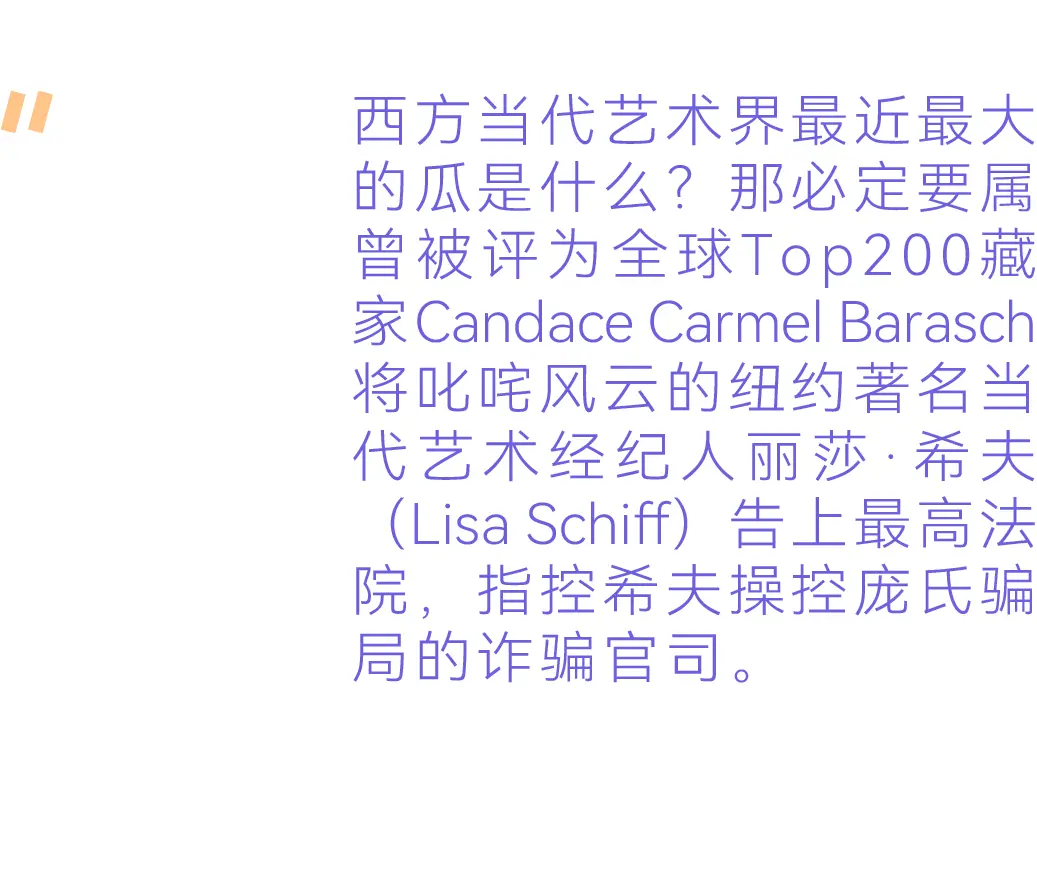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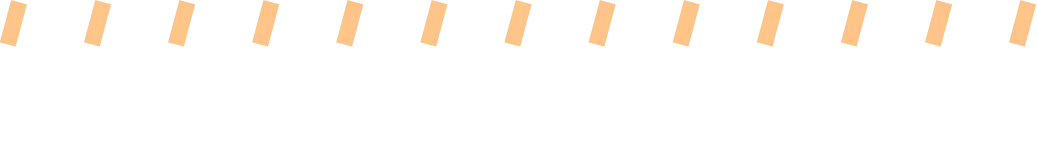

地產鉅富繼承人的Candace從2000年起開始涉足當代藝術收藏。二十年間,她和律師老公作為慷慨的藝術贊助人和熱忱的藏家活躍在當代藝術圈。他們的收藏範圍從藍籌至新星,覆蓋幾乎所有媒介和代際,是各大國際畫廊和拍賣行的VVIP客户。除了藝術市場,Candace 還持續資助藝術家展覽及創作,是包括惠特尼美術館在內的多個重要機構委員會的成員。比如,聖路易斯當代藝術館計劃在2024年重磅呈現的藝術家陳保羅 (Paul Chan) 大型個展,就離不開Candace 的支持。

2004年,Candace 結識了麗莎·希夫。
藝術顧問麗莎·希夫的職業生涯從90年代末的富藝斯開始,“那是一個還沒有artnet的時代。” 也是藝術工業迅速蜕變的時代。金融資本的操作模式剛開始滲入藝術市場。“一片混亂,我説的是積極的混亂,老牌拍賣行被肢解重新組裝成新的東西,過程一定是混亂的。” 希夫曾回憶。離開富藝斯後,希夫去了一家專注於二級市場的藍籌畫廊,並在那裏學到了如何嫁接交易,以及藝術顧問是如何工作的。

全球Top200 藏家、地產鉅富繼承人Candace Carmel Barasch
2002年,希夫建立了自己的藝術諮詢公司SFA,為了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希夫僱用了藝術PR公司sutton為自己的品牌造勢。藉助好萊塢明星客户羣體的東風,生意發展迅速,在她的客户名單裏不乏包括羅伯特·德尼奧、梅格·瑞安、李奧納多·迪卡普里奧等國際巨星,被認為是北美地區最“靠譜”的藝術顧問之一。希夫多次主持了巴塞爾藝術節的對談,是瑞士以及紐約諸多重要藝術機構的委員會成員,並且是《紐約時報》《彭博社》等等頭部媒體藝術版面的一線採訪對象。她在藍籌畫廊,藝術機構和藏家中揮灑自如,裏森畫廊就曾公開感謝麗莎·希夫的支持:“我們跟希夫合作多年,她一直是我們的藝術家的堅定支持者,我們之所以能將作品送入世界上最好的私人收藏,希夫功不可沒。”

麗莎·希夫的藝術諮詢公司SFA 在美國紐約Tribeca的空間
相識近20年,Candace自述和希夫之間的情誼幾乎可以比代“家人”,兩人經常合體出現在社交場合,並每天保持着高頻聯繫。在2019年《紐約時報》的專訪中,Candace親暱地將希夫稱之為“犯罪同夥”,並毫不諱言自己之所以能在當代藝術界大展拳腳,建立起600餘件的當代藝術收藏,全靠希夫的專業指導。而就在事發前一週前,希夫還在ins上po出自己和Candace一起在惠特尼看了藝術家Josh Kline展覽的合影,並動情地説:“能夠認識Candance 真的很榮幸,藝術家的大讚助人。

今年4月,希夫(左一)在ins上po出自己和Candace(右二)
一起在惠特尼看了藝術家Josh Kline展覽的合影
作為巨大財富的持有者,Candace給予了希夫令人難以置信的信任。在她長達20餘年的當代藝術收藏經驗中,Candance全權委託希夫作為自己的代理人,負責架構和協商一切收藏交易。雖然和圈裏諸多勢力都很熟稔,但Candace很少與畫廊或賣方直接聯繫購藏事宜。她將這一切都交給了希夫。更令人驚訝的是,Candace竟然還通過希夫進行藏品的付款:她將錢款打給希夫,再由希夫付給畫廊或經紀人。

2019年11月,亞德里安·格尼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大型個展之一 “我轉過了我的臉”在聖彼得堡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白廳”拉開帷幕。格尼為了這次展覽,集中蓄力創作了一系列新作,大型解構抽象繪畫《uncle 3》是其中最令人記憶深刻的作品之一,暴力的解構畫面,充斥着格尼標誌性的扭曲的肉體和爆發的情緒。就像藝術家所説的:“你的眼睛無法辨識出形象,但大腦知道,形象就在那。”

亞德里安·格尼在聖彼得堡國立艾爾米塔什
博物館個展 “我轉過了我的臉”現場
2021年4月,希夫知悉此作可售。她第一時間將這個消息分享給了Candace。很快,Candace聯同自己的丈夫和朋友共同買下了《uncle 3》,Candace佔50%股份,其他兩人各佔25%。
2022年11月,Candace等人決定將此畫交給希夫,通過香港蘇富比私洽平台再銷售,並以250萬美元的價格成功交易。按約定,希夫從中獲得25萬美元的佣金。
此時,距離Candace等購買此畫僅一年半,距離藝術家創作此作不到3年。諷刺的是,希夫曾公開表示:“我不服務妄想投資藝術賺錢的人。我只跟願意長期持有作品的藏家合作。” 但如此快進快出的“短平快”操作,幾乎可以説是藝術市場投資運作的範例。
這也是藝術界的弔詭之處,整個行業似乎就像格尼展覽的名稱“我轉過了我的臉”,假裝這些事情不存在,不能説,實際上卻乾的比誰都歡。

亞德里安·格尼《uncle 3》
交易完成後一個月,各位“股東”收到部分錢款,餘款180萬美金希夫許諾在3月付清。但付款日期一拖再拖,直到5月,股東們仍舊沒看到180萬長什麼樣。
5月,股東之一,也是這次跟Candace聯名上訴的藏家,開始坐不住了。因為家庭原因,他急需這筆錢,他幾乎是請求希夫支付餘款。希夫冷漠地回了兩個字:“在辦”。
一週後,當再一次面對股東們的質問,希夫終於承認:“錢沒了。你們跟我律師説吧”。

至此,Candace和希夫友誼的小船徹底翻了。Candace等立刻將希夫告上法庭,指控她詐騙,非法侵佔他人財產,要求她賠償205萬美金。在接下來的調查取證中,Candace的律師團隊發現真相遠不止這消失的205萬美金。
這些年,希夫看似過着奢靡的生活:2.5萬美金一個月的房子,幾個孩子高昂的私校學費,流水一樣的奢侈品,頭等艙旅行,10萬美金一期的戒癮療養。“所有的都是VIP,她從不用優步,永遠都是提前定好專車服務。” 一個熟識希夫的人説。但與此同時,希夫在不停地跟人借錢,延遲對客户的付款。
其實,格尼《Uncle 3》的全款,蘇富比香港早在1月底就已經支付給了希夫。但希夫挪用了這筆錢用於支付私人債務和維持奢侈的生活。拔出蘿蔔帶出泥,經過調查,希夫數年前便已深陷債務漩渦,她光鮮的生活,看上去龐大的生意版圖,和星光熠熠的社交名單背後,是不斷挪用客户匯給她用於買作品的購藏款和賣作品的收益;拆東牆補西牆,東家騙來西家還,“以卡養卡”地在不同客户的追款下輾轉騰挪。
疫情爆發前,希夫曾一度考慮過終止這一切,申報破產,但因為懼怕被調查入罪放棄了這最後懸崖勒馬的機會。就像穿上了紅舞鞋的女孩,明知道這樣跳下去會累死,但仍舊無法控制地瘋狂跳着絕望的舞蹈。
當格尼事件爆出後,Candace接到了多個畫廊追款電話,她非常疑惑:什麼?自己明明通過希夫付了錢,卻仍被追債?從不與畫廊直接協商購藏的Candace第一次開始了和各畫廊的溝通,而得到的回答令她目瞪口呆。多年來,希夫不斷貪墨挪用Candace付給她的作品款。其欺詐行為涉及從藍籌到中生代到年輕的全階層畫廊和藝術家。僅就Candace這一個客户而言,希夫涉案金額已經達到660萬美金。

Candace 曾通過希夫以60萬美金購藏Wangechi Mutu2019年為
大都會美術館定製的雕塑《The Seated IV》 ©️大都會博物館
通過現有的材料來看,希夫的欺詐手段主要有兩種:
第一,鳩佔鵲巢:希夫將本屬於Candace的作品佔為己有。
Candace曾在佩斯畫廊買了一件45000美金的作品,當Candace向佩斯追要作品時,她被告知此宗交易的買家是希夫的顧問公司,而非Candace,所以雖然Candace是付款人,佩斯也收到了錢,但現在卻沒辦法放貨給她,因為法律上的“作品所有人”是希夫。
希夫的慾壑難填還可以從Candace 出資16萬美元買下的兩張90後藝術家Chloe Wise的油畫作品上看出來。出售這兩張作品的Journal畫廊清楚地知道藏家是Candace,而希夫只是代理人。但希夫仍舊多次擅自聯絡畫廊,希望畫廊將貨直接放給她。好在畫廊遲遲沒有照辦,不然,這兩張作品恐怕也很難保得住。
第二,挪佔錢款,虛假交易:Candace 曾通過希夫向Gladstone畫廊全款購藏了Sarah Lucas 39萬美金的雕塑作品CASANOVA,以及 Wangechi Mutu 2019年為大都會美術館定製的雕塑《 The Seated IV》,價格60萬美金。這兩件作品的錢款均已被希夫挪用,至今仍未清付。

Candace曾通過希夫以39萬美金的價格向Gladstone畫廊
全款購藏了Sarah Lucas的雕塑作品CASANOVA
除了藍籌畫廊,還有Pilar Corrias、Nino Maier、Andrew Kreps等集中製造市場新星的中生力畫廊也有多宗交易款項被希夫挪用。
更可怕的是,希夫的欺詐行為很可能不僅限於Candace這一位客户。如果只是一兩件糾紛,或許可以用溝通不足、誤會、巧合等等來解釋。但從現在的資料看,希夫的行為已經形成了明顯的規律。“ 藏家、藝術家、畫廊,涉案者遍佈在藝術界的每個層面。我們估計馬上就會出現新的受害者。” Candace 的律師説。

幾個月前,我曾以新晉藏家程先生的遭遇寫過一篇關於真假藝術顧問的文章。在那篇文章裏,我從新晉藏家的角度談了談如何篩選靠譜的藝術顧問,如何與他們一起工作。而麗莎·希夫的案件暴露出,
哪怕是資深藏家在處理和藝術顧問的關係上,依舊可能出現令人匪夷所思的“騷操作”。比如Candace 幾乎所有的購藏都通過希夫進行付款,而她更是將自己的所有收藏,毫無邊界地全部交給希夫進行打理——這給予了希夫可以在不引人懷疑的情況下隨意調動、出售、佔有Candace的作品的機會。“金錢加上信任加上不透明等於麻煩”。一位長期從事藝術犯罪諮詢的律師説。
我們要思考的是,這很可能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問題,它也反映出了整個藝術市場的體制性弊病。對這次的希夫案,很多人表示無法理解。希夫並不是一個純靠上天眷顧的幸運兒,她受過良好的教育,她擁有敏鋭的商業嗅覺和靈活柔軟的身段,可以説,她的能力襯得上命運賜予的機遇。但恰恰是這種強大,讓類似醜聞更加令人唏噓:這些人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衣冠楚楚,活在社會的最上層,但他們最終選擇犯罪。到底是什麼促使他們跨過道德和法律的底線?
“希夫們”為什麼會積聚起如此龐大的債務,而不得不鋌而走險?這當然可以説是某個人生活的失敗,但作為一個藝術顧問,我很想借此,從這個職業的角度來談一談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首先,確實,作為藝術顧問,你似乎需要和客户站在同一個社會階層上:你們要去相同的餐廳,出現在相同的社交場合,去同一個地方度假,住同一個酒店,送孩子們去同一個學校,穿相似級別的品牌服裝,拿相同的包包,等等。只有這樣,你才能接觸,並和他們建立起友誼,或者合作關係。但隨之而來的,是鉅額的費用與開銷。
比如香港巴塞爾期間,大客户集聚的奕居和瑞吉酒店,每晚房費上萬。去往香港的航班上,大家津津樂道誰與誰同機,誰遇到了誰,如果想跟大藏家們談笑風生,藝術顧問是否有不坐公務艙的選擇?答案是:沒有。這似乎是行業性質決定的,想要服務高淨值財富人羣,就需要先成為他們的一員。只有這樣,才值得高淨值財富人羣給予信任。不然,你就是不配。
但這其實是個偽命題。這個世界上確實存在家裏有礦,純粹熱愛,想實現自我價值的“王子公主型”打工人。但問題是,這些“王子”和“公主”的服務對象極為有限,通常都是家族內部長期關係人。
而更廣大的藝術顧問永遠不可能比自己的客户還有錢。客户們用“他是不是和我一個財富階層”來評判顧問的可靠性是非常荒謬的,高淨值財富階層壞人多的是。
王思聰説過很多蠢話,但有一句話我覺得他説得很對:“我不在乎朋友的家世,還是要看人本身,是不是好玩、人品好,有錢沒錢太不重要了。反正都不如我有錢。” 如果一個藝術顧問看起來比他的客户還有錢,而每一筆交易都似乎是他/她在幫你的忙,帶着你玩,我只能説,這很有可能是她/他在迎合你的慕強心態,而並非真實的他/她。請你多一份心眼,仔細查一查。
而且,這樣的慕強心態,逼迫着藝術顧問不得不斥重資打造出一件虛偽的“ 國王新裝”,一邊假裝自己“不差錢”,一邊將所有掙到的錢都扔進了社交,旅行等“維護關係”的活動上,經濟情況入不敷出,現金流脆弱得像一棵豆芽菜。
我還見過很多偽裝時間久了,真的以為自己是“他們的一份子”,自我欺騙到放縱慾望膨脹,從而跑偏的“藝術顧問”。他們無法正視自己是服務財富人羣的第三產業人,而開始認為自己其實就是超高淨值人羣的一員。他們仿效客户的生活方式,追逐着從不屬於,也不會屬於他們的窮奢極欲的享受,並從中獲得虛幻的滿足。
所以,一姐一直認為,藝術顧問,是個高風險職業。我們每天需要面對太多的誘惑,心理上很容易產生不平衡,陷入奢靡的彩虹泡泡,忘記了自己到底是誰。如何放平心態,擺正位置,不妄自菲薄,也不自命不凡,真正的把“藝術顧問”這個職業當成一份工作,不卑不亢地把握自己與客户的關係;謹慎地計算成本回報,勤奮踏實地耕耘下去,而不僅僅是把它當作用於社會階級提升的金身,一步登天的靈丹妙藥,和粉飾自我的偽裝,是個非常大的挑戰。
藏家們也需要認識到,不以出身論英雄,不要看一個人穿什麼,吃什麼,住什麼,要看他/她真正做了什麼。物質是最容易偽造的,你以為的 “我們之一”有時只不過是一個假象。更不要説,所謂的“我們”都時常朝不保夕,尤其是在現在全球經濟下行的情況下。畢竟,連美國都要變成“失信人”了。
最後,一姐再一次強調,不要給藝術顧問打作品款。面對毫不設防的鉅額財富,跨過道德法律的那一條線,有時真的只需要一個bad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