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譯:他沒了,我真心疼......_風聞
影探-影探官方账号-美日韩剧资深鉴赏员,电影专业老司机06-03 13:15
作者| 甜茶
來源| 影探
羅京民走了。
在此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這位演員的名字,但始終記得他的臉、他的角色,想必你也認得其中幾個:
《孫子從美國來》中的老楊頭,《士兵突擊》中許三多的父親許百順,從1993年的《站直囉別趴下》到2022年的《人生大事》,《平凡的世界》《山海情》《北平無戰事》《生死線》也有他的身影。
不常當主角,但總是點睛。



從上到下:
《孫子從美國來》《士兵突擊》《人生大事》
他最華彩的角色,是《我的團長我的團》中郝獸醫。
遺憾的是,羅京民的專訪很少,因此回顧他的人生,作為觀眾總難窺探細節,這是太多演員的宿命。
去年寫過一篇文,關於《我的團長我的團》(文章鏈接戳丟光了臉,才拍出一部神作),限制於篇幅,角色只匆匆帶過,也未提及“郝獸醫”一角。
卻沒想到是這樣的機會,才提筆為“郝獸醫”寫篇人物傳記。

藉此:
以一個角色來祭奠一位演員。
以一種死亡應答另一種死亡。
 戲
戲
《我的團長我的團》敍事於1941年。
全面抗戰爆發後的第十個年頭。
戰火將大半個中國燒出瘡口。
潰兵敗將們蜷縮在滇西小鎮禪達苟活度日,共享同一個名字“炮灰”。

郝獸醫,本名郝西川,陝西西安人。
做老百姓時匆匆趕往戰場救助傷兵,然後被傷兵裹挾進潰軍大潮,套件軍裝,變成了軍醫。
他的醫術很怪:
三分之一是中醫,三分之一是西醫,三分之一是自己久病成醫。
他能把腳氣治成截肢。
因為沒治好過任何人,所以被稱為“獸醫”。

有人胳膊潰爛了。
郝獸醫望聞問切加摸心臟看舌頭,主觀加客觀地亂用,他用一切在無器械情況下能用的診療手段。
但在禪達,有診療,無治療。
沒人信他的醫術,他才五十六歲,就被炮灰們不客氣地稱為“老頭子”和“老不死的”。
可郝獸醫總是熱心。
每一個傷兵都是他的傷員。
包括張譯飾演的孟煩了。

孟煩了的一條傷腿是裝死時被日本兵刺的,他所在的連隊拿着刺刀跟敵人的坦克對拼,全死了,就活下他一個。
豪情壯志早熄滅了,少年中國夢也碎了。
他心中不平,嘴上毒辣,覺得被虧欠了。
仗,他是不想打了,只想治好這條爛腿。
反正好死不如賴活着,賴活就得變成扶不上牆的爛泥、爬不出坑的爛蛆。
想不明白了:
“我不要明白,只要我的腿!我只要知道很多人比我更爛!”
郝獸醫卻難受:
“你才二十四歲,就跟人比爛了。”

當炮灰們被整編成川軍團。
郝獸醫追隨這羣比他年輕二三十歲的漢子們一起行軍,坐飛機、進緬甸、穿叢林、上南天門、守祭旗坡……
他是綴在他們後面的尾巴,也是行走在他們中間的火苗。
儘管他沒殺過半個敵人,沒救活過一個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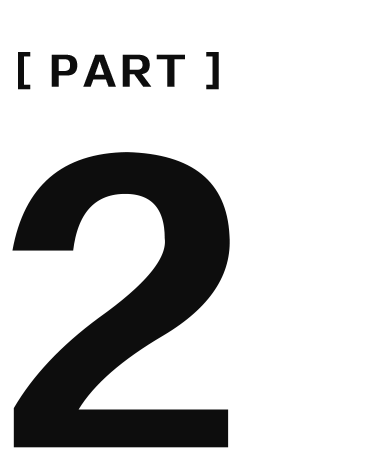 善
善
郝獸醫把炮灰們當孩子,他叫他們“娃娃”。
他敏鋭、悲憫,記掛着他的病人。
康丫臨死前,肺部被日兵擊中,他説想吃一碗山西老家綿羊肉刀削麪,所有人都在笑他侃他。
郝獸醫卻忙不迭地接茬兒:“我去找”。
此時他們剛經歷一場惡戰,窩在禿山頭的凹坑,鬼子的增援提前趕來,並帶來毒氣。
戰火再起再停。
郝獸醫也不跑,拿着濕布給傷員堵嘴,直到白眼一翻暈了過去,醒來時便去尋康丫。
康丫説他要照照鏡子,以前他做運輸兵時,最愛照後視的鏡子,炮灰們把刺刀磨亮拼在一起。
郝獸醫在暗中擦亮火柴,想映出康丫的臉。
康丫一直喃喃:看不見,看不見……然後死去。

郝獸醫給康丫蓋土前,端來繃帶當成面,並附上一盒罐頭:
“刀削麪,羊肉,山西綿羊肉,就着吃。”

炮灰想説:“連死人你都要騙啊?”
但看見郝獸醫那雙全無戲謔只有悲傷的眼睛,就都不再説話了。
忘不了郝獸醫那雙盈滿淚的眼睛。
在暗處,比殘酷的夜色更涼更沉。
也可品出羅京民演技裏那驚人的感召力。

郝獸醫是眼淚最多的那個人。
豆餅受傷後,郝獸醫給他擦身子,嘀咕着要給他一幅乾淨屍身。
直到豆餅被帶去師部醫院。
郝獸醫才露出笑臉:
“豆餅娃有救了,明兒我要到廟裏燒香。”

炮灰們總是笑他。
説“郝獸醫擦汗,就莫得好事嘞,準有人死。”
説“獸醫,一會我燉你的骨頭,給你煲湯喝。”
説“死老東西,有種就站出來。”

炮灰們總是言不由衷,但郝獸醫包容着炮灰們的嘲諷、不甘與痛苦。
所以團長龍文章渡江偵查時要帶着郝獸醫。
他認為:就算我死了,至少獸醫的話還有人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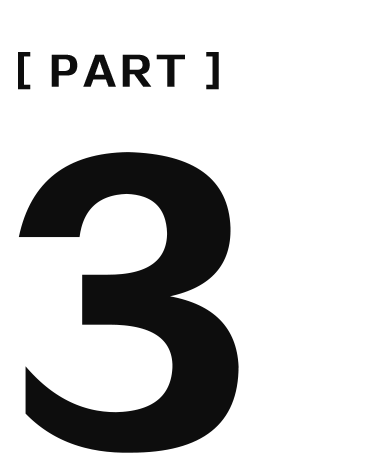 別
別
郝獸醫越來越糊塗了。
不到六十歲的臉上有了九十歲的皺紋。
他總是問鑰匙在哪,説鑰匙丟了,想找鑰匙。
炮灰們被放置在談判桌上,投擲、博弈、消損…..上頭想派他們攻下南天門。
孟煩了去問郝獸醫。
孟:“讓咱們上趟南天門,死個精光,功勞全給不相干的人佔。你幹不幹?”
郝:“為啥?給死也要給個痛快吧?”
孟:“拿堆炮灰換個南天門,何樂而不為?”
郝:“我日他個何樂而不為!”


可等到孟煩了再問郝獸醫:“值嗎?值啊。”
郝獸醫卻説:“值啊,換得值啊。”
他曾説:“日本人的心肝跟我們長得可是一樣的啊。”
他又説:“反正只要跟小日本鬼子打仗,就不叫狗拿耗子。”
孟煩了怕自己不知道為什麼去死。
龍文章怕底下的兵不知道怎麼活。
郝獸醫怕娃娃們不知道怎麼活,又怕娃娃們無辜送死。

但郝獸醫死了。
他只是在那坐着,就被日兵的九二步炮瞄中,跌到崖下。
一個團怒了。
炮灰們打了自從上祭旗坡後最慘烈的一仗。
慘烈到完全不顧寒酸的彈藥儲備。
唯一的一門迫擊炮調到最大射程。
迷龍臉上出現許久未出現的仇恨。
團長幫着克虜伯親手打出幾十發炮彈,終於掀翻了對面那門九二步炮。
就為了一個活着不多、死了不少的破老頭子。

孟煩了和迷龍一起冒死下到峭壁下搶回郝獸醫的屍體。
繩子穿過老頭兒的肋背。
繩子拉起時,郝獸醫像和太陽融為一體,變成沒有翅膀的老天使。
迷龍張大了嘴號啕哭泣,孟煩了也忍不住眼淚。

在收拾遺物時。
孟煩了翻出老頭兒的零碎:
針線、破布頭子、線團、哈喇了的油……每一樣都是為了能給炮灰們搭把手。
還有一紙信,來自獸醫兒子的同僚。
敵軍包圍,援兵不到,獸醫的兒子在中原戰場力戰殉國。
在《我的團長我的團》書裏(書出版在劇本成型之後),編劇蘭曉龍補充道:部隊公然投敵,兒子不從,被陣前槍決。
“死則死矣,連小勝都沒得半個。”
不是死在敵人倒下,而是死在自家人的槍口。
臨死前,獸醫反覆唸叨幾次:
“我是傷心死的。”
“我是傷心死的。”
“我還是傷心死的。”

他在傷心什麼呢?
兒子?娃娃們?
還是到死不能還鄉?
糊塗的時候他説:“黃土土坡下大雨了。”

被炸死前他的手裏攥着孟煩了為了埋汰他寫的《笑林廣記》:
“初從文,三年不中;後習武,校場發一矢,中鼓吏,逐之出;遂學醫,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人生竟一無是處。
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這是孟凡了開的最惡毒的一個玩笑。

郝獸醫的死對炮灰團來説是“父”的隕落:
“我們不僅失去了一隻在死時可以握住的手,還喪失了我們中間唯一的老人。我們只剩下二三十歲人的衝動和瘋狂,因為我們喪失了一個五十七歲人的沉穩和經驗。我們失去了軟弱,可並沒有變得堅強,我們發瘋似的想念獸醫的軟弱。”

郝獸醫普通但稀缺,軟弱卻可依靠。
所以孟煩了一邊埋汰他,一邊又在做決定前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郝獸醫死後,孟煩了説:
“他從不惡毒,中國人習慣為死人説好話,這是我能為他想到的最好的一句話。”
羅京民去世後,張譯發文:
“心疼你啊,老爺子……”

根據羅京民生前意願,他去世後不設靈堂、不收花圈、不收禮、不發訃告、不舉辦告別儀式。
於是觀眾與他在現實中的交集,再少一分。
他願意把自己藏起來。
羅京民是1956年生人,直到50歲才憑藉《士兵突擊》出名,去世時67歲。
沒有受到過狂熱追捧,但奉演藝事業為一生。
有多少演員如他一樣呢?
要念要想,便念便想那些作品去。
這是他的意願,也是觀眾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