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代號“木匠”的特工父親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06-28 21:07
真實戰爭故事2023年06月28日 20:15:250人蔘與0評論
大家好,我是霞姐。
2019年5月,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間諜博物館新館開館,這是一家全球間諜藏品最多的私家博物館。
博物館5樓是秘密電訊展區,展區首位的玻璃罩後面,有一張中國面孔。文字介紹中,把他發明的“無形電台”, 稱為“一個小聰明家的天才發明。”
這個小天才發明家,叫塗作潮,一名代號“木匠”的紅色特工。

塗作潮出生在湖南,年少家貧,早早輟學做過一段時間木匠。
1920年11月,木匠塗作潮成了湖南勞工會的首批會員。後到了上海謀生,在1924年上海工人運動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第二年,因未經批准開槍擊傷歹徒暴露了身份,為保護他,把他秘密派往蘇聯留學。
塗作潮“暴躁,喜弄手槍” “不鎮靜,不知秘密工作” “很勇敢,能站在團體以內”。
以上是蘇聯同學給他的評語,可見他並非特工的天選之人。
對於在蘇聯學習的這一段,塗作潮自傳中只有簡要記載:1925年11月進入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1927年夏天開始接受軍事訓練。
直到1991年前蘇聯部分檔案解密,塗作潮的兒子塗勝華藉助各種關係,才查到父親在俄羅斯的檔案。
207頁的資料中,駕駛、射擊、戰場指揮、格鬥、爆破、密寫、印刷、化裝、防止説夢話泄密、信鴿技術……
一個優秀特工所具備的技能,塗作潮都一一掌握。

六大會議舊址
檔案顯示,1928年六七月份,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召開。
塗作潮作為旁聽代表,向中央呈遞了3份請求儘早回國參加武裝鬥爭的報告,裏面都提到,希望能儘快掌握毒氣、火藥和炸彈技術。
時任中共中央軍事部書記的周恩來在其中兩份報告上分別作了批示:“留下學習待討論”和“待決”。
除了提交報告,塗作潮大會期間還三次發言,這也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周恩來瞭解他曾經的經歷後,拍拍他的肩膀,高興説:“你幹過木匠,我們以後就叫你木匠吧。”
至此,“木匠”也成了他的代號。
另有一份檔案則提供了塗作潮的去向:1928年10月26日,經共產國際同意,由中共選派6名學員,秘密學習無線電技術,女生不宜。
塗作潮以首選列入名單。
為了掩護這次調動,1928年11月6日,共產國際向東方大學發了假調令:調沃羅達爾斯基同志去列寧格勒托爾瑪喬夫軍事學院學習。
真實情況是,塗作潮與劉犧吾、宋廉和覃顯猶,去了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為期11個月。
成立於1924年的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一直處於絕密狀態,直到1974年,蘇聯方面才公開承認列寧格勒有那麼一所學校。
學校絕密,學生信息更是。

報務員的選拔是異常嚴格的。
他們要有超出常人的記憶力,要有絕對安全的出身背景,要對保密原則無條件服從。
他們還得要有一雙靈巧的手。
那小小的發報機上,你稍微輕輕一碰就是“嘀”,你稍微手沉一點就變成“嗒”了,輕重拿捏之間都是扭轉乾坤的大事,錯不得。
而一旦被選中,他們的世界裏,從此就只有“嘀、嗒”兩個聲音了。
可惜作為首批入選的學員,塗作潮學習無線電報卻十分吃力。他沒有學過數學課程,無線電公式對他來説無異於天書。
學校要求報務員每分鐘能記錄下100個電碼,而塗作潮連30個都記不全。
教員給他做了一個語氣委婉的不合格判定:高等數學的知識幾乎等於零,有可能無法完成一年的強化學習。
就在塗作潮對留學生涯感到一片茫然時,學校政委給他指了條明路:報務學不好,就專攻機務。
機務就是組裝、維修電台,勉強算是“電工”一類吧。
電工和木工雖然相差十萬八千里,但塗作潮心靈手巧的天分卻被激發了出來,他觸類旁通,學起機務來如魚得水,不合格的報務員反倒成了最優秀的機務員。
塗勝華在查找檔案的同時,還四處尋找與父親同時入學的另外3人的下落。他從父親的自傳裏看到,宋廉1931年開了小差,下落不明。
直到1996年,塗勝華找到了曾在列寧格勒東方學院任教的李一凡老人。李回憶,劉犧吾與他都曾被流放西伯利亞,劉在流放期間死去。
為尋找“小廣東”覃顯猶的下落,塗勝華幾乎查遍廣東每個縣市的黨史辦。2006年前後,才偶然得知其為廣西武威人。
多方尋找到了覃顯猶之孫,得知覃顯猶多年前已在加拿大去世。塗勝華匯款給其後人,請代為祭掃。
一個老人的逝去,猶如一座圖書館的滅失。何況還是個特工。
在塗勝華兒時的記憶裏,父親塗作潮總是很忙,而且還很窮,連他上幼兒園的費用也支付不起。
他們家附近就有個幼兒園,塗勝華好羨慕,裏面的小朋友對他説,每天午餐後他們都可以吃一個蘋果或者鴨梨。
有一天,塗勝華正好奇趴在幼兒園門口使勁往裏看,塗作潮遠遠走過來,低聲訓斥:“有什麼好看的,回去!”
塗作潮時任上海電機廠的廠長助理,級別並不低,可怎麼還那麼窮?
儘管如此,在塗勝華心中,父親依然是神秘而無所不能的。
比如鄰居忘帶鑰匙,塗作潮能像蛇一樣從鄰居家的氣窗穿過,無聲落地,開鎖。
再比如有一次,塗作潮找出家裏的果凍,用温水溶化後,整整齊齊放在一個方形的盤子裏,塗勝華以為父親是要做點心,守在一旁翹首以盼。
只見塗作潮讓大女兒把用紫藥水謄寫的履歷,“啪”貼在了果凍上,紫色的字全部印在果凍上。
然後又拿出幾張白紙,整齊貼在果凍上,用手一捋,果凍上的字竟然複印到白紙上,一份變多份。
塗作潮有些得意地揚着手中的紙説:這是我在蘇聯上學時學到的。
當時年幼的塗勝華有點難以置信,寫字歪歪扭扭的父親,竟然在蘇聯留過學?只是太小沒有追問。
塗作潮一萬八千字的履歷複印了五六份,一份有52頁之多,除交給上級審查之用外,還藏了兩份在家中。
這成了塗勝華時常偷看的精彩“小説”,也成了他了解父親的一個藍本。
塗作潮蘇聯留學歸來,先分配到上海中央特科的四科,即交通科,任機務員和機務教員,參與無線電訓練班的工作。
後被調到了中央蘇區,任中央紅軍總司令部電台機務員,做了很多重要工作。

塗作潮(右二)和延安特科戰友(1944年)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任紅軍第一個無線通信材料廠廠長的塗作潮,因患有惡性痢疾,隨後方部隊轉移,與大部隊失散,輾轉找到長沙的大伯。
大伯提議,找不到組織不如向國民黨自首算了,以他當時的技術,也是國民黨急需的人才。
這時,大伯的一個朋友卻對他説:不行,你是對黨宣過誓的人,還是從一而終好。
這節“黨課”堅定了他的信仰,他拿着湊來的路費,徒步、乘車輾轉千餘公里前往上海尋找組織。
後受中央秘密派遣,於1936年9月從上海潛入西安,在那裏秘密裝配了三部電台。
鑑於塗作潮精湛的電訊技術,他被留在了西安。
“西安事變”前3天,塗作潮奉命搬進了張學良的公館,在那裏裝配能向全國通報的、輸出功率為100瓦的第三部電台。
在張學良公館,塗作潮見到了身穿一套黑色中山裝的周恩來,周恩來也遠遠見到他,招呼道:“木匠啊!木匠!我們又見面了。這些年你吃苦了。”
塗作潮激動得有些不知所措,只是簡單地重複着説:“你好!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
此時周恩來已經剪掉他蓄了六七年之久的大鬍子,只是茬口還參差不齊。周恩來摸着自己的胡茬説:“喂!木匠,你有刮臉刀嗎?”
塗作潮回答説:“我沒有刮臉刀。只有刀片,也不太快了。”
周恩來用塗作潮的剃鬚刀片刮乾淨了臉, 然後容光煥發地走出張公館,同蔣介石談判去了。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塗作潮受命隻身前往上海,開始另外一場血雨腥風的電波暗戰。
此時的上海早已是一座孤島,塗作潮需要一個新的身份,好隱藏自己。
對於塗作潮來説,開設無線電修理行做社會職業掩護是最合適的,因為這是他的專長。
但開修理店,如果修理不了當時上海最流行的超外差收音機,就可能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超外差收音機從國際流入上海沒幾年,它和以前市售的再生式或者超再生式收音機相比,靈敏度和選擇性更好。
塗作潮此時的超外差技術,僅限於在蘇聯老師那裏學到的一些蜻蜓點水的理論,而自己的實踐卻一點沒有。
他開始惡補超外差技術。
半年後,塗作潮有底氣了,就在上海赫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常德路572號,開設了恆利無線電公司。
從1937年7月到1940年,塗作潮自學超外差技術不僅有了很大的長進,而且讓他在有意無意間,發現了中頻再生現象可以臨時充作差頻振盪器的秘密。
這為他後來發明無形收報機奠定了基礎。
打理修理店的閒暇之餘,塗作潮還得和上海三教九流打交道。有一次,一個經常同塗作潮一起玩牌的米店老闆對他説,你像共產黨。
塗作潮聽了之後暗暗吃驚,但仍不露聲色,若無其事地問哪裏像呢?
三十多歲事業小有成就,一個人住一棟房子,平時問得多,説得少,又沒有老婆孩子。怎麼看都有問題。
塗作潮不動聲色回答,房子我租出了一半,租金兩兩相抵還有點剩餘。至於老婆問題嘛,請你幫助介紹一個。
米店老闆提醒了他,他向組織彙報後,上級要他找個沒文化的婦女,有文化容易看穿他,真夫妻、假同志,條件一條:不能要孩子。
幹這行的,説不定哪一天就掉腦袋了,留下孤兒寡母悽慘不説,還難照顧。
這次,塗作潮沒有全聽,找了個帶孩子的寡婦,後來他們夫妻也生了五個孩子。矇在鼓裏的妻子是個樸實的紡織女工,她並不知道自己的枕邊人,每天做着掉腦袋的事。
1939年冬天剛剛結束,塗作潮接到新任務,配合中央蘇區來的報務員李白,做好上海的情報工作。
李白是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的原型,是中央軍委三局局長王諍的得意門生,李白到上海從事地下情報工作直接受他指揮。

塗作潮(左三)與王諍(左四)的合影
在延安總枱,李白相對應的收報員是秦巖,王諍的愛人。可見當時中央對李白的重視程度。
塗作潮和李白會合後,作為掩護,在威海衞路338號開設了福聲無線電公司,一樓店鋪,二樓途家四口,三樓李白夫婦。
福聲,幸福的聲音。多麼美好的期待。
店裏,塗作潮是老闆兼師傅,李白是賬房先生兼學徒。
那時的上海,諜戰風起雲湧,無數神秘電波穿過日軍的封鎖,在深夜中肆意穿行,與同樣龐大的情報網絡結合時,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可怕戰鬥力。
塗作潮的特長派上用場。他通過在無線電商店購買的一些零配件,給李白改裝了一台非常獨特的電台。
該電台功率小、電波信號弱,但通過塗作潮對波長、天線的巧妙處理,照樣能把電波信號清晰傳遞到1500公里外的延安總部。
秦巖曾經回憶説,當她在軍委總枱第一次接到李白台發來的信號時,圍在周邊的眾多情報系統領導人一片歡騰。
更絕的是,李白的這部電台,搭載了兩個小線圈,既能發報也能收報,如果緊急狀況下卸載掉這個線圈,它就是一部普通的收音機。
這被後人稱為天才發明的無形收報機,救了李白一命。
電台的偵測與反偵測是一場殊死的較量,每部秘密電台的守護者都知道,説不準哪一天,你的對手就會找上門來。
李白人很聰明,報務、機務均學得如魚得水,師徒二人也配合密切,但這時福聲公司的一個學徒卻無故失聯了。
避免將來出事時被敵人一網打盡,師徒二人分了家。
塗作潮將製作發報機和無形收報機,以及全套的機務技術給李白,作為出徒的禮物。
日軍進駐租界後,秘密工作變得更加危險。
1942年9月的一天,正在修理收音機的塗作潮,突然接到緊急通知:李白被日本人逮捕了。
李白在日本特務破門而入的幾秒鐘內,扯掉了收報機上兩根臨時焊接的小線圈,把它們拉直、揉亂,丟在一邊,變成一台普通收音機。
消息傳來,所有和李白有接觸的同志第一時間被迫撤離,和他接觸最多的塗作潮也在撤離之列。
臨走前,塗作潮才對妻子説了實話:我真名叫塗作潮,我是共產黨,我們的領袖是毛澤東。
他還説,假如自己回不來的話,要妻子千萬記住,如果是共產黨坐了天下,就去找毛澤東,他會管你們孃兒幾個吃喝拉撒的。共產黨要是沒有坐天下,帶着孩子改嫁,再也不要提塗作潮的名字。
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李俠被抓進憲兵隊,堅貞不屈,不招認自己是共產黨或者是抗日分子,最後給放出來了。
影片沒有講出的真實故事是:日寇的無線電專家整整用了8個月時間來研究、審查李白的設備。
他們的技術鑑定是:發報機完好,處於工作狀態;收音機反覆驗證,只能收音,不能發報。只有發報機,沒有收報機,無法形成現行電台的證據。
沒有現行電台的證據,是影片沒有講出的李俠獲釋的技術原因。
如果塗作潮凡事按照教科書辦事,將永遠不會有無形發報機的發明。
因為自打有了超外技術的那天起,就伴隨着中頻再生引起的二次振盪,或者中頻再生造成的嘯叫。教科書是必須消除之,絕無廢物利用或者變廢為寶的道理。
塗作潮的特別之處卻是,仔細留心這種嘯叫,也順着中頻再生的問題往下想問題。別人都要去之而後快的問題,他卻逆向思維地加以利用了。
偶然也好,必然也好,他經意或不經意間,把這層窗户紙給捅破了。
也就是説,如果塗作潮沒有嫺熟地掌握了超外差技術,就絕不會有後來無形收報機的發明。
當然,也不會有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精彩片段。

大家可能會好奇, 即便沒有現行電台的證據,日寇為什麼就放了堅貞不屈的李白了呢?
要知道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是日寇專門迫害抗日誌士的特務機關,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真實的歷史是,擔保李白出獄的是周佛海,汪精衞偽政權的警政部長兼上海特別市市長。
周佛海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投敵後,為了給自己留一條後路,也通過種種渠道,和重慶的國民政府保持着聯繫。
而周佛海的兒子周幼海恰恰就是中共黨員。
李白被捕後,營救他的中共特科骨幹之一華克之,在自己多如牛毛的社會關係中,選定了一個恰如其分的中間人—任庵。
任庵的父親是一個滿清重臣,家境富可敵國。任庵和周佛海的私交很好,周佛海就順水推舟做了這個人情。
李白被保釋出獄後,一直留在上海從事暗戰工作,直至上海解放前夕再次被捕。
這一次,李白沒能被救出,臨刑前,他對隔空相望的妻子説:“天快亮了,我等於看到了,不論生死,我心裏都坦然。”
上海解放,黨組織在李白就義的地方,找到他的遺體。李白的追悼會上,上海市領導、烈士遺屬和親密戰友們都在主席台就座。
從解放區回來的塗作潮站立在台下千餘羣眾隊伍中,無人知曉他們一起打過的那些勝利之戰。
塗作潮家庭合影(1948年在西柏坡)
關於無形收報機的秘密,塗作潮是準備帶進棺材的。
1958年,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製片廠找到塗作潮,瞭解背景故事,同時請他為影片中的抗戰時期製作道具,塗作潮欣然答應了。
如果通過電影講出了無形收報機的秘密,則全中國起碼幾百萬台收音機都有可能成為臨時收報機,造成巨大的治安隱患。
如果讓收音機收報,則觀眾中懂得無線電通信的人馬上會質疑影片的真實性。
於是,塗作潮做了個假道具,即影片中和收音機連接在一起的、放在收音機上的差頻振盪器。
電影道具電鍵製作好後,塗作潮讓兒子試了試,兒子興致勃勃地按了幾個按鍵,突然回頭,只見父親滿臉悲傷説:“只有鬼才收得着。”
劇組給了30元道具費,塗作潮婉拒,電影拍好後,他拒絕在電影后面署上自己的名,劇組宴請致謝,又婉拒。
電影首映,塗勝華想到其中有父親的一份功勞,不禁有些自豪,換好乾淨衣服,興高采烈地準備去看電影。
母親卻低沉地説:“你有什麼好高興的?你要去和一個已經犧牲了好多年的好人見面。高興得起來嗎?”
這部傳奇式的電影風靡一時,塗作潮卻突然被開除黨籍,降兩級。
本就拮据的家,經濟狀況一落千丈,生活最困難時,一家人靠打撈江裏的菜葉充飢。

艱難過了五年,周恩來知道塗作潮的情況後,給他甄別“平反”,調往北京四機部休養。
臨行前,塗作潮特意到極司菲爾路76號門外照了一張側身照。
多年之後,塗勝華才知道這張照片極不尋常,因為“職業特務從不拍照,怕留下痕跡”。
他預感到“木匠”將一去不復返了。
到了四機部,塗作潮開始變得“反常”,別人喝茶看報打太極拳,他白天干木工、鐵匠活,晚上整宿整宿出去釣魚。
他釣來的魚自己不吃,都拿去送人。送魚有個固定的點兒,包括橫二條衚衕的伍雲甫家。
那時的塗勝華已14歲,無法理解父親的此種怪舉。後來一位心理醫生告訴他:一個人心裏憋了太多秘密,必須要找個渠道發泄,否則會瘋掉。
周圍的鄰居不知道穿着破衣爛衫的塗作潮是何許人,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
“木匠”消失了。

一張滿是秘密的特工的臉
1966年,塗作潮得知小兒子要出京串聯,將要行經過江西,塗作潮突然眼睛放光。
他問塗勝華要不要去南昌,如果到南昌記得去城崗村,找他的救命恩人魏朝鵬。説完還不放心地將“城崗村”三個字寫出來。
魏朝鵬是塗作潮履歷裏頗佔篇幅的人名,當時塗勝華年幼,不知道他對父親的重要。
這是塗作潮到北京後第一次主動提及他的過去,塗勝華看着眼前衣衫襤褸的父親,這才知道,如果不是魏朝鵬,塗作潮的特工生涯也許早在1931年就結束了。
那時,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作戰中活捉了國民黨前敵總指揮張輝瓚,國民黨上下大為驚恐,要保其性命,要求中共派人前往南昌商談釋放張事宜。
塗作潮和同事接受任務後,搭乘國民黨的水上飛機到了九江,然後坐船轉至南昌。隨手買份當地報紙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報上登載:張輝瓚已被槍決,其人頭放在門板上順水漂到了吉安。
人頭已落地,同國民黨的談判就無從談起,他們二人的生命安全處於危險之中。兩人立即決定離開旅館,撤回上海。
他們化裝成國軍黨軍官,借遊山玩水的名頭混出城,冒雨前行15 公里到城崗魏村,兩個人幾乎精疲力竭,於是進入城崗魏村暫時躲避敵人的追捕。
當地鄉紳魏朝鵬見塗作潮兩人全身濕透,招呼進家避雨。上茶時,魏朝鵬上了四碗茶,用青洪幫的暗號試探塗作潮是否為幫裏遇難兄弟。
恰好塗作潮在上海時和青幫有交道,自是應付自如。
誤以為是青幫兄弟的魏朝鵬對塗作潮二人禮遇有加,藏匿於魏家半個月有餘,躲過風聲必須回上海時,魏朝鵬準備了衣服和一船瓷器,把自己扮成塗作潮的隨行僕人,護送二人離開。
在臨別之際,魏朝鵬提議三人金蘭結義。於是三人交換金蘭譜,就地結拜。
塗作潮一直記着這份救命之恩,在建國初期,就曾多番尋找魏朝鵬的下落,甚至到過魏朝鵬家鄉所在地的農會或有關組織,都被告知查無此人。
塗勝華心想,此行一定要去問問魏朝鵬,父親説的是否屬實。但因其中途有變,未到江西,魏朝鵬一事被擱置。
塗勝華回到家後,父親大失所望。
這時的塗作潮,生活過的黑白顛倒,宛如一個行屍走肉,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或許他認為這樣,自己一直隱瞞的秘密就可以帶進黃土了。
但他的秘密還是被人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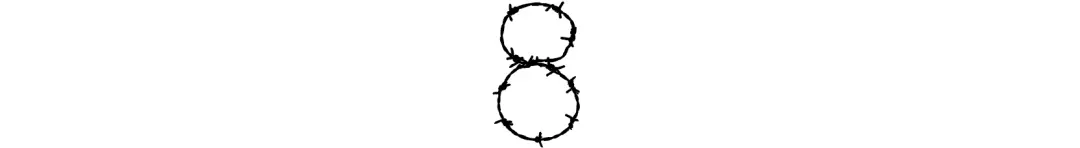
來勢洶洶的造反派把家團團圍住。
塗作潮手持10多斤的鐵棒,一臉殺氣,一躍跳到一米多高的蜂窩煤棚的頂上,用湖南話吼了幾嗓子:“毛主席、周總理,救救我呀,我是塗作潮,我是1924年入黨的塗作潮……”
就是這個為保護黨的秘密打死也不透露半分的特工,被以“國際間諜”關進四機部的牛棚,不僅他自己落得殘疾,年僅25歲的二兒子塗中華也被牽連受虐致死。
塗勝華每次去探望父親,父親都問及二哥的安危,塗勝華謊稱一切都好。塗勝華自以為隱瞞得很好,可他忘了父親是做過特工的人。
塗作潮出獄時也是塗勝華去接的他,回家的路上,塗作潮剛開始一言未發,走到一半,突然質問:你二哥的事,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原來塗作潮從兒子塗勝華送給他的換洗衣物裏,發現一條二兒子的毛褲,猜測出二兒子不是死了就是瘸了。
判斷兒子不幸後,塗作潮不吃不喝躺在牛棚一個星期,是難友硬灌糖水才得以活過來。
在牛棚,塗作潮遭上1000小時的刑訊逼供後,被迫交代了無形收報機的工作原理——中頻再生。
但他只交代出工作原理,製作工藝卻報了個假的——兩個線圈:
一個接中頻放大的輸出,另一個接收報機振盪管的輸入,適度的電感耦合形成中頻再生;具備機務知識的報務員就能駕馭這個臨時差頻振盪器了。
專案人員信以為真。如果他們照貓畫虎地做一遍,就會發現這個製作工藝是假的了。
塗作潮猜準了沒人會去試做。
對於無形收報機的秘密,塗作潮堅守了一輩子。
直到2007年,他的三兒子塗延華開始仿製無形收報機的實體可操作模型。
他在幾十次的努力中發現,如果按照父親説的製作工藝,永遠不會成功。
當然塗延華最後成功了。
他為父親叫好,無形收報機的製作工藝原來是這樣,而且竟然如此簡單!
今天,只要把無形收報機的圖紙畫出,任何一個從事無線電通信的人都能一眼看出這個間諜收報機的奧妙:中頻再生形成差頻振盪器。
這是一個説起來簡單,做起來很難的事,如果沒有機務技術,僅僅是一個技術嫺熟的報務員,是無法駕馭這個世界上最廉價的無形收報機的。
塗作潮出牛棚第二個星期就癱瘓了。
他所有的檢討書、申訴信件,幾乎都由兒子塗勝華代筆,父親終於卸下偽裝,讓兒子多了幾分理解。
他説:父親是個天真的理想主義者。
有一日塗勝華正代寫着父親的申訴,有領導找到了家,通知塗作潮去參加周恩來的遺體告別。
塗作潮用未癱瘓的左手接過信,整個人都在發抖。
塗勝華用輪椅推着父親參加了周恩來的告別儀式,他們的花圈很快就被覆蓋了,送的人太多了。
儀式上塗作潮悲痛萬分,涕泗滂沱。
這是塗勝華第一次見父親掉眼淚,也是最後一次。

1984年12月31日,塗作潮也走完了隱秘的一生。
去世前,他對家人交代了兩件事:找到魏朝鵬,報答他當年的救命之恩;自己連累了二兒子,希望死後能同葬一處。
這可給塗勝華留了個難題,二哥去世時沒有任何功名,無法和父親同葬進八寶山,他只得將父親從八寶山遷出,和二哥同葬在普通陵園。
如果塗作潮只是個碌碌無為的小人物,塗勝華覺得自己給他修一座豪華的墳頭也算敬了孝。但他越瞭解越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父親塗作潮一生不僅有他的傳奇故事,還代表了那個時代被歷史所遺忘的無名英雄們。

1979年特科戰友重聚,塗作潮坐着輪椅參加
可探尋一個特工的隱秘往事,不是容易的事,光有心可不夠。
不知一切是否早已註定,塗勝華遺傳了父親半個商人的基因,塗作潮在上海潛伏時,經營過幾家店都比較成功。
塗勝華後來做起國際電訊商務,竟也順風順水。
二十多年過去,他花費了200餘萬元,從海內外收集到和父親相關的資料證件1400餘件,家裏完全容納不下,就這樣,“塗作潮陳列室”被搬遷至燕郊獨立的院落。
夜深人靜時,塗勝華看着陳列館裏有關父親塗作潮過往的資料,常常忍不住想要問問:老塗,你看你的“秘密”都被我挖出來了,那些年,如果你知道做紅色特工會有這樣的結果,你還會不會願意做“木匠”。
沒有人回應塗勝華,陳列館裏只有英魂,沒有父親。
父親的兩個遺願只完成了父子同葬,怎麼才能找到救命恩人呢?
1995年,塗勝華以8塊錢一小時的時薪,僱了一個勤工儉學的女學生,讓她用兩星期,一天8小時幫他尋找魏朝鵬。
暑假回來,女學生拿着118元票據找塗勝華報銷,説很抱歉,自己沒能找到魏朝鵬。
塗勝華知道學生因為愧疚而報少了,按之前的預算支付400元的工資和300元的實報實銷款。
女學生將此事高興告知了她父親,老父親心想,世間還有這等好人,趕緊聯繫了一個姓魏的好友,希望好友幫忙找找。
三日後,魏朝鵬的下落找到了。
原來當年魏朝鵬的村子的確離南昌很近,只離了15公里,父親把村名記錯了,不是城崗村,而是城崗魏村。到了1954年城崗魏村又改名為鄧坊村。
塗勝華聯繫上魏朝鵬的後人得知,早在土改期間,魏朝鵬就含冤去世。
其實魏朝鵬的結局,塗作潮早已料到,當年他被造反派迫害時,坐在地上就仰天長嘆:“我當了一輩子共產黨都被打得半死,魏朝鵬救我這個偽裝成國民黨的人,現在他可能更慘咯。”
幾經奔波,塗勝華終於幫魏朝鵬洗去冤屈,當地政府重新給他家頒發了表彰通報,並舉辦了魏朝鵬見義勇為的表彰大會。
後來,塗勝華得知魏朝鵬的墓地因修路而拆遷,和其後人商議後,將重達200公斤的墓碑運到北京,存放在“塗作潮陳列室”裏供三代人敬仰。
曾經“撒謊”結義金蘭的兄弟,匆匆一別的幾十年後,終於“再見面”了。
塗勝華想,如果父親還活着,也一定會支持自己這樣做。
塗作潮骨子裏是個重感情的特工,他去世後,兒子在他的遺物裏找到一些匯款單據,有他曾經戰友的遺孀,有曾經給他幫助的朋友後人,還有一些不認識的人。
塗勝華也試着去尋找這些陌生的名字,看看父親還藏着什麼他不知道的秘密。
塗作潮沒正經讀過幾年書,常和塗勝華提起的只有一本小學課本,叫《董景安六百字》。
後來塗勝華找到這本書,發現裏面有寫“人有恩於我,不僅謝之,更當報之”。
想必,這句話影響了特工塗作潮的一生。

喜歡看諜戰片,除了驚險刺激,我想更多是這羣人身上還藴藏了人類的聰明和才智。
層層暗影中的特工世界,假假真真,假假真真,存在你看到的世界,也存在你看不到的世界。
猶如冰山之下更有冰山。
而我們看不到的冰面之下,陽光最為稀缺,黑暗從不匱乏。
不管如何探究,有我們知道的故事,也有我們以為自己知道的故事。但更多,是我們永遠無法知曉的秘密。
塗作潮不管是特工還是木匠,在親人眼裏,都只是丈夫和父親。
在他人生的重重暗影下,照進來的絲絲陽光,不僅映射出人性中最極致的黑暗,也照出了人性中最寶貴的良善。
這是他最打動我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