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偽裝者”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07-07 08:52

· 這是第5280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 何菲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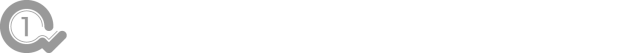
今年看的第一場電影是《無名》,好友、影視製片人顧桑在南昌路的上海科技影城包場。
導演程耳屬於準一線但偏小眾的導演,1999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他低產、好打磨,注重格調,加上畢業作品和《無名》,一共創作了5部電影。

該片講述了抗戰全面爆發後(1938年到1945年期間),在上海汪偽政府的情報部門裏,中共情報人員、日軍特務、汪偽政權特務、中統特務、中共叛變人員等多方勢力斡旋較量的故事。我黨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們通過錯綜複雜盤根錯節的敵後情報系統,建立了更廣泛的統一戰線,直至抗戰勝利前夜。
儘管該片故事的落地性欠佳,構圖、佈景、燈光、音效等卻精美上乘,讓《無名》保有了電影藝術的古典、鄭重、嚴肅與體面和知識分子趣味。
看完《無名》正是黃昏,走到南昌路時我有點恍惚,彷彿又回到20世紀二三四十年代那個波詭雲譎的年代。
南昌路是原法租界“梧桐區”既高雅又市井的地方,是老上海天然的建築博物館,裏、弄、坊、邨、別墅等5個等級的弄堂,在這條短短1600多米的小馬路上匯於一爐。
南昌路在舊上海有着不俗的風雲往昔:科學會堂、大同幼稚園、原民革聯絡處、國民黨原老吳稚暉舊居,林風眠故居、原法國總會俱樂部舊址、有原汪偽內政部長陳羣舊居雲集;南昌路100弄的老漁陽裏2號是1920年陳獨秀到上海後的居住地和工作地,是共產黨成立前後《新青年》的編輯部,是上海紅色文脈的起點。
這裏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始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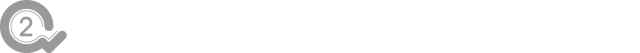
毛主席曾説,“我們要消滅敵人,有兩種戰爭:一種是公開的戰爭,一種是隱蔽的戰爭”。這些年我看過不少諜戰題材影視劇,上海是最重要的場景地。
歷史上,上海也是諜海風雲最頻繁的發生地,其次才是香港,還有一部分在廣州、重慶、南京、哈爾濱、天津、武漢、西安等地。
19世紀末至20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多方勢力盤桓、牽制,合作、爭鬥,是全球政治風雲的小鏡像,是間諜之都,紙醉金迷與鮮血淋漓並存。
鴉片戰爭以後上海開埠,它被切割為華界和租界,還有華洋共管、性質不明的租界越界築路區。它們共同影響着城市的發展,重構着城市空間。
當年公共租界北區以北,是日本盤踞的虹口,租界以西是越界築路、華洋共管的滬西。
“越界築路”指上海公共租界在界外修築道路,並進而事實上取得一定行政管轄權的附屬於租界的“準租界”區域。主要分佈在滬西和滬北,共築馬路40條,其中滬西28條。滬西越界築路最遠的虹橋路西端距離公共租界西部邊界靜安寺附近已有10公里。
據《長寧區志》記載,“越界道路路名除了愚園路、虹橋路外,均以英美總統、將軍、公使、駐滬領事、工部局總董、商人等名命名。”
作為遠東的經濟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商貿條件,政治格局非常複雜。
當時的上海,不僅在中國範圍內特殊,在世界範圍也極為特殊:**“二戰”期間,上海是全世界唯一不需要簽證就能進入的城市。**1933~1941年間,有3萬猶太人為躲避納粹迫害逃到上海,上海成為猶太人的避風港,是難民和間諜聚集、情報和信息集散之地,蘇、美、英、德、日等國情報人員雲集,從各自利益出發從事着各種諜報活動。
舊上海的資源與權利一直處在被各種勢力瓜分掌控中:當地政府、淞滬警備司令部、法租界公董局、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總商會等江浙華人財團、本土幫會,以及日本海軍陸戰隊駐軍、蘇聯的共產國際、國內地方軍閥、國民黨內的反對派、各國使館等外交勢力、韓國的流亡政府……各種錯綜複雜、撲朔迷離、驚心動魄在舊上海呈現出難以替代的神秘。
1937年上海淪陷後,上海的華界民不聊生,租界依舊歌舞昇平。木心曾描寫當時的上海:“蘇聯的大輪船彩旗招展在黃浦江口,好萊塢影片與莫斯科影片同時開映,這邊桃樂賽摩娜巧笑,那邊夏伯陽怒目,國際間諜高手雲集,誰也不放過遠東最急劇的情報漩渦。”
當年上海在物理空間形態上也呈現出豐富的都市景觀羣像,各類複雜的行政機構、報館、出版社、電台、電影公司、洋行、飯店、舞廳、咖啡館、電影院、教堂、武館、煙紙店、文人學者、革命志士、明星富商、各路洋人云集,使得上海的一路一景,都可能是諜海風雲的真實場景地。
那些紛繁複雜的勢力有權力的縫隙,還有法外之地的混亂,有合作,有爭鬥,有制衡,有博弈。
在不同政治勢力的背後,衍生出了無數的情報力量。中統、軍統、中央特科、國民黨復興社、日本特高課、蘇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汪偽76號、日本巖井公館等情報組織在爭鬥角力中暗潮澎湃、風動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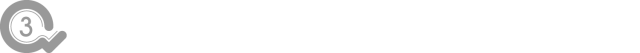
有人總結這些年國產諜戰劇都有個套路:如果發生地在上海,跳舞不是仙樂斯就是百樂門,敵我雙方室內的書櫥後必有暗道,日本特務高官都有穿和服下圍棋的橋段……更重要的,走路必經外白渡橋。
的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上海,虹口日佔區和公共租界之間的重要通道,是蘇州河黃浦江交匯處的外白渡橋。外白渡橋是外灘萬國建築博覽羣的起點,在上海城市發展和構建上海想象過程中,發揮着巨大作用。
它不僅是一座橋,更是一個文化意象,也是當年諜報人員經常出沒的場景地。昔日在解放上海的戰役中,在外白渡橋也曾發生驚心動魄的故事。
與外白渡橋近在咫尺的上海大廈,原名百老匯大廈,如碉堡般矗立在蘇州河畔,曾是上海最高建築,也是俯察一江一河、近賞外灘、陸家嘴的最佳觀景點。因地處蘇州河與黃浦江的交匯處,百老匯大廈在軍事上有着重要地位。
抗戰爆發後,“孤島”時期的百老匯大廈雖地處租界,卻被日軍盤踞。日本特務機構特高課駐地,日本文化特務機構“興亞院”的分支機構都設立於此,汪偽76號特工頭目李士羣也是在百老匯大廈的酒宴上被日軍毒死的。抗戰勝利後,一批美軍在華機構、英美新聞機構都遷居進來。
解放上海戰役時,它是毗鄰外白渡橋的最危險的火力點。上海的最後解放,也是以百老匯大廈回到人民手中為標誌的。
1951年,百老匯大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改名為上海大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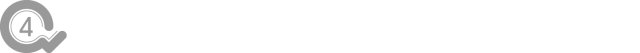
一直覺得虹口的氣息很文學,很諜戰,很左翼,很複雜。勢力盤根錯節,前世今生莫衷一是又一言難盡。丈量過世紀,穿越過狼煙,風華和史詩感永聚不散。
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世紀30年代,我黨在哈爾濱路290號的德式洋房嘉興路巡捕房建立了租界巡捕體系中的第一個中共地下支部。
而原名施高塔路的山陰路,則在二三四十年代的文藝作品中不時出現,是當年中共地下黨人、愛國民主人士、左翼文人、社會活動家、日本僑民居住或時常出沒的所在,不僅有風花雪月,更有波詭雲譎。
交錯陸離的弄堂網絡、結構複雜的民居樣式,也為我黨的地下革命工作提供了天然掩護。
紅磚紅瓦的大陸新村,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新式里弄,短短几十米弄堂,魯迅、茅盾、謝旦如等毗鄰而居。
魯迅先生在大陸新村9號和許廣平及獨子周海嬰度過了人生最後的四年半時光。這套建築面積約230平方米的三層住宅,保留了大先生當年生活時的原貌,雖簡樸無華,卻有着別樣的氛圍感,彷彿能觸到大先生莊嚴憂鬱的氣息和最深的孤獨。
而大陸新村8號則是魯迅紀念館第一任負責人、新中國博物館事業的開拓者謝旦如的故居。這位“紅色小開”為黨的地下工作急公好義,千金散盡,曾開設西門書店和公道書店,前者是共產黨的秘密聯絡點,後者則掩護黨組織活動。
他先後兩次冒生命危險在自己位於徐匯、南市的寓所掩護瞿秋白夫婦,還為保護革命史料以身許國。
四達裏的弄堂阡陌縱橫、宛如迷宮,有着柳暗花明的幽微,這樣的地形特別適合中共地下黨員、左翼作家沙汀,他在描寫複雜而錯綜的場面上有其特殊的才能;恆豐裏是早期新式里弄,結構極為複雜。中共中央黨校1926年就設於弄內90號。1927年中共江蘇省委舊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指揮部聯絡點也在恆豐裏。
花園裏2號,還曾居住過紅色間諜、日本進步記者尾崎秀實。他是內山完造的好友,派駐上海3年多,結識了許多中國左翼文化人士,撰寫多部政論性著作。
魯迅《阿Q正傳》最早的日文譯本,由他撰寫序言《論中國左翼文化戰線的現狀》。
那些年,中共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們與各方勢力巧妙周旋、殊死較量,處處有漩渦暗礁,時時險象環生。1927年,由周恩來同志親手締造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較為成熟的情報保衞機構——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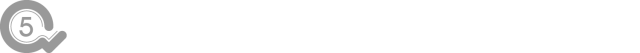
這支神秘的隊伍在隱蔽戰線的對敵鬥爭中縱橫捭闔,立下了彪炳史冊的不朽功勳,鍛造成為屹立於白色恐怖中紅色戰鬥堡壘。那些親歷中央特科戰鬥洗禮的革命戰士,在此後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成立後,大多成長為黨的隱蔽戰線、文化戰線和統一戰線的領導、骨幹。
其中的傑出人物是“紅色特工”潘漢年。他的舊居位於原法租界淮海中路1350弄愉園5號,從抗戰後期至1947年,潘漢年曾在此居住。這幢毫不起眼的三層小樓,在風雨如晦的歲月中,是中共地下黨的秘密站點之一,是潘漢年領導上海地下黨開展地下鬥爭和統戰工作的中共地下機關。
而同在“梧桐區”的嘉善路117弄24號,是中央特科成員錢壯飛的在滬舊居。作為中共隱蔽戰線的“龍潭三傑”之一,他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最高核心層,為中共獲取重要的密碼本,在顧順章叛變後及時發出警報,為保衞黨中央的安全作出重大貢獻。
而那些更不起眼的照相館、藥房、書店、理髮店、診所等,也常常是我黨的秘密聯絡點。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機關舊址(永樂邨)設立於江蘇路389弄21號。這處建於1930年、假四層聯列式住宅,曾是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派駐在上海的秘密領導機關。它在刀尖上行走,有力配合着解放戰爭正面戰場的較量。情報人員互相不知彼此身份,直至新中國成立後,脱去西裝旗袍,換上軍裝的那一刻……
如今,那些看似普通的住宅,依然在“梧桐區”老弄堂的一隅,見證上海真正成為領航中國、通達世界的“魔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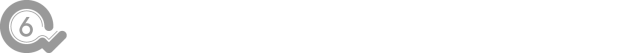
咖啡館在中共黨史中也有着特殊的一筆,因為多開在租界,能為革命工作起到特殊掩護作用。
魯迅日記裏曾多次出現類似“午後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午後同前田寅治及內山君至奧斯台黎飲咖啡”的記錄。
當年魯迅與左聯成員、地下黨代表秘密接頭的地點,經常設在虹口的公啡咖啡館二樓包間,1929年左聯第一次籌備會就在此舉行。而舊日霞飛路(今淮海路)上的DD’S(據稱為一家俄僑開設的咖啡館)也是郁達夫、徐志摩、徐悲鴻等社會名流經常出沒之處,地下黨人常在此傳遞情報。
因為價格不菲,當時上海只有文人墨客、中產及以上人士才能時常出入咖啡館。**1937年上海淪陷,但****孤島時期的上海,咖啡館亦出現畸形的繁榮。**俄僑和猶太人最佳的謀生手段就是經營咖啡館。咖啡館也成為各方諜報人員傳遞情報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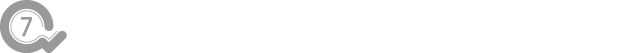
好的諜戰,一定與信仰有關。曾活躍於上海文化界與政商界的中共黨史上唯一五重間諜(身兼中共、中統、軍統、日偽、青紅幫五重身份)的袁殊、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揹負漢奸罵名深入魔窟的美女作家關露、南湖紅船上的王會悟、“永不消逝的電波”李白,“按住蔣介石脈搏”的沈安娜、促成父親傅作義起義的傅冬菊等……
還有更多的無名英雄,在特殊戰線上戰鬥不息,閃耀着“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理想主義光芒。
隱蔽戰線是個看不見硝煙的戰場。看那些隱姓埋名、英勇無畏戰鬥在敵人心臟的無名英雄的傳奇軼事時,我總會有“身許家國難許卿,寸寸皆是意難平”的感慨,他們的故事與情感,沒有明火,沒有聲息,卻落子無悔。
功勳比天,名字與過往,卻隱入塵煙。

作者:專欄作家,中國作協會員,上海市作協會員,國家二級音樂編輯。SMG知聯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