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家丨齊澤克論左翼必須擁抱法律和秩序_風聞
听桥-07-16 06:33

2023年6月30日,法國東南部城市裏昂,警察施放催淚瓦斯後,抗議人羣四散奔逃。圖源:Jeff Pachoud/AFP via Getty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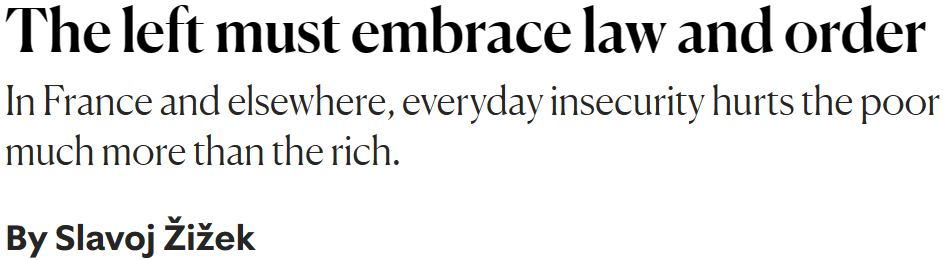
原文截圖
左翼必須擁抱法律和秩序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
在這個愈發燥熱的夏天,兩件事抓到了公眾的眼球: 俄羅斯的流產兵變和法國的暴力抗議。儘管媒體已詳細報道了這兩件事,但其中一個共同特點卻被無視了。
6月27日,警察在巴黎的楠泰爾(Nanterre)郊區射殺了一位名叫納赫勒(Nahel)的17歲男孩,之後,劫掠行為和縱火攻擊在法國全境蔓延。在全國城市裏,暴徒設置路障,點燃火堆,向警方投放煙花,警方則使用催淚瓦斯、高壓水槍和眩暈彈還以顏色。
當警方開始充當獨立代理人,威脅説,除非馬克龍總統解決危機,不然他們就要造反時,事情變得甚至更不妙了。警方發佈的聲明無異於昭示,國家權力大廈的外表出現了一道裂縫:警方內部的強硬派響應騷亂時,威脅要對自己的國家採取行動。
可以預見,左派的敍事是:警方有種族偏見;法國的平等(égalité )是虛構的;年輕移民之所以造反,是因為他們沒有未來;這場危機的解決之道不是派出更多警察鎮壓,而是從根本上改造法國社會。憤怒情緒已積聚多年,納赫勒之死是最新一次引爆,將那些情緒公開化了。暴力抗議是對問題的響應,而非問題本身。
這一敍事揭示了一些真相。2005年,兩名少年在被警察追捕時觸電身亡,隨後,抗議活動爆發:那一刻,釐定了法國青年移民生活的一整套偏見和排斥大白於天下。但,徹底改造社會,以解決身份、經濟排斥和殖民造成的不公這樣一些歷史性難題,正是一個製造難題的方案。在看不到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時,它假定結果是進步性的。
例如,地方的巴士對運送來自巴黎邊緣地帶、低收入郊區的工人極其要緊,但抗議者以之作為攻擊目標,這表明了兩件事: 騷亂毀掉了維持普通人生計的基礎設施;那些破壞活動的受害者是窮人,而非富人。
假如用解放的願景加以維繫,公眾的抗議和暴動就可能發揮積極作用:例如,2013至2014年的烏克蘭廣場起義,以及在伊朗,因庫爾德女性拒絕穿戴那種矇住全身、只留眼睛的長袍而引發的持續抗議。有時,甚至威脅要採取暴力行動,也是政治解決的必要手段。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上台以及小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美國民權抗議,自由派評論人士推崇的這兩大歷史性勝利之所以能成為現實,是因為有非國大的激進一翼和更激進的美國黑人採取暴力行動的可能作為奧援。因為存在這些威脅,結束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和廢除美國種族隔離的談判取得了成功。
但那並非今天法國的情況,對這個世界的受苦受難者來講,暴力反抗不大可能終結於任何形式的進步性和解方案。假如法律和秩序得不到迅速恢復,最終結果可能是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當選新總統。反移民的民族主義者正在瑞典、挪威和意大利掌權,為什麼不在法國呢?馬克龍給自己準備的人設,是一個沒有堅定政治立場的技術官僚。可一度被視為優勢的某種立場,現在看來卻是致命的弱點。
在俄羅斯,人們很難忽視葉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進軍莫斯科一事的滑稽本質。在克里姆林宮向他提出條件後的36小時內,事情就結束了。普里戈任避免了被送上法庭,但被迫從烏克蘭撤出他的僱傭軍,並前往白俄羅斯。我們沒有充分獲知究竟發生了什麼: 他的進軍行動,是要佔領莫斯科的全面進攻,還是如普里戈任自己暗示的那樣,只是一個空洞的威脅,一個不應實現的姿態?整個事件也可能是商業談判的殘酷形式:企圖阻止一部法律的通過,該法律規定,像瓦格納集團這樣的非正規部隊必須接受正規武裝部隊指揮。
無論那是一場未遂政變,還是一場通過兵變進行的商業談判,事情都佐證了這樣一個現實: 俄羅斯正變成一個失敗國家,不得不將失控的軍事幫派當成一場骯髒交易中的夥伴。
法國和俄羅斯的事件是歐洲邁向動盪、危機和失序趨勢的一部分。今天,失敗國家不只在從索馬里到巴基斯坦再到南非的全球南方。假如我們衡量一個失敗國家是基於國家權力的崩潰,以及意識形態內戰氣氛的升温、僵持不下的羣眾集會和公共空間的愈發不安,那麼俄羅斯、法國、英國甚至美國理當收穫差不多的理解。
2022年6月19日,德克薩斯州共和黨人批准的一些法案宣稱喬·拜登總統“並非合法當選”,並指責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John Cornyn)參與了兩黨關於槍支管制的談判。他們還在一個宣稱同性戀是“一種不正常的生活方式選擇”並呼籲德克薩斯州的學童“瞭解未出生孩子的秉性” 的平台上投了票。
第一項法案即宣佈拜登的當選無效,是美國邁向“冷”內戰的明確步驟: 政治秩序的非法化。在法國,談論即將到來的內戰在極右翼那裏是合乎禮數的必要之舉(de rigueur)。6月30日,能言善辯的極右翼政界人士埃裏克·澤穆爾(Éric Zemmour)在法國電台發表意見時,將騷亂描述為“一場內戰和種族戰爭的開端”。
在這樣的一般情形下,左翼必須扛下法律和秩序的口號,視如己出。新近歷史的最令人沮喪的事實之一是,2021年1月6日,狂暴的革命羣眾侵入權力寶座的唯一案例發生了,當日,唐納德·特朗普的支持者衝擊了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大廈。他們認為前一年的總統選舉是非法的,是由企業精英組織實施的盜竊。左翼自由派的回應混雜了迷戀和恐懼。我的一些朋友哭着説: “我們應該做這樣的事情!”。見證“普通人”侵入國家主權之巔,製造一場暫時中止公共生活規則的嘉年華時,他們當中,有人羨慕,也有人譴責。
通過發動大眾攻擊權力寶座,民粹主義右翼由此竊取了左翼對現行體制的抵制嗎?我們現在唯一的選擇,要麼是腐敗精英控制的議會選舉,要麼是極右翼控制的起義?難怪民粹主義右翼思想家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宣稱自己是“21世紀的列寧主義者”: “我是列寧主義者。列寧……想摧毀這個國家,這也是我的目標。我想把一切都搞垮,摧毀今天的所有建制力量。”儘管民粹主義右翼對1月6日發生的事欣喜若狂,但自由派的左翼卻表現得像是優雅的舊式保守派,要求國民警衞隊鎮壓叛亂。
在這一古怪局面的源頭,我們發現了無政府狀態和野蠻威權主義的獨一無二的混合。我們正進入一個叛亂和暴民統治,和前所未見的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時代。這就是哲學家凱瑟琳·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所稱的“野蠻的垂直性和難以駕馭的水平性的結合,這種結合既愚蠢、醜惡,又前所未有”。而且,歷經多年的緊縮政策,國家的“社會職能”遭到侵蝕,它現在只能“通過使用暴力”表現自身。
這就是何以不能只將國家貶低為支配工具至關重要的理據所在。在發生自然災害、公共衞生災難時和社會動盪時期,進步力量必須竭力奪取並利用國家權力,不只要在緊急情況下平息人們的恐懼,還要打擊那些恐懼,那些人為製造出來,控制不同人羣的種族主義的、仇外的、性別歧視的、反進步取向的恐懼。
左翼不應畏懼承擔更多確保普通民眾安全的任務: 有清楚跡象顯示,年輕幫派的行為舉止愈發敗壞,他們威脅到從車站到購物中心的公共空間。提到這樣的敗壞往往被不屑地視作反動,因為人們堅持認為,我們必須審視失業和制度性種族主義等現象的“更深層次的社會根源”。
但假如左翼無視公共安全,他們就是在向敵人讓出一個滿是憤懣的重要領域,在一個無政府的時代,這樣的憤懣會將民眾推向右翼。日常生活的不安全感對窮人的傷害,遠遠大於那些平靜地生活在封閉社區中的富人。
(作者是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本文原題“The left must embrace law and order”,見於英國《新政治家》週刊,2023年7月5日一期,7月4日上線。正文中的斜體字和超鏈接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不保證正文理解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