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遊民:拿着一線城市的工資,我在老家嘎嘎亂殺_風聞
星海情报局-星海情报局官方账号-关注“中国制造”的星辰大海08-11 11:30

“靠,又TM回來了!”
華北夏夜的燥熱令人心煩意亂,看着北京西站南廣場擁擠的人流和地下通道里昏暗的燈光,來北京開會的我忍不住一句“國粹”脱口而出。不論是進站安檢還是出站排隊,擁擠的人流總會讓人感到一股莫名邪火。

擁擠往往意味着無序與混亂,意味着“僧多粥少”的資源困境,意味着為了獲得和常態下相同的服務體驗,你不得不額外付出時間與金錢。
不巧的是,北京恰恰就是一個擁擠的城市——2100餘萬人生活在1.65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上——人口密度甚至已經超過了我們印象裏地狹人稠的東京。從政府官員到學者專家,大家都承認了一個現實:北京,正想方設法破解過度擁擠和公共資源緊張的難題。
“資源困境”這個抽象的概括最後會具像化地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後在每一個不經意的瞬間給你一巴掌,包括但不限於:打車軟件上北京西站那200多人的排隊序列,知春路地鐵站裏漫長的換乘通道,百子灣一個合租單間3000元/月的租金,還有當年死活都預約不到的朝陽醫院的專家號……
結束三年的“北漂”生活回到老家生活幾個月後,我忽然發現,我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勸説自己努力去適應北京的生活了。
平心而論,這樣的表述對北京來説很不公平,因為這些問題絕非是“北京特色”。

任何一個人口超越承載能力的城市,最終都會面臨類似的問題:北京西站固然打車難,難道虹橋站就很容易嗎?朝陽醫院的專家號固然一票難求,難道華山醫院和瑞金醫院的專家號就隨到隨取麼?
在我們這個發展中國家,我們註定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面對、經受並最終解決資源總量不足和資源分佈不平衡的問題——大城市同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大量的資源,結果導致大城市遇到了人口爆炸,小城市苦悶於資源短缺。
把一部分資源和人口從一線城市裏分流出去,已經成為了一種必然趨勢。
而這種必然,也催生了一個新的羣體——“拿北京工資,在老家生活”的遠程工作者,他們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正在過着“數字遊民”的生活。
對他們來説,工作不再是一個約束自己自由的枷鎖,反而成為了追求自由的階梯。前不久還是“打工人”的他們,突然拿着過萬的工資,在小城市裏過上了“財務自由”的生活。
這樣一個羣體的壯大,讓我們看到了一種解決中國當前諸多社會問題的新可能。


“拿北京工資,在老家生活”
是一種什麼體驗?
“領導,有件事情想和您聊一下……”,時間倒回到今年3月底的一個早晨,在醖釀許久之後,我決定和老闆提出一個“十分離譜但卻頗具可操作性”的計劃:我要申請回老家進行“遠程辦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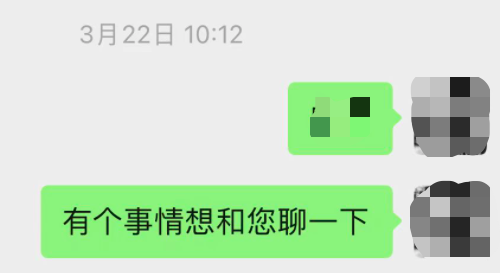
簡單來説就是,
我想“拿着北京的工資,在老家生活”。
但令我沒想到的卻是,這個有點瘋狂的計劃,老闆卻非常乾脆地就批准了——或許是老闆年輕的時候曾經當過報社記者的緣故,而一個記者,是不應該天天坐在辦公室裏朝九晚五的。
總之,在經過並不複雜的工作交接手續和談話後。5月3日,我正式結束了三年的“北漂”生活,回到了武漢老家。
踏出車站,解脱的感覺立竿見影。這種解脱的“鬆弛感”源自於資源的充足:人雖然也不少,但再也不必計算時間,也再不必心中暗懷爭搶之意,因為你知道你不必爭分奪秒、不必暗自盤算,也總有一份屬於你的東西在那裏等着你。

很多文章就是我在老家這書桌上寫的
第一個給我這種鬆弛感的是武漢站的出租車——武漢站外的出租車永遠都是“車等人”的狀態——上百輛出租車的洪流緩緩流動、等待進場,而排隊上車的旅客卻只有十幾個人。
住在屬於我自己的、二環內、地鐵口100平米的家裏,早上九點睡到自然醒,起牀洗漱後去小區外面的早點攤子上來一碗鮮香撲鼻的牛肉粉,慢悠悠晃回來的時候再去取個快遞,然後回家,躺在沙發上,吹着空調,刷幾個短視頻,靜靜等待十點鐘開始上班。

離開北京,意味着遠離公司。
遠離公司,意味着不用坐班。
不用坐班,意味着無需通勤。
無需通勤,意味着時間自由。
沒有通勤,沒有打卡,不需要坐地鐵,不需要趕班車,**通勤距離只有“牀-洗手間-書桌”這短短的幾米。**別的不説,光是這套100平米的房子,如果在北上廣深,哪怕是家裏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賣掉怕是也買不起。但在武漢、鄭州、西安、成都等城市,一般人努努力還是可以搞定首付的。
之前的某篇文章裏,我曾經提到過我2021年去河南安陽拜訪朋友時候的經歷:兩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一頓早飯吃了兩碗扁粉菜外加幾盤子餅和兩碗豆漿,最後結賬時候發現才花了26塊錢。其實別説安陽這種四線城市了,就算是在武漢這種常年頂着“高消費、低收入”標籤的省會城市,20元也足夠安排一頓堪稱豪華的早飯。

這一桌,只要26元,對於我工作的北京城區來説是不可能的
而在那篇文章裏我沒有説的是:由於我們倆好多年都沒見面了,所以晚上去酒吧喝了半宿。六杯雞尾酒和N杯可樂下肚之後,已經到了打烊的時間。
當服務員拿着票據向我們走來的時候,看着滿桌的酒杯和飲料,我心裏盤算的內容頗為“不體面”:今天豁出去了,1000塊錢以內都能接受。但當服務員將小票遞給我之後,我差點笑出聲:一大桌子雞尾酒、飲料、零食,最後才花了不到200塊錢。
當然你可以質疑這雞尾酒是否正宗,但我想的卻是——別管什麼正不正宗了,難道高價就一定正宗?這點錢放在任何一線城市同類型的酒吧裏,撐死也最多買兩杯。但在四線小城市,這足夠你喝到打烊了。
比低物價水平更重要的是時間和空間的自由。
“你要不要來趟上海?”,五月的某日,多年未見的好友Eelly給我發了條微信,“你還欠我一頓火鍋。”
如果我仍舊在北京的公司裏坐班,那麼面對朋友的邀請,我大概率仍然會甩出不少於三個不鹹不淡的推脱理由——忙工作/要開會/難請假……但當我在武漢家中看到這條消息的時候,我的反應卻是打開12306,立刻訂了一張去上海的高鐵票,順手又訂了從上海去揚州,從揚州去合肥的高鐵票——因為這些地方,也有我不少多年沒見的朋友。

我不知道如果我依舊留在北京,是否還會有心思去見這些朋友——坐班制對人的約束,不僅是制度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儘管如今許多企業已經實行了“彈性工作制”,但再怎麼有彈性也是坐班,員工總還是要走出家門到公司去的,而晚一些到公司也意味着晚一些回家。更何況各家互聯網大廠通常都會提供“車補”,這種福利在執行中不可避免地會演化成了對深夜加班的鼓勵。
在互聯網企業扎堆的海淀西二旗,這裏的晚高峯不是尋常認知裏的晚上六七點,而是晚上九點到凌晨一點。每到此時,司機師傅們便會從北京各處蜂擁而至,後廠村和西北旺每天晚上都要迎來一次“更晚的高峯”。
但在“遠程工作”的語境下,“時間約束”和“地點約束”開始變得意義索然。
但正如那句老話所説“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免費的)”——“數字遊民”的生活固然給打工人帶來了空前的自由,但同時也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個世界是很公平的——你享受了什麼福利,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以及責任背後的壓力,反之亦然。
當我在享受擊碎坐班制的自由時,一種壓力也如影隨形地鎖定了我。
“等下兩點鐘我們開個會討論一下最近的工作進度”,老闆在工作羣裏發了這樣一條消息。
“不好意思,你們先聊,等下我要開個會”我略帶歉意地向一起吃飯的朋友們説道,然後在飯店裏找了個安靜的角落坐下。
在傳統模式下,辦公室是幹活兒的地方,家裏是休息的地方,外面是玩的地方。哪怕是996,一天之中也總有那麼幾個小時是屬於自己的。但對遠程工作來説,時間開始變得模糊了。你下午兩點便完成了今天的工作任務並不一定意味着兩點之後的時間就是完全聽你安排——因為或許在五六點鐘,一條新的任務就會把你拉到辦公桌前。
自由了,但沒有完全自由。
比“選擇性自由”更尷尬的問題則是溝通障礙——遠程辦公之中,對方能否秒回消息就成了關鍵。在辦公室裏,站起來看一眼就能知道有沒有溝通的必要。但在遠程辦公的情況下,我們卻會盯着對話框,看看對方有沒有回消息。
人總是不喜歡等待的,尤其是工作中的溝通往往是突如其來。這也就導致你失聯的每一分鐘,對於你的同事而言都約等於一個小時。我曾經極度焦躁地抱着手機等一個同事的回覆,但事後心平氣和再去看,也不過短短十五分鐘而已。
於是,為了及時回應,領導、同事、工作羣開始強勢入駐微信置頂,淘寶購物車裏也多了幾款輕便的通勤揹包——為了兼顧自由和工作,走到哪裏都要揹着電腦。
更值得注意的是,回到家鄉儘管節約了不少的房租成本,但問題是,外出活動的次數也大幅增加了——最後算總賬,每個月花出去的錢竟然比在北京的時候還多一些。
真正的問題,在於那些遠程辦公以及背後切換城市帶來的“不可逆”損失——遠程辦公最致命的短板是讓人們跳槽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對員工來説,遠程辦公儘管能賦予時間、地點的自由,但卻極大阻礙了“辭職和換工作”的自由。小城市沒有那麼多心儀的崗位,即便有也給不到太高的工資,一旦辭職或是“被優化”,人們極大概率需要再次返回北上廣深。
權衡各方面的利弊後,總體來説,遠程辦公這種工作方式是可以有效提高員工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的。甚至從個人體驗來説,全面遠程辦公對於員工個人幸福感的提高堪稱“藥到病除、立竿見影”。但比較遺憾的是,並非是所有行業都適合如此——甚至大多數行業都不適合如此。

同樣根據《中國遠程居家辦公發展報告》,IT/通信/電子/互聯網行業是遠程辦公崗位的主要貢獻者,2019年便已經貢獻了44%的遠程崗位,而第二位的商業服務行業貢獻率僅為16%。
事實上,能夠適應遠程辦公的崗位大多都有“單體化”的特性——即一個人就能獨立完成工作——在線客服、銷售、主播、網課教師、設計師、程序員、編輯……這些並不需要親身實地就可以創造價值的崗位都屬於此類。
而絕大多數的製造業從業者和服務業從業者,除了少量設計和運維崗可以遠程外,大多還是需要面對面到現場去的。

還有誰會因為遠程工作者受益?
在離開北京,回到老家後,我曾經認真想過一個問題:“武漢會是最後一站麼?”——在中國大地上,多得是地方比武漢的生活成本更低,我為什麼不能更進一步地去那些地方呢?那樣豈不是更爽?
只是現實很快就把我拉了回來,我發現我根本去不了別的地方。
一是因為家庭,我老婆辛辛苦苦做題十幾年才從小縣城奮鬥到了武漢安家落户,豈能允許我開“歷史的倒車”再把她送回去?二是因為在當下的時間節點上,論及生活品質,“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的差距”比“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的差距”要大得多。
當下來看,一線太昂貴,四線太無聊,綜合一看,還是二線最好。像我這樣的遠程工作的人,其實內心裏追求的還是提高生活品質的性價比。
因此我們可以做一個判斷:哪裏能提高生活品質的性價比,哪裏就能吸引越多遠程工作的數字遊民。
這個判斷的依據是:根據中國近些年人口流動的趨勢,一線城市和三四線小城都是人口流出的“重災區”,二線城市成為了人口流入的“紅利區”——其中最耀眼的,不是舒緩安逸的成都,不是精緻美麗的杭州,而是GDP剛剛過萬億的湖南長沙。長沙連續15年蟬聯“中國最有幸福感的城市”,今年更是成為了“人口增量第一城”(常住人口增加了18.13萬),背後的密碼,就是長沙的“煙火氣”——這裏非常適合消費,花小錢,享大福,生活極具性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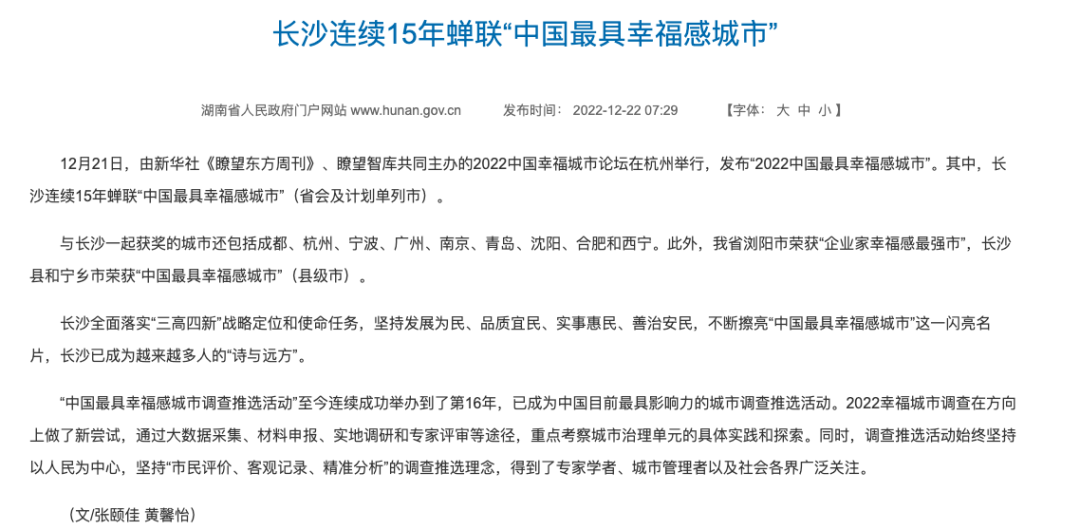
長沙是“中國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當我們説某個地方有“煙火氣”的時候,我們説的其實是這個地方房價低,這個地方有深入毛細血管的商業終端,這個地方有完整全面的連鎖品牌佈局,這個地方有完善便利的交通基礎設施,以及最重要的,這個地方整體消費水平不能高。
北京上海的平均月薪都在18000元以上,即便因遠程辦公而降薪,大約也能有15000元/月。這個收入拿到四線城市,大家都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短期來看,最先吃到數字遊民紅利的,可能是房地產行業和民宿行業。
“身懷利器,殺心自起”,拿着一線收入的數字遊民們到了小城市豈能還安於合租?百子灣一間13平米的合租卧室就要3000元/月,只能容下一張牀和一個衣櫃;安陽134平米三室兩廳兩衞整租也只要1500元,大到你可以開party……不論是租是買,這價格差異哪個在北上廣深捲過的人看了不迷糊?

實際上,在素以浪漫吸引文青的雲南“大理福尼亞”,民宿從業者已經賺到第一波“數字遊民紅利”了——大理古城的民宿長租報價已經達到了3000元/月,當地數字遊民主題社區的價格稍稍便宜,但也已經高到了2600元/月——這是個遠高於當地平均整租價格的數字,甚至已經在逼近北上廣深,但仍然有人趨之若鶩。
國外的情況也差不多,只是數字上比國內更觸目驚心——在南美哥倫比亞的麥德林,由於氣候宜人,這裏聚集了大量的美國“數字遊民”。在人均GDP僅有300美元的哥倫比亞,當地合租卧室價格已經漲到了1300美元/月。
中國有很多風景秀美的小城市,如果你恰好在這些地方有間可供出租的房子,不妨試試推銷給那些數字遊民們。
不過,我並不看好這些和西方類似的、高濃度的“數字遊民社區”或着“數字遊民聚集地”——首先是性價比並不高,光這一點就已經刨了“數字遊民”的根。其次是,到一個更陌生的地方,和一羣更陌生的人在一起工作,這和入職一個新公司有什麼區別?這還不如回北京和親愛的老同事們聊天打屁來的開心。
更何況大量高薪數字遊民的聚集勢必提升當地消費水平,只怕時間長了,當地人對於這些突然拉高他們成本的外來者也會充滿敵意。

説到底,佔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還是“日子人”,如果家鄉發展的好,我們還是更願意留在本鄉本土的。所以,我的判斷是:長期來看,更適合中國寶寶體質、更可持續的“遠程工作”,反而更應該出現在普通的、熟悉的、平凡的地方,形式上也不是歐美那種到陌生地方工作或者當自由職業者,而是受僱於某家企業,只是進行遠程工作。
中國未來更長期的“遠程工作紅利”,獲益者應當是三四線城市連鎖商業和深入毛細血管的商業終端而不是房地產行業——因為高薪遠程工作者的迴流,會誘發乃至引爆三四線城市的消費升級。
不知道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朋友們有沒有看過三四線城市的小紅書和大眾點評,實際上三四線城市的朋友們也有自己的網紅打卡地。安陽比較有歷史的“倉巷街”老街,在當地網紅的眼裏就是安陽版的“南鑼鼓巷”——雖然南鑼鼓巷在北京已經屬於低端商圈,但並不妨礙三四線城市追隨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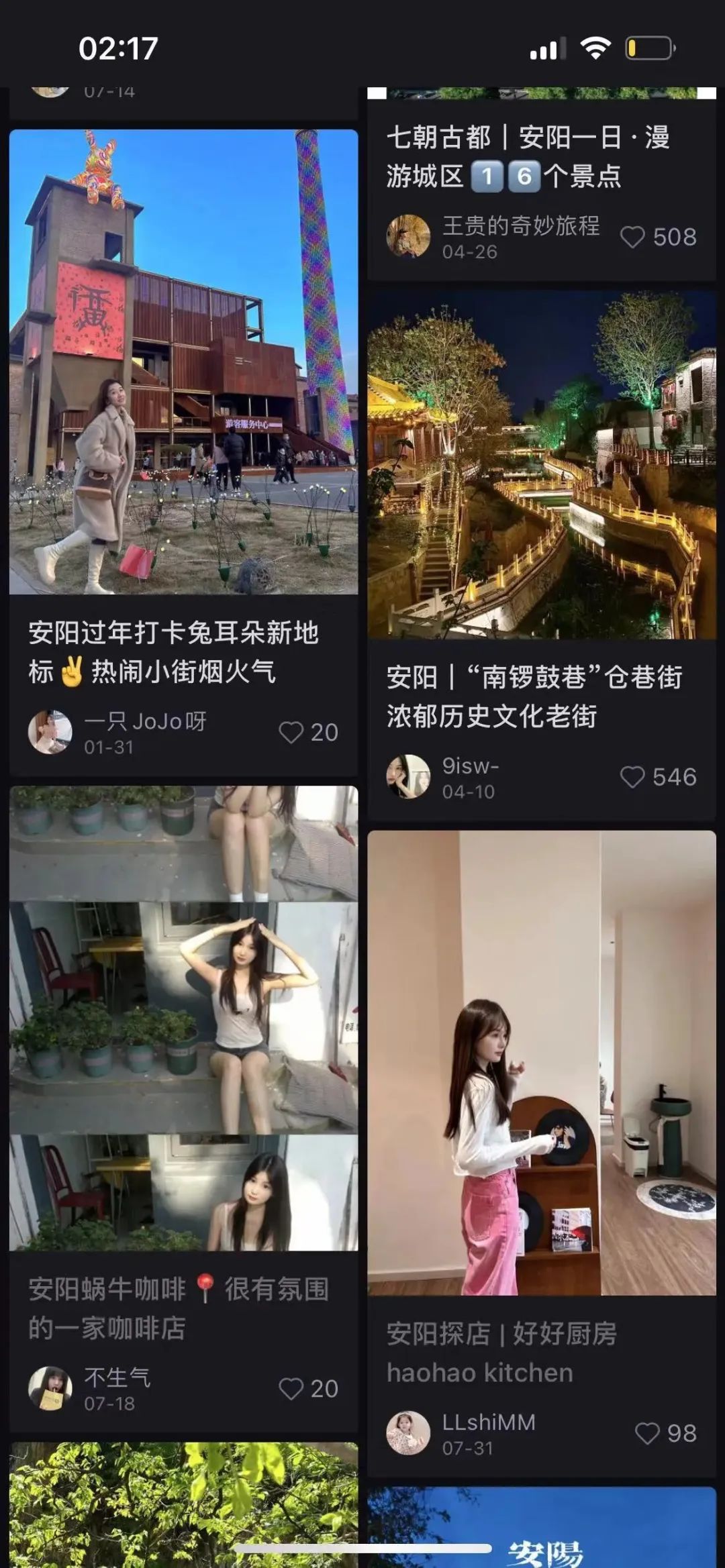
僅從這種模仿行為來看,也能看出三四線居民迫切的消費升級需要。更何況很多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朋友可能沒見過三四線城市的一些老攤子——對我而言,最觸目驚心的一幕莫過於我曾經親眼看到過一個老太太在路邊擺攤,賣的東西卻都是一些早已發黃發黴卻從未開封、年齡可能比某些00後都大的老產品。

三四線城市因為沒有那麼多那麼大的產業,所以收入沒有那麼高,品牌們也不怎麼樂意來,但這不代表三四線城市的老百姓就不需要咖啡館、酒吧、夜店、茶社、西餐廳之類的升級消費場所——雖然這些都是小商户,雖然和大城市的同行比起來他們的模仿略顯拙劣,但它們就像胡椒麪一樣能瞬間拉高一個城市的煙火氣指數。

在家裏寫累了就去外面喝喝茶
在未來的某天,當拿着過萬薪資的遠程工作者開始成建制迴流的時候,這些商户們起飛的時候就到了。還是那句話:拿着北京15000元的月薪回到人均工資4000的老家,那還不是嘎嘎亂殺?杭州的房東聽説阿里巴巴漲薪都知道要提高房租,老家的商户們自然也會“聞絃歌而知雅意”。
實際上,雖然當前還沒有成建制的“遠程工作返鄉潮”,但隨着人口開始逐漸從一線城市迴流,隨着人口結構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縣區合併,連鎖商業品牌的下沉如今已經非常顯著。
連鎖商業領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認為“不需要咖啡”的縣城,星巴克和瑞幸正在激烈對壘,喜茶也不甘示弱,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裏就在全國三四五線城市裏佈局了278家門店。與之同步的,則是優衣庫、迪卡儂、永旺、宜家等等我們熟悉的連鎖商業的下沉——優衣庫表示每年會開80-100家門店,一半以上會在三四線城市;迪卡儂也説要向三四線城市進軍;永旺説自己未來的方向是渠道下沉和主題化;宜家也號稱投資100億搞下沉。
下沉市場,其實已經一片熱土。
當老家縣城和省會一樣擁有這些連鎖商業的時候,當遠程工作的技術、制度條件越發成熟的時候,當我們的高鐵列車已經公交化的時候,人們一定會思考:我們留在大城市的意義是什麼?
某種意義上來説,遠程工作者和家鄉小城是相互作用的,越多高薪的遠程工作者們回家,家鄉才會有越多資金迴流和發展機會,才會被更多的企業所留意到。最可怕的局面,莫過於陷入了死循環——高薪的遠程工作者們看不起自己的家鄉,導致老家小城一片凋敝,消費升級遲遲不來,大家看了,越發堅定了自己跑路的決心。
如果都這樣,那這遊戲可就沒法玩兒了。

離開一線城市,企業的“得與失”
“座標成都,年薪幾十萬,工作三年以上公司送你一台汽車”。
這白日夢一樣的offer不是“霸道總裁”小説裏的虛構,而是我的朋友L君對員工的承諾。
L君的公司差不多二三十人的規模,前段時間公司整體搬到成都去了,“一共只流失了兩個人,還是兩個在生小孩的孕婦,大部分人都願意跟着公司一起搬到成都去。”L君得意的跟我説道。他在成都給核心團隊每人開幾十萬的年薪,這在成都算很高收入了,別人根本挖不動他的人,同時在成都幹三年以上的老員工,每人他還給發一輛車,搬到成都去後整個團隊的幸福感指數提升了很多。
L君向我透露了選址當中的一些門道,他説當時選址的時候看了不下十幾個城市,最後選定了成都,一開始我很是納悶,“你又不是成都人,你跑成都去幹什麼?”,他説首先選城市不能太小,三線以下的城市基本上你就招不到什麼好的人了,本地沒有什麼像樣的高校,外地的優秀人才也不愛來。像成都、武漢、西安這個量級的城市剛剛好,人才選擇多,同時該有多東西都有,文化生活也很豐富,比如年輕人愛看個演唱會或者足球比賽,成都基本都有,而你要是跑三四線城市去,生活還是差很多。成都房價一兩萬塊錢,公司員工要不了幾年都可以買得起房子了,穩定程度大大提升。
“穩定人心”這件事對企業來説意義非凡,尤其是對小公司來説,誰也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培養的熟練人才被競爭對手挖過去。
因此,對企業來説,“遠程辦公提高跳槽成本”這件事其實頗有價值——因為在北上廣深杭這些聚集了大量頭部企業的城市來説,人們跳槽的成本很低,大家都聚在同一座城市,甚至集中在同一個街區,對跳槽者來説,改換門庭不過就是換一個地鐵站下車而已,但工資卻能漲不少,這何樂而不為?
我認識的一個新媒體公司老闆(簡稱Z君)前段時間把某個核心團隊從上海搬到了天津,如今他在天津已經僱傭了二三十人,在談到為什麼選擇天津時Z君指出,“天津本地人卷的,都跑到北京去了,留在天津的,都是自動篩過一道的,沒有那麼卷,在天津本地安家落户,可以長期安心工作。”
之前Z君在上海的時候,他的員工穩定性很差,經常有其它公司開出翻倍的薪水來挖他們的人,在生活成本如此之高的上海,人根本不經挖,辛辛苦苦培養了好久的人才,就這樣流失了,非常可惜。如今核心團隊搬到天津後,他的團隊穩定性很好。他給團隊平均開一兩萬塊錢的月薪,這點錢在北京上海競爭力很一般,但是在天津就有相當的吸引力了,他們不喜歡招那種頂級名校畢業的,也不喜歡招那些博士和碩士,而是注重實用。
這些年,不管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很流行在二三線城市設點,把一部分員工和業務放過去,這裏面既有整個公司搬過去的,也有把某些獨立部門和業務放過去的,甚至還有一些員工分散在各地辦公的案例。

以華為為例,華為現在在深圳、上海、北京、武漢、南京、成都、東莞、西安、杭州、蘇州等城市都設有研發中心。華為是分佈式辦公的典型企業。
騰訊在深圳、廣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也都有規模不小的研發和運營團隊,著名的王者榮耀是在騰訊成都基地研發出來的,微信是在騰訊廣州基地研發出來的。
分佈式辦公的好處是可以充分利用各地的人才資源。對於華為和騰訊這樣體量的公司來説,一個地區的人才資源是遠遠不能滿足它的需求的,以華為為例,它的研發人員超過10萬人,深圳一地的人才供給遠遠不能滿足這麼龐大的需求,而在各個主要中心城市成立研發中心後,華為就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的高校和同行等資源,就近吸引人才,形成一個個很強的研發中心。同時在二三線城市建立研發中心,也大大降低了成本。
而廣大中小企業也有很多人開始嘗試分佈式辦公。我們以虎嗅網為例,這家總部位於北京的公司的員工總數在一兩百人的規模,它有一個核心的部門的負責人平時在廣東惠州工作,而這個部門的員工則分散在五六個城市,他們並不需要都待在北京。
只不過,風險也是對等的。你固然消除了核心員工跑路的風險,你固然降低了企業的運營成本,但你也把自己置身於一種更大的不確定性之中。
2021年10月4日,Facebook遭遇了一次時間長達6小時的崩潰——35億用户無法登錄網站,關聯於Facebook的各種應用如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等等都陷入了癱瘓狀態——而這起災難的源頭就在於遠程工作,遠程辦公作為疫情下的應急選擇,造成了維修人員無法快速到場的窘境,bug的時間延長後,大量關聯於Facebook而生存勞動的個人、企業乃至政府機構工作陷入停滯。
在遠程辦公的環境下,如果微信、釘釘、飛書……這些互聯網基礎設施如果出現故障了該怎麼辦呢?
而更深層次的風險,則在於遠程辦公所引起的信任危機。離開北京回武漢之前,我曾經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一位多年的好友。大兄弟聽説我要回來了非常高興,但也給了我一點小小的建議:“遠程辦公”之後,你必須要拿出比原來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成績。因為如果在辦公室出了岔子,你可以有一萬個藉口;但如果“遠程辦公”出了岔子,那麼問題有且只有“遠程辦公”一個。
古代皇帝擔心外派邊疆的領兵大將,今天的管理層又何嘗不憂慮遠程辦公的員工和大部門?
如果一家企業全面實現了遠程辦公,那麼也就意味着企業對員工的掌控力被極度稀釋——競業風險驟然提高,只要對方開價合適,遠程辦公的員工完全有機會一心二用,上午給別人打工,下午給自家打工。另外,遠程辦公很可能也意味着企業文化的煙消雲散。遠程招聘、遠程入職、遠程辦公、遠程辭職……那麼除了需要上五險一金之外,這個員工和外包勞務人員又有什麼區別呢?
在過去的三年疫情中,因疫情管控而居家的我們進行了一場2億人蔘與的遠程辦公社會實驗,一個很有趣的看法就此產生了:存在感最低的是中層管理者,因為核心決策高層制定,具體執行基層落實,中層幹部是個傳話筒?這也是互聯網帶來公司架構扁平化後的挑戰,數字移民把這個問題放大了——公司可以不可以只需要工作羣,不需要辦公地。
令人興奮的利益混雜着令人恐懼的後果,這使得許多企業在面對是否轉型遠程辦公時猶豫不決。

一切都是關於資源的平衡
《三國演義》裏有個很著名的片段叫“荊州城公子三求計”。講的是荊州劉琦被蔡氏一族逼的危在旦夕,使出了一招“上屋抽梯”逼諸葛亮救他。智慧的諸葛亮只説了一句話,就讓劉琦同志轉危為安。

這句話,叫**“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這個典故,講的是戰國時代晉文公重耳和他兄弟申生的故事。申生留在皇宮裏最終被人害死,重耳跑到外面周遊列國卻最終活下來成就霸業。
細細想來,不論是過去衝向大城市的小鎮青年,還是今天的數字遊民,大家其實都頗有些“晉文遺風”——樹挪死,人挪活。
大城市同時聚集了資源和人口,小城市同時失去了資源和人口,結果導致了大城市苦於臃腫,小城市擔心萎縮——兩邊都不是很開心。
但今天,我們卻發現了一種可能性:遠程工作者使得人口和金錢從大城市流向小城市。在這個過程裏,遠程工作者獲得了更高的幸福指數,大城市疏解了人口,小城市獲得了消費。
這,或許能成為破解資源分配不均衡問題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