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李旻昊|政治共同體與政權:家—國關係的深化認識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08-24 15:06
徐勇|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部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李旻昊|華中師範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6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家”在中國學界曾經長時間消逝。2010年以來,對“家”的研究日益活躍起來,“家”不僅成為多個學科關注的對象,而且成為2022年學界研究的熱點。在中國,自古以來“家”與“國”便緊密相連,如有“國之本在家”,以及到當代有“家國情懷”等諸多相關表述。學界對“家”的關注不僅僅在於“家”,更在於“國”。但“國”具有政治共同體和政權的雙重屬性,從“國”的不同屬性來理解“家”,便會得出不同的認識,從而造成學界對“家”的認識分歧。只有釐清“國”的雙重屬性,才能將“家”安頓到合適的位置,進而深化對家—國關係的理解。
對“家”的認識分歧及原因
家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關係。”“家”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在中國最初是從否定性的角度認識的。早在20世紀初,中國文化界興起了一股“廢家”“毀家”思潮。改革開放後,隨着社會科學的恢復重建,“家”重新成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而“家”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源於其在中國遠遠超越“家”本身的價值,具有政治、社會、哲學、歷史等多方面的意藴。
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國”。從英文的“國家”一詞來看,都只有不同於“家”的“國”的含義(country, state, nation),而這些詞彙進入中國後,均被翻譯為“國家”,這既是中國人的智慧,又是基於中國的經驗。**因為在中國,“家”有着極其特殊的地位,家庭甚至被視為政治生活中負責的成分,深刻影響着中國國家演化的進程,所以,研究“國”不能不關注“家”。**筆者較早地從政治學角度關注到“家”的問題,曾在2010年闡述家族政治是家族組織長期控制或影響政治體系的一種政治形態,表現為家族力量在一個政治體系裏具有支配性地位和特殊影響,需將血緣性家族納入政治體系中考察,並提出家族政治在亞洲影響深遠的命題。在2013年又發表了《中國家户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比較》一文,提出家户制是中國的本源性傳統,能夠對當下和未來產生深遠影響並長期發揮作用。之後,筆者所在的田野政治學團隊提出了“家户制國家”的概念,將農户與國家關聯起來。
改革開放後,以研究微觀社會組織見長的人類學和社會學對家庭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主要限於家庭組織及家庭變遷本身。進入2010年後,“家”再次成為社會學研究的熱點,但已不限於家庭組織本身,而有了更為宏大的理論和方法論意義,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為肖瑛2020年發表的《“家”作為方法:中國社會理論的一種嘗試》一文。該文認為,“家”對於中國而言是一種總體性的和“根基性的隱喻”,要將“家”作為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的基點。
哲學界則將“家”提升到“家哲學”的高度加以認識,通過對中西方的比較,突出“家”在中國文明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對“家”問題研究較多的孫向晨認為:“‘家’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傳統,還應該從文明論的高度來思考‘家’問題。文明論視角顯示出中華傳統中‘家’問題藴含的某種更廣泛、更深遠的維度。”
隨着“家”問題日益引起學界的關注,《探索與爭鳴》刊發了一系列相關論文。其中,政治學者對“家”有着不同認識。任劍濤認為,目前對於“家”作為中國社會與國家重建的根本着力點的論述,多建立在“家”的哲學提純上面,其對社會學界和哲學界將“家”置於一個很高位置的認識持謹慎態度。譚安奎與任劍濤的觀點類似,提出“政治理論是否需要家的出場”,並對政治共同體所需要的本體論基礎與家哲學的前景做了進一步討論。
政治學者對“家”的位置持審慎態度,不是一般地論“家”,而是從國家及家—國關係的角度來加以認識。在他們看來,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家國同構”時期,正所謂天下一家,“家”是天下的基礎,即組成國家的基本單元是家庭而非個人。而在以獨立的個人為基礎的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家”是否還有過往的地位大可置疑。但無論如何,“家”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正在探索與爭鳴中走向深入。“家”得以成為多個學科關注的熱門話題,顯然不限於“家”,更在於“國”,在於對現代國家建構的關注。一些政治學者對“家”的地位認識之所以與哲學、社會學的學者有所不同,便在於國家的視角,特別是基於現代國家建構的維度。當然,哲學、社會學的學者將“家”提升到一個很高位置,顯然也不只是簡單的“提純”,也有關於國家建設的宏大考慮。因此,不同認識和分歧的關鍵在於對國家的認識。
近代以來,隨着民族國家的崛起併成為世界體系的基本單元,國家便成為一個十分重要但又需要從不同角度加以界定的問題。列寧曾經為之苦惱,深感國家問題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是“一個最複雜最難弄清的問題”。從國家的基本含義來看,其具有雙重性:一是由人民、國土和公共權力等要素構成的政治共同體;二是專門指國家政權,是一種“特殊的公共權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指出,國家與其脱胎而出的氏族組織在性質上有兩個方面的不同,“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第一點主要指政治共同體,第二點則專指國家政權。而這兩點又是緊密聯繫、相互依存的。沒有公共權力,也就無所謂人民、國土等概念,人民、國土等要素不可能自動組成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沒有人民、國土等要素,公共權力也就缺乏依託。但政治共同體與國家政權又有區別。當人們籠統使用國家概念時,其側重點往往不同。正是因為如此,列寧曾經為之苦惱。當下學界對“家”的認識分歧,關鍵在“國”,根本在於對國家概念雙重性認識的取向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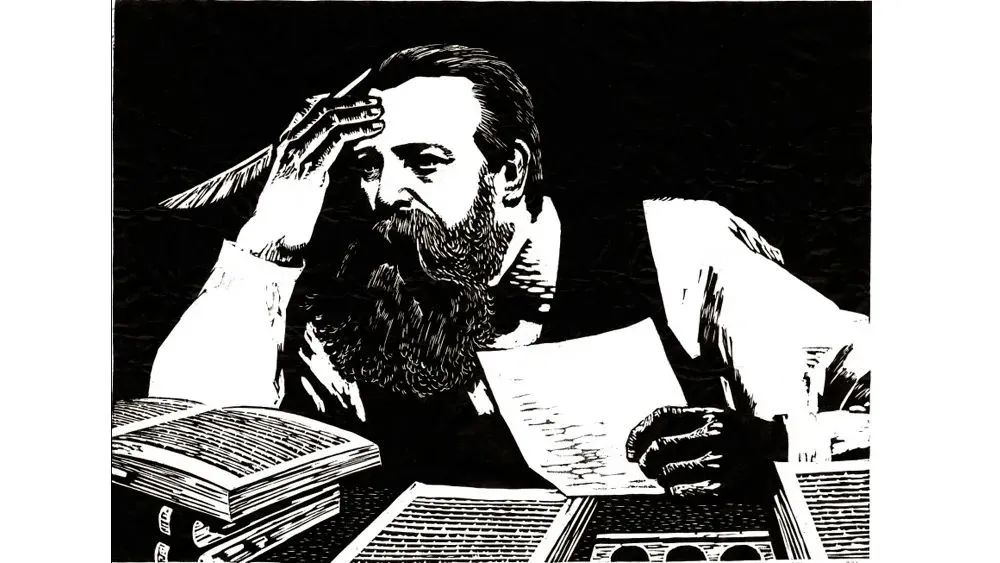
國家雙重性的偏向:中西演變
“家”得以成為學界的熱門話題,涉及家與國、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大背景。國家雙重性的表現形式不同,人們的認識取向也就有所不同。
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人類歷史的演進具有共同的規律性,也有不同的路徑和特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指出國家起源於氏族組織的共同規律,同時也分析了國家產生的不同路徑。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家庭關係是人類最初甚至是唯一的社會關係。但隨着國家的產生,國家與其脱胎而出的血緣母體的關係有所不同,人們對國家的認識也就不同。
在西方,“國”從“家”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開篇便是講“家”,其在《政治學》中引述名句:“先營家室,以安其妻。”由若干家庭組成村坊,再由若干村坊組成城邦。“君王正是家長和村長的發展。”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家務管理”,即如何“治產”。但是,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城邦是比家庭和村坊更為高級的團體,人類在城邦中生活才是政治動物,從而具有政治屬性,有了公民的存在。“城邦本來是一種社會組織,若干公民集合在一個政治團體以內,就成為一個城邦。”

城邦雖然產生在個人和家庭之後,但在本性上先於個人和家庭。城邦在性質上是與家庭、村坊不同的政治共同體,其擁有公共權力,並來源於獨立的公民的授予,而家庭只是一般的私人性的社會生活組織。因此,古希臘人更為重視作為公共權力的國家。由公共權力的獲得、配置而產生了不同的政制,從而有了政治學。政治學的開端便是研究城邦政制。
在古希臘之後,西方也經歷了因為血緣關係而獲得統治權的封建時代。早在亞里士多德時期便認為,君主制來自家長制,是原始家屬關係的延續。到了17世紀,這一學説得到了系統論證,形成所謂的“家長統治説”,認為政治權威是家庭治理的必然結果或派生物,政治權威可按照家庭治理方式加以統治。家長統治以父權和夫權為中心,其權威是與生俱來、不可動搖的。但“家長統治説”受到了洛克的嚴厲批判,即在《政府論》的上篇中,洛克對作為君主制來源的家長制進行了大量批判,以動搖君主制的權威基礎。而在《政府論》下篇,則主要論述“政治社會”。“政治社會”不同於家庭,是自由的個人基於維護自己的權利,與其他人通過契約而形成的,以便獲得舒適、安全、和平的生活,並使自己安穩地享受自己的財產和獲得更大的保障以免受到侵犯。“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於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在這方面,自然狀態有着許多缺陷。”在洛克眼裏,國家是政府統治的共同體,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人民授予,家是父母子女構成的共同體,家長權力是自然的,同時也是有限的。但國家是由一個個自由的個人組成,其從過往作為政治權威來源的“家”中脱離開來,離“家”出走。
到19世紀時,黑格爾進一步將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區分開來。他認為,家庭的基礎是婚姻,體現着一種愛的倫理精神,“作為精神的直接實體性的家庭,以愛為其規定”,“婚姻實質上是倫理關係”。而其將市民社會看作是處於家庭與國家之間的差別階段,是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成員的需要,通過保障人身和財產的法律制度,和通過維護他們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來的。但市民社會的有序運行需要國家的指導,黑格爾將國家看作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的東西,並具有自主性。
總體上看,近代以來西方有關國家的認識,主要從國家政權的角度加以理解,其依據是國家與社會的分離,來自社會又高於社會的國家是一種特殊的公共權力。韋伯更是直接將國家界定為具有支配性的國家權力,這正是從公共權力的角度來看,“家”與“國”沒有什麼聯繫,因為公共權力來源於獨立的公民個人授予。進而,“家”在現代西方政治學中處於缺失位置。但如果從政治共同體的角度看,作為人羣的社會和作為公共權力的國家本身便包含其中,難以體現二者的分離與對立。
古希臘城邦民主政體和古羅馬共和政體的產生,對過往血緣關係與國家結合的方式給予了摧毀性的打擊。**但在中國,作為血緣單位的“家”與作為政治單位的“國”長期未分離,並非古代希臘和羅馬國家那樣在“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被炸燬的“空地”上生成,而是繼承了舊社會的大量因素。**在侯外廬看來,就家族、私有和國家而言,“‘古典的古代’是從家族到私產再到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亞細亞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裏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陳代謝,新的衝破了舊的,這是革命的路線;後者卻是新陳糾葛,舊的拖住了新的,這是維新的路線。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後者卻是‘人惟求舊,器惟求新’”。“這就是説古代希臘、羅馬的國家完全衝破了家族血緣關係的束縛,家族與國家之間不存在結合的關係;而中國的國家仍然處在家族血緣關係的束縛之中,家族與國家處於相結合的狀態。”即血緣關係及其組織單位在中國一直延續了下來,國家與社會並非二元分離和對立的狀態,而是相互滲透和依賴。
在中國,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要高於作為公共權力的國家,人們更多的是從政治共同體的角度來看待國家。從國家組織的角度看,集“家”為“國”,“家”是“國”的縮小,“國”是“家”的放大,“國”之本在“家”;從國家制度看,由家長制到君主制;從國家治理看,將國家治理置於家庭之中,“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家盡孝,在國盡忠,家國一體。在中國的話語中,國家更多的是一種包含無數個家庭在內的政治共同體,組成國家的基本單元是家庭而非個人,所謂“天下一家”。芬納因此指出:“中國被當作‘國家’,一個‘家庭的國家’:簡言之,國家就是家庭的放大。這正是中國社會與西方價值相悖的地方之一。”
家國一體的關係為中國文明進程提供了超穩定的根基。但是,近代以來,國家的戰爭失敗使得人們深刻反思中國的文明和國家的弱點,將“國”之失敗歸之於“家”。從國家權力看,君主制表現為“一家天下”,要求“天下為家”,只有通過民主革命推翻君主制,才能實現“天下為公”。從政治共同體看,天下由億萬個有着自己利益需求的家庭組成,存在內在張力,每個人都為“家”,何人為“國”?延續已久的家庭制度牢牢限制着個人,已成為新國家建構的桎梏。新文化運動對長期延續的家庭禮教進行了激烈的批判,有人提出“萬惡家為首”,主張“廢家”“毀家”,為了“國”而須“破家”。這一思想和運動影響很大,後人稱之為“家庭革命”。隨着民主革命的深入,毛澤東對於與舊的統治制度聯為一體的家庭權力給予了批判,認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其中的族權與夫權都來自傳統的家庭制度,併成為政權統治的社會根基。
近代以來的民主革命具有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雙重性,重新構造了家—國關係,並注意到國家的雙重屬性。從國家政權的角度看,將“家”與“國”分離,以民主制替代君主制。從政治共同體的角度看,動搖了君主制的根基——家族權力,要求建立以公民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新社會。
現代國家雙重建構中的“家”
隨着民主革命的推進,“家”的地位日益降低。但是,“家”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並沒有消失,直至人們重新認識“家”。儘管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一直在破“家”,但“家”卻是難以繞開的存在。家庭出身具有很強的政治屬性,一度出現了“血統論”。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革命隊伍內的家長制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
造成以上狀況的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民主革命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而是面臨國家危機的急迫應對。民主革命否定了家長制,但對這種歷史非常悠久的陳舊社會現象的影響缺乏足夠估計,且其本身的消失也有一個歷史過程。與此同時,因為傳統社會的家國一體,民主革命要推翻國家政權,對傳統國家政權賴以存在的“家”也持根本否定態度,未能在學術理論上進行多層次認識。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2010年以來,“家”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併成為學界的熱點議題。
近代以來的民主革命對“家”持根本否定態度,主要是基於政治革命,換言之,作為民主革命對象的“家”是被視為傳統國家政權根基的政治化的“家”。而“家”作為經濟社會本體反而被遺忘並淡化了。作為經濟社會本體的“家”是農業經濟社會的產物,並長期發揮着積極作用。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實行人民公社體制以來,“家”便以各種方式表現自己,並展示其生命活力,只是因為政治原因造成“包產到户”三起三落。隨着農村改革,“包產到户”得以正名,並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名得到制度上的確認。被視為“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的一家一户的生產單位能夠受到農民歡迎,必有其內在原因。這就需要重新認識“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筆者在2013年發表的《中國家户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比較》一文中提出了兩種東方傳統:村社制與家户制。中國很早就超越了村社制傳統,進入更高的層次——家户制。在當下和未來的中國農村發展中,必須高度重視和深入挖掘這一基礎性制度和本源型傳統,精心釐定本國的傳統制度資源,才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家”作為中國無法割捨的傳統制度資源,就存在如何對待的問題。2010年以來,“家”得以成為多學科關注的論題,重要原因便在於此。而發生分歧的焦點又在於對國家雙重性的理解。政治學者對“家”持審慎態度,主要是從國家政權的角度來理解“家”。“家”與“國”分離是國家政權產生的標誌,這在於“家”與“國”是兩種性質的組織。“國”是繼“家”之後產生的高級組織,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繼“國”產生之後,“家”主要是私人性,“國”則是特殊的公共權力。兩種不同性質的組織,必然要求兩種不同的制度;“國”是比“家”更高級的組織,也就必然要求有更高級的制度。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政體(憲法)為城邦一切政治組織的依據”。洛克則認為:“父權固然是一種自然的統治,但決不能擴展到政治方面的目的和管轄範圍。”
從人類文明和國家進程的實踐看,“家”與“國”日益分離是總體趨勢。即使是在中國,隨着作為國家政權的“國”的建立,“國”也不是“家”的簡單放大。在傳統中國,“國君”的地位是由權力決定的,家庭關係服從權力關係。“家”與“國”的重疊,不僅傷害“國”,也傷害了“家”。“家天下”的皇帝儘管擁有最高權力,但其家庭生活並不幸福。皇帝女兒不愁嫁,重要的不是女兒而是皇帝。可憐生在帝王家,骨肉相殘最悽慘。中國的國家進程是“家”與“國”不斷分離的進程,只是這一分離的進程太緩慢。儘管近代以來,隨着“家天下”制度的推翻和建立共和國,“家”與“國”的分離進程加快,但這種分離不是基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這就導致傳統社會中滋生的家長制這類陳舊社會現象在“反傳統”的過程中自然延續。我國的政黨和國家組織制度都是民主集中制,但傳統家國重疊模式下的家長制作為一種文化模式深刻影響政治過程,並會損害民主集中制。鄧小平將家長制視為“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的論斷是精當的。這種狀況只有隨着經濟社會變遷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進才有可能加以改進。現代國家建構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天下為公”,國家公共權力為天下公器而不得私有私用。在“家”重新回到學術視野之時,必須將作為私人性的“家”與作為公共權力的“國”區別開來。
哲學、社會學的學者將“家”置於很高位置,在相當程度上是從政治共同體的角度理解的。中國歷史上主要是從政治共同體角度看待“家”的。近代以來,民主革命對“家”持根本否定態度。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市場經濟發展,個人的地位日益突出,“家”的地位進一步弱化。學界將“家”置於較高位置,一方面是對過往對“家”簡單否定的匡正,另一方面是挖掘本土資源,希望糾正片面西方化的傾向。應該説,從政治共同體建設的角度看,以上認識有一定價值。國家不僅僅是一種特殊的公共權力,也是人們賴以存續的政治共同體,即使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主權國家仍然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單位。人們不僅需要有一個民主的政權,也需要有一個強大的政治共同體。
現代國家建構包括現代國家政權和現代政治共同體的雙重建構。從現代政治共同體建構的角度看,“家”是重要的組織資源。孫中山從政權的角度主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但從政治共同體的角度又認為家族是比個人更為有效的組織資源。鄧小平從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的角度批判家長制,但從政治共同體的角度又認為要吸取歐洲的經驗教訓,重視家庭的作用,強調“家庭是個好東西”。在中國,“家”作為構建政治共同體的治理資源十分難得。西方國家離“家”出走,並不是不要“家”,而主要是指國家政權與家庭的分離。但是,西方國家是建立在市民社會的基礎上,市民社會的重要特點是個體化。這種人人為己的市民社會並不是理想社會,否則無須國家。黑格爾將“家”定義為“愛”,與定義為“利”的市民社會區別開來,便説明市民社會並不能替代家庭。特別是西方的市民社會所造成的個體化趨於極端,為國家治理帶來諸多問題。西方國家雖然開始注意家庭建設,但缺乏“家”的資源。
總體來看,“家”之所以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不在於“家”本身,而在於家—國關係,只有從政治共同體和政權的雙重屬性理解“國”,才能將“家”安放到合適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