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安奎|家-國之結與家哲學的黯淡前景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08-24 15:10
譚安奎|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5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來源於網絡

譚安奎教授
近些年來,國內學界對“家”的討論十分熱烈。這種討論既超越了對家族、宗法制度進行批判的傳統範式,也不同於西方學界對家庭內部性別關係與性別正義的持續聚焦。這些研究越來越立足於中西比較的視野,着重發掘家的本體論意涵及其衍生出來的其他價值,從而嘗試探索一種兼具中國文化底藴和普適意義的“家哲學”。其中,家所體現的生生不息、在代際中存在的現象學-生存論意向對於反思乃至替代現代個人主義的形而上學假定所具有的理論潛力,得到了越來越深入的闡發。當然,箇中立場也有差別。例如,孫向晨對西方個人主義的現代性採取了更為積極的接納態度,因此主張個體與“親親”構成“雙重本體”;而張祥龍則更鮮明地強調,在個體、家與集團這三體當中,唯有家是真正源發性的、自足的,因此享有“原本體”的地位。
任何一種家哲學的登場,似乎都不得不面對家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本文關注的是其中最核心的家國關係問題)。一方面,種種家哲學針對個人主義的現代性而立論,它們實質上都是羅爾斯意義上的“整全義理”(comprehensive doctrines),包含着本體論、倫理學和政治學等多方面的理論含義。另一方面,把家歸於私人領域幾乎被視為一種關於現代性的常識信念,中國近代以來更是從政治層面對家文化開展過高強度的批判。因此,家哲學必然會直接或間接地引申出家國關係問題。當然,對這一問題的再思考,不能直接從公私二分的現代定勢框架出發,因為那有可能以一種既定的結論或成見掩蓋了家哲學新近的理論拓展所帶來的啓發。
**鑑於家哲學具有明確的中西比較的自覺,甚至有為西方現代性糾偏的強烈意圖,本文便從反思西方政治理論傳統中的家國關係開始。**我們將分析闡明,家沒有成為西方政治和政治理論的基礎,這本身不是一個現代問題;但政治理論是否需要家的出場,卻是古今有別。在此基礎上,我們將基於功能、本體與倫理三重視角的交錯分析,揭示家國之間的複雜糾纏。
西方政治理論的無家可歸與有家可(不)用
政治生活中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是政治權威的構成,以及它能否獲得人們的自願服從。從經驗上講,家庭是人們最自然的生活單元,家庭中的權威與服從關係,對人們而言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這就為人們以某種形式對家庭與政治進行類比,或者從家庭到政治進行推演提供了空間,家庭也就在相應的意義上被視為政治權威的基礎。中國式的家國同構、君父一體是這種思維模式的典型,種種形式的父權制政治理論則是其極端表現。古希臘哲學家對於“家庭—村落—城邦”這一自然進程的刻畫,似乎也使得家庭在政治秩序的想象和維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後文將會闡明,這其實並非是在理論上讓家庭為政治奠基)。雖然從家庭到政治的延伸模式各有不同,而且有時還得采用法律擬製的手段,但其中包含着對家庭與政治關係的共同設想:由於家庭中的權威與服從關係是自然的,經過不同形式的延伸和推展,政治權威也就顯得是自然的。在這裏,家庭為人們服從政治權威提供了心理、情感和道德上的基礎,而家庭的教化也被期望發揮這樣的政治功能。
現代政治理論在這個問題上大異其趣。一旦我們認為,政治狀態和國家乃是基於個體間的同意而人為建構起來的,從家庭向政治延伸或進行推演的“自然”鏈條就被切斷了。更有甚者,由於個體成了理論起點,不但國家、政治生活不再是自然的,家庭的自然性也可能遭到否定。例如,霍布斯對家庭關係的解釋,就完全是按照其政治模式來展開的:母親對孩子的最初支配,以及父親通過支配母親而對孩子形成的支配權,都與血緣、親情或天倫無關。相應地,在沒有政治權威支撐的情況下,家庭內部的秩序,包括父權,本身就處於自然狀態而缺少穩固性,因此不可能成為政治權威得以依託的力量。有研究者指出,經早期現代自然法理學家尤其是霍布斯和普芬道夫對家庭的去自然性和政治化改造,政治哲學不再借助家庭內部的權威結構為政治服從提供道德和情感基礎,這使得現代政治處於巨大的風險之中:“破除了家庭對政治共同體的構成作用,在每個個體作為陌生人加入政治社會的那一刻,不僅個體必須經歷自由與理性的新生,政治共同體也同樣在原則上要再經歷一次從自然權利的放棄到政治義務的建立的理性洗禮。無數次個體性的洗禮,是否會不可避免地導致革命的風暴,恐怕是現代利維坦最終無法擺脱的難題吧。”言下之意,家庭的缺席決定了現代政治的無根性,現代政治秩序因而喪失了穩定性的基礎。
雖然家國之間的類比或擬製可能為人們在政治中對權威的服從提供一些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但如果就此認為政治的內在不穩定源於缺少了家庭的政治功能,或者認為這種功能的存在是政治秩序的真正根基,則在歷史和理論上似乎都是難以自圓其説的。在家國同構最為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中,王朝“天下”難道不是一直處於週期性的動盪之中嗎?反過來,作為西方政治秩序持久穩定的歷史典範,羅馬共和國的長期存續又何曾被嚴肅地歸因於家庭所發揮的政治功能?後世最為強調的其實是它的制度,特別是混合政體,然後是它的公民宗教。從理論上講,西方古典政治哲學對政治秩序的論證,主要也不是建立在家庭的政治功能之上的。相反,我們看到的恰恰是對家庭的相對貶低或限制。用布魯姆的話來講,柏拉圖持有”雙重自然”學説,即認為情慾與理性、肉體與靈魂都是自然的,不過前者為低級的自然,後者為高級的甚至神聖的自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重自然分別對應着家庭與理想城邦。因此,雖然《法律篇》並不像《理想國》那樣主張在統治階層中廢除家庭,但家庭也是首先需要通過立法來馴化的對象。在對家庭的態度更為温和的亞里士多德那裏,公民友愛也要高於家庭友愛,家庭作為私人領域在價值上也無法媲美城邦政治生活。在這個意義上,亞氏其實也持有“雙重自然”的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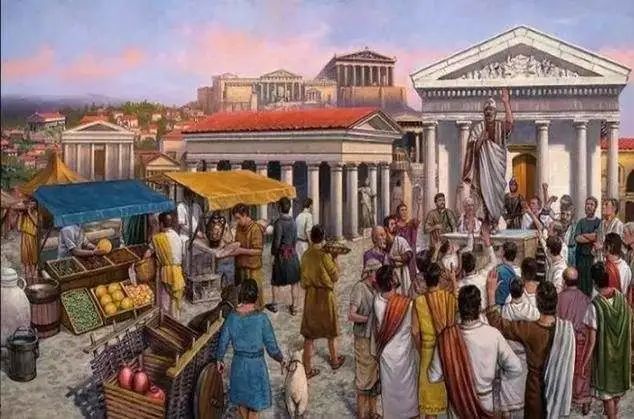
**我們需要強調的是,“雙重自然”學説的內在結構表明,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學中,從家庭到城邦並不是一種自然的延伸或同構關係,而是有倫理上的質變或飛躍,這一點不能因為“家庭—村落—城邦”的歷史進程而被掩蓋。**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或者至少是低估了“人就其自然本性而言是政治動物”這個古典信條。誠然,亞氏在《尤台謨倫理學》中也説過,人不僅是政治的動物,而且是家的動物。他甚至説,“友愛、政治制度和正義的源泉(origins and springs),最先正是見之於家庭”。這似乎是在明確主張從家庭到城邦的自然延伸。但亞氏給出這一判斷的關鍵理由之一是,“在單個的家庭事務內部,可以看到全部的政制形式,包括真正的和腐化的形式……家父的權威是君主制的,夫妻一起構成了貴族制,兄弟則形成了共和”。這説明什麼呢?它表明,亞氏其實不是在以家庭的模式來分析城邦政制,而是在以城邦政制的模式來分析家庭。換言之,這並不是一種從家庭到國家自然延伸的理論思路。當然,強調這一點並不是要完全否定家庭的政治功能,因為如果國在政治和倫理上高於家,那麼,國賦予家以培育良善公民的職責,反倒是自然而然的。**只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恰恰是政治想象在塑造着人們對家庭的理解,而不是相反。**至於西方最為極端的父權制政治理論,它根本上也不是在用家庭形象來塑造政治,而是在為政治提供神學根據。霍布斯、洛克所要面對的費爾默的父權制主張便是如此,它試圖以亞當為起點,認為上帝把世界交給亞當來統治,並代代相傳。因此,它本質上是一種關於君權神授和世襲君主制的理論,並未在任何意義上抬高家庭本身的政治地位。
基於上述理解,我們就不必驚訝,為何一旦有了個體化的政治哲學前提,家庭就在政治上被邊緣化,甚至在政治哲學上隱遁不見了。當然,這並不是説個體化的政治哲學就會提出廢除家庭的主張,而是説,家庭似乎不再成為重要的理論議題,甚至古典政治哲學賦予家庭的政治教育功能都無關緊要了。現代主權國家強調的是個體化的、平等的服從,而個體化意味着破除任何傳統的自然統治和自然權威,家庭無疑首當其衝。因此,除了霍布斯對父權的去自然化、去倫理化處理,洛克、盧梭也都對父權展開了政治批判。同樣,中國近代轟轟烈烈的家庭革命的根源之一也是國家觀念的抬升所帶來的衝擊,因為要建立普遍、平等服從的國民國家,就得讓個體擺脱家的束縛,此謂“為國破家”。
個體化前提下的政治哲學關注的焦點是對權威之正當性的政治辯護問題,而政治正當性的基礎則是個體之間的同意。形形色色的契約論在早期現代紛紛登場且各種變體延綿不絕,其根源正在於此。在契約論者那裏,只要如此這般地理解作為個體的人,特別是他們的行為動機,就能夠理解他們之間通過契約進入政治社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政治辯護不是一個歷史過程,相反,霍布斯、盧梭喜歡用“一霎那”“一瞬間”來表達主權者或政治共同體得以建立的訂約“時刻”。康德則更明確地承認,社會契約只是一種理性的觀念。同樣的道理,政治辯護也不是一個社會教化過程。因為有了上述對人以及契約邏輯的理解,人也就被期待按照這種契約的結果去對待自己和他人,並服從相應的政治權威。換言之,這裏麪包含着一種自我的倫理轉化,而不是教化。有契約論研究者認為,縱觀從霍布斯到羅爾斯的契約論傳統,“政治辯護與倫理轉化在過去和當前都是社會契約理論的兩個構成性維度”,這個判斷是頗有見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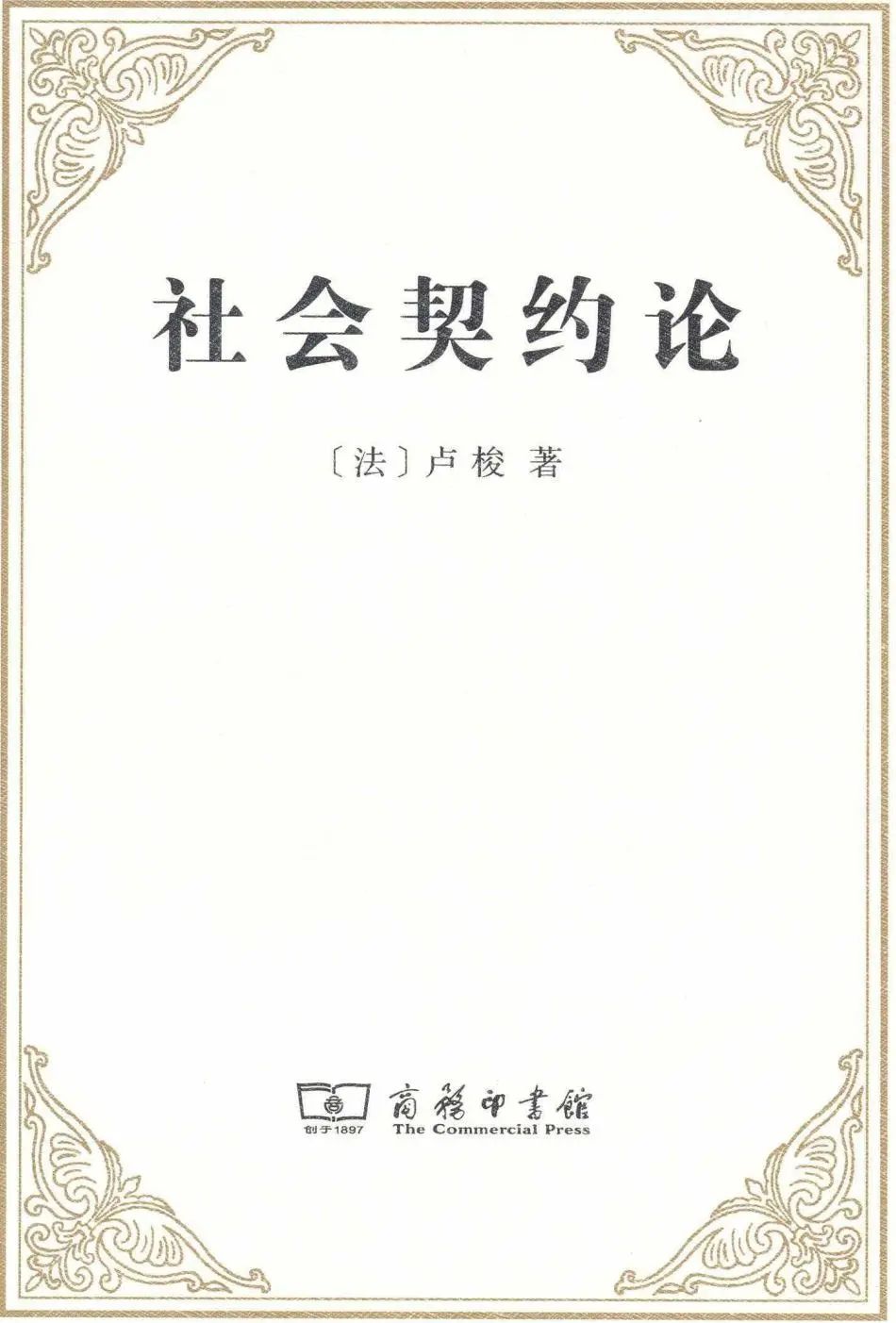
**個體化導致政治正當性問題擺脱了對歷史、教化的依賴,這可以解釋家庭在政治哲學中的邊緣化,甚至是缺席。**這不是人們是否想要或需要家庭的問題,也不是人類是否需要繁衍或特定政治共同體是否需要代代存續的問題,而是政治哲學理論要旨的變化和相應的理論自洽性問題。從個體直接過渡到國家的契約論,首先往往把國家工具化了,這是政治哲學研究中的老生常談(盧梭、康德和羅爾斯一脈的契約論傳統稍有不同,在此不予展開)。一旦國家沒有了內在的倫理含量,也就無須家庭繼續扮演傳統社會賦予它的政治教化的角色了。事實上,家庭作用的弱化,確乎是古今分野的一個重要標誌。在傳統社會中,家庭是基本的經濟、宗教乃至政治單位,而在現代社會中,家庭不再充當這樣的基座或組織者的角色,它主要是一個社會化的代理機構。而且即便如此,“家庭並非惟一的,甚至並非主要的社會化單位”。相對來説,學校、監獄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國家規訓與社會教化的承擔者。英國歷史學家麥克法蘭認為,個體從家庭中獨立出來,以及家庭功能的全面弱化,早在13世紀以降的英格蘭就出現了,而這是他把現代性的起源放在彼時彼地的根本理由。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不能指望家庭的自然情感以及特定的服從關係能夠自然地延伸到政治上去。現代社會中的故事可能恰恰相反。對此,對家庭的作用多有申述的當代德國哲學家霍耐特有明智的判斷:“孩子對‘父親’或‘母親’的感受,是受到社會對父母角色期望影響的;我對我父母的感情,首先依賴於我的父母是否滿足了規範的要求,即我作為他們的孩子在我的成長期,是否滿足了社會規範對他們所提出的要求。”由此可見,雖然西方政治觀念本身存在明顯的古今之別,但在家庭與政治的關係上,有一個根本點並未改變:是政治想象在塑造人們對家庭關係的理解,而不是反過來。
我們不妨總結一下:在西方政治傳統中,家本來不曾扮演政治或國家的哲學奠基石的角色,也不存在從家到國的自然延伸的邏輯。就此而論,西方政治/國家理論本來就是“無家可歸”的,這不能被理解為一個純粹的現代事態。但在功能層面,家庭是否被期望扮演政治教化的角色,即在政治上是“有家可用”還是“有家不用”,則有古今之別。政治理論上既無家可歸,又有家不用,則是典型的現代問題了。
在世代中存在:
本體論視野中的家國關係及其倫理難題
家庭的不在場雖然並不影響現代政治哲學在理論上的自洽性,而且它恰恰是這種自洽性的內在要求,但它似乎是以忽視另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為代價的。讓我們對此稍作解釋。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社會契約是“一瞬間”就可以訂立的,因而事實上也就是隨時可以完成的。因為它處理的問題只是政治秩序之正當性的檢驗標準,這個標準,尤其是確立這個標準的契約程序是明確的,也是隨時可以拿來使用的。羅爾斯對此説得最為明白。他説,我們可以想象人們“時不時地”彼此討論他們生活於其中的制度是否符合正義,因為原初狀態不過是在塑造我們看待自身和社會的一種觀點(point of view),“我們隨時都可以從這一必要的觀點出發來看待社會世界”。這是因為,社會契約論重在關注政治秩序的正當性基礎,也就是正當的政治秩序在觀念上和道德上的“生產”問題。正當性檢驗是每一個成熟的個體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的,但經得起檢驗的政治秩序是否需要、如何能夠持續地實現自身的“再生產”,這個問題在社會契約論中幾乎付之闕如。鑑於人們生活的世界乃是一個世代交錯、生生死死的世界,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刻都不可能完全是由理性成熟的個體訂約者所構成的**,因此,政治秩序的再生產也同樣是一個隨時隨地的、現在時態的考驗,而並不純粹是一個面向未來世代的將來時態問題。**
由於忽視了這個問題,在個人主義的社會契約論中,訂約者雖有個體的長遠利益計算,但缺乏超乎個體的、跨世代的長程和動態視野,以及相應的實踐理性能力。誠然,羅爾斯的契約論在這方面有明顯改進,因為它建立在一個明確的前提之上,即政治社會是一個世代相續的公平合作體系:“政治社會總是被視為一種無限延傳的社會合作系統,認為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上其事務將走向終結而且社會要走向瓦解,這種觀點與政治社會的觀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直面了政治秩序的再生產問題。但是,在羅爾斯那裏,這首先是一個強勢的政治理論預設。而且,從政治生活實踐的角度來看,它也可能是一個合理的預設。但既然它對訂約者提出了較通常的個人主義契約論厚重得多的倫理要求,因此也意味着對人或公民的極為不同的理解,我們就必須追問它的理由和基礎何在。尤為重要的是,這種預設意味着它並不像社羣/共同體主義所批評的現代自由主義傳統那樣,從原子主義的立場來理解人,相反,它其實已經把人“在世代中存在”這一本體論問題呈現出來了。
在世代中存在的本體論視角本來不是契約論的強項,而是它的軟肋。因此,柏克從這個視角出發,對契約論進行過嘲諷式的批評。他説,“國家確實是一項契約”,但“它並不是以單隻服從屬於暫時性的、過眼煙雲的赤裸裸的動物生存那類事物為目的的一種合夥關係”,它“不僅僅是活着的人之間的合夥關係,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經死了的人和將會出世的人們之間的一種合夥關係”。柏克使用了契約論的語言,但抽空了契約論的內涵,他最終是用有機論的國家想象來呈現國家所包含的世代延傳性的,而且並未對在世代中存在這一本體論視角提供哲學上的説明。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阿倫特也許是最鮮明地凸顯政治生活之世代延傳性本質的哲學家。在她看來,政治意義上的共同世界乃是我們與同輩、先輩和後輩所共有的。公共領域吸收和保存了人們試圖在時間的自然流逝中所挽救下來的東西,並使之在不斷的延續中熠熠生輝。她甚至提出,公共領域的公共性意味着某種俗世的不朽(earthly immortality),“嚴格來講,沒有這種邁入潛在的俗世不朽的超越性,任何政治、共同世界、公共領域都無從談起”。阿倫特使用了半文學、半神學的詩性哲學表述,傳遞了跟羅爾斯相同的觀點:政治世界的本性就是世代相續的。問題是,如此理解的政治世界背後潛藏的那種本體論視角,該如何得到哲學上的表達呢?
**“家”作為一個哲學範疇的出場,正是在這裏顯現出其必要和價值。**家是個體存在的源發性空間,是每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論經驗。而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在於,這種生存論體驗首先正是上文所説的“在世代中存在”的體驗,因為個體甫一降生,就處於代際關係之中了。在這個意義上,它作為一種關係結構超越了個人意志,也無法還原為其中的任何一方。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人的自我的構成性要素(雖然這種關係從倫理上如何規定的問題仍然是開放的),因而不僅具有確定無疑的源初性,而且具有不可否定的本體論含義。張祥龍因此贊同他所理解的儒家主張,即“人的終極存在不在個體而在原初和真切的人際關係,也就是家關係,特別是親子關係之中”。他甚至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世代時間”或“代際時間”的概念。
有人可能會懷疑這種基於家的本體論的普遍解釋力,因為畢竟存在為數不少的未婚者乃至不婚者。但這至少在部分的意義上是一個誤解,因為它首先把家還原為婚姻的建立,進而無視家的代際關係之維。未婚或未成家、不婚或不成(自己的)家,不等於一個人能夠脱離家而存在,尤其是不等於他或她脱離世代結構而存在。未婚或不婚,可能影響到新的世代關係的建立(這取決於是否生育子嗣),但卻無法否定每一個人身處其中的既有的世代關係結構。換言之,世代關係的普遍性是回顧式的,而不是前瞻式的。一些中國學者強調家的本體論地位,其焦點亦在縱向的世代關係,即“親親”這個維度,而不是橫向的夫妻關係之維。夫妻關係當然有豐富的倫理含義,而且它對我們理解政治關係也有啓發(本文第三部分將會討論這一點),但就本體論而言,“親親”所體現的世代關聯則因其源發性而更為根本。這是中國式家哲學在現象學上的敏鋭性之所在。
突出在世代中存在這一視角的家哲學,為我們超越西方早期現代個人主義契約論的政治思維,尤其是把“世代相續的政治社會”納入政治哲學思考提供了本體論上的必要條件。當然,它是必要而非充分的條件。因為在世代中存在的本體論既然是回顧式的,它在原則上就不能否定個人不再延續任何新的世代關係的自由。而當我們把政治社會視為一個世代相續的體系並對個體提出相應要求的時候,這已經確定無疑是前瞻式的了。**此時,家哲學碰到的挑戰與其説是本體論的,不如説是倫理學的——我們是否應該不顧個人在世代關係延續問題上的自由選擇,而專斷地將其置於一個世代相續的政治社會框架之中?**其實,家哲學倡導者孫向晨一方面主張個體與“親親”構成雙重本體,同時又強調個體相對於“親親”的優先性。那麼,這種優先性該如何解釋呢?它根本上應該源於個體本體所藴含的倫理力量,也就是現代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基礎性地位。此時,家作為另一個本體的提出,主要就是想對現代性提出一種療救性思路。
如前所述,家的本體論地位重點在於“親親”的縱向維度。如果説這種本體論構想是有吸引力的,那麼,它所包含的倫理含義在政治上卻有可能是成問題的。**在這方面,最典型的莫過於關於西方的沉默權與中國傳統的親親相隱之間的爭論。**孫向晨提出,“隱”是化解倫理秩序與法律序之間衝突的一種普遍機制,但“隱”背後的價值秩序在現代西方和中國傳統中卻是不同的。換言之,即便我們可以在家的問題上提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本體論,但仍然會面對不同的政治倫理。與沉默的“權利”不同,在中國傳統中,親親相隱是作為一種倫理義務而提出的,這是家庭倫理試圖規避或壓倒外在政治、法律秩序的表現,它是試圖把“親親”直接延伸到政治領域的結果。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到,“親親”自身在本體論上的可欲性與倫理學上的合理性之間是存在張力的。這或許也可以説明,為什麼把家作為唯一的“原本體”,乃是一個過強的主張。
**世代相續的家庭,不僅是經濟與人口的生產單位,而且是人倫關係的再生產單位。**政治社會也有一個歷時性的再生產問題,這是家與國可以類比的空間。現在看來,鑑於上述本體論與倫理學之間的衝突,我們對這種再生產的類比需要十分審慎。這種審慎不僅在現代社會是必需的,它對於我們恰當理解西方古典政治理論也是必要的。有人認為,既然亞氏主張從家庭中可以看到政制的源泉,而且家庭對人倫關係的再生產與政治友愛關係的再生產是相似的模式,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在亞氏那裏,政治科學也可以被解釋為家政管理的延伸。這種解讀現在看來是誤導性的。事實上,在西方古典思想中,政治社會的延續所需要“再生產”的東西,也是在本質上不同於”親親”的政治關係,而不是“親親”的自然延伸。
**至於現代政治,它強調的普遍個人權利具有明顯的不偏不倚的特徵,因而與“親親”自然的偏倚性取向構成直接衝突。**更有甚者,如果現代國家還追求更厚重的、平等主義的公平正義,這種衝突就會更加劇烈。在這些背景下,家庭人倫關係的再生產,對政治社會的再生產來説似乎反而構成了一種制約甚至破壞。此時,我們就要提出一個看似十分尖鋭且反常識的問題:現代政治為什麼不廢除再生產意義上的家庭?這就再次回到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討論的家庭的政治功能問題。這裏強調“再生產”,意在突出倫理、教化的含義,而不是指夫妻關係的締結與經濟、人口的“生產”。以羅爾斯為例,既然政治社會要被設想為一個世代相續的公平合作體系,那麼,它所需要的遵循公共理性要求、願意按照兩條正義原則去行動的公民的教化、培育,直接由國家主導的機構來完成,豈不是有利於越過“親親”所設置的倫理、情感障礙?或者,他至少可以像女性主義以及其他批判理論家那樣,完全否定私人領域(包括家庭)與公共領域的先在劃分,尤其是這種劃分對於政治正義的意義,因為,“為了讓某種東西成為公共的東西所開展的鬥爭,乃是一種為正義所作的鬥爭”。然而,羅爾斯既沒有主張廢除家庭,也沒有完全否定家庭與政治的距離。而且在這兩個前提下,他還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徑直把家庭當作私人領域的傳統窠臼,因為他明確地把家庭視為社會基本結構的一部分,而後者乃是政治正義的基本主題。這是否意味着,家還有重要的政治倫理潛能有待發掘,從而可以進一步豐富我們對家國關係的認知呢?
從世代到夫妻:
作為人為產物的家庭與作為共同體的國家
家庭制度對於世代相續的公平合作體系的再生產存在顯見的不利,但羅爾斯仍然接受家庭制度對正義原則構成的對應約束。對此,有研究者認識到,對羅爾斯來講,真正的理由在於兒童要成長為充分合作的社會成員,需要經過必要的道德發展,這種道德發展要求由密切的成人-兒童關係所提供的愛和信任,而這是任何由國家運作的機構明顯不大可能滿足的。至於更多的人們支持家庭,或對之有強烈的傾向,這些理由對羅爾斯來講反倒沒有決定性的道德力量。這個説法看來是試圖從道德心理學的角度去確認家庭對於政治社會再生產的功能和倫理意義。但嚴格説來,如果我們僅僅停留於此,那就不過是在迴避問題,因為家庭提供的親密關係,恰恰有可能構成了政治社會所強調的社會正義及相應的公民美德成長的障礙。
作為深受黑格爾主義影響的思想家,霍耐特對家的倫理價值及其政治功能多有闡發,但我們從中似乎可以看到一種不同的思路:“如果人們能夠從中看清,一個民主性的共同體,是多麼依賴於它的成員究竟有多少能力去實現一種相互合作的個人主義,就不會長久地一直否認家庭領域的政治-道德意義;因為要想讓一個人把他原先對一個小團體承擔責任的能力,用來為社會整體的利益服務,這個人必須擁有的心理前提,是在一個和諧的、充滿信任和平等的家庭裏建立的。”這個提醒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既有政治上的前提——個人主義、相互合作與民主,也有對家庭關係模式的特定預設——和諧、信任和平等,而且二者是相互匹配的。這裏的家庭,已不是傳統意義上那種自然的權威-服從關係,更沒有家長主義的影子。説到底,首先是家庭接受了現代社會、政治倫理上的要求,並被這些要求所塑造,然後才有家庭發揮政治功能的空間。如果民主沒有首先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塑造家庭關係,也就是沒能在家庭中確立平等(首先當然是夫妻之間的平等關係),任何一種家哲學都無法論證家庭對於這種政治社會的再生產的意義。同樣的道理,在羅爾斯那裏,他所設想的良序社會是否能夠確保兒童的道德發展達到一定的程度,以使其足以歷時地維繫正義的社會?有人指出,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能無法在生活於羅爾斯式的良序社會之前去給出確定的解答。這些都再次證明了本文一再強調的判斷:在西方關於家國關係的理論傳統中,首先都是政治在塑造家庭,而不是從家庭自然地延伸到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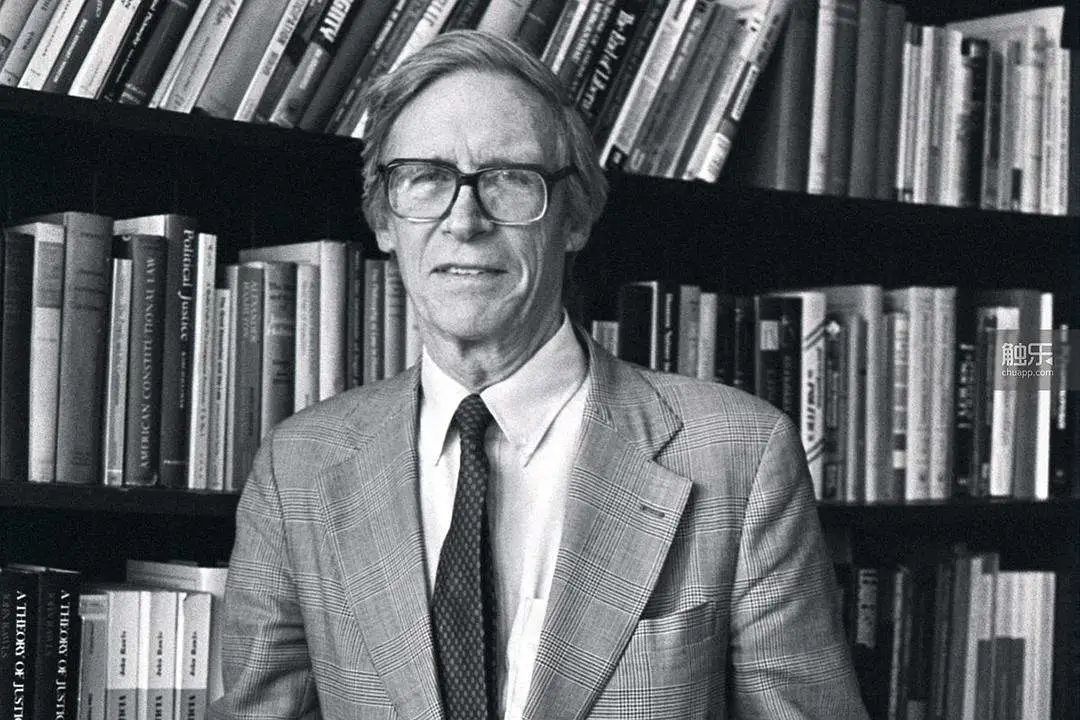
羅爾斯
**個人主義與權利政治對家庭的塑造,首要的成果就是把家庭的焦點從縱向的世代關係轉向橫向的夫妻關係,而這一點當然有諸多社會及理論上的後果。**如前所述,世代關係之所以具有源發性的本體論地位,恰恰在於它是個人生而入乎其中的結構,因而在根本上是超乎個人意志的。因此,個人主義對個人意志的強調,固然也會影響到代際關係的延續,但它使得關於家庭的首要問題變成了諸如是否要與人結成夫妻關係、究竟是否要“成家”,以及選擇與誰結為夫妻、夫妻之間如何相處之類的問題。**換言之,家的第一義,從一個存在論的規定項變成了一個意願上的選擇題,以及一個倫理上的思考題。**相應地,人們對家的理解,不但把重心從家族拉向了核心家庭,而且最終放在了夫妻關係上。進而,在以夫妻關係為中心的家庭中,個人的權利和隱私意識也在提升。這不僅是西方社會史和現代化歷程中的一個重要面向,人類學的研究也表明,即便在家文化傳統如此強烈的中國,1949年以來的變遷也與之若合符節:“家庭變得更加私人化;家庭生活以夫妻為中心,家庭成員也更具個人權利的意識,於是就又產生了對個人空間和隱私的更多要求。在更深的層面上,這種變化標誌着人們在私人生活領域對個人權利的要求在增加。”
基於個人自願選擇、從而也往往是更趨於平等的夫妻關係,其信任、平等所帶來的示範、薰陶,以及在教育孩子、處理代際關係時的實踐(如果夫妻選擇生育孩子的話),當然也就影響了家庭中的世代關係,並能夠以此為個體化的和民主的政治社會的再生產作出貢獻。這是我們在現代社會中可以合理期待的景象,它體現的是家庭在被政治塑造的前提下對政治的建設性作用。但這是否窮盡了現代家庭對於現代政治的意義呢?難道現代家庭只是在微觀的層次上濃縮了現代政治中的個人主義?此時我們或許就會想起本文第一部分所説過的觀點:純粹個人主義的、契約式的現代政治在理論上本來完全可以讓家置身事外。在國家被視為個體的工具的地方,家庭對於政治幾乎是一種理論上的障礙。因此,當我們在現代政治語境中再次強調家的意義,尤其是像羅爾斯那樣把家庭作為社會基本結構的一部分時,我們對政治、國家的理解本身也一定要發生某種改變。**這種改變,首先就是要超越基於私人間契約的工具式國家觀,讓國家承載更多的非工具價值,從而為家在政治中的積極角色提供理論空間。**與早期現代以及後世自由至上主義的契約論不同,羅爾斯式的契約論雖然仍然具有鮮明的個體色彩,但它把政治社會理解為世代相續的公平合作體系,這就賦予了國家更厚重的倫理色彩。事實上,羅爾斯自始至終都認為,“一個政治社會自身就可以是一種內在的善”,正義的制度則是“社會所有成員共享的終極目的”。這些看起來都像是典型的社羣(共同體)主義的表達。
但一個明顯是人為建構的、大規模的政治社會,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共同體呢?通常來説,共同體除了意味着人們擁有一套共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還意味着它是個人自我認同的根源或構成性內容,因而不可能是人為建構的,而且它往往應該是規模較小的。在滕尼斯關於共同體與社會的二分法中,家庭因此被視為共同體的典型。然而,當家庭的中心轉向橫向的夫妻關係之後,家庭本身首先也成了一個人工製品,一個人為建構的產物。此時,家還是一個共同體嗎?如果我們對家的共同體屬性都無從確證,政治社會之為共同體似乎就更是無從解釋了。反過來説,同樣作為人為建構的產物,如果家的共同體屬性能夠得到説明,也許可以為我們把國家理解為政治共同體打開新的理論窗口。
黑格爾對於家哲學的意義此時就體現出來了。他認為,純粹個人之間的合意,就像經濟契約一樣,是沒有倫理性的。這是他批評社會契約論的重要依據。但他一方面認為夫妻關係和家庭的建立乃是基於個人的同意,另一方面又堅持強調家庭的倫理性。在黑格爾那裏,家庭的建立意味着雙方同意各自放棄自身自然的和個別的人格,共同構成一個“單一人格”。由此,自然衝動被降格,精神的紐帶則提升為不可解散的東西,超出了激情和特殊的偶然性。形成“單一人格”,表明家庭是一個超越夫妻任何一方的倫理整體。但既然夫妻關係本身就建立在個人同意的基礎之上,為什麼又説這個新的倫理整體的精神紐帶“不能解散”?難道這是指夫妻不能離婚嗎?這聽起來彷彿跟一次性自願賣身為奴在邏輯上相當。
但這顯然不是黑格爾的意思。**黑格爾的上述觀點至少可以從夫妻關係的兩個相互關聯的特徵來加以説明:一是它的不可還原性,二是它的內在價值。**夫妻關係是由兩個獨立的個體人為建立起來的,但一俟建立,它便不能被分解或還原為兩個完全獨立實體的簡單相加。在這個問題上,它跟朋友間的友誼非常相似:“友誼就是認識到有某種東西不屬於兩個主體中的任何一方,而為雙方共有。”夫妻關係也一樣,它是不能還原為其構成各方的,因為它是某種超越於個體性的事物,意味着雙方的“共同分享”。有人用“內在關係”來刻畫這類關係的性質。與此同時,它的不可還原性表明,它具備了超越個人工具性考慮的獨立地位和內在價值。這意味着,夫妻雙方在思考其行為選擇的時候,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這種關係本身,而非相關的兩方”。在這裏,這種關係本身成了夫妻雙方各自的自我認同的一個構成性部分,同時也部分地決定了他們對自己利益的想象。因此,對夫妻關係本身的維持就可以成為一項獨立的理由,影響乃至決定丈夫或妻子各自的行為選擇,這與各方只考慮自己或只考慮對方的情況都不一樣。這種為雙方共有、共同分享且具有內在價值的關係,雖然不是不能從形式上和法律上解除,但説它超越了分離的個體的意志和激情,卻是完全成立的。
**因此,即便以夫妻關係為中心的家庭首先是一個人為建構之物,它仍然不失其倫理特徵。**在此意義上,它依舊是一個我們可以切近觀察和體驗的共同體。這就為我們思考政治社會的倫理性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主流的現代政治理論,尤其是自由主義傳統,對把國家或政治社會視為共同體的傾向非常敏感,因為共同體似乎總是讓人想到一副壓抑個體的面孔。但現代夫妻關係的基礎和特徵告訴我們,共同體可以是人為建構的,它源於個體意志,但又不可還原為個體的簡單集合。而且,就像家庭一樣,它之為共同體,最根本的東西正在於人為建構起來的、個體身處其中的這種關係本身,而不必是某種先於個體、外於個體或高於個體的實體。所以,維護共同體,也就是維護這種關係本身。如前所述,追求公平正義的現代政治既需要堅持個人主義的建構主義傳統,又需要超越工具論的國家觀,把政治社會理解為一個共同體。現在看來,以夫妻關係為中心的家的概念,可以為此提供一個可供參照的理論模式。

事實上,這種以建構性關係為本質的政治共同體概念,在羅爾斯那裏已經初步浮現出來了。他認為,只有當自由的人們之間有一套可以得到相互承認的合作原則,“人們之間(between persons)的真正的共同體”才有可能在其共同實踐中形成,否則的話,“他們的關係”對他們來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強力之上的。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這種理解,政治共同體存在於“人們之間”,而共同體是否真實,關鍵也在於他們的“關係”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這正是我們在此所説的不外於個體、以關係為實質內容的建構性共同體的意思。這樣的共同體,就像以夫妻關係為中心的家庭一樣,都可以為其成員所高度珍視,併成為他們據以行動的獨立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它們也可以被視為個體自我認同的構成性要素。然而,自我認同的構成性並不等於本體上的源初性,因為這種構成性乃是個體建構的結果。
**因此,以夫妻關係為中心的家庭即便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建構性政治共同體的可能性,但它同樣無法為我們提供“世代相續”的政治共同體的充分想象。**而這種在世代中存在的本體論構想,乃是源於家庭中縱向的世代關係的源初性。這恰恰是黑格爾關於家的思想無法支撐中國式家哲學的本體論構思之處,因為他和霍耐特都重在強調婚姻的個人基礎與現代特性。這意味着,在個體化的背景下,世代相續的政治共同體所需要的本體論基礎(如果它確實需要的話),是無法由家哲學來提供的,這是家國之間在現代社會難以克服的距離。這是否意味着現代政治在本體論上和代際視角下的無根性,我們尚難斷言。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們要去尋找這種根底的話,家,不再是一個有希望的方向。這可能預示了家哲學作為一種整全義理的黯淡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