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 | 從宋明道學與西方形而上學之別看中西文化分野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10-11 19:40
鄧曉芒|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9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鄧曉芒教授
朱熹是中國最後一個形而上學家,在他之後,陸王及其後繼者雖然也吸收了某些形而上學的因素,但已不再有真正的形而上學衝動了。而以朱熹為代表的宋明道學最典型地揭示了儒家倫理哲學一旦提升為“倫理學之後”,所可能呈現出來的比較完善的理論構架,但也暴露了自身的問題。這些問題通過與西方形而上學的比較可以大致看出來。本文將考察道學與西方形而上學在有與無、知與行、言與意這三個最基本的原理上的異同,並將這種比較深入到具體的中西文化差異。

朱熹
有與無
**中國形而上學從先秦道家以來,經過魏晉玄學,直到宋儒,始終脱離不了“以無為本”的大原則。凡是開始拋棄本無立場而轉向崇有者,均顯示其背離形而上學而下降為形而下之器的趨勢。**這一點,在宋明道學的創始人周敦頤的太極圖中已經看得出來。他把“無極而太極”設定為天理之根源,萬物之終始,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而不直接定為“太極”?這要從“太極圖”的來源來説明。太極圖的前身是道教的“無極圖”,來自道士陳摶(871—989)刻於華山石壁之上的無極圖,甚至有人説太極圖“本名無極圖”。“無極”一詞出於《道德經》第二十八章“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與前文“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以及後文“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兩句相併列,可見“無極”之説本於老子貴無論。但為什麼又要改“無極圖”為“太極圖”呢?因為周敦頤正是要藉此而將道教和道家思想引入儒學。“太極”一詞出自《易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易經》中,太極是最高的,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指的就是太極,以下的兩儀(陰陽)和四象八卦等都是由道所“生”的形而下之器。那麼在“太極圖”中,太極和無極又是什麼關係呢?按周敦頤的説法是“太極本無極也”。(《太極圖説》)朱熹對此解釋得很細緻:“無極而太極,不是説有個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説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朱子語類》卷九十四)“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朱子語類》卷九十五)因此,在“無極而太極”中,“太極”就是“道”,也就是“理”,“無極”則是用來描述“太極”的,它表明“太極無方所,無形體,無地位可頓放”。(《朱子語類》卷九十四)令人想起老子的“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道德經》)整個來説,則相當於對老子“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德經》)的詳解。
**可以設想一下,假如不講“無極”而只講“太極”,又會如何呢?顯然,那就會將最高的太極等同於“有情有狀”的形下之器,而拉不開形上形下的距離。**而當人們成天陷在形下之器中,所有的行為舉止都將是應運而生,因時而動,沒有一個“應當”的標準和維度來評價和衡量,則全部倫理道德都將失去了根據。即使有既定的傳統和道德範例供人仿效和敬仰,也只能是教條式的模仿和接受,説不出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的道德沒有自然模型來參照,就只剩下盲目崇拜和迷信,只能靠動之以情來煽動,甚至靠武力和強制來維持,氣魄再大,也是行之不遠的。所以連孔子也説:“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但他沒有點明,德和禮之所以是不能強加的,就在於它們是講道理的,而且這個道理不是一時一事的行動技巧,而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人人認可的自然之理、天然之理(天理)。這就需要跳出一切存有而立足於虛無之境來看待這個世界和萬物,要從無中生出或推出萬有來。**所以,給“太極”加上“無極”的頭銜實際上是為“太極”加冕,使之不僅代表“存在者整體”,而且提升到“有與無”這一至高無上的層次,這才是形而上學或倫理學之後的層次。也只有在這一層次上,才有可能建立起指導實踐哲學的自然模型。**所以陸九淵要毀掉這一模型,就必須否定“太極”之上還有“無極”。他認為《繫辭》只説了“易有太極”,周敦頤《太極圖説》卻在之上加了個“無極”,“疑非周子所為”,應該去掉。

陸九淵
**雖然在宋代以前,儒家倫理並沒有意識到建立自己的實踐模型的重要性,更沒有着手去創建它,以至於一旦要為自己尋求形而上學的根據時,就只有到老莊那裏去借用;但有時也顯露出了一些自發地到更高處尋找模型的傾向。**這種傾向通常表達為:“天”怎麼樣,我們就怎麼做。如《論語·陽貨》中説,“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只做不説,我也就只做不説了。又據説有人問孔子,為什麼見大水必觀,答曰:“夫水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見大水必觀焉。”(《荀子·宥坐》)這是更加直接地把自然現象當作自己實踐行為的模型了。再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乾卦》)以及“地勢順,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坤卦》)。君子效法天地,剛健而寬厚,因而“天行”和“地勢”都可以看作君子德行的模型。所以張岱年在講中國哲學的人生論時説:“中國哲學的文章與談論,常常第一句講宇宙,第二句便講人生。更不止此,中國思想家多認為人生的準則即是宇宙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表準;關於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關於人生的根本原理。”這話不但適用於儒家,也適用於道家。這隻要看看《道德經》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慾,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即可明白。但由於儒家沒有專門去探討宇宙的根本原理,而只是將這原理當作旗號,所以更常常表達為“第一句”和“第二句”相互對照的方式。試想,如果沒有這些模型,儒家倫理學將失去理據,只剩下情感的感召,在説服力上將受到很大的削弱。一旦添加了模型,儒家的倫理説教就會變得理直氣壯,不容置疑,甚至天經地義了。只是儒家沒有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這些模型上,這成了道家所關注的主要話題。
相比之下,西方形而上學則不需要這一套模型,而是直接去尋找萬物的“開端”,也就是尋找萬物的本原或始基(ἀρχὴ),這就是古希臘阿那克西曼德的名言:萬物由之產生的東西,萬物又消滅而復歸於它,這是命運規定了的。巴門尼德則把這個東西確定為“存在”。到了亞里士多德,則把形而上學的任務規定為研究“作為存在的存在”(實際上是“作為存在者的存在者”)。這裏面至少在字面上沒有任何隱喻、類比或修辭,不是為了轉用於道德實踐(當然也不排除可以貫徹在道德實踐中),而是為了把握萬物的本體(實體)到底“是什麼”;也不是為了加強道德説教的底氣和説服力,而是出於對宇宙萬物的好奇心和窮根究底的興趣。所以黑格爾的《邏輯學》一開始就為“用什麼作開端”的問題殫思竭慮,他的答案就是“純存在”或“純有”。**當然,西方形而上學作為物理學“之後”,也並不就是一種簡單的物理學上的發現或規定,而是一種“反思”性的規定;換言之,不是經驗到了諸多事物都是存在物而歸納出來的結論,而是反思到我們在規定萬物時所必須考慮和運用的概念和方法。**所以在柏拉圖那裏,一切形而上的問題都是“理念論”範圍中的問題;亞里士多德正式建立形而上學則是依靠我們的語法習慣和説話方式作為線索,這種線索本身則被系統化為形式邏輯的“工具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則更是思維和存在的統一體,而這個統一體所展示的則是上帝,“只有上帝才是一切實在中之真實者,最高的實在”,它是“包含有反思在內”的。

《邏輯學》黑格爾著 人民出版社版
這樣一種物理學之後的形而上學,所針對的不是人的道德實踐活動,而是人的思維對萬物存在的把握,所以它的開端必然只能是存在(有),而不可能是無。**如果要從整體上把握萬物,那麼存在或有肯定是第一個範疇,因為它是萬物的最抽象、最普遍的共相。**當然,對於存在着的具體的事物而言,一切哲學範疇都是最抽象、最普遍的概念,例如“實體”“原因”“質”“量”等,不像“動物”“橡樹”之類的概念那樣只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例如,我們可以説,一切存在着的東西都是實體,都有原因,都有質和量,等等。但“存在”範疇比這一切都更抽象、更普遍,因為我們可以直接説,實體、原因、質或量都是“存在”,但我們卻不能直接説,實體就是原因,原因就是質,或者質就是量,這需要進一步論證才行,否則就是“混淆概念”了。“存在(有、是)”在一切範疇中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不僅體現在它比其他範疇更高、更普遍之上,而且體現在,唯有它能充當語句中的“系詞”(“是”),因此能夠用來“説”其他範疇,而其他範疇則只能作為謂詞而隸屬於它之下。
至於和“存在(有)”相反的“無”,在西方形而上學中雖然也少不了談論,但頂多只是作為存在或有的陪襯,它是寄生於“有”之上的,我們甚至可以説“有一個無”。但像莊子那樣説“無有一無有”,這在西方哲學看來是不合法的,因為你只有承認了“有一個無有”,你才能説“無有一無有”,而這與你的前提是自相矛盾的。但這在中國哲學看來很自然,因為並不是我要説“無有一無有”,而是天地萬有本來就出乎無有,連無有本身也一無所有。這與巴門尼德的命題“存在(者)存在,非存在不存在”的意思恰好完全相反,前者肯定無為根本,後者則否定了一切無的可能。莊子在另一處説:“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莊子·知北遊》)這説明“無無”(也就是“使無成為無”)是凡人不可能做到的,因此當他“無有”時,他並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無有是他的第一原則,不可能再去追問它的根據了。在西方,只有上帝才能在一片空無中創造出整個世界來,也就是能夠使無“無化”而成為有;但前提仍然是“有上帝”。所以黑格爾把這種以“有”(有上帝)為前提的“無”稱作“絕對的否定”,在這種意義上,“‘無’的最高形式,就其自為地來説,就會是‘自由’。但就其深入自身中最高的凝聚性並且本身是一種絕對的肯定而言,它就是否定性”。而在道家哲學及中國傳統形而上學那裏,“無”作為“道”的“最高形式”既不是否定,更不是“自由”,它本身毋寧是一種原始肯定的自然狀態。
**但老莊也好,宋儒也好,他們所講的“無”都不是一個孤零零的“無”,而總是和“有”處在某種關係中,對“有”發生着某種本質性的影響。**老莊的無中生有,宋儒的無極而太極,所表達的都是某種特定的無,即能夠化身為有的無,這在《易經》中被概括為一個字——易。據説“易有三義——簡易、變易、不易”(《易緯•乾鑿度》)。簡易是指它作為最高範疇可以概括一切,無須其他解釋而簡明易懂;變易是該字的本義,易就是變;不易則是形容它的貫穿一切的永恆性,《易經》作為“變經”,是永恆的經典。簡易和不易都是引申義,只有變易才是實際的意思,而這變易主要是指由無變有,以無極為太極而“生”出萬物。

《易經》
**變易思想在古希臘也是最古老的哲學思想,從米利都學派的“無定形”(ἄπειρον,音譯作“阿派朗”,派生出另一個意思即“無限”)就開始了。**到赫拉克利特則提出:“萬物流變,無物常住”,“人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所以“我們既踏進又不踏進同樣的河流;我們既存在又不存在”。但從“萬物流變”中直接引出“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有又無),也就是把“變易”看作有和無的統一,這是中國《易經》中的變易思想從未想到要做的一項工作,否則的話,“易”就不會具有“簡易”的意思,而會成為一項“支離事業”了。而赫拉克利特從“變易”中分析出“存在”和“不存在(無)”兩個方面,恰好啓發了巴門尼德對這兩個方面分別進行考察,後者得出的結論是:“一條路,存在是存在的,不可能不存在,這是可靠的途徑(因為它通向真理);另一條路,存在是不存在的,非存在必然存在。”為什麼説前一條路才通向真理呢?因為“能夠被表達、被思想的必須是存在,因為僅僅對存在而言這才有可能”,相反,“決不能證明存在着非存在”。所以,“現在只留下一條途徑可以言説,這就是存在是存在的”。這裏值得我們高度注意的是,巴門尼德在這裏用作判定標準的就是“表達”“言説”,以及與此相聯繫的“思想”和“證明”,因為根據希臘哲學(以及西方哲學)重視“邏各斯”( λόγος,即“話語”)的語言學精神,“存在(是)”本身就是使一切詞彙能夠結合為有意義的命題和語句的不可缺少的紐帶,即“系詞”。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亞里士多德要將“作為存在(有)的存在(有)”設定為他的《形而上學》的核心主題,而黑格爾在《邏輯學》中也要以“存在”而不是“非存在(無)”作為整個體系的開端了。這都是因為,如果不這樣,其他的“話”就都沒法“説”了。而一旦設定了存在(有、是)作為開端,則可以用來“説”任何事物,如亞里士多德説,“我們甚至對‘非有’也説它是‘非有’”。而一旦説開了,則有和無的絕對區別就消失了,所以黑格爾在確定了“邏輯學”的開端是“存在(有)”之後,接下來就説:“但這種純有是純粹的抽象,因此是絕對的否定。這種否定,直接地説來,也就是無。”然而,在這種意義上被直接理解為“無”的“有”是“一個不可言説之物;它與‘無’的區別,只是一個單純的意謂(Meinung)而已”。換言之,“有中之無”是並未在“有”中説出來的,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我將這樣理解的“無”稱作“以有開端的無”。
**在黑格爾看來,儘管有直接就是無,但仍然要將有作為開端置於無之前,理由是無在有中不可“言説”,這是西方形而上學由先天基因中帶來的特色,並不適用於中國的形而上學。**例如,老子《道德經》開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顯然也是把不可道、不可名的常道常名歸於只可意會、不可言説的了,但這並不妨礙老子將“無名”置於“有名”之先。這就定下了中國形而上學的基因編碼,即不可説也沒有關係,你可以在自己心中去玩味,去體會,就像程顥所説的,“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外書》卷十二)換言之,中國的形而上學中,不可説的東西才是最高層次的東西,天理、道、無極而太極,這都是不能説、只能靠自己去體會的東西;或者説,即使説了,也只是“強字之”“強為之名”,(《道德經》)即姑妄言之,然後讓你自己去“得意忘言”、去“悟”。中國古代的“有”並不作系詞用,系詞的功能通常用意會的辦法來充當;因此語言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引發意會,在這方面,“有”和“無”相比並不具有天然的在先性,反而因其可以名狀言説而處於形而下的層次,“無”則屬於形而上的話題。
**當然,中國哲學也並沒有否定“有”,佛家的“假有真空”“五藴皆空”在中國儒道看來也是過於偏激的。**老子也只是説“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宋儒更是隻把無當作有的一個入口處,是建立一個總體的模型所必要的,接下來就埋頭於萬有之理的闡述了。反過來説,同樣,西方哲學自巴門尼德以後也沒有否定無,而是將無理解為一種“否定”的行動而納入“有”之中,使“有”具有了內在的能動性。黑格爾曾反駁中國以無開端的哲學(即老子哲學)説:“如果照這個説法,無真是那種推理的結果,並造成以無為開端(如中國哲學),那就連手都不用轉了,因為在轉手之間,無就已轉為有了。”**我曾就此批評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誤會,因為道家從無到有的推演“不是靠‘轉手’或否定的能動過程,而是靠‘無’這一最高抽象水平的自然下降才產生出來的……這才使無本身也成了有”。**所謂“自然下降”,比如説生殖,通常叫作“化生”。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即黑格爾的體系從有開端並不是他個人的愛好問題,“而是一個由整個文化心理傳統所決定的問題;因為以有開端的無必然是能動的否定,必然是一個東西的自身異化、外化,這才能產生外向、進取、自由的衝力和打破自身限制的哲學,才有反思和向自身的復歸;反之,以無開端的有則只是自然生成(‘忽而自有’),只是在一切外來影響面前保持內心的清靜無為,只是萬有的無區別、無所謂和個體的消融”。“在對‘無’的理解上則必然是:前者理解為運動發展的內在衝力,後者理解為寂寞無為的寧靜狀態;前者理解為分裂、矛盾,後者理解為和諧無爭;前者理解為自由意志,後者理解為自然無慾或扭曲意志(‘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以無開端的有和以有開端的無是中西兩種不同文化結構的模式,而之所以形成了這樣兩種互相顛倒的模式,是因為相對而言,西方文化所立足的是認知和科學,中國文化所立足的是行為和德行。這就必須從知與行的關係來理解這種差異。

黑格爾
知與行
我曾講過,**中國形而上學本質上是一門實踐哲學,即“倫理學之後”,只不過採取了一種認知哲學的“模型”而已。**它即使涉及了一些認識論問題,也不是為了藉此來追求“真理”,以便獲得與客觀世界相符合的知識,而只是為了給人的倫理行為尋求某種宇宙論的根據和認知上的辯護。在老子那裏,提倡一種反智主義,主張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道德經》)在認識論上只限於一種“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的直覺觀照,只要憑藉這種觀照,就能“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直擊形而上的本體;相反,“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道德經》)到朱熹,則主張“事事物物皆有個極,是道理極致。蔣元進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先生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只是個極好極善的道理”。(《朱子語類》卷九十四)所以凡有一物,必有一理,此理號稱“物理”(陰陽動靜之類),其實乃是倫理(仁義誠敬之類)。因此當他鼓吹“格物致知”,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工夫”時,常令人誤解為認識論上的經驗主義。其實與客觀事物的知識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是通過待人接物而懂得在君臣父子的倫理體系中學會如何“做人”的道理而已。格物是為了窮理,即懂得“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語類》卷九十五)用馮友蘭的話説,“朱子所説格物,實為修養方法,其目的在於明吾心之全體大用……若以此為朱子之科學精神,以為此乃專為求知識者,則誣朱子矣”。所以,對於朱熹的“無極太極”之説中形上形下的關係,不但要從“本末”上來理解,如“理和氣”的關係,更要從“體用”上來理解,即“知和行”的關係。
**與之相反,西方形而上學從一開始就是立足於知識論之上的。**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開篇第一句話説的就是:“求知是人類的本性。”他在比較了各種各樣的知識,如感覺、經驗、技術和工匠藝術等實用的和非實用的知識(如工匠藝術、數學,後者產生於閒暇)之後認為,理論知識比生產的知識更有智慧,而“智慧就是有關某些原理與原因的知識”。其中,哲人的智慧高於一切其他智慧,因為“為這門學術本身而探求的知識總是較之為其應用而探求的知識更近於智慧”。哲人“為求知而從事學術,並無任何實用的目的”,“所以我們認取哲學為唯一的自由學術而深加探索,這正是為學術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學術”。西方傳統的科學精神就是由這種超功利的哲學精神所決定的。而這樣的探求就是“理性”(νοῦς,又譯作“神心”)的功能,“它是思辨活動,它在自身之外別無目的可追求,它有着本己的快樂……這是一種高於人的生活,我們不是作為人而過這種生活,而是作為在我們之中的神”。並且,“只有這種活動才可以説由於自身被熱愛,在理論思維之外,從這種活動中什麼也不生成。而從實踐活動中,我們或多或少總要得到另外的東西”。“因此若以理性為至善,理性(神心)就只能致想於神聖的自身,而思想就成為思想于思想的一種思想……惟全善的神心歷萬古而常單純地以大自我為思想。”這足夠説明,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探討的是“對思想的思想”,即“理性”,而這就是超然世外的“神”。它與人的實踐活動、包括人的倫理生活沒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種純粹的思辨智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肯定也能促進實踐智慧,但那已是第二層次的意義,不足以動搖思辨智慧的獨立自足性。
**這樣的“理性”並非宋明理學家所設想的“天理”或“萬物之理”。理性雖然也體現在萬物之中,但並非萬物的經驗屬性(“條理”“肌理”“紋理”“腠理”),而是思想本身的法則,即邏輯規律。**亞里士多德由此建立起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相當完備的形式邏輯體系。而由於這套體系超越萬物之上的純粹抽象的性質,它就成了運用於具體事物之上以獲得真理的“工具論”,從而形成了西方認識論主客二分的“符合真理論”的格局。到了黑格爾那裏,雖然通過對形式邏輯的辯證的改造而克服了主客二分,達到了認識論、本體論和邏輯的一致,但理性本身超越於感性世界之上的“絕對認知”性質與亞里士多德的“對思想的思想”仍然是一脈相承的,他的《邏輯學》則被看作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前所預先制定的藍圖。在這裏,不需要什麼“模型”來為人的道德倫理活動提供模仿的榜樣和樣板,而是將理性直接運用於物理和倫理之中,只不過這種運用和理性思維本身的規律(即邏輯)在層次上還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正如黑格爾在《小邏輯》§2中所説的:
概括講來,哲學首先可以規定為對於對象的思維着的考察。但如果説“人憑藉思維而與禽獸區別開來”這話是對的(這話當然是對的),那麼一切人性的東西就是因為並且僅僅是因為其憑藉思維而起作用才是人的。不過由於哲學是一種特有的思維方式,通過這種方式,思維成為認識,成為把握概念的認識,所以哲學思維總還是與在一切人性的東西中活躍着的思維、甚至與造就人性的東西為人類性的思維有所差別,哪怕它與這些思維自在地不過是同一個思維也罷。這一區別又與這一事實相聯繫,即:由思維建立起來的、人性的意識內容,首先並不顯現在思想的形式中,而是顯現為情感、直觀、表象的形式——這些形式必須與作為形式的思維區別開來。
**“作為形式的思維”也就是作為邏輯的思維,但不限於形式邏輯,而是辯證邏輯,即概念本身的辯證推演。****這種概念推演與倫理學沒有關係,相反,一旦運用於現實生活,它往往是對傳統倫理學命題的解構。**例如,黑格爾《邏輯學》開端的“有—無”結構在其動態過程中達到了有無的統一,“這種統一就是變易(Das Werden)”。這純粹是一種概念進展,是從有到無、又從無到有的這一回轉過程所形成的第一個“具體概念”。變易概念的自否定成為“限有”(定在),限有則自否定進到“無限”,也就是突破有限的限制。這種對無限的理解還只是一種“壞的或否定的無限”,“這種無限只不過表示有限事物應該揚棄罷了”。黑格爾批評説:“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有限只是應該加以揚棄的,無限不應該只是一否定之物,而應該是一肯定之物。在這種‘應該’裏,總是包含有一種軟弱性,即某種事情,雖然已被承認為正當的,但自己卻又不能使它實現出來。康德和費希特的哲學,就其倫理思想而論,從沒有超出這種‘應該’的觀點。”只有當這種一味否定的無限返回到自身的肯定,才從壞的無限上升到真無限,成為具有無限否定性的限有,即“自為存在”(自為之有)。這就達到了自我意識的主體性(自由),它恰好是對康德等人的“應該”的倫理思想的突破。
我們也可以把黑格爾這種具備了真無限的鋒芒的變易看作對《易經》的變易思想的批判。《易經·繫辭上》説:“《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句可以看到老子“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以及“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德經》)的影子。“易”就是從無思無為到感通天下的過程,但為什麼無思無為就能夠感通天下呢?這裏用了一個否定句:如果不是天下“至神”,如何能夠做到這樣。下面接着説:對於這個“至神”的變易過程,“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對此有人注曰:“‘深’謂深廣難測,‘幾’‘幽’謂幾微、幽微未明。”這些都是神秘主義的説法,意思其實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聖人正在研究着呢!但無論如何,萬事萬物就是這樣從無中生出來的,而一生出來,就帶上了倫理色彩。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經·繫辭上》)
**這段話清晰地展示了人倫道德通過天地萬物的變易而來的過程。**然而,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與尊卑貴賤男女和賢人之德究竟有什麼關係,這裏其實並沒有論證,也不需要論證。這是現成的教義,它只是告訴人們,什麼叫做“天經地義”,什麼叫做“不易”之理。後面講無思無為感通天下,倒是有點要説一説這個“天下之理”是如何來的意思,但卻歸之於“至神”和“幾微”。總之是你信就行了,不信你會遭詛咒。這裏提供了一個倫理教化的模型,如果你想做個“好人”、君子,就“應該”把自己的行為往這個模型裏面套,不用問為什麼。但這也未免過於“簡易”了。
**黑格爾不可能認同這種“應該”。**他連康德、費希特那種用純粹實踐理性推出來的“應該”都看不過眼,而偏要在客觀事物的變易法則和自我意識的主體性(這是一切真正的倫理法則的前提)之間找到過渡的中介,而不能用此岸和彼岸的對立來隔絕它們。在《精神現象學》中,由變易而來的真無限性正是通往自我意識的中介:
無限性或者這種純粹自身運動的絕對不安息,即,凡是以某種方式,譬如説,作為存在而被規定的東西,毋寧都是這個規定性的反面,這種不安息雖然已經是前此一切階段的靈魂了,然而只有在內在東西中它自身才自由地顯露出來。現象或力的轉換本身已經將它顯示出來了,但是它首先是作為解釋而自由地顯露出來的;並且由於它最終對意識而言才是對象,才是它所是的東西,於是意識就是自我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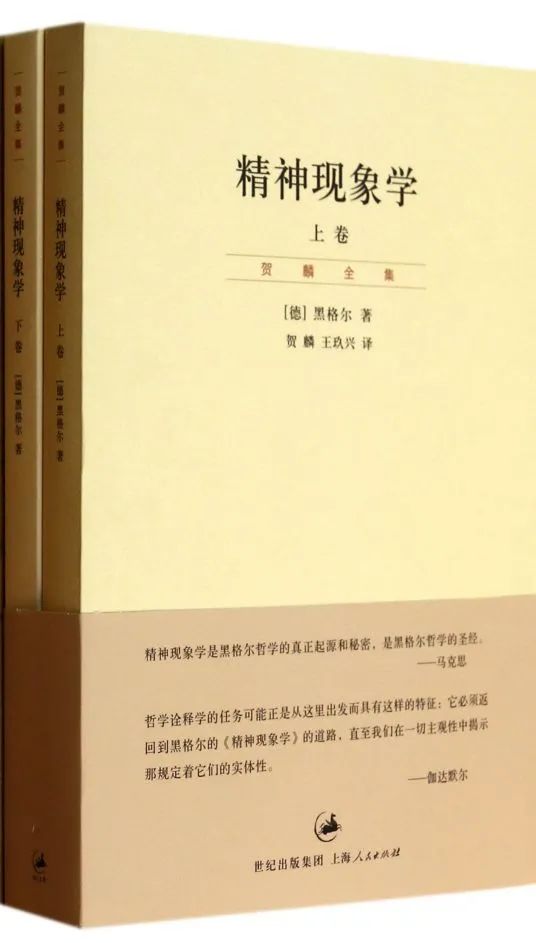
《精神現象學》黑格爾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絕對不安息”就是絕對的變易。這不僅僅是從無到有的生成,而是每個存在之物向自己的反面轉化。它最初顯現為現象或力的轉換,但只有在“內在的東西”中才不受外部干擾地顯示出來。這種顯示最初是作為觀察者從外部所作的“解釋”,但其實它只有對意識而言才是對象,觀察者對於對象變易的解釋其實就是觀察者自己內部的變易,意識就成了自我意識。被康德推到自在存在中去的東西,現在就被黑格爾納入了自我意識之中,成了“自為存在”。“由於這種無限性的概念是意識的對象,所以意識就意識到這區別同樣是直接被揚棄的東西;它是本身自為的,它是對無區別者的區別,或者説,它是自我意識。”而在《易經》中,變易的原因始終只是自在的存在(自在之物),但它不像康德那樣歸之於“不可知”,而是歸之於“不必知”。因為,是否能從科學知識上對這種變易加以認知,這對於倫理行為而言並沒有任何影響。而從道德實踐意義上對它的認知則是每個人生來已經到手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天德良知”。所以《易經》通過變易而顯示的倫理規範僅僅處於意識水平,而未達到自我意識。
黑格爾説:“要認識意識通過知道它自身而知道些什麼,還需要多費周折”,其中跨出去的第一步,就是要意識到“自我意識就是慾望一般”。這正好是宋儒包括明清以來的儒家以“存天理,滅人慾”為旗號努力要排除掉的。為什麼要排除掉?就是因為個體的慾望(私慾)與既定的倫理秩序(天理)相沖突。沒有人想到可以通過理性和邏輯來擺平各個個體的私慾之間的關係,從而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上重新建立一種講道理的倫理秩序,這只是西方文化的套路。而這種中西文化的差異,又可以追溯到對知與行的各有側重:西方文化看重的是邏輯理性,無論是科學精神還是倫理思想,都必須以邏輯理性為基礎,因而必須把“美德”建立於“知識”之上(蘇格拉底);而中國文化看重的是實踐效果(荀子《儒效》),在既有的社會狀態下效果好的倫理原則不用認識,只須誠心接受和情感認同,被奉之為“天理”“天道”或“太極”來遵守。
言與意
**可見,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是建立在語言即“邏各斯”之上的,沒有對語言以及語言規範(邏輯)的重視,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以及後世一切形而上學的構想都是不可能的。**其實,早在巴門尼德那裏,“言説”就已被當作“存在物存在”的證明了。“我也不能讓你這樣説或想:它從非存在物中產生。因為,存在物可以不存在,這件事是無法言説和不可思議的”,所以必須把這條途徑“當作不可思議、不可言説的途徑拋在一邊(這確實不是真正的途徑)”,沿着這條思路“是什麼都學不到的,因為你既不能認識非存在(這確乎是辦不到的),也不能把它説出來”。即使你在語言中固定了某些名詞,如既存在又不存在、變易等,都只不過是空洞的聲音,是無法言説的。為什麼無法言説?是因為缺少一個系詞“是”(存在)。
正因為如此,亞里士多德把“作為存在的存在”(作為是的是)定為他的《形而上學》的核心問題。今天的人(特別是在海德格爾以後)更傾向於把巴門尼德的“存在存在”譯為“存在物(或存在者)存在”,把亞里士多德的“作為存在的存在”譯為“作為存在者的存在者”,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顯然忽視了他們的“存在”作為系詞“是”的重要性。我們無法理解他們的“存在者”為什麼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因為沒有存在者,我們仍然可以研究很多其他的東西,如理想、信仰、幻想、感情、美,還有非存在者、無等。但是如果沒有“是”,這一切都不用談了。“是”作為一切言説的根才是亞里士多德把“作為是的是”定為《形而上學》的主題的更根本的原因,所以每當他遇到需要解釋的問題時就擺出證據,看看我們平常是怎麼“説”這件事的,也就是説,我們通常是怎麼對這件事説“是”的。當我們只説一個字,例如我説“家”,這還不能算是言説,因為這個單詞的發音如果不聯繫其他的發音是沒有意義的(別人甚至不知道你説的jiā是漢語還是其他語言,同一個“家”的發音,德語中是“Heim”,英語中是“home”,都不一樣);只有當你説:“這是我家”,或者説“家是温暖的”,這才成“話”,才有意義。
古代漢語一般不太把“是”當回事。《説文解字》曰:“是,直也,從日、正。”以日為正,當然是肯定的意思,“正確”或“對”的意思,如説“實事求是”“是非對錯”;或用作指示詞,如説“是日”“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相當於“此”“這”。可組合成“是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謂”(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惟……是……”(唯利是圖、唯道是從)。偶爾也有作系詞(A是B)的用法,如“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崇有論》)但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省掉系詞“是”,而用兩詞接續的方式表示:“A,B也”,如説“虛無,有之所謂遺者也”,意思完全一樣。但古時不用標點,後一種説法更需要敏鋭的意會能力,而這是中國古代哲人的強項。所以,當中國人讀到老子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即使無標點,在句法上也絲毫不會感到困難。試譯作西文,若不準用“是”字(如英文的is,德文的ist),則是根本無法看懂的。
**所以,中國古代哲學和形而上學不是很在乎句子的邏輯清晰性,所重視的更多是詞彙內涵和隱喻的深度。**由此而有莊子“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之説。《易經·繫辭上》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對言、象、意三者的關係,是以“言”和“象”作為激發出“意”來的引子,一旦得意,即可忘象忘言。**所謂“忘”,並不是要廢掉它們,而是不要執着於言象這些外在的聲音形象,不去追究它們的邏輯關係,而是要藉此沉入內心,玩味體會,才會豁然開朗,彰顯真諦。**宋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五有:“此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雖然“不待明言之”,但已有“絕句”在;絕句“極佳”,佳在何處?不在言中,而在“言外”。言外之意是什麼?這裏講的是“幽怨之情”,其實也可以是幽微之幾、玄妙之門,“陰陽不測之謂神”。(《易經·繫辭上》)雖然“神無方而易無體”,但它卻可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同上)就是説,代替語言的是行動,易道體現於人的德行中。而德行則發乎人內心深處與易道玄通。後面這層意思在《易傳》中未能展開,因為儘管點了一句“形而上者謂之道”,但接下來講的全是形而下之器(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錯之)。因為此書的性質是對一部占筮之書的解釋,注重的是聖人在治國之術方面以及君子在臨事決策方面的可操作性(吉凶)。至於對人的內在心性的體驗方面,則是儒家“道統”(子思、孟子等人)所關注的重點。
**而在宋明道學中,則是將這兩方面融為一體了。**朱熹的一段話正可以説明這種融合的模式:“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衝穆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太極圖説注》)形而下之器是“以其著者觀之”,其中有動靜陰陽之區別,有區別就有可操作性;形而上之道則是“自其微者觀之”,雖然“衝穆無朕”,但已隱含其理於自身中。所以,太極、道或理就是那無形中打通雙方的“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説卦》)之所以如此之“神”、如此之“陰陽不測”,正是因為“太極”就是“無極”。“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載,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也正因為理之無方所無形態,無乎不載而“無聲臭影響之可言”,所以顯得十分神秘。雖説是“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朱子語類》卷九)但“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朱子語類》卷五)所以他又説:“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朱子語類》卷四)理“無所湊泊”,不能從聲臭影響來説它,雖然要“附着”於氣即言語動作等之上,但本身畢竟不是氣,因此不能用言語等來窮盡之。由此而生出朱熹所謂“格物窮理”之論: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大學章句》)

《大學章句》
**這裏無形中吸收了佛教的由漸悟到頓悟的方法。正是因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大禹謨》)是極為困難的,沒有這套格物致知、從漸悟到頓悟的工夫,根本做不到。陸王心學認為朱熹這一套日復一日的“工夫”實在是過於“支離”了,不如“用敬”而頓悟,畢其功於一役。其實,理學與心學雖然在“工夫”如何做上背道而馳,但出發點卻是一致的,即萬理在一心中。正因為萬理具於一心,所以朱熹認為應當從萬物中一件一件去“求放心”,像孟子所説的:“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而陸王則恰好認為,既然萬理已具於一心,所以不須外求,反身而誠即可,這也是孟子説的“: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比朱熹小十幾歲的南宋理學家陳普的詩《孟子·求放心》綜合了這兩種境界:“放豚無跡竟西奔,着意追求孰用功。惟必操存能主敬,依然不離這腔中。”如何能夠單靠“主敬”就收回“放心”?陸王偏於居敬守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庸》第十九章)但對這段話的理解,朱熹的意思是要下足工夫,你不是聖人,只是“誠之者”,所以做不到“從容中道”,而必須“擇善而固執之”。**他説:“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慾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中庸章句注》)王陽明則放言:“滿街都是聖人!”(《傳習錄》)意思是,誠與不誠在乎一念之間,只要你心誠,你就和天道合一了。當然,其實也沒有那麼容易,按王陽明的意思,還得“破心中賊”,而且很“難”。只有破完了,剩下的才是“聖人”之“誠”。區別在於,朱熹下的是在外面致知窮理的工夫,王陽明下的是在內心做清潔的工夫。但兩者都要“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大學章句注》)
**但究竟什麼是所謂“天理”,始終是神妙莫測的。**朱熹認為《大學》“格物,不説窮理,卻説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朱子語類》卷十五)物固然離不得理,而理卻有時離物;離物,則無法言説,不可捉摸。朱熹有時又説:“有是理便有是氣”,“理未嘗離乎氣”(《朱子語類》卷一)似與此處矛盾。但此處討論的是“言理”“言物”,彼處則是就有無立論,“有是理便有是氣”,但“有理”不見得能夠“言理”,這裏其實並無矛盾。所以他説:“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朱子語類》卷七十五)言理只有從事物上可言,就理本身則不可言。**因此他所謂“理事無礙”只是就本體有無來説的,而在言説表達上恰好是有礙的,具體事物之理可知,統一的“理本身”則不可知、不可言。雖然不可言,但卻可行,因為“行”屬於“事物”。我説不出來,但我可以做給你看。**朱熹經常拿莊子的“庖丁解牛”來比喻“即物窮理”,陳榮捷説,朱熹在《語類》中六次引用莊子的“庖丁解牛”,“藉以説明理之得名,理之會通,徐徐觀眾理,隨次漸進,養生之術,無適而不見仁見義。舉凡理這觀念,為學之方,與修養之道,皆可於庖丁解牛而得”。庖丁由技而進於道,經過多年的實踐才做到“依乎天理”,最後“終於突破了對於事物的表象直觀,而達到了對於內在於事物的道或理的把握。這也就是格物致知的根本精神”。**但試問,庖丁能將他所把握到的道或理説出來或告訴別人嗎?顯然不行。**文惠君自以為“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矣”,(《莊子·養生主》)其實未得,除非他自己花幾十年也去經歷一番,否則正如斫輪老手七十年的經驗也無法傳給自己沒有這番經歷的兒子一樣。(《天道》)難怪程顥慨嘆“天理”只能“自家體貼”出來,別人説的都不算數。這些都説明,如何得天理的過程固然可以説出來,但天理本身無法説出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所以還是“言不盡意”“意在言外”。
宋明道學和西方形而上學的比較,頭緒眾多,話題紛擾,糾纏不清,但大體説來,**不外乎上述三個層面,從有無、知行、言意三對概念中,透露出來的是中西哲學各自不同的傳承理路和文化背景。如宋明道學在有無關係上主張以無開端的有,西方形而上學則只相信以有開端的無。**這是因為中國文化所立足的是行為和德行,而西方文化所崇尚的是認知和科學。正因為如此,**在知和行的關係上,道學的形而上學本質上是一門“倫理學之後”的實踐哲學,**它即使涉及一些認識論問題,也不是為了追求“真理”,而只是為了給人的倫理行為尋求某種宇宙論的“模型”;西方形而上學則把“對思想的思想”看作哲學的最高目的,即超感性的神。而這樣一來,在言和意的關係上,西方形而上學的理性精神骨子裏是一種語言的“邏各斯”精神,它通往上帝的聖言,只能是意在言內,講究的是邏輯的清晰性;而道學的精神則是意在言外,無論理學或心學,都是如此,將語言的隱喻性發揮到了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