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哇,餘華都給朱一龍新片點了贊_風聞
Sir电影-Sir电影官方账号-10-23 08:38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
恭喜華語電影。
又喜提一部高票房水平的電影,首日票房就已經超過5千萬。

Sir不是在説反話。
要知道,這部電影能如此出圈實在不容易。
雖然,有着餘華小説改編的光環,有着朱一龍演員的流量。


但,加上青年導演的名字“魏書鈞”。
味道就不一樣了。

△預告片這字幕配得“恰到好處”
説實話,這部電影Sir看了。
可以非常篤定地説。
這部電影是現今年輕導演“幹翻”商業片的最好“投名狀”。

相比於那些靠營銷、靠話題,在爭議聲中回本的電影,它更能代表新一代國產文藝片該有的樣子。
以及尊嚴。
畢竟,在國產商業片導演集體“隱身”的時代。
它可以證明。
電影,不該是八面玲瓏、投其所好,它該有自己的表達,有自己的風格,每一個寫上“某某某導演作品”這幾個字的導演,都該對得起“作品”這兩個字。
哪怕,它不會獲得滿堂喝彩——
河邊的錯誤

01
誰是瘋子?
1987年,26歲左右的餘華寫下了這篇非常先鋒的小説。
一部戲仿的偵探故事,《河邊的錯誤》。
故事説是小鎮刑警馬哲,碰上了一則棘手的連環殺人案,兇手開始鎖定了當地的一個不明來路的瘋子,可最後,馬哲才發現,“瘋”的另有其人……
你可以將這部小説,看做是一部披着偵探外皮,內裏卻着重描寫情緒、心理的氛圍流故事。
幾年後。
這個小説被張藝謀相中,買下了版權後,卻囿於不知道怎麼改小説劇本,遂放棄。

可就在接洽的過程中,他看中了餘華的另一部小説,拍出了電影——《活着》。
更符合那個時代下,張藝謀的口味。
那麼《河邊的錯誤》呢?
版權幾經轉手。
最終,等來了兩個“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後生。
不僅把電影改出來了,還改出讓餘華高度讚賞的評價:幹得不錯,祝賀你。
這就是本片的導演魏書鈞,和編劇康春雷。
當然。
劇本剛拿到手時,康春雷也犯難,沒能找到劇本的抓手,直到,他們發現了這本小説集的序言裏有這樣的一句話:
命運的看法比我們更準確。

而這個故事的改編,也是以這句話展開的。
在餘華的小説裏,對於命運的看法向來是悲觀的,最典型的,《活着》。
當福貴看着龍二被綁着押送刑場,聽着五聲槍響,他被嚇的尿了褲子。回到家裏對媳婦兒説——
那院房要是不輸給龍二
這五槍打的就是我

福貴因為沉迷賭博,卻又被留了一條命,這種發自內心的一種小人物式的慶幸,以塞翁失馬的心態,樂觀地接受着自己註定“貧窮”的命運。
其實,命運要比我們走得更遠。
在《河邊的錯誤》裏,也有極強的,關於命運的暗示。
就説一個細節。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馬哲的那輛紅色轎車的車牌。
上面給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提示,渚31415。這行數字眼熟麼?
π≈3.1415.…..圓周率,一個無限不循環的無窮小數。
它無限趨近於,但,卻永遠不等於。
這也暗示着馬哲,永遠接近於真相,但,卻無法真正找到真相;他所困的案子雖然結束了,可,他腦海裏的幻覺,卻永遠不會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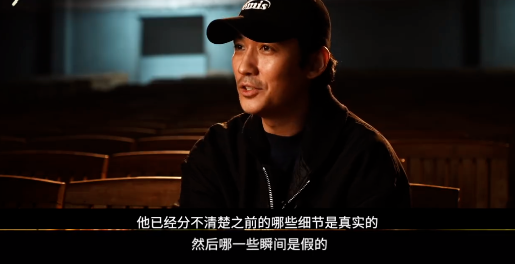
這部電影像是在談論每一個逃不開命運的人,宛如倉鼠一般,永遠在籠子裏不停地跑下去。
《河邊的錯誤》的定調與內容,就已經註定是一部逆流而行的電影。
就看它剛拿下了第7屆平遙電影節拿下費穆榮譽最佳影片,迷影選擇榮譽獎;
走上76屆戛納電影的紅毯,入圍一種關注單元提名;

甚至還走入各大高校巡演,就連發出的幾則花絮,都是在認真談論文學,討論電影拍攝。
它就是要告訴觀眾,這部電影,它就不是一個主流的、商業的、大眾的、娛樂向的電影。
而是一部鏡頭語言非常有張力的,作者性電影。
在電影裏,有着許多可以深度解讀的細節——
比如説,鏡子。
在電影裏,鏡子的作用,其一,就是人物內心的真實映襯。
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
電影中,有時虛實混亂的場景下,坐在鏡子對面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反而是他們內心最想説的話。
比如,許亮。
在第一次與警察見面時,他坐在鏡子前面説的那些奇怪又模稜兩可的話。
開始還覺得這個人,挺奇怪,彷彿是盼着警察快點把他抓走。
但,看才知道許亮的某些癖好,不允許被公開。
而他坐在鏡子面前説的那番話,你完全可以看做是他此時的一個自白。
他經歷了什麼,表面沒有説。但,他內心只想在此時求個了斷。

當馬哲與妻子在卧室裏,討論未出生卻被檢查出有可能智力發育問題的孩子,去和留時。
他宛如一個被手銬銬住的“犯人”,在鏡子面前開始自己的剖白。

再比如説,瘋子。
影片確切的嫌疑人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瘋子,於是電影的後半段,有不少情節所説的,就是抓捕瘋子。
但,電影裏的瘋子,只有一個人嗎?
一個例子。
馬哲在射殺瘋子之後,鮮血噴濺到牆上的鐘馗捉鬼圖上。
鍾馗是鬼,捉的也是“鬼”。
所以這一場鬼捉鬼,馬哲是真的捉到了瘋子嗎?

他記得自己開了4槍。
可子彈卻一發沒少。
他捉的是瘋子,還是瘋子就是他?

電影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反而是在用蛛絲馬跡,去讓觀眾沉浸在電影中,體會人物驚恐、瘋狂的情緒。
讓人去想。
那一次次的死亡事件,受虐癖的老人、不“現實”的詩人、異裝癖的理髮師、沒有顧忌的小孩……殺死這些“異類”的,只是一把可以觸摸的,有實體的刀嗎?只是某一個瘋子嗎?
它與其他的類型偵探片不同,這些偵探片裏最後總有一個兇手。
但,這部電影裏,它偏偏就讓故事變得越發玄乎,甚至偏離了正常軌道,而將觀眾一同帶入了馬哲的“瘋子”世界。
答案是什麼?
不重要。
就連《河邊的錯誤》裏的“錯誤”,到底是什麼錯誤?
是馬哲的錯誤?瘋子的錯誤?還是時代、羣像的錯誤?
餘華在小説裏沒有給出答案,魏書鈞在電影裏也沒有給出答案。
答案,需要你們自己去看。
02
逗你玩
坦白説,Sir之所以喜歡《河邊的錯誤》不在於它的藝術水平有多高,而是在當下華語片的範疇裏,它很難得地讓我們看到了視聽、藝術,以及作者性較高水準的結合。
什麼是作者電影?
通俗來説,就是明顯具有個人風格特徵的影片,讓電影具有獨特的語言、可以自由表達思想和情感的工具。
《河邊的錯誤》,正是一部非常典型,也非常到位的作者電影。
但。
與上一輩追求藝術風格的作者電影不同的是,在魏書鈞的電影裏,風格本身不重要,怎麼表達才重要。
簡單來説。
他其實一直在追求“在****場感”。
他在改編故事的時候,不僅僅是將故事描述清楚,還要將這個小説帶給自己的感受,通過電影傳達出來。

可以説,這部電影就是魏書鈞的一種表達。
舉個例子。
比如,從電影剛開始,公安局局長就讓馬哲把辦公室,搬去一個廢棄的電影院裏。
這是小説裏沒有的情節。
但因為將辦公室場景,挪上了電影院舞台。
給人的感覺,就變成了,宛如一場戲中戲的開始。

這種設定是非常大膽的。
包括後來馬哲坐在觀眾席上的位置,以及夢中的電影裏出現了殺人案的“真相”,它有意地擴大了這部電影的荒誕性,戲劇性;以一種戲中戲的方式,讓畫面、故事,變得更不真實,甚至於,還有一種隱喻:
這個世界,本就是一場真假莫辨的大戲。
為什麼這麼做?
其實就是導演對觀眾觀感的一種干涉,他告訴我們,這是一部電影,故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説了什麼。
這樣的設計其實四處可見。
比如一開場,很多人會發覺,怎麼這部電影是那麼的“不清晰”?
原因,是導演使用了16毫米的膠片在拍攝。
在成熟的工業體系內,這並不是主流的格式(一般都是35毫米),16毫米的素材在監視器上呈現的效果看着都非常模糊,導演也無法調整演員的面部表情微表情,但魏書鈞為什麼這麼做?以至於到後來,你甚至能在影片裏發現明顯的噪點?
導演的解釋是。
他需要16mm所表現出來的年代感。

只是如此嗎?
其實這也對觀眾的提醒,正如那一個個主觀鏡頭——
兇案發生時,柴刀直接伸進了鏡頭中,讓觀眾不是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而是以主觀視角,一位“參與者”,進入這種恐懼之中。

或者電影幾次讓演員直接望向鏡頭,讓演員們也成為“審視者”,與觀眾在畫面裏直接交談。

導演並不想讓觀眾沉浸在一個兇殺案偵破的故事裏。
而是抽離出來。
看看這個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
這樣的“冒犯”,並不舒適。
但,他就是要讓觀眾通過不舒適,而去直面這部電影裏的情緒。

你無時無刻地會感知到導演對於這部電影,有着自己獨到的,甚至,驚奇的靈感火花。
很顯然。
魏書鈞在自己其他的作品裏,也有這樣明顯的“在場感”。
在《野馬分鬃》上映後,周遊評價魏書鈞是:
他有時感知的不是鏡頭面前的演員,而是整體環境,甚至後面的一輛列車,或是窗簾上的一個洞,或者是一陣風。
他不是隻坐在監視器面前。
而是,無處不在。
還記得在《永安鎮故事集》裏,有一隻流淚的眼睛,意外出圈。
這並不是演員隨意畫在玻璃上,被偶然抓拍下來的畫面。
而是導演與製作團隊測量車內温度,用加濕器升高車內的濕度,最後,實驗了許多版本後,終於拍出了一隻“恰如其分”的眼淚。

雖説這個細節非常刻意。
但,卻是導演此時特意留下的一句話,一種情緒。
《河邊的錯誤》裏,也有如此刻意之處。
還記得在電影裏的兩處相聲麼,一個是侯寶林的《醉酒》。
説的是兩個醉漢,其中一個對另一個説,你證明自己你沒有喝多,那就順着手電的光柱爬上去。另一個説,我爬上去,你一關燈,我不就掉下來了。

另一個是馬哲與瘋子在小飯館裏,在廣播裏聽到的馬三立的《逗你玩》。
小偷想偷一户人家門口晾着的衣服、被子,可門口卻有個看着這些物件的小孩,小偷跟小孩介紹自己叫:“逗你玩”。
每當他偷一件衣服的時候,小孩都會報告媽媽,“有人偷衣服了”,媽媽問:誰啊?小孩答:逗你玩。
在編劇康春雷在設定人物時,就已經想好了這兩部相聲。你可以認為這是他們二人,都是“瘋子”、“醉漢”;他們之間的追逐遊戲,不過就是逗你玩。
但,也有一種感覺——
在你越發認真地想從電影裏,找蛛絲馬跡想尋得答案時,導演就越是“逗你玩”。
他在與觀眾玩着另一種“貓捉耗子”的遊戲。
他想要給的,不是答案。
而是一種體驗。
讓觀眾去在電影裏獲得、感知,在電影中,變得敏感。
這也是我們現在國產電影市場所欠缺的。
03
就是要幹翻
一個很顯而易見的現狀是,當下的華語片裏,“電影”這個詞越來越不重要。
甚至不是老馬所説的film和cinema之爭。
在國內。
是“電影”和“小品”、“視頻”、“社會新聞”同台競技,是新導演的作品拍出來,你往往搞不清,它究竟該屬於哪一類,是名導們的作品,要麼是被刪得支離破碎,要麼就成為命題作文,用自己的名字背書。
導演這個職業逐漸隱身。
變得沒名沒姓。
但。
讓人尚存希望的是,在這一年裏,我們其實看到了許多青年導演,帶着非常犀利的作品出現。
像是,孔大山的《宇宙探索編輯部》作為第五屆平遙電影展的費穆榮譽最佳影片,依舊是以一種偽科幻、純文藝片的拍攝,成為國產電影裏的一匹黑馬。

而對於同在平遙獲獎的魏書鈞來説,《河邊的錯誤》也終於成為了他“幹翻”國產電影的最好力作。
也許這些作品還不夠完美。
但Sir看中的是,這一代90後的青年導演,他們極強的自我表達。
他們往往不管不顧——
比如在這兩部電影裏,他們都加入了詩歌。
甚至,在《河邊的錯誤》裏,還特地請來了莫西子詩飾演電影裏的“宏”。


詩歌的運用,可以是一種文化壁壘,讓觀眾進入電影產生困難;但,詩歌也是一種渠道,它讓那些被觸動的觀眾,迅速進入導演所描繪的場景中。
這種方式雖然會讓電影更有走入“小眾門檻”之嫌。
但,也是如今難能可貴的一種美感。
他們往往會“以下犯上”——
就像“00後整頓職場”。
在魏書鈞的這三部作品裏,都有把“心要野”刻在明面兒上的勁兒。
《野馬分鬃》裏,他讓周遊飾演的阿坤,坐在教室裏懟老師,還當着老師的面,撕碎教科書,親自給老師上了一節擬音課;

《永安鎮故事集》裏,導演戲裏戲外,都繞不開“華語電影”的偉大復興;

《河邊的錯誤》,用一顆小小的乒乓球,貫穿了馬哲的生活。
它可以是胚胎,是責任,是比賽,也是榮譽。

縱觀魏書鈞的三部電影,他有着太濃厚的“迷影”氣質。
從做電影、拍電影、最後融入電影,這三部作品裏都離不開“電影”這個主題元素。
甚至,這三部電影拍來拍去。
拍得還是他自己。
從中傳的音響導演專業畢業,他將自己大學時的感受,化成了《野馬分鬃》裏的左坤;拍電影過程中的糾結與無奈,融入了《永安鎮故事集》裏被架着下不來台的導演;在《河邊的錯誤》裏,他又將人與電影的虛實混淆,讓馬哲難辨真假。
魏書鈞在三部長片裏,都毫無保留地投入了自己對電影的痴迷。
而這種“痴迷”,在如今的電影市場中太難得了。
所以説到底。
Sir想要支持的其實並不是《河邊的錯誤》這一部電影,也不是魏書鈞這一個人,我們為之搖旗吶喊,為這些有瑕疵的年輕人搖旗吶喊,其實也不過是厭棄了這個商品化、程式化、大數據化的環境,厭棄了這個無限討好每一個觀眾的市場。
就像豆瓣上,《河邊的錯誤》下有一則高贊評論:
拍電影不能讓觀眾試圖理解你。
Sir反而覺得,如今的國產片所缺的,恰恰就是一些能讓觀眾能去揣摩、思考電影內核的作品。
我們需要能“磨一磨”大腦,不被規定,不被輕易解讀的作品。
甚至,可以有更多不同理解、看法的電影作品。
還記得在蘇珊·桑塔塔的《沉默的美學》裏有這一樣的一句話:
**“如今佳片的重要特徵(比任何時候都突出)就是獨樹一幟,**而商業片卻採取了過度膨脹、墨守成規的製片方式,無所顧忌地組合或再組合,以圖再現昨日的輝煌。”
這句話放在當下的國產電影創作環境裏,非常合適。
在這個“作者”沒名沒姓的時代。
能讓像是《河邊的錯誤》這樣的作品留下來,很不容易。
而這些後浪導演。
就是在幹翻着國產電影裏墨守成規的模式,一成不變的講故事模式,與固定的審美習慣,雖然莽撞,但他們卻依舊用着不撞南牆不回頭的精神,跟一切“看扁”自己外界死磕着。
所以“作者”死了嗎?
“電影”死了嗎?
在《河邊的錯誤》裏,Sir看到這樣一個細節。
一羣人在拆電影院的招牌,忽然,“電影”兩個字重重地掉了下來。
使得路過的人驚了一大跳。

這下算毀了吧?
但仔細看。
幾經翻騰之後,這兩個字,依然完好如初。
這就是魏書鈞的態度。
電影沒那麼容易死,所以,我們也不必以曾經的“經驗”倚老賣老,更不必寄希望於重現“昨日輝煌”,甚至不必過於悲觀。
因為只要這羣年輕人鋭氣還在。
未來。
自會走出他們全新的路。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點擊閲讀往期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