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火的特產,拼手速還得靠運氣_風聞
福桃九分饱-福桃九分饱官方账号-同名微信公众号:futaojiufenbao。10-28 19:20
寒風乍起,黃葉滿地。北京的秋天,就這麼毫無徵兆地來了。在這個簡短、彌足珍貴的時節,全北京城最難買的特產也開始登場了。
高碎(也叫高末),這種一斤四五十塊的茶葉末,別看其貌不揚便宜大碗,要是沒買到,真錯過了就是一整年。


“店裏的高碎全都賣完了,您明年再來吧。”
每年高碎開賣的時候,都是店裏售貨員最費嘴皮子的時候。
等着盼着熬過了一年,饞這口茶的大爺大媽們,天矇矇亮就帶着馬紮、板凳去排隊。
早上八點開門營業時,大幾百號的排隊大軍已經從大柵欄排到了前門,這時還得麻煩執勤保安來維持秩序。這場面,誰看了都得記一輩子。2000多斤的高碎,常常不到半小時就能賣光。

© 北京日報微博
前幾年就有“茶蟲子”連跑五家店,排了四五天愣是沒買到的新聞。最後給人家氣到往北京人民廣播電台打電話吐苦水,才從茶友手裏兑了十斤高碎,踏實過了冬。
因為搶購食品上演又燃又炸的場景,有多少年沒在網絡上見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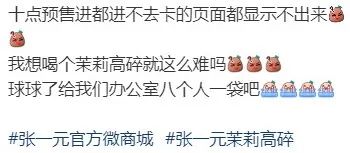
幾十塊一斤的高碎,倒也不是非得藏着捂着,吊人胃口。只是每年八九月份上的新茶,等賣得差不多了高碎才能到貨,而且僧多粥少,有多少都不愁賣。
久而久之,茶葉鋪門外排高末的場面也就成了北京城的一大奇景。

看到這裏,或許有人會問了,高碎究竟有什麼魅力,能吊足北京人的胃口,讓一座城的人痴迷留戀上百年?
問這話的外地朋友,肯定想不到,高碎之於北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特殊存在。
那是一種刻在DNA裏的味覺傳承,也是一種化在骨子裏的羈絆。

高碎(也叫高末)在北京的粉絲基礎,可不是一天兩天積累而成的。北京人對它的迷戀,根源還是在茉莉花茶上。

© 圖蟲創意
北京人喝茶,講究睜眼就要沏滿,喝起來就是一整天。準確地來説,整個北京城的一天,都是從一壺熱茶開始的。

不管五冬六夏,還是寒來暑往,北京人都得趕着腦子清醒前捅開火,確保用一杯又香又燙的釅茶喚醒靈魂。也只有在這股清幽的茶香裏,北京人才能把日子過得調順。少了這點香味兒,幹什麼都好像差點兒事。
所以説,老北京人的血管裏流沒流麻醬,眾口難調不敢妄打包票,但十個老北京人的血管裏,八個流的得是茉莉花釅茶,恐怕只多不少。
這裏名氣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當數老舍先生。旗人出身的老舍先生,從祖上流傳下來的喝茶習慣,到他這一輩喝得更兇了,他確實是一喝一整天。
“有一杯好茶,我便能萬物靜觀皆自得。”

每天六七點沏好茶,八點準時進書房開始寫作,什麼時候寫夠3000字,喝完一壺茶,什麼時候才算完成一天的碼字任務。出國訪問必須帶着大茶缸,裏面還得隨時續着熱茶。
比起高檔花茶,讓老舍更割捨不下,幾次三番都要寫進作品裏的是高碎。
就像《正紅旗下》寫到給自己辦“滿月酒”,因為父親手頭拮据,掏不起幾桌酒水錢,只要抓了大把的高碎沏茶,用“清茶恭候”賓客,也算盡了心意。
這種用高碎沏出的茶,在老舍家裏和他的文章裏隨處可見。
“用小沙壺沏的茶葉末兒,老放在爐口旁邊保暖,茶葉很濃,有時候也有點香味。”
雖不能讓他養出品茶的道行,但也填補了文人雅興。這種茶,幾乎貫穿了老舍的一生,陪伴他的寫作之路從低谷走到巔峯。
在話劇《茶館》中,老舍寫裕泰茶館的王掌櫃要討好秦二爺,大老遠看到對方走過來,就低頭哈腰地迎過去不説,還必須高門大嗓對着夥計喊一聲“李三,沏一碗高的來!”

明着告訴房東:您在我這兒跟他們(普通茶客)不一樣。您懂行會喝,我更會孝敬。
初到北平,一門心思攢錢買車的祥子,只敢喝高碎的大碗茶配窩窩頭。
您看,高末的土著粉絲羣有多廣!上到吃“洋飯”的秦二爺,下到賣苦力的車伕,誰都喜歡喝,誰都喝得起。因為這玩意,東西是好,架子也沒那麼大。
甭管您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大買賣家的東家,喝這個不寒磣,兜裏兩子兒出來混飯轍的,喝這個也不叫敗家。
主打的就是一個眾生平等、一視同仁、以茶會友、莫提身份。
正是因為吃透了這點普世滋味,一輩子讓高碎“醃入味兒”的老舍,才能用寥寥幾筆憑着一杯大碗茶,還原出一個又一個北平故事。
現在的老舍茶館門口,四十多年沒漲價的大碗茶,用的還是他最常喝的高碎。

大概也是因為只有這個味兒才能讓人一口穿越回那個“神仙老虎狗,生旦淨末丑”的老北平。
對它念念不忘的,還有“民國饞人”唐魯孫先生。

這位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吃主兒,受祖上福廕,家裏來自各地進貢的茶葉應有盡有,什麼普洱猴魁都能喝得頭頭是道。中年旅居我國台灣省後,卻格外想念北京的高末。
有一次給台北的朋友煮茶葉蛋,唐魯孫先生心血來潮地抓了一把高碎當茶底,想給他們嚐嚐這種平平無奇的“妙物”,但結局可想而知。
那一刻會吃懂行的老饕頓悟了,茶離了那片土地,味道就會差之千里,人離了那片土地,怎麼回憶都不對。

説了那麼多高碎的門道,到底它是如何拿捏住北京人,又是怎麼成了老北京心中的白月光的?這還要從高碎的出身和逆襲之路説起。
高碎(也叫高末)顧名思義,就是高檔茶葉裏篩出來的碎末。最早賣高末的不是張一元,而是鮮魚口附近的天興居。

改作二葷鋪子之前,天興居前半拉門臉是間大茶館,是專供居住在西南城周圍提籠架鳥的客人喝茶聊天。
掌櫃的恆四和前門吳德泰茶莊的老闆,是嗑過頭,拜過把子的盟兄弟。
每年明前雨前的好茶賣完之後,吳德泰茶莊就會收拾鋪面,把掃出來的茶葉末混合一起,分送給親戚朋友喝着玩。
分到天興居這兒,滿腦子生意經的恆四,喝出了茶葉末是正經好茶掃出來的高檔貨,隨即低價買了不少,沏成了大碗茶,給客人落座時喝。
誰想到這種不買白送的茶葉末一露面,就捕獲了懂茶之人的歡心,不是天天來櫃上喝茶的常客還買不到。再到後來,物美價廉又有品質保證的高末,漸漸傳開了,成為落魄旗人喝茶的首選。
那時候的北京,水質又硬又澀,再好的紅茶綠茶沏出來味道也不對。只有九窖九制,用茉莉花燻出來的花茶才能壓得住邪味兒。

© 圖蟲創意
明末清初,一路從草原邊塞殺到關內的八旗子弟,因為水土的問題,也不得不從喝奶茶改成喝花茶。再到了清末民初,八旗子弟的鐵桿莊稼沒了,旗人架子卻不能倒。
祖上喝奶吃肉的習慣,更是養成了比漢人更愛喝茶解膩的習慣。能一日無肉,絕不能一頓沒茶。

每天早晨洗漱前,家家都要先沏上一壺高末,喝足喝夠了,把五臟六腑都燙熨帖捋順溜,再把熱油條、馬蹄兒燒餅和粳米粥端上來,洋洋灑灑地吃起來。
對吃喝有講究,還好“窮擺譜”的旗人,十個大子兒的茉莉香片喝不起,一個大子兒的高末可是管夠。
別看高末是打掃出來的邊角下料,可揉開了看,滿滿都是茶芯和小芽。

而且沏茉莉花茶講究的是“燜”,頭一道水砸下來,多數茶葉還是沏不開,非要到二道水再燜上十來分鐘,才能把茶泡出琥珀色,燜成香氣撲鼻的“釅茶”。
高碎可沒那麼麻煩。本就是嫩葉茶珠堆的碎末,一道水下去就有色有味,香氣通天。那一口下去有多香,我都不敢想。
隨沏隨喝,不管自家飲用或是待客都不算跌份兒。

還因為身小力薄,稍微見水就飛沙走石,飄得滿壺都是,又得名為“滿天星隨壺淨”。這也無妨,只要小紫砂壺一沏,刺繡的壺套一罩,誰還看得出裏面沏的是吳裕泰還是滿天星。
再説“高碎”(高末)這名字也特別藏拙,到茶館一叫,甭管它有多碎,至少也還佔個“高”字。
沒落的旗人把高碎喝成了家常飲料,平頭百姓又把高碎喝成了精神慰藉。
普通人家過日子沒那麼多説頭,茶味道越濃,顏色越重越過癮。小泥爐子上煨着一壺高末,隨兑隨喝,香味燜得透透的,茶湯沉得紫紅,勞作飯後喝一杯,照樣賽過活神仙。
這種喝高碎的習慣,隨着滿漢通婚的文化交融更是傳遍了四九城。
建國後,接地氣的高末更是成了工人老大哥的心頭好。上了一天班,到家來一搪瓷缸子沏得釅釅的高碎,去火解渴還醒腦提神,故此得名“勞保茶”。

▲50年代吳德泰買高末的排隊人羣
正是有這份幾代人續出來的情分,高碎在老北京人眼中早就不是一種飲料,而是一味專治他們脾氣秉性的“苦口良藥”。
心裏有什麼不痛快、不得勁,一杯茶下去都能換幾分鐘的心平氣和。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放着馬連道茶葉城幾層樓的毛尖白毫不去買,非要點燈熬油地排隊搶幾十塊一斤的張一元。
不是因為喝不起好茶,而是帶點鄉音故情的高碎,喝順了口就再難戒斷。
也幸好,這股“高碎熱”能細水長流。
日久見人心,茶久了也如此。只要高碎一天不退熱,老北京的味道就不會被沖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