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比較》_風聞
平常-无尽世界。11-02 14:25
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
張強
“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專題的任務是對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年代學歷史與現狀作較為全面的總結,目的是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參考。這一專題研究現已告成,並將由貴州人民出版社結集出版,相信它對我國早期歷史的斷代研究會有所裨益。現就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分別擇要述之。
年代學研究的歷史
古代近東歷史傳統上包括兩河流域、北非的埃及以及小亞細亞的赫梯。兩河流域與赫梯的古代文字形式是一種用削成楔形的蘆葦壓印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與形、聲、意兼備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樣,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漸漸被棄用,最終成為無人知曉的“死文字”,人們對這些地區的認識與瞭解也只限於《舊約聖經》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亂、有時甚至是歪曲的記載。自上一世紀初起,隨着近東地區大量泥板文書、碑刻和紙草文書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釋讀成功,塵封了幾千年的兩河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才為世人所知。全方位研究這些古代文明的新興人文學科——亞述學、埃及學、赫梯學的建立,標誌着古代近東各地區年代學研究的開始。歷史學家在建立年代框架的過程中,不斷修正着前人的舊説;在釋讀新的考古文獻與科學化研究手段的進程中,不斷改寫着這些早期文明的起迄。
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發端較早,第一部系統的年代學著作是公元前三世紀末埃拉託斯特奈斯所著的《編年史》。他利用當時在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工作之便廣泛涉獵前人著述,在綜合希臘各城邦不同編年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統一的紀年體系。埃拉託斯特奈斯的後繼者們不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關希臘早期的歷史年代,而且還有所創新。公元前一世紀,卡斯托爾的年代學研究延伸到兩河流域和埃及,並把這些古王國的歷史同希臘羅馬傳統聯繫起來。這種紀年方法在公元四世紀尤塞比烏斯的著作中表現得更加完善。然而,無論哪一種體系都是相對的紀年,也就是説將某一歷史事件的發生確定在另一已知的歷史事件之前或之後的紀年方法。所謂的“公元紀年”,是六世紀著名宗教法規學者小狄奧尼修斯創立的。他根據羅馬的紀年傳統,推算出耶穌基督誕生於羅馬建城後的第753年,這一年即為基督元年,為公元元年。宏觀上講,以公元紀年為座標、一元時空意義上的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絕對年代框架的建立,正是以公元元年為出發點並將羅馬儒略曆向前延至遠古時代的一種時間排序。
年代學研究的現狀
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在構建各自內部年代框架過程中所使用的史料表現出不同的特點:近東地區多為王表、名年官表、碑刻、印章等以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為載體的考古遺存;西方古典則以古代的希臘、拉丁文獻為主。如何利用這些考古遺存和古文獻中所反映出的紛繁複雜的相對年代記錄,並藉助於自然科學手段把它們換算成現行的絕對公元紀年,研究方法上言之,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在這一方面的差異恰恰綜合了我國早期年代學研究中所遇到的難點問題。
現代年代學研究業已表明,世界各古代文明初啓及早期城邦時期有關年代的文獻記載相對匱乏。所以,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者在構建絕對年代框架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是由資料較多的晚期向早期追溯的研究方法。一般而言,年代學意義上的早期與晚期的劃分,是以兩河流域、埃及的公元前三千紀、希臘公元前六世紀末、羅馬共和國早期來分別界定的,至於這些文明地區在此之前的大部分早期歷史年代,年代學者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並以“c.”(拉丁文“circum”之縮寫,意“約”)或“?”等字符來表示某一絕對歷史年代的不確切性以及年代學研究上的無奈。開始於公元前18世紀的赫梯歷史,鑑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兩河流域、埃及等周邊地區的歷史密切相關,這種往來在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中均已得到證實。赫梯整個的年代框架正是在參比兩河流域、埃及年代學研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赫梯年代學這種參比所獲得的年代值很大程度上倚賴於與之相關的年代記錄的準確性。利用兩河流域、埃及、赫梯的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的相互印證來交叉定年亦體現出近東年代學研究上的一大特點。
原始文獻中的天象記載之於年代學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古代埃及歷史上中王國和新王國時期兩次天狼星偕日同升的記錄即是構建埃及絕對年代框架的主要依據。兩河流域公元前二千年紀的文獻資料雖然相對豐富,可亞述王表與巴比倫王表卻出現殘斷,無法賡續上溯。所幸的是,有關這一時期金星運行的天象記載彌補了王表中的缺損。但是,由於觀測天狼星地點的不同以及金星發生的多值性,可供選擇的年代值也各有差異,從而形成了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中所出現的“上限、中限、下限”以至“極上限、極下限”幾種不同的定年體系,而任何一種定年體系的選擇,均會影響到整個年代框架時間上的前移或後推。1987年在瑞典歌德堡大學舉辦的年代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天文學家、考古學家、物理學家和歷史學家曾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與會學者針對採用哪一種定年體系更為合理未能達成一致性意見;儘管大多數年代學者傾向於“下限”的定年體系,但爭議迄今未止。
當然,利用自然科學手段有時可以幫助我們直接確定人工製品的年代。譬如考古出土的木、骨等有機物可以通過14C測定出年代;磁性度測量與熱發光技術可用來測定陶器的年代。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所測試樣品的污染以及“祖傳物”因素往往會影響到測試結果的精確度,歷史學家因此要做出自己的判斷與選擇。
事實上,亞述學、埃及學、赫梯學在我國的研究剛剛起步,對西方古典學的研究也相對滯後,而作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年代學的研究與介紹更顯薄弱。我們希望以“夏商周斷代工程”為契機,加強該領域的研究介紹。有理由相信,我國早期歷史斷代研究的途徑和手段對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也將會有所啓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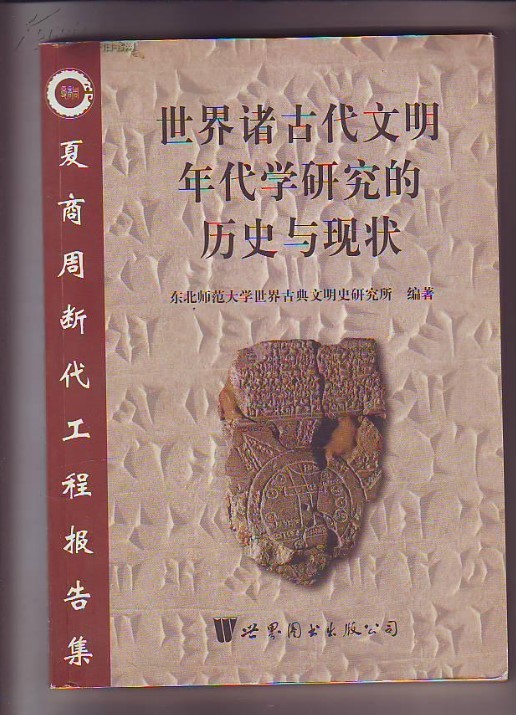
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比較
李學勤
國家“九五”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啓動後,為了解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情況並取得借鑑,專門設立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專題。現在這一專題複雜繁重的各項工作,已由東北師範大學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純教授等多位專家順利完成,其成果將作為專著出版。這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進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其中由張強教授執筆的《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綜述》一文(以下簡稱“張文”),對專題成果作了簡要的概括。
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而且目前仍在不斷發展之中。這表明,古代文明的年代學,本身就是一種學科分支,正在繼續深入和提高。當代的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的研究,都採取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結合的途徑,融合了歷史學、文獻學、文字學、考古學、科技測年(主要是測年)和天文曆法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也遵此途徑。
外國古代文明的年代學,所能憑藉的材料不外是傳世文獻記載、古文字銘刻以及其他考古學的成果,這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也極為類似。傳世文獻一般是年代學研究的起點,比如人們對古代近東的知識,最初只能依據《聖經》及希臘、羅馬的一些作品。後來才有了考古文物,特別是古文字的大量材料,使研究工作的基礎大為改觀。不過,即使在現代,傳世文獻仍有寶貴的研究價值。如埃及古史的王朝系列,見於公元前三世紀僧侶曼涅託的《埃及史》,近世的研究只是對曼涅託的系列做了修正和補充。“夏商周斷代工程”廣泛使用文獻、考古和古文字材料,與其他古代文明年代學的研究亦屬相同。
“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專題成果為大家介紹的情況,我覺得有以下幾點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由文獻依據豐富、編年基本可靠的歷史時期,逐次上推到依據較少、編年不明的較早時期,是年代學探索通用的方法。
張文在講兩河流域年代學時説:“由於初史時期研究資料的匱乏,兩河流域年代學者一般採用由文獻相對豐富的晚期向早期推進的研究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年代學,也正是這樣做的。《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託始於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這一年表有可信的文獻基礎,例如《春秋》經傳的紀年,因有許多次日食記錄而獲公認。因此,西周列王年代的研究,必須立足於以公元前841年為開端的這一年表,而西周的積年又是夏、商積年的推定所不能缺少的。
時代越向上推,所依據的文獻及古文字材料內的記述便越模糊,越多分歧。這是由於時間距離遙遠而自然造成的。恰和人們觀察空間距離遙遠的外星系只能得到微少的信息一樣。埃及王朝系統的早段,從前王朝時期到第一中間期,即第一至第十王朝,有不少王名佚失無存,列王的次序也有不同説法,不定性顯然很大。同樣,對於中國古史中的五帝時期,以及夏和商代前期,都不能要求其年代有與後世相同的準確性。
第二,古代近東的古文字材料裏,有不少王表或名年官名錶。有的表相當詳細,甚至記及月日。這類材料的時代,有些本身就很古,如埃及的帕勒摩石刻,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年表》等,為重建當時年代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中國的情形不同,文獻中的世系、年表,出現的時代都比較晚。商和西周的世系,雖有甲骨金文可予證實,但缺乏近東王表那樣系統的在位年數。這是我們年代學研究的不利條件之一。這種缺撼有望從考古發現中彌補。前些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竹簡內整理出一篇《年表》,有周列國君主年數,可惜業已殘碎,不能恢復。西晉初汲冢發現的《竹書紀年》,有夏商周諸王年數,但未能完整保存下來。
張文提到,西方古典年代學第一部系統的作品,“是公元前三世紀末埃拉託斯特奈斯所著的《編年史》。他利用當時在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的工作之便,廣泛涉獵前人著述,在綜合希臘不同編年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統一的紀年體系。”《竹書紀年》是魏國史家的作品,有一定的思想傾向,記事終於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比埃拉託斯特奈斯要稍早些。
從戰國到漢初,像《竹書紀年》、《年表》這樣的書,肯定還有不少,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説:“餘讀諜(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今後再發現這類材料,以至更早的世系、年表,確是可能的。但當前研究中國古代的年代學,還更多依靠出現較晚的文獻。這包括世系、王年的材料,也兼指關於天象的記述。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年代學研究,處境更接近西方古典年代學。傳世文獻,不分中外,都有考信辨偽的問題,如張文説的,“鑑於年代學研究資料來源與古代近東的差異,西方古典在古籍整理與校勘過程中,對晚期文獻中一些早期年代的記載始終面臨着‘信古’與‘疑古’之爭。”他所舉特洛伊戰爭的例子是很生動的。年代學研究的進展,特別是有關考古發現的增加,業已説明晚期文獻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古代傳統並非空穴來風,無所依據,無論在古代近東史還是在西方古典歷史的研究過程中均證實了這一點。”
第三,傳世文獻和出土古文字銘刻內的天象記錄,是年代學研究十分重要的依據。對這類記錄進行現代天文學的推算,常可在古史年代間確定關鍵性的絕對年代點,對年代學起重要的作用。
這方面的典型事例,如張文所舉,有埃及年代學上的天狼星偕日同升記錄,兩河流域年代學上的金星泥板等。大家知道,有金星觀測記錄的楔形文字混板的出現對漢謨拉比在位年代的推斷,起了可稱是革命性的影響,而漢謨拉比年代問題在整個古代近東年代學中是至關重要的。
張文説:“根據古巴比倫王朝第十位王阿米嚓杜喀在位的第一——十年有關金星觀測記錄,是確定古巴比倫時期絕對年代的關鍵所在。現代天文研究對阿米嚓杜喀元年所得出的多種公元年值,巴比倫第六王漢謨拉比元年因此也出現了多種選擇。鑑於漢謨拉比時代豐富的史料與考古遺存以及14C研究方法的應用,為阿米嚓杜喀絕對年代的最後選定提供了相應的解決辦法。”這已經顯示出天文學推算怎樣與文獻學、考古學及科技測年方法互相配合。在專著《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中,收有金星泥板的釋文,並作了詳細論述。
“夏商周斷代工程”已公佈的一些研究成果之間,甲骨文武丁、祖庚日月食的推算,其學術價值堪與埃及的天狼星記錄、兩河流域的金星記錄相媲美。武丁是殷商名王,他的歷史地位同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相埒。經過研究,已獲得與甲骨分期順序全然一致的武丁時期五次月食的唯一解,使武丁的在位年數有相當準確的估計。
第四,年代學研究有時有某種假設,該假設是根本的、必要的,卻沒有充分論據去證實。有些天文曆法的推算,就有着這樣的假設。
古埃及的天狼星偕日同升記錄的推算,是很好的例子。孫小淳在介紹古代近古年代學中的天文問題時説:“用天狼星偕日出定年代的方法是基於一個非常根本的假設之上,就是古埃及的民用太陽年從未有過調整。……古埃及民用曆法明明分一年為三季,為尼羅河氾濫期、冬季和夏季,如果不作置閏的調整,那曆法上的三季很少是和實際季節符合的,……嚴格説來,只有天狼星週期1460年中起始的那一年季節才真正地名副其實,這對注重農業的古埃及人來説同樣也是很奇怪的。然而,埃及的年代學正是建立在這種不變的民用太陽曆的假設之上。自從1904年德國學者梅耶爾提出這種假設之後,埃及年代學的大廈就逐步建立起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強有力的證據推翻這種假設,於是假設竟成為公理一般;而如果沒有這個假設,就無從談埃及的天文年代學。”
中國年代學的天文曆法推算,也有一個假設,便是紀日干支的連續性:紀日干支依照六十日一週循環,自上古到今天,沒有調整也沒有間斷。如果離開這個假設,也無法談中國的天文曆法推算了。好在前述甲骨文日月食的唯一解,儘管不是這一假設的充足證明,仍能使我們相信紀日干支的連續能夠上溯到商代武丁這樣早的時期。
第五,就目前年代學研究現狀而言,年代學者對各文明地區早期的大部分年代定年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即使是資料相對豐富的晚期的一些年代,也會因記載上的相互矛盾或因多種選擇而無所適從。中國古代的年代學,在這一方面亦不能例外。
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包括各種科學,從來即是向真理不斷趨近的過程。有人試想以簡單的方式一下子解決好多疑難問題,甚至宣佈已經掌握了年代學的全部秘密,這隻能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我們努力爭取的,是我們在當前主客觀條件下可能達到的最好成果,無法避免所謂“年代學上的無奈”。
在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的研究方法中,只有一項是我們不能採取的,即“同時期參照法”。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個國家並時存在,它們的文獻與考古材料每每彼此聯繫,可以互相對照補充。中國的夏、商、西周是疆土廣袤的王朝,具體情形與外國殊有不同。我們在當中原時與邊遠地區的考古研究中,也經常運用對比參照的方法,但和外國年代學上的“同時期參照法”究竟是不一樣的。其餘外國年代學的研究途徑,我們都在採用。我們還在進行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如有字甲骨的14C測年實驗,是國內外還沒有人嘗試過的。
現代意義的古代年代學研究,在中國的歷史還很短。我們正在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需要不斷吸取借鑑外國古代文明研究的經驗。為此,我們要對“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專題的各位專家學者的勞動表示由衷的感謝。我們更確信,中國的古代文明的研究將會對人類文明歷史的探討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完)
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包括各種科學,從來即是向真理不斷趨近的過程。有人試想以簡單的方式一下子解決好多疑難問題,甚至宣佈已經掌握了年代學的全部秘密,這隻能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我們努力爭取的,是我們在當前主客觀條件下可能達到的最好成果,無法避免所謂“年代學上的無奈”。
在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的研究方法中,只有一項是我們不能採取的,即“同時期參照法”。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個國家並時存在,它們的文獻與考古材料每每彼此聯繫,可以互相對照補充。中國的夏、商、西周是疆土廣袤的王朝,具體情形與外國殊有不同。我們在當時中原與邊遠地區的考古研究中,也經常運用對比參照的方法,但和外國年代學上的“同時期參照法”究竟是不一樣的。其餘外國年代學的研究途徑,我們都在採用。我們還在進行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如有字甲骨的14C測年實驗,是國內外還沒有人嘗試過的。
現代意義的古代年代學研究,在中國的歷史還很短。我們正在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需要不斷吸取借鑑外國古代文明研究的經驗。為此,我們要對“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專題的各位專家學者的勞動表示由衷的感謝。我們更確信,中國的古代文明的研究將會對人類文明歷史的探討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