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野孩子,西北音樂還有誰_風聞
摇滚客-摇滚客官方账号-有态度地听歌、看剧11-04 11:15
來源 | 搖滾客

今日BGM,《永隔一江水》,宋毛人;王洛賓
樂夏結束,從線下到線上的演唱會狂歡也已經落幕。
可是在這場從盛夏到深秋的相聚裏,我依舊充滿了遺憾。
這些遺憾與節目無關,只是我對一些樂隊的期盼不止如此,比如有一種期待叫做我想聽布衣唱一首《三峯》。
西北的風沙會在他們的音樂裏化作戀人的繾綣低語,漫長的前奏會自動篩選沒有耐性的聽眾。
三峯,布衣樂隊 - 布衣1995 成立於寧夏的布衣,有一種西北大漢獨有的質樸灑脱,這種來自秦腔的氣質浸潤在旋律和嗓音中。
在樂夏的舞台上,來自西北的漢子們唱出最真誠的歌,用他們音樂裏的生命力打動我們,然後像個深藏功與名的大俠,瀟灑地轉身離開。
同樣來自西北的野孩子,第二季因為音樂理念不同直接中途退賽,他們的音樂裏也有種遠離城市喧囂繁華的自然寧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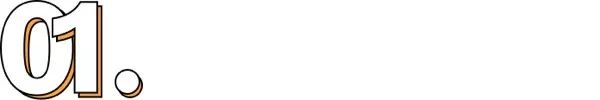
黃河流域、黃土高原,在這片以黃色為基調的土地上,有很多我們熟悉的名字和聲音。
不同於温柔婉約的南方,西北的風沙粗糲磨人、黃河流水奔騰席捲着整個黃土高原,在這種環境下催生出來的西本音樂,自帶一種蒼茫雄渾。

西北人好像天生就會唱歌,吼出來的那種,不颳風的日子裏天空透藍,風沙彌漫的時候盡情喊上幾嗓子黃土高坡也被喊得透亮。
蘇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歌聲裏有着對土地和生命的記錄,他的聲音自由而高亢,讓來自自然的聲音成為音樂的一部分,也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我始終熱愛《賢良》裏他縱情地呼喊,天然又純粹。
生長於黃土高原的蘇陽早年間或許也曾被西方重型搖滾樂所誘惑,但在輾轉之後他還是沒能忘掉自己的根在哪。
那是骨子裏抑制不住的關於黃土地關於黃河水關於沙漠關於綠洲關於絕望關於希望關於想有個婆娘的吶喊。
那是融入血液的放蕩不羈走馬關西,那是呼吸裏的獵獵風塵。
它代表着黃土高原乃至整個西北的一種精神:熱情、勤勞、堅忍、頑強、樸素、固執。

蘇陽突破了搖滾樂和民族音樂的界限,歌唱着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鮮花、勞動與愛情。
他表達着無數黃土地和藍天之中掙扎的升斗小民們最基本最真實的想法:活下去,像拉拉纓一樣強韌的活下去。
俗世的“賢良”讓他刺痛又不屑。
另一個紮根於民間的西北音樂標誌人物,是自稱有些歌唱的很騷氣的張尕慫。
每次,他有些歌確實很騷氣,和二手樑龍的騷還不一樣,裏面有一種粗野的真實。
讓人一聽就是屌絲的生活寫照,一邊是樂呵呵的自嘲,另一邊是赤裸裸的無奈。
在這樣的屌絲消解裏,他的很多歌都帶着一股子難登大雅之堂的“粗俗”,但是粗俗得可愛。

從張尕慫的音樂裏,我們能感受到那是一個個真實的生命,他們是生長在黃土高坡上也被困在其中的真實的人,有慾望、有過往。
在唱歌的同時,他也在向我們講述一些接地氣,卻又很真實很柔軟的東西。
在用生活寫出來的音樂裏,有他對生命的敬意。
談論西北的民謠,離不開張瑋瑋和野孩子。
前段時間,張瑋瑋的新專《沙木黎》發佈,新的嘗試帶來了新的感覺,但我還是對當初那張《白銀飯店》念念不忘。
《白銀飯店》是一張要從第一首一口氣聽到最後一首的專輯,娓娓道來裏,是白銀這個小城市的故事,也是張瑋瑋的故事。
每個人的生命裏都會有一座空空的米店,唱歌的人走心,聽歌的人也走心,歌的背後,是生活。
有人説**“西北是中國民謠的根,蘭州是西北民謠的魂。”**
《蘭州蘭州》這首依託在蘭州基底上而唱的歌,不只是一首歌,它還代表着一段有關於西北的記憶和那些過往遇見的人。
低苦艾的歌裏有曠野風沙的氣息、粗糲的底色搭配生動的旋律,將蘭州這座城市唱得灰暗而美麗,指引所有人大漠的方向和回家的路途。
西站西站,上車就走,有座位。
白馬浪,到了。
蘇陽、張尕慫在人間來去、大俗大雅,張瑋瑋的幽怨之情娓娓道來,低苦艾頂天立地,布衣往事無牽掛,野孩子黃河之水永恆經典。
還有已經提累了的崔健、趙牧陽和黑撒、郭龍、馬飛、吳吞、馬條、張淺替……
西北的樣子,西北人的性情,在他們的歌裏就能聽到。

西北的風沙裏種不出玫瑰,但能催生出中國搖滾的萌芽。
當豐富的民俗音樂融合了搖滾樂、西式的民謠表現手法,就形成了風格鮮明的中國民謠搖滾或者説是民宿搖滾的一個重要部分。
1988年,中國唱片集團發行了《西北風》唱片集,崔健的《一無所有》被收錄其中,中國搖滾從粗獷豪邁的西北風格出發。
敞亮的旋律、歌詞搭配上民族樂器,西北的豪爽之氣裹挾着風沙席捲而過,人們的生活被具象化,也被真實地記錄。

2019年,蘇陽拍了一部紀錄片《大河唱》,記錄黃河流域傳唱千年如今卻已經日漸式微的三種民間音樂形式 :三絃、皮影和秦腔。
當時的排片少得可憐,後來剪輯後上線B站,播放量至今也不到19萬,但只要是看過這部片子的人,都一定忘不了其中那些鮮活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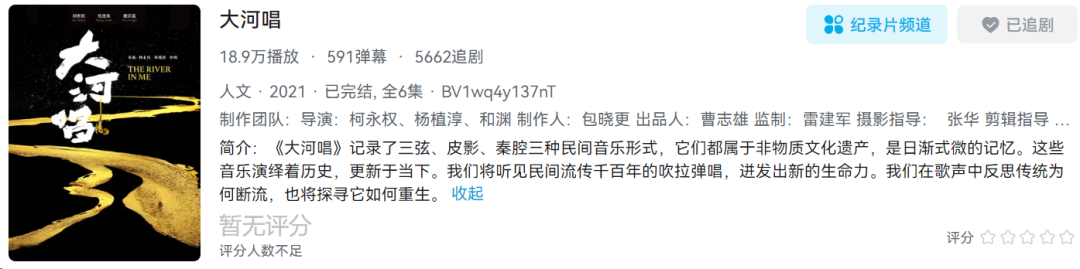
在影片裏,只有忠實的記錄和好聽的歌曲、配樂,沒有旁白的解讀,也沒有對日漸式微的傳統民間藝術的俯視或憐憫。
他們只是記錄,在演員一邊唱歌一邊説出來自哪的時候,鏡頭正好切換到他的家鄉,家鄉貧瘠的土壤和旁邊樹立的風力發電機產生了強烈的對比。

這些普通藝人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都在這片土地上。
鏡頭下是灰色的世界,天色蒼茫,憂慮的梯田層層疊疊,遙遠的天邊春雷滾滾。
“這最開始就十二個人。我六個太爺,帶着媳婦,住在這了。”這句話,讓我想起馬爾克斯筆下那個雋永的故事。

他們是演員,也是莊稼漢,拿起樂器、裝扮上台之後,他們代表藝術,唱唸做打樣樣俱全。
可是下台的那一刻,他們就回到了人間,把三絃換成鋤頭,用莊稼人的樸實支撐起一個古老農耕文明的延續。
當蘇陽的音樂與戲台上的民歌閃回拉扯,當舞台下聽歌搖旗的年輕人和戲台下寥寥無幾的老年人重合,你就會意識到,音樂將一切傳承了下來。

當城市與農村、現代與傳統、工業與農耕重合。
當王洛賓老先生唱起那首《永隔一江水》,當無數精彩卻沒落的民間藝術在這個時代找到了傳承,我們的搖滾也就有了雛形。

西北音樂人的身上有股江湖氣,也有一種獨特的詩意,是當年的大漠孤煙直,也是如今的西北偏北。
西北偏北,劉東明 - 北京的雨季漫長的西北風作用下沙塵年復一年地堆積,風沙孕育出了黃土高原,也孕育了接地氣的西北音樂。
風聲呼嘯間,是一代又一代民間藝人的傳承和無數普通人鮮活的一生,他們生活在黃河邊,聽着説書,唱着花兒……

民間傳統藝術或許逐漸衰敗,甚至有一天無人知曉,但是傳承不絕。
或許有一天,已經不知道過了多少年後,有人會在黃河岸邊捧起一抔沙,種下一棵樹,輕聲哼唱:“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