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霸權思維的歷史附會(轉載文章)_風聞
文渊紫光-11-05 09:25
“修昔底德陷阱”:霸權思維的歷史附會(轉載文章)
作者:時偉通
來源:《歷史評論》2023年第5期
作者單位:中國歷史研究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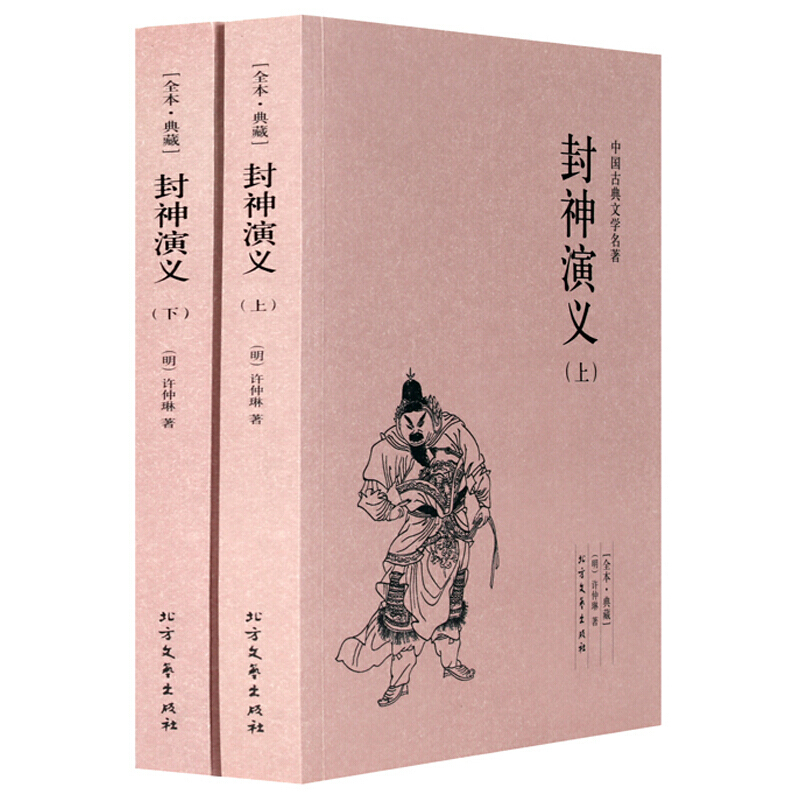
“修昔底德陷阱”論將美國長期奉行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邏輯、“國強必霸”的自身經驗、對中國一貫的敵視、自居為中國“恩人”的傲慢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所謂“陷阱”論本質上就是帝國主義邏輯的理論投射,用之解釋中國則扞格不通,用之分析美國恰好“相得益彰”。
2012年,美國學者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命題,並以此定性當下及未來的中美關係。2017年,他出版專著《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系統闡釋其“陷阱”論:當“崛起國”威脅取代“守成國”時會產生嚴重的結構性壓力,一些微小的火花都能引發大規模衝突,未來中美大概率也無法避免戰爭。事實上,艾氏此論並非建立在歷史真實之上,而是“借古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偽託修昔底德來闡述自己的外交理論。更重要的是,艾氏以帝國主義的霸權思維看待中國,這本身就是以己度人,不過是帝國主義邏輯的理論投射而已。
以今律古 附會歷史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論屬於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艾利森先是預設中美之間可能一戰的結論,建構出理論內容,進而與修昔底德關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原因的相關評論聯繫起來。究其本質,艾利森的這一做法不過是一種歷史附會。
艾利森最重要的依託是修昔底德的那句經典解釋——“真正的原因是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然而,修昔底德從未提及所謂“崛起國”和“守成國”,更未把雅典和斯巴達視為“崛起國”和“守成國”。與修昔底德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及後世的許多歷史學家,都將雅典和斯巴達視為希臘世界的兩強,一個稱霸海洋,一個稱霸陸地。古希臘史專家陳村富教授經過考證指出,艾利森所謂“在前490年波斯入侵之前,斯巴達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已經持續超過一個多世紀了”,此説純屬杜撰,在修昔底德和希羅多德的著述中均找不到原話。關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修昔底德那句經典解釋只能視為其中一個原因或者一個前提,但他並未否認其他因素的影響。耶魯大學古典學家卡根教授認為,斯巴達的盟友科林斯在推動斯巴達走向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修昔底德的解釋只能算作“一家之言”,諸多學者認為修昔底德的判斷過於籠統,不完全符合事實。艾利森非但不去探究真相和關注上述爭論,反而杜撰出“在修昔底德看來,最根本的原因是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存在着結構性壓力”的説法。
除了偽託歷史,艾利森的理論存在明顯邏輯漏洞。從他的理論框架看,“崛起國”和“守成國”爭奪的是主導權或霸權,前者尋求的是權力或主導地位,而後者主要擔憂自身地位不保;嚴重的結構性壓力在“崛起國對守成國威脅至極時產生”,此時戰爭最容易爆發,而且戰爭通常由崛起國挑起。但他對具體案例的分析卻時有矛盾。比如,他認為法國與哈布斯堡王朝競爭的領域是“領土和多方面利益”,戰爭的責任方是守成國法國。作為“崛起國”的奧斯曼帝國,企圖佔領神聖羅馬帝國、滅亡“守成國”哈布斯堡王朝,戰爭的責任方在“崛起國”。“崛起國”瑞典的目標是“解除守成國哈布斯堡王朝對自己的安全威脅”,而哈布斯堡王朝的恐懼則是“出於對波羅的海南部出現一個強權的本能恐懼”,瑞典成為戰爭的挑起者。在這裏,恐懼成了雙向的,雙方的衝突成了傳統的地緣衝突。可以説,艾利森列舉的每一個案例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被籠統地歸因於“修昔底德陷阱”。
結構性壓力是否會導致戰爭?回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問題上。公元前479年波斯第三次入侵希臘失敗後,雅典開始擴張,到前446年雅典擴張基本結束。斯巴達大部分時間都在“坐等”雅典崛起,甚至還在前446/445年與雅典締結《三十年和約》,在事實上承認了雅典的海上霸主地位。等到前432年,如卡根所説,雅典的擴張已停止,很難談得上對斯巴達構成威脅時,斯巴達卻對雅典宣戰。因此,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史實根本無法支撐艾利森的論斷。或許艾利森也知道結構性壓力無法解釋戰爭的爆發,於是在分析伯羅奔尼撒戰爭時説:“修昔底德找到了導致戰爭的三大主因——利益、恐懼和榮譽”;分析一戰時,他説這場災難與其説“因為無知,還不如説是因為誤判”。當艾利森引入主要原因,又沒有闡述清楚結構性壓力和這些主因的關係時,等於承認了自己所謂的結構性壓力並不必然導致戰爭爆發。就此,“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根支柱也被他自己推倒了。
沿襲舊説 以己度人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不僅在史實和邏輯上漏洞百出,在內容和邏輯框架上也毫無新意。“結構性壓力”最早由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學者肯尼思·沃爾茲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沃爾茲認為,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國際體系結構即主要大國間的物質權力分配影響國家行為的選擇,進而導致人類歷史上頻繁發生戰爭和衝突。“崛起國”和“守成國”提法,來源於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奧根斯基的“權力轉移論”中的“挑戰者”和“主導國”,以及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米爾斯海默“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中的“修正主義國家”和“維持現狀國家”(霸權國)。奧根斯基認為,國際體系中一個新興大國崛起後,會成為要求改變現狀的“挑戰者”,而體系的主導國希望維持現狀,由此雙方產生圍繞國際秩序主導權的競爭,很可能會以戰爭收場,最終完成權力轉移。米爾斯海默認為,在國際體系中,修正主義國家總會力圖攫取權力和主導地位,甚至不惜以武力改變現狀。艾利森的核心概念和邏輯框架均直接來源於上述理論和框架,也都未能超越他們。那麼,艾利森為何費盡心思,杜撰出一個毫無新意而且根本站不住腳的概念呢?
面對中美關係不斷惡化的事實,各界迫切希望理解中美關係的現狀和未來。總的來説,有兩種可依賴的路徑:一是歷史類比,如近年來比較流行的“1914年一戰幻影”和“新冷戰論”;二是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其中“權力轉移論”和“進攻性現實主義”近年來尤受關注。艾利森敏鋭並巧妙地將兩種路徑嫁接,提出了自己版本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一糅合了歷史類比和國際關係理論的概念的確博人眼球,但艾利森的訴求並不限於此。
與其説艾利森是在警示中美兩國吸取歷史教訓,毋寧説他是在提醒美國決策者,中國會尋求用武力取代美國的主導地位,美國應做好戰爭準備。艾利森絲毫不掩蓋自己的意圖。早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裏,他就呼籲美國人,尤其是那些天天向中國説教“更像我們一些”的美國人,應該回想一下自己的歷史,意指中國會像歷史上的美國一樣,不甘心屈居第二。在專著的開篇,他提到自己把與他人合編但尚未出版的《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的一部分,交給當時的中情局局長戴維·彼得雷烏斯,意在使決策者正視中國的崛起和挑戰。在書中他宣稱,“在考慮中國何時以及如何使用武力時,單純考慮我們會採取何種行動是不夠的”。
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比附下,艾利森處處把中國比作意在“變更現狀”的雅典。中國的發展被他先入為主地視為要“稱霸”,要成為“亞洲和世界上的頭號強國”,而且不惜通過發動戰爭來實現這一目標。為此,他罔顧事實、偷換概念,把1950年志願軍入朝作戰、1969年珍寶島自衞反擊戰和1996年在台海試射導彈等中國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領土完整的正義之舉,曲解成為實現“修正主義”目標的先發制人行動。而美國則被他視為與斯巴達一樣的現狀維護者和受害者。他在專著開篇即説,斯巴達有權質問雅典,是誰給雅典的繁榮提供了安全的環境,喻指美國同樣有權質問中國,是誰給中國的崛起提供了條件。這一點,他在2012年的文章中説得清楚:戰後60年裏,美國治下的“太平洋和平”為亞洲國家實現前所未有的發展提供了經濟和安全保障。
但這種為霸權背書的論調根本經不起事實檢驗。在波斯大舉入侵希臘時,積極抗敵的是雅典而非斯巴達。斯巴達長期敵視雅典,甚至當雅典為整個希臘與波斯作戰時,斯巴達還想着偷襲雅典。晏紹祥教授考證後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是斯巴達強加給雅典及其盟邦的。美國也不是什麼和平的提供者和保障者,戰後亞太地區爆發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美國要麼是戰爭的挑起者,要麼是煽動者。20世紀80年代後,亞太國家的整體性發展絕非美國的“恩賜”,而是得益於和平穩定的國際大環境和中國巨大市場的開放。在諸多事關亞太和平穩定繁榮的重大問題上,沒有中國的參與、支持和配合,單靠美國是無法解決的,20世紀90年代初柬埔寨問題的解決、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的結束均是例證。
帝國主義邏輯的理論投射
“修昔底德陷阱”論將美國長期奉行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邏輯、“國強必霸”的自身經驗、對中國一貫的敵視、自居為中國“恩人”的傲慢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所謂“陷阱”論本質上就是帝國主義邏輯的理論投射,用之解釋中國則扞格不通,用之分析美國恰好“相得益彰”。近年來,中美關係出現重大轉折,甚至如基辛格所説,“再也回不到從前了”。出現這一問題並不是中國意在取代美國的主導地位,恰恰相反,責任在美國而不在中國。
二戰後,為維護霸權地位,美國一直不遺餘力地針對和削弱最有可能威脅其地位的國家。例如冷戰時期的蘇聯一直被美國針對和打擊;即便其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騰飛、一度有望追趕上美國時,也遭到美國嚴厲的制裁和打壓。因此,只要是有可能或被認為有可能威脅其霸權地位的國家就會遭到美國打擊。如今的中國恰恰就被美國視為其霸權地位的威脅。2010年,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美國迅速出台了針對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這絕非巧合,而是美國的慣用手段。
但美國所謂的“威脅”有很大臆想成分。諸多學者強調,二戰後,美國都是根據想象的“威脅”而非真實的威脅採取行動,對中國尤其如此。自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簽訂以來,美國從未平等地看待中國,要麼把中國視為一個低劣的“他者”,要麼視為一個可以改造的“他者”,有時還把中國視為“威脅”。這一對華認知充分體現了美國長期以來自詡為“例外”、“恩人”的心態,以及自私自利的行動邏輯。
在中國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美國再次使用慣用手段打擊“威脅”其地位的國家,中國被渲染成了最大“威脅”。美國已深陷“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只會助長其對中國的誤判,最終受害的是美國自己。歷史已經給美國留下了足夠多的教訓:1950年聯合國軍仁川登陸後,杜魯門、麥克阿瑟等認為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既無力也不敢出兵援助朝鮮,這種誤判讓美國在朝鮮付出了慘重代價;20世紀60年代肯尼迪和約翰遜時期,美國視中國為比蘇聯更大的“威脅”,在想象的中國“威脅”下,美國在亞太投入巨大成本,最終深陷越戰泥潭,霸權地位受到嚴重衝擊。認真吸取歷史教訓,儘快讓中美關係回到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軌道上來,才是美國的正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