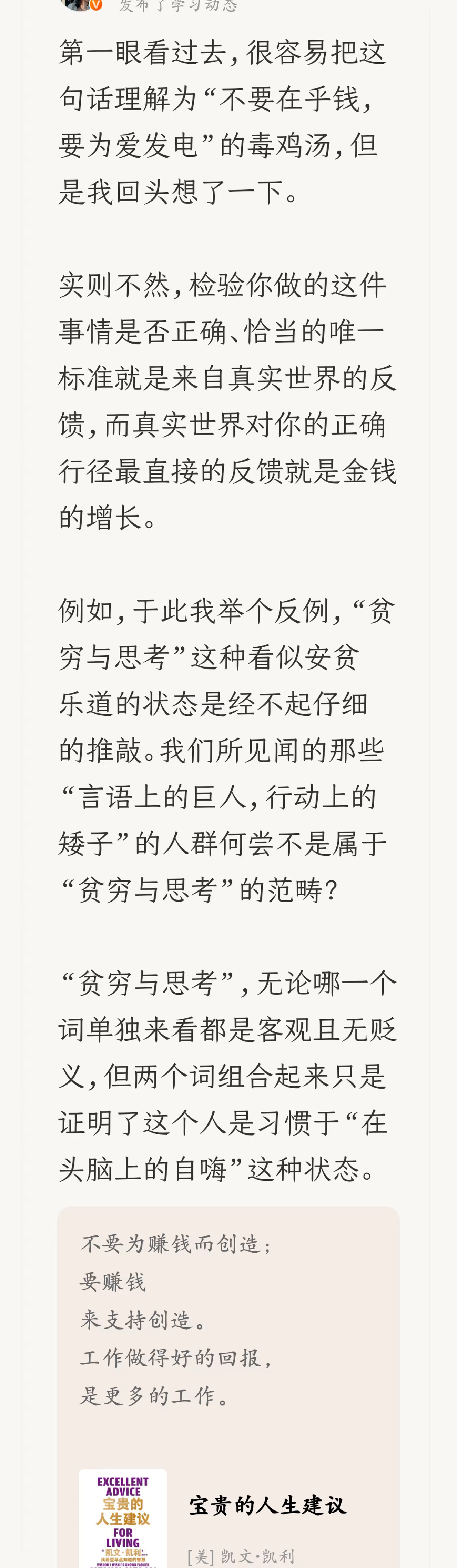兩種“安貧樂道”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11-12 18:05
在一個國學研究羣裏,有位同仁(就是上次和我討論中國哲學為什麼是“人世”的哲學而不是“入世”的哲學那位——見《不離世,方為真脱俗——與友人談儒家精神》一文)説:
“我發現了一件有點隱晦的事,自己在學習中哲與心理學的時候,能隱約察覺到每個學科都有各自擅長的話題領域,但也有避而不談的領域。可能也是我看的書實在太少了,還沒看到相關的長篇大論。例如,我現在能看到,中哲似乎在迴避對“金錢”這一個話題的談論,似乎會唯恐媚俗;心理學好像在否認命運的客觀存在,不太願意深究外在客觀命運的話題。
我就在琢磨,“安貧樂道”好像有點反人性,很難做到。
以前,我還專門琢磨過了“人與金錢”的關係,發現自己好像不太喜歡“貧窮與思考”這類生活。我還是喜歡“學以致用”的生活,通過運用自己的學識來解決問題,然後看外界對我的反饋判斷我的思考是否正確。金錢是來自外界最直接的反饋。”
我回應:
“樂道是追求,安貧是一種豁達的心態。
並不是説我們都要去找窮日子過。孔子説:“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另外,你總會碰到比你有錢的人,與之相比,你處於相對的貧,如果你的志並不在經商與之競爭的話,那你除了安貧樂道,還能怎樣?”
她立即表示贊同:
“嗯,謝謝老師,這麼一説,我就很清楚了,我之前理解錯了,以為是要刻意地去過苦日子。”
想了一會兒,我又指出:
“除此之外,有一個辦法可以不用安貧樂道,即實現共產主義,或儒家所謂大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無所謂貧富了,自然也無所謂安貧了。
但在這個奮鬥過程中,還是需要安貧樂道的,還是要以艱苦奮鬥為榮,苦中作樂,以苦為樂。就像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裏寫的志願軍戰士説的:“我們在這裏蹲防空洞,是為了祖國人民不蹲;我們在這裏吃雪,是為了祖國人民不吃雪。”
方誌敏同志説:“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但對這些話,她就不再有任何贊同的表示了。
和她説這些的時候,其實我內心是有些吃驚的:作為一名研究傳統文化的研究生,她怎麼會把“安貧樂道”理解為“刻意去過苦日子”呢?
但我又想了一想,答案或許就隱藏在她剛才説的這段話裏:
“以前,我還專門琢磨過了“人與金錢”的關係,發現自己好像不太喜歡“貧窮與思考”這類生活。我還是喜歡“學以致用”的生活,通過運用自己的學識來解決問題,然後看外界對我的反饋判斷我的思考是否正確。金錢是來自外界最直接的反饋。”
她的邏輯,如果充分展開,是這樣的:
1.“道”不能空談,要能解決問題才叫“道”或“真理”;
2.問題解決沒有,不能由我自己説了算,而要看外界給我的反饋;
3.金錢是來自外界最直接的反饋;
4.因此,有金錢回報,你的道才是能解決問題的真道;反之即是偽道;
5.所以,有道之人必然不會貧;
6.所以,“樂道”是不需要“安貧”的;
7.所以,“安貧樂道”是個偽命題;
8.所以,叫人“安貧樂道”並不是真的叫人“樂道”,而是要人刻意地去過苦日子,然後標榜自己有“道”而聊以自慰,就像過去有些人説的“越窮越光榮”,或者今天有些人譏諷的,“越沒錢的人,就越熱衷於談政治”。
不難看出,以上論證的最根本要害在於“3.金錢是來自外界最直接的反饋”。
什麼樣的“道”才是以金錢為最直接的反饋的呢?當然是“賺錢之道”。換言之,只有對“賺錢之道”而言,有沒有以及有多少金錢回報,才是反映你“得道”與否的最直接反饋或者説標準。而樂於“賺錢之道”的人,當然是不可能“安貧”的。
一切“道”,都不過是“賺錢之道”———這就是這位研究國學的研究生潛意識裏的東西。
於是我批評了她。她似乎也贊同我的批評。
所以我真的説服她了嗎?
其實並沒有。
只要仔細看一看,就會發現,在她所贊同的我的那段話裏,我只是給她開了一碗心靈雞湯:
“樂道是追求,安貧不是故意找窮日子過,而是一種能看得開的心態。世上總有比你富的人,你不安貧樂道,還能怎麼樣呢?”
她要是真的喝下了這碗雞湯,大概是可以心平氣順、隨遇而安,説不定還可以自我感動一番了。
可是這真的好嗎?
你看她之前那種“想要解決問題”的願望、那種要從客觀世界得到反饋的務實精神、那種對中國哲學和心理學逃避現實的反感、那種聲稱自己就是想要金錢來證明自己的坦率——這種種都體現了什麼?
體現了一種強大的生命力、一種不甘示弱、斬釘截鐵的權力意志、一種積極進取的行動的渴望,甚至可能是她被自己所感到的拜金主義的大環境激發起的一種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與狼共舞”的決心和勇氣。
與這些相比,我開出的心靈雞湯反而顯得庸俗怯懦了。
是的,不能不這樣的。
在一個貧富懸殊,而且很多富者取財無道、為富不仁的世界上,僅僅像我那樣勸説貧者,讓他們消食化氣、自我解嘲,讓他們和顏悦色、低眉順眼地“安貧樂道”下去,其實是一種偽善的説教,説得嚴重些,是在販賣精神鴉片乃至培養幫閒奴才。
與其這樣,還不如讓她保持原來那份強悍的血性——何況那裏面説不定還有一種於連·索黑爾式的反抗精神呢。
正是因為隱隱約約意識到了這一點,我才説出了後面那段話,希望她理解到真正的“道”是共產主義,是讓物質上的“貧”和“富”成為沒有意義的事情。真正的“安貧樂道”不是忍氣吞聲自我安慰,或是獨善其身故作高蹈,而是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理想,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去進行積極勇敢的鬥爭。
既然有勇氣做於連·索黑爾,為什麼沒有勇氣做保爾·柯察金呢?
她大概還不能接受這一點——很多知識分子,連同我在內,都還太小資、太自我。
希望她能早些明白:
1.我其實很欣賞她的勇氣和現實感;
2.我其實講了兩種“安貧樂道”:
有隱士的安貧樂道,有戰士的安貧樂道。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後者,是革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