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俠”葉檀,面對死亡邊緣_風聞
她刊-她刊官方账号-提供最潮流的时尚和娱乐资讯,陪你遇见最美的自己35分钟前
作者 | 周婧
來源 | 她刊
作為中國財經圈鳳毛鱗角的女性評論員,葉檀至今仍活躍在大眾視野裏。長達20多年,她筆耕不輟,在紛繁複雜的經濟現象中輸出精準的判斷、犀利的評述。財經江湖人稱“葉女俠”。
她還是一名創業者,團隊裏她給自己取花名,用的是“姑姑”“張三丰”,都是武俠小説裏有絕對能力的照顧人的角色。生活中,她創造了一種女性敍事:自我價值的實現是重要的,工作永遠放置在首位。生活因此被工作填滿,一週7天工作7天。
直到去年7月,她確診乳腺癌。過度的消耗讓她的身體成為了廢墟。一個“工作永動機”不得不被迫停下來。走不了路,身體侷限在牀上,她開啓了漫長的自我追問:到底什麼是有意義的?如何定義成功?人的價值感在哪裏?這或許是所有人都會面臨的人生困境。
九個月後,葉檀重回鏡頭,她第一次在大眾面前,袒露自己的疾病、脆弱、過去的焦慮和漫長的失眠鬥爭。過往的人生經驗裏,她一直刻苦奮進,相信努力就會有回報,現在經歷着最猛烈的生死疲勞,她變得柔軟了——“努力是一部分,運氣是一部分,坦然接受。”
女俠消失了,迴歸普通人葉檀。

女俠消失了嗎
“女俠”葉檀做了20多年的媒體人,56歲這年,她親自闢謠了自己的死亡新聞。起因是2023年6月,有媒體發文稱,“著名財經博主葉檀今晨去世”。謠言出現數小時後,葉檀在微博上回應:“我活着,治療很有效”。
謠言是如何產生的,或許要追溯到更早前的4月。葉檀出鏡在自己的頻道,視頻裏她穿着休閒衣服,頭戴一頂白色帽子,人憔悴不少,臉色也暗淡。往日干練、犀利的葉檀消失了。現在,她盤腿坐着,懷裏抱着貓,語氣緩慢地解釋,“9個月沒有拍視頻,原因是我生病了,很重的病。”
她坦言,2022年7月,自己確診了乳腺癌,晚期。
在巨大的疾病面前,身體的摧殘是肉眼可見的。她的左側胸部,結節從“綠豆”胖成“異形鴿子蛋”,再變成“一枚鮮豔的玫紅色腫塊”。隨之而來的是疼痛,從刺痛感到一陣陣抽痛,胸椎繞着胸部,像是固了一個燒紅的、熱的鐵圈,緊緊的套在身上。她穿不了內衣,起身也越來越慢。
確診病情的前兩天,葉檀還在照常上班。作為公司年紀最大、加班最狠的人,她每天早上9點到公司,深夜11點回家,再覆盤一天的工作,到凌晨兩三點才能睡。一週7天工作7天。人累了要休息,她不得不見人,不得不寫文章,不得不開會,一旦忙起來,所有精力集中,“開會時大腦是亢奮的,興奮感遠遠蓋過了疲憊。”葉檀説。
十幾年如一日的工作慣性太大,她的身體對普通的疲憊失去了感知。2021年下半年,她做了一次體檢,醫生提醒她左側乳房,去做個檢查,葉檀並未太在意。胸部刺痛已是老毛病了,五六年前她查出乳腺結節,這是大多數女性都有的小毛病。偶爾的刺痛感,也很快被忙碌的工作掩蓋了過去。
2022年上半年,葉檀左側胸部的刺痛越來越強烈。那段時間,她關在上海閔行區的小區內無法出門,能出門了,又想着工作的事,這一拖,又是幾個月。
葉檀很少提及身體的不適,連疲憊也儘量遮掩。她56歲了,同事們幾乎很少注意到她的年紀,“從不喊累,精力好像永遠用不完。”一位同事感嘆。葉檀説自己身體的耐受力比一般人強,“但痛還是痛”。
繁忙的日程中,身體和心理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在6月30日。那天晚上,按照預先的安排,她要做一場直播,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她堅持自己上場。為了掩蓋蒼白的臉色,化妝師給她抹上厚厚的粉底和腮紅。整整三個小時,葉檀和嘉賓對談,語言密集,精神高度集中。
直播進入後半段,她的胸口開始出現一陣陣抽痛,疼痛的間隙越來越短。她坐着悄悄用胳膊抵住身體,強行將痛感壓下去。到直播結束,她在小圓凳子上坐了半天,發現自己站不起來了。
之後,她被半拖半抬着塞進車裏,送進醫院。等待10來天,核磁共振結果顯示,葉檀的整個脊椎都已在癌細胞的攻擊下,變成白色。醫生告知她,乳腺癌是4期,且發生骨轉移,5年生存率只有22%,已經沒有任何做手術的意義,只能保守治療。
一位負責直播的同事回憶,“那場她完成得非常漂亮,沒有讓任何人看出來。”外人看不到的“強撐”一面,終究讓血肉之軀撞了一次紅線,“工作永動機”不得不被迫停下來。
住進上海瑞金醫院的前一天,她頂着一絲氣力安排好工作,家庭,寫好了遺囑。此後的一段時間,外界偶爾還能看到她出鏡的視頻——那是團隊同事們通過剪輯呈現出來的。
公眾印象裏那個眼神堅定,語言犀利點評財經的“葉檀”消失了。
身體最弱的時候,她只能斜斜地躺着,下牀每一步,都要人攙扶。她的骨頭很脆弱,坐在病牀上時,醫生們不止一次地提醒,這樣的姿勢可能高位截癱,躺着或者站直都比坐着好。葉檀根據醫生的建議,先做化療把快速發展的癌細胞壓下去。在腫瘤醫院,病友們把化療隱晦地稱作“掛水”,隨着化療藥水一點一滴流入靜脈,她的力氣也一點一點被抽走。
疾病的殘酷之處在於,再強硬的人也會被它貶折為弱者。她在“住院日記”裏記錄下這段長達九個月的“特殊經歷”:
「 第一次掛水後精神還可以,以為自己是特殊的那一個,後來深刻地瞭解,疾病和因果一樣公平,只是時間到不到而已。
第二次掛水後腿開始邁不開,眼皮變得沉重,講話只剩氣音。
以前一天可以飛三座城市,現在成了緩慢的爬行動物,烏龜都比我爬得快。」
隨之治療深入,頭髮開始大把大把地脱落,她索性把頭髮剃光。比失去頭髮更嚴重的,是心理的衝擊,意味着體能一天天衰落。化療藥使她的手指和腳趾逐漸麻木。為了降低血流速度,她在大冬天裏戴着冰手套,光腳穿着冰腳套,凍得直哆嗦。
好在治療有效。幾個月下來,癌細胞活性逐漸降低。2022年12月底,醫生宣告化療結束。
患上癌症,普通人無法克服潛意識的恐懼,葉檀説,自己也在確診後花了四,五個月接受這個事實。投入到與癌症搏鬥的戰場,她幸運存活下來。
九個月後,葉檀重回鏡頭,她感到自己的一部分已經消失了,她仍然熱愛工作,但她想要的意義感和價值感,要到別處去尋求。

圖/患癌後首次出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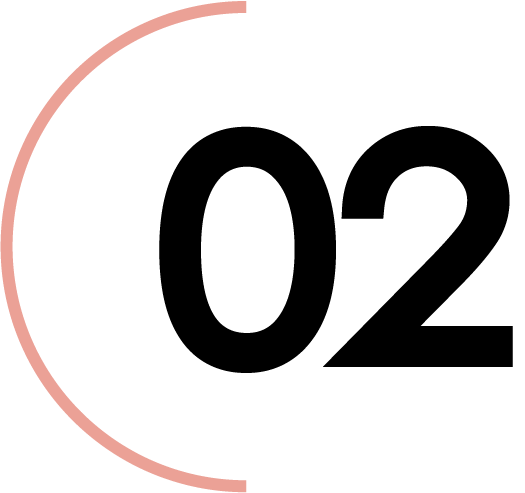
一個永遠在追求自我價值的人
作為財經圈最“毒舌”且出鏡率最高的女人,葉檀有一張形象鮮明的臉。她鍾情於在資本市場發表自己的見解,除此之外,她並不真正想要與世界一起來分享自己。“以專業知識分享來示人”是她給自己的定位。
2016年,《新週刊》將“年度知道分子”獎項頒給葉檀,評價她是“一個啓蒙者、理性派和傳媒人。”葉檀接過獎盃笑稱,得到這個獎項鬧了很大的動靜,“有些人舉着刀”就過來了。
那年,她寫了篇《我眼中最無前途的十個中國城市》,文章中她點名長春、蘭州、南昌、温州等幾個城市,各個地方媒體、政府智囊逐條反駁,掀起一波波輿論熱潮。
“在人情主導的社會里,説好話容易,評論問題,非常困難。”作為不吐不快的職業評論員,她的直率,“毒舌”總能引起關注,她在熒幕上的形象深入人心。
進入財經領域,葉檀是半路入門,她在許多場合講到這段經歷,稱之為“興趣使然,符合內心的選擇”,追求自我價值排在首位,許多規則在她這裏被打破。
在復旦大學求學,葉檀讀的是歷史,當時她的導師正在研究江南市鎮經濟,這使她看見歷史和經濟的結合,心裏種下了一顆種子。畢業後,她先後供職於復旦大學和上海社科院。在某種程度上,她過上了許多人羨慕的穩定生活——工作清閒,收入不錯,且有一定社會地位。
但葉檀並不喜歡。書讀多了,視野漸寬泛,她逐漸感知到自己需要知道財富的流通,才能看懂這個世界。2000年前後,恰逢紙媒方興未艾,財經媒體開始興起。她開始為報紙撰寫財經評論。
面對跨界和轉型,她有一種壓力——憑什麼進入財經領域;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份也使得她受到攻擊,“人們會質疑你的邏輯、情商以及智商”。
葉檀是實踐派,她説,人生不是規劃出來的,不是談出來,而是做出來的。有兩三年時間,她將精力全放在了研究財經上,閲讀大量財經類書籍,一看就看到天亮,每天堅持寫一篇財經評論稿。
2004年,葉檀離開書齋,進入《每日經濟新聞》報紙,負責評論版面。砸掉鐵飯碗的那一天,一片全新的廣闊天地,在她面前徐徐展開。作為專攻明清政治史與經濟史的博士,同時又是財經評論員,葉檀要做的,就是以史為鑑,梳理未來經濟的走向。普通老百姓他們沒有機會接觸這些宏大的經濟命題,葉檀站在中小投資者這一邊,為他們答疑解惑。
在資本市場,葉檀有一種直率,敢説的魄力。那幾年,她是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的常客,節目中,她和主持人竇文濤聊對於當下經濟、婚戀市場、以及年輕人觀念的看法,常常輸出犀利的觀點。她説:“在中國,如果男人到了40歲還沒房子,就是苟活”;“在當下的婚姻市場中,流行的是丈母孃經濟”。
曾有媒體問她:公開發表尖鋭言論的專家不怕惹出眾怒、捱罵嗎?葉檀説怕,也要説。怕不怕,都得幹事,反正怕也沒用,索性不怕。2021年,葉檀在網上評論孟晚舟事件,引來一片惡意解讀。她發文稱:“我堅持為健康的市場化發聲,這個理念,我一定會堅持,不打算改。”
站在離錢最近的行業,葉檀需要保持敏鋭和理性的頭腦。她有一股“狠勁”。每天她閲覽財經新聞,查看市場數據,準備文章選題,和人討論,有時還要參加會議。任何時候,她抱起電腦打字,在火車站、機場,飯桌上,她都能創作。
20多年來她始終保持着緊張,高壓的工作狀態。她享受其中,“我的幸福感和存在感,來自於我的工作”。她不相信事業家庭兩不誤,時間有限只能顧一頭,她把生活和家庭的權重不斷調低。沒有時間逛街,不得不購置衣服的時候,她會一次性買足一年份。
過往的人生裏,她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朝“上”走的,人活着要奮鬥,大眾眼中她是“獨立的女性知識分子”,獨立就是有選擇權,她解釋,“我可以選擇這樣的生活,也有權利不選擇。”
2014年前後,新媒體飛速崛起,葉檀選擇了創業,成立了自己的財經工作室。2017年又創辦公司,團隊最多時有110人。
為什麼要創業,葉檀覺得這是自然而然的選擇,“我大概覺得我上輩子有點任務沒完成”,她想做出點事。團隊中跟隨她多年的青城楨楠認為,葉檀是一個冒險家,“她本人是社恐的,做企業要對人管理,要去見投資人,是一種更高的挑戰。”
近幾年,她不斷強調自己創業者的身份,而不僅僅被定義為評論員。“看別人做企業總是很輕鬆,各種挑刺,還不如自己去做,到市場裏去游泳。”不創業她可以過得很好,但她迫切地想要看看自己有沒有做企業的能力。
作為創始人需要找項目找合作,她強迫自己去跟人應酬,把應酬也當作必須完成的一項工作。飯局社交,她不擅長説虛話,不懂得推脱,認真的勁頭上來,別人敬酒讓喝多少她就喝多少。只要答應了完成這個工作,即使身體再難受,她也會堅持到底。
她不斷給自己加碼,定目標,往死裏向目標靠攏,到不了就會不斷覆盤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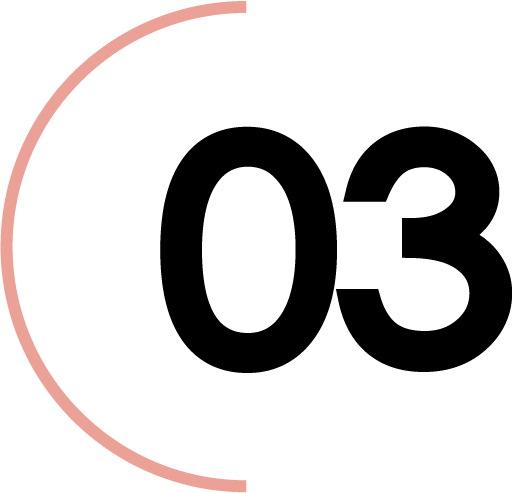
拼命工作,然後呢
2022年,用葉檀的話説,就是“一把劍懸在每家公司頭頂。”出不了門的幾個月,她感到焦慮,每天睜開眼,十幾萬要出去,公司上百號員工要吃飯,卻一分錢也進不來。
她在一篇文章裏寫道,疫情期間無法和合夥人、投資人見面,其他線下業務也驟停。怎麼辦,“要活下去,必須革自己的命。”她帶着團隊轉型,做起了新業務——線上直播。
每週兩場直播,下線後她還要拉着團隊做覆盤。從視頻的畫面,燈光,色調,到標題的字號,每次都有各種各樣的細節問題。葉檀稱自己是一個完美主義者,“覺得每件事情都很重要,都要處理都要去做,什麼事情都快、要完美。”
葉檀對自己極為苛刻,做事嚴謹。團隊的成員提到一件小事,有一次她和外部的團隊合作做一門課程,她邊錄邊修改,最後幾乎是全篇推盤了。只要從她手裏出去的內容,小到100字左右的直播預告,她都會親自把關。
對於員工來説,如果能力達不到她的要求,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她的要求極高,文章裏一些遣詞用句是不是有待推敲,數據引用至哪裏,有沒有錯別字。很少有人具備和她一樣的文字天賦,也很少有人與她的步調保持一致。參與到團隊中的人,不乏她的仰慕者,或看着她的節目過來的人,但工作就是工作,每個人都領教過她的高壓。
作為老闆,她看中結果,文章閲讀量和傳播量是最直接的評判標準,她追求增長的數字,在意外界的評價。
因為工作太狠,每天熬到凌晨,大概20年前,她就已經患上失眠症,需要藉助藥物睡覺。她從未休息過一天,永遠保持着戰鬥的狀態,緊繃着神經,直到這場大病出現。
當一個巨大的痛苦來臨,她的第一反應是沒感覺。那是一種麻木和抽離的狀態,壞消息太多,大腦接收不過來。住院,全面檢查,全身PET-CT、血檢、心超,穿刺……穿刺的時候做了局麻,她聽到醫生嘟囔了一句,太硬了太硬了,針都歪了!
葉檀內心有點慌張,又有點不可思議。命運的弔詭之處在於,以前她總是自己做選擇,強調獨立,現在,疾病由不得選擇,無論多麼不情願,無盡的時間,她困於方寸之牀。
她唯一要的就是我要活下去。
第一次會診,醫生説首先要治療的不是胸部,而是骨頭,骨頭變成空洞,就像被蛀蟲蛀了一樣,她面臨的是可能的高位截癱。治療了三個月,醫生説有好轉,又三個月,化療、靶向治療很快見效,她和骨水泥手術擦肩而過。半年到12個月,她的骨頭從白花花的一片到正常的黑色,從勁椎胸椎到腰椎,形成了一副完整的骨架。醫生説這就是一個奇蹟。
活着,成為她最大的武器。
“有人得了同樣的病,做出了同樣的努力,甚至更努力,但是應答不好。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得到什麼樣的結果,有個人努力的成分,但最重要的是運氣。” 對於這樣一個治療結果,葉檀認為自己很幸運。
她結結實實地在死亡邊上走了一遭,悚然感到自己是要死的,人終有一死,那一切還有什麼意義?人生的前50年,她無比積極,與一個向上的時代迎頭碰撞,不僅自我成就,甚至感受到了自由。
所以當巨大的疾病來臨,可以想象她有多麼迷茫,過去建立的價值感和意義感都被打破了。復出工作後,每一位來訪者都會問她一個問題:這麼拼命工作,後悔嗎?
在大眾視野裏20多年,她不曾向外界展示自己,她一直小心防備。一個冬日的早晨,在家裏的二樓,她靠在椅子上,語氣緩慢地接受訪問。她做好準備了。
她的回答是:如果回到過去,我仍會是那個狀態,我不後悔。

圖/葉檀坐在家中的沙發上
回溯奮鬥的前半生,葉檀做的每一次選擇都充滿了與時代的共振。
她生於1967年,在杭州,母親生下3個女兒,她是長女。她經歷了文革,但對於那個遙遠的年代已經沒什麼記憶。到了讀書的年紀,恢復高考,當時的社會氛圍推崇知識改變命運,即便家裏都是女孩,她沒有感到被歧視。沒有人約束,她照着自己的興趣去探索。後來她考進復旦大學,那個年代這是很高的起點。在媒體的黃金年代,言論百花齊放,她個性張揚,就像魚找到了水。再過十年,社會掀起創業浪潮,傳遞的信息就是鼓勵個人去奮鬥去拼搏,拼搏就會有回報。她理所當然地去創造新的世界。
成功由什麼因素決定,很難説。歷身期間,很難不讓人對命運產生困惑。離開體制,去做評論員,她説當初做選擇的時候對未來一概不知,“很多人跟我説不可能,在國內就沒有這樣的評論員。等我寫了一段時間,很多人又説沒有必要這麼做。”多年後,她才意識到能做選擇是“奢侈”的。“那個時候還能吃上一口飯。我有更多的餘力去夠到更高的東西。”
在財經行業沉浮多年,葉檀明白,很多風險是不可控的,歷史有大週期、小週期,人也一樣。今天從影響社會這個更大的層面來看,個體的力量還是太小。
“人在時代裏浮沉,努力是一部分,運氣是一部分,要承認自己的侷限。”

第二次生命,“做好該做的,剩下交給老天爺
停止化療的當天,葉檀想做的第一件事很簡單:每天走一萬步。一萬步對她此刻的身體來説,是不敢奢望的數字。愚公一般,她每天幾百步幾百步地挪着。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她能走上三千步、五千步。走着走着,一萬步就到了。
她仍然對自己要求很高,只不過轉換到了另一個人生軌跡。她為自己鼓勁,為恢復體力堅持鍛鍊,身體給了她另一種回報。
今年4月,醫生建議她恢復部分工作。她素顏,包着頭巾,重新出現在公司。團隊的成員們才知道她經歷了什麼。不止一位同事驚歎於她的精神意志力強大,“沒有強大的心態、沒有極大的信心,是不可能恢復這麼快,普通人談癌嚇都嚇死了。”疾病沒有讓她強悍的靈魂撼動絲毫。
生活被一場大病改變,很多工作被迫停止,她逐漸對自己“鬆綁”。“每天去做的一定是事務性的工作,而不是有意義的工作,有意義的事情,做一兩件就可以。”
什麼是有意義的事?得病後她為這個問題惶惑不已,陷入了精神危機。她一度懷疑自己,“過去幾十年的努力辛苦,是不是全部白費了,我還不如過上平常的日子,我生一個娃,我就成功了。”生病後身心都太脆弱,她想到自己的遺憾,想到為工作所付出的代價,她想在生命的最後抓住一些東西。
人生就是這樣,不是所有的代價都能償還。葉檀後來想,如果説我有一個孩子,什麼問題就解決了,那這個世界也太簡單了。
她想弄明白,為什麼焦慮。“每天都在想,第二天要做什麼,下個季度要做什麼,再下一個年度要做什麼。”她追求財富也認可財富,一個獨立的個體,必須可以“自負盈虧”,存夠錢才有抵禦風險的能力。但人的用度是有限的,“有什麼安全不安全?如果你的感受好了,錢少一點,你也會覺得安全。” 想清楚這些問題之後,她的不安全感下降了。
她也開始卸下心裏包袱。以前,她説,“只要女俠二字,還在我身上,我覺得,我就應該肩負起財經女俠的重任。”“女俠”的標籤戴着身上太久了。現在,她覺得完成了當時的使命,迴歸普通人, 重度失眠二十年後,她學會了好好睡覺。
但有些堅持還存在。復出後她拍攝的第一條視頻,第一遍她沒有化妝,沒有穿對衣服,感覺不對。團隊們又去她家重新拍了一次。對內容的質量,她會一直堅持。
公司不能不管,她在考慮目前的能力能做多大的事。許多事她學着放手,不跟自己較勁。生病之後,她開始慢慢理解許多人在工作上無法做到如此。“放手他們會摔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不強行介入他人的因果。”身體原因、家庭原因對工作的影響,成為她逐漸能夠感同身受的事情。
每三個月,葉檀要去醫院複查一次,她將這一過程形容為“拆盲盒”,頭頂永遠有一個不確定性懸在那裏。每21天,她要進行一次靶向治療,每天要還吃調節內分泌的藥物。她不想給大眾帶來一個幻覺,在院子裏曬曬陽光,擺弄下自己種的蔬菜,看似愜意閒適。這不是常態。常態是她還是要長跑醫院,確保自己的病情穩定滿1年、2年,更長,在埋滿地雷的小路上,走完全程。
疾病本身不是真正的困擾,更多的是內心的傷痛。
身處其中,葉檀遇到了許多和她一樣患病的女性。她們坐在一起聊起病情,甚至職場、生活這樣的私密話題。一位姐妹告訴她,從19 年到現在,已經治療了四年,中間復發,仍每天正常上班。她自己照顧明年高考的孩子,父母照顧着她。等孩子高考結束,她打算帶着父母旅行,好好補償這幾年難言的愧疚。
她也看到了家屬和病友的猙獰,丈夫因為妻子失去女性特徵而選擇拋棄,那是人性幽暗的一面。有的女性治癒多年以後還無法面對鏡子中的自己,那難看的傷疤,以至於不敢去公共浴池游泳。
乳腺癌帶來的切膚之痛,讓她生出更多的悲憫心。葉檀重回鏡頭,第一次在大眾面前,袒露自己的疾病、脆弱、過去的焦慮和漫長的失眠鬥爭。她説,疾病就是疾病,它就是一種不幸,不要過度自責,也絕對不要陷入羞恥感裏。這一次她想要向外界獲取勇氣和信心,“救人也是自救。”
第二次生命如何過,她想把該做的事情做好,其餘的,別人的事情交給別人,老天的事情交給老天。前半生她用工作體驗人生,現在她用人生在置換工作。
今年10月,她去北京見蔡磊。蔡磊曾經是京東的副總裁,現在他是一個得漸凍症的病人。兩個重病的人約定要好好活着。能活着的人,才算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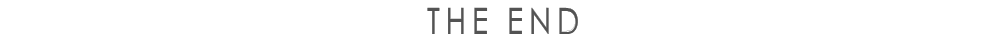
監製 - 她姐
作者 - 周婧
微博 - @她刊iii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