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以色列文化人、知識分子在表達上“更誠實”,跟美歐人比説話更沒有把門的_風聞
梅华龙-北京大学西亚系助理教授-3小时前
我們都知道,如果被貼上“反猶”的標籤,在西方是會丟工作的;我們也都知道,如果反亞裔,在西方是什麼實際責任都不用負的。即便在疫情期間反亞裔變得更常見、更敏感的時候也是如此。
我今天想起的這則舊聞,主要並不是想討論西方的反亞裔、反華傾向。這個話題,三天三夜也説不完。我其實跟大家分享的是另一個視角,即我遇到的一些以色列人“體面人”落後於西方虛偽白左社會幾個版本的“文化敏感性”——翻譯成人話就是:我遇到的一些以色列文化人、知識分子,在表達上“更誠實”,跟處在類似位置的美國和歐洲人比,説話更沒有把門的。有時候我也想不出來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這位音樂家其實並不是非常典型,因為他十四五歲就搬到美國了,之後學習和教學、表演生涯基本上都在美國。我不敢説他這種説話方式是來自小時候得到的、令很多人引以為豪的“沙漠仙人掌”性格,還是他那天喝多了。因為一件事你偶爾説一句,沒什麼;反覆説三遍,那隻能説是捱揍挨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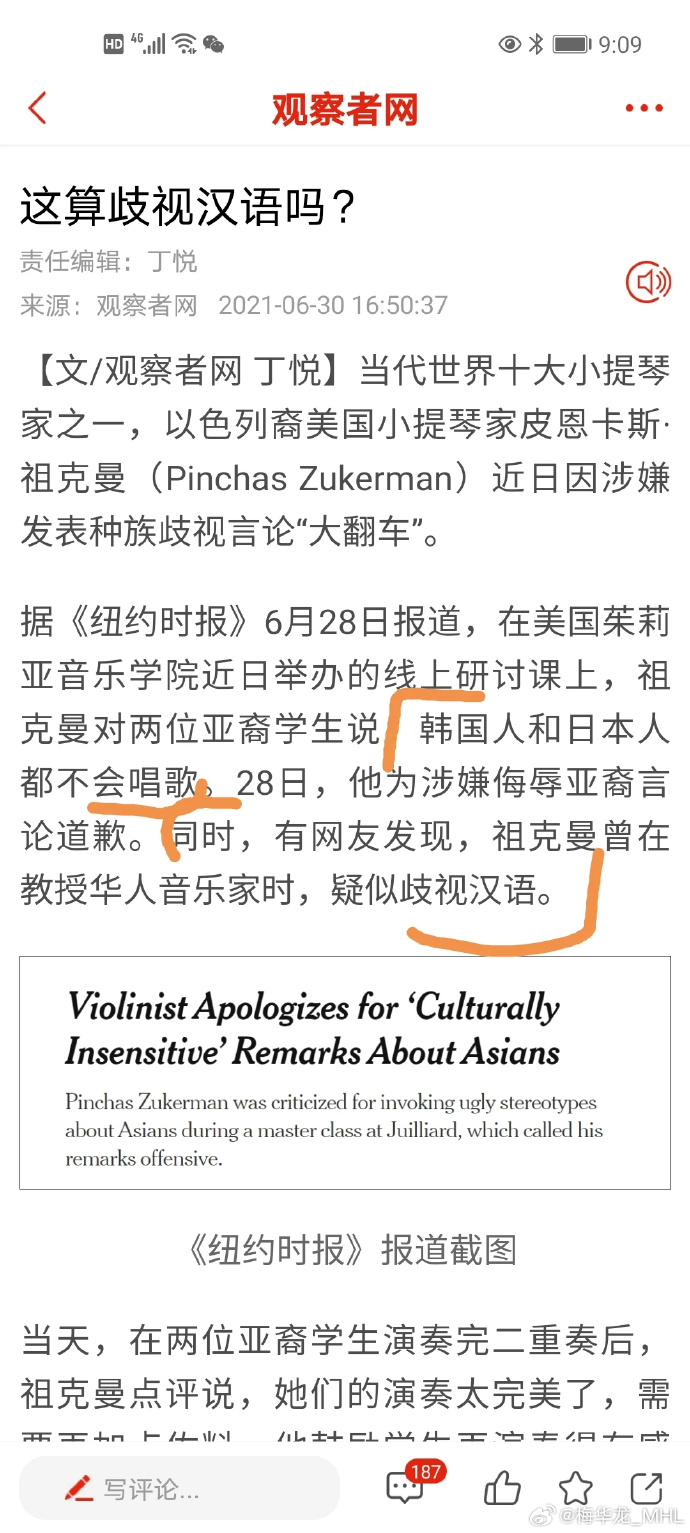
第一次發現這一點是2010年去海法,民宿的主人一看就是一位很喜歡東方主義殖民風情的大媽。我説我們來自中國,然後她表示:我對你們那邊很感興趣,我喜歡泰國。
第二次跟這個類似,2018年出,去戈蘭高地的路上住在一個基布茲裏,主人看起來比耶路撒冷的大部分人都要友好,但他們看見我們時還是忍不住做出了泰國那種雙手合十作揖的動作。
第三次是在去特拉維夫的大巴上,一位大爺看見我是中國人,然後在讀一本古代西亞城邦研究的書,大為驚訝。跟我聊了幾句説:“我知道你以後可以幹什麼,你可以回到中國去教英語!”
我説:為什麼?我也不是學英美文學的。他説:“因為中國人沒有人能講好英語,你講得還不錯。”——我還是沒理解他的自信從何而來。這個大爺還跟我罵普京,揶揄不同的社會制度,還説什麼藏族文化如何如何——直到我告訴他我今天去特拉維夫就是為了跟一位有藏族血統的學弟吃飯,他特別愛國。他終於閉嘴了。
第四次是今年四月份請來的某位女詩人。她給我們做講座的時候提到在上海見到了一位漂亮的小女孩,很有“東方美”——這時候她雙手放在眼角處向上拉起,對着所有聽眾做了一個眯眯眼的動作。所有人都震驚了,真的,憤怒的成分要少於震驚,因為真的沒想到她能當場做這個動作。
在一個連説巴勒斯坦這個詞都屬於反猶的社會,在一個連猶太人都不能要求他們停止轟炸的社會否則就算自我仇恨的猶太人的社會,他們的文化敏感度其實是非常低的。他們只是對自己在意的事情渾身都是敏感點,碰不得;但他們對於亞非拉的尊重是很低很低的,近乎於沒有。這都是教育造成的。
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覺得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在歐美這些明顯受過教育、看上去有點經歷和“品味”的人,大部分是白左。他們很虛偽,但他們在表面上是不敢説這種的。我的導師,一位美國猶太老人,在認識我六年後才敢跟我開關於狗肉的玩笑,我也沒當回事。因為至少一開始人家對我是完全當成和其他人一樣去對待的,不管心裏怎麼想。
在美國那些年我只遇到過一個特別蠢的種族主義者——我假定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種族主義者,但那麼蠢的很少——是我導師一門課的助教。那時候我還是碩士生,還要申請博士。有一次我下課想去問他一個問題,他趕時間,但人很禮貌,一直回答我問題。這時候那個女助教正義感爆棚,找了個機會讓我導師走了,然後把我攔了下來,我覺得很不解。我説,教授還沒説完吧?
她説:他下節課在harvard yard,很遠,中間只有幾分鐘,他要遲到了。
我説,哦那好,我不知道他下面還有課。
這時候這個大姐突然跟我説了兩句日語。我瞪了她一眼:我是中國人,日語我不會幾句。您要幹什麼?
她説:你不會日語嗎?我以為你們的語言差不多。我在日本生活過。我瞭解你們的文化,你問他問題是為了留下個好印象,因為你還要申請博士。
我説:我問問題是因為我那塊沒聽懂。而且我想再説一遍:我是中國人,我們的文化和日本的文化不一樣,而且我相信你也不懂日本文化,否則你應該知道日語和漢語不甚相同。你的話很侮辱人,屬於種族主義。
後來我告訴了導師,導師找她談了談,我不是那種天天叫什麼種族主義、反X主義的人,我沒有向學校反映。
但我想説的並不是美國人(她不是猶太人,她老公是;她是基督徒)多麼反華。我也不想強調某些以色列人多麼反華。我其實這些年來一直覺得最有意思的是,為什麼跟我打過交道的以色列人那麼少,美國人要多很多,但這種愚蠢種族主義者要多好幾倍。
我想,這或許跟以色列還沒有完全白左化有關係。即便是這裏面屬於知識分子圈子的人,説話也沒有美國那些條條框框。這種條條框框是來源於表面和平的——因為黑人、亞裔、原住民、拉丁裔屬於絕對意義的被壓迫者,所以表面可以要求體面。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矛盾仍在進行中,雖然佔絕對優勢,但巴勒斯坦人的人口比例還是太高了,所以這種對立感就更強,白人移民—殖民社會的真正底色就更明顯。
其實針對亞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包括而不限於疫情期間以色列媒體和普通人的對華歧視),我見到的以色列人評價其自己人,也是口無遮攔的,把歧視寫在臉上不加掩飾。
比如2010年我結識了好幾個語伴(那時候那邊的中國學生不多,那幾個東亞系的一起來找我練漢語,我練希伯來語)。其中有個男生跟我説:那些正統派,哈瑞迪,他們下的崽子太多了,是社會的累贅。我很驚訝地看了看他:你用的是“下崽”這個動詞?他説是啊,他們不配當人,他們生那麼多,也沒拿自己當人……
有時候你覺得他們的説話方式和八九十歲的老爺爺老奶奶或五六歲孩子差不多,有種沒經歷過當代人類社會影響的感覺。白左化較低,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覺得未必都是壞事。説實話,想起以上那些不愉快,其實我並沒有很不愉快。我覺得以色列社會一些看起來比美國好的地方,可能也與這種低白左化有關。比如在美國認識的一個以色列同學就直接説:在你們美國還要花錢在網上看電影?在以色列直接下載,什麼版權不版權的!
而且他們的學者比美國知名高校的學者架子要小很多。我的感受就是在那邊跟教授混熟比在美國容易,美國(所謂名校)的教授則更容易文質彬彬而高高在上。其實,這説明這個社會還有樸實的一面。當樸實的一面沒有被好好引導,或被帶歪了的時候,可能呈現出我們現在看到的無理取鬧、瘋瘋癲癲、缺乏同情心、巨嬰心態、自我中心,但如果方向被帶正了的話,則不管某些以色列精英想多麼擁抱西方,但其實他們跟很多西方國家相比還是更有點西亞傳統文明社會的樣子的。沒有那麼受西方政治正確那套的影響。他們只需要多學學真正的傳統文明,把善解人意、禮貌和好客學來,嘴巴大不大其實不重要。
我有位很喜歡的以色列阿卡德語老師,長得跟德國兵差不多,跟我爸同齡。他幫了我很多。左翼,覺得錫安主義沒救了。他説話的風格也是非常驚人的。他有一次跟一個羅馬尼亞同學説:你們那邊是不是不買那些電子產品?我記得羅馬尼亞有點窮。然後對方瞪了他一眼……當時課上有位天津學姐,使用英文名,他每次點名回答問題都會揶揄:你箇中國人為什麼給自己一個美國名字?
還有一次他問我在中國大學都有什麼課。我説我們有這有那然後還有體育課。他不以為然:大學生學什麼體育?我年輕時以色列學生也要做操什麼的,有什麼用?你是培養學生還是培養驢?驢的體育肯定比你們好。
他的説話風格疑似是有點太超前了……但這個國際班的學生們(美國人、韓國人為主)都很喜歡他。
他真的不是壞人,不僅在推薦信方面幫我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我旁聽了一學期,最後被他“轉正”了,拿了學分和成績。不僅如此,他好像和餐廳的某個巴勒斯坦清潔工大叔關係挺好,每次賣不出去的三明治,都在他的課上被扔到教室裏,一筐一筐的(因為他的課很晚)。然後他會拿一個吃,然後還告訴我們:有免費晚餐還愣着幹嘛啊?
他的揶揄態度是對所有人的。他年輕時因為和導師打架,所以沒有博士學位,只是Mr。所以他反覆要求大家叫他名字:我不是博士,也不是教授,我只有一個名字。
他還會自嘲自己失敗的婚姻:別看我兒子多,可我老婆少啊。一個都沒有。
所以,是不是這樣:只要自己選擇一種更平等的價值觀,他們的大嘴巴和不敏感就會換一種風格?當你平視其他人同時大大咧咧時,大家覺得你是個不太會説話的好人;當你歧視大家然後大大咧咧時,你的每次無心之舉都會變成新的罪證。
所以説那個社會是有救還是沒救呢?其實都看他們精英一念之差了。(第二個標籤指:看見具體的廣義巴勒斯坦的猶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