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惡人,全靠他救活了_風聞
Sir电影-Sir电影官方账号-12-02 08:48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
7天,730萬人看過,累計票房3.1億。
這就是曹保平新作《涉過憤怒的海》的成績,也是在國慶檔之後處於冷靜期的國產片市場的最好成績。
而且,至今仍處於票房冠軍的位置。
曹保平贏了。
他不僅準確無誤地戳在了觀眾的G點上,還看似跑贏了審核,把“大尺度”直接打在了銀幕上。

如今,作品好於90%的犯罪懸疑片。

也讓國產片終於有一部作品擺脱了“有噱頭,沒有內容”的短劇式大爽片。

但與此同時。
他也站在了爭議的風口浪尖之上,包括“父親”,包括“二次元”,片中的許多情節設計,都引來了一部分人的不滿。
為什麼我們對曹保平的電影欲罷不能的同時,又會很容易感到不適?
今天,Sir就想聊聊曹保平。
一個本該是“大多數”,卻最終成了“稀缺品”的導演。
01
和審查“對抗”的人
對很多人來説,曹保平就是個“刺頭”。
他曾説過這麼一個故事:
在上大學的時候,有一次老師要求他們交短片作業,於是他寫出了這麼一個場景:有一個生病的女孩住在筒子樓裏,隔壁,有一對情侶在做愛,而女孩,則拿了一根葱和兩個雞蛋準備給自己煮麪吃。
低俗嗎?
曹保平不這麼認為。
但結果,還是被老師罵了一頓,説他故事有隱喻、格調低,思想境界不高。
無獨有偶。
在他參加工作之後,類似的事情又發生了。
有一次,他寫了一個劇本《紅棉襖,紅棉褲》,把一個抗戰故事寫出了另一種風味,“寫地主一家在那個時候,共產黨也不敢得罪,日本人也不敢得罪,因為日本人住他們家裏了,他就兩頭虛與委蛇,委曲求全,最後一家全被殺掉了。”
現在看起來,就像是另一個版本的《鬼子來了》。
但。
最後劇本被拍成電影之後,將劇本里黑色的、殘酷的部分刪了,關鍵時刻展現人性抉擇的部分被一筆帶過,變成了一個英勇抗擊日劇的主旋律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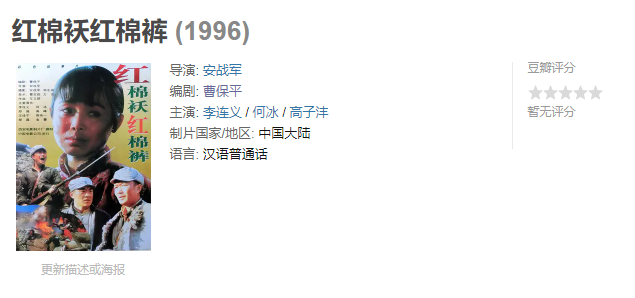
所以你看。
無論是“生病”和“做愛”兩種生命狀態的對比,還是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人性展示,對於“審查者”(老師或導演)來説,都是不合時宜的。
這使得他每走一步,都會遇到重重關卡。
一個例子。
成名作《光榮的憤怒》。
在電影前期,這部片一直卡在劇本審核上,他在接受《南方週末》的採訪時“吐槽”説:“電影管理部門給羅列的意見多達幾十條,比如:怎麼可以這樣描寫黨的最基層支部書記,他會那麼猥瑣,他會那麼雞賊,會不擇手段,靠欺騙人把4個村霸打倒呢?而光天化日之下,又怎麼可能出現那樣的鄉村惡霸呢?”
怎麼可以,怎麼可能。
就是這些“不可能”讓《光榮的憤怒》拍出來後,出現了狗尾續貂的“天降神兵”,他彷彿只講了一半的精彩故事。
而之後呢?
《李米的猜想》,因為投資商的要求,刪掉了50分鐘的戲份。
《烈日灼心》,因為死刑場景,他又不得不再次刪減和調整。
就連《追兇者也》,一部喜劇犯罪片,也刪掉了一段王友全和女友在天台上的激情戲。
至於《狗十三》和《涉過憤怒的海》,一個是拖了5年才上映,一個是壓了4年才公映,其中的曲曲折折,到底遇到了什麼樣的麻煩,更是無人知曉了。
可以這麼説。
曹保平每一次,都會像個不聽話的“刺頭”一樣不停地挑戰着審查的底線,或是“隱喻”,或是“格調”,或是“思想境界”,總之就是在可與不可之間反覆遊走,這讓許多人“頭疼不已”。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
Sir覺得,還是因為他所關心的對象的緣故,無論是生病的女孩,還是騎牆的地主,他們都是“負能量”的形象,甚至於,如果你看過《烈日灼心》,可能會記得一大羣主流社會排斥的邊緣人羣。
仔細看下面這個場景。
假軍人、吸毒者、肇事者、超生者、小蛇頭、刻私章、製毒藏毒、電話詐騙者、假藥販子、小姐……

一個又一個。
於是曹保平就像影片中那個偷聽的房東一樣,牢牢地記住了這些人。
比如“殺人犯”,也就是《烈日灼心》;“製毒藏毒者”,也就是《她殺》;“復員軍人”,也就是《涉過憤怒的海》(現在版本中已經刪去了老金的這一身份設定)。
這便構成了他的“灼心三部曲”。
是的。
相比於正能量、大團圓這些詞,曹保平感興趣的東西恰恰相反。
所以與其説他是與審查對抗。
不如説,他是更關心那些被遺忘、被歧視、被這個社會所不容的“底層人”,並在他們身上,找到人性的扭曲之處。
這也是為什麼他與同為第六代的導演相比,賈樟柯、張元、王小帥、婁燁,風格差別太大的原因。
他重故事,“愛”惡人,別人重自我表達。
就像是本《故事會》,與《詩歌精選》這些雜誌混在報刊亭裏,顯得那麼與眾不同。
02
演員的“絕望”
所以如果用一個故事來形容曹保平的風格,Sir覺得,可能還是很多年前,他在當老師時讀的那個故事。
那一次,他是在編劇課上,讓同學們花15分鐘寫一個聽過最有價值,必須是真實的故事。
在第二堂課。
他念了覺得最好的一個故事——
哈爾濱郊外的下午,夏天,天氣炎熱,有一條土路停了一輛堆滿西瓜的卡車,天太熱了,父子倆決定躺在車底下睡覺。睡了一會兒,兒子説,爸爸我渴了,我要吃西瓜。爸爸説,我們的西瓜是賣的,不能吃。爸爸看見路邊有賣西瓜的,賣得比自己的西瓜便宜,他説,你等着我給你買西瓜去。正在買的時候,卡車的手剎鬆了,車突然往下滑,正好壓在兒子的大腿上,把腿壓斷了。爸爸聽見兒子一聲慘叫,回頭看見很多人在幫忙把車頂住,不讓車繼續滑。爸爸大喊一聲,給我讓開,開到倒擋,並沒有停車,而是從他兒子腦袋上軋了過去。爸爸説,你們報警吧,我們家太窮,真的養不起殘廢的兒子。
來源:《影帝制造機”曹保平》|界面新聞
是的,這個故事戲劇衝突很強,但又隱含着“真實”,為什麼躺在車下睡覺,為什麼去別人的攤位買西瓜,為什麼要軋死親生骨肉,本質上其實只有一個字:窮。
窮困,會讓人徹底絕望。
老實説,這樣的故事很少有人會拍出來,畢竟人們害怕一個故事不真實,但同時,又害怕故事太真實。
而曹保平恰恰覺得有價值的只有後者。
於是。
你在他的電影裏,可以看到各種幾近癲狂的“絕望感”。
這會讓演員覺得很痛苦。
就如黃渤説的,《涉過憤怒的海》的劇本就像一杯釅茶,雖然人的感受程度不同,但每個人喝第一口的時候都會打一個激靈。
在一天的拍攝結束後,黃渤會找人喝酒聊聊天,“不能一直待在電影裏邊,時間長了會憋得很難受。”
郭濤説,“拍《烈日灼心》這部戲我心很累,就像經歷了一場災難一樣的感覺,你沒辦法解脱。”
鄧超在拍《烈日灼心》時,在拍攝最後執行死刑的那段戲,是真的有專業醫生拿針扎進靜脈裏注射,他説:“我在那個時候是回不來的,就是我躺在上面抽抽抽……沒了。全部都是那樣一個極致的狀態,我的眼睛也閉不上了,然後一個眼睛大一個眼睛小;臉部的肌肉都痙攣得亂七八糟了,那個樣子我也預料不到,我也沒有做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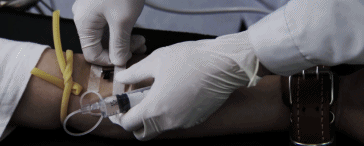

為什麼會這麼極端?
因為他的劇本的底色,人物角色往往都會進入一個極端環境中,並進行一個毫無希望的反抗。
因為在他的鏡頭裏,角色本就身處一種無法自拔的生活漩渦之中。
在《涉過憤怒的海》開頭,老金一直盤算着自己一艘漁船能掙多少錢,一隊漁船去掉工人的花銷,又能掙多少,夠不夠女兒留學。
這與《烈日灼心》裏陳比覺算着伊谷夏幫他們還的醫療費,或是《李米的猜想》裏李米念着男友寄來的信上,郵戳的數字,如出一轍。
他們都沉浸在自己的小算盤裏。
嘀咕一些旁人都不知道在幹什麼的算式。


鏡頭裏的人,有的為學費,為了醫療費,為了找男朋友…….
這些算式是他們的生活的奔頭,也是他們對渴望的東西、生活,痴迷的狀態。




他們“軸”。
並且都妄圖在生活中尋找一個出口,可最後,也是徒勞,是被迫認命。
但,他們又沉醉於盤點這樣的算式,不論何時何地,想起這些數字,反而感覺愉快。
他們將算式當做困苦生活裏的“嗎啡”。
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既定的無望的命運,註定與自己的親人、愛人失之交臂。
但,還是願意停留在這樣的“臆想”中。
這也是熱衷於描寫“絕望”的曹保平,隱藏着的“温柔一刀”。
導演看似讓人物面對自己的命運有自由最大化的選擇,可命運卻又以另一種方式駛上了它既定的軌跡。

但,其實,他們的命運也如牲畜一般,掌握在別人的手裏。
03
人本就是動物
沒錯,在Sir看來,在曹保平的鏡頭下,他往往拍的不是“人”,而是“動物”。
他試圖找到人身上的“獸性”。
一方面,你可以把它當做一種隱喻。
比如,《狗13》。

鏡頭多次將少女李玩與一隻叫愛因斯坦的狗放在一起,少女與愛因斯坦一同長大,在丟了狗之後,急瘋了的李玩在院裏“汪汪”地叫着。
彷彿她已經知曉叫回愛因斯坦的語言。

所謂狗,何止愛因斯坦一隻?
或者,《烈日灼心》。
那三隻分別叫白雪公主、葫蘆娃、小巫婆的小金魚並非閒筆,它們是故事重要轉折之處,也隱喻了對應的人物。


三隻跳出魚缸曬死的小金魚,也成為了辛小豐他們三兄弟未來的走向——在即將“缺氧”的環境中,為了求生,只能殊死一搏。

甚至《涉過憤怒的海》裏,人,也是魚。
在電影裏,小娜的生日正好是日本的男孩節(五月初五),導遊介紹,在這個日子裏,家家户户都會掛鯉魚旗。
爸爸,是黑色的鯉魚旗,母親,是粉紅色的鯉魚旗。

小娜在神社裏將所有硬幣拋進水裏希望神能給她賜下滿滿“緣分”,下一個鏡頭,就是一支黑色的鯉魚旗,慢慢地沉到了水缸裏。
這也是小娜父親的鯉魚旗。
與此同時呢。
另一方面,“動物”,也是人去除了現代社會賦予的“人性”之後,最本能的反應。
人性不過是獸性的保護色。
就像《烈日灼心》裏。
道哥與伊谷夏其實是兩隻老虎,互相搏鬥。

或者《涉過憤怒的海》裏。
周迅飾演的景嵐**,彷彿一隻母狼。**
景嵐為了護自己的“惡童”兒子, 她所表現出來的那股遇神殺神的勇氣,以及在最後,得知兒子可能被殺後,撞死老金未果,自己也開車衝下山坡。

當老金追得越緊,她“女人”的身份就越削弱,她大紅色的口紅沒有了,耳朵上的耳環越變越小。
也是在此時,齜出獠牙,顯露本色。


《烈日灼心》裏,有這樣的一句話:
在我眼裏,人是神性和動物性的總和
就是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
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惡

人,本身就是具有動物性的。
在許多文藝作品中,人面對極端的處境時,會規束自己的行為將理性壓制於動物性之上,與“天性”、“動物性”的搏鬥,最後,成就“人”的理性至上。
但,曹保平的電影裏,他將人性與動物性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中,並沒有孰高孰低的判斷,甚至,有時候還有共存的時刻。
像是《追兇者也》裏的這個橋段。
買兇者掐住殺手的鼻子,責怪殺手辦事不牢,買兇者咄咄逼人,兇手礙於“買賣”唯唯諾諾,此時是“人與人”之間的較量;
但,當喘不過氣的殺手揮手就是一刀,劃破買兇者的頸動脈,此時又變成了“動物”之間的較量。

一瞬間,人與動物的形態,瞬間轉換。
在這裏。
不論是什麼地位,什麼身份的角色。
最後它沒有好人,也沒有壞人,就只剩下“人”最本能的“動物性”。
他彷彿撕開了人生的虛無與無奈。
告訴我們:
**人與世間萬物一樣,不過也是在服從命運的安排,**在無數的偶然中,走向了既定的必然。

04
挑釁觀眾的人
這樣拍出來的故事,註定是會引起爭議的,它從根上就不會那麼“正確”。
就拿少數羣體來説。
曹保平在當年的《烈日灼心》裏就拍過少數羣體的生活,那次是同性人羣,本該是國產電影形象的一大突破,可依然有人覺得,這是在獵奇與消費他們。
同性元素充滿了獵奇式的消費
台詞就差把恐同寫在腦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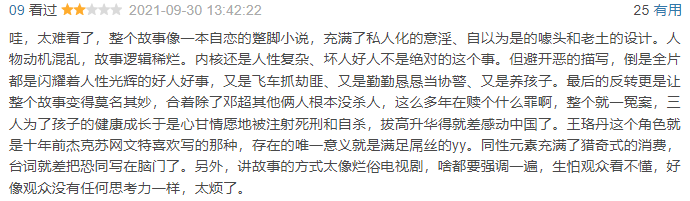
而到了《涉過憤怒的海》,更嚴重了,因為電影裏出現了coser的形象,就有人覺得這是對二次元羣體的抹黑。
不尊重二次元文化
更不尊重受原生家庭傷害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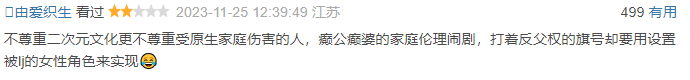
是在消費或者抹黑嗎?
倒也未必,因為在他的電影中,他一直是無差別地“挑釁”所有人。
包括觀眾。
其實從影像呈現來説,曹保平的犯罪片更像是處於日片與韓片的中間地帶,都是底層犯罪,韓片重視覺刺激,日片重人性挖掘,而曹保平呢,兩個都要。
他既要有可以刺激的觀眾的視覺衝擊。
也會在讓觀眾不舒服的時候表達自己的思考。
舉例來説。
曹保平會把最醜陋的東西,直給到你的面前,讓你不舒服。
比如直視人的本能疼痛——
在《烈日灼心》裏,阿道自己給自己縫針的場景,將鏡頭直接拉成大特寫。

比如把牀戲拍出“醜陋”——
沒有浪漫、沒有愛情,更像是以一種有目的而為之的慾望宣泄,慾望成了人物走向極端的內在驅動,就像《涉過憤怒的海》裏,其實是雙方互相壓制與征服。

他甚至想在《烈日灼心》裏,將屍體高度腐敗的“巨人觀”呈現出來,最後因為費用太高而放棄了(還好沒錢 )。
)。
他是真狠啊。

與此同時。
他也會時刻挑戰着你的“三觀”。
渣男,最後贏得了痴心女友的寬恕;殺人犯,獲得警察的憐憫,甚至一度還能成為“好人”;殺手,殺人的目的,是想與女朋友過上穩定的日子;父親,自私地只為保全的尊嚴,並不愛自己的孩子。
……
所以是故意製造“奇觀”,以達到聳人聽聞的效果嗎?
確實,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影片就很容易兩頭不靠,要麼變成獵奇的展示,要麼變成獸性的宣泄。
但在多數情況下。
曹保平還是做到了與那些為了“大尺度”而大尺度的電影不一樣,他在這些不舒服的背後,表達出了一種真實。
台灣影評人焦雄屏評論曹保平的電影風格——
從現實主義出發,逼近角色審視其生存狀態,在痛苦和沒有出路的僵局中迸現人性,而且自始至終沉浸在悲觀的氛圍中,這是中國式的黑色電影。
真實與荒誕共存,生活與求生之間拉扯,突破現狀與安於保命的糾結。
最後,便釀成了曹保平電影裏的底色——
悲劇。
老實説。
如果單純從電影創作的角度來看,這些其實也都不稀奇,畢竟每個國家(地區)似乎都會有這樣一批創作者,在商業和藝術,大眾與小眾,視覺與深度之間尋找平衡點,形成自己的風格。
就像90年代的邱禮濤,或者拍出《看見惡魔》的金知雲。

他們看似拍出了一種毀滅性的快感。
骨子裏表達的,卻是人性的複雜。
而這樣的作品,本該是一個國家(地區)犯罪片裏的大多數,是一種常態的。
但可惜。
國產片裏,我們只能見到一個曹保平。
或許是因為審查。
或者是因為商業。
甚至是因為我們不敢違逆主流的三觀。
我們的電影總是在緊跟着大眾的刻板印象,不容許出一絲偏差:好人只能純潔無瑕,不然就是心懷不正,壞人不能獲得成長,不然就是給他洗白,人們小心翼翼地順從着這個社會的情緒,並靠着這種迎合,獲得票房,獲贏得流量。
而這。
恐怕也是為什麼有人即使對《涉過憤怒的海》不太滿意,但依然願意推薦的原因。
我們這樣的電影,這樣的導演,實在太稀缺了。
説到這裏,Sir忽然想起曹保平作為演員,出演的一部致敬庫斯圖裏卡《地下》的短片來。
那是一個電影拍攝的場景。
曹保平頂着個爆炸頭,飾演着一個吹着小號,一直在原地轉圈的演員。

攝製組精益求精。
每一個道具每一個場景都必須精確地復刻出原版的精髓。
可忽然。
有一羣穿着白大褂的人衝了進來,制止了這場拍攝。
這時候我們才知道。
這羣努力的電影人,包括管虎、曹保平、張元、唐小白、郝傑……不過是一羣精神病院的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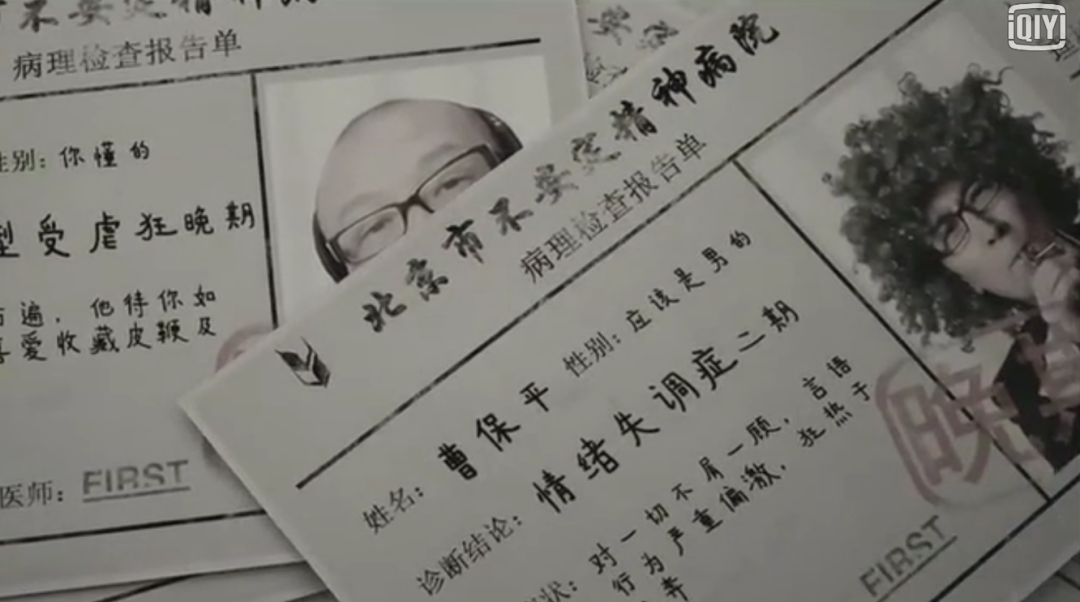
瘋子是不容於世的,他們遊離於這個社會體系之外。
但同時。
就像《鬥牛》裏黃渤飾演的牛二,《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古倫木,又或者像新片《河邊的錯誤》瘋癲的羣像,他們的瘋言瘋語,説出一個時代的真相。



如今。
這個社會上,小心翼翼守着每一個規矩的“好學生”太多了。
所以我們會珍惜每一個“瘋子”。
電影需要“瘋子”。
否則千篇一律的迎合與妥協,也實在太無聊了。
而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
何嘗,又不是如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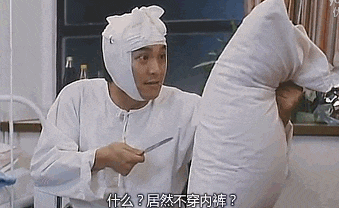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點擊閲讀往期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