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拿破崙》是拍給誰看的?_風聞
前益-12-08 00:29
同樣是半個歐洲踩在腳下的人,又同樣是在失敗於遠征俄國,拿破崙和希特勒究竟有啥區別?
有一種人,認為沒啥區別,都是暴君。
另一種,慕強者,也認為沒有區別,只要是強人,無論是秦始皇,還是拿破崙,希特勒,風雲際會大一統,他們就崇拜。其實,拿破崙,跟希特勒、袁世凱有啥區別呢?都是在共和國裏當皇帝的竊國大盜麼
英國人雷德利·斯科特拍了一部電影《拿破崙》,其實反應的就反映英國人如何看待拿破崙的,《拿破崙》的片尾字幕中,閃過拿破崙歷次戰役當中的傷亡人數,加這一段是為了幹嘛呢?無非就是為了説明拿破崙折騰這一番,死的人不少,實屬罪孽深重。

電影《拿破崙》遭到全世界拿破崙粉絲的聲討,這些強人崇拜者,原本希望看到一部體現拿破崙雄才大略和魅力的鴻篇鉅著,結果卻看到了一個糟糕至極的蹩腳野心家情史。於是,電影遭到了輿論的炮轟,除了英國,在導演的故鄉,相當多的影迷稱讚這部電影的精良,並認為電影重現了他們眼裏的拿破崙皇帝形象。
拿破崙瞧不起英國人,説那是“小店主的國家“,英國人也瞧不起拿破崙,從19世紀一直延續到了今天。電影《拿破崙》當中也多次提到“克倫威爾”這個名字。在大多數英國人看來,拿破崙充其量就是他們歷史上“護國公”克倫威爾的翻版而已。有什麼了不起的?
在法國,以及很多地方,拿破崙被視為英雄,享有盛譽,為人所傾倒。但在英國,卻出奇地沒有多少令人着迷的感染點,英國人所銘記的,反而是他混亂的情史和糟糕的戰敗結局,以及尤其令英國人厭惡的殘暴獨斷之帝王形象。
英國人之所以如此貶損地看待拿破崙,是有其資本的,不論拿破崙的崇拜者如何渲染其軍事奇才,但拿破崙不僅僅自始至終都未能在戰場上擊敗英國,而且最終被英國人在戰場上擊敗,且淪為英國的囚徒,面對拿破崙,英國人為什麼要崇拜他?
不僅對拿破崙,英國文化界歷來對軍事統帥,凱撒式的征服者,都不那麼推崇。
英國人曾經幾乎征服整個世界,在其征服世界三百年的戰爭中,英國湧現出無數驍勇善戰的軍事征服者,打敗西班牙的德萊克、擊敗路易十四的馬爾波羅、征服印度次大陸的克萊武、征服北美大陸的沃爾夫。但這些戰功赫赫的軍事梟雄,在歷史上幾乎沒有知名度。威靈頓公爵的威名,則是得益於西班牙人和法國人甚至俄國人的記憶,英國人自己是不太在乎的。
我們很少能夠看到英國電影或者小説歌頌自己的軍事英雄,三百年來,儘管英國有着百戰不殆的軍事成就,卻從未有多少軍事英雄被大眾文化所銘記。德萊克、克萊武和馬爾波羅治下的英國軍隊真正征服了世界,但又有多少人知道?相比之下,拿破崙、庫圖佐夫和腓特烈大帝則具有極強的傳奇色彩。
更糟糕的是,克萊武晚年被議會聆訊,威靈頓晚年被公眾圍攻,軍事征服者在英國的公眾文化中並不是一個非常令人着迷的存在,盎格魯撒克遜人雖然以武力征服了世界,但其觀念中卻不存在對凱撒的迷戀。哪怕是傳媒文化極度精彩的20世紀,英國名將黑格和蒙哥馬利也是以平庸而存於大眾視野之中,至少他們並不是輿論關注的焦點。
另一種人,之所以崇拜拿破崙,那是因為只要是強人,只要是推動歷史的“偉人”,無論是秦始皇,還是拿破崙,希特勒,風雲際會大一統,他們就崇拜。擁有最大的權力,君臨天下,獨攬生殺予奪的大權,人民的安危禍福全仰仗權力的意願,權力無所不能,所以必須頂禮膜拜。這種對權力的崇拜實際上是巴結,是諂媚,是行賄。例如過去的拜龍王。在中國神話裏,龍王從來不是善良或公正的化身。神話裏的龍王多半是兇暴的,任性的。因為它掌握着既能造福又能為禍的水資源,所以不得不求它拜它。
雖然這些人,會説拿破崙推動了歷史什麼的,可是他們也説不出這些具體是什麼,認為只要是“歷史偉人“,“歷史偉人“的活動就必然是“事物自然進程的自覺和自由的表現“。“歷史偉人“帶來的一些好處,不可能是非意圖的結果。
在電影《拿破崙》最後放片尾之前,突然來了這麼一句“謹以此片獻給LULU”。LULU是誰?LULU原來是老雷的一條寵物狗,去年走失了,老雷很懷念它,就在片尾這樣寫,原來這是一部老雷拍給寵物狗看的的電影,大概這部電影會受到炮轟,惡評,也在老雷意料之中吧?
歐洲啓蒙運動的中心在法國,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的等人的思想,隨着拿破崙戰爭向歐陸傳播。被説爛了的《拿破崙法典》其實只是拿破崙所推進的政治改革、司法改革中最顯眼的那一小部分。他通過一場以其名字命名的戰爭,將啓蒙運動的思想,傳遍了整個歐陸。
比如“王在法律下“這個概念,在英國,早在1215年英國中小貴族逼着無地王約翰簽署《自由大憲章》的時候就確立了,英國的法制理念,走的是先有貴族限制王權,然後再由新興中產、鄉紳去限制貴族、最終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路徑。
這條路是漸進的,所以一個典型的英國思想家,討厭任何激進革命的折騰,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英國思想界就對大革命持否定的態度,一直延續到今天,認為法國大革命,總體是負面的。
但問題在於,英國思想家忽略了,或者不理解法國這樣一個具體情況。
在中世紀晚期,法國利用英法百年戰爭的契機,走出了典型封建制度,國王利用他的敕令騎士取代了封建騎士,並將各地的封建主大貴族請到巴黎和凡爾賽去“杯酒釋兵權”,最終逐漸走向了一種絕對君主制。
這種絕對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時代達到了極盛,路易十四説“朕即國家”時,他是完全認真的。法國王權如果再照着這個趨勢發展一點,就會向同期亞洲的君主制看齊,徹底成為一個王在法律之上,如太陽一般照耀一切的存在。

路易十四
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的確有法制,但法制是在王權之下的,更為要命的是,由於法國文化制度是當時歐洲大陸的標杆,當時的整個歐陸各國都朝向法國看齊,所以這種王在法之上的理念其實在逐步侵染整個走出中世紀之後的歐洲。各國紛紛在建立絕對王權。
但就在這個時候,法國王權剛極必折,發生了脆斷,大革命爆發了。羅伯斯庇爾在處死路易十六的演講中説“國王必須死,因為共和國需要生”。從某種意義上説,這個論斷其實也有道理。法國當時的那種狀態,確實需要通過消滅絕對王權來解放民眾。
但問題在於,路易十六的腦袋一旦落地,法國人發現國王沒了,但賴國王以存在的法制也沒了,法國隨後便進入了人頭亂滾“一切反對一切”的恐怖十年當中。法國大革命熱烈的呼喚自由,但事實證明,一個社會僅有自由是不夠的,必須同時擁有法制,社會的運轉才能夠正常。否則如同雅各賓黨人當政時代一樣,沒有任何人的權益受到法律保障,自由就真成為了一種“毫無意義的嗜血狂歡”。

而在這個時候拿破崙來了,他利用他超強的能力,給法國帶回了兩樣東西——法制與王權。表面上看,這似乎僅僅是對波旁王朝時代絕對君主制的復辟,但實際上,拿破崙在這個過程中,悄悄調整並明確了王權與法制之間的關係——法律不再是匍匐於王權腳下,可以任由王權揉搓、更改的治民工具,而成為一種剛性的,國王和皇帝本人也不可逾越的社會通則。
這對歐陸來説是一個意義非常深遠的轉折,由於拿破崙之後曾經將自己的這套體系用武力推向幾乎全歐陸,並建立一系列短暫的“波拿巴王朝”國家。這些國家當中的國王們,至少在法理上都是承認拿破崙法典,保障民權的理念,以及“王在法律下”的概念的。等到拿破崙兵敗俄羅斯,各國舊貴族紛紛復辟,他們驚奇的發現自己治下的領土再也回不到過去了,因為權利啓蒙這件事,具有不可逆性。當曾經被拿破崙的三色旗插上過的土地,都已經習慣了拿破崙法典和法制敍事,王權再想把國家拉回到過去貴族們口含天憲、予取予求時代,已經不可能了。
“風能進,雨能進,皇帝不能進。”德皇威廉一世拆毀老農的磨坊,結果被後者一怒告上帝國法庭,並被判令賠償後者損失的故事,常常被人們津津樂道。但人們常常忽略的是,這件事之所以能發生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原因恰恰在於德國就是拿破崙戰爭的主戰場所在,幾十年前,拿破崙曾經用槍炮給這片土地來了一波“硬核普法”,德國在1848年革命後確立的那些法律信條,很大程度上就是數十年前拿破崙法典的翻版。有這套任何人在法律下、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在,德皇毀了人家屋子,當然要原價賠償損失。可是這事兒在拿破崙戰爭前的普魯士是不可想象的——那個年頭,普魯士不過是一個“有國家的軍隊”,從平民到貴族,你都是國王的僕人,而國王則是國家的僕人,大家尊卑分明,你還談什麼個人權利。
在大革命之前,教士作為第二等級,擁有着高於平民的特權。異端裁判所是一個獨立於司法部門之外的奇特機構,專門處罰那些不信神、褻瀆神或者不按權威的解釋來信仰神的人。推廣引申下來,後來已故的國王,甚至高官(當時大多也為教士),也會被尊為和神靈一樣,任何人要敢議論他們的功過是非,也會同樣犯“瀆神罪”——他們的形象就這樣被完好的維護起來,實現了神化。然而,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產生了孟德斯鳩。他論述到,“瀆神罪”是一種荒謬、可笑又愚蠢的罪名。
“首先,瀆神發生在人和神之間,所以不能構成犯罪。因為法律規定只有人才享受名譽權,神並不是責權主體,既然無權,又何來侵權?其次,受“侵害”的對象是神,而不是任何人,神既然沒有起訴、沒有控告,法庭能用什麼理由去傳喚瀆神者呢?最後,一個人對神不尊敬,不承認神的存在,甚至説神像只是一團泥土,這些言論雖然“不中聽”,但對於公眾利益以及個人利益並無實際損傷,司法部門的官員如果強行介入,稀裏糊塗地去追究、查禁這類行為,就是多此一舉,會讓懦弱、魯莽的人都奮起反抗自由,將自由毀於一旦。每個人對神的理解不一樣,尊敬程度也不同,在普通人看來只是平淡的話可能在狂熱信徒的耳中會變成瀆神言論。如果官員袒護狂熱者,那麼任何人都不敢再對發表言論,因為他們都感到不安全,懦弱和魯莽的人就這樣毀掉了所有人對神進行思考的權利。“
所以,孟德斯鳩説:“一定要為神復仇的念頭,是弊端的源頭。尊重神是應該的,但為神復仇卻毫無必要。”“瀆神罪”並不是罪,法律調節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涉及神。對於那些不信神或者瀆神的人,適合的懲罰應是剝奪他們參加宗教儀式、進入神殿、禮拜神像的權利,不准他們向神祈福,不讓他們受到神的庇佑,這就足夠了。”
歐洲啓蒙運動的中心在法國,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的等人的思想,隨着拿破崙戰爭向歐陸傳播。被説爛了的《拿破崙法典》其實只是拿破崙所推進的政治改革、司法改革中最顯眼的那一小部分。後來的歐洲民族國家,甚至美國,都模仿或者參考了拿破崙建立的國家體制
於是你就可以理解一個怪現象——為什麼同為拿破崙戰爭時代的敵國,與英國人對拿破崙的不屑一顧不同,德國人尤其是其知識分子,對拿破崙卻大都推崇到無以復加。
黑格爾稱拿破崙為“馬背上的最終意志”,恩格斯説拿破崙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貝多芬曾經想把自己的交響曲獻給他。迄今為止最權威的一本《拿破崙傳》,是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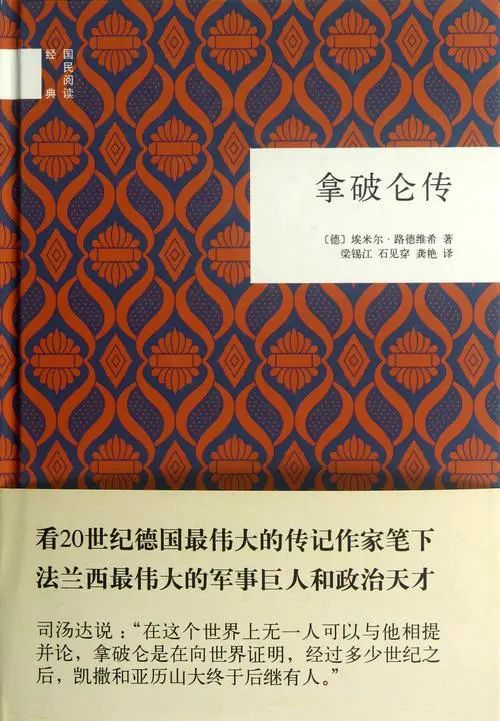
堪稱拿粉巔峯神曲的《兩個擲彈兵》,由德國大詩人海涅作詞,德國大音樂家舒曼譜曲,這首歌以悲壯的頌歌的方式表達了對拿破崙的無限推崇——但它的詞曲作者卻是兩個德國人——兩個曾經遭遇拿破崙的“侵略”,若基於民族主義有充分的理由去恨他的人。這算不算“德奸”“帶路黨”呢?
《波蘭沒有滅亡》(後來的波蘭國歌),也直接唱到“拿破崙已經告訴我們,如何去取得勝利。”
所以,為什麼同為歐洲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波蘭人等等會對拿破崙的觀感迥異。一切的一切,取決於在那個人到來之前,他們是否已經擁有了他要帶給他們的那些東西。
不過,從拿破崙稱帝的那一刻起,他的衰敗就已經開始了
這條下坡路的起點,其實正是被很多“拿迷”所津津樂道的拿破崙稱帝后大封元帥。
元帥制度本來是法國在中世紀就形成的傳統,當國王不敢或不方便外出征戰,而整個軍隊又需要一位獨當一面的將領統御時,法王就會冊封他信任的將領為“元帥”
也就是説,法軍中的元帥本來是稀少(甚至很多時候獨一)、並必須在關鍵時刻獨當一面的存在。
可是拿破崙在稱帝之後,卻大封他手下的將領為帝國元帥,整個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共冊封了二十六名帝國元帥。
表面上看,這似乎説明了拿破崙時代法軍將星璀璨、人才濟濟。但如果你真的細緻去考察這二十六個元帥的名單,你會發現這裏面“水貨”非常多。比較公認的説法是,在拿破崙這二十六帥當中,真正有能力獨當一面的,大約也只有達武、蘇爾特、馬塞納、拉納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

達武元帥
其他大部分元帥,要不然就如繆拉一般,是負責騎兵的“專門人才”,要不然乾脆如內伊一樣,讓他打一場勝仗容易,讓他通盤考慮一下全局,實在是“臣妾做不到”的猛子將、甚至庸才。
實話實説,拿破崙手下的大部分元帥,多數時候其實都只是頂着元帥的頭銜,在做原本將軍就能做的事情。拿破崙的大封元帥反而導致了整個法軍指揮系統的混亂、將領們的不相統屬和矛盾重重——原本你是上將我是中將,你是少將我是准將,那我必須聽你的,但現在大家都是元帥了,誰服誰啊!
這種元帥“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噩夢,集中爆發於拿破崙的西班牙戰爭當中,由於拿破崙所派去的幾位元帥之間的互不統屬、且矛盾重重,他們得以被英軍的威靈頓將軍反覆上演各個擊破。
於是就有了拿破崙打威靈頓,怎麼打怎麼贏,威靈頓打拿破崙手下那幫元帥,怎麼打怎麼贏的奇景。
拿破崙大封元帥的行為,不僅沒有分擔自己的軍事指揮壓力,讓他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政務上,反而加重了他的指揮負擔,因為以前依靠將領之間階級關係就可以協調好的指揮鏈,在他大封元帥之後徹底亂掉了,弄得他什麼事情都必須事必躬親。
那麼拿破崙為什麼要錯誤的選擇大封元帥呢?這裏面,除了“拿皇吃肉,元帥喝湯”,你都當皇帝了,不給老兄弟們一個元帥當實在説不過去的封功臣因素之外。更主要的,還是一種“不得已的權謀”。
拿破崙死後幾十年,大清出了天王洪秀全,創造性的在還沒得到半壁江山的情況下封了兩千多個王。被很多後世史家嘲笑為沒文化。但實際上,洪秀全此舉其實有着“樸素的權謀智慧”。
所謂“眾建諸侯少其力”,皇權最為致命的問題,就在於它是拒絕分享的,甚至哪怕被分享名聲與威望,也不可以。
但無論是“王”,還是“元帥”,這些榮譽都天生具有聚攏名聲的效果,名聲日顯就會成為威望,威望日隆就會挑戰皇權。
於是,作為“初代創業者”的洪秀全如果不想身邊再出一個東王楊秀清,拿破崙如果擔心手下在自己遇到危機時也來一場“霧月政變”。他們唯二的選擇就都是:要麼不封,要封就大封。用頭銜的通貨膨脹,去稀釋它對自身皇權造成的威脅。
當然,不那麼聰明的洪天王做的比較誇張,封了兩千多個王,所以破產速度更快。拿破崙就謹慎的多,才封了二十多個元帥,但一樣逃不出破敗的命運,因為這就是皇權的詛咒。
實際上,在拿破崙稱帝之後,不僅他麾下的元帥們因為才不配位、階層混亂而指揮水平下降。拿破崙自身的指揮水平,也在急速下降。
“主力會戰的勝負,決定戰爭中的一切。”這是克勞塞維茨在系統的總結拿破崙戰爭之後説出的名言。
其實在克氏説出這段話以前,拿破崙本已在軍事實踐中作到了這一點——在他前期指揮的所有戰爭當中,拿破崙都力求先集中優勢兵力,消滅對方的有生力量,必要時甚至會大踏步的後撤,通過戰略迂迴創造對己方的有利態勢,然後通過殲滅敵軍主力獲得戰略主動權。
但是,在拿破崙稱帝之後,這種謀略智慧在他的指揮藝術中逐漸消失了。三皇會戰中將奧斯特利茨城堡讓給聯軍,幾乎成為拿破崙戰略藝術的絕唱。在此後的征戰中,拿破崙越來越放棄敵軍有生力量、而去重視被他原先棄之如敝履的有政治意義的城市,比如莫斯科和柏林……
拿破崙之所以非要放棄原先正確的指揮思路,由精明的“爭軍”轉向笨拙的“爭城”,説白了還是因為皇權。
在當上皇帝之後,拿破崙的心態隨着他的地位一起發生了變化。
拿破崙所稱的皇帝,emperor其實不是皇帝,只不過是對標中國皇帝進行的翻譯,其前身來自拉丁文imperiator(英白拉多)。英白拉多的稱號是軍事指揮官的榮譽稱號。羅馬的軍事指揮官需要獲得決定性的大勝,然後帶領軍隊到羅馬參加凱旋儀式(閲兵遊行,從廣場到神廟),然後被士兵們稱為英白拉多。
英白拉多在歐洲理念中真正的意思其實更接近“統帥”甚至“英雄”,這個頭銜是在民眾的歡呼中產生的。它更接近於現代意義上的總統,或者終身執政官。拿破崙建立的帝國,是模仿羅馬的,不是傳統歐洲中世紀的王朝。
英白拉多是民選的英雄,既然作了英雄,那你就必須不斷地在對外戰爭中取勝。而民眾,他們是不懂得你的戰略迂迴有多麼高深莫測、你殲敵於一役的籌劃是多麼高妙的。你想在今天搞“存人失地”,為的是後天的“人地皆存”,得到消息的民眾可能明天就在巴黎築起街壘,把你推翻罷免了。
所以在拿破崙稱帝(英白拉多)之後,來往於他的御帳和巴黎之間的軍需官,多了一項“軍需物資”——巴黎的報紙。身為皇帝的拿破崙,指揮再也不能像做將軍時那樣隨心所欲了。
所以當了英白拉多不能後退、更不能戰敗,只能從勝利走向勝利,或者至少看上去“勝利”了——在西方歷史上,這是所有想當“大帝”的人,都甩不脱的詛咒。
晚期的拿破崙,徹底被這個詛咒栓死了。精明的庫圖佐夫看到了拿破崙的這種困境,在1812年拿破崙徵俄時,説服沙皇執行堅壁清野、分段阻擊、層層遲滯、外加遊擊襲擾的戰術。拿破崙想要莫斯科,那就讓他莫斯科好了!於是拿破崙得到了莫斯科,卻輸掉了整個戰役。
當上皇帝(英白拉多)的拿破崙,不僅要把虛幻的勝利榮光給巴黎民眾,也要獎賞他的親族另一種他們原本不配擁有的東西,那就是他曾經反對的封建王權。
是的,大封元帥的同時,拿破崙大封了自己的親族。
他的長兄,約瑟夫·波拿巴,先封那不勒斯國王,後封西班牙國王,其任內西班牙狼煙四起,消耗了他弟弟大量的精力。
長妹,埃利薩·波拿巴,封托斯卡納總督,法蘭西公主。
二弟,路易·波拿巴,受封荷蘭國王。
二妹,波麗娜·波拿巴,受封瓜斯塔拉公爵夫人和法國公主。
三妹,卡洛琳·波拿巴,與拿破崙的元帥繆拉成婚,兩口子被封為那不勒斯國王和王后。
最為搞笑的,是他的幼弟哲羅姆·波拿巴,這個人事後被證明沒有任何執政才能,但就因為是拿破崙的弟弟、而且最聽話,拿破崙單獨給他劃定了威斯特伐利亞王國這個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獨立存在的封地給他,哲羅姆上台之後,僅僅幾個月就把原本富庶的威斯特伐利亞搞的國庫空虛。併成功引發了德意志地區對其兄長的敵意,為拿破崙在萊比錫會戰中的慘敗埋下了伏筆。
拿破崙賴以崛起的法國大革命,本來是反封建世襲的,可是稱帝之後的拿破崙卻在“封建親戚”這一點上,走向了曾經的自己的反面,為什麼呢?
這裏面最為重要的,其實還不是家族裙帶的私心,還是皇權效忠問題——拿破崙無奈的發現,只有親屬才能保證對他權威的絕對忠誠。
對這一點證據,是拿破崙其實還有個大弟——呂西安·波拿巴。
在拿破崙的眾多兄弟姊妹當中,呂西安是才能最為出類拔萃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不亞其兄長,但就是這個最有能耐的弟弟,拿破崙卻唯獨沒有給他封王。因為呂西安拒絕聽從拿破崙的指揮,甚至連為封爵而離婚這件事都不肯做,最終拿破崙將他流放到了意大利,斷送了這個弟弟靠自己能力掙來的政治前程。
是的,帶領其領民做匍匐於皇權之下絕對服從,這可能是拿破崙“封建親戚”唯一的理由和最想要得到的結果。
拿破崙試圖仿照古羅馬的制度體系,在法國建立了一個英白拉多+議會的複合政體。這個政體在保證英白拉多足夠開明、接受監督和罷免、並受民眾擁戴時,是可行的。但它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法蘭西人的皇帝”再怎麼英明偉大,也只能是法蘭西人的皇帝,他不能成為荷蘭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的皇帝,拿破崙如果真的把這個體系推廣到全歐,就必須在被他征服的其他國家制定憲法、建立議會、然後讓當地人民推選自己的“英白拉多”——但這就又意味着法國將對這些被征服地區失控。法國將重新陷入國際博弈的被動。
於是無奈的拿破崙只能選擇啓靈於他曾反對的封建制,靠封建親戚來遙控這些被征服的國家。畢竟“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只有血緣是保證不會背叛的鐵則。
但這件事,其實也很難説。比如他兄弟中才能僅次於呂西安、相對比較成器的路易·波拿巴(拿破崙三世他老爹),走馬上任荷蘭國王之後,那真的是想執政為民,為了“窒息”英國,拿破崙要求荷蘭必須參加他的“大陸封鎖體系”,路易立刻嗆聲,説我們荷蘭是商業民族,做生意就是荷蘭人的命!你怎麼可以為了法國的利益,讓荷蘭老百姓利益受損呢?
被頂撞的拿破崙大發雷霆,專門去信給路易,説“我親愛的弟弟……我把你安置在荷蘭王位上,是因為我認為你是一名忠誠的法國公民,可你採取的措施同我和法蘭西對你期望的完全相反。……從你一意孤行的迷途上回轉過來吧,做個誠心誠意的法國人!否則,你的百姓也將擯棄你,你將成為被嘲笑的對象而離開荷蘭。”
你看,在這封信中,其實就暴露了拿破崙式“共和皇權”的關鍵問題——他的統治基於民意,但皇權卻需要絕對的服從,那麼被要求絕對服從的民意,還是民意嗎?這本身就是一個無解的悖論。
其實路易與拿破崙的爭執中,還涉及到拿破崙稱帝之後最大也最愚蠢的一個錯誤,那就是大陸封鎖政策。
拿破崙的崛起發生在一個微妙的時間點上,那就是英國正在爆發第一輪工業革命:1776年,瓦特改良出第一款實用蒸汽機,並向市場推廣,人類工業進程的車輪開始隆隆啓動。
工業化的本質,是用機器代替人手,提高生產效率,完成或正在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天生對市場和原材料擁有龐大的需求。而歐陸作為離英國最近也最大的原材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對正在“長身體”的英國當然至關重要。
也正因如此,英國才會對恐怖十年之後的督政府、以及拿破崙執政時代的法國依然採取極端敵視的態度——按照時任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在撕毀亞眠條約時的議會發言,拿破崙在法國扶持和鼓勵其工業這件事本身,就是在“窒息我們的工業”。

小威廉·皮特首相
而在英法矛盾因為市場和原材料的爭奪變得不可調和之後,稱帝后的拿破崙認為自己有能力將小威廉·皮特所説的這種“窒息”搞的更加徹底一點,於是就有了大陸封鎖政策。
所謂“大陸封鎖”,簡而言之,就是法國通過實現歐陸霸權、協商或者強迫其所有盟國和附庸都不與英國展開經貿往來。斷絕英國所必須的市場和原材料,窒息英國的工業發展。當然拿破崙也沒有愚蠢到認為已經對工業化食髓知味的歐陸可以回到前工業時代。他給出的方案是“進口替代”——也就是在法國大力扶持、發展本國工業,讓法國的工廠接替英國去滿足歐洲的商品需求。
而且實事求是的説,拿破崙對英國的訴求也不算過分,他在1812年遠征俄羅斯時曾在書信中明確寫道“最終,精疲力盡的英國將拱手投降,同意和歐洲大陸分享貿易的成果。”
換句話説,拿破崙並不是想要徹底窒息英國的工業化,你肯分我一杯羹,英法並肩站在產業鏈頂端一起發財,我就滿足了。
這個計劃看似有理有利有節,工業革命時代的世界貿易邏輯已經不同於之前的大航海時代,它遵循三個殘酷的經濟法則:
第一,有且只有一個國家或經濟實體可以佔據工業時代的產業主導地位。
第二,有且只有一種貨幣可以保持世界貨幣的霸權地位。
第三,所有工業時代的商貿參與者,都必須完全打開自己的市場,融入到統一的全球市場中,才能獲取這場“飢餓遊戲”的入場資格。
而如果你讀過亞當斯密的名著《國富論》,你就會知道,亞當斯密早已預見了這些法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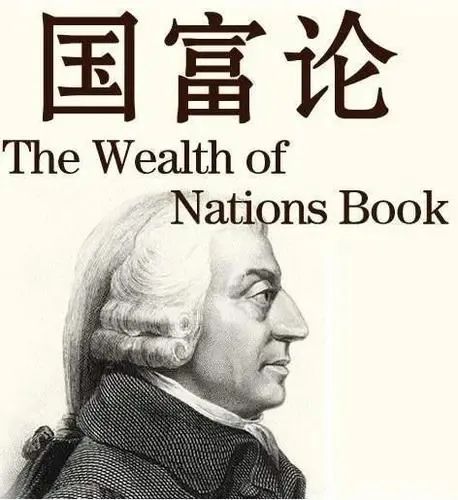
確切的講,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正是因為讀了亞當斯密的書,並以其為師,認識到了正在到來的時代的經濟法則的殘酷性,才堅定地執行了自由經濟學説,力圖讓英國在這場殘酷競賽中先發一步以獲得主導權。並在法國試圖迎頭趕上的時候,咬牙執行了絕不妥協、絕不“分享”的策略,以扼殺這個競爭對手。
小威廉皮特是睿智、殘忍卻又清醒的。
而拿破崙是不幸的,他年輕時代讀了很多書,但唯獨不理解亞當斯密。所以他錯誤的將目標定為了“與英國分享貿易(產業主導權)”這個絕對不可能實現的願景;並且更加錯誤的選擇了封閉自身的市場,試圖以進口替代迎頭趕上英國。
這是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因為拿破崙的士兵再能征善戰,也無法與經濟規律作戰。
果然,在大陸封鎖期間,掌握海權並因此掌握全球貿易的英國與困守大陸的法國之間的生產效率差距被進一步拉大,大陸封鎖令的締約國為了追求更廉價的商品進口與更昂貴的原材料出口,開始紛紛默許甚至支持走私貿易。而拿破崙為了維持大陸封鎖體系,開始頻繁的以利誘、以威脅、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在這個過程中把自己耗的筋疲力盡,並敗光了之前的“解放者”形象。
最終,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公開宣佈撕毀與法國的《提爾西特合約》,退出大陸封鎖政策,公開與英國恢復貿易。拿破崙為了維持自己搖搖欲墜的封鎖之網,阻止其他國家效法,不得不遠征俄羅斯,最終在寒冬中折戟沉沙。
而沙皇撕毀合約的原因,除了沙俄祖傳的賣隊友技能之外,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俄羅斯的經濟已經無法忍受沒有英國這個全球貿易引領者參與的環境了。
實際上,如果拿破崙沒有稱帝,他的這個錯誤本是有望得到及時糾正的。
因為法國當時也有自己的傑出經濟學家。比如古典經濟學派法國代表人物、《政治經濟學》的作者,被李嘉圖稱為“(歐洲)大陸首先正確認識並運用斯密原理的人”的讓·巴蒂斯特·薩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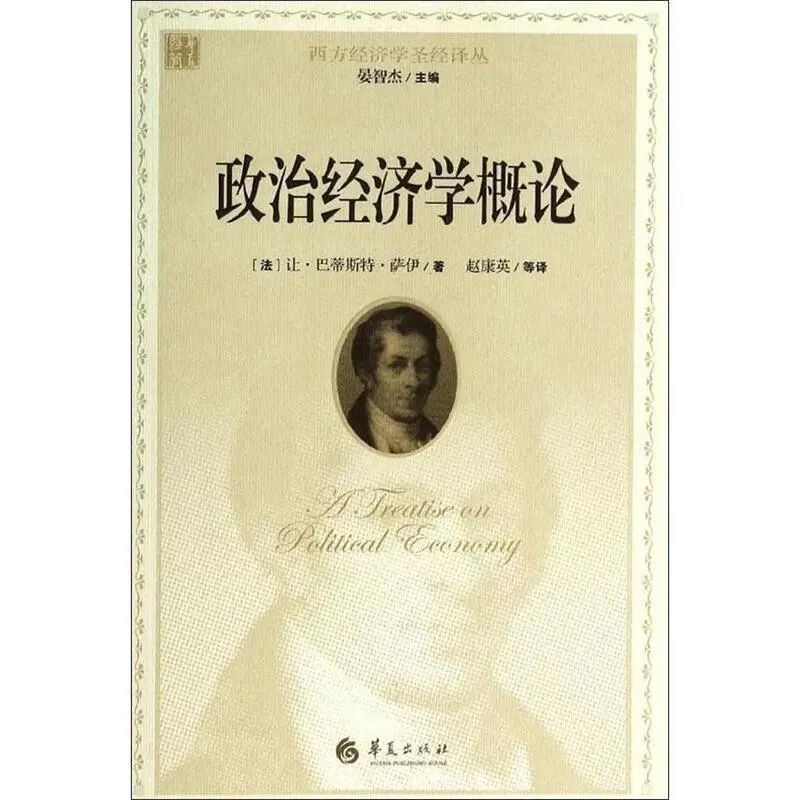
薩伊本來是拿破崙的好友,拿破崙下達大陸封鎖令時正受到拿破崙的重用,擔任法蘭西財政委員會的主席,他在聽到皇帝在柏林下達的命令之後,立刻在《哲學、文藝和政治旬刊》上發表文章,反對拿破崙推動這條政策。認為此舉“不是在窒息英國,而是讓法蘭西自己窒息自己”,想要在經濟上與英國爭衡,就必須堅持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政策。
可是,薩伊的這番謀國良言,換來的卻是拿破崙的勃然大怒,拿破崙甚至不惜一改自己之前定下的出版寬鬆政策,下令《旬刊》停售,並將薩伊立刻解職,之後再也沒有任用他。
這個曾經的薩伊好友之所以下達如此嚴酷的命令,其實也是其帝位使然——由於拿破崙是皇帝,就像他的征戰不再能允許失敗一樣,“大陸封鎖令”無論正確與否,從頒佈那一刻起,就只能有執行這一條路。糾錯的空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於是喪失糾錯能力的策略、通往了耗盡國力的征途、而耗盡國力的征途則通往了俄羅斯的凜冬。法蘭西帝國和他皇帝的榮光終於在這凜冬中灰飛煙滅了。
這就是拿破崙的失敗之因——無論是大封元帥、封建親戚、指揮失當還是大陸封鎖,所有這些錯誤,其實最終通向一個罪魁,那就是他自己在加冕典禮上撿起並帶上的那頂沉甸甸的皇冠。皇冠束縛了拿破崙、改變了拿破崙,讓他從堅決化為了固執、從睿智變為了狹隘,從靈巧墮入了笨拙。
然而拿破崙留下的悖論也是深邃的,像法國這樣的國家,在當時並不擁有分權與自治的傳統,所以大革命之後出現一位強人去登頂稱帝完成統合成為了一種必然。但這個必然也引發了必然的悲劇。
從這個角度來説,拿破崙甚至應當感謝威靈頓,感謝後者在滑鐵盧戰役中擊敗了他,讓他不用頂着那頂其實無人可以承受其重的“英白拉多冠“慢慢衰朽,而是留下了一個還算光輝和偉岸的身影,以讓後世的歐洲人在他離開後的時代中去懷念和推崇。
也許正因如此,威靈頓才會説“勝利,那是除了失敗最大的悲劇。”
威靈頓看到了他在用擊敗拿破崙成就拿破崙——那個巨人退場了,滑鐵盧的鮮血洗去了皇權沾染在他戰袍上的污漬,許多年之後,在壓抑中爆發的人們,將只記住他高撐三色旗帶領革命軍衝鋒的背影,而淡忘了他被猝然打斷的朽敗。
對拿破崙來説,失敗,也許是比勝利更好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