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文明型國家:一種元敍事的開端?
【文/張維為】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把‘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融為一體的‘文明型國家’,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堅持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既學習了別人之長,也發揮了自己的優勢,實現了一種對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實現了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是筆者2010年在一篇題為“‘文明型國家’視角下的中國模式”的論文中提出的觀點,隨後筆者又通過一系列論著不斷深化這一觀點。
西方主流媒體敏感地注意到了“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概念,但在相當長時間內持嘲諷調侃的態度。然而,近年來俄羅斯、印度、伊朗、土耳其等非西方大國紛紛稱自己為文明型國家,不少西方政治人物、專家學者也開始熱議這個概念,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開始驚呼:20世紀是“民族國家”的時代,21世紀將是“文明型國家”的世紀。顯然這個概念觸及了西方敍事的核心困境,即自由主義、民族國家、“西方中心論”等元敍事的危機。

《經濟學人》文章截圖:《亨氏痼疾:“文明國家”間的衝突》
本文簡要回顧提出文明型國家的初衷,討論中國可能是一種“理想型”的文明型國家,探討文明型國家敍事是否會成為一種新的元敍事之開端。
一、為何提出文明型國家?
筆者十多年前提出文明型國家的命題和敍事,主要源於筆者對中國模式及其背後的中國理念、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研究,包括走訪100多個國家後形成的國際比較,也源於自己對西方關於中國和世界主流敍事的不滿和解構。2010年前後,雖然中國崛起已經震撼了整個世界,但在西方話語的影響下,國內不自信者眾多。美國領導人克林頓公開表示,中國是一個走在歷史錯誤道路上的威權國家,這種話語竟然主導了很多國人對中國的認知。筆者對此深感憂慮,多次提出我們必須首先自信地肯定中國模式,再自信地解決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中國崛起必須伴隨自己政治話語的崛起,否則中國的崛起將功虧一簣。2011年,西方和親西方勢力圍繞“7·23”動車事故發動的輿論戰嚴重衝擊中國高鐵發展,就是一個例子。
有感於當時普遍存在的不自信,筆者在論文中這樣寫道:“中國模式使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所有特徵,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四大因素’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優勢:我們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資源和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我們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我們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系,我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但是如果我們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放棄中國模式,轉而採用西方模式,那麼我們‘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可能很快就變為我們最大的劣勢:‘文明型國家’的‘百國之和’變成‘百國之異’,強調和諧的政治變成強調對抗的政治。我們‘百國之和’的人口將成為中國混亂動盪的温牀;我們‘百國之和’的疆土將成為分裂主義的沃土;我們‘百國之和’的傳統將成為無數傳統紛爭和對抗的藉口;我們‘百國之和’的文化將成為不同文化族羣大規模衝突的根源。中華民族崛起的夢想將被徹底斷送。”在《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2011年)等著作中,筆者又進一步展開了這些觀點,包括文明型國家崛起對外部世界產生的影響。
文明型國家的提出,也是為了區別於海外漢學界長期流行的關於中國是“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的敍事。“文明國家”敍事的經典表述由美國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所述:中國是“一個佯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眾所周知,民族國家在西方主流敍事中等同於現代國家,白魯恂承認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文明,但認為這種古老文明更多是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包袱,而非財富。
英國學者馬丁 · 雅克(Martin Jacques)通過其專著《當中國統治世界》,使“文明國家”概念更為中性化。雅克認為,作為一個“文明國家”,中國永遠不會變成一個西方國家,中國的崛起只會遵循自己的發展邏輯和自己的文明對合法性的認知,中國的崛起必將對世界格局演變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雅克亦認為,中國在“文明國家”和“民族國家”兩者之間存有張力,這種張力“可能會把中國拉向不同的方向”。他推斷,中國今後可能會在東亞以某種形式復活朝貢體系,可能導致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某種挑戰。
針對雅克的觀點,作為長期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學者,筆者認為今天的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而其文明特徵使其與眾不同。筆者認為中國已經成功地把“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融為一體。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中國不會恢復朝貢體系,也不會擁抱種族優越論。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的特點是集古代與現代為一體,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使中國在不少方面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超越。換言之,“文明型國家”與“文明國家”概念的最大差別在於:前者首先認為中國是一個現代國家,且融“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為一體,這也是西方話語信徒最難接受的;後者則聚焦中國“古老文明”,且“古老文明”和“現代國家”常處於矛盾狀態。
隨着文明型國家敍事在世界範圍內的崛起,今天除了學術界小範圍,“文明型國家”和“文明國家”兩個概念之區別已日益模糊,兩者幾近可以互換使用,包括筆者在內的多數學者對此不持異議。在相關的文明敍事中,這兩個概念現已變得互相兼容,文明型國家敍事也因此獲得了更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然而,瞭解這兩個概念最初的差別有利於我們更為準確地把握文明型國家及相關爭議的背景及其正在產生的廣泛影響。
二、一個“理想型”的文明型國家?
文明型國家敍事現已走出象牙塔,成為最重要的國際主流政治敍事之一。從迄今為止的關於文明型國家的討論來看,幾乎所有參與者都繞不開中國這個國家,畢竟“文明國家”“文明型國家”等論述幾乎都是圍繞中國逐步形成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學者們爭論這樣一些問題:中國這一古老文明能否成為現代國家?中國將崛起還是崩潰?中國成功崛起的文化原因是什麼?中華文明與中國現代化是什麼關係?中國崛起將對世界格局的演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可以説,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辯催生了一系列中國是“文明國家”“文明型國家”的敍事,隨後又衍生出其他文明型國家的敍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可以説是文明型國家敍事的開端,是文明型國家的“範例”,甚至就是一種“理想型”的文明型國家,即一個延綿不斷長達數千年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
美國學者塞繆爾 ·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預測一個文明內部的一些國家與另一個文明內部的一些國家(即“一個文明、多個國家”類型)之間會發生衝突,但未預見到“一個文明、一個國家”類型或“一個古老文明、一個現代國家”的文明型國家類型。這種國家的崛起必然對外部世界和國際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作為一個“理想型”的文明型國家,中國具有“四超一合”的特徵。“四超”指的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和超豐富的文化積澱。“一合”指的是這“四超”中的每一項都通過中國模式實現了古代與現代的結合。這一切已經並將繼續深刻影響世界格局的演變。
首先,“超大型的人口規模”。我們有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疆土上的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歐洲相比,一個歐洲的中等“民族國家”大約是1400萬人口,所以中國的人口大約等於100個歐洲中等“民族國家”的人口之和。這是中國在自己漫長曆史中由“百國之和”逐步整合形成的。但中國通過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已經普及了現代教育。中國每年培養的工程師數量超過西方國家培養的工程師數量的總和,僅這一事實就永遠改變了世界。中國今天在大數據、電動汽車、可再生能源、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領域內領先全球,都離不開中國的工程師紅利。超大型人口規模產生的規模效應使中國所做的一切都可能產生巨大的全球影響。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擁有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向世界輸出最多的遊客,是130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3—2021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38.6%)超過七國集團(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國家貢獻率的總和(25.7%);七國集團中經濟實力最強的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為18.6%,不到中國的一半。
其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這也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但現代國家的體制建設使我們建立了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下難以想象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和強大的國防力量,徹底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百餘年的“捱打”問題,使我們得以在超大規模的國土範圍內進行長時間段的空間佈局和戰略規劃。今天中國廣袤的國土上覆蓋着全球最大、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網和高速公路網以及世界一流的數字基礎設施。中國具有一般“民族國家”難以企及的中央—地方良性互動關係、東西南北中協調互助關係和巨大的地緣輻射能力。
再次,“超悠久的歷史傳統”。這意味着在人類知識的幾乎所有領域內中國都有自己的傳統,它們不斷地演化、發展和適應。例如,西方自由主義敍事習慣於指責中國所謂的“一黨制”,然而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中國幾乎一直實行某種“統一執政集團”治理模式,這符合文明型國家本質上是自己漫長曆史中“百國之和”形成的政治需求,否則這樣的國家就要解體。“統一執政集團”模式帶來了中國特有的注重整體利益的治國理政傳統,形成了與自由主義民主模式下的“部分利益黨”截然不同的“整體利益黨”模式。中國共產黨正是這種傳統的延續和發展,從而使中國可以在黨的領導下從國家與民族的整體與長遠的利益出發進行中長期的規劃,推動各種必要的改革。這些都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難以實現的。
最後,“超豐富的文化積澱”。中華民族在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文明歷史進程中,創造了氣勢恢宏、內涵豐富、綿延不絕的文化成就,包括儒、道、釋互補,儒、法、墨共存的政治文化。這與西方自由主義對抗性文化傳承形成鮮明的對照,對這個充滿宗教衝突、族裔矛盾、社會對抗的世界具有啓發意義。中國還有延續數千年的民本主義政治文化,其核心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意味着國家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社會領域所推行的政策,最終都要落實到改善民生上,包括物質和非物質方面的民生。與中國這種民本主義實幹興邦模式相比,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在越來越多的國家裏更像一種“空談誤國”模式。
隨着文明型國家敍事變成一種國際主流政治敍事,作為文明型國家的中國正受到日益增多的關注,特別是整個非西方世界的關注。它們幾乎都在研究中國是如何成功的。文明型國家話語今天在世界上成為一種“顯學”,某種意義上也是許多國際有識之士對中國表示的敬意。當然中國的成功也引起了西方一些勢力的恐懼和敵意,畢竟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崛起的,一些人感到不適是很自然的。然而,文明型國家敍事對西方民族國家、自由主義、“西方中心論”等元敍事的衝擊,才是更具顛覆性的。
三、一種元敍事的開端?
2020年1月《經濟學人》雜誌刊文指出,文明型國家今天成了“時髦概念”,“中國學者宣佈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而不是那種已經過時的19世紀的民族 — 國家。然而,俄羅斯總統普京也跟着中國(hopped on the bandwagon)宣佈俄羅斯文明型國家的地位使其免於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解體。印度還在爭論自己是否為文明型國家,文明型國家的候選國還包括美國,甚至土耳其,乃至歐盟,這個名單還在擴大”。其實,儘管印度學界對文明型國家存有爭議,但印度領導人,從莫迪總理到蘇傑生外長近年都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印度作為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莫迪認為,應該“在深層的印度文明中,而非19—20世紀的西方思想中,尋找現代印度的根基”。
雖然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非西方大國對文明型國家的定義不完全相同,但它們似乎有一種共識,即它們各自代表獨特的文明,它們反感西方的發號施令,並抵制西方界定的所謂“普世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文明型國家話語的崛起確實挑戰了西方主導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與此同時,文明型國家敍事對許多西方人士也很有吸引力。面對歐洲“ 再國家化”勢頭帶來的挑戰,法國總統馬克龍幾乎公開推崇文明型國家理想,他把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作為這樣的例子,並宣佈法國的使命是引導歐洲進入文明覆興。對西方右翼來説,文明型國家敍事往往意味着捍衞傳統價值觀、抵制自由主義代表的文化墮落;對西方左翼來説,它更多地顯示了對本土文化和歷史的尊重,以及對西方帝國主義和自由主義霸權的拒絕。
文明型國家話語也使西方不少有識之士反思西方“普世價值”話語面臨的危機。“普世價值”敍事聲稱這些價值是普世的,而非西方的或歐洲的,更非猶太教的,然而正如歐洲政治學者布魯諾 · 馬塞斯(Bruno Maçães)所述:自由主義的西方“現在已經死亡,因為它造成了全球的無根化(rootlessness)”。他進一步斷言:有些人主張回到歐洲的啓蒙運動,然而正是啓蒙運動產生的自由主義以其追求“普世化”的傾向,導致西方陷入目前的困境。它使西方,特別是歐洲,脱離了自己的文化根基。他還指出,“西方社會為了實現其普世目標而犧牲了自己的特定文化”,使西方社會深陷分裂,而重新塑造一個西方文明的共同身份實屬不易。
美國學者內森 · 加德爾斯(Nathan Gardels)認為,“中國通過宣稱自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實際上正在遏制西方,它在質疑西方提出的主張的普遍性”,“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在世界上更好地存續發展,西方自身也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加德爾斯指出,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的社會凝聚力,與西方自由主義社會的日趨分裂形成了鮮明對照。他也擔憂文明型國家在以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中將領先美國。他的觀點可以説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文明型國家及其敍事的崛起給西方自由主義帶來的挑戰。他眼中的中國社會的凝聚力,其實也是文明型國家對西方以個人主義為本的所謂“現代性”的超越,這是一種軟實力的超越;他提到的中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可能領先美國,則是文明型國家對西方現代化水平的超越,這也是一種硬實力的超越。加德爾斯似乎認為,在軟硬實力兩個方面,西方長期壟斷數百年的霸權地位都受到了文明型國家及其話語崛起的挑戰。
筆者也注意到,《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中被外國學者引用比較多的兩段話分別是:“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並能通過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隻能是一種推演和假設;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並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麼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今天看來這也是難以實現的願景。”“文明型國傢俱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藴,不會跟着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會沿着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座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這種文明型國家不需要別人認可也可以獨立存在和發展,它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在很多方面過去與別人不一樣,現在也與眾不同,今後也還是自成體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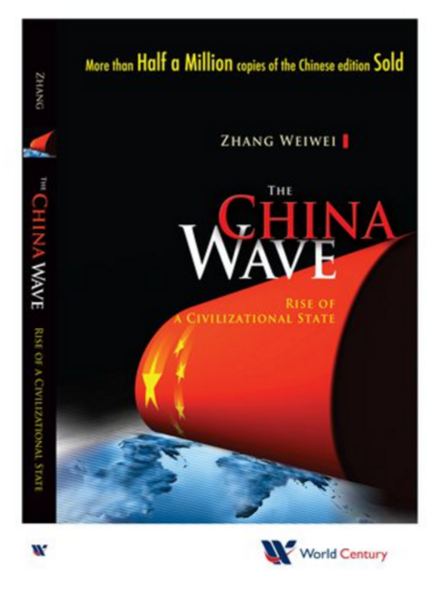
《中國震撼》英文版
應該説這些外國學者抓住了筆者論述的核心:前一段話意味着文明型國家敍事可能顛覆西方“民族國家”的元敍事,因為在“民族國家”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現代國家,特別是“文明型國家”;後一段話意味着文明型國家敍事可能顛覆西方自由主義的元敍事,即西方界定的“普世價值”不是普世的,而是地方的,也不存在什麼“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各國人民都應該根據自己的民情國情和文化歷史傳承探索自己的成功之路,這才是人間正道,或者叫文明型國家的元敍事。本質上這種敍事解構的不僅是西方民族國家和自由主義話語,而且是支撐這兩種話語的底層邏輯,即“西方中心論”的元敍事。
如前所述,英國《經濟學人》2020年1月刊文指出,20世紀是民族國家的時代,而21世紀將會成為“文明型國家”的世紀。美國《國家利益》雜誌2022年發文概述“文明型國家對西方自由主義秩序的挑戰”,指出“文明型國家吸引了各式各樣的非自由主義者”。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義精英十分擔憂文明型國家元敍事對“民族國家”“自由主義”“西方中心論”等元敍事的顛覆,儘管元敍事這個概念本身存有爭議。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 · 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早在1970年代就把後現代時代定義為“不相信元敍事”的時代。
他甚至具體論述了現代“民族國家”元敍事確立後給世界帶來的災難:合法性建立在民族這個理念之上,但為了爭取到正確的民族理念,人們付出的是無窮無盡的爭論和戰爭。他反對元敍事的“總體性”原則,認為後現代哲學要致力於解除總體性原則對不同知識的束縛。然而以筆者之見,自由主義、民族國家,及其背後的“西方中心論”元敍事一直是西方的主流敍事,而從人類社會認識世界的規律來看,尋求對事物發展的某種“總體性”把握十分重要,中華文明和中國模式更是相信整體思維和長線思維,並從中受益良多。如果利奧塔所説的法國啓蒙主義元敍事和德國思辨主義元敍事走向終結,那麼更加包容開放平和的中國文明主義元敍事或文明型國家元敍事,也許可以指向更好的人類未來。
總之,西方長期主導的民族國家、自由主義、“西方中心論”元敍事,西方現代化所代表的硬實力,西方現代性所代表的軟實力,今天都受到了文明型國家及其敍事崛起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文明型國家敍事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元敍事之開端,其意義可能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更加彰顯。全球秩序正在變得越來越呈橫向狀態,即非西方世界,特別是中國,在財富、權力和思想等領域內與西方世界越來越平起平坐,而非過去那種西方位於上方、非西方位於下方的縱向狀態。更多的國家將沿着文明共同體乃至文明型國家的方向發展,這可能是一種大勢,西方主張的“普世價值”最終可能被新的“人類共同價值”(如和平、發展、團結、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取而代之,這將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世界各國都應該為實現這樣的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和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