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羽:20年前對美國市場的“錯失”,恰恰造就了今天的華為
【文/李英羽】
華為在美國市場二十幾年屢戰屢敗的努力,最能體現其“堅韌性”這一基因性質的素質,但美國市場最終成為華為全球化的“金甌缺”,不過,這樣的市場格局,並不能否定華為的全球化體格,實際上,這一格局正反映了今天全球化的真實圖景,也許,只能用一種詩意的語言來表達這個真實圖景:殘缺的,才是完美的。
這一圖景,是全球化發展中“國家”這一角色發揮作用的一個必然結果,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社會制度、文化,在全球化中不同的地位、追求和作用所致,超出了華為自身的能量。
市場干將入美,確定初期市場策略和主攻產品
從 1993 年在硅谷建立蘭博公司、1998 年引入 IBM 進行 IPD 和 ISC 變革,在來來往往不間斷的考察交流、與供應商溝通、參觀各種高科技展會的幾年裏,華為對美國信息技術、通信行業已經相當熟悉了。美國不僅是世界信息技術高地,引領着先進技術發展的方向,還是通信行業一個成熟的、統一的、高利潤的龐大市場,是所有通信設備商的必爭之地,對於華為來説,亦是如此。
幾乎與進入歐洲市場同步,華為在 2000 年底將成功開拓了亞太市場的常崢派到美國,研究在這裏能賣點兒什麼。經過一番考察,常崢選擇在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成立美國代表處,註冊子公司 Futurewei。達拉斯有美國當時著名的本地電信運營商MCI WorldCom (世界通訊公司)、SBC (西南貝爾電訊公 司),華為的友商愛立信和加拿大北電也在此地,近郊的理查森市是一個高科技企業聚集區,有北美“電信走廊”之稱。
經過幾年在亞太海外市場探索和拓展,常崢對華為國際化發展已經有了相當深入的思考。2001 年初,似是呼應半年前楊杜教授的《世界級領先企業之路》,常崢也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國際化是實現“世界級企業”宏大願景的必由之路,並對實現國際化提出了一系列扼要建議,大部分建議都在華為後來的國際化發展實踐中得到應用和實現,包括以全球化為終極追求目標,學習西方“遊戲規則”,要敢於讓人走出去,打造國際化隊伍,建設全球 IT 平台和共享組織,克服地理距離和時差等,是華為歷史上對國際化建設難得一見的系統性思考。
在其頗具遠見的國際化藍圖設計中,就市場開拓策略,常崢的建議是先走 “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但同時也要關注“城市和城郊”的發展,因為城裏人也會經常出來看看,所以要在城郊多設點,讓城裏人慢慢感受這些變化。
華為在美國的早期市場拓展就是採用在郊區設點的策略。2002 年,一家小運營商 LeapWireless 使用華為提供的全網CDMA 移動通信基站和交換機設備, 在全美推出每月只有 29.99 美元的不限流量、不限時長的顛覆性話費套餐,一時成為美國廣大郊區人民的最愛。同時,華為也與 MCI WorldCom 洽談在其美國本土以外的“郊區”市場合作,提供 IP 網絡產品供應和本地服務。2002 年 5 月開始,華為在 WorldCom 美國實驗室進行了長達九個月的入網測試,也通過了國際關口局應用下的業務測試。但在合作框架協議簽署前一天,兩家公司同時收到了思科的律師函,合作告終。
而在產品選擇策略上,華為美國團隊經過一段時間的市場下沉調研後發現,在這個高端通信市場,自己除了在 CDMA 領域,網絡系統通信設備並沒有適配市場的拳頭產品,反而是數據通信產品 QUIDWAY 系列交換機和路由器具備市場優勢。原因在於:一是華為產品推出時間晚,採用了最新的處理器,各項技術指標普遍好於市場霸主思科的產品;二是價格低,能為渠道商讓利提供足夠大的空間。

思科,全球最大的網絡技術公司。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在當時北美企業網數據通信市場中,思科已將其之前的競爭對手3COM的份額擠壓殆盡,市場上幾乎只有思科一家,壟斷帶來的利潤率高達 70%,但留給渠道商的毛利空間卻非常小。華為美國團隊在進行市場調研時,不少思科的渠道商反饋,年底一算賬,毛利只有 10% 多一點,剛夠給員工發工資。
在確定將數據通信作為美國市場主打產品後,華為從深圳派出一眾數據通信產品線主力員工前往美國,代表處制定了拓展兩級渠道分銷體系策略,目標是半年內在北美三十個主要城市發展五十家左右的渠道分銷商,提出了“唯一不同的是價格”的產品宣傳策略。之後,市場拓展團隊迅速行動起來,驅車奔波在美國廣袤的東西兩岸之間,幾乎跑遍阿拉斯加之外的各州主要城市,與在展會上見過面的渠道商溝通洽談,銷售額迅速見漲。
為了進一步打開美國市場,華為在 2002 年又將突破東非市場的劉京青派往美國,負責西部市場開拓,其借力於一位非常優秀的本地員工老湯姆,拿下了 LeapWireless 的 CDMA 合同。2003 年,華為將國內市場一線營銷經驗非常豐富的干將徐展調入美國,成立美東分部,與東部寬帶運營商也很快進入實質性交流,但之後受思科訴訟影響,美東市場開拓就此停滯。
2006 年,任正非在一個內部講話中説,美國市場還沒有實現真正的突破,英美的文化與管理基本是相通的,所以要將英國作為培養管理幹部的基地,將英國的管理輸出到全球重點市場。這個重點市場,應該是指向美國。但後來並沒有清楚地看到這一人事策略得到實施。
2009 年,英國電信 CTO 馬特 ·布羅斯離職,華為招聘其入職美國。馬特曾主持英國電信“二十一世紀網絡”項目,華為藉此打開了歐洲高端市場。馬特是美國人,華為對藉助其打開美國市場寄予厚望,給予優厚的激勵,但結果並不如人意,其於 2012 年在美國國會對華為舉行聽證會後離職。
而越到後來,越多的非市場因素左右了華為在美國的存在。2010 年,華為派出曾成功突破中東市場、當時已任全球銷售部總裁的丁少華前往美國,擔任這一重要市場的國家代表,但到此時,華為在美國市場的形勢發展,已非個人能力可為。
思科知識產權訴訟,華為從美國暫時收縮
思科在 2003 年對華為發起的知識產權訴訟,是通信產業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對華為來説,尤為重要。雖然案件本身最終以雙方和解告終,但華為數據通信產品就此撤出美國市場,標誌着華為以直接方式進入美國市場的第一次努力以失敗告終。
而訴訟案產生的更深遠的影響是,從此之後,思科在美國市場對華為形成 了一道無形壁壘,在美國政界一直髮揮着遏制華為的影響力,此後華為在美國市場做出種種努力,但一挫再挫,形勢不可逆轉。
思科是 IP 與數據通信技術領域裏的王者,通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的一系列併購,超越了之前的領先者3COM公司,成為新興的互聯網產業網絡設備市場的霸主,其路由器產品具有絕對控制地位。
華為美國團隊經過本地市場調研,選擇數據通信作為主攻產品後,也就意味着要與思科在其“大本營”市場正面作戰,華為在當地有影響力的媒體刊登廣告:“它們唯一的不同就是價格”,背景圖案是舊金山金門大橋,這是思科的標誌,其意自明。
採取這一進攻性策略,華為的信心源於其在中國數據通信市場對思科取得的節節勝利。
華為從 1996 年開始進行數據通信產品開發,經過數年積累,到 2001 年,已具備了完整的交換和中低端路由器產品系列,並開始規模銷售。到 2002 年,華為在中國路由器市場佔有率直逼思科,成為思科在中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思科主動下調中國市場的價格,平均降幅達 15% 至 20%,也未能阻止華為的高歌猛進,只是稍微減緩了自己的下滑速度。在海外,華為 2002 年的數據通信產品銷量同比增長 200%,當然這是在小金額和小基數基礎上的大幅增長,但反映在思科的市場佔有率上,2002 年前兩個季度就從 80% 下滑至 73%。
美國的數據通信市場規模佔全球 40%,作為思科本土市場,這裏的銷售佔其整體銷售額六成以上。華為進入美國後,市場團隊快速、高效運作,以價格為利器,複製其在中國市場的成功,思科的“噩夢”正在到來。2002 年 6 月,亞特蘭大通信展之後,華為數據通信產品在美國市場的銷售就比上一年度增長了將近 70%。雖然這也是在一個小基數、小金額基礎上的增長,但思科擔心的是趨勢。
思科揮起的反擊華為的大棒,是美國高科技市場的常規武器:知識產權訴訟。
2002 年 12 月中旬,思科全球副總裁從美國來到深圳,向華為正式提出知識產權交涉,華為拒絕承認侵權,否認抄襲思科軟件,但還是選擇息事寧人, 主動停止在海外銷售有爭議的路由器產品。經過近一個月溝通,雙方未達成任何協議,不歡而散。
2003 年 1 月 23 日, 中國春節假期前幾天,思科在美國提起訴訟,指控華為及其美國子公司盜用部分思科源代碼,應用在華為路由器和交換機的操作系統中,對思科專利形成至少五項侵權。對華為的指控涉及專利、版權、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等八大類、二十一項罪名,幾乎涵蓋了知識產權訴訟所有領域。
訴訟之前,思科公佈了一個在全球投放一億五千萬美元廣告的計劃,為訴訟華為製造有利輿論聲勢。其發起訴訟的目的並非為尋求賠償,而是遏制華為的市場發展勢頭。
這一系列行動,思科用時半年,精心策劃。
思科起訴後,華為成立了由郭平和費敏、洪天峯等數位副總裁主導的應訴團隊,包括知識產權、法務、研發、市場、公關等多個部門,集中公司主要力量來應對這場可能影響公司命運的重要訴訟。因為知識產權可謂高科技企業 “命門”,一旦敗訴,被認定為侵權,對當時正在準備開拓歐洲高端國際通信市場的華為來説,形象就此崩塌,將是一個致命打擊。實際上,這種影響後來確實是發生了,華為在英國的數據通信產品市場拓展就因思科訴訟而終止。
郭平隻身赴美,停留近半年時間,是思科訴訟戰的“前敵指揮”。他同時兼任與 3COM 公司合資談判負責人,這一談判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此時基於訴訟需要,華為做了一些讓步。在訴訟案首次開庭後僅三天,華為與 3COM 宣 布,雙方將組建合資公司。
經過一系列訴訟和輿論戰,最終結果是,2003 年 6 月初,美國法庭駁回了思科申請下令禁售華為產品等請求,拒絕了思科提出的禁止華為使用與思科操作軟件類似的命令行程序。不過又頒佈了有限禁令:華為停止使用有爭議的路由器軟件源代碼、操作界面及在線幫助文件等。
2004 年 7 月,雙方達成最終的有條件庭外和解協議,訴訟案獲得一個相對和諧的結局。
這一訴訟結果,大大好於任正非最初提出的“小輸就是贏”的期望,華為沒有背上抄襲、侵權的惡名。取得這樣的戰果,得益於華為對訴訟祭出的“三板斧”。
一是在對商業壟斷極其敏感的美國市場環境中,華為找到了“反壟斷”的 反擊點,認為思科通過私有協議獲得市場高達 70% 的市場佔有率和利潤率,形成事實壟斷,而思科訴訟華為的本質,是害怕競爭。華為也藉此論點,在媒體上反擊思科為訴訟“發動了一場散播錯誤信息的運動”,在輿論上扭轉了最初的被動局面。
二是取得 3COM CEO 在法庭上的支持性證詞,稱雙方在成立合資企業前, 3COM 公司已花了數月與華為公司的工程師會面交流,並測試了產品,在此過程中,他“目睹了華為公司世界級的工程能力”,“相信從合資企業運出去的產品在世界上將是獨特的和有競爭力的,並且這些產品是在完全尊重各公司知識產權的基礎上設計的”。
三是邀請斯坦福大學教授數據通信專家丹尼斯 ·艾利森(Dennis Allison), 作為獨立第三方專家,他詳細比較了雙方產品源代碼的差異,認為思科對華為複製其代碼的結論言過其實,在證詞中也解釋了部分相似可能來自相同的開源,或者其他商用軟件組件。
華為無線研發專家曹江對思科訴華為一案有非常詳細的事件回溯和專業分析,其最後總結頗具信服力:源代碼抄襲肯定是沒有的,因為路由器產品使用的嵌入式軟件,其設計與硬件的相關性很大,抄襲並不節省開發的複雜性和工作量,此外,也有可信的人證予以證明。但用户界面的仿製是存在的,在很大程度上,這是華為考慮用户習慣了使用思科產品,換用華為產品時會更容易上手。
雖然訴訟判決在法律上沒有禁售華為產品,但華為還是選擇撤回了在美國銷售的幾十台路由器,此後也沒有繼續在數據通信領域在美國拓展,而此時, 華為還沒有更具優勢的產品來打開美國這個高端通信市場,思科訴訟案打亂了華為在美國市場的拓展節奏。
當然,凡事有弊有利,思科訴華為,對華為也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對內,使華為更為注重知識產權保護,是華為在國際化過程中最早意識到學習西方“遊戲規則”的重要一課。對外,則提升了華為在國際通信業界的知名度。
思科起訴華為時,思科已是國際知名通信設備商,數據通信業界的“大哥大”,而華為還在亞非拉“第三世界”的偏僻角落裏苦哈哈地“刨”市場,在歐洲繞着電信“豪門俱樂部”的大門尋找間隙撬開一個門縫兒。由於華為刻意低調,甚至在中國,通信業之外,也沒有多少人知道華為,這場中美之間的第一次高科技企業知識產權訴訟,一時令華為在業界廣為人知:能讓美國的知名企業舉起大棒子敲,應該還是有幾斤幾兩的,大象怎麼會在乎一隻螞蟻呢?況且訴訟結果也證明,華為是有自己的技術實力的。
這樣的廣告效果,在 2019 年年中美國發動對華為的不對等打擊中再次體現。任正非一開始就説,感謝美國,感謝特朗普,為華為在全世界打了一個大大的免費廣告。
思科案讓世界知道了還有個搞通信的華為,美國對華為的打擊,讓全世界都知道有一個華為,5G 通信技術很厲害。

三種進入方式均告失敗,“金甌缺”終成定局
華為突破美國市場,前後使用了三種方式。第一種,直接進入;第二種, 通過併購,曲線繞道;第三種,通過合資,繼承市場。
直接進入方式是華為的首選,但第一次嘗試以思科訴訟案暫告失敗。
在通信產業史上,每一次技術更新、網絡代際交替,都是設備商改變格局的大好機會。到 3G 時代,華為向美國發起了新一輪直接進入的努力,2005 年
3 月,華為的 3G 分佈式基站在歐洲和美國開啓了一次拓展“雙城記”。
2005 年初,當華為 3G 分佈式基站在荷蘭 Telfort 網絡開始實驗網測試時,美國通信運營商 T-Mobile 技術團隊也被這一創新的解決方案所吸引,與華為進行了多次互訪交流,之後華為技術團隊在 T-Mobile 美國實驗室進行了技術功能測試,結果令客户滿意。不過在進行網絡規劃分析時,華為一線項目組認為,如果能將基站射頻拉遠單元輸出功率提升一倍,會更有利於贏得T-Mobile 的合同,國內研發團隊決定就此進行技術攻關,承諾 2006年上半年提供樣品測試。
2005 年 11 月,T-Mobile 派出技術評標團隊,分別對華為香港客户、深圳基地和上海研發中心全面考察後,決定“以 120% 的努力向高層推薦華為”,華為率先進入兩家短名單,並第一個進入實驗室測試環節。
在與 T-Mobile 客户的互動中,華為一線項目團隊一直將關注點放在摸清客户關鍵業務需求、提升產品技術競爭力方面,對市場商務獲得的信息相對模糊,商務決策由公司作出。
在實驗室設備測試進行的同時,華為與 T-Mobile 展開了幾輪商務談判。2006 年初,T-Mobile 發來傳真,沒有選擇華為,測試也隨之終止。即使後來餘承東出馬,親自前往美國做最後努力,也未獲成功。事後有人回憶,餘承東當時難以抑制自己的悲痛,哽咽着安撫備受打擊、抱頭痛哭的一線拓展團隊。
同樣的悲情時刻,在 2018 年 1 月拉斯維加斯 CES 展上再次上演。華為原計劃在 Mate 10 系列手機發佈會上宣佈與 AT&T 已達成的銷售合作,在最後一刻因美國國會議員出面阻撓而取消,餘承東在演講台上幾經躊躇後,發表了一段充溢着悲憤與激情的即興演講。華為手機多年來為進入美國市場的努力也就此告終。
回頭來看,2005 年與 T-Mobile 的合作應該是華為運營商網絡設備進入美國市場最後的一次好機會,是一個比較單純的市場交易,但華為與其失之交臂。
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美國 T-Mobile 技術團隊對分佈式基站價值的肯定,增強了華為對這一產品發展方向的信心。而華為研發團隊致力於為打開美國市場而進行的射頻技術攻關最終成功,成為一個意外收穫,這使得分佈式基站在性能上進一步優化,實現了從局部場景應用向全場景的突破,從而在 2006 年獲得了英國沃達豐的大額訂單並進行規模部署,也使之成為華為拓展全球 大、中、小不同類型的運營商客户的新武器。
進入 4G 時代,華為在全球通信業立足已穩,但美國政府對華為的忌憚和敵意已經非常明顯,多次拒絕了華為在美國的企業併購和技術專利收購申請。
2009 年初,在巴塞羅那通信展上,美國最大通信運營商威瑞森(Verizon)公佈其 4G 供應商名單,華為作為六家競標者之一落選。其 CTO 公開表示,最終選擇愛立信和阿爾卡特朗訊兩家設備商,是因為它們提供了合理的價格和條款。而外界認為,是因為華為缺乏大規模部署 4G 網絡經驗,提交標書時間也比較倉促。但其實,這已經不是 2006 年華為丟掉 T-Mobile 3G 合同那麼簡單的商業事件了。
這在後面的事件中可以得到證明。2009 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干涉華為與AT&T的4G合同。2010 年,美國商務部干預華為與 Sprint 公司價值五十億美元的 4G 網絡合同投標。雖然此時華為已經足夠小心,為了進入 Sprint 供應商名單,與一家由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前副主席創辦的企業 Amerilink 合作,以打消美國的安全顧慮。
至此,十多年過去,華為在美國主流通信運營商大 T 這裏,沒有獲得任何突破。
不過在 CDMA 領域,華為與這一技術的發明者美國高通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還有一些作為空間,但 CDMA 技術終究是一個被旁落的 3G 通信標準,產業鏈很快就沒落了。
2004 年 12 月,華為獲得美國 CDMA 通信運營商 NTCH 旗下 ClearTalk 品牌的移動網絡合同,併成功商用,高通公司總裁兼董事長在商用啓動儀式上到場祝賀。在 LeapWireless 這裏,華為 2006 年後又陸續獲得 3G、基站和調制解調器的一些小額合同。
2007 年,華為嘗試轉向有線電視領域尋找合作機會。2009 年初,美國第三大有線電視公司考克斯通信( Cox Communications)選中華為,為其部署基於 SingleRAN 的 CDMA 無線網絡。
2009 年 8 月,華為協助運營商 Clearwire 部署美國首個全國性 WiMax 網絡。WiMax 是由美國傳統 IT 廠商英特爾發起的一個移動通信標準,但由於種種先天原因,並未形成全球產業鏈,熱鬧了幾年就歸於沉寂。華為在 Clearwire 的合同,也並未為其在美國帶來更多市場機會。
此外,據行業分析師估計,美國寬帶網絡通信公司 Level 3 自 2009 年以來,從華為採購了兩億美元的光纖網絡設備。
華為對美國市場的第二種嘗試,是通過合資迂迴進入,但也命運不濟,成效不大。
2003 年 3 月, 華為與 3COM 成立合資公司,簡稱 H3C,雙方分別持有 51% 和 49% 的股權。根據協議,合資公司在中國和日本市場以 H3C 品牌銷售數據通信產品,在其他市場則以 3COM 品牌銷售。這樣,華為數據通信產品以 OEM 方式迂迴進入美國市場。
但兩年過後,3COM 在北美市場卻一直進展不順,其品牌效應已經喪失。2005 年 11 月,華為如約將合資公司 2% 的股權轉讓給 3COM,後者獲得合資公司控制權,華為得到的承諾是,原來由 3COM 負責的二十多個國家,包括北美市場將全部開放給華為。
但最終的市場結果證明,在與 3COM 的合資行動中,華為的最大收益,可能就是在思科訴訟案中獲得美方的有利證詞,合資本身並沒有為華為海外市場拓展帶來成效,反而給自己培養了一個競爭對手。2006 年 11 月,華為將合資公司的剩餘股權出售給 3COM,完全退出 H3C 經營,從中獲得了一定的財務收益。

3COM接手H3C後更換了新的企業標誌。左側為新企業標誌。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個合資“借道”案例,是 2006 年 2 月,華為宣佈與加拿大通信設備商北電合作,成立一家開發寬帶接入產品的公司,北電將持有多數股份,總部將設在加拿大渥太華,合資公司開發的產品將由華為和北電包銷,同時,北電可以開始銷售華為現有的寬帶接入產品。
設立這一合資公司,華為試圖繞道加拿大這個北美自由貿易區國家,曲線進入美國。但是,此時的北電,已是時乖運舛,經歷了 IT 泡沫破滅後大幅裁員、股價大跌、技術演進方向判斷失誤、財務造假引發集體訴訟,正走向崩潰邊緣,簽約後數月,北電即宣佈停止與華為的合作,其最終於 2009 年宣佈破產。
值得一提的是,操辦了這一次合資的北電一方 CEO,是美國人邁克 ·扎菲 羅夫斯基( Mike Zafirovski ),算是華為老熟人。2003 年,在其擔任摩托羅拉公司總裁時,差點兒以一百億美元出手收購了“冬天”中的華為。但由於簽約前摩托羅拉高層人事變動,這樁收購沒有被新任 CEO 批准,華為繼續自力更生,活了下來。
合資不成,還可以考慮收購,以繼承收購對象現有市場和客户,這是華為進入美國的第三種方式。
2007 年 9 月,華為聯手貝恩資本競購 3COM,開價高出 3COM 當時股價 44% 。最初,3COM 同意了交易,但六個月後,CFIUS 以“危害美國政府信息安全”為由阻止了交易,貝恩資本退出,交易夭折。
2009 年北電破產,2010 年摩托羅拉分拆,在兩家公司資產拍賣過程中, 均有消息傳出華為試圖參與競購,任正非在 2019 年時對外界確認這兩次收購意圖:“我們曾經想收購北電,最後因為商業考慮也沒有做。沒出價,雙方談論了收購方式。……過了幾年,摩托羅拉垮了,華為反過來想收購摩托羅拉時,也沒做成。”
北電的無線資產由愛立信購得,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愛立信自此成為北美最大的電信設備商,而美國市場從 2008 年僅佔愛立信全球銷售收入7%、排名第三,到 2010 年即以 23% 的全球佔比排名第一40 ,美國成為愛立信一個巨大的“類本土市場”。
至此時,美國市場已有三家通信設備供應商,華為進入的空間非常小。
到 2010 年,華為在美國市場“終局”已顯。在美國商務部部長直接致電 Sprint CEO “表示關切”導致華為失去 4G 大單機會後,華為內部對進入美國市場已不抱希望。而美國政府對華為的各種阻撓行動越來越頻繁,提出各種“莫須有”的指責,包括華為非上市公司,股權、運作不透明,任正非有部隊工作背景,華為受中國政府控制可能進行間諜活動,等等。2011 年 2 月,華為副董事長鬍厚崑發表一封公開信,澄清長期存在的不真實謠言和斷言。
2012 年 10 月,在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調查後,美國國會對華為和中興兩家公司進行國會聽證。聽證會之後,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布報告稱,華為和中興產品威脅美國國家安全,並警告美國電信公司不要採購它們的設備。至此,美國政府對華為設備與美國國家安全的關係,明確定性了。
2013 年 4 月,在華為分析師大會上,華為輪值 CEO 徐直軍表示:“華為運營商業務未來主要的增長市場是發達國家地區,但不包括美國。”外界解讀,華為正式放棄在美國通信運營商市場的努力。

華為與美國,一個匪夷所思的現代商業“奇觀”
華為對美國市場的錯失,始於一樁知識產權訴訟,雖然在之後的努力中, 有華為自己的決策失誤,但終究是基於商業的誤判,然而事情卻一步步走向一國政府對企業家施以個體的政治“綁架”和對企業的一場商業“謀殺”,雖然背後有思科這隻“看得見的手”的推力,但最後演變的結果,可以説是近代世界商業史上一個令人匪夷所思、歎為觀止的“奇觀”“異事”。
一個世界上最崇尚自由競爭、靠實力説話的市場,卻不允許一個依靠自己的技術實力、通過激烈競爭走出國門、在全球立足並進而領先的公司,進入這個市場。
一個吸引了全世界優秀人才,創造出半導體、計算機、互聯網等先進技術的國家,讓全世界享受這些技術發明帶來的巨大便利,卻不允許應用了這些技術而創新、製造的產品來造福自己國家的人民,讓他們享受優質而廉價的通信服務。
多少年來,美國的優秀跨國企業、專業諮詢公司,紛紛遠渡大洋,來到中國,指導華為如何經營、發展自己的跨國業務,管理自己的全球員工,助力了華為的壯大,而美國政府卻勢要將華為消滅於無形。
美國傾舉國之力不對等地持續打擊華為,其目的從一開始的令人費解發展到後來的昭然若揭,而任正非對美國的認知也在逐漸發生變化。
從 1992 年第一次訪美,任正非對美國技術的先進和美國人的敬業精神的讚賞就溢於言表。此後隨着華為與美國在技術、企業管理、市場拓展等各方面的交流日增,任正非對美國的認知也日益豐富和切實。
比如,對美國是一個開放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的認識,任正非曾提到,華為早先進入美國市場時,總是擔心自己一家小公司是否會受到排擠,但AT&T在華為測試設備時,就告訴他們,“美國是最不保守的,誰的東西好就用誰的”。
對美國在技術上的創新、引領作用,任正非説:“我們要重視它對未來標準的認識。如果美國不用 TDD,它就不可能成為國際標準;如果美國推動 WiFi,WiFi 就能進攻這個世界。”美國是一個創新力井噴的地方,“第一,美國 保護創新…… ;第二,美國人不怕富,人不怕張揚,否則哪有喬布斯?美國對喬布斯很寬容……他的早期是不被認同的,沒有早期哪來晚期。我們要學習美國的創新精神、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
美國最為任正非稱頌的,是其人才吸引和使用機制:“美國就是利用它的機 制把全世界的人才拉到那裏去,到那裏去以後,都在美國生蛋。”華為從美國好不容易“買了兩個蛋回來,一打開才發現是中國蛋。為什麼不把中國雞留在中國生蛋?為什麼中國的雞跑到國外去?……我們要超越美國就要向美國學習”。
任正非以美國為榜樣,學習美國的一切優秀之處,來強壯華為。雖然早在 1997 年他就已經認識到,“未來的信息產業最終是中美兩國的對抗”,但這種認知還是基於技術層面的,並不是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預判。
對內對外,任正非都極少表達對各國政府和公共政治的態度,其自身定位就是一個企業家,對國家的貢獻在於税收,與國家的關係在於遵守法律,任正非要求員工絕不參與政治活動。而他除非出於商業需要,並不與政府官員有交往。
但對美國政府的態度,任正非在 2010 年逐漸有所表達。在一次談到“開放、妥協、灰度”文化時,他以美國作為反面警示員工,“看着華為慢慢地也強大起來了,我們有些幹部生長的驕嬌二氣,越來越像美國,霸氣也在我們的幹部中滋長,我們要學會示弱”,並説明,這句話是他幾年前對美國一個政治家説的,“主要不太贊同美國的單邊主義,太強勢、太霸權,也許它弱勢一點, 不僅世界和平,而且擁護它的人更多。大家都往後退一些,才能夠形成穩定的 結構”。
2010 年美國商務部干預 Sprint 與華為的 4G 合同後,任正非對美國態度大變:“我們提出了新的歷史使命,在信息領域裏與美國公司正面競爭。我們過去的觀點是比較韜光養晦,儘量迴避與美國公司正面競爭。”但現在,“我終於放下精神包袱了,終於敢於直面和美國公司正面競爭了,不再顧忌什麼了,不再向它們妥協了。以前總一直抱有希望,美國這麼優秀的國家,會公正的……我們最後的希望沒有了,美國的傲慢與偏見,反而使我們挺起了胸脯,直面競爭了”。
此後,華為高層內部意見統一,提出要“瀟灑走一回”,敢於與美國正面競爭、超越美國公司,“最多就是輸……垮了也無怨無悔。只要努力奮鬥就能瀟灑走一回,我們要敢於拼搏。大時代變化太快,華為這種後發的優勢已開始體現出來,我們要敢於領先、超越、駕馭這個時代”。
到 2016 年左右,華為已經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國際化企業,在中美兩國競爭中的敏感地位和潛在風險。在當年的一個內部講話中,任正非提出要強化合規建設,認為華為的市場已覆蓋一百七十多個國家與地區,法律遵從是企業在全世界生存、服務、貢獻最重要的基礎,明確“我們不僅要遵守各國法律、 聯合國決議,而且在敏感地區視美國國內法為國際法。不然,我們就不可能全球化”。
2019 年,美國對華為發起精準、定點打擊,任正非在接受加拿大媒體的採訪時明確表示,“5月份以後,我們認為美國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華為公司,孟晚舟事件只是起頭”。他認為,美國不會取消“實體清單”,這並不是因為華為犯了什麼錯誤而受懲罰,而是美國想要消滅華為,美國對華為是“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但即便認清了美國的最終目的,任正非也堅持向美國學習。2020 年 7 月, 在與中國各高校的交流座談中,他提到美國的打擊,“一個大棒打下來,把我們打昏了,開始還以為我們合規系統出了什麼問題,在反思;結果第二棒、第 三棒、第四棒……求生的慾望使我們振奮起來,尋找自救的道路”。但任正非説:“無論怎樣,我們永遠不會忌恨美國,那只是一部分政治家的衝動,不代表美國企業、美國的學校、美國社會。我們仍然要堅持自強、開放的道路不變。你要真正強大起來,就要向一切人學習,包括自己的敵人。”
在堅持向美國學習的同時,任正非一以貫之地堅決反對民粹主義,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要求全體員工要正視美國的強大,看到差距,堅定地向美國學習,“永遠不要讓反美情緒主導我們的工作,在社會上不要支持民粹主義,在內部不允許出現民粹,至少不允許它有言論的機會。全體員工要有危機感,不能盲目樂觀,不能有狹隘的民族主義”。
2003 年,華為差一點把自己變成一家美國公司,以一百億美元賣給摩托羅拉。任正非後來提到華為這次不成功的“賣身”,感慨地説,“歷史是一場誤會”。
華為與美國的糾葛、恩怨,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串接一串的由企業到國家、由商業到政治、由內而外、漸積漸累的一場大大的“誤會”。人類歷史發展中很多重大變化都源於一場“誤會”,但是,正如後人細究,很多“誤會” 的發生,又都顯示着某種“歷史的必然”。華為在美國的遭遇,其實也是一種 “歷史的必然”。
二戰後的全球化,是西方世界,尤其是以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經濟的一體 化。在此過程中,全球資源重新分配,帶來國家、市場利益調整,進一步導致國家力量的不平衡,特別是美國的一國獨霸逐漸失去其絕對優勢地位,而中國經濟快速崛起, 凸顯出與西方相異的政治運作體制的巨大優勢。國家間政治體制與民族文化的差異,並未因經濟、生產的全球化而彌平、消失,反而因國家力量的不平衡進一步割裂和對立,使得這些差異更為顯性化。在國家與民族的對立、紛爭表面之下,底層的文化價值觀差異發揮了深度割裂的作用。因此, 當經濟和生產的全球化發展到相當深度時,全球化中的另一個主體角色“國 家”開始出手,對全球化進行再平衡,進行“逆全球化”。“逆華為的全球化”, 就是其中掀起的一朵巨大的浪花。
這是今天深度全球化後顯現的一個“大坑”。率先走出中國、實現全球化的華為,“身先士卒”地掉到了這個“坑”裏。那些還沒有或者剛剛走出中國、 實現國際化的中國企業,只因其在代表先進性的科技領域和代表安全的國防領域裏領先,預示着中國“國家”力量的崛起,它們和華為一樣,也一個個落進了美國的“實體清單”裏,成為美國對全球化“再平衡”的行動對象。
華為在美國的故事,並不匪夷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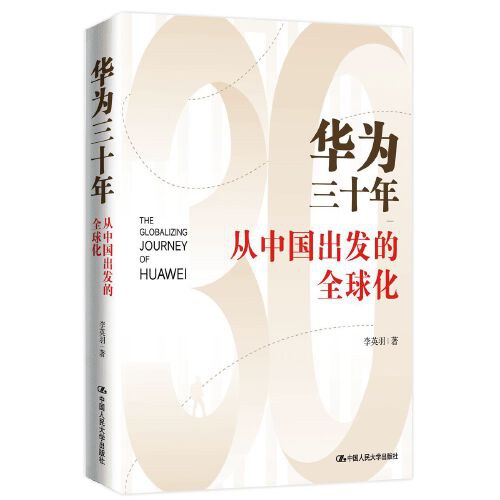
李英羽:《華為三十年: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