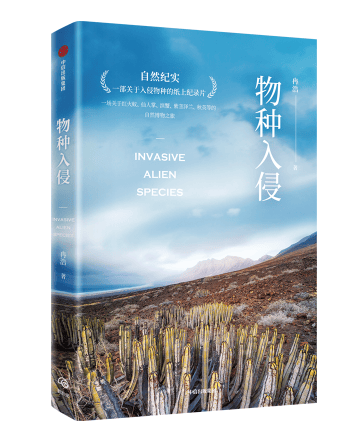冉浩:為何越來越多“小強”進軍北方?
【文/冉浩】
開燈睡覺的一晚
春末的某個晚上,我們一行人風塵僕僕地入住了南方的一家賓館。這是一家條件還不錯的賓館,大堂很氣派,房間也很寬敞,我獨享一張大牀。
只不過,問題就出在這張牀上。
當我拖着疲憊的身子衝完澡,正要睡覺時,就看見枕頭旁邊,在牀頭和牀體的黑暗縫隙裏,伸出了一對長長的觸角,還露出了一個小腦袋,就像齊天大聖頭上的兩根長翎一樣微微擺動。我順着“大聖”的頭往陰影中望去,好傢伙,是一隻碩大的蟑螂!
哪怕我有點兒昆蟲學的背景,遇到這種場面,也有點兒不淡定了。
我決定試着抓住它。
我打算用手去捏住它的觸角,把它拎出來處理掉。
然而,現實比想象殘酷多了。這傢伙只往後移動了不到半釐米,就完全縮進縫隙裏,我的手根本伸不進去。我和它就這樣大眼瞪小眼,陷入了僵持狀態。

善於躲藏在角落裏的美洲大蠊
那一刻,我有點兒想聯繫前台換房,但想想時間太晚了,就不願折騰了。更關鍵的是,倘若一個賓館出現了蟑螂,就絕不會是一間客房的孤立事件,所以換房沒有意義。難道三更半夜的,我還能叫上同伴重新找旅店嗎?我要置接待方的顏面於何地?還是忍了吧。
但是,關燈睡覺時,內心仍然很糾結。既然知道了這裏有蟑螂,覺就很難睡踏實了。更何況我睡熟了還有打呼嚕的毛病,如果有隻蟑螂跑到我嘴裏,估計我也不會知道。請不要笑,我當時真是這樣想的。
不過,作為一個瞭解昆蟲的人,我很快有了對策。蟑螂這類昆蟲有個很明顯的習性,那就是避光性。也就是説,它們不喜歡在強光下活動。於是,我把卧室的燈全都打開了,然後倒在牀上矇頭大睡。可能由於身體非常疲乏,我這一覺睡得很香甜,至於其間有沒有吞下蟑螂,誰知道呢?
次日清晨,臨走之際,我趁着大家都在大廳無人注意的時候,小聲提醒了前台關於房間有蟑螂的事情,對方自然是連聲道歉和致謝,至於後來他們到底有沒有治理,那就不知道了。
我遇到的這種蟑螂,通常被稱為美洲大蠊(Periplaneta americana),差不多是蟑螂中體型最大的,是南方城市家庭中最常見的害蟲之一,也是入侵物種。但它的原產地不是美洲,而極有可能是在非洲或南亞的熱帶地區,目前認為是非洲的觀點佔主流,在非洲南部和西部的熱帶地區還可以找到美洲大蠊的野生種羣。不過,毫無疑問,它們很早就在美洲安了家,那裏也成為它們向世界各地擴散的重要站點。
美洲大蠊過去也被稱為“船蟑螂(ship cockroach)”,這説明它和船隊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
1945年,詹姆斯·瑞恩(James Rehn)曾提出假説,他認為美洲大蠊是隨着黑人奴隸貿易的某條航線從非洲西海岸到達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但在威廉·貝爾(William D.Bell)引用的一則私人通訊裏,提到了1625年在美洲收集的美洲大蠊樣本。雖然黑人奴隸貿易的歷史更久遠,但這個時間記錄仍比那條航線的開闢記錄要早,這就意味着,要麼在更早的時候美洲大蠊已經通過其他路線入侵了美洲,要麼這條貿易路線的開闢時間比之前認為的更早。
儘管美洲大蠊最初的擴散路線比較模糊,但不管怎麼説,它的原產地確實不在美洲,包括它的近緣種屬在美洲也都沒有分佈。在我國,美洲大蠊入侵的歷史也很難確認,該物種被收錄在了《中國自然生態系統外來入侵物種名單(第四批)》中。
作為一種室內害蟲,美洲大蠊帶來的最直接的麻煩就是讓人的身心在極短的時間內變得不太愉悦,特別是當你躺在牀上休息時卻不知道它們什麼時候會爬到你的身上、鑽進你的衣服和書包,或者偷吃你的食物和儲糧,等等。當然,毫無疑問的是,它們有可能攜帶病菌,比如綠膿桿菌、變形桿菌、沙門菌、志賀菌屬、傷寒沙門菌及寄生蟲卵。即使你稱之為“爬行的蒼蠅”,那也不為過。

處於不同發育階段的大大小小的美洲大蠊
不過,蟑螂的行蹤要比蒼蠅隱蔽得多。它們與我們的活動時間幾乎不重疊。因此,它們往往會在入侵你家很久之後,才會因為一些偶然的事件與你相遇。有個很有道理的説法是,倘若你在家裏發現了一隻蟑螂,那就意味着你的家裏已經有了一羣蟑螂。當然,它們的社會性其實並不太強。
這些蟑螂是從哪裏來到你家的?也許是隨某個物品被攜帶進入,也許是通過門窗的縫隙等從鄰居家或環境中來。總體來説,建築物越久遠、居住的時間越長、居住的人員越多越雜,蟑螂出現的概率就越大。當然,也與居住環境的整潔程度有關。與那些在野外大肆擴張的入侵物種不同,這些室內入侵物種在野外的生存狀況並不好,它們依附於人的居住環境,人口越多,它們的生活就越滋潤。
更小更強的“小強”
近年來,另一種蟑螂——德國小蠊(Blattella germanica)在我國快速擴張。
德國小蠊在體型上比美洲大蠊小很多,它們雖然都是蟑螂類,但親緣關係還是有點兒距離的。嚴格來講,蟑螂應該是指蜚蠊類昆蟲,在分類學上屬於昆蟲綱蜚蠊目,種類繁多,我國也有不少本土物種。在所有可以被明確地稱為蟑螂的昆蟲中,有大約不到1%,也就是不到40個物種,是生活在人類住所中的。目前在我們家裏鬧得很兇的那幾種,其中多數都不是本土物種。
德國小蠊的來源問題可能比美洲大蠊還要撲朔迷離,以至於迄今為止生物學家都沒有在野外找到德國小蠊的種羣,這意味着我們無法準確地知道它們的原產地。是歐洲的德國嗎?很遺憾,這也是個烏龍事件。
事實上,德國小蠊被歐洲人所熟知是通過著名的七年戰爭。這場涉及全球殖民列強的戰爭主要發生在1756到1763年,雖然規模不及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但也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格局。
在這場戰爭中,英國殖民勢力獲得了大量好處,法國則遭到重創。俄羅斯的態度前後搖擺,在大部分時候,它與普魯士(德國前身之一)處於敵對關係。這種關係也體現在對待這種蟑螂的態度上,俄羅斯人稱其為“普魯士蟑螂”,德國人則稱其為“俄羅斯蟑螂”。但最終一錘定音的是生物科學命名法的創立者林奈。1767年,林奈描述了這種昆蟲,並根據自己手中標本的產地賦予其種小名“germanica”(德國的),為它們正式貼上了德國標籤。
但根據詹姆斯·瑞恩的推測,這種昆蟲和俄羅斯有關——它們可能在俄羅斯南部潛伏了數百年,並且在另一場更早的從1618年到1648年席捲歐洲的三十年戰爭中被帶到了西歐。至於德國小蠊是如何到達俄羅斯的,瑞恩認為源頭可能還是非洲,主要是東北非地區。
唐乾(Qian Tang)等人在2019年發表的論文則認為,德國小蠊看起來和亞洲熱帶地區的一些蜚蠊物種具有更近的親緣關係,由此認為德國小蠊可能源自南亞,在18世紀前後入侵歐洲,並從那裏快速向世界各地傳播。

德國小蠊
德國小蠊的擴散勢頭非常兇猛,它們已經取代了一些地方原本的室內蟑螂物種,甚至是一些地方的美洲大蠊。相比之下,德國小蠊有一些顯而易見的優勢。它們的產卵量更大,發育時間更短,因此具有更大的繁殖潛力。此外,德國小蠊的雌蟲會將卵鞘攜帶在身上,這無疑增加了卵的安全性,提高了成活率。德國小蠊較小的體型也使得它們更容易隱藏,以及通過一些微小的通道進行轉移。
從防控上講,德國小蠊還有一個麻煩之處:很容易因為長期使用特定藥物而表現出耐藥性,且似乎比美洲大蠊更突出。根據武漢市鐵路局的調查,由於列車內長期使用化學防治手段,測試中的德國小蠊對7種殺蟲劑均不同程度地產生了抗性。貴州畢節的調查顯示,當地不同區域的德國小蠊對不同的殺蟲劑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抗性,這可能與當地使用殺蟲劑的傾向有關。其他一些地方也有類似的報道。
德國小蠊產生抗性的原因可以歸結為行為和生理兩個方面。
一些信息顯示,具有抗性的德國小蠊似乎在行為上有規避相應藥物的趨勢。這些抗性行為往往也與毒餌的拌料成分相關聯,也就是説,德國小蠊不只是在識別藥物,也在識別與藥物一同投放的誘餌。
這很好理解,對昆蟲起到篩選作用、促進抗藥行為產生的是藥物與餌料的混合物,自然產生的規避行為也是針對整體成分的。因此,在投藥一段時間後,改變餌料的成分有助於減少德國小蠊對毒餌的抗性。
不過,生理上的變化才是德國小蠊產生耐藥性的關鍵所在。
一方面,在抗性德國小蠊體內,代謝活動也發生了變化,比如一些酶的活性提高。
酶是生物體內用來改變生命活動速度的物質,由生物體內的細胞合成,並作用於特定的生命活動過程。不同的酶能夠實現不同的功能,比如,一些酶能促進一些物質的合成,另一些酶則能加速一些物質的分解。
水解酯酶的活力提高能夠幫助對抗藥物毒死蜱,事實上這類酶對有機磷類、氨基甲酸甲酯類藥物的抗性起關鍵作用,對除蟲菊酯類藥劑也有一定的作用。多功能氧化酶則可能與對抗除蟲菊酯類藥劑有關,事實上,它能夠將脂溶性有毒物質轉變為水溶性物質以加快其排出體外。除此以外,谷胱甘肽S–轉移酶是昆蟲體內主要的殺蟲劑解毒酶。簡言之,這些酶的活性的顯著提高會增強德國小蠊的耐藥性。
另一方面,一些抗性德國小蠊身體細胞表面的藥物受體變得不敏感了。
受體是細胞表面的特定結構,能夠接受來自細胞外的化學信號。當然,這些信號從本質上説就是一些化學物質,被激活的受體會啓動細胞的某些生命過程,其中一些是有利的,而另一些則可能是致命的。
比如,高毒性的接觸性有機氯類殺蟲劑狄氏劑會抑制神經興奮,其實就是干擾神經之間的化學信號受體,但如果德國小蠊的γ–氨基丁酸受體發生突變,就會產生耐藥性,這一突變往往發生在該受體的第302位氨基酸上。這一突變會同時產生對環戊二烯類和吡唑類、有機氯類、二環磷酯類和二環苯甲酸酯類等作用機理類似的殺蟲劑的抗性。
除以上這些因素以外,近年來,還有研究表明德國小蠊腸道內的微生物等也有助於提高其耐藥性。
總而言之,德國小蠊是一個因為化學殺蟲劑的篩選作用而導致入侵物種局部種羣產生耐藥性的典型例子。鑑於此,如果使用化學藥劑對德國小蠊進行殺滅,就應該定期更換藥物,或者對藥物進行交替使用,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控制德國小蠊的種羣,同時保證藥物的殺滅效果。此外,也可以考慮使用生物類殺蟲劑,比如寄生菌粉等。
當然,對付德國小蠊,還得像對付其他入侵物種一樣進行綜合治理,包括改變室內起居環境、切斷傳播通路、定期清理等,在大多數情況下只靠藥物控制是很難將其徹底清除的。
全球變暖與南蟲北上
法老蟻、白蟻甚至是德國小蠊和美洲大蠊,其實更適合温暖的環境。它們之所以能夠在北方擴散,主要原因是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暖氣設施的普及,它們能夠藉助室內温暖的環境躲過寒冷的冬季。一旦脱離了人類的居住環境,南蟲在北方生存還是很不容易的。
不過,現在的形勢有所變化,一些原本只能在室內生活的蟲子,如今有了更多進入野外的機會,其背後原因正是全球變暖的氣候現象。
儘管仍有一些人認為這是因為我們正處在地質歷史上的間冰期,但全球氣候正在變暖是不爭的事實。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大約升高了0.85℃,1983—2012年是過去1400年來最熱的30年。這與人類社會持續向大氣中釋放温室氣體有關。自1750年工業化開始以來,大氣中的温室氣體明顯增加,到2006年5月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達385ppm(百萬分之一含量),增加了30%;今天,這一數值突破了400ppm。
氣候的變化干擾了原本的洋流和大氣環流,造成陸地上的氣候異常;除了全球平均氣温的升高,也帶來了局部地區的極端乾旱或多雨,極端高温或低温。但總的來説各地的平均氣温還是升高了。這一變化引起了生態系統的響應,也帶來了許多問題。
昆蟲是變温動物,不具備體温調節能力,因此它們從發育到活動都受到温度的影響,甚至可能超出多數人的估計。
以蒼蠅為例,它們的活動時間變得越來越長,由於昆蟲的生長發育與温度有關,卵的孵化、幼蟲的成長速度正在加快,食源性疾病的發生概率將因此上升。目前,全球每年約有1/10的人受到食源性疾病的困擾。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彎曲桿菌造成的食物中毒。
彎曲桿菌是一種腸道細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經由蒼蠅傳播,患者通常在感染細菌的2~5天后出現疾病症狀。常見的臨牀症狀包括腹瀉(經常帶血)、腹痛、發熱、頭痛、噁心和(或)嘔吐,病程會持續幾天,並且有可能造成嚴重的併發症,甚至致人死亡。它是腹瀉的四大病因之一。加拿大科學家根據蒼蠅活動的變化對這一疾病進行了預測,預計到2080年,蠅類數量的增加將造成當地彎曲桿菌中毒的發病率翻倍。
再比如蚊子。有很多臭名昭著的疾病都可以由蚊子來傳播,包括瘧疾、黃熱病、登革熱、淋巴絲蟲病等。其中,瘧疾每年能造成2億多人感染。患者通常在被攜帶病毒的蚊蟲叮咬後的一到兩週內出現症狀,一開始症狀可能會比較輕,包括髮熱、頭痛和寒戰,難以發現是瘧疾。但如果不在24小時內進行治療,惡性瘧疾就可能會發展成嚴重疾病,往往會致命。
近年來,隨着旅遊、貿易等全球人口、貨物的流動,一些原來只侷限在某些地域的蚊媒疾病呈現出輻射傳播的勢頭。
比如,白紋伊蚊(Aedes albopictus)是我們身邊一種常見的蚊子,因為身上長有黑白斑紋而被外國人稱為“亞洲虎蚊”,可以傳播多種致命疾病。它們在20世紀最後的20年內入侵了美洲,現在已經成為那裏最常見的蚊子之一。白紋伊蚊喜歡較炎熱的環境,並且因為氣候變暖而逐漸北上,如果全球變暖的趨勢繼續,它們有望進一步擴大地盤。
另一種被稱為北美瓶草蚊(Wyeomyia smithii)的蚊子雖然沒有太大危害,但卻被發現基因和繁殖週期都發生了改變,以適應日益變化的氣候,這絕不是一個好兆頭。
昆蟲對氣候變暖的響應不僅限於此,它們的適生區域正在拓寬,或者説地理分佈範圍正在擴大。比如,1960—2000年,日本的主要水稻害蟲稻綠蝽(Nezara viridula)的分佈範圍向北擴展到大阪,遷移了70千米。再比如,黑腹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的耐熱種羣的分佈範圍在澳大利亞東海岸提高了4個緯度。這就是在北半球出現的“南蟲北上”的現象,這一現象在我國同樣明顯,大約20年前,我在任國棟教授的應用昆蟲學課上就聽過這個詞了。
在一個國家內部的本土物種由南向北擴張,也算生物入侵嗎?
是的,這毫無疑問。界定生物入侵的地理範圍不是以國界為標準的,而是以其原有分佈地和原有生境為標準的。當一個物種進入新的分佈範圍或新的生境,並對被入侵的生態系統造成破壞時,就可以被視為入侵物種。
另一個問題是,昆蟲和植物的關係受到了影響。
在某種意義上,昆蟲和植物是一個整體,雙方處於某種類似於合作的狀態。植物為昆蟲的幼蟲(或若蟲)提供食物,昆蟲的成蟲反過來為植物傳粉。由於昆蟲的壽命很短,它們在一年的特定時間裏處於特定的狀態,比如,在某些月份處於以進食和生長為主要目標的幼蟲期,而在另一些月份則處於以繁殖為主要目標的成蟲期。在正常情況下,昆蟲的發育階段和宿主植物的生長階段是匹配的,比如在某些植物開花的時候,為它們傳粉的昆蟲也恰好變為成蟲狀態。
然而,氣候變化不僅改變了昆蟲的生長週期,也會影響植物的生長週期。這會導致昆蟲和植物在時間匹配上出問題,也就是同步性受到破壞,其結果可能不利於植物,也可能不利於昆蟲,或者可能對兩者都不利,並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的關係變化。比如,格陵蘭的一種木蝨(Cacopsylla groenlandica)由於孵化時間與原寄主物種柳樹的發芽時間不再匹配,其寄主由一種柳樹擴大到了4種柳樹。
這是一種衝擊和混亂,倘若我們跳出昆蟲與植物的範疇,放眼整個生態系統,其受到影響的規模還要宏大得多。
(本文節選自中信出版集團於2023年4月出版的新書《物種入侵》,作者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