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顛倒了的中心與邊緣——地緣政治學的善惡之辨
【文/傅正】
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與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的分別在哪裏?德國區域主義地理學家赫特納曾經打過一個比方,二者的關係“同地理植物學或地理動物學和植物地理學或動物地理學的關係相同”。[1]地緣政治學屬於政治學的範疇,政治地理學則是地理學的分支。

波黑戰爭中被圍困的薩拉熱窩
然而在實際應用中,地理學與政治學的界線往往模糊不清,比如我們很難判斷1992年—1995年的波黑戰爭或今天關於南海島礁的爭議到底適用於政治地理學還是地緣政治學。區域地理是自然條件或歷史形成的結果,而邊界劃分卻是國家意志的產物,“政治地理”與“地理政治”實難分開。赫特納(Alfred Hettner)接着説道:如果人們越過德國的邊境,向奧匈或者甚至向俄羅斯走去,就會感覺到這種情況;但是,這種差別只表現為地區自然情況的細微不同,例如厄爾士山的我國邊界這邊和那邊,其特點基本上是一樣的。人們可以具體地懷疑,政治地理學的考察究竟應該深入到國家性質中多大程度。[2]
倘若赫特納説得還不夠明確,那麼他在美國的擁躉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就索性認定,“在政治地理學的領域,地理學被用於特殊的目的,並超出求知的範圍,因此地緣政治學是地理學在政治上的應用”。[3]如哈特向所言:設以國家地區劃分地球上任何地區都是“自然劃分”,亦即都受自然條件決定,這當然是謬誤的;因為這一現象本身就是文化現象,所以國家也好,國家的任何要素(如疆界)也罷,都不可能是自然的。[4]
1897年,政治地理學之父弗里德里希·拉採爾(Friedrich Ratzel)就在《政治地理學》一書中強調,“國家是屬於土地的有機體”,“當一個國家向別國侵佔領土時,這就是它內部生長力的反映。強大的國家為了生存必須要有生長的空間”。[5]政治地理學無疑出自國家對於領土及其資源的佔有訴求,地緣政治學則起源於國家佔有與自然邊界的不吻合。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准此而論,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不只關乎地理劃分,亦關乎國家意志與民族精神。借用修昔底德的智慧,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不是因為二者的不同,而是因為二者的相同,對同一個事物有相同的慾望。隨着地理大發現的推進,對土地以及自然資源的佔有慾望代替了古代人和中世紀人對於權力或榮譽的慾望,並擴散到全球。
問題是,這種以土地佔有為目的的政治鬥爭現象有善惡之別嗎?如果把政治哲學定義為對“什麼是政治正義”的規範性研究,那麼地緣政治學能具有政治哲學的品格嗎?
世界帝國的歐亞兩翼:“東方問題”與中亞問題
修昔底德曾指出:荷馬雖出生在特洛伊戰爭以後很久,但是他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臘人”來稱呼全體軍隊……荷馬甚至沒有使用“異族人”一詞,大概是由於希臘人那時還沒有一個獨特的名稱,以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區別開來。[6]
直到波斯人入侵才使希臘城邦真正聯合起來,有了本族人與異族人的意識。從這個意義來説,希波戰爭不僅是後來斯巴達和雅典分裂的開端,更是“希臘人”的開端,希波戰爭創造了希臘世界。修昔底德也許沒有想到,希臘人與波斯人的分別在兩千年後會變成歐洲人與亞洲人的分別,正如英國軍事理論家富勒(John Fuller, 1878-1966)的名言:馬拉松戰爭是“歐洲出生時的啼哭”。希臘半島連同整個巴爾幹半島將成為歐亞地緣政治交鋒的前線。
1453年是歐洲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夏天,奧斯曼土耳其佔領了君士坦丁堡。同年10月,在波爾多的英軍向法國人投降,英法百年戰爭結束。它們是對歐洲歷史影響深遠的兩件事情。
在歐洲人看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意味着古典世界的悲劇性終結,“荷馬和柏拉圖的第二次死亡”。伊斯蘭教越過東正教的地盤與天主教發生了正面衝突,並一度深入到維也納附近。地中海的權力平衡發生了徹底改變。[7]1529年,哈布斯堡家族因抵擋土耳其人對維也納的進攻而獲得了巨大聲譽,“事實上,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能宣稱自己對基督教世界的領導權,部分是基於西方國家聯合抵抗土耳其人的需要”。[8]

1265年拜占庭帝國
另一方面,英格蘭人退出法蘭西,標誌着他們喪失了成為大陸國家的機會,淪為歐洲的邊緣。1533年1月,亨利八世強娶女侍官安妮·博林為妻,英國正式脱離了天主教廷。這場在當時看來不倫的婚姻不只是因為愛情,更是因為亨利八世與哈布斯堡家族的矛盾。[9]此後雖經短暫的反覆,英國終究走上了一條與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道路。
事情並沒有結束,1480年,莫斯科公國脱離金帳汗國的統治,“自然而然地意識到了自己是拜占庭的繼承者”,“於是便產生了‘莫斯科—第三羅馬’的概念” 。[10]久而久之,在歐洲邊緣的另外一側,興起了一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力量。從此以後,巴爾幹半島和小亞細亞成為歐洲人始終揮之不去的“東方問題”,直至今日。
歐亞大陸的另外一端呢?1502年,什葉派穆斯林在波斯建立了薩法維王朝,在遜尼派穆斯林世界的中心打入了一個楔子。該王朝甫一建立,便與西亞、中亞的遜尼派爆發了長期的戰爭。可能因這一重大事件造成的連鎖反應,分別位於今天北疆、東疆的準噶爾汗國,吐魯番蘇丹與南疆的葉爾羌汗國大打出手。苦於西北邊患的明王朝不得不宣佈閉關絕貢,連接中國與歐洲的陸上通道就此斷絕。當時的人們不會想到,由此引發的地理大發現將徹底改變世界的格局:哥倫布本來試圖開闢新航路,以迂迴的方式打擊伊斯蘭力量,但這最終導致了美洲、亞洲新殖民帝國的崛起,歐洲外部的力量開始制約或者平衡原來的歐洲。[11]
最終,處於歐洲最外部的英、俄兩國,登上了世界帝國的寶座。
限於篇幅,我們姑且略去中間冗雜的歷史過程,把時間推移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1820年—1827年,新疆發生張格爾叛亂,英屬印度政府暗中資助叛軍,為其提供火器,訓練軍隊。這是英國染指新疆的開始。
面對叛亂頻繁的南疆地區,清廷曾有一場辯論。時任伊犁將軍長齡上疏建議在南疆西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和闐)改行土司分封制度,實則放棄對南疆的直接統治,將其變為屬國,“可以服內夷、制外患”。[12]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武隆阿更建議放棄南疆:“臣以為西四城環逼外夷,處處受敵,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東四城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13]二人都是前線指揮官,可見主張棄守者不在少數。幸而道光皇帝聽從兵部尚書玉麟的建議,駁斥了上述意見,最終平定了張格爾叛亂。

龔自珍
值南疆未靖之際,龔自珍在1820年、1829年分別寫下《西域置行省議》和《御試安邊綏遠疏》,由此帶動了清代西北邊疆史地之學的研究。考慮到其經世之學的定位,我們完全可以將它視為中國近代政治地理學的開端。1830年,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成立,它的前身是皇家海軍下屬的全球勘測與製圖機構。[14]該學會甫一成立就全程參與了後來英國政府近東、中亞政策的制定。與之對抗,俄國地理學會於1845年成立,歷任主席皆由皇室成員擔任,副主席不是軍隊將領,就是政界高官,其中最後一任副主席碩卡利斯基中將在蘇維埃時期繼續擔任學會主席,直到1931年。[15]
地緣政治的現實造成了地理學研究的興旺發達。綜之英俄兩個跨歐亞世界性國家的地緣政治交鋒史,有幾個時間段特別值得注意。
1853年10月20日,克里米亞戰爭爆發,這是維也納體系下的歐洲第一場大規模戰爭。對此,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每當革命風暴暫時平息的時候,一定要出現同一個問題——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東方問題”。[16]
每當歐洲革命爆發時,沙皇俄國就會藉助鎮壓革命擴大它在歐洲的影響力,充當起“歐洲憲兵”的角色。每當革命的烈火燃燒到巴爾幹半島時,“歐洲憲兵”又會搖身一變為民族自決的堅定支持者。奧斯曼土耳其和沙皇俄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就會因為東正教和斯拉夫民族問題而爆發。克里米亞戰爭正是1848年革命的直接後果。

克里米亞戰爭
從表面上看,俄國輸掉了戰爭,但其影響遠不止於此:
在俄國的歷史上幾乎已經成為一條規律:即每當俄國在歐洲受到挫折,它就加快在亞洲的挺進。[17]
1854年,沙皇與英法聯軍激戰正酣,俄國奧倫堡總督彼羅夫斯基就控制了中亞希瓦汗國的外交權,並制定了首先消滅浩罕汗國,控制帕米爾高原與鹹海之間的錫爾河與阿姆河流域的戰略方針。1856年11月,甫一取勝的英國就抽出手來發動了對波斯的戰爭,並迅速取得勝利,“它表示阿富汗從此脱離了伊朗的影響而落入英國的勢力範圍”。[18]
恩格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上述事件的內在關聯:關於兩個亞洲大國俄國和英國可能在西伯利亞和印度之間的某處發生衝突的問題,關於哥薩克和西帕依在奧克蘇斯河兩岸發生衝突的問題,自從1839年英國和俄國同時出兵中亞細亞以來,常常被人們談論着……當最近一次戰爭開始的時候,俄國有可能進攻印度的問題,又重新提出來了……在1856年英國-波斯戰爭時期,整個問題又重新引起了討論。[19]
恩格斯稱英、俄為“兩個亞洲大國”,表明革命導師對於中亞地緣政治背後的全球衝突有着異常敏鋭的判斷。試問一個區域性國家又怎麼會具有陸權、海權二元鬥爭的全球性視野呢?
卡爾·施米特後來談到英國的海權戰略時,特別提到了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這位保守黨黨魁早在1847年的小説《唐克雷德》(Tancred)中就建議,“女王應該集中一支強大的艦隊,並與她的全部王室成員和上流精英一起出發,把帝國的所在地從倫敦遷往德里。那裏,她將發現一個龐大的帝國等待着她,擁有第一流的軍隊和充足的儲備。”對此,施米特評價道:
他預感到,英國這個島嶼不再是歐洲的一部分。它的命運不一定非得與歐洲聯繫在一起。它可以就此啓程,改變其作為一個海洋性世界帝國的首都的位置。這艘船可以在這裏起錨並在另一個地方拋錨。這條巨大的鯨魚,利維坦,可以又動起來,找尋其他的海洋了。[20]
處於歐洲西側邊緣的英國“不一定非得與歐洲聯繫在一起”,處於歐洲東側邊緣的俄國又何嘗不在歐洲道路受阻的情況下,轉向在亞洲尋找出路呢?此誠如麥金德所言:“海洋上的機動性,是大陸心臟地帶的馬和駱駝的機動性的天然敵手。”[21]兩種機動性把歐亞大陸連成一體。
值得強調,後有“撒謊大王”美名的俄國外交官尼古拉·巴甫洛維奇伊格納季耶夫奉命出使浩罕、布哈拉兩個中亞汗國,並於1858年10月11日完成簽約任務,取得了在阿姆河上的航行權。伊格納季耶夫甫一完成中亞之行,就迅速奔赴中國“調停”第二次鴉片戰爭。他成功誘騙清政府簽訂中俄《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不僅颳走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也使俄國獲得了在喀什噶爾的貿易特權。用恩格斯的話説,“俄國由於自己在塞瓦斯托波爾城外遭到軍事失敗而要對法國和英國進行的報復,現在剛剛實現”。[22]
海權論之父馬漢便總結道,俄國的擴張是從兩翼而不是從中間進行的,它會從其領土的西部和東部各選取一箇中心點,向南作扇形推進。[23]俄國人在歐亞大陸兩翼的行動是殖民擴張,英國人在相同地方回推,豈不同樣是殖民擴張?
另一個時間段是19世紀70年代。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法國凡爾賽宮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5月28日,巴黎公社失敗,“東方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面對歐洲大陸局勢的變化和俄國人在亞洲的蠢蠢欲動,英國自由黨政府做了些什麼呢?
英國前首相、保守黨人德比勳爵(Lord Derby)無情地指出:“格萊斯頓真的相信科布登的理論,即當人們變得文明時,戰爭就會越來越少。但是在普法戰爭中,自由派感到震撼和困惑。”[24]
我們萬勿對引文中的“自由派”等閒視之。據英國歷史學家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透露,所謂的自由派最初誕生於“防止天主教國家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建立統一的君主政體”,“這裏其實是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治下的德意志諸侯的獨立自由”。[25]往後,這種自由主義出現在凡爾賽體系對於戰敗德國的處置中,也出現在美國政府對於二戰後中國事務的處理中。
在亞洲,自由黨政府一貫奉行“精明無為”(masterly inactivity)的政策,甚至幻想由俄國代替野蠻人控制中亞會對英屬印度的進出口貿易大有好處。[26]此舉引發了皇家地理學會的強烈不滿。羅靈遜爵士(Sir Henry Rawlinson)一再提醒眾議院,俄國人有通過中亞進軍印度的完整計劃,再不採取行動,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將要受到挑戰。
正是在中歐問題、“東方問題”和中亞問題的多重壓力下,1874年年初,保守黨政府贏得大選,那位曾經主張遷都印度德里的迪斯累利再次出任英國首相,隨即在“東方”和中亞全面遏制俄國擴張,並扶持佔據中國南疆的阿古柏偽政權。1877年4月,第十次俄土戰爭爆發;1878年11月,第二次英國-阿富汗戰爭爆發。
此時,蘇伊士運河已經通航,英軍從朴茨茅斯港出發不用一個月就可以到達印度;聖彼得堡到奧倫堡的鐵路也已經通車,俄軍可以用更短的時間到達中亞。鐵甲輪船和鐵路列車的機動性,代替了帆船和駱駝馬匹的機動性,英、俄兩國的鬥爭更加成為世界島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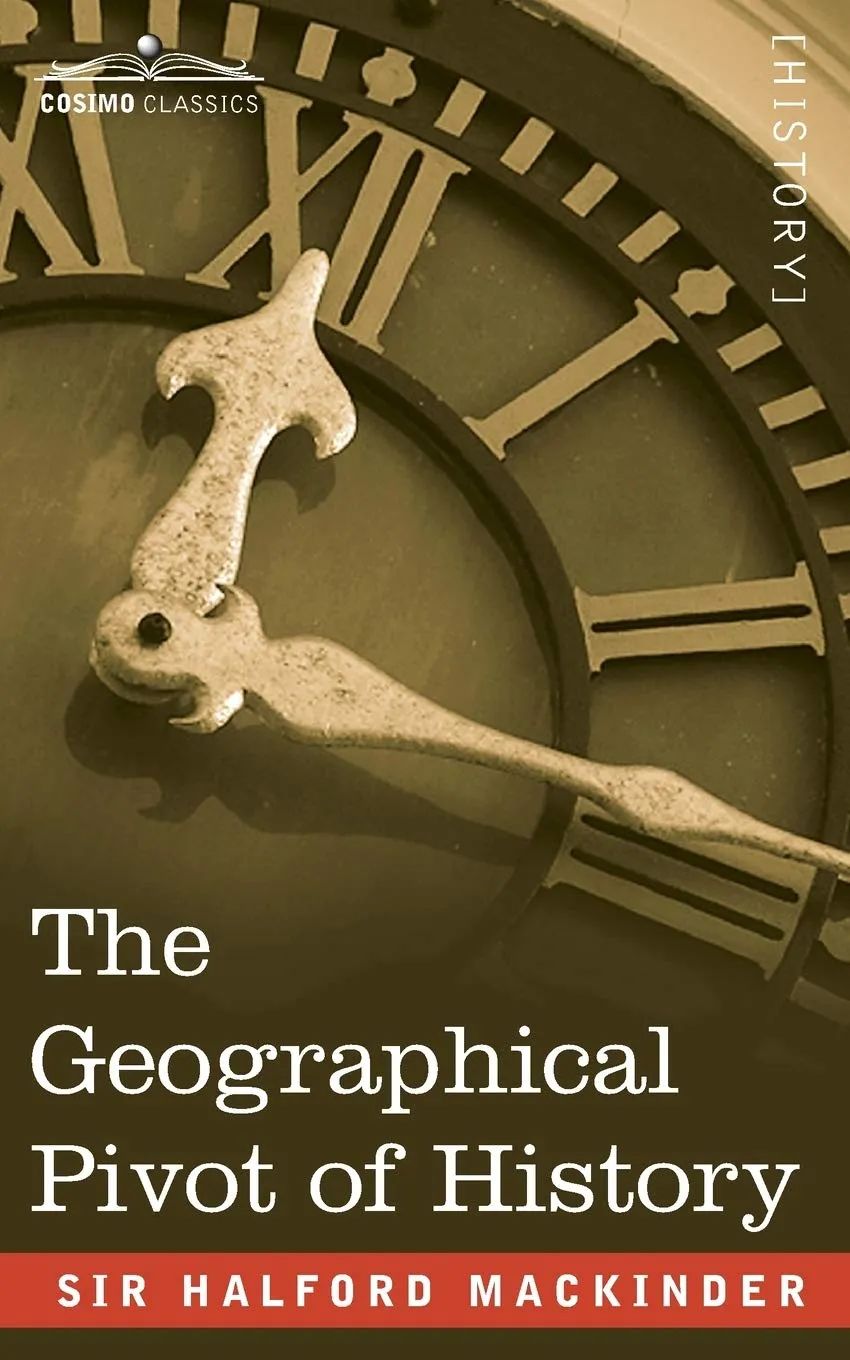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埃及、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波斯、中亞,這些英、俄歐亞世界性帝國交鋒的廣泛地帶一頭連着歐洲的中心——神聖羅馬帝國,另一頭連着南亞的中心——印度與東亞的中心——中國。把它們連成一片,正好就是麥金德所説的“內新月形地帶”。
民主的外學與內學:麥金德的均勢戰略
1887年1月31日,麥金德在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了論文《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1884年,沙俄吞併了中亞戰略要地謀夫(Merv,今屬土庫曼斯坦的馬雷省)。從謀夫到赫拉特的阿富汗西北大門洞開,情形誠如英國地理學家馬爾文(Charles Marvin)所言,如果俄國人進佔謀夫,“我們將不得不接受俄國給兩個帝國劃定的邊界,而把威脅印度最好的地點讓給俄國”。[27]一方面,皇家地理學會反應強烈;另一方面,自由黨政府卻無所作為。麥金德在這個背景下宣讀論文,不可能不想到這些。

Henry Rawlinso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在文章的結尾處,麥金德指出,他的研究“都是從科學的統一性這一假設來説的”。如果放棄了這種統一性,科學研究還會剩下什麼?
選擇的辦法是把科學與實用分開。接受這種辦法的後果將是兩者都遭到毀滅。實用的知識將被教師拒絕,而且在後半生中也難以領會;科學的知識將為大多數人所忽略,因為它缺乏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的因素。老於世故的人、學者、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將會失去他們的共同講台,世界將會變得淺薄。[28]
他是在批評英國地理學界不懂得知識的實用性嗎?非也,英國的地理學研究向來都跟殖民主義的腳步綁在一起,這個道理還輪不到年輕的麥金德來教。他毋寧是在批評自由黨政府和英國民眾對於國家可能遭到的地緣政治挑戰不甚了了。皇家地理學會的幾名資深會員都對這篇論文深表支持。
在麥金德宣讀論文後只有幾星期,牛津大學就決定在地理學方面設立一個為期五年、薪水300英鎊的講師席位,由學會每年捐助150英鎊。[29]
1899年,地理學教席升級為地理學系,英國的國家戰略正式成為大學體制的一部分。
1898年,也就在麥金德成為牛津大學首任地理學系主任的前一年,保守黨干將喬治·寇松(G. N. Curzon)出任印度總督。寇松上任之初就制定了使西藏成為英俄之間夾層的戰略方針,並在1904年利用日俄戰爭的時機入侵了西藏。西藏逐步淪為英國的勢力範圍。
此時的麥金德,正式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1910年—1922年,他擔任了格拉斯哥的卡姆拉基(Camlachie)選區保守黨議員;1919年—1920年又出任英國駐南俄的高級專員。尤為值得驕傲的是,1920年—1945年,麥金德出任帝國航運委員會主席;1926年—1931年,更榮獲英國樞密院顧問官兼帝國經濟委員會主席。毫不誇張地説,麥金德的地理學研究既是皇家地理學會學術成果的體現,更是保守黨政策的反映。他的貢獻在於把二者上升到世界文明史的高度。
在麥金德看來,世界古代文明史就是一部處於歐亞大陸樞紐地帶的草原文明四散而出,入侵內新月形地帶農耕文明的歷史。他不無擔憂地指出:
現在俄國取代了蒙古帝國。它對芬蘭、斯堪的納維亞、波蘭、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壓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擊。在全世界,它佔領了原由德國掌握的在歐洲的中心戰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擊,也能受到來自各方的攻擊。它的現代鐵路機動性的充分發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任何可能的社會變革,似乎都不會改變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線之間的基本關係。[30]

李鴻章簽訂《中俄天津條約》
芬蘭、斯堪的納維亞、波蘭、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構成一條陸獸波希墨特與海怪利維坦的廣闊交鋒地帶。[31]它是波希墨特走向海洋的必經之路,更是利維坦圍堵陸獸的弧形包圍圈。偏巧這道包圍圈缺掉了它在東亞的關鍵一環。
保守黨政府確實有與清政府結盟對抗俄國的計劃。但是,這個計劃在世紀之交最終為英日同盟所取代。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簽訂,日本正式取消了治外法權,首次獲得了與西方列強的平等地位。九天以後,甲午戰爭爆發!
麥金德的上述高論發表於1904年1月25日,1902年,第一次《英日同盟條約》簽訂。他在皇家地理學會宣讀完這篇論文僅僅半個月後,2月8日,日本聯合艦隊突然襲擊駐旅順港的俄國太平洋艦隊。
須知1896年,沙俄利用“三國干涉還遼”的良好形象,誘使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規定俄國獲權在中國東北修建作為西伯利亞大鐵路支線的東清鐵路(後稱“中東鐵路”)。1903年7月14日,東清鐵路建成通車。時至1904年年初,西伯利亞大鐵路只差貝加爾湖一帶100多公里就全線貫通了,屆時從彼得堡到奧倫堡,再到海參崴、旅順港將連成一片。麥金德説“它的現代鐵路機動性的充分發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是在提醒誰?我們不敢妄下定論,惟可以肯定,山縣有朋等人恐懼一旦鐵路貫通,日本在遠東的優勢就將蕩然無存,極力促使日軍趕快發動戰爭。
這場戰爭究竟包含了怎樣的文明價值呢?
1904年7月,日俄戰爭進行到高潮時,西奧多·羅斯福描寫道,日本是“一個美好而文明的民族,它應該擁有與其他文明國家完全平等的地位”。同時,他對俄國不抱任何期望,除非“俄國人民能夠走上自由、開明、自治的道路”。[32]

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日軍圍攻俄軍雞冠山堡壘
與老羅斯福的態度完全一致,馬漢早在1900年前就認定,“日本加入歐洲大家庭的行為充分顯示了該國的優秀品質……亞洲大陸的其他國家看到日本的變化後,也會尋求同樣的革新力量使自己復興”。[33]
正是出於類似意見的影響,清廷朝野上下習慣性地認定,日俄戰爭的本質是“立憲國戰勝專制國”,並在“速開國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至覆亡。一戰後,國人又在威爾遜主義的蠱惑下以為“文明戰勝野蠻”,人類世界開始邁向“太平世”。問題是“文明國家”的入場券是什麼呢?接受了西方價值觀的中華民國真的享受了“文明國家”的待遇嗎?
對於這點,親身參與巴黎和會討論的麥金德倒是直言不諱。他尖鋭地抨擊國際聯盟的五大國協商制度只是徒有其表,“不足以阻止它們之中的一兩個爭取霸權。”“説不定各較小國家有鑑於這次事件所暴露的赤裸裸真相,將設法各自聯合。”他鄙視威爾遜的和平主義理想,亦如他當年鄙視威爾遜的政治偶像格萊斯頓。“我們不能趕時髦;民主必須考慮到現實。”[34]直到1943年二戰正酣之際,已至耄耋之年的麥金德曾回憶起兒時的一段經歷: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那時我還是剛剛進入地方語法學校的小男孩。一天我帶回家一條新聞,那是從貼在郵局門上的電報得知的,拿破崙三世和他的全部軍隊已經在色當向普魯士人投降。英國人為之震驚,他們在精神上仍沉浸在特拉法爾加的偉大勝利和拿破崙自莫斯科潰敗的振奮之中……美國也穩固崛起,進入大國之列。然而,它的崛起目前還只能在統計表中測量;雖然在我的童年,一些人已經對美國人的足智多謀印象深刻,因為我記得,在我們的教室中有一幅畫,描繪“梅里馬克”號和“監視者”號之間的戰鬥(發生於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筆者注),它們分別是第一艘鐵甲艦和第一艘船面旋台炮艦。德國和美國就這樣與英國和俄國並肩崛起。[35]
德國的崛起打破了維也納體系英俄製衡的地緣政治格局,它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美國的崛起則代表了新的海權-陸權均衡,預示了後來的雅爾塔體系。麥金德説得很現實,和平的保障既不是人類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不是物質條件的發展,而是政治力量的平衡。
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當然分別來自於心臟地帶和外新月形地帶,二者平衡的前提是不存在統一的內新月形地帶。彼時美國地緣政治學家鄧恩概括:
任何統一歐洲的計劃都會把它們放在從屬於德國的地位(不管協定的法律條款如何規定),因為除非德國淪於四分五裂的境地,不然,它在大陸上仍將是最大的國家……
中國也同樣還不至於有能力把它的統治擴張到全部亞洲沿海地區。[36]
總之,陸權國家和海權國家都需要內新月形地帶的破碎化,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這裏無關乎民主憲政,惟關乎國家意志和地理空間。
索爾·科恩(Saul Cohen)指出,“將麥金德的觀點放在歷史與當代的角度看,冷戰時期美國的遏制政策是以1904年及1919年的心臟地帶世界領域為基礎的。冷戰後美國的均勢目標更多的是對1943年全球觀的響應。”[37]我們大可以在喬治·凱南、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的著作中看到麥金德的影子。看來,東方人理解民主和文明,不能僅僅從英美的民主理論家那裏去學,更要從它們的戰略學家那裏去學。[38]比如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代議制政府》今天仍是我國高校政法專業的必讀書目,但有幾人會去顧及他強硬的殖民主義態度呢?[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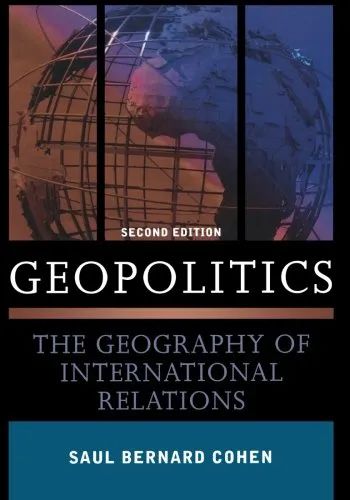
Saul Bernard Cohen《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麥金德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毫不掩飾地向世人展現了帝國主義海權文明的政治本性。艾倫·沃爾夫(Alan Wolfe)曾一語道出西方政治體制的兩重性:
一張臉是民主的、民眾的,關心民主合法性,並爭取大眾對政治秩序的支持;另一張臉像卡西烏(Cassius)一樣精幹、野心勃勃,而且是自由主義的(取其經典的意義),負責資本的積累,並保護執行積累的機構。[40]
“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庶幾反映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學與內學。
地緣政治有善惡嗎?施米特、彼得羅夫的回應
1950年夏天施米特在《大地的法》的前言中,特別感謝“以麥金德為代表的地理學家們”。然而,他隨即筆鋒一轉,強調:“不過,法學的思維還是明顯不同於地理學。法學家對事物與土地、現實與領土的知識並非源於地理學家,奪海的概念具有法學而非地理學的印記。”[41]
“劃分、丈量領土當然跟地理學有關,古希臘人甚至據此發展出完善的幾何學。但是土地佔有背後的法權關係呢?施米特特別指出“奪海的概念具有法學而非地理學的印記”,儘管馬漢等人高談制海權,但他們真的清楚所謂海權理論藴藏的文明變革嗎?”
偏巧俄羅斯地緣政治學家瓦列裏·彼得羅夫(Valery Petrov)對於施米特的聲明毫不買賬。他徑直將施米特劃入地緣政治學家的行列,稱施米特的“全部思想觀念與地緣政治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42]彼得羅夫不懂地緣政治學與政治哲學的區別?未必,他明白指陳,劃分敵友才是地緣政治的首要問題:“委婉地説,西方地緣政治對歐亞俄羅斯的態度是不同的。因此,在“朋友-敵人”這一示意圖框架內來研究這些學説是合理的。“地緣政治朋友”與“地緣政治敵人”(卡爾·施密特的專用術語)這兩個概念沒有精神上的負擔,並可以轉移到不同的客體上。”[43]
施米特在談到毛澤東比之列寧的優越之處時,特別強調列寧的敵我關係仍然是抽象的,而毛澤東的敵我關係卻是具體的。“一言以蔽之,毛澤東的革命比列寧的革命更根植於本土。”[44]

《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
瓦列裏·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於寶林 、楊冰皓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同樣可以説,馬漢的陸、海對立停留在抽象的層面,麥金德則已經意識到敵對關係不可能“受到限制和規範”,後者遠比前者更根植於本土。[45]一個明顯的對比是,馬漢滿以為日本在接受海洋普世主義文明之後,會成為歐美的一部分[46],但麥金德早在1904年年初日俄戰爭爆發之前就考慮到:“假如中國被日本組織起來去推翻俄羅斯帝國,並征服它的領土的話,那時就會因為他們將面臨海洋的優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陸資源加到一起——這是佔有樞紐地區的俄國人現在還沒有到手的有利條件,構成對世界自由威脅的黃禍。”[47]
馬漢和麥金德兩人誰更能洞悉到政治的本質?答案不言而喻。然而,不管麥金德對於國際聯盟和威爾遜主義的普遍和平框架多麼不屑一顧,他仍然缺乏對於敵我關係的哲學提升。
從這個意義上説,不是彼得羅夫不懂地緣政治學和政治哲學的差別,而是他理解的地緣政治學有着更高的理論品格。我們完全可以順着彼得羅夫的意思,稱施米特為“地緣政治學家”。這裏的地緣政治學不僅關乎國家的對外政策,更關乎國家的文明本性。
根據施米特的定義,“法”(Nomos)來自於對土地的“佔取”“劃分”和“放牧”。他接着指出:據此,法是一個民族社會和政治規則在空間上變得可見的直接形式。對牧場的初次丈量和劃分,也就是佔取和緊隨其後的具體定位。用康德的話説,法是“在地面上分清你我的法律”。或用另一個英文詞彙表述,是根基性的合法資格(radical title)。法是將大地的地基和地面以特定方式加以劃分和定位的標準。[48]
施米特所説的“佔取”(Landnahme),不只是民法學意義上的“佔有”(occupatio)。它不僅意味着權利主體對於無主物的先佔取得,更包含了一整套空間秩序的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説,每一次地理大發現都包含了新的空間劃分和秩序制定。
在中世紀,儘管歐洲諸邦之間戰爭頻繁,但它們在羅馬教廷之下有一個基督教文明的共同身份。巴爾幹半島以東,直布羅陀海峽以南是異教徒的世界。誠然,基督教世界內部也有殘酷的戰爭和屠殺,甚至於“它們毫不愧疚地將歐洲以外的人,穆斯林或印第安人,作為公開的或秘密的幫手、或者乾脆作為盟友投入到廝殺當中”。[49]施米特接着説道:
這種敵意的爆發是令人恐怖的;他們相互指責對方是殺人犯、強盜、強姦犯、海盜等等。只缺少一項指責,而這項指責通常是奉送給印第安人的;他們不指責歐洲人自身為食人番。除此之外,各種充斥着憤恨、惡毒的語彙無一缺失。然而,所有的這些指責在如下一個佔支配地位的事實面前都戛然而止了:歐洲人共同瓜分了新世界。[50]
地理大發現對新世界的瓜分不惟創造了新的秩序規則,並最終戰勝了基督教世界內部的既有規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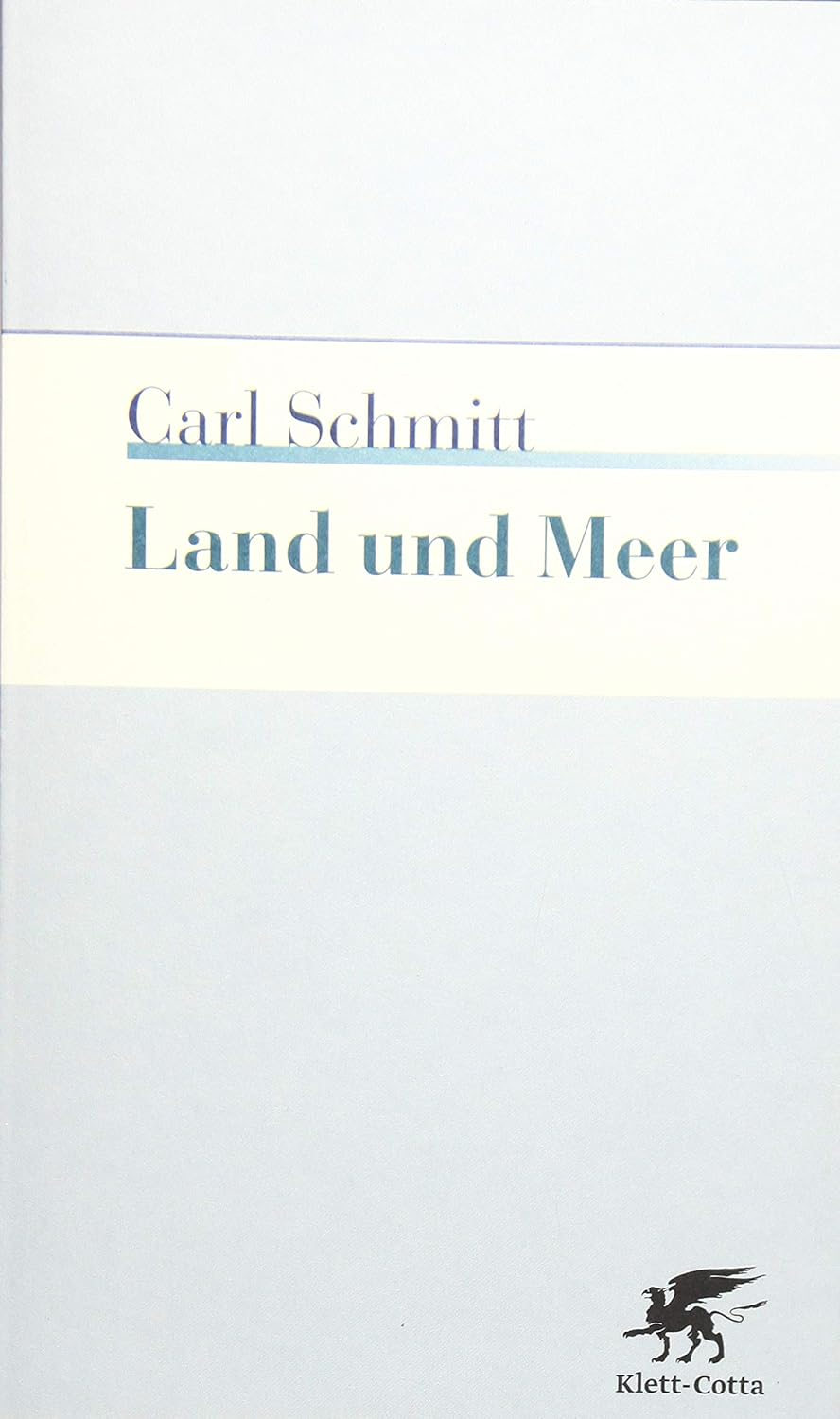
《Land und Meer》Carl Schmitt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559年,天主教西班牙和新教法國之間簽訂了《卡託-康佈雷齊和約》,“這一協定屬於天主教和新教奪海勢力之間宗教戰爭的年代”。“以此線為界,歐洲結束,新世界開始。以此線為界,歐洲的法律,尤其是歐洲的公法,也失去了效力。”[51]一邊是天主教統治下的舊世界,受到國際公法的保護;另一邊是新教支配下的新世界,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筆下的“自然狀態”發軔於此。
英國法上“例外狀態”(Ausnahmezustand)的概念,在所謂的戰爭法(Martial Law)上,明顯是基於劃出自由真空領域的設想。例外狀態作為一種困守狀態(Belagerungszustand),在19世紀的法國成為了一種法律建制。[52]
考慮到前述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Sims)的研究,天主教國家與新教國家在對待神聖羅馬帝國時採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前者奉行主權國家的原則,意圖加強神聖羅馬的凝聚力;後者鼓吹地方自治的自由主義原則,意圖削弱神聖羅馬的國家能力:
歐洲的王權之爭進一步產生的壓力,是會讓德意志變成英格蘭和荷蘭那樣的議會政體,還是變成法國或西班牙那樣的君主政體,抑或是重新陷入過去200多年來所經受的內憂外患之中呢?[53]
可以説,宗教改革把奪海的原則引申到了歐洲內部。從此以後,歐洲便存在兩種國際法原則,一種着眼於平等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一種聚焦於主權者與臣民之間的界線劃分。對此,施米特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
卡巴拉主義者聲稱,波希墨特試圖用自己的角或牙齒撕碎利維坦,而利維坦則用自己的鰭堵住這個陸地動物的嘴和鼻子,使得它無法進食和呼吸。[54]
陸獸的作戰原則是佔領對方的土地,控制對方的人口,消滅對方的有生力量。海怪則不然。伊麗莎白女王時期,“成百上千的英國男人和女人變成了海盜資本家。這同樣從屬於我們這裏所説的從陸地到海洋的根本轉型過程”。[55]戰爭的目的是捕獲對方的財產,封鎖對方的海岸線,戰爭的理由變成了普遍的自由貿易權利。
英國人既然奉行基於自由貿易原則的無限制戰爭,就預設了個人權利在邏輯上優先於主權國家。儘管霍布斯的“利維坦”看起來強大無比,但仍然奉行了這條原則,是故它充其量不過是人為製作出來的技術中立機器而已。正如施米特所言:
隨着國家被看作人類計算的一個人工產品,決定性的一步就邁出了。所有進一步的發展,比如從機械鐘錶到蒸汽機到電動馬達再到化學或生物過程,都是技術和自然科學思想自身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並不要求任何新的形而上學決定……這種轉化由霍布斯來完成。[56]
這種把個人置於國家之先的做法徹底破壞了“人是政治動物”的古典原則,更隨着“制空權”的出現,發展出了後來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説的“全球內戰”或“全球治安戰”模式。譬如1999年,美國以“人道主義干涉”為名對南聯盟進行了長達78天的狂轟濫炸,對象不只是軍事目標,也包括民用設施、公共工程,有如代表國家暴力機關的警察用警鞭不斷敲打違法亂紀者腦袋的治安舉措。人類歷史進入了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的時代。[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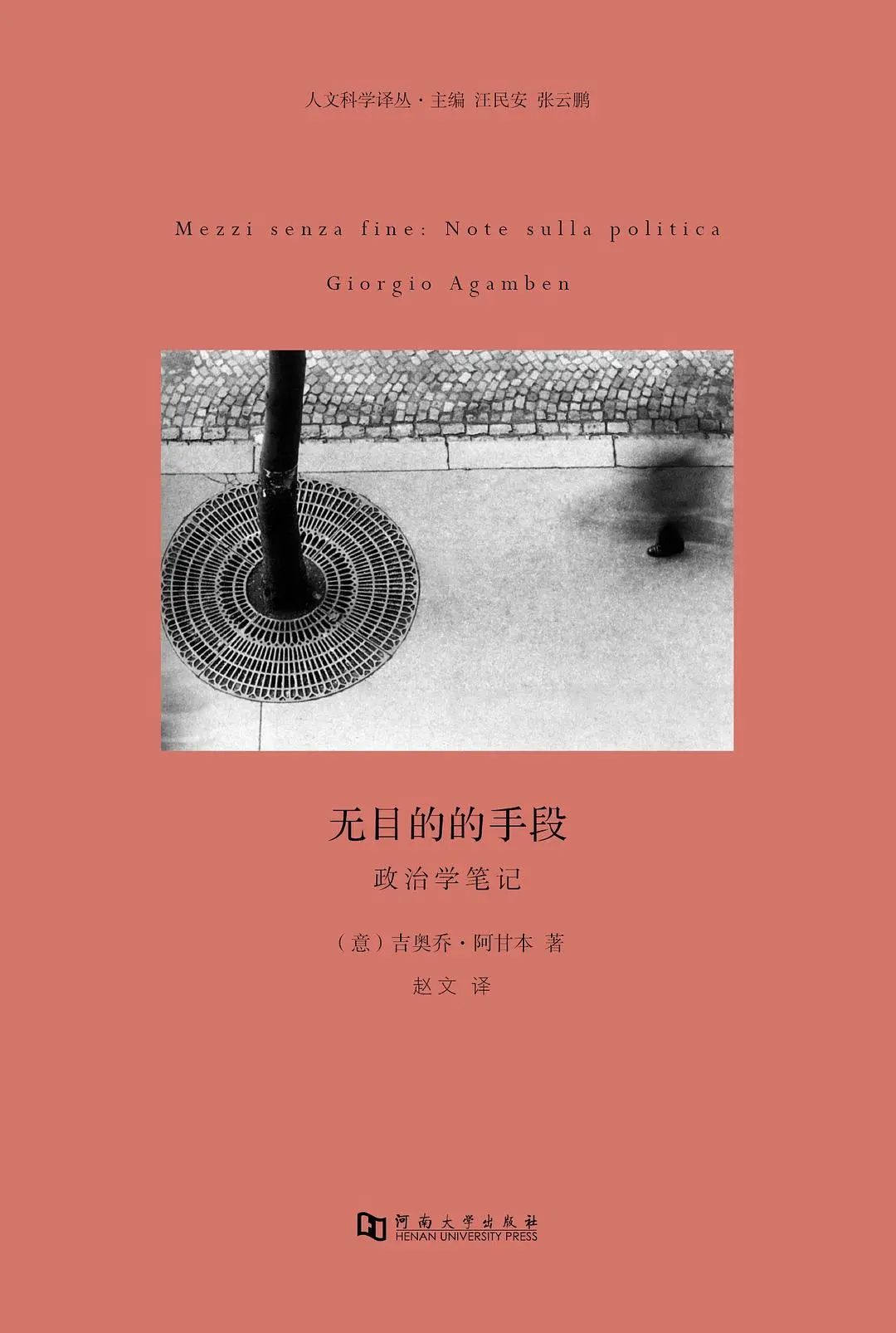
《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 吉奧喬·阿甘本著,趙文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
為此,施米特求諸傳統的歐洲公法原則。在他眼裏,“正當的戰爭”就應該像騎士決鬥那樣不問對錯,只問雙方是否符合保障決鬥公平的程序。這是一個令人混淆的表述,戰爭真的沒有對錯之分嗎?不,它恰恰建立在陸權、海權正邪之分的前提之上,它也可能成為“東方-西方的對峙”,“東方是陸地,西方是海洋”。[58]最大陸權國家的戰略學家彼得羅夫就據此指出了地緣政治的善惡之別。
《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一書共有四章,彼得羅夫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了“地緣歷史善惡二元論”。有趣的是,彼得羅夫在這裏隻字未提地緣戰略,甚至沒有像施米特那樣上溯法權理論,而是關注起宗教問題。他列舉了幾種反基督教思想,如共濟會的“所羅門教堂”、納粹主義的“千年帝國”等。不論這些思想有何不同,究其實質:
所有這一切跟猶太教地球的夙願相近似,因此猶太人拒絕了基督的上天價值,並期待自己的猶太地球“救世主”(這是猶太教的實質)。對“人間天堂”的渴望意味着對上帝王國的不信任,甚至這一點在忘卻渴望的意義情況下“改造不完美世界”的願望受到驅使時,它經常減輕建立撒旦王國的困難。[59]
摩尼教靈知主義和猶太教神秘主義或幻想通過“光明戰勝黑暗”建立“地上天國”,或以為佔有神性就可以揚棄一切秩序規則。[60]與這種做法截然相反,真正的基督教徒始終“在上帝王國裏永遠地生活”。[61]
大航海和宗教改革帶來的不僅僅是法權關係的變革,更是新教上流社會與猶太金融資本家的秘密聯盟:
所有集中起來的拒絕天主教的言行使反基督教力量有了批評它旨在進一步分化西方基督教合適的藉口。新教的宗教改革運動在猶太人明顯的影響下開始了。猶太人“成為了時髦……公爵和大學直接招聘猶太語教師,並且不僅在德國和意大利,而且在法國和波蘭設立專門的教研室”。“馬丁·路德本人教授猶太語”,“在猶太人那裏打聽情況”,保護他們。[62]
事實上還不待宗教改革,早在12世紀,猶太裔基督教神學家約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1135-1202)就通過把三位一體學説歷史化,完成了“人間天國”的理論構造。[63]在彼得羅夫看來,歐洲精神正受到猶太神秘主義強有力的挑戰,承擔拯救基督教文明的重責只有落在俄羅斯東正教的肩上。
如今,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和法國式的多元主義成為“神聖世俗化”的最新表現形式。它們或者顛倒了古典的善惡標準,或者乾脆取消了善惡的區分,讓人分不清楚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在這些來勢洶洶的政治思潮面前,堅守傳統的俄羅斯倒顯得離經叛道了。“正是在這個進程的背景下,俄羅斯的離經叛道在全世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64]可見彼得羅夫講的是地緣政治問題,關注的卻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根基。
1938年,英法等國為了禍水東引不惜製造“慕尼黑陰謀”;另一邊,日本關東軍挑起張鼓峯事件,蘇聯的外部局勢迅速緊張起來。一首題為《假如戰爭在明天》的嘹亮軍歌頓時響徹廣袤的俄羅斯大地。它的頭一段歌詞為:假如戰爭在明天,從這邊到那邊,從極東到極西都已做好準備,全國的人民羣眾團結起來,把敵人無情的全部消滅。在天空,在地上,在海洋中,唱軍歌真雄偉,真豪邁。假如戰爭在明天,我們今天就要準備好戰爭。[65]
“從這邊到那邊,從極東到極西”正是俄羅斯廣闊戰略縱深的最好寫照,這是它能夠戰勝拿破崙、希特勒的重要前提。然而,“冷戰”的失敗卻足以警醒俄羅斯民族,真正可怕的敵人不在天空,不在地上,也不在海洋中,而在社會文化精英的思想中,這裏沒有如此廣闊的戰略縱深。[66]一旦他們誘使人民放棄了“我們今天就要準備好戰爭”的精神根基,俄羅斯也就失掉了任何取勝的可能。
面對美國新保守主義改造東正教、伊斯蘭教和儒家文明,在地面上建立“天國”的企圖,彼得羅夫索性設計了俄羅斯、印度、中國、伊朗的“反大西洋傳統文明大陸集團”。從表面上看,這不過就是當年豪斯霍費爾(Karl Haushofer)“柏林—莫斯科—東京軸心”的放大版。但是,彼得羅夫新大陸聯盟的基礎絕不只是政治地理上的生存空間[67],它更以四種文明共同遭受的精神挑戰為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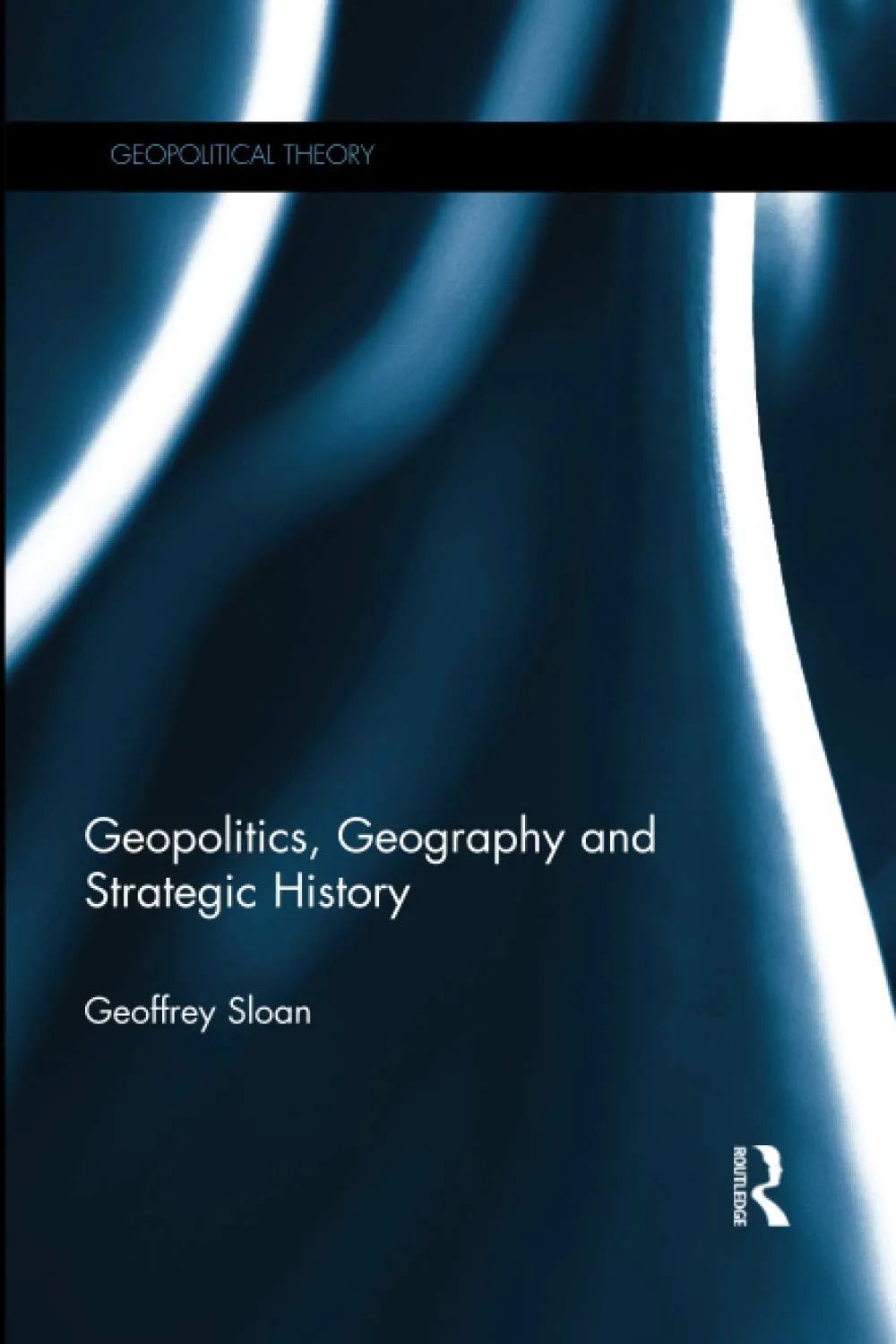
Geoffrey Sloan 《 The Geopolitics Reader》
“在這種情況下,俄印中伊國家的軍事潛力起到的將只是輔助作用。文明、精神武器將成為取勝的主要因素。”“俄羅斯的倫理學是這樣的,它與亞洲的倫理學非常相似,但完全不同於高利盤剝的新教徒的倫理學。”彼得羅夫接着指出:俄印中伊國家文明聯盟的最大意義在於這個聯盟具有多樣性,每一個國家在文化上具有獨特性,有着古老傳統的人民具有忠誠性,以及人民當時在接收其他有意義的事物(無論它會起到積極作用,還是起到消極作用)時具有完全的開放性。[68]
由此看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戰爭(無論是軍事上的戰爭,還是意識形態上的戰爭)有沒有正邪之分,而在於什麼才是正義戰爭的標準,是“普遍文明”還是保家衞國?哪個更符合城邦動物的自然本性?
歐洲國家的邊界線長期變動不居,有時很難説清楚到底誰才是某片領土本來的主人,只能暫時懸置歐洲國家戰爭的正義性問題。這不是取消了正義,而是避免它受到其他原則的干擾。中國既沒有強迫日本改變文化信仰,又沒有入侵過日本,中日之戰孰正孰邪豈非一目瞭然?
從這個意義上説,彼得羅夫庶幾給出了地緣政治的哲學定義,儘管歷史上的俄國東正教確實不像他所説的那樣敦厚善良。
顛倒了的中心與邊緣:古今文野之辨
1878年的農曆二月初二,波斯國王出訪倫敦,英王贈之以勳章。這個今天看來再正常不過的外交禮儀,卻在當時的英國輿論界引發軒然大波——半文明國家怎麼能享受與英國對等的待遇?時任中國駐英公使郭嵩燾在目睹了這一幕後,不禁感慨萬分: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者尚無其人,傷哉![69]

出訪歐洲的第一位波斯君王納賽爾·丁·沙赫
郭氏在對比中國傳統夷夏之辨與西方現代文野之別時,恐怕沒有意識到,二者在本質上有多麼不同!對此,唐曉峯教授有一段論述發人深省:古典的文野之辨,文明一方對於野蠻一方,除了要“懷柔遠人”、“邊境晏安”之外,基本別無所求,更恨不得以長城永久隔限其往來(中國和羅馬帝國都修過長城)。而此時的文明一方對於野蠻一方,卻要侵入、統治、剝奪。[70]
質言之,無論是古代中國人還是古代歐洲人,都相信確實存在一種超越人類意志的自然秩序,人處於這種自然秩序中,便只能順應它。文明人與野蠻人毋寧處在不同的自然秩序層級之上,最好將二者隔離開來,使之互不僭越。與此不同,近代西方人卻將文明與野蠻視為歷史進步的不同階段,文明作為歷史的發展方向,必將取代野蠻。
古今文野之辨之轉化取決於古今政治哲學的轉變。大抵從中世紀晚期的唯名論哲學開始,例如威廉·奧卡姆(William of Occam)等人就已經明確地把維護勞動對於土地的佔有權視為政治正義的前提。用霍布斯(Thomas Hobbes)轉述英國經院哲學家的話説,“正義就是將每人自己所有的東西給與自己的恆定意志。”霍布斯接着説:這樣説來,沒有所有(即沒有所有權)的地方就沒有不義存在;而強制權力沒有建立的地方(也就是沒有國家的地方)就沒有所有權存在;在那種地方所有的人對一切的東西都具有權利;因之,沒有國家存在的地方就沒有不義的事情存在。[71]
如果霍布斯説得還不夠明確,那麼洛克(John Locke)索性把私人財產權視為自然權利的根本。如其所言:他的身體所從事的勞動和他的雙手所進行的工作,我們可以説,是正當地屬於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東西脱離自然所提供的和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態,他就已經摻進他的勞動,在這上面參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東西,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財產。既然是由他來使這件東西脱離自然所安排給它的一般狀態,那麼在這上面就由他的勞動加上了一些東西,從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權利。[72]
在古代哲人那裏,人的技藝與自然秩序具有同一性,越是好的技藝越能體現自然目的。例如,亞里士多德既稱政治為統治技藝,又強調政治體現了自然的目的,二者毫不矛盾。[73]然而,近代哲學家把自然降格為供人操作的質料狀態,正如洛克所説,“由他來使這件東西脱離自然所安排給它的一般狀態”。直至康德的觀念論哲學,這種人對於自然質料的操作更成為理性進步的歷史過程:
理性使人類得以完全超出於動物社會的第四步和最後一步就是:他理解到(不管是多麼模糊地)他才真正是大自然的目的,大地之上所生存着的沒有任何一種東西在這方面可以和他相匹敵。當他第一次向羊説: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賜給你,並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我,並且把它揭下來穿在自己的身上……這時候,他就具備了使他的本性可以超出於一切動物之上的一種特權,他不再把它們看作是和自己同類的被創造物,而只把它們看作是由他任意支配以達到自己所喜愛的目標的手段和工具。[74]
康德的“自然地理學”正是近代地理學的先驅。[75]文明人對野蠻人的地理大發現就是康德理性進步的歷史現實。誠如韓國學者金容九所説,“至於無主地的概念,其前提就是由於土著人是野蠻人,因此並不具備保有財產權的法律能力”。[76]殖民主義者對野蠻人的態度不就是康德對羊的態度?這裏不僅包括海權國家對於印第安人,也包括俄國人對於中亞人的態度:自18世紀後期以來,俄國採取了種種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個別哈薩克首領一旦宣誓臣服於俄,俄國即宣稱其土地與人民皆屬於俄,而對其徵税和徵取烏拉差役,敲詐勒索,日甚一日。[77]
另外,霍渥斯(H. H. Howorth)曾指出:“俄國在侵略中亞的過程中,還有一個攫取領土的手段,就是先讓那裏的民族臣服於俄國,讓這些臣服了的民族去搶佔領土……考夫曼還向希瓦汗國提出:沙皇的臣民到了哪裏,俄國即在那裏進行統治。於是,俄屬哈薩克人所到之處,如新河、阿克察庫耳、布坎山以及從克孜勒·庫姆到新河伊爾基拜的所有道路,都被認為是屬於俄國的了……”[78]
俄國人的擴張方式符合歐洲內部的主權國家原則嗎?看來地理大發現不只是大航海的事情,也與俄國東擴息息相關。施米特所説的肆意掠奪和佔有“自由真空領域”的現象不僅僅出現在美洲、非洲,同樣也出現在歐亞大陸的腹地,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未必沒有相似的形而上學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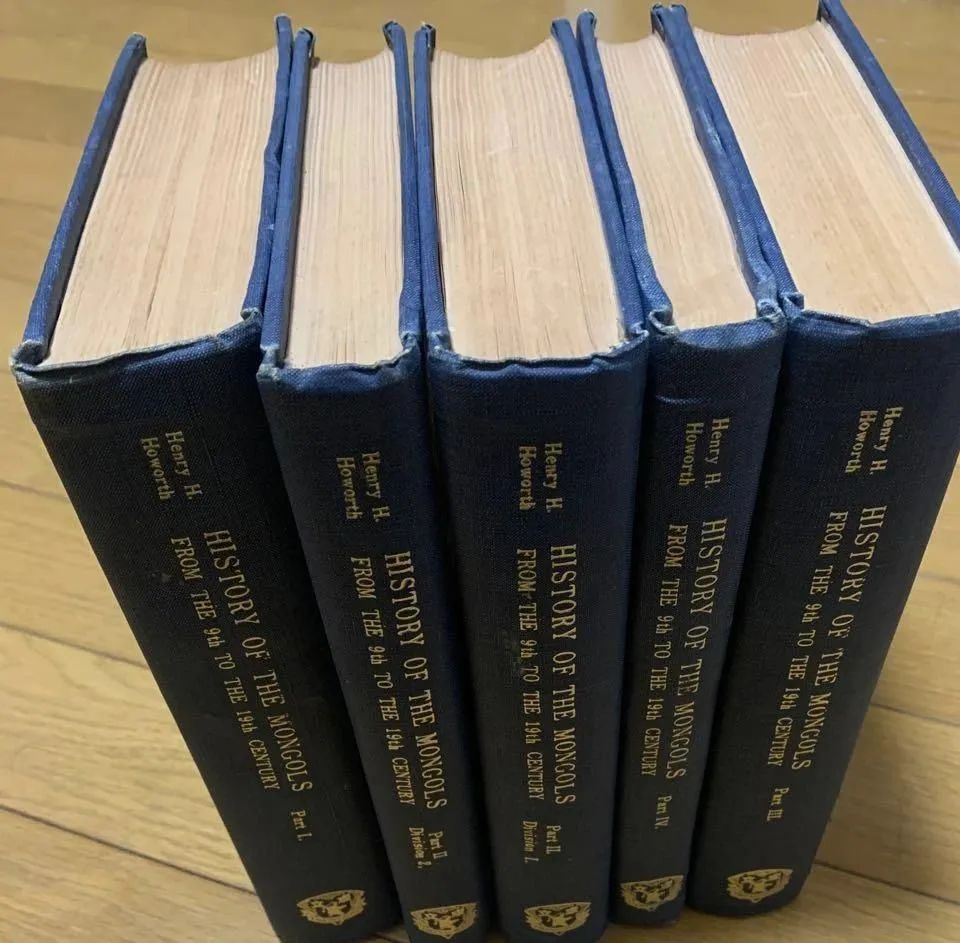
《History of the Mongols: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nry Hoyle Howorth
郭嵩燾曾説過:“近年英、法、美、德諸大國角力稱雄,創為萬國公法,以信義相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79]上古三代與西方近代文明的簡單類比,竟讓彼時一干洋務派產生了這樣的錯覺,以為西洋諸國不過“癬疥之患,猶可以信義籠絡之”。殊不察“國際法意味着歐洲‘大國’乃至‘基督教世界’的法律,實際上就是保護上述世界的貿易、旅行乃至傳教自由的一種法律秩序”。80只不過到了19世紀,上述“基督教世界”與“非基督教世界”的區分變成“文明”與“野蠻”的區分。
恐怕正是由於對西方近代佔有權觀念的糊塗,李鴻章、郭嵩燾們竟在阿古柏偽政權行將覆亡之際,仍聽信英國人的哄騙,一再上奏朝廷要求放棄南疆。[81]不知出使英倫的郭氏是否瞭解,那個被英國媒體譏笑為“哈甫色維來意斯里得”(half-civilized)的波斯,長期以來遭到英、俄兩國的輪流出賣,幾無信義可言。
在西姆斯筆下,歐洲近現代史就是一部歐洲邊緣國家圍繞歐洲中心控制權的爾虞我詐的鬥爭史。我們不難發現,神聖羅馬這個歐洲中心,連同巴爾幹、尼羅河下游、小亞細亞、兩河流域、波斯、印度、中國這一系列人類古老文明的發祥地,竟然變成了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到底誰才是中心,誰才是邊緣?
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描繪了古代草原遊牧文明和內陸農耕文明的鬥爭史,就顛倒了二者之間的主從關係。他區別中心與邊緣的標準不再是自然秩序和文化的向心力,毋寧是權力主體的能動性。這是一次馬基雅維利式的顛倒。
時至今日,藉着“一帶一路”的東風,麥金德、馬漢等人在中國學界受到了空前的禮遇。然而,中國倘要建立自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就不能停留在對外政策的高度。她需要在文明史的視角上把業已顛倒的中心-邊緣關係再倒轉回來。惟其如此,才能説我們真正超越了陸權-海權的二元論。
1 [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88頁。
2[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第188頁。
3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Lancaster, Pa.: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 1939, p. 404.
4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p. 403。中譯本參見[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學的性質——當前地理學思想述評》,葉光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05、503頁。
5[美]普雷斯頓·詹姆斯、傑弗雷·馬丁:《地理學思想史》,李旭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13頁。
6[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徐松巖、黃賢全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7 參見[英]羅傑·克勞利:《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陸大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44頁。
8[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孟維瞻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
9 亨利八世的前妻凱瑟琳系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員。早在13年前,即1519年,亨利八世就參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角逐,並敗給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
10[俄]瓦列裏·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於寶林、楊冰皓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頁。
11[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第32頁。
12趙爾巽等:《清史稿》第38冊,《列傳第一百五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456頁。
13趙爾巽等:《清史稿》第38冊,《列傳第一百五十五》,第11477頁。
14參見[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的政治學之研究》,譯後記,王鼎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頁。
15參見張豔璐:《1917年前俄國地理學會的中國邊疆史地考察與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第15頁。遺憾的是,目前尚未見到我國學者對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專題研究。
16馬克思、恩格斯:《不列顛政局。——迪斯累裏。——流亡者。——馬志尼在倫敦。——土耳其》,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頁。
17Labanov Rostovsky:Russia and Asia,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3, p. 147,轉引自許建英:《近代英國和中國新疆(1840—1911)》,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頁。
18王治來:《中亞通史·近代卷》,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頁。
19恩格斯:《俄國在中亞細亞的進展》,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6—637頁。
20[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林國基、周敏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頁。
21[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林爾蔚、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57頁。
22恩格斯:《俄國在遠東的成功》,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頁。
23參見李義虎:《地緣政治學:二分論及其超越——兼論地緣整合中的中國選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頁。
24[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第224頁。
25[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第7、9頁。
26參見Henry Rawlinson: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John Murray, 1875, pp. 146-147。
27Charles Marvin:The Russians at the Gates of Heart,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5, p. 49.
28[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第43頁。
29[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引言,第2頁。
30[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第60頁。
31“波希墨特”和“利維坦”的典故分別出自《舊約·約伯記》第40、41章。上帝創造了一個形同河馬的龐然大物稱霸陸地,又創造出一個類似鱷魚的巨大怪獸統治海洋。霍布斯曾經用這兩個怪獸作為書名,分別論述內戰狀態和統治狀態。然而,施米特用二者隱喻陸權國家和海權國家。本文在施米特的意義上使用這對術語。參見[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第7頁。
32[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第250—251頁。
33[美]艾爾弗雷德·賽耶·馬漢:《亞洲問題》,載[美]艾爾弗雷德·賽耶·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年):附亞洲問題》,附錄,李少彥等譯,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頁。
34[英]麥金德:《1919年1月25日發生在法國外交部的事件的札記》,載[英]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附錄,武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80頁。另見[英]哈福德·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的政治學之研究》,王鼎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頁。
35麥金德:《環形世界與贏得和平》,[英]哈福德·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的政治學之研究》附錄二,王鼎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176頁。
36[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序言,劉愈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5—6頁。
37[美]索爾·科恩:《地緣政治學:國際關係的地理學》,嚴春松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
38參見劉小楓:《麥金德政治地理學中的兩種世界文明史觀》,載《思想戰線》2016年第5期。
39另一個與之有關的例子是邊沁(Jeremy Bentham)的學生包令(Bowring John),此人充當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急先鋒。
40[美]艾倫·沃爾夫:《合法性的限度——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矛盾》,沈漢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67頁。卡爾·施米特對於這種兩重性另有深刻的判斷,二者分別基於自由主義、多元主義的議會制與強調公意(general will)同一性的民主制。馬克斯·韋伯設計《魏瑪憲法》的初衷在於協調這二重性,但魏瑪共和國的危機恰恰在於沒能處理好二者的矛盾。參見[德]卡爾·施米特:《當今議會制的思想狀況》,載[德]卡爾·施米特:《政治浪漫派》,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220頁。
41[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歐洲公法的國際法中的大地法》,前言,劉毅、張陳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2[俄]瓦列裏·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25頁。
43[俄]瓦列裏·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144頁。
44[德]卡爾·施米特:《游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附識》,朱雁冰譯,載[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劉宗坤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頁。
45[德]卡爾·施米特:《游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附識》,朱雁冰譯,載[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308頁。
46參見[美]艾爾弗雷德·賽耶·馬漢:《亞洲問題》,載[美]艾爾弗雷德·賽耶·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年):附亞洲問題》,附錄,第515頁。
47[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第63頁。
48[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歐洲公法的國際法中的大地法》,第37頁。
49[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第43頁。
50[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第43—44頁。
51[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歐洲公法的國際法中的大地法》,第62—63頁。
52[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歐洲公法的國際法中的大地法》,第69頁。
53[英]布倫丹·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第32頁。
54[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第7頁。
55[德]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第26頁。
56[德]施米特:《霍布斯國家學説中的利維坦》,應星、朱雁冰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5頁。
57參見[意]吉奧喬·阿甘本:《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趙文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145版。
58[德]卡爾·施米特、什克爾:《與施米特談游擊隊理論》,盧白羽譯,載劉小楓(選編):《施米特與政治的現代性》,魏朝勇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頁。
59[俄]瓦列裏·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57頁。
60參見[美]埃裏克·沃格林:《沒有約束的現代性》,張新樟、劉景聯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61[俄]瓦列裏·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57頁。
62[俄]瓦列裏·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64頁。
63相關論述,參見劉小楓:《約阿希姆的“屬靈理智”與“歷史終結”論》,載《海南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64[俄]瓦列裏·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66頁。
65歌詞翻譯,引自百度百科“如果戰爭在明天”詞條。
66例如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宣傳部長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著名理論:只有走進極權主義政黨的內部才能打敗它。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精英也一度流行過“堡壘從內部攻破”的信條。
67參見Karl Haushofer, “Why Geopolitik?” in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Gearóid?London and New York: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3, pp. 33-35。豪斯霍費爾發表此文時,納粹德國已經進攻蘇聯,他的聯盟設想不復存在,但其理論基礎並沒有發生變化。
68[俄]瓦列裏·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第164—165頁。
69郭嵩燾(著),鍾叔河、楊堅(整理):《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4年版,第491頁。
70唐曉峯:《地理大發現、文明論、國家疆域》,載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20頁。
71[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09頁。
72[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論政府的真正起源、範圍和目的》,葉啓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9頁。
73例如某些西方學者不清楚古人眼裏的自然與技藝的關係遠不同於今人,卻斷定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存在巨大的邏輯矛盾,以為霍布斯完勝亞里士多德。參見David Keyt, “Three Fundamental Theorems in Aristotle’ s Politics”, Phronesis, Vol. 32, No. 1(1987)。
74[德]康德:《人類歷史起源臆測》,載[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68頁。
75參見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pp. 38-39。
76[韓]金容九:《世界觀衝突的國際政治學——東洋之禮與西洋公法》,權赫秀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頁。
77王治來:《中亞通史·近代卷》,第223頁。
78霍渥斯:《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第3冊,第950頁,轉引自王治來:《中亞通史·近代卷》,第306頁。考夫曼,時任俄國突厥斯坦總督,在中亞素有“半個沙皇”之稱,清代史料有譯作“高甫滿”。
79郭嵩燾(著),鍾叔河、楊堅(整理):《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第91頁。
80[韓]金容九:《世界觀衝突的國際政治學——東洋之禮與西洋公法》,第18頁。
81參見許建英:《近代英國和中國新疆(1840—1911)》,第142—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