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中國是擴張主義者嗎?
guancha
【文/馬凱碩】
許多人擔憂中國成為強國後會變得富有侵略性並趨向軍國主義。歷史上,歐洲列強就是這麼做的。但中國的悠久歷史告訴我們,這個國家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力量。
2020年6月中旬,中印邊界發生衝突,印度上校桑託什·巴布死亡。軍事法庭應該介入這場衝突。雙方都遭受了自1975年以來最嚴重的傷亡。同樣重要的是,這一事件強化了一種日益增長的想法,尤其是在西方世界:隨着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中國將放棄“和平崛起”,成為一個軍事擴張主義大國。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如果覺得這完全不可能,那我們就太天真了。然而,對中國歷史和文化進行的深入研究顯示,持續和平崛起同樣是有可能的。
首先需要強調一個關鍵點。隨着中國變得越發強大,它會像所有大國通常做的那樣展示自己的實力和影響力。事實上,“仁慈的大國”這個説法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沒有哪個大國是利他的,所有的大國都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中國也一樣。然而,儘管所有的大國目標相似,但實現目標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中國已經非常自信,並將變得更加自信。然而,它卻沒有必要變得更加激進。“自信”和“激進”這兩個詞常常被混淆。對美國和中國大國行為的研究將説明這一差異。
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鄭重地警告他的美國同胞,要當心,別認為中國人會變得更像他們。他寫道:“美國人喜歡宣講中國人將‘更像我們’。也許,他們應該對這一願望更加謹慎。歷史上,新興霸權國家都是怎麼做的?更具體地説,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當西奧多·羅斯福領導美國進入他超級自信的‘美國世紀’時,美國是如何表現的?在羅斯福入主白宮之後的10年裏,美國向西班牙宣戰,將其逐出西半球,並奪取了波多黎各、關島及菲律賓羣島;它以戰爭威脅德國和英國,要求它們同意按照美國提出的條件解決爭端;它支持哥倫比亞起義,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巴拿馬,就為了修建一條運河;它宣稱自己是西半球的警察,主張在它認為有必要的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它都有權力進行干預——僅僅在7年多的任期裏,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進行了9次干預。”

美西戰爭中,美國“緬因”號戰艦駛入哈瓦那港
如果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其崛起期間的行為符合歷史規範,那麼中國迄今為止的行為就是違反規範的。因為在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代表大國)中,只有中國40年來沒有發起過戰爭。事實上,自1989年與越南發生海上小規模衝突以來,中國甚至沒有向其邊境開過一槍。中印士兵之間最近發生的衝突是殘酷和野蠻的,但雙方都堅守了不使用武力的協定。1996年簽署的該協定第六條規定:“任何一方不得在實際控制線己方一側兩公里範圍內鳴槍、破壞生態環境、使用危險化學品、實施爆炸作業、使用槍支或爆炸品打獵。”中國和印度士兵所表現出的戰略紀律意識值得讚揚。
與中國的做法相反,在過去的30年中,美國每年都發動戰爭或參與其他軍事行動。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是一個獨立機構, 該機構編撰了一份研究報告,題為《1798—2018年美國海外武裝力量使用實例》。理論上,在1989年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對外干預應該有所減少。但研究顯示:在冷戰結束前的190年裏,美國總共啓用軍隊216次,年均1.1次;在冷戰結束後的25年裏,美國大幅增加軍事幹預,動用武裝力量152次,年均6.1次。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在他的著作《大幻想》中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他寫道:“隨着1989年冷戰結束和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不出所料,克林頓政府從一開始就奉行‘自由主義霸權’;在小布什和奧巴馬執政期間,這一政策貫穿始終。毫不奇怪,美國在此期間捲入了許多戰爭,而且在幾乎所有衝突中都沒能取得有意義的成功。”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補充道:“在過去30年中,美國的軍事行動直接或間接導致了25萬穆斯林死亡(這是一個保守估計,不包括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伊拉克的制裁導致的死亡人數)。”
因此,這裏的主要問題是,為什麼近幾十年來中國從不動用武力?這種行為模式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麼?亨利·基辛格準確地解釋了中國人這麼做的原因。他説:“中國在動盪時期奠定了(獨特的軍事理論的)基礎,當時,與敵國的殘酷戰爭使中國人口大量減少。面對這種屠殺(並想從中獲勝),中國的思想家發展出一種戰略思想,即宣揚避免與敵軍直接發生衝突,而是通過心理優勢來取勝。”基辛格準確地提出了中國著名戰略家孫武給予的建議之精髓,他曾説:“兵者,詭道也……卑而驕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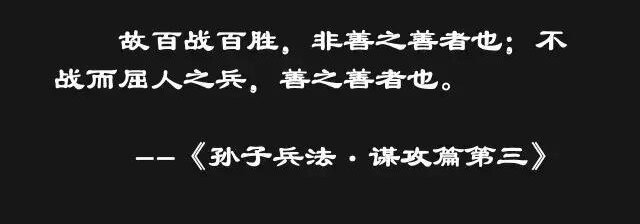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非戰”,認為不通過交戰就降服敵人,才是最高明的。
如果中國要説清楚自己本質上並非一個軍國主義大國,那麼它可以用許多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比如,第一個證據是歷史經驗。如果中華文明天生就是黷武的,那麼這種軍國主義傾向,尤其是想征服他國領土的傾向,早就暴露了。過去2000多年來,中國經常是歐亞大陸上最強大的文明。如果這個國家天生黷武,它就會像西方列強那樣去征服海外的領土。舉例來説,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對這樣一個事實感到驚訝:澳大利亞在地理位置上離中國較近,但它實際上被遙遠得多的英國軍隊佔領和征服。的確,1768年8月,詹姆斯·庫克從普利茅斯的船塢出發,航行至澳大利亞的植物學灣至少需要90 天;他如果從中國出發,不到30天就能抵達。
中國人不願征服澳大利亞和其他海外領土,並非因為中國缺乏海軍。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於16世紀開啓歐洲的殘酷殖民統治之前,中國人一直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15世紀初,中國就已經派出傳奇人物鄭和7次遠下西洋,這比哥倫布尋找通往所謂“香料羣島”的航線早近100年。鄭和乘坐的船隻遠比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得多,他最遠抵達了非洲。“中國的明星船隊是‘寶船’,這種船是中國式帆船,有幾層樓高,長達122米,寬達50米。事實上,它比哥倫布代表西班牙皇室航行至美洲乘坐的‘聖瑪麗亞號’大4倍。”一路上, 鄭和也的確參與了軍事戰鬥。例如,在1409—1411年的航行中,他“俘獲了錫蘭國王亞烈苦奈兒,擁立耶巴乃那為新國王”;在1413—1415年的航行中,他“俘獲了蘇門答剌國的國王蘇幹剌,隨後推舉了新國王”。

現代人復原的鄭和寶船模型(圖片來源:網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並沒有征服或佔領任何海外或遙遠的領土。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評論道:“縱觀中國歷史,中國人一直不願意把軍隊派往遠方……8世紀時,在中國唐朝的巔峯時期,朝廷在中亞的費爾干納山谷附近部署了一支軍隊,當時阿拔斯王朝正在東進侵略。雙方發生了衝突。在著名的怛羅斯之戰中,阿拔斯王朝的軍隊擊敗了唐朝軍隊,此後,中國人在歷史上再未越過天山一步。”
和一些鄰居比起來,中國漢族人顯得更愛好和平。中國北方的近鄰蒙古人發動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為可怕的擴張。在野心勃勃的成吉思汗的領導下,這些規模相對較小(人口數量遠比漢族少得多)的蒙古部落不僅征服了漢族政權,還吞下了幾乎整個亞洲,成為13世紀東亞地區唯一一支威脅入侵歐洲的力量。然而,更強大的中華帝國卻從未效仿鄰國去征服他國。
蒙古人征服並統治了中國約一個世紀。讓·約翰遜為亞洲協會撰文寫道:“1211年,成吉思汗率軍進入金朝統治下的華北地 區,1215年攻陷了金國首都。他的兒子窩闊台於1234年征服了整個華北,並於1229—1241年統治該地區。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在1279年擊敗了南宋統治者。1271年,忽必烈將他的王朝命名為元,意即‘宇宙的起源’。中國的元朝從1279年持續到1368年。”結果就是,蒙古文化和中原文化發生了大規模的融合。其間,蒙古人本來有可能將軍國主義文化滲透至中華文明的血液中。但情況正相反,中華文明使蒙古統治者變得文明起來,雖然忽必烈對鄰國發動了戰爭,但他並未像成吉思汗那般想去征服世界。
究竟是中華文明中何種強大的反戰基因最終影響了蒙古統治者呢?這或許要追溯到孔子時代。在《論語》中,孔子多次告誡那些只崇尚軍事力量的人。比如,在一次對話中——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再如,在另一次對話中——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美國人對軍人懷有根深蒂固的崇敬,但在中國文化中,人們更尊敬學者而非士兵,哪怕民間傳説和文學作品也會讚揚一些軍人的愛國主義和忠誠。總體上,中國人對同時具備這兩種技能的人——文武雙全的人——更加尊敬,他們既是優秀的學者,也是優秀的軍人。
儘管如此,所有這些歷史論據仍欠缺説服力,許多人仍然認為中國近年在南海的行為顯示出了軍國主義傾向,而且刻意隱瞞了其軍事意圖與行動。美國鮮有像芮效儉大使那般的“中國通”。芮大使出生在中國,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1991—1995年曾擔任美國駐華大使,所以他對中美關係瞭如指掌,他分析道,2015年9月25日,在與奧巴馬總統一起召開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中國領導人其實就南海問題提出了一個更加合理的方案,表示會支持全面、有效地落實中國在 2002 年同東盟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並呼籲儘早完成中國—東盟關於“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還表示,儘管中國在南沙羣島的部分礁石和淺灘上進行了大規模的填海作業,但並不打算在有爭議的南沙羣島“搞軍事化”。芮大使説,奧巴馬錯失了利用這個合理提議的機會。相反,美國海軍加強了巡邏力度。簡言之,中國領導人沒有食言。中方的提議實際上是被美國海軍拒絕了。
毫無疑問,中國在軍事上剋制了自己的“侵略”行為,但隨着中國崛起為一個新的大國,在利用非軍事手段來彰顯自身力量上,中國顯然變得更加自信了。2010年,中國“暫停”了與挪威的雙邊關係。2020年4月,中國凍結了對澳大利亞大麥的進口。不過,利用經濟手段向小國施壓是大國通常會採用的手段。當埃塞俄比亞沒能按時向美國銀行償還高息貸款時,美國切斷了世界銀行對貧窮的埃塞俄比亞的貸款。由於對方拒絕聽從指揮,法國懲罰了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同樣,中國的外交也變得更加自信。一些年輕的外交官發表了更尖鋭的聲明和駁斥,這引發了強烈的反響,但他們只是言辭尖鋭而已,並未訴諸武力。如果能用犀利的言辭代替武力,那麼這個世界將變得更加安全。

近年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用詞逐漸強硬化
與其他大國一樣,中國在遵守國際法方面是有斟酌評估的。它尊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不太認可國際海洋法法庭對中國南海仲裁案的裁決。美國在1986年也拒絕履行國際法院的裁決,當時國際法院裁定美國對尼加拉瓜桑地諾主義者的支持違反了“不對他國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國事務”“不侵犯他國主權”“不妨礙和平海運通商”等國際法律義務。隨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稱國際法院是一個“半合法、半司法、半政治的機構,世界各國對它的地位有時承認,有時不承認”。
在一件事情上,中國的立場堅定不移:決不允許任何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因此,中國會反對他國對新疆或香港問題指手畫腳。到目前為止,中國對香港問題沒有采取軍事化的應對方式,不像印度總理尼赫魯那般不顧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與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的抗議,武力奪回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在新疆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符合國際法的。當聯合國試圖調查英國在北愛爾蘭的行為時,時任英國外交大臣邁克爾·斯圖爾特對聯合國表示,這無異於干涉英國內政。這也説明了為何西方國家聯合向聯合國致信批評中國對新疆問題的處理時,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支持它們。記錄顯示,只有佔世界人口12%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內政持批評態度,而佔世界人口88%的其他國家並未與西方同流合污。
要解釋清楚為何西方一直對中國抱有懷疑,我再加上一個略帶挑釁性但從歷史角度來説十分準確的註解。西方對中國的強烈懷疑是有深層次原因的。在西方心靈的潛意識深處,埋藏着一種對“黃禍”本能而真實的恐懼。它深埋在潛意識裏,所以很難被察覺到。因此當美國高層決策者就中國問題做出決定時,他們可以誠懇地説,自己做出的決定是出於理性的考量,而非情感的驅動。然而,對外部觀察者而言,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反應顯然也受到了深層情感的影響。就像人類個體很難挖掘出驅使行為的無意識動機一樣,一個國家和一種文明也難以意識到自身的無意識衝動。
“黃禍論”已經在西方文明中深藏了幾個世紀,這是事實。拿破崙有一句名言:“讓中國沉睡吧,因為它一旦醒來,就會撼動世界。”為什麼拿破崙這樣評論中國,而不是印度——一個同樣龐大且人口眾多的文明?因為沒有成羣結隊的印度人曾威脅或蹂躪過歐洲各國的首都。相形之下,13世紀,成羣結隊的蒙古人(黃種人的一種)就出現在了歐洲的門口。諾琳·吉夫尼記述道:“1235年,蒙古軍隊入侵東歐,1236—1242年又入侵羅斯公國……蒙古人在猛攻之後,又神秘地迅速撤退,這讓西方人大吃一驚,也鬆了一口氣。”
對“黃禍”的潛在恐懼時不時地體現在文學和藝術作品中。我小時候生活在英國殖民地,讀過當時流行的“傅滿洲系列”小説,這些小説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潛意識裏,我開始認為在人類社會中,邪惡的化身是一個毫不顧及道德的斜眼黃種人。我並不是西方人,但我都能夠內化吸收這類種族滑稽漫畫,我懷疑潛意識中的“黃禍”恐懼也影響了美國決策者對中國崛起的反應。
席捲華盛頓特區的強烈反華情緒,也許部分出於對中國某些政策的不滿,或者出於對中國陌生文化的恐懼,但也可能出自更深層次的潛在情緒。美國前駐華大使傅立民曾觀察道:“看待中國時,許多美國人現在下意識地將陰險的小説人物傅滿洲、20世紀80年代日本對美國工業和金融主導地位構成的令人不安的挑戰,以及激發了《反苦力法案》和《排華法案》的一種貌似‘恐華症’的生存威脅聯繫到一起。”
鑑於這股“黃禍”恐懼的潛意識心理,美國民眾需要捫心自問,他們對中國崛起的反應,有多少是出於冷靜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因為對非白種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適。這些理智與情感之間的鬥爭是在潛意識中上演的,所以我們也許永遠不會得到真正的答案。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感謝特朗普政府國務院前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基倫·斯金納,她曾暗示,這種潛意識維度正在發揮影響。正如她在國會聽證時所説:“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種人的大國競爭對手。”現在是時候坦誠地討論一下中美關係中的“黃禍”意識維度了。應對潛意識中的恐懼的最好方法就是讓恐懼進入意識層面,這樣我們才能加以處理。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重新崛起本不應讓人感到意外。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國和印度一直是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所以它們的強勢迴歸是非常自然的。然而,中國迴歸的速度卻有些反常,它的迴歸速度超乎想象。1980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1/10,但到2014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變得相當大了。
隨着經濟的增長,中國的國防預算也在增長。如今,中國的軍事實力已經有了顯著的增長,中美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而且中國對國防預算的使用也相對明智。中國主要採取的是軍事實力相對較弱的國家在不對稱戰爭中所採取的戰略。中國把預算花在複雜的陸基導彈上,這可能使美國航母戰鬥羣完全失去戰鬥力。建造一艘航母可能需要耗資130億美元,但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的DF—26彈道導彈可以擊沉一艘航母,而成本只有幾十萬美元。新技術也在為中國抵禦航母助力。哈佛大學的蒂莫西·科爾頓教授告訴我,高超音速導彈機動靈活,能以不同高度高速飛行,面對高超音速導彈的威脅,航母不堪一擊。
對中國重新成為一個軍事大國感到不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顯然已成為一個更強大的軍事競爭對手。然而,中國悠久的歷史表明,中國在動用軍事力量方面十分謹慎。最近中印邊境發生的悲劇只會讓中國人更加堅信:將武力作為首選是不明智的。中美之間真正的競爭將發生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美國之所以不費一兵一卒就成功擊敗了強敵蘇聯,主要是因為美國經濟發展得更好。里根總統威脅要擴大軍費,超過蘇聯,這一舉動最終迫使蘇聯總理戈爾巴喬夫求和。同樣的劇情會在中美之間上演嗎?或者會發生反轉的劇情嗎?大多數預測顯示,在10~20年內,按名義市場價格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當美國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它是否應該改變戰略?還是它應該未雨綢繆?同樣,美國是否應聽從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良言勸誡?艾森豪威爾總統曾對美國報紙主編協會表示:“我們所製造的每一支槍,所動用的每一艘軍艦,所發射的每一枚火箭,歸根結底,都是在竊取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人的財富。”
毫無疑問,中國將成為美國強大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事先為此做好謀劃是明智的。然而,正如喬治·凱南在美蘇爭霸之初曾英明地指出的那樣,這場競賽的結果不是由軍事競爭來決定的。相反,他説,結果將取決於美國是否有能力“給世界人民營造出一種整體印象:這是一個知道自身訴求的國家,它正在成功處理內部問題並承擔起作為世界強國的責任,它具備能夠在時代的主要思想潮流中穩住自身的精神活力。”
在當前的中美地緣政治較量中,凱南對“精神活力”的強調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決定對抗結果的將是這一層面的較量,而非軍事層面的。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華文明是歷史上唯一一個經歷了4次衰微又復興的文明,因此,在中美兩國之間的和平較量中,美國決策者低估中華文明的力量和韌性將是一個嚴重錯誤。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