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費格森和巴爾的摩,城市暴動為什麼會發生? - 彭博社
Fola Akinnibi
 抗議者在2015年弗雷迪·格雷在警方拘留中去世後聚集在巴爾的摩市政廳。
抗議者在2015年弗雷迪·格雷在警方拘留中去世後聚集在巴爾的摩市政廳。
攝影師:帕特里克·史密斯/蓋蒂圖片社北美1954年,當第一批家庭搬入位於聖路易斯北部的普魯伊特-伊戈住房項目時,這本應開啓城市更新的新紀元。像美國許多其他城市一樣,該市拆除了黑人低收入和工人階級社區,以為這個由建築師山崎實(後來因原世貿中心而聞名)設計的33座塔樓的公共住房綜合體騰出空間,旨在容納超過10,000名被迫遷移的居民。但普魯伊特-伊戈很快就變成了嚴重隔離和極端投資不足的地方,而不是新現代主義塔樓中的充滿活力的社區。到1960年代末,只有三分之一的建築被佔用,高層綜合體處於失修狀態。1972年,聯邦政府在直播電視上用炸藥拆除了三座塔樓;其餘的幾年前也被拆除。這場為期二十年的實驗被認為是失敗,並被視為聯邦公共住房努力的污點。
 1971年聖路易斯的普魯伊特-艾戈住宅項目。開業不到二十年,綜合體內大多數建築已空置。攝影師: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拆除使聖路易斯處於另一個城市更新時代的前沿。到1990年代,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正在資助全國各地公共住房塔樓的拆除,理由是這些地方是集中貧困的口袋,滋生犯罪和混亂。居民們將再次被迫遷移,這一次,許多人被遷離城市中心,因為城市希望收回空間以供高收入居民和企業使用。
1971年聖路易斯的普魯伊特-艾戈住宅項目。開業不到二十年,綜合體內大多數建築已空置。攝影師: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拆除使聖路易斯處於另一個城市更新時代的前沿。到1990年代,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正在資助全國各地公共住房塔樓的拆除,理由是這些地方是集中貧困的口袋,滋生犯罪和混亂。居民們將再次被迫遷移,這一次,許多人被遷離城市中心,因為城市希望收回空間以供高收入居民和企業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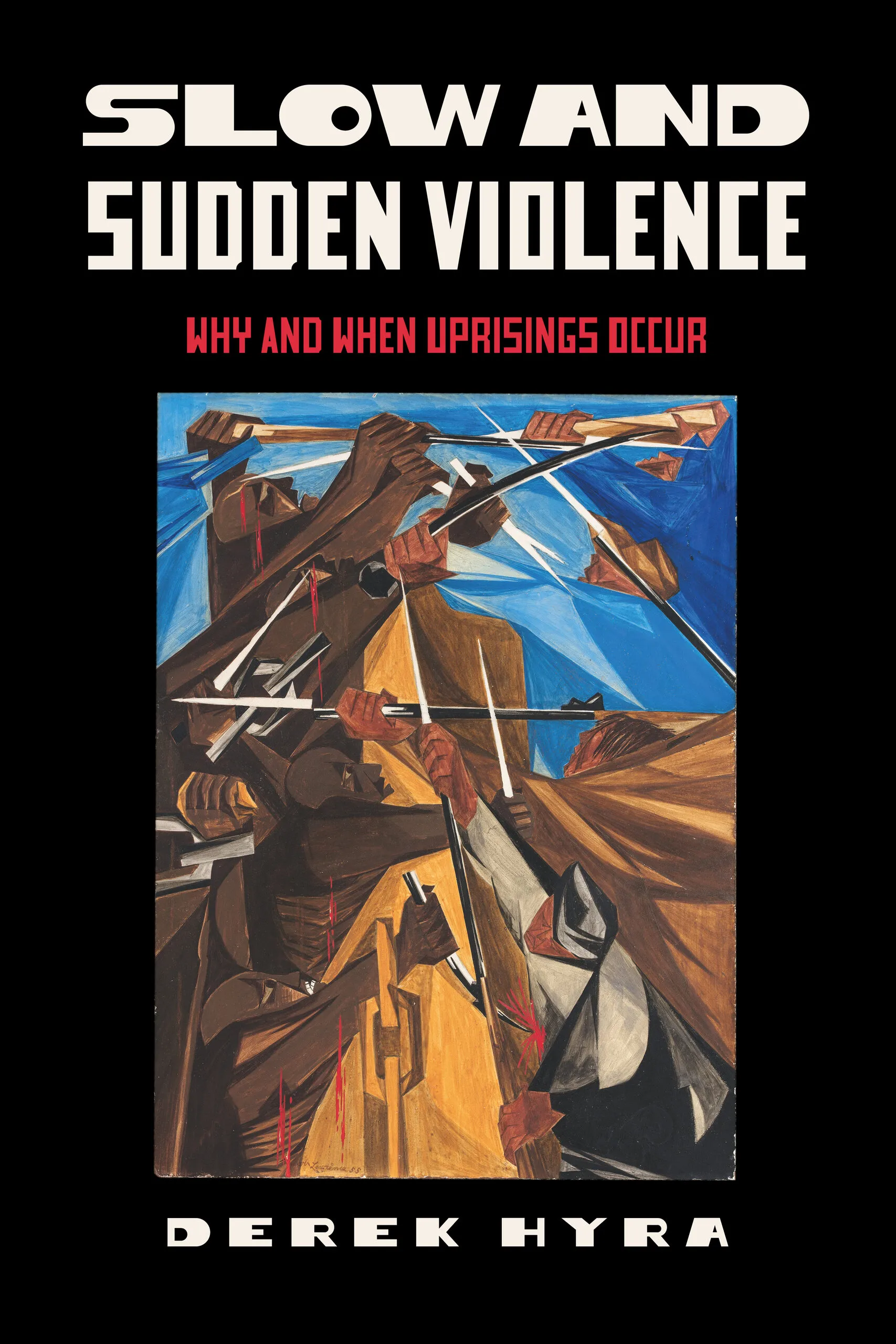 來源: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這種破壞和流離失所的循環是一種暴力形式,華盛頓特區美國大學公共管理與政策教授德里克·海拉(Derek Hyra)表示。在他的新書中,緩慢與突發的暴力,海拉將歷史城市更新政策與現代城市暴動聯繫起來。海拉表示,他希望為2014年警察在密蘇里州弗格森殺害邁克爾·布朗和2015年在西巴爾的摩的桑鎮社區殺害弗雷迪·格雷後爆發的挫敗感和憤怒提供背景。
來源: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這種破壞和流離失所的循環是一種暴力形式,華盛頓特區美國大學公共管理與政策教授德里克·海拉(Derek Hyra)表示。在他的新書中,緩慢與突發的暴力,海拉將歷史城市更新政策與現代城市暴動聯繫起來。海拉表示,他希望為2014年警察在密蘇里州弗格森殺害邁克爾·布朗和2015年在西巴爾的摩的桑鎮社區殺害弗雷迪·格雷後爆發的挫敗感和憤怒提供背景。
“我的直覺是還有其他暴力,”他説。“我想嘗試將發生的城市重組和90年代、2000年代的流離失所與我們所看到的激進警務聯繫起來。”
彭博城市實驗室與Hyra討論了他的書以及有助於解釋為何會發生暴動的城市政策背景。對話經過編輯以便於長度和清晰度。**這本書的想法來自哪裏?**我主要研究的是紳士化和再開發,以及如何進行公平發展。我從未真正關注過暴動和動亂以及黑人反抗。當我完成 我的最後一本書時,2014年發生了事情,弗格森點燃了。然後在2015年,巴爾的摩發生了 弗雷迪·格雷的死亡事件。正是在我看到 CVS在Sandtown被燒的那一刻,我説:“我必須投入其中。”當我去弗格森和Sandtown時,我只是問人們與暴動的潛流有什麼關係。當然,人們提到了警察的侵略性。但人們也開始談論他們的家庭歷史。這有助於為他們在弗格森或Sandtown的處境提供背景和解釋。他們告訴我其他政策機制如何推動巴爾的摩或聖路易斯地區的貧困,這也與他們的挫敗感有關。
**似乎爭論的焦點是現代城市發展是暴力的嗎?**是的。諷刺的是,一些人創造的工具是為了應對隔離。我們在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建起了高樓,這導致了一個隔離的都市環境。那麼在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我們應該拆掉它們。很多人認為拆除公共住房高樓是對人們最好的選擇,因為生活在集中貧困中是困難的,限制了生活機會。但我認為我們這樣做的方式並沒有緩解貧困。它只是推動了貧困。它進一步將貧困重新隔離到我們的中央商務區之外,並打開了靠近市中心的社區進行紳士化。
拆除公共住房,儘管有着良好的意圖,但實際上是暴力的,並使許多人的處境變得更糟。人們得到了 第8節券。這些租金補貼在哪裏被接受?在低需求住房社區。貧困就集中在像東南費格森這樣的地方。然後我們使用其他政策,比如 税收增量融資,那麼誰從中受益呢?好吧,它投資於曾經有公共住房的社區。現在公共住房消失了,社區開始紳士化,我們有高收入人羣搬入由税收增量融資促進和刺激的便利設施。
**這場反抗與那種暴力有關嗎?一個跟隨另一個嗎?**高樓倒下,然後新的牆壁豎起。警察監督的牆壁。在這些社區中,基於種族和空間壓迫的循環,愈演愈烈的挫敗感。人們在被迫遷移時,只能繼續生活,生活在集中貧困中。當暴力的警察殺戮發生時,它釋放了日益增長的挫敗感。
 2014年11月29日在密蘇里州弗格森的坎菲爾德公寓前的示威。攝影師:埃裏克·泰爾/華盛頓郵報通過蓋蒂圖片社我試圖將緩慢的政策暴力與貧困的集中聯繫起來,然後是警務的突然暴力。當你將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時,這就是動亂的配方。我們國家的對話確實集中在警察暴力上。我們正在嘗試改革警務,但我們對慢性貧民區做了什麼?我們是否投資於黑人和棕色社區?我們是否停止或減緩了城市更新?我們是否最小化了黑人遷移?我認為沒有。
2014年11月29日在密蘇里州弗格森的坎菲爾德公寓前的示威。攝影師:埃裏克·泰爾/華盛頓郵報通過蓋蒂圖片社我試圖將緩慢的政策暴力與貧困的集中聯繫起來,然後是警務的突然暴力。當你將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時,這就是動亂的配方。我們國家的對話確實集中在警察暴力上。我們正在嘗試改革警務,但我們對慢性貧民區做了什麼?我們是否投資於黑人和棕色社區?我們是否停止或減緩了城市更新?我們是否最小化了黑人遷移?我認為沒有。
**政策制定者如何打破這些循環?**利用税收增量融資來刺激服務不足地區的經濟發展,但同時與可負擔住房政策相結合。我們必須將對話從城市更新轉向公平發展。公平發展是指以最小化遷移的方式投資於低收入的黑人和棕色社區。不要拆除公共住房——保護公共住房,同時引入高收入人羣。我認為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我希望城市領導者和聯邦政策制定者考慮如何以公平的方式進行投資。
我們需要應對不平等的政策,而地方領導者無法單獨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擁有來自聯邦政府的強大社會安全網,而我們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這個安全網。當你查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的預算、可負擔住房的預算、社區經濟發展時——進入市政當局的資金並不足夠。我認為我們需要在聯邦層面進行政治海嘯式的變革,以進行更大的投資,最終將其轉移到地方層面。但我也認為地方領導者必須承擔政治風險。**有沒有你看到的市政當局或地方,即使是小規模的,做得對的地方?**有一些元素。波特蘭經歷了動亂和騷亂。他們已經推出了 可負擔住房的債券。我認為市政當局必須考慮長期;他們必須引入額外的資源。我們為建設學校、圖書館和游泳池推出債券公投,但有多少市政當局推出長期債券來提供可負擔住房?並不多。華盛頓特區是另一個經歷了大量城市更新的地方,但那裏[市長]穆里爾·鮑澤創建了一個示範項目,實際上 幫助小企業獲得房地產。當城市更新發生時,不僅僅是居民的遷移,還有商業遷移,位於城市更新地區的小型家庭企業也需要地方或聯邦政府的幫助。**話雖如此,這似乎又在發生。有沒有人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確實似乎這些發展和遷移的力量不斷髮生。[弗格森和巴爾的摩]似乎在重複導致他們最初發生騷亂的週期。如果我們不解決慢性遷移創傷,我們將再次發生騷亂。除非我們進行必要的公平發展,否則今天會有騷亂,明天會有騷亂,永遠會有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