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丨國族主義的幽靈_風聞
听桥-2小时前

圖源:NASH WEERASEKERA ILLUSTRATION FOR FOREIGN POLI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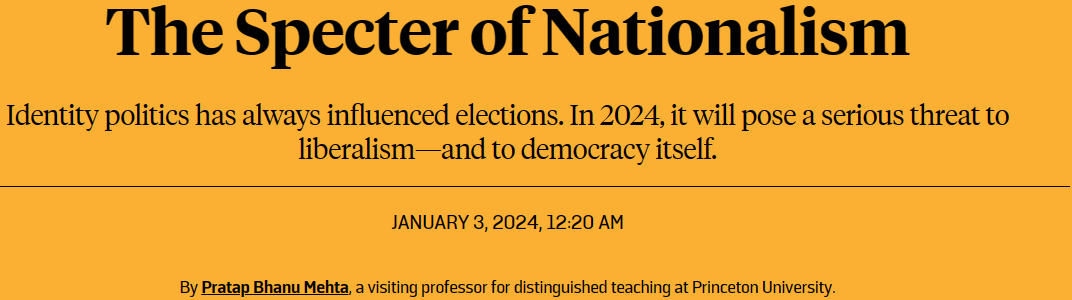
原文截圖
國族主義的幽靈
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
世界正迎來關乎民主之未來的關鍵一年。
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南非和美國(這裏只臚列將在2024年邁向投票箱的少數幾個重要國家),選舉通常會是例行公事。但這些民主國家中的許多正處在一個拐點。極化、制度敗壞和威權主義的加劇浪潮能否被逆轉?或者,民主會到達某個斷點嗎?
每個民主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有品質。在今年舉行選舉的每個國家,選民都將根據通貨膨脹、就業、人身安全和對未來的信心等熟悉事項評判在任政府。但伴隨2024年世界各國大選而來的不祥預感源自一個顯著事實: 國族主義(nationalism)與民主之間來之不易的和解正蒙受重壓。
民主的危機,一定程度上是一場國族主義危機。今天的國族主義似乎關涉四個議題: 國族如何定義成員資格; 它們如何普及某個版本的歷史記憶; 它們如何確定主權身份; 它們如何因應全球化的力量。在每一種情況下,國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往往都處在緊張狀態。民主國家傾向於駕馭而非化解這種緊張關係。
但在世界各地,國族主義正慢慢扼殺自由主義:今年,這一趨勢可能以破壞性的方式加速。2024年投票的公民人數將超過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年,他們不只將投票給某一特定領導人或政黨,還將投票給他們的公民自由的未來。
國族主義關切之一:成員資格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各社會是如何為成員資格設定範圍的。
假如一個政治共同體是主權國家,它就有權決定將誰排除在成員之外,或將誰納入成員之列。自由民主國家歷史上選擇了各種各樣的成員標準。一些國家選擇了特定的種族和文化元素,而另一些國家選擇了公民標準,僅僅要求忠於一套共同的憲法價值觀。
實踐中,包括移民的經濟優勢、與特定人羣的歷史關聯、人道主義考慮在內的一系列考量指引着自由民主國家的移民政策。絕大多數自由社會處理成員資格問題並非基於某種堅定信念,而是經由多種多樣的安排,其中一些安排較其他安排更開放。
成員資格問題在政治上愈發突出,原因可能各不相同。在美國,南部邊境的移民潮在政治上凸顯了這一事項,甚至迫使拜登政府改變其承諾的一些自由開明政策。誠然,移民在美國總是重大政治問題。但自唐納德·特朗普上台,它獲得了新的鋭勢。特朗普的所謂“穆斯林禁令”儘管最終被廢止,仍提醒人們意識到,或公開或隱蔽的新形式歧視是存在的,這些歧視將構成未來美國移民制度的基礎。
由全球衝突以及經濟和氣候困境引發的歐洲難民危機正在影響每個國家的政治。瑞典對其融合移民的模式愈發擔憂,2022年就已迎來一個右翼政府。在英國,其退歐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對移民問題的擔憂。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領導的政府將實施2019年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這部法律排除了來自某些鄰國的穆斯林難民尋求公民身份的渠道。對新德里來説,成員資格方面的關切是出於優先考慮一個龐大多數族裔的需要。同樣,在南非,移民的地位也正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成員資格問題的愈發凸顯,令人擔憂自由主義的未來。鑑於自由主義價值觀歷史上與形形色色的移民和成員資格制度相容,自由開明的成員資格制度或許並非創建自由開明社會的必要條件。有人可能會説,沒有一個控制良好的成員資格政策,更有可能攪亂自由主義所依賴的社會凝聚,進而損害自由主義。但一個值得留意的事實是,從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到荷蘭的海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 ,世界上許多支持封閉或歧視性成員資格的政治領導人,恰好也反對自由主義價值觀。這使得在反移民和反自由主義之間劃清界限變得更加困難。(歐爾班是匈牙利現任總理。海爾特·威爾德斯,生於1963年,是荷蘭極右翼國會議員。其領導的自由黨在去年11月的荷蘭國會選舉中成為眾議院第一大黨,未來的新一屆荷蘭政府將由自由黨領銜組閣,威爾德斯將成為荷蘭首相。——譯註)
國族主義關切之二:歷史記憶
國族主義的第二個維度是對歷史記憶的爭奪。
所有國族都需要某種值得利用的過去:一個可以成為某種集體身份和自尊的基礎的,將其各路民眾團結在一起的故事。歷史和記憶的區別可以被誇大,但至關重要。正如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所論,記憶尋找事實,尤其是那些符合對記憶主要對象之尊崇的事實。記憶有一種情感特質: 它被認為要感動你,並構成你的身份。它劃定了各共同體的邊界。歷史則更超然;事實總是會將身份和共同體複雜化。
歷史並非一個道德故事,也並非總是意識到其選擇性的來之不易的知識的一種非常困難的形式。
記憶是最容易作為一個道德故事而加以持守的。它不只關乎過去。記憶是關乎一個人的集體身份,要加以保持和發揚光大的一種永恆真理。
記憶在政治舞台上正越來越地被強調。在印度,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歷史記憶是鞏固印度教國族主義的重中之重。今年1月,莫迪將在阿約提亞(Ayodhya)開放一座供奉羅摩神的廟,這座廟在1992年印度教國族主義者摧毀一座清真寺的同一位置建起。它是一個重要的宗教象徵,但對執政的印度人民黨的敍事而言,一樣是重中之重;那個講述是,印度人最重要的歷史記憶不應是英國的殖民統治,而應是伊斯蘭教一千年的征服史。莫迪宣佈,8月5日,即2020年這座廟奠基的日子,與8月15日,即1947年印度從英國獨立的日子,一樣重要,都是國家的里程碑。(阿約提亞,是印度北方邦古城,被認為是印度教神祇羅摩的出生地。——譯註)
在南非,記憶問題看似沒有多麼凸顯。但納爾遜·曼德拉時代的妥協正愈發受到質疑。一些人現在認為,當時的妥協着眼於社會團結事業而犧牲了經濟正義。面對持續的不平等、經濟上的擔憂和下降的社會流動性,許多南非人正在質疑曼德拉的遺產,以及他是否已盡心盡力,賦權於這個國家的黑人。這反映出,人們對執政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黨的一些幻想破滅了。但這一再度審視,一樣可能重新釐定現代南非理解自身的記憶。

圖源:ÁLVARO BERNIS ILLUSTRATION FOR FOREIGN POLICY
在美國,圍繞如何講述國族故事的爭奪可以追溯到開國元勳那裏。但圍繞這一論題的辯論在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顯眼,從特朗普到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這樣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候選資格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作為美國人意味着什麼,以及如何“重振美國”。
例如,佛羅里達州為如何講授黑人歷史的教學設定了可疑的標準,試圖規範學生學到的有關種族和奴隸制的內容。這不只是一場關乎教育學的政治的較量; 其背後,是一場更重大規模的焦慮不安的政治辯論,關乎美國如何銘記其過去,因之會如何建設自己的未來。
國族主義關切之三:人民主權
國族主義浪潮的第三個維度是對人民主權或人民意志的爭奪。
人民主權與國族主義總是關係密切,因為前者有賴於一個具有獨特身份和彼此之間特別團結的民族概念的形成。法國大革命期間,受讓-雅克·盧梭思想的啓發,人民主權被認為有一個單一的意志。但假如人民的意志是整體的,那麼如何解釋差別呢?此外,假如人與人之間存在天生的差別,那麼如何弄清人民的意志呢?
擺脱這一難題的一個辦法是,看看誰能有效執行能幹人士的意志:在這一過程中,代表另一方背叛那一意志,而不只是對它進行其他解釋。為執行那一意志,人們必須嚴厲譴責代表其他觀點的任何人為人民之敵。在這一意義上,對被理解為單一實體的“人民”的虛誇的調用,總是存在反多元主義的風險。哪怕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都接受了一種多元主義的和代議民主的概念,仍有一絲團結的痕跡被轉移到了國族那裏。一個國族不是一個國族,或者不能獲得一種意志,除非它是統一的。
民眾以他們的國族身份為基準,集結在一個單一的意志周圍: 我們因為X 而是印度人,或因為Y而是美國人。有時,這樣的身份釐定可以相當有成效;它提醒公民,是什麼給了他們的特定共同體一個獨特的身份。但國族主義的一個特點是,它努力為自身的抗爭騰出空間。反對派失去了合法地位或遭到污名化,不是因為他們在政策問題上有不同看法,而是因為他們的看法被認為是反國族的。國族民粹主義者的言論往往針對那些被視為挑戰了他們的國族認同願景或他們將國族主義當作基準的做法的力量,這並非偶然。隨着國族認同變得更具爭議性,只有強用手段才能實現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作為一種政治風格的國族民粹主義,其興旺發達不是通過找到人民之敵,而是找到國族之敵,某些禁忌往往被用來衡量那些敵人。從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到莫迪、歐爾班和特朗普,幾乎所有現代民粹主義者區分民眾和精英都不是根據階級,而是根據真正代表國族的人。誰被評定為真正的國族主義者?對精英的文化蔑視獲得了力量,不只因為他們是精英這一事實,還因為他們可以如同過去那樣,被不再是國族一部分的精英代表。這種修辭越來越多地將差別視為煽動性的,而不僅僅是意見分歧。
例如,在印度,國家安全指控被用來對付那些質疑政府克什米爾立場的學生。學生的質疑不只被視為一種挑戰(或可能是一種被誤導的觀點) ,還被視為一種反國族行為,必須用刑事手段對付。
國族主義關切之四:全球化
國族主義危機的第四個維度與全球化有關。即使在這個超全球化時代,國族利益也從未消失。各國接受全球化或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因為它們認為那符合它們的利益。但在今年所有民主國家的選舉中,一個關鍵問題是重新考慮它們參與國際體系的條件。
全球化既造就了贏家,也造就了輸家。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或印度的過早去工業化,勢必促使人們重新考慮全球化。這一切甚至發生在新冠大流行病之前,這場流行病加劇了人們對依賴全球供應鏈的擔憂。
各國越來越確信,明確主張對經濟實施政治控制——他們有能力訂立合法的社會契約——有賴於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條件。趨勢是更懷疑全球化,並出於國家安全或經濟原因尋求更大程度的自給自足。“美國優先”和“印度優先”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中國已成為一個競爭對手的背景下。(本段刪去幾個字。——譯註)
但此時此刻似乎成了國族主義政治中一個重大得多的拐點。全球化在謀求增進國族利益的同時,也緩和了國族主義。它將全球秩序描述為一種不同於零和遊戲的東西,在其中,所有國家都可以通過更大程度的一體化而相互獲利。它並不懷疑世界各國的團結。但民主國家正越來越多地放棄這一假設,這將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更少的全球化和更多的保護主義將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更多的國族主義:這一趨勢也將損害全球貿易,尤其是對較小國家來講,這些國家需要不斷興起的邊境和商業開放浪潮。
民主能否成功穿越國族主義的困境
這裏描述的國族主義的四個特徵——成員資格、記憶、主權身份和向世界開放——自民主肇始以來就與其影形不離。
所有民主國家都面對自身嚴重的經濟挑戰: 美國的不平等和工資停滯,印度的就業危機,南非的腐敗。經濟問題和國族主義政治之間不存在必然的二元對立。莫迪等成功的國族主義政治家將自己的經濟成功視為鞏固國族主義願景的一種手段。在緊張時期,國族主義是表達冤屈的語言。它是政治家賦予人民歸屬感和參與感的手段。
國族主義是身份政治的最有力形式。它通過強制性身份的稜鏡看待已被它限定於身份的個人和他們擁有的權利。國族主義和自由主義長期以來就是相互競爭的力量。假如圍繞國族主義的利害關係降低,而不是升高了,那麼它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就更容易駕馭。但在2024年的許多選舉中,這些國家的國族認同性質會在上述四個方面受到威脅,是愈發可能的。這些選舉可能散發民主的活力。但假如最近的歷史可以作為參考,那麼國族主義在政治中的突出地位更有可能對自由主義價值觀構成威脅。
國族主義的推進形式不允許自身的意義被質疑,或試圖維護特定羣體特權,這通常會造成一個更分裂和極化的社會。印度、以色列、法國和美國都面對某種形式的這一挑戰。記憶問題和成員資格問題最不易通過簡單的政策審議就可以解決。它們利用的真相無關於可以作為共同立場基礎的事實。例如,眾所周知,我們選擇自己的歷史往往是因為我們的身份,而不是相反。
或許最重要的是,對開明自由(liberal freedoms)的攻擊往往打着國族主義的旗號而名正言順。例如,假如言論自由被發現指向了一個深受珍視的民族神話,那麼它最有可能發現自己的侷限性。每一個樂意縮減公民自由或對體制的公正不屑一顧的新興民粹主義或威權主義領導人都會披上國族主義的外衣。國族主義允許這些領導人通過使用“反國家”的謠言來鎮壓異議。從許多方面來説,今年的各國選舉大可能決定民主能否成功穿越國族主義的困境:或者,國族主義是會遭到貶低還是碾壓。
二十世紀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偉大歷史學家喬治·莫斯(George L. Mosse) 1979年在他於希伯來大學的就職演講中描述了這一挑戰: “假如我們不能成功賦予國族主義以人性的一面,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會像愛德華·吉本描述羅馬帝國衰落時那樣描述我們的文明: 鼎盛時期,温和舉動盛行,公民尊重彼此的信仰,但它卻因不寬容的狂熱和軍事專制而衰落。”
(作者是設在新德里的智庫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訪問教授。本文原題“The Specter of Nationalism”,見於美國《外交政策》雜誌2024年冬季號,2024年1月3日上線。小標題為譯者添加。譯者聽橋,對機器提供的初步譯文有校閲,並有多分段。無法確保準確理解。)

《外交政策》2024年冬季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