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遊戲”——象徵界真實、想象界真實與實在界真實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昨天 21:42
周志強 | 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大學創新團隊“文化轉型與現代中國”特聘專家、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11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日本學者東浩紀提出“遊戲現實主義”這一命題,旨在説明現實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所呈現出來的不同“理念”,這帶給我們虛擬現實時代理解現實主義的新思考路徑。事實上,**現實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技法,還是特定時期知識制度和認知範式的“文體/樣式”(style)。**近代科學的發展,誕生了“新現實”,人們使用科學性的理解方式來重新看待人與世界、人與物的關係,這就有了經典的現實主義。電影、電視等電子媒介的崛起,令藝術形象的生產呈現出新的可能性:越來越多的動漫形象被創造出來,這些形象不再是現實事物或人物形象的“反映”,而是使現實形象嫁接、變形或乾脆完全擺脱現實形象的影響,自成形象體系。這體現了東浩紀所論大塚英志提出的動漫現實主義之想象力環境的作用:動漫的製作圍繞角色生產展開,從而超越了經典現實主義的“生活邏輯”,創生出一種動漫性的行動邏輯。而虛擬現實則顛覆了“傳播”這一命題的關鍵內涵:在虛擬現實中,信息發出的時刻,就是身體感知到信息的時刻,“傳播”“媒介”都彷彿消失了一樣;虛擬現實打破了傳統文藝的存在形態,“讀者”“觀眾”這些概念將會消解,“玩家”這一概念成為新的藝術學和美學消費範疇。**經典現實主義訴之於認識論而呈現真實,動漫現實主義訴之於想象界而呈現真實,虛擬現實則是“身體的直接現實”。**經典現實主義與動漫現實主義讓讀者、觀眾待在文藝作品之外,以“心靈之眼”完成審美活動;虛擬現實卻讓人們的身體與作品中的角色共處一處,同行同聲乃至同感,人們在虛擬現實世界“生活着”,如同經歷一個大型的遊戲人生,以遊戲的經驗構建另一種現實,這就是“遊戲現實”,也就有了以“玩家”為中心的遊戲現實主義。
簡言之,虛擬現實時代,“遊戲態”的生活正在提供真實的生命經驗,遊戲現實主義反轉了現實主義的遊戲規則,它令現實主義的“分析師辭説”消解,從而敞開了玩家通向實在界之途——遊戲現實主義讓虛擬時代的新型主體“玩家”站在了實在界的位置。
“象徵界/歷史真實”與“想象界/理念真實”
**經典現實主義乃是一種象徵界的真實,換言之,它需要把人們的生活現實經驗納入歷史性的言説序列之中。**張賢亮在《綠化樹》(1984年)中講述飢餓中的章永璘接受馬纓花給他的一個白麪饅頭,他突然發現這個饅頭上竟然有一個指紋印。
我已經有四年沒有吃過白麪做的麪食了——而我統共才活了二十五年。它宛如外面飄落的雪花,一進我的嘴就融化了。它沒有經過發酵,還飽含着小麥花的芬芳,飽含着夏日的陽光,飽含着高原的令人心醉的泥土氣,飽含着收割時的汗水,飽含着一切食物的原始的香味……
忽然,我在上面發現了一個非常清晰的指紋印!
它就印在白麪饃饃的表皮上,非常非常的清晰,從它的大小,我甚至能辨認出來它是個中指的指印。從紋路來看,它是一個“羅”,而不是“箕”,一圈一圈的,裏面小,向外漸漸地擴大,如同春日湖塘上小魚喋起的波紋。波紋又漸漸盪漾開去,盪漾開去……
噗!我一顆清亮的淚水滴在手中的饃饃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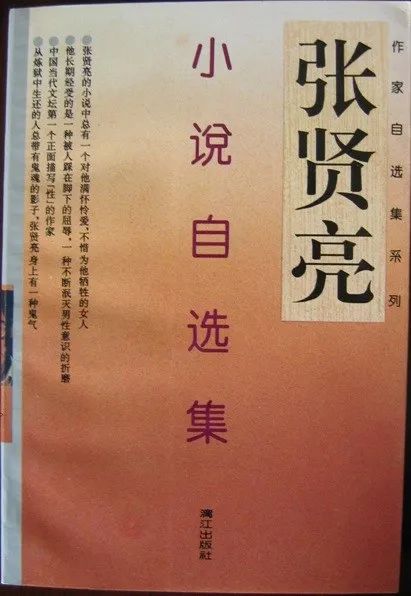
《張賢亮小説自選集》
“四年沒有吃過白麪做的麪食”的人看到白麪饅頭這一場景,在作者筆下並沒有表現出動物對於食物的生理性反應,而是爆發出詩意的感受:“宛如外面飄落的雪花”“飽含着小麥花的芬芳”“飽含着夏日的陽光”;而這個指紋印則“如同春日湖塘上小魚喋起的波紋。波紋又漸漸盪漾開去,盪漾開去……”假如我們以弗洛伊德的方式來分析這一段落,立刻就會感受到敍述者對“飢餓”這一創傷的執着迷戀,以及對“飢餓”這種痛苦本身的拒認。換句話説,張賢亮是要把“苦難”這種經歷看作“苦難的歷程”,是達到人生另一種高度必然經歷的磨練,由此,“章永璘的飢餓”就不再是普通人的飢餓,而是一種富有歷史命運感的“飢餓”。馬纓花對這位“知識分子”的命運表達出悲嘆:“她大概看見了那顆淚水。她不笑了,也不看我了,返身躺倒在炕上,摟着孩子,長嘆一聲:‘唉……遭罪哩!’”這就更加證實了主人公遭遇的“飢餓”與實際生活中眾多人的“飢餓”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含義:一個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不僅值得普通人同情,更值得大家一起去反思。“飢餓=遭罪”,這就完成了經典現實主義對於“飢餓”這一生活真實經歷的轉義:飢餓的歷史真實乃是“遭罪”;反之,只有“遭罪”的飢餓才是真正的飢餓,或者説只有值得被歷史反思和銘記的飢餓,才是真正的飢餓。
另一個有趣的案例是中篇小説《塗自強的個人悲傷》(2013年)。來自鄉村的主人公塗自強勤懇誠實,不畏艱辛,並努力拼搏;但是,塗自強考研時父親自殺,喪失命運爬升機緣;工作後微末的工薪讓他的生活捉襟見肘;老闆逃跑、老母生病,令其走投無路,終患肺癌離世。小説寫一個失敗青年的一生,把一個人所能遇見的苦難都集於一身。這種純屬偶然性的“個人悲傷”當然不屬於“歷史真實”,從而也就被很多人視為“不真實”。這部小説當然是現實主義的,但是,又是被經典現實主義所拒絕的。
顯然,**經典現實主義要營造的是符合象徵界秩序的現實,是呈現特定敍事規範和價值訴求的一種歷史真實。**對於經典現實主義來説,“符合生活”不是關鍵,“符合生活邏輯”——一種從歷史視角敍述的“現實真實”——才是關鍵。
**動漫現實主義則體現出新的現實構建方式和角色行動邏輯。**手冢治虫的《鐵臂阿童木》(1952年)和萬籟鳴的《大鬧天宮》(1964年)名噪一時,但是,仍然與《米老鼠和唐老鴨》(1924年,華特·迪士尼)、《貓和老鼠》(1961年,吉恩·戴奇版,1965年,約瑟夫·巴伯拉版)有着截然不同的現實行動邏輯。前兩者雖然是動漫作品,卻遵循經典現實主義的行動邏輯,不僅故事事件有前因後果,角色的行為也是仿照人的行為進行,並且其主題內涵也是對現實社會政治的表達或比照。而在後兩個作品中,角色遵循不同於人的世界的行動方式:唐老鴨或者湯姆貓,都會在跑出懸崖後的懸空狀態下繼續奔跑,直到發現自己已經臨空後才墜落;住在客廳裏的貓(人的現實邏輯世界)被住在角落裏的老鼠(動漫性的現實世界)到處追打;無論遭遇碾壓還是錘擊,他們也都會在“死”後突然復活,然後迅速行動去報復對方。在這裏,**動漫現實主義並不是指動漫作品中的現實主義,而是指現實主義的一種新的文體理念:人類的生活現實不再是這類作品的直接所指,而是成為其隱秘的“終極所指”;對於不同角色生動行動的玩味和富有創意的製作,成為這些作品審美消費的重要方面。**同時,動漫現實主義越來越有能力把想象界的現實呈現出來,並且把作品所創生的世界鎖定在超級真實、願望乃至慾望真實之中;而經典現實主義則塑造象徵界的現實,追求深度意義的歷史真實。如同“最好吃的漢堡在海報上”,海報上的漢堡色澤飽滿、形態完美,在現實生活的世界中,這個漢堡是無法找到的,它指向的是一種“漢堡的超級真實”:按照“漢堡”這種食物的理念來説,海報上的漢堡表達了漢堡能體現出來的人類可以想見的食物之本真狀態。這正是動漫現實主義之“真實”:只有在自由使用符號進行表達,而不是按照象徵界的法則來設置符號的時刻,人們對自身世界的願望乃至慾望,才能在各種角色和角色行動的場景中暴露出“本真狀態”。在《你的名字》(2016年,新海誠)中,不僅恐怖的“彗星撞地球”擺脱了災難政治的象徵界束縛,而且,少男少女穿越靈魂、空間、身份和身體的愛情,更是呈現出人類願望或慾望層面上的“愛情本真之真實”:還有比這種動漫現實主義作品中的愛情更像愛情的東西嗎?在生活現實中,“愛情”是作為一種富有召喚魅力的事物被表達的,它也總是遭遇各種現實困境,甚至愛人的體臭都能成為戳破愛情神話的暗器;而在動漫現實主義中,這些生活現實的邏輯都被放置到了一邊,愛情的“超級真實”面孔,即所謂“純粹的愛情”活靈活現且光耀奪目。在《你的名字》中,靈魂的呼喚不僅變得簡明扼要,不必計較是否合乎“生活邏輯”,而且,男主人公為了一個彷彿有神秘關聯的女生瘋狂地在隕石墜落前去改變時空,這種愛情激情恰當地詮釋了來自想象界的幻想卻可能是世界之純粹真理的道理——難怪那些充滿愛情幻想的女生不願意帶男朋友一起看這部電影,因為現實生活中的男朋友,如何配得上這種“真正愛情”?

電影《你的名字》
顯然,經典現實主義致力於歷史真實的呈現,動漫現實主義則無意識地暴露了理念真實(也許這種真實包含着撕裂和悖論),那麼,在數字技術時代,遊戲現實主義的真實性何在呢?
遊戲現實主義的事件真實
“遊戲現實主義”這一概念並非單純地指向遊戲中的現實主義,或遊戲如何抵達現實等命題。東浩紀原本想追問的是一個相對簡明的問題:像遊戲一樣設置小説,從而令小説呈現出新的現實主義特色。“東浩紀的原意‘遊戲經驗的小説化’是以電子遊戲為主體的,是將遊戲敍事看作一種新形式、新時代的‘現實主義’,然後探索這種新式的現實主義如何被文學藝術理論所闡釋。”所以,遊戲現實主義這個概念帶出了這樣一個命題:遊戲敍事也是一種關於現實的敍事。
**我們至少可以看到遊戲敍事的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將“遊戲”作為一種敍事邏輯來構建小説。**從升級打怪、修仙修真到重生逆襲、穿越玄幻,網絡文學的敍事機制採用了電子遊戲的模塊性組合方式,而“常被認為是網絡文學源頭的作品《風姿物語》(羅森,1997)最初曾是日本電子遊戲《鬼畜王蘭斯》(1996)的同人小説;網絡文學早期流行的西方奇幻設定受到桌面角色扮演遊戲《龍與地下城》(1974)的重要影響;2004年左右形成熱潮的‘網遊小説’以真實存在或虛構的網絡遊戲世界作為故事展開的空間,為此後拆除遊戲系統的玄幻、修仙升級文的誕生鋪平了道路;網絡文學中千姿百態的幻想世界的出現,可能與電子遊戲所帶來的關於‘平行時空’的感受密切相關;網絡文學中‘萌點’突出的‘人設化’角色也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日系角色扮演遊戲與文字冒險遊戲的影響……”在這樣的敍事中,依照生活邏輯建立起來的故事創造被依照遊戲邏輯建立起來的故事設置替代,情節流程讓位於模塊化組合。所謂“一言不合,殺你全家”的網文俗套不過是一種比較實用的模塊組合方式,隱藏在這種遊戲性的組合方式背後的是人們的痛苦遭遇。這種遭遇被作者從其現實語境中剝離出來,也就是從人們對自身的痛苦遭遇不得不理解和接受的現實態度中剝離出來,讓它變成遊戲性敍事中不必理解和接受的事件,讓原本看似合情合理的生活現實,變成痛苦境遇的事件性寓言。所以,**諸多遊戲性敍事中所製造的“爽”,歸根到底乃是現實生活中的“不爽”;只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些不爽被附着了前因後果後變成了似乎有存在理由的東西。**遊戲性的敍事,恢復了苦痛遭遇的事件特性:任何苦痛,其實都是現實秩序的意外斷裂,是現有的現實理性無法進行合理化敍事的證明。所以,那些贅婿文、重生文或逆襲文中的“一言不合,殺你全家”橋段,既顯示了主人公對欺凌或侮辱自己的人所採取的報復方式之“爽”,也“暴露”了現實生活中欺凌或侮辱的內在邏輯:任何時刻,之所以普通人遭遇欺辱,不過是欺辱他們的那些人掌握了欺辱他人的力量或位置而已。任何為欺辱他人的行為所做的合法性辯護都在這裏失去了意義——“被欺辱的苦痛”乃是不可化約或解釋的事件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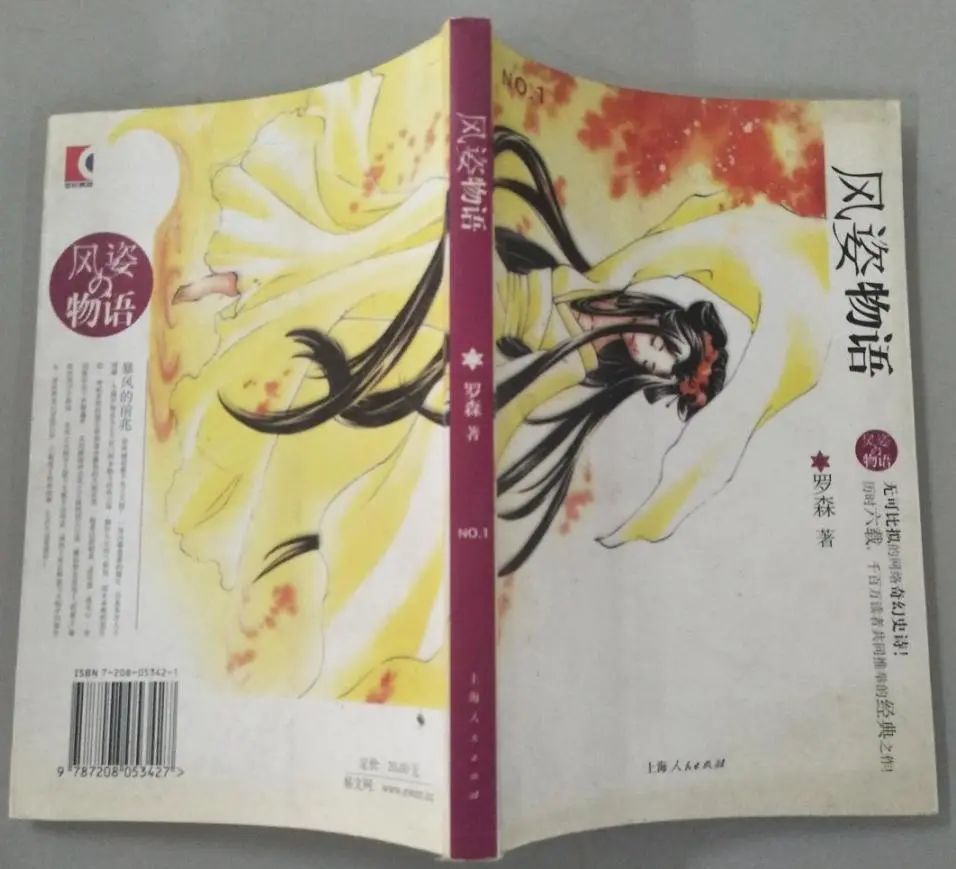
羅森著《風姿物語》,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遊戲敍事的第二種形式就是虛擬現實本身的敍事,即遊戲本身乃是敍事。****這集中體現在虛擬現實時代電子遊戲敍事行為中。**電子遊戲藉助特定的故事框架展開,這類似經典現實主義敍事,有時候也採用動漫現實主義的敍事,它構成了電子遊戲敍事的內容層面;而“電子遊戲敍事”還有另外一個敍事層面,即玩家通過“自己”在遊戲中的行動“生成”情節的敍事,這是電子遊戲敍事的行動層面。一方面,電子遊戲採用故事建構其可玩性,另一方面,玩家藉助這種可玩性,不斷地使用電子遊戲敍事內容生成屬於自己的故事流程,即將各種各樣充滿邏輯的故事轉換為自己玩遊戲的不可知性,也就是將自身完全事件化。所以,典型的遊戲現實主義讓玩家成為真正的主人公,並“釋放”玩家性格、性情或能力,構建截然不同的另類人生經驗。在這裏,電子遊戲讓“遭遇”成為真實,而不是讓遭遇的故事成為真實。“遭遇”不是玩家在電子遊戲中遭遇的任務或故事,而是玩家與電子遊戲本身的“遭遇”:玩即事件性的遭遇。電子遊戲,尤其是虛擬現實時代的電子遊戲,允許玩家完全投入到角色中,並且彷彿角色即自我。於是,**遊戲現實主義將自我(主體)定位成玩家的時候,又是玩家讓自我擺脱主體的社會性安排,不再追求同一性角色自我的時刻,是玩家自由地享受充滿矛盾的自我角色的時刻。**在一款名為《極樂迪斯科》(Disco Elysium,2019年,ZA/UM)的遊戲中,玩家所操縱的遊戲主角會在遊戲進程裏接觸到各種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這些觀念構成了遊戲的“思維”系統。其中,玩家給主角“裝備”不同思維就會獲得不同能力或數值提升,如玩家給主角“裝備”上“無從解釋的女權主義議程”思維,主角在對抗男性角色時“爭強好勝”技能值就會提升兩點,主角從數值層面被玩家塑造成一個“女性主義者”。但是隨着遊戲目標的不斷變化,要“裝備”的“思維”也需要隨之改變:想要打倒身高體壯的男人,就要加強“鋼筋鐵骨”,而若想説服一個聰明絕頂的商人,就得擅長“故弄玄虛”。簡言之,思維的“裝備化”使得主角不再是秉持某一觀念的某個主義者,而是在各種思想裏漫步的“遊玩者”。在《極樂迪斯科》的故事裏,任何“主義”都沒能成為解決這個故事中問題的良藥,每個“主義”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卻又從未發揮理想的作用。遊戲系統讓主角變成一個搖擺不定的“思想小偷”,持續接受着不同的思維觀念,卻從未信仰其中的任何一個;遊戲故事將玩家拋入沒有任何解決方案的實在界之深淵,把玩家原本完整統一的文化政治身份打成碎片。

遊戲《極樂迪斯科》
在《極樂迪斯科》的豆瓣網頁中,我們看到了其中這樣三條評論。
剛開始玩時,我以為我打開的是《烏合之眾》《娛樂至死》《1984》《百年孤獨》《黃金時代》。玩半小時後,我發現我打開的是《共產黨宣言》《純粹理性批判》《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説》《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追憶似水年華》。(豆友63235291,2020年3月20日)
這不僅僅只是遊戲而已,我認可自由主義的繁華與壓迫,“康米主義”的激昂與瘋狂,民族主義的團結與歧視,現代主義的張狂與迷茫,理想主義的偉大與虛幻,人道主義的仁慈與失意。我是個道德家,我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政治中間派,精通馬佐夫社會經濟學的康米之星,擁有遙視能力的天王巨星,法律的化身,新自由主義街區天字一號條客,昭示末日來臨的第八封印者,傳統主義瘋狗,無可辯駁的女權主義者,形容枯槁的民族主義者……還是金曷城警督見識過的最好的警探,但我還是沒有留住她,我無知又可悲,我真的被打擊到了,我無法劃清界限,我是混沌的,相互制衡的,萬變的,彩色幽靈。(Paze,2022年9月22日)
我的腦子,我的意識,我的鏡子,一切我碰過的東西都詩人哲學家似的,講話都文采飛揚一套一套的,晚上睡個覺腦內簡直在開寫作研討會。我本人一張口卻滿嘴屁話。貫穿全篇:我是誰?我要去哪兒?我信仰什麼?我有怎樣的價值觀……剛開始的時候猜測作者的政治立場、作者想要我有怎樣的政治立場,不存在的,幾乎是按着政治光譜把每種觀點都踩一腳,大廈將傾之時你堅持什麼理論都沒用,總會在現實中碰壁。你只能站在人這邊。通關後回想,幾乎所有讓我感動的人和事都是無關政治的,就一個個鮮活的人或生物或者一陣海風,在一個每況愈下的機器中帶來取暖的相濡以沫的善良。就是不變壞,我抽煙喝酒依然是個好偵探。“你是我遇到過的,最美麗的生物。”(“溏心衝浪板”,2020年3月19日)
**顯然,完整統一的自我不過是對自我的一種設定(主體化),遊戲現實主義暴露了“自我角色”的完整統一的幻想性屬性:自我角色的統一不過是掩蓋生命歷程之無序性的事件真相。**這裏,重要的不是電子遊戲玩了什麼(經典現實主義和動漫現實主義的邏輯),而是“玩”這個行動的非邏輯性:玩就是玩本身,它不謀求確定性,逃離對它的意義規定。**遊戲現實主義真正讓敍事文本的接受者——一個在傳統敍事中被抽象化了的角色,恢復了其事件性的真實面孔。**在遊戲現實主義之外,“我”屬於關於“人”的敍事的各種故事,而在遊戲現實主義之中,“玩家”重返被各類事件衝散的“我”之症候:“我”不過是用來證明“我之同一性假象”的用語。
簡言之,經典現實主義通過一種總是知道一切的方式創造出富有掌控力的“主體信心”,動漫現實主義則凸顯這種信心之放大後的“純粹自我”,而遊戲現實主義卻讓“玩家”恢復了人之為人的根本性內涵:“我”的遭遇才是每個人生存的真實,而不是對這種遭遇的過剩性解釋(象徵界真實)或純粹理念化(想象界真實)。
現實主義的“遊戲”
**顯然,從象徵界真實、想象界真實到實在界真實,我們可以得到關於現實主義文體理念的三個層面:**其一,現實主義是對生活的反映,現實主義致力於以寫實的方式來表達現實生活的內在邏輯和歷史真諦;其二,現實主義是對現實的反應,動漫現實主義以商品戀物癖式的迷幻表達世界的本真性;其三,現實主義是通達真實的遊戲,遊戲現實主義向人的生活的根本不可能性敞開,呈現世界之多異性,近似於“multitudes of multitudes”。
**作為“反映”,現實主義確立了科學主義的人文精神:**冷靜客觀的描寫,乃是揭示人類世界之真實性的有效手段;只有採用一種冷靜客觀的尊重生活的態度,真正的生活狀況才能被認識和理解。所以,魯迅、茅盾堅持寫實主義的態度,因為只有這樣,現實生活的殘破不全和衰敗頹廢才能被反映出來,也才能激活人們的拯救意識。
作為“反應”,現實主義又是對現實社會之生存狀況的干預、介入,將特定的理念或精神作為敍事的意義框架,對現實的狀況進行重組或改寫。“約翰·康斯太布爾(John Constable)的著名油畫《乾草車》(The Hay-Wain)(1820—1821)提供了對鄉村的不可否定的積極觀點……農村是從和諧、美麗、安定、傳統、和平、純潔和美德的角度得到表徵的。為什麼這些意義被附加在這張畫及其他相似的油畫中的鄉村上呢?約翰·巴洛(John Barrel)(1980)給自己設置的任務就是揭示出在英國18和19世紀風景畫(為富人而生產的著作)中起作用的意識形態,他是在即將到來的資本主義農業以及它所包含的階級鬥爭的背景中闡釋這些意識形態的……”在資本主義的殘酷掠奪與鄉村優美的風景化之間,《乾草車》構造了現實主義的“反應性”關係。

油畫《乾草車》
**作為“遊戲”,現實主義卻呈現了“真正面孔”:現實主義歸根到底乃是追求關於人類生存的真實境遇的方式。**遊戲現實主義將人放置在了“實在界位置”上,“玩家”通過“戲弄人生”,反而直麪人生之實在界真實:我們在一次次的“遊戲”中,追逐世界的變動不居和偶然匯聚,令特定的秩序不斷被打斷,完成一次次的“玩”。“玩”恰是人類生存的“實在界真實”,它把人類的社會生活從形而上的層面解剖開來,也就把各種各樣的“文化賦魅”行動,變成了一種“遊戲行為”。
顯然,遊戲現實主義體現了現實主義的新遊戲方式:現實主義的文體理念中不僅僅有揭露和批判的拯救性政治,也有回到人自身而沉浸享樂的快感政治。現實主義的三種面孔,體現了理解“真實”的三種有趣方式:科學主義為主導的現實主義注重修辭的文體政治學方式;人文主義為主導的現實主義追求想象力大爆發的文體符號學方式;遊戲性為主導的現實主義擁抱實在界的文體遊戲學方式。
**遊戲現實主義乃是以遊戲的方式觀察和理解現實,這樣的設定體現了虛擬現實世界成為人們現實世界之行為法則的可能性。**齊澤克曾經提到2016年的擴增現實遊戲《寶可夢GO》(任天堂、寶可夢公司、Niantic Labs)。
玩家用手機上的全球衞星定位設備及相機去捕捉、打鬥以及訓練虛擬的寶可夢(Pokemon),這些精靈在屏幕上出現的方式彷彿它們和玩家是在同一個真實世界的地點出現的一樣:當玩家在真實世界內移動,代表他們的遊戲角色同時在遊戲地圖中移動……我們通過電子屏幕這一幻想框架來觀看現實以及和現實交接、互動,而這個中介框架利用虛擬元素增強了現實。這些虛擬元素支撐着我們參加遊戲的慾望、推動我們在現實中尋找它們,缺少了這種幻想框架我們將對現實完全不感興趣。
**齊澤克想要説明的是遊戲方式與當代意識形態建構方式的一致性。**在齊澤克的論述中,人們使用《寶可夢Go》這款遊戲,乃是按照虛設的框架來支配自己現實的行為,所以,“雖然《寶可夢Go》將自身呈現為某種全新的、建基於最新科技的東西,它實際上依靠的是一種舊的意識形態機制。意識形態就是擴增幻景的實踐”。齊澤克在這裏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他看到了虛擬現實和意識形態共同的虛設性,卻忽略了虛擬現實與意識形態之間政治功能的截然不同。意識形態是一種“説服”人們同意現實的方式,而虛擬現實卻不僅僅是對現實的“擴增”,還是對現實的“重設”:在現實中不存在意義的地方去創生意義,這正是人們尋找“寶可夢”的邏輯。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齊澤克才是正確的,“寶可夢迫使我們面對幻象的基本結構,將現實轉化成一個意義世界的幻象功能”。

擴增現實遊戲《寶可夢GO》
遊戲現實主義的秘密恰在於此:它將現實生活的邏輯“轉義”為“遊戲性”,令意識形態的説服性失去了現實硬核的支撐——對於電子遊戲的審查制度,正無意中説明了這一點。也許正因如此,經典現實主義在經由動漫現實主義而與遊戲現實主義遭遇之後,才令其表意悖論浮出水面。一方面,現實主義秉持精神分析師一樣的“辭説”,充滿信心地將現實症候轉換成健全理性。另一方面,遊戲現實主義暴露出現實主義的德勒茲式悖論:症候可能恰好出在精神分析師身上,因為他瘋狂地相信存在一種健全的理性。